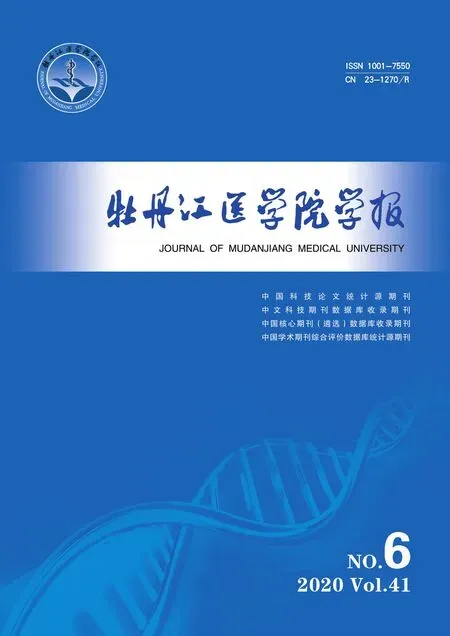COVID-19疫情期间医学生应对倾向在人格与负性情绪间的作用
2020-12-24颜桑桑郑建盛林志萍王守安郑金林
颜桑桑,郑建盛,林志萍,谢 群,王守安,郑金林
(莆田学院,福建 莆田 351100)
2019年12月以来,湖北省武汉市陆续发现了多例不明原因肺炎,后被证实为2019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rona Virus Disease 2019,COVID-19)[1]。2020年3月10日,COVID-19在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蔓延,累计确诊病例数超过10万人,世界卫生组织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 于2020年3月11日宣布COVID-19疫情呈现全球大流行。此次疫情不仅导致人们生命与财产的重大损失,更是对公众心理健康造成巨大的冲击和损害[2]。
大学生作为心理尚未完全成熟的社会储备人才,这一特殊群体在疫情发生期间不仅学习和社交受限,而且接触网络疫情信息过载,可能出现不同程度的压力应激反应,产生恐慌、焦虑和抑郁等不良情绪[3]。其中,医学专业大学生对与自己专业密切相关的疫情进展关注度更高,可能更容易出现心理问题。D 型人格,又叫“忧伤型人格”,包括消极情感和社会抑制两种亚型,有学者认为,D型人格者对外界环境或人际交往缺少安全感,常抑制情感的表达,处于长期的慢性应激状态,更容易出现恐惧焦虑、过度担忧等负性情绪[4]。
除了先天的人格特质,后天的面对负性事件的应对方式也对个人情绪起着重要的作用,但这两者之间对情绪影响的贡献程度、交互作用及因果关系尚未得到较多报道。在医学研究中,变量间的影响关系往往不是直接因果链关系,而是通过一个或一个以上变量的间接影响产生的,此种间接影响称为中介效应,中介效应分析是当前揭示心理现象间复杂关系的热点方法。
本研究一方面调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下医学生焦虑、抑郁的负性情绪状况,另一方面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应对方式对负性情绪起到的中介效应,并借此了解医学生负性情绪的影响因素及作用机制,为给予及时有效的心理筛查和干预提供科学依据,对进一步奠定医学生未来从业心理素质具有重要意义。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采用整群抽样的方法,选取福建省莆田学院2016级~2019级临床医学和护理学专业的在读本科大学生作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2016级~2019级临床医学和护理学专业学生;学历层次为四年制或五年制本科。排除标准:休学或退学;不愿意合作者。共发放问卷642份,回收有效问卷634份,有效率为98.8%。
1.2 研究工具
1.2.1 D型人格量表(Type D Personality Scale,DS-14) 由 14个条目组成,包括消极情感(NA)和社会抑制(SI)两个维度,每个维度表包括7个条目,第2、4、5、7、9、12、13为消极情感,第1、3、6、8、10、11、14为社会抑制,各条目均采用采用0(完全不符合)~4(完全符合)五级计分法,其中条目1、3为反向计分,两个维度得分范围均为0~28 分,总分越高表明D型人格倾向越大,当NA≥10分且 SI≥10分时判断为具有 D 型人格[5]。
1.2.2 医院焦虑抑郁量表(Hospital Anxiety and Depression Scale,HADS) 是国内外公认的测试负性情绪的权威自测量表之一,同时适用于患者和一般人群[6]。该量表包含焦虑和抑郁两个亚量表,用于测试焦虑和抑郁的问题分别为7个,规律交叉混合排列,每题按0~3计分,亚量表的得分超过7分时说明存在焦虑或抑郁状态。总分越高说明负性情绪水平越高[7]。
1.2.3 简易应对方式量表(Simplified Coping Style Questionnaire,SCSQ) 该量表20个条目组成,分为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两个维度的分量表,采用多级评分,即0~3的评分标准。积极应对维度所包含的条目由1~12题组成,得分为该维度所有条目总分和除以条目数;消极应对维度由13~20题组成,得分为该维度条目所包含的条目总分除以条目数,应对倾向=积极应对分-消极应对分,得分越高,说明应对方式越积极[8]。
1.3 资料收集与整理方法从2020年1月23日至2020年2月23日,在知情同意的前提下,采用统一编制的问卷调查表对纳入的研究对象以班级为单位进行逐一实名网络调查。调查结束后,对调查问卷逐一复核、复查,做好问卷回收率、有效率统计工作,如有缺漏应予以电话访谈的形式进行补填。
1.4 统计分析采用SPSS 22.0软件对D型人格、负性情绪、应对倾向进行统计描述和Spearson相关性分析,通过依次构建线性回归方程进行初步中介效应分析,采用Amos 21.0软件进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和中介效应检验。P<0.05表示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一般情况本研究调查的634名大学生的年龄范围为18~22周岁,平均年龄(19.31±0.92)周岁。其中,临床医学专业282人,占44.5%,护理学专业352人,占55.5%。大一占21.1%、大二占33.6%、大三占38.5%、大四占6.8%。目前担任学生干部的占32.8%、非学生干部的占67.2%。男89人,占14.0%;女545人,占86.0%。生源地为城市或县城的占24.6%,生源地为乡镇或农村的占75.4%。独生子女的占15.9%,非独生子女的占84.1%。处于恋爱状态的占24.9%,非恋爱状态的占75.1%。
2.2 负性情绪情况142人呈现焦虑状态,占22.4%,呈现抑郁状态的有146人,占23%,不同性别研究对象的焦虑抑郁情况见表1。

表1 研究对象的焦虑、抑郁状态情况
2.3 D型人格、应对倾向与负性情绪间的相关性分析对D型人格倾向、应对倾向、负性情绪得分分别进行两两Spearman秩相关性分析,应对倾向与D型人格、应对倾向与负性情绪之间均呈现负相关,相关系数rs分别为-0.476(P<0.01)和-0.450(P<0.01),D型人格与负性情绪之间呈现正相关,相关系数rs为0.600(P<0.01),见表2。

表2 D型人格倾向、应对倾向、负性情绪得分之间的相关性(n=634)
2.4 应对倾向在D型人格与负性情绪间的中介效应分析为了检验应对倾向在D型人格与负性情绪之间的作用,采用依次检验法,构建简单的中介模型(X=D型人格,M=应对倾向,Y=负性情绪),依次构建如下三个线性回归方程:方程1:Y=cX+ε1、方程2:M=aX+ε2、方程3:Y=c’X+bM+ε3,当三者都有统计学意义,说明M在X和Y之间产生了部分作用,当c’无统计学意义时说明是完全中介效应。本研究结果显示,D型人格、应对倾向与负性情绪均存在具统计学意义的线性回归关系,应对倾向在D型人格与负性情绪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对总效应的贡献率为effcetm=a×b/c=-0.484×-0.235/0.637=0.179,即17.9%。见表3。

表3 应对方式在D型人格与负性情绪间的中介效应分析
2.5 中介效应检验建立D型人格、应对倾向和负性情绪的结构方程模型,结果显示,D型人格对负性情绪既有直接效应也有通过应对倾向介导的间接效应,各变量之间的路径系数见图1。

图1 各研究变量之间关系的结构方程模型图
研究表明,模型各项适配度指标良好,其中,卡方自由度比值(χ2/df)为0.800,RMSEA<0.001,GFI、AGFI、NFI、RFI、IFI、TLI、CFI等均大于0.90,表示模型拟合良好,见表4。

表4 结构方程模型适配度指标
进一步采用Bias Corrected Bootstrap法对中介效应进行显著性检验。利用重复随机抽样的方法在原始数据中抽取2000个Bootstrap样本,生成1个近似抽样分布,用第2.5百分位数和第97.5百分位数估计95%的中介效应置信区间[9]。结果显示,该中介模型的总效应、直接效应、间接效应的95%CI均不包括0,P值均小于0.05,提示应对倾向在D型人格与负性情绪间的中介效应有统计学意义,见表5。

表5 应对倾向在D型人格与负性情绪间的中介效应检验
3 讨论
当代大学生作为未来社会建设主力军的一个重要社会群体,其身心发展正处于走向成熟的特殊过渡阶段,常面临着来自学习技能、人际交往、情感问题和生活就业等多重压力,极易出现不同程度的心理问题[10]。有研究显示,近年来大学生焦虑、抑郁的检出率正逐年上升,焦虑和抑郁是目前高校大学生的主要心理问题[11-12]。
多数学者认为该现象在医学生中更为显著,是自杀的高危因素之一[13-14],究其原因,可能与医学专业学生学业时间相对长、课业任务重、就业面相对窄等有关[15]。临床医学和护理学专业的特殊性,决定其将来工作岗位具有与患者面对面密切接触的特点,其心理素质不仅直接关系到他们自身的学习、生活及工作质量,更可能影响今后所服务患者的心理健康,因此,关注医护学生的负性情绪状况显得尤为重要。
在此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高发流行期间,本研究调查结果显示,634名医学生中有22.4%呈现焦虑状态,有23%呈现抑郁状态,与昌敬惠[16]等人于2019年1月31日至2020年2月3日期间对3881名广东大学生进行调查的结果相似,其研究对象的焦虑和抑郁情绪的检出率分别为26.60%与21.16%,根据冯凤莲[17]等报道,2018年医学院校本科大学生焦虑、抑郁情绪检出率分别为12.94%和19.53%,低于本次研究调查结果,可能很大程度上与COVID-19疫情流行导致的应激反应有关,尚缺乏进一步的对比数据。
但同样的应激事件,人格健全的人能够很好地面对,不易造成心理损害,社会心理学方面的观点认为,人格特质直接决定着个体适应能力,从而影响身心健康[18]。本研究Spearman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D型人格与负性情绪之间呈现正相关,相关系数rs为0.600(P<0.01),线性回归模型表明,D型人格是负性情绪的危险预测因素(t=20.768,P<0.001)。与国内外的研究结果相类似[19-20]。
本研究结果显示,无论是焦虑还是抑郁,其检出率均是女性均低于男性。其内在生理学机制可能是女性的孕激素比男性为高,孕激素有拟γ-氨基丁酸 (Gamma aminobutyric acid GABA) 能, GABA 抑制促肾上腺皮质激素释放激素CRH(corticotropin releasing hormone)和促肾上腺皮质激素 (adrenocorticotropic hormone,ACTH) 的合成和分泌,从而降低与负性情绪密切相关的血清皮质醇水平[21]。另一方面的重要原因可能是女生在遇到应激事件时会更擅长内省,心理韧性较好,在应对方式上表现得更为积极以促进自我成长,而男生的心理刚性受挫后更倾向于采取压抑、逃避等消极应对方式。
因此,除了人格特质,应对方式与心理健康也密切相关[22]。本研究发现,积极应对倾向与抑郁、焦虑情绪得分呈负相关,与吕婧[23]等的研究结果相一致,即积极应对在应激事件及负性情绪的关系中发挥调节作用,属于心理健康的保护性因子。当面临挫折事件和挫折情境时,大学生如果能采取解决问题和求助等积极应对方式来应对,可以顺利处理好当前困难,则较少出现焦虑、抑郁等负性情绪[24],而那些处于负性情绪状态的人往往是因为采用消极的应对方式[25]。
本文对D型人格倾向、应对倾向、负性情绪得分分别进行两两Spearman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三者之间两两均呈现有统计学意义的相关关系(P<0.01)。逐步检验的线性回归方程结果表明,D型人格、应对倾向与负性情绪均存在具统计学意义的线性回归关系。以D型人格为自变量,以应对倾向为因变量的线性回归方程的标准化回归系数为-0.484,以D型人格为自变量,以负性情绪为因变量的线性回归方程的标准化回归系数为0.637,而加入应对倾向为自变量后,D型人格的标准化回归系数降低为0.523,提示应对倾向在D型人格与负性情绪间可能起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对总效应的贡献率为17.9%。这与马慧[26]等对河北省某高校960名本科大学生的调查结果相似。
本研究通过构建结构方程模型进一步进行中介效应检验[27],结果表明应对倾向在D型人格与负性情绪间的中介效应有统计学意义,即D型人格对负性情绪既有直接效应,又有通过应对倾向这一中介变量介导的间接效应。因为D 型人格者往往对环境和自身状态的改变采取相对悲观的态度,更倾向于采取消极的应对方式,进一步加剧负性情绪问题。相反地,积极的应对方式具有重要的缓冲作用,有利于维护个体良好的情绪体验,在D型人格与负性情绪中起到重要调节效应。
综述所述,COVID-19疫情下医学生有不同程度的负性情绪,应重视对D型人格医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期间可以通过搭建网上心理咨询平台、开通心理援助热线、开展训练等方式使大学生能够得到及时有效的心理疏导[28]。人格特征虽是很难改变的,但可以针对应对方式进行指导与矫正,鼓励其在面对困难、挫折情境时多采取积极应对方式,如解压放松、改变想法、转移注意和倾述求助等,避免消极应对方式,培养其处理问题的能力,增强心理自我调适,从而减少负性情绪,维护和提高医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
本研究尚有不足之处,其一,考虑到可行性,调查范围及样本量不够大,使研究的外推性受限,其二,本研究为横断面调查,不能精确对比疫情前后医学生的负性情绪变化,在后续的研究中,将采用配对设计的重复调查方法分析COVID-19疫情对医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进一步增大样本量并扩展研究因素,为提高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提供科学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