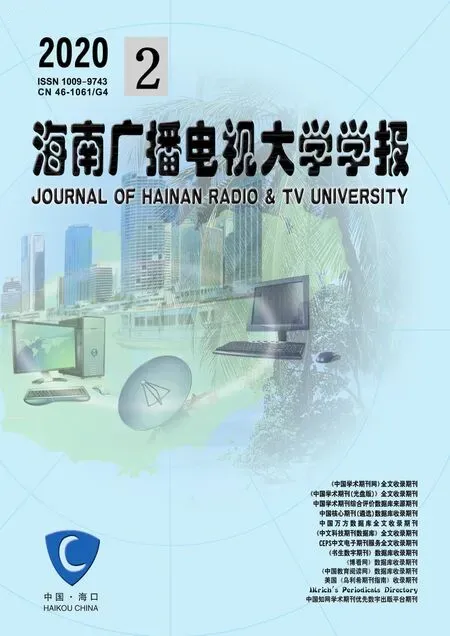奥登诗歌的滑稽与崇高
2020-12-20史笑添
史笑添
(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00)
一、滑稽与崇高的融汇问题
通常地,在滑稽与崇高、喜剧与悲剧的两两组合中,学者倾向于令喜剧归附与滑稽,而令悲剧归附于崇高。但在实际情况中,悲剧未尝没有滑稽成分,譬如《罗密欧与朱丽叶》开头凯普莱特家仆的淫秽对话、《哈姆莱特》中掘墓人的歌谣;而喜剧也未尝不产生崇高,譬如《鸟》中构思宏大的“云中鹁鸪国”、《屈身求爱》中郝嘉斯先生对爱情的论说,可见事实上它们彼此属于一种通融关系。而这种通融的因由,首先是基于戏剧所反映的生活本就掺杂了崇高与滑稽。当剧作愈来愈贴近日常生活,这种折衷掺杂的要求就愈明显。正如博马舍《论严肃戏剧》所说,往常悲剧的凶杀犯罪,已经脱离了日常生活,而只有讽刺的喜剧,却又显得轻浮。基于这一问题,博马舍和狄德罗等人推广了悲喜剧,将悲剧喜剧融进一炉。而上述的文论史进程,又随即带出两个追问:其一,既然悲剧和喜剧两种体裁可以融汇,那么滑稽与崇高这两种范畴,是否也有融汇的可能?其二,进一步地,既然“悲剧”和“喜剧”已经变成了“悲剧性”和“喜剧性”,从而流布到其他体裁,譬如诗歌、小说之中,那么这些体裁里能否也出现滑稽与崇高的融合呢?
W·H·奥登(Wystan Hugh Auden,1907—1973)的诗歌或许就是一个融合了滑稽与崇高的好例。奥登被普遍认为是艾略特之后最伟大的英语诗人,而历来论者对他诗歌兼有滑稽崇高的特性都颇为留意。如特里·伊格尔顿评价奥登的诗歌中:“琐碎和重要,罪恶与纯真,随意地比肩而存(1)(英)特里·伊格尔顿著:《如何读诗》,陈太庆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同时,奥登对三流小说的狂热喜好、他自己编选的《19世纪英国次要诗人选集》,也都可以说明这一点。奥登的夫子自道也是:“一种审美的宗教对轻佻之物和庄重之物并无明确区分(2)(英)W·H·奥登著:《染匠之手》,胡桑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586页。。”这些资料都向读者显示,奥登其人其诗,可以说是一个滑稽与崇高的对立统一体。虽然将滑稽与崇高融为一体的作品为数不少,甚至莎士比亚的许多戏剧都是如此,但奥登是一个过于显著的范例。首先,滑稽和崇高的并置对他而言不仅是一种技巧,更是他许多作品的主题。即奥登的作品,很大程度上依靠了这一点。正如他自己说的:“一名诗人格外渴望由个人喜好所引领…比如关于滑稽可笑的差诗的问题(3)(英)W·H·奥登著:《染匠之手》,胡桑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63页。。”其次,奥登明确意识到了自己的这一特色,故而在多篇文论或散文中,都留下了对此的论述,故此更有权威性,也避免了郢书燕说的将其他人的理论强行附会到奥登作品中的可能。
通过分析其诗歌对这两种范畴的融汇方式,并抽象成一种普遍性原则,本文试图解答以上两个追问。而首要的行动,就是通过文本细读方式剖析一些奥登诗歌,来观察诗歌各个部分是如何就这一问题起作用的。
二、奥登诗歌的对立统一
笔者试图先用文本细读法分析奥登《战时组诗》的第一首(4)查良铮编译:《英国现代诗选》,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107:“从岁月的推移中洒落下种种才赋/芸芸众生立刻各分一份奔进生活/蜜蜂拿到了那构成蜂窠的政治/鱼作为鱼而游泳,桃作为桃而结果。/他们一出手去尝试就要成功了/诞生一刻是他们仅有的大学时期/他们满足于自己早熟的知识/他们安守本分,永远正确无疑/直到最后来了一个稚气的家伙/岁月能在他身上形成任何特色/使他轻易地变为豹子或白鸽/一丝轻风都能使他动摇和更改/他追寻真理,可是不断地弄错/他羡慕少数的朋友,并择其所爱。”。在这里,首先吸引人注意力的是诗歌叙述者所处的角度。杨周翰曾评论奥登“取景的角度当是居高临下的”,诚然,正如《奥登诗选》在这首诗下的脚注所言:“奥登转化借用了《圣经·新约·启示录》中神谕般的口吻(5)(英)W·H·奥登著:《奥登诗选:1927-1947》,马鸣谦,蔡海燕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年版,第253页。。”一种俯视的叙述角度,暗示了叙述者的可靠与自信,甚至显示出叙述者不凡的身份。亦即从语调和语义上而言,本诗已然具有一种崇高性。但“种种才赋”的体现,则是“构成蜂窠的政治”,这里将代表极大权力的政治,解释为筑造蜂窠的原料。依康德的观点,崇高是无形式的绝对的大,而在此处政治的威力随即被消解为蜂窠材料。中国古代有“南柯一梦”的典故,在此处依然适用,昆虫的政治被视作戏仿崇高的滑稽。所以可以发现,崇高与滑稽在此处形成了对立,并由此赋予这句诗张力。第二段中,上述的蜜蜂、鱼、桃,并未接受教育,“一出手去尝试就要成功了”。可以将之同《创世记》的名句“事就这样成了”相比对。而由此引发了一种语义上的朦胧:可以将第二段理解为一种褒义的浑然天成,也可以根据上一段的滑稽色彩,认为这种比附实际上是反语,讽刺动植物们浅薄的沾沾自喜。第三、四段的描写对象其实是一个谜语,而可以轻而易举地推断出谜底是“人”。但谜语本身暗示了不确定性。同时,人类在诗中也被描写为不确定的,他可以被轻易地塑造或改变。这与前两段动植物的“生来如此”产生对比。而且,比起描写动植物的褒义词,奥登在此采用了贬义词,并使它们分别具有崇高和滑稽的特征。
因此,这首诗歌表面上在主旨方面出现了复义,而且这种复义完全由崇高和滑稽构成。考虑到奥登个人的观念和思维,我们又能够确定这首诗通篇都是反语。这不仅因为奥登是一个众所周知的左派,更因为他在文章中一直赞美人类的可变性。如《物种夫人的公正性》中,他说:“人类一直能随心所欲发展自身……人类没有特定的功能,还是在学习掌握所有周边环境的孩童(6)(英)W·H·奥登著:《序跋集》,黄星烨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年版,第600页。。”这与上引诗歌的意味如出一辙。那么,这种情况下,滑稽与崇高不仅融汇,而且它们相互成为了彼此。这种现象的可能性的基础在于,诗中崇高的词语和滑稽的词语,大多是一些修饰词,而关于道德的修饰词,是最为主观的。譬如诗中“一丝轻风都能使他动摇和更改”,是一个充满滑稽意味的贬义语句,但在较为正式的序跋中,奥登对这种特性使用的是褒义的“随心所欲发展自身”。正是这一手段,令滑稽变为崇高,崇高变为滑稽,奥登实际上在反抗话语权的命名和定性。所以,模仿圣经口吻,形容琐屑的动植物,在诗中是滑稽的,但滑稽本身正是目的所在。因为话语权同样在使用这种滑稽的类比进行自我美化,而奥登正是将这种行为的滑稽显现出来。现实生活中的角色,同诗中的角色进行了错位。诗中的动植物被讽刺,并不代表奥登要讽刺现象世界里的动植物,其对应的角色是现实生活中被异化、物化的人。而诗中的人并不指代现象世界中的所有人类,它指代“真正的人”。
可见在这首诗歌中,滑稽与崇高得以融汇,它们各占据诗篇的一半篇幅,可谓势均力敌。而奥登的策略在于,他并不是将两种范畴置于一个针锋相对,以至于引起违和感的地步,而是巧妙地令两者相互转化,即对立统一,一体二用。推动这首诗的力量,不是滑稽与崇高的争斗,而是滑稽与崇高的突转。采用这种方式,二者之间的关系被赋予条理和秩序,因此反倒清晰地产生了文本间的张力,令滑稽与崇高的相容从一种主题、风格,转变成一种文学性。但这一结论还是不够的。据此可以看出奥登这一行为成功的奥秘所在,但这根本上仍然是一个现象。作为诗人,从创作方面可以不追问下去,但作为文艺学,却必须探索究竟。问题就在于,滑稽与崇高得到了转化,但转化的根基在何处,即:滑稽与崇高这两种范畴各自特性如何,为何可以相容。这一问题仍需要得到解答。
三、虚无中的新崇高
奥登的前人里尔克在《给一个青年诗人的十封信》中提到了滑稽与崇高的关系:“纯洁地用,它(暗嘲)就是纯洁的…在严肃事物的影响下…它就会强固成为一个严正的工具(7)(奥地利)里尔克著:《给一个青年诗人的十封信》,冯至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版。。”里尔克对奥登影响巨大,譬如《战时组诗》中,他充满敬佩地追忆里尔克在慕佐城堡的写作,还曾撰写《英语里尔克》一文,盛赞里尔克对英语诗歌产生的巨大影响。里尔克对滑稽与崇高的观点,很可能对奥登起到了影响。但里尔克本身遭受“玄学气”的批评,在此,他阐明的是:滑稽是一个可以与崇高融合的范畴;而他含糊过去的是:滑稽怎样受到“严肃事物的影响”,从而成为“一个严正的工具”。而这正是本文需要讨论的。
法国哲学家让-吕克·南希说过:“崇高很时尚,虽然这种时尚很古老。”这意味着,当代的崇高与以往截然不同,成为了一种“没有个人的崇高”,即以往的崇高变为无用与荒谬,失去了指向超越的客体的可能性。正是在这一情况下,奥登的前辈艾略特写作了《荒原》。但与此同时,这一时代似乎对滑稽是有利的。康德提出一种“乖讹说”:“笑是一种从紧张的期待突然转化为虚无的感情。”奥登举出的一个例子可以佐证:
母亲(对着失明的女儿):亲爱的,现在闭上眼睛,数到二十。然后睁开眼睛,就会发现你能看见东西了。
女儿(数到二十之后):可是,妈咪,我还是看不见。
母亲:今天是愚人节(8)(英)W·H·奥登.胡桑译,《染匠之手》,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500页。!
奥登对此的评论是:“它能暗示我们何谓真正的喜剧感。”言下之意,对复明的期待被消解,这构成了喜剧感。而同时,复明的激动意味着个人克服疾病无穷威力的激动,这又具有某种崇高感,这个例子本身具有现代性,因为在古典文学中是无论如何没有这一笑话的。那么这同样辅证了,古典的崇高在现代的媒介与精神空虚中已经被解构。譬如,利奥塔在《非人》中批评怀旧式崇高:“他们将生命的全部包含进同一个意义单位;就像神话中那样组织和分配时间:故事从头到尾整齐划一,甚至还押上韵(9)(法)利奥塔:《非人》,罗国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他的意思是,宏大叙事成为一种有关完美的谎言,人们希求这种理念作为超越的、拯救的力量。当这种力量的存在被否定,也就没有其余的力量可以与之对等,故此这里呈现出一种虚无。上文已经阐明,奥登对滑稽的概念,也是期待滑落虚无。此处“虚无”又成为了崇高的起点,故此“滑稽与崇高如何融汇”的问题,在现代可以等价于“崇高如何自虚无中重构”的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进行一个追问:“虚无”意味着什么。既往的崇高之物无法奏效,即无法重新唤起崇高的感觉,即“崇高”不能被如此阐释出来。但另一方面,即使是现代人,依然能够感受到“崇高”,否则人们就不可能真正理解“崇高”这一词语。可见此处的“虚无”犹如佛教所谓的“无”,并不是完全的空无,而是在“无”之中蕴含着“有”,即“存在”,但这种存在又是不可阐释的,自性是空无的,故而又不能对外部显现出来。这种“不可阐释”的崇高,在利奥塔处也得到了论述。而在利奥塔秉承的后现代主义看来,人切实的感觉,而非感觉的对象,才是最高的。故而崇高的意味是在威胁的时刻,感受到某事物将要发生。换言之,重点在于“发生”的存在,而不在于“何物”在发生。顺带着,对“崇高物”的阐释,转变为对“崇高感”的抒发,转变为虚无的威胁之中“存在着不能用理性进行表达的感觉,这种感觉不处在线性的时间之中,也不在另一个世界,另一个时间之中,它就在这里,它就是此在,就是本身(10)张胜利:《利奥塔的崇高理论》,《兰州学刊》2006年第3期,第94页。。”
把利奥塔认作后现代主义大师,把奥登认作现代主义诗歌大师,这一种定义本身可能就是谬误的限定。不论如何,既然利奥塔声称过,后现代并不外于现代,它永远是现代的一部分,那就不妨用利奥塔的崇高理念来检验奥登。在利奥塔看来,“有什么要发生”,即是一种期待。在这里,问题得到了澄清。崇高可以被转换成“虚无——期待”,而滑稽可以被转换成“期待——虚无”。按照燕卜荪的说法,诗歌本身或多或少具有复义性,何况如前所述,奥登的诗歌本身就侧重于滑稽与崇高的转换,它就像一个钟摆,在“期待”与“虚无”间来回摆动,而两种轨迹产生了“滑稽”与“崇高”,然而二者又都被塑在一座钟内,即属于一体。在《关于喜剧性的笔记》中,奥登作出了类似的结论:“意志的流动方向也随之逆转…大多数小丑的喜剧效果就是以这样的矛盾为基础的(11)(英)W·H·奥登:《染匠之手》,胡桑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500页。。”在此处,滑稽被理解为崇高意志的逆转,即崇高落入空虚,即不可阐释的即将到来之物被期待以某种方式体现出来,但这种体现被证明无效,而且平庸且粗俗。而当平庸与粗俗的环境下,重新出现某个迹象,预言即将到来的改变者时,崇高就摆脱了滑稽的桎梏,开始显现出来。在《美术馆》中,奥登解构了利奥塔所谓的“怀旧式的崇高”,将之转为滑稽,却又建立起新的现代的(或曰后现代的)崇高。代替殉道者之崇高的,是溜冰的孩子,在他人狂热希冀神迹时,对生活本身的坚信,对“狗还会继续过着狗的营生”之存在的信仰。也就是在虚无的胁迫下,依然坚信溜冰、狗的营生还会继续,“并非一切皆尽”。崇高在转为滑稽后,这基于日常生活,拒绝宏大叙事的滑稽,又以另一种面目表现出了新的崇高。
四、结 语
通过对奥登诗歌的研讨,可以总结出滑稽与崇高在他诗歌中是怎样相容的:二者并不是被针锋相对地设置在同一句子或同一个情景里,从而避免了在这种情况下作品内部无法达到和谐统一,乃至支离破碎的问题。奥登将滑稽与崇高设置成一个事物的两面,它们自然地相互转化,却不曾同时地、矛盾地产生对立,正如白昼与黑夜的关系一样。而由此,它们从一种主题或风格产生了张力,亦即产生了文学性,要素进而成为点睛之笔。而进一步地,本文指出崇高与滑稽转化的根基:崇高是“虚无—期待”的过程,而滑稽是这个过程的反面:“期待—虚无”。这是站在处于具体的奥登作品的角度,抽象地讨论美学范畴之间的关系、相容性。随着现代社会发展,崇高这一范畴已经不同于古典对“崇高”的侧重。个人内在的、不可阐释的、瞬间的感受成为现代意义的崇高,在荒诞中产生了一种“有”意味的预感。滑稽在博马舍的论述中是“浅薄的”,而本文论证的是,滑稽的深刻性在于它反映了虚无与荒诞。在这种情况下,现代的滑稽与崇高拥有融汇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