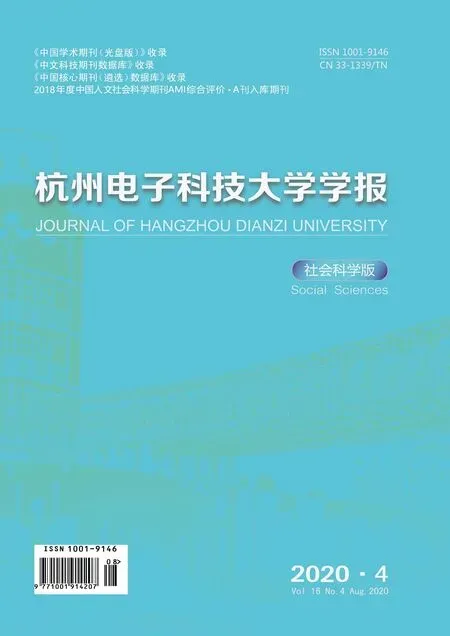王阳明“心即理”命题内涵及当代价值
2020-12-20陈海威
陈海威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8)
说到阳明心学,人们经常会联想到“心外无理,心外无事”这句著名的哲学论断,其实这句话只是对阳明心学“心即理”这一哲学命题的部分阐释,如果没有深入理解“心即理”的涵义,“心外无理,心外无事”很容易让人形成阳明心学属于虚无主义的印象。事实上,“心即理”作为阳明心学的逻辑基础,有着丰富的内涵,吴震先生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心即理’乃是阳明哲学的第一命题,是其心学思想得以确立的标志,无论是稍早的‘知行合一’说还是略晚的‘致良知’说,都应置于‘心即理’的基础上才能得到全面的理解”[1]。那么,什么是“心即理”?其真正内涵又是什么?要解答这一问题,我们必须从“心即理”提出的背景谈起。
一、“心即理”提出的背景
“心即理”是阳明心学的逻辑基础,也是阳明心学与程朱理学的分水岭,这个问题需要从《大学》的“格物致知”说起。
《大学》原为《礼记》第四十二篇,相传为曾子所作,程颢、程颐把它从《礼记》中单独抽出,编次了章句,朱熹又将它与《中庸》《论语》《孟子》合编,称为“四书”。《大学》能位列“四书”之首,与它的特殊地位有关,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言:“子程子曰:‘大学,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也。’于今可见古人为学次第者,独赖此篇之存,而论、孟次之。学者必由是而学焉,则庶乎其不差矣。”[2]由朱熹这段话可看出,正是这种“入门”的作用决定了《大学》在儒家经典中的地位与价值。
这种“入门”集中体现在《大学》首章,简而言之就是“三纲”和“八目”。所谓“三纲”即“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八目”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三纲”指明了儒家修证的方向,“八目”则阐述了俢证的具体步骤。“八目”中从“格物”到“平天下”是层层递进的关系,如同上楼梯,必须从最低处开始,正如王岳川先生所言,“《大学》八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一个从小到大,从客观到主观,从个体到人类渐进修为的过程,而格物致知的重要之处在于它们是‘大学之道’的起点。”[3]
遗憾的是,“格物”心法从孟子之后出现了断层和混乱,王阳明在《朱子晚年定论》中谈到这一问题,“洙泗之传,至孟氏而息。千五百余年,濂溪、明道始复追寻其绪。自后辨析日详,然亦日就支离决裂,旋复湮晦。吾尝深求其故,大抵皆世儒之多言有以乱之。”[4]118根据刘宗周的说法,“格物之说,古今聚讼者有七十二家”[5]之多,如东汉郑玄解释为:“格,来也。物,犹事也。其知于善深,则来善物。其知于恶深,则来恶物。言事缘人所好来也。此致或为至。”[6]北宋司马光解释为:“《大学》曰致知在格物,格犹捍也,御也。能捍御外物,然后能知至道矣。”[7]在二程那里,“格物”有“至”和“穷”两层含义:“格,至也。物,事也。事皆有理,至其理,乃格物也。”[8]365“格犹穷也,物犹理也,犹曰穷其理而已也。”[8]316朱熹继承了程颢的说法并加以发挥,认为“格,至也。物,事也。穷至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不到也。”[9]王阳明认为,正是历史上这种众说纷纭让“格物致知”显得扑朔迷离。
朱熹本来也是一家之言,但从元朝中期开始,他的学说不断受到推崇,到了明朝已经成为科举取士的唯一标准,以绝对统治地位渗透到儒家士子文人的骨髓中。朱熹主张“即物穷理”,且“一草一木皆含至理”,曾言“格物者,格,尽也,须是穷尽事物之理。若是穷得三两分,便未是格物。须是穷尽得到十分,方是格物。”[10]219又说:“世间之物,无不有理,皆须格过。古人自幼便识其具。且如事君事亲之礼……今人皆无此等礼数可以讲习,只靠先圣遗经自去推究,所以要人格物主敬,便将此心去体会古人道理,循而行之。如事亲孝,自家既知所以孝,便将此孝心依古礼而行之;事君敬,便将此敬心依圣经所说之礼而行之。一一须要穷过,自然浃洽贯通。”[10]214朱熹对“格物”的解读容易产生以下推论:第一,理存在于物上;第二,格物就是到物上求理。这种推论很容易导致学者到外物上求理,王阳明“格竹”就是他年轻时对朱子学说的懵懂实践。《年谱》记载,王阳明二十一岁时,“一日思先儒谓‘众物必有表里精粗,一草一木,皆涵至理’,官署中多竹,即取竹格之;沉思其理不得,遂遇疾。”[4]1027此次格物失败对一向自信满满的王阳明打击很大,但从长远来看,这无疑也是一次有价值的“试错”,因为这为他后来的“龙场悟道”埋下了伏笔。
王阳明“龙场悟道”究竟悟到了什么?《年谱》记载:
“(正德)三年戊辰,先生三十七岁,在贵阳。……日夜端居澄默,以求静一。……因念:‘圣人处此,更有何道?’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寤寐中若有人语之者,不觉呼跃,从者皆惊。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4]1031
由上述记载可知,王阳明最大的收获就是“大悟格物致知之旨”。这个“旨”究竟是什么?《年谱》没有细说,但在被誉为“王门入门教典”的《大学问》中,王阳明对此做了详细的解释:
“何谓身?心之形体运用之谓也。何谓心?身之灵明主宰之谓也。何谓修身?为善而去恶之谓也。吾身自能为善而去恶乎?必其灵明主宰者欲为善而去恶,然后其形体运用者始能为善而去恶也。故欲修其身者,必在于先正其心也。……物者,事也,凡意之所发必有其事,意所在之事谓之物。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归于正之谓也。正其不正者,去恶之谓也。归于正者,为善之谓也。夫是之谓格。”[4]826
这段话通过论述身心的相互关系,指出修身的根本在于心,并明确指出:格物就是正心,就是从源头上为善去恶。这正是王阳明悟到的“格物致知之旨”,这与朱熹的物上求理完全相反,转向了心上求理的路径。
这一发现,也同时奠定了心学的立足点。王阳明在龙场困境中反复思考“圣人处此,更有何道?”经过苦苦思考,他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圣人与凡人最大的区别就是心。圣人也会遭遇困境,如舜曾被父亲和弟弟多次陷害,周文王被商纣王无故羁押,孔子也曾经历过陈蔡之厄,但是这些圣人都能坦然面对困境,遵循大道,素位而行,根本原因是因为他们内心能时刻以良知为主宰,遵循天理,不为个人荣辱得失乃至生死所动。所以说圣人的关键是在于心,心上没有私欲遮蔽就是天理,圣人的秘密就是在心上用功,这可以说是王阳明在龙场的最大发现,以至于他后来多次指出,“夫圣人之学,心学也。学以求尽其心而已。”[4]228“圣人之学,心学也。尧、舜、禹之相授受,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十六字诀。此心学之源也。”[4]217
关于“格物致知”,王阳明后来在给学生讲学时提到,“及在夷中三年,颇见得此意思,乃知天下之物本无可格者。其格物之功,只在身心上做,决然以圣人为人人可到,便自有担当了。”[4]111正如吴光先生指出,“在王阳明看来,他过去按照朱熹‘格物’说去‘格竹子的道理’是‘求理于外’,是不正确的方法。正确的格物方法应该是‘只在身心上做’,即求理于心。他虽然没有直说‘心即理’,但实际上他所谓‘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一语,已包含了‘理在于心’‘心外无理’的思想了。”[11]
二、“心即理”的内涵
“心即理”是王阳明在特定历史背景下提出的哲学命题,对其内涵的理解必须结合当时的社会环境。
首先,“心即理”具有极强的针对性。王阳明年轻时也笃信朱熹的格物理论,但屡屡碰壁,经过九死一生机缘巧合才领悟到格物的要旨,他对自己的发现兴奋不已,但同时也深知朱子格物思想的影响之深,想要改变这种现状绝非短期可以轻易做到。这如同一艘大船,方向已经出错,但众人浑然不知,仍在用力划桨,此时唯有奋力呼号,才能引起人们警觉。王阳明提出“心即理”与朱子的“即物穷理”大相径庭,犹如一颗深水炸弹,在当时引起很大的反响,振聋发聩,客观上也加速了他思想的传播力度。
其次,“心即理”具有警示性。《传习录》记载,有弟子拿程颢“在物为理”质疑“心即理”的提法,王阳明认为应该把“在物为理”改为“此心在物即为理”才对,并阐述了“心即理”的立言宗旨,“我如今说个心即理是如何,只为世人分心与理为二,故便有许多病痛。……分心与理为二,其流至于伯道之伪而不自知。故我说个心即理,要使知心理是一个,便来心上做工夫,不去袭义于外,便是王道之真。此我立言宗旨。”[4]112王阳明认为,分心与理为二,会有把私心误做天理的病痛,“心即理”的提法可以警示人们心与理本为一体,不可分割,防止学者出现知行不一的弊端。
最后,“心即理”反对悬空想象。王阳明指出,“故致知者,意诚之本也。然亦不是悬空的致知,致知在实事上格。如意在于为善,便就这件事上去为,意在于去恶,便就这件事上去不为。”[4]111“心即理”并非让人悬空去想象出一个理的存在,而是强调心遇到事后才能呈现出具体的理,表明心与理的融合必须在具体实事上才能实现。
以上是从宏观角度对“心即理”提出背景的解读,但具体到实践层面,心与理的融通并非可以自然发生,尤其对于初学者而言,必须遵循一定的原则和主旨,通过做工夫不断打磨自己的“心镜”,才能达到“心即理”的融通境界。如何完成这一过程,就涉及到“心即理”的具体内涵。如果从微观层面考察,“心即理”的内涵包括“正心”“用心”“恒心”三个层面:
第一,正心。所谓正心就是从源头上保持意念的至善,这是王阳明主张的“格物”主旨,也是“心即理”的第一要义。王阳明指出:
“心者身之主宰,目虽视,而所以视者心也;耳虽听,而所以听者心也;口与四肢虽言、动,而所以言、动者心也。故欲修身在于体当自家心体,常令廓然大公,无有些子不正处。主宰一正,则发窍于目,自无非礼之视;发窍于耳,自无非礼之所;发窍于口与四肢,自无非礼之言、动。此便是修身在正其心。”[4]826
因此,正心的实质就是要去除私欲的干扰,恢复心的本体。心的本体如果没有私欲遮蔽,遇事发动即是天理,这正是王阳明提出“心外无事,心外无理”的依据,他在与徐爱的对话中曾对此进行过阐述:
先生曰:“心即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
爱曰:“如事父之孝,事君之忠,交友之信,治民之仁,其间有许多理在,恐亦不可不察。”
先生叹曰:“此说之蔽久矣,岂一语所能悟。……心即理也。此心无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不须外面添一分。以此纯乎天理之心,发之事父便是孝,发之事君便是忠,发之交友、治民便是信与仁。只在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用功便是。”[4]2
“此心无私欲之蔽,即是天理。”用这种本心事父、事君、交友、治民即是孝、忠、信、仁,原本如此,“不须外面添一分”,这正是正心的妙用,也是“心即理”的第一要义。
第二,用心。用心就是要专注,就是要集中精力在一件事上,这是“心即理”的第二层涵义。心与理之间的阻隔很多时候是因为主体没有集中注意力,影响到了自身对客体的洞察能力,因此,专注是实现“心即理”的重要途径。王阳明多次强调专注对为学的作用,他在《书玄默卷》中指出,“玄默志于道矣,而犹有诗文之好,何耶?弈,小技也,不专心致志则不得,况君子之求道,而可分情与他好乎?”[4]243告诫玄默要专一,不能因诗文爱好而分心。他对学生周积的教导,更说明了专注的重要性:
江山周以善究心格物致知之学有年矣,苦其难而不能有所进也。……阳明子曰:“子未闻昔人之论弈乎?‘弈之为数,小数也,不专心致志,则亦不可以得也。’今子入而闻吾之说,出而有鸿鹄之思焉,亦何怪乎勤而弗获矣?”于是退而斋洁,而以弟子之礼请。阳明子与之坐。盖默然良久,乃告之以立诚之说,耸然若仆而兴也。……明日,又言之加密焉,证之以《中庸》。乃跃然喜,避席而言曰:“积今而后无疑于夫子之言……[4]211
这段文字生动记叙了周积学习“格物致知”的过程。周积刚开始不专注,所以学无所获,后来痛下决心,虔诚拜师,连续几天集中精力学习领悟,终于对困扰他多年的“格物致知”问题豁然贯通,王阳明写这篇序的主旨就是为了阐述用心对为学的重要性。
第三,恒心。恒心就是要能持之以恒,有坚强的意志,无论顺境逆境,都能不断精进,这是“心即理”的第三层涵义。王阳明曾言:
“诸君只要常常怀个‘遁世无闷,不见是而无闷’之心,依此良知忍耐做去,不管人非笑,不管人毁谤,不管人荣辱,任他功夫有进有退,我只是这致良知的主宰不息,久久自然有得力处。一切外事亦自能不动。”又曰:“人若着实用功,随人毁谤,随人欺慢,处处得益,处处是进德之资。若不用功,只是魔也,终被累倒。”[4]94
“心即理”的融合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持续的工夫磨炼,需要有恒心。唯有远大的志向才是恒心的根本保证,因此王阳明非常重视学者“立志”,他在《示弟立志说》中指出“夫学莫先于立志”,“是以君子之学,无时无处而不以立志为事。”[4]231
“心即理”是阳明心学的逻辑基础,正心、用心、恒心是对阳明心学的全新解读。王阳明曾言:“是故君子之学,惟求得其心,虽至于‘位天地,育万物’,未有出于吾心之外也。孟氏所谓‘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者,一言以蔽之。”[4]212当然,要说明的是,“心即理”的内涵虽分为正心、用心、恒心三个层面,但三者之间并非各自独立,而是一体三面的关系,可以用“立志”这一富有心学特色的命题加以贯穿,王阳明曾把为学比作农夫种田,“君子之于学也,犹农夫之于田也,既善其嘉种矣,又深耕易耨,去其蝥莠,时其灌溉,早作而夜思,惶惶惟嘉种之是忧也,而后可望于有秋。夫志犹种也,学问思辨而笃行之,是耕耨灌溉以求于有秋也。志之弗端,是荑稗也。志端矣,而功之弗继,是五谷之弗熟,弗如荑稗也。”[4]211正心如同“嘉种”,用心、恒心就是“深耕易耨,去其蝥莠,时其灌溉,早作而夜思。”不同时期,三者可能各有侧重,但其根本目的并没有不同,就如同一粒种子从发芽到参天大树,其外在形态虽然发生了变化,但不变的是其生生不息的内在生命力。只有正心、用心和恒心三者同时兼具,共同作用,才能达到“心即理”的最终融通境界。
三、“心即理”与工匠精神
自2016年以来,工匠精神已经连续四年被写入政府的工作报告,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也提出“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弘扬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营造劳动光荣的社会风尚和精益求精的敬业风气。”这是中国政府立足于国际产业变革大势,做出的全面提升中国制造业发展质量和水平的重大战略部署,其根本目标在于改变中国制造业“大而不强”的局面。在促进产业升级、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的背景下,工匠精神已成为经济转型的迫切需求。
工匠精神简单说就是劳动者在工作中表现出的敬业、专注,对产品质量一丝不苟、精益求精、不断创新的品质。从内涵构成上看,工匠精神既有物质层面的载体,又有精神层面的内核,“如果要给工匠精神下一个完整的定义,应该是指工匠在良好人文修养和高超职业技能结合下形成的一种精神理念,它既体现为工匠的气质,又体现为产品的品质。”[12]如果把工匠精神比作一棵树,那么产品是树冠,技术是树干,而匠心则是树根。产品是工匠精神的物质载体,技术是工匠精神的实现途径,匠心则是工匠精神的内在魂魄。一个工匠大师,首先是因为他有了一颗匠心,才有了精湛的技艺和精美的产品,因此匠心培育是工匠精神的根本。从表面看,劳动过程是劳动者通过手艺和技术生产了产品,但实质上是劳动者主观意志外化的过程,从阳明心学的角度来看,心是身的主宰,人的所有劳动生产过程都是在心的主宰下完成。中国古人强调“道技合一”“心合于道”,因此“心即理”对匠心培育具有重要意义,具体而言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正心是工匠精神的前提。正心就是去除私欲的遮蔽,以良知来面对日常工作,这有助于劳动者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形成爱岗敬业的职业道德。工作者的劳动态度决定了产品的质量,被誉为“经营之圣”的日本企业家稻盛和夫说过:“缺乏对工作高度的热爱就不可能取得卓越的成果。”[13]因此,对劳动者而言,无论从事任何职业,首先都应该做到正心,认知到工作的价值和意义,以高度的责任感和热情投身于工作,这是工匠精神的前提和基础。
第二,用心是工匠精神的关键。用心就是要专注于自己的业务,一门心思深入。任何技艺,都学无止境,一个人的专注程度决定了他对细节的把握,正如王阳明所言,“道无精粗,人之所见有精粗。如这一间房,人初进来,只见一个大规模如此。处久,便柱壁之类,一一看得明白。再久,如柱上有些文藻,细细都看得出来。然只是一间房。”[4]19同样一间房,用心的人可以看清细节,不用心的人只能看到一个大概,这正是大师和普通劳动者的区别所在。
第三,恒心是工匠精神的保证。中国古人认为技艺的最高境界是“道技合一”,达到这个境界需要持续不断的练习,如庄子笔下的庖丁、欧阳修笔下的卖油翁,都是持续精进、熟能生巧的典范。大发明家爱迪生也曾说过:“我从来不做投机取巧的事情。我的发明除了照相机,没有一项是由于幸运之神的光顾。一旦我下定决心,知道我应该往哪个方向,我就会勇往直前,一遍一遍地试验,直到达到我的目的。”[14]凡事能持之以恒,这是许多人成功的诀窍,也是工匠精神养成的必经之路。
四、结语
“心即理”作为阳明心学的基础性命题,具有丰富的内涵,对当代工匠精神培育具有借鉴意义,正心、用心、恒心分别可以从价值观塑造、学习策略和实践方法等方面对工匠精神的养成提供参考。正心、用心、恒心是一体三面,以“立志”作为统领合为一体,因此“立志”对劳动者工匠精神培育意义非凡。王阳明曾言“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虽百工技艺,未有不本于志者。”[4]828
“立志而圣则圣矣,立志而贤则贤矣”,2019年4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引用王阳明这句话,鼓励新时代中国青年要树立远大理想。同样,作为新时代的建设者,广大青年也应该在学习和工作中有意识培养工匠精神,使工匠精神成为一种民族性格和日常习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才能早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