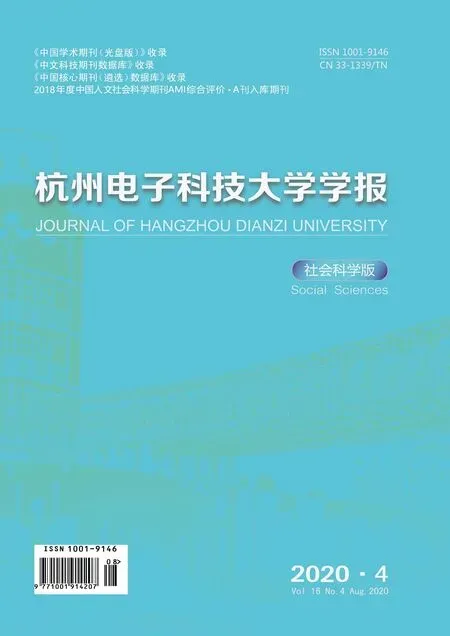全球价值链理论及实证研究综述
2020-12-20宋燊通
任 重,宋燊通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经济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8)
自19世纪David Ricardo提出“比较优势理论”以来,从Heckscher-Ohlin资源禀赋理论到Samuelson的古典贸易理论,传统国际贸易理论一直基于三个经典假设:市场是完全的且生产规模报酬不变、同一行业生产者具有同质性、各国仅从事最终产品贸易。20世纪70年代,由于贸易环境发生变化,Krugman对第一个假设的有效性提出质疑并引入规模报酬递增模型,从而奠定了不完全竞争背景下国际贸易理论的分析框架。20世纪90年代,生产者同质这一假设已经无法准确描述当时国际贸易企业在资本规模和组织方式等方面的巨大差异,Melitz(2002)[1]提出企业异质性这一概念,推动了后来“新-新贸易理论”的发展。随着中间品贸易的盛行,最终产品贸易不再是国际贸易学的主要研究方向,全球价值链理论(或被一些学者称之为“新-新-新贸易理论”)被国际贸易学者纳入研究的范畴,并逐渐成为国际商品加工贸易的主要研究方法。
当前,越来越多的研究机构都投身于经济全球化和数字科技进步对各个经济体影响的研究中。以经济合作发展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为代表的国际机构和国际组织通过重新整合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中的附加值结构,探讨了国际经济活动中价值的分配机制,这必然会涉及到全球价值链理论和实证方法的研究。而随着全球价值链研究的不断深入,其理论体系和实证方法又有了哪些新的内涵呢?
一、全球价值链的发展历程及其主要研究内容
全球价值链这一概念是在洛克菲勒基金会赞助的“全球价值链计划”(2000-2005)的讨论中首次被集体描绘出来的,其思想最早起源于Jones & Kierzkowski(1990)[2]提出的生产分工理论。通过对国家间价值分配结构和机制的研究,Gereffi等(2005)[3]对这一概念进行了具体化。随着中间品贸易研究的盛行,在Feenstra和Hanson(1995)[4]研究基础上,Baldwin(2006)(1)Baldwin R. Globalisation: The Great Unbundling. Helsinki: Economic Council of Finland, 2006.更精确地定义了全球价值链中的关键概念。Grossman和Hansberg(2008)[5]认为其优点在于能够充分地利用各国资源禀赋优势,并最大限度地发挥生产工序中不同环节的规模经济,提升经济发展效率,从而获得更多专业化分工下的经济利益。
而关于全球价值链的实证研究则开展较晚,从早期Dedrick等(2008)(2)Dedrick J, K Kraemer, G Linden. Who Profits from Innovation in Global Value Chains? A Study of the iPod and notebook PCs. Report prepared for the Sloan Industry Studies Annual Conference, Boston, 2008, May 1-2.基于企业经营数据进行单个产品的附加值分析,到之后投入产出法的产业增加值和主要经济体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分析,全球价值链实证研究经历了从微观向宏观的演进。邢予青和Detert(2011)[6]以某一特定微观企业为对象,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进行了案例研究,发现传统贸易统计方法错误地将产品的全部价值计入处于国际生产链最后阶段的国家,极大地增加了作为出口平台的国家与目标市场国家的贸易失衡。李昕(2012)[7]利用世界投入产出数据(WIOD)研究发现,中国贸易总额和贸易顺差均显著低于通关统计。王直等(2015)[8]利用多部门贸易增加值数据,重新定义了官方统计的贸易增加值和重复计算部分,这种方法已经成为国内全球价值链测度的主流方法。
二、全球价值链理论研究的最新进展
(一)增加值实际有效汇率的提出
Bems和Johnson(2012)(3)Bems R, R Johnson. Value-Added Exchange Rates. NBER Working Paper, 2012, NO.18498.提出增加值实际有效汇率,拓展了增加值贸易的研究方法。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传统实际有效汇率不再是合适的度量指标,这种现象主要体现在两方面:(1)利用消费者价格指数无法获得有效结果,因为消费者价格指数综合的是产品价格,而产品价格的增加值分散在不同的国家;(2)随着国家间生产分工的日益增长,贸易总值不再是无偏权重。而后,Koopman等(2014)[9]设计了能够将总出口分解成不同增加值来源的完整方法。总出口可以分解为被外国吸收的国内增加值、先出口后返回国内的国内增加值、外国增加值以及重复计算四个部分,根据交易模式进一步计算,从而得出各个产业部门不同的增加值来源。通过这种分解,可以详细了解贸易品的增加值来源和价值流向,这对贸易政策的制定有着重要意义。
(二)全球价值链中的异质性
异质性是全球价值链研究的另一个重要问题,现有研究主要从三个方面来考量:企业异质性、地理区位异质性和劳动力市场异质性。
1.企业异质性
传统投入产出表仅提供所有类型生产者的平均投入信息结构,可能会导致加工型贸易盛行的国家分析结果出现部分偏差。为解决这一问题,Koopman等(2012)[10]将中国投入产出表分成若干子账户,将加工性部门单独列出。在他们研究的基础上,Tang等(2014)(4)Tang H, F Wang, Z Wang. The Domestic Segment of Global Supply Chains in China under State Capitalism. Working Paper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Dallas Globalization and Monetary Policy Institute, 2014, No.186.进一步细化了其方法,将企业规模和所有制结构等企业特征纳入考虑范围,并将中国投入产出表按企业类型和中国工业普查数据以及贸易的统计数据相结合来研究价值链上企业的异质性。Ma等(2015)[11]从双重维度(加工贸易,出口商还是非出口商)、企业所有权信息等方面考虑企业异质性对价值链升级的影响,并依此计算出国内增加值的分配。
2.区域异质性
目前多国投入产出表将国家看作全球生产网络上的一个节点,但一些国家,特别是大国,还具有其内在的空间结构。对于地域相对广阔而一体化程度较低的国家,其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在参与全球价值链的进程中处于极为严重的不平衡,这将会对一国经济发展产生不利影响。Hidalgo和Hausmann(2009)[12]研究表明经济复杂度可以用来度量一个国家相对于其他国家的异质性程度,他的研究表明在过去20年里大多数国家的经济复杂度排名没有什么变化,而北非是一个例外,这在一定程度上和其地理位置接近欧洲市场有关,这也进一步说明区位异质性对全球价值链融入有一定的影响。Suder等(2013)[13]通过引入中国、日本、韩国跨区域间的投入产出表,将各国区域间投入产出数据合并在同一表中,以便在多国投入产出框架下研究一国区域内的异质性。考虑到地理区位的重要性,还有一些学者对区域内价值链的异质性进行研究,并且就其能否融入全球价值链的问题展开了讨论。张会清(2017)[14]从距离和语言的角度出发,研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状况,发现距离和语言是贸易潜力的重要影响因素。这从侧面反映了地理条件的异质性对各个国家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影响。
3.劳动力市场异质性
一国的要素禀赋的差异决定了其产业结构,进而决定其贸易结构的差异。在影响一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要素中,劳动力市场异质性正是要素禀赋差异的直接原因之一,比较不同国家劳动力市场的异质性,可以发现劳动力素质对贸易增加值的影响。Feenstra和Hanson(1995)(5)Feenstra R, Hanson G. Foreign Investment, Outsourcing and Relative Wages. NBER Working Paper, 1995, NO.5121.通过实证研究发现高技能劳动对贸易增加值的贡献显著,而低技能劳动对贸易增加值的贡献并不显著。Timmer等(2014)[15]从受教育程度区分了三种异质性劳动力,并采用欧盟的WIOD数据库结合KLEMs数据库,对不同技能劳动力市场的贸易增加值份额进行了实证研究。该研究发现高技能劳动力的份额逐年增加,低技能劳动力的份额逐年下降,而中等技能劳动力的份额则变化不大,这种差异与当前对全球价值链的研究更多地采用任务难度来决定财富分配的分析方法有较大关系。
(三)全球价值链长度理论
根据生产分工理论,如果技术进步或消费者市场变化,商品生产存在进一步细分的可能,这会导致更精细的劳动分工,以及更高的资源配置效率和更低的边际成本。传统投入产出分析法只衡量产业间的关联性或关联强度,而不关心产业内的分工,这对分析全球价值链上的产业国际分工没有任何帮助。Dietzenbacher等(2005)[16]提出了平均扩展长度(APL)投入产出模型,回答了产业链长度问题。该模型通过计算每个分支的工序数量来衡量每一个产业链分支长度,从而衡量行业的细分水平。Inomata(2008)[17]运用东亚数据,从后向平均扩展程度和前向平均扩展程度两个角度,研究了区域生产体系的结构变化,发现中国停留在区域供应链的最下部分,说明我国长期在全球价值链中承担着最终组装者的角色。
全球价值链领域对价值链长度问题的另一个研究方向是识别各国在价值链中所处的位置。如果一个国家的产业链分工位置离初级产品更近那么该国就处于这条价值链的上游位置,反之,离最终产品更近,则处于下游位置。李焱等(2018)[18]利用了全球价值链长度计算公式,对2000-2014年中国汽车产业全球价值链长度进行测算,发现中国汽车产业全球价值链长度由2000年的3.29增加到了2014年的3.99,整体呈上升趋势,这说明我国汽车产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地位正逐渐上升。因此研究全球价值链长度理论,对分析一国产业的发展状况和国际分工地位有着重要的作用。
三、全球价值链实证研究评述
(一)全球价值链实证研究方法综述
全球价值链实证研究主要围绕数据的选取和实证方法的创新两方面来展开。数据选取有两种途径:一是获取企业业务层面的数据,这在实际操作中有不小的困难;另一种则使用多国投入产出表来描述企业的产出状况。微观数据适用于分析价值链治理安排的形式,及其对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而通过投入产出表的宏观数据来描绘价值链时,可以从系统层面捕捉广阔背景下价值链配置全貌。
实证方法选择上则较为丰富,其主要问题是,在多阶段贸易过程中,贸易成本的核算不够准确。国外学者在分析内含于多阶段国际生产流程中的贸易成本时,一般会用到多国投入产出模型。Los和Temurshoev(2012)(6)Los B, U Temurshoev. Distance-Based Measures of Globalization in a World with Fragmented Production. Presentation at the World Input-Output Database (WIOD) Conference on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Globalization, Groningen, Netherlands, 2012, April 24-26.提出全球价值链长度不一定要像平均扩展长度公式(APL)中一样,计算生产阶段的数量,而可通过使用两个相关行业的地理距离或运输成本的货币价值来计算,这大大简化了计算难度。Muradov(2016)(7)Muradov K. Trade Costs and Borders in the World of Global Value Chains. Nineteenth Annual Conference of Global Economic Analysis, Washington, DC, 2016a, June 15-16.提出了一种量化累积贸易成本和计算前向和后向跨境平均次数的新方法。当投入产出系数以基础价格计算时,贸易成本可以通过增加额外一行的贸易成本系数整合到投入产出矩阵中。他的方法需要使用一种Leontief矩阵替代方法来计算全球投入产出逆矩阵。通过事先将矩阵分解为对应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的对角线和非对角线分块矩阵,这不同于其他方法在事后再进行分解,在某种程度上提高了计算的准确度。国内学者则主要是在数据的使用方法上进行创新,吕越等(2017)[19]采用2000-2006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国海关进出口数据库以及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的合并数据,考察了全球价值链嵌入对生产效率的改善效应。Meng,Ye等(2017)(8)Meng B, M Ye, S Wei. Value-added Gains and Job Opportunities in Global Value Chains. IDE Discussion Paper, 2017, No. 668.对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增加值收益以及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距离(总生产链长)进行了测算,以考察各不同部门在增加值贸易中的就业机会的创造与分配。
(二)实证研究的可行性和挑战
得益于当今统计学和数据科学的快速发展,全球价值链的微观实证研究具有了可行性:一方面相关统计数据的可获得性越来越高(多国投入产出表-国际商品和服务交易的系统且详细的图谱;企业的微观数据;制造商以及咨询公司的分析报告)。另一方面,计算机对海量数据处理能力的提高,使得在面对企业微观数据时,能以更高的效率对数据进行清洗、处理以及相关指标的测算。
1.使用企业业务数据
在使用企业业务数据时,无需借助任何形式的统计推断,而通过其经营绩效间接反映企业价值链的参与程度,这对于描述生产链的实际结构是十分有用的。李平和王文珍(2018)[20]研究了参与全球价值链对企业续存的影响,发现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有助于延长其续存时间,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参与全球价值链对一般贸易型企业、技术密集型企业以及非国有企业存续时间的促进作用更大;中介模型回归结果显示融资能力提升、企业规模扩大以及要素配置效率改善是全球价值链影响企业存活的重要渠道。微观数据是对企业的微观结构进行更为细致的描述,这是使用投入产出表数据所不能反映的,但也有不足的地方:(1)分析对象为特定或少数的企业活动时,不能反映整个价值的流动趋势。(2)Dedrick等(2008)(9)Dedrick J, K Kraemer, G Linden. Who Profits from Innovation in Global Value Chains? A Study of the iPod and notebook PCs. Report prepared for the Sloan Industry Studies Annual Conference, 2008, May 1-2.指出企业业务报表没有将员工薪酬列出,这在国民经济核算框架中是增加值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分析时常与其他类型的生产成本混杂在一起,难以计算。(3)产品层面的分析方法只考虑直接投入品供应商的增加值结构,而价值的产生是在生产过程的每一阶段,因此增加值分析应该能够跟踪产业链的所有阶段,零部件的生产也需要进一步分解其增加值来源。
2.通过投入产出表来描绘区域产业价值链
在引入投入产出法之后,全球价值链的实证方法更加丰富了,附加值贸易测度方法是研究区域产业价值的重点。Koopman等(2010)(10)Koopman R, W Powers, S Wei. Give Credit to Where Credit Is Due: Tracing Value Added Global Production Chains. NBER Working Paper, 2010, NO.16426.在“国际投入-产出表”(WIOTs)基础上提出了国内增加值比例法。赖伟娟和钟姿华(2017)[21]利用此方法测算中国1995-2009 年期间制造业及子行业在GVC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及其演变情况。但投入产出法也并非完美,Sturgeon等(2013)(11)Sturgeon T, Nielsen P, Linden G. Direct Measurement of Global Value Chains: Collecting Product and Firm-Level Statistics on Value Added and Business Function Outsourcing and Off shoring. In Trade in Value Added: Developing New Measures of Cross-Border Trade, 2013,289-320.指出投入产出法具有一定的局限性:(1)部门分类以工业类别为基础,无法确定某项具体任务如研发或装配创造的增加值;(2)交易以属地标准记录,生产活动被领土边界界定,导致国家间增加值的归属不准确;(3)投入产出表没有具体的交易性质信息,价值链定性分析困难。
四、评述与展望
(一)总结和不足
在全球价值链理论方面,本文主要从增加值有效汇率的提出、全球价值链异质性和全球价值链长度理论三个方面进行综述。我们发现,在当前全球价值链的理论研究进展上,增加值实际有效汇率的提出,有助于了解贸易产品的增加值来源和价值流向,但在处理复杂价值链问题时,这种研究方法可能需要进一步验证。另外,从参与主体异质性角度来讲,除了以上提到企业异质性、地理异质性、劳动力异质性之外,政策环境、经济规模、人口结构和文化差异也可以作为全球价值链异质性的参考指标,这极大地丰富GVC参与主体异质性的内涵。全球价值链长度理论方面,除了现有的APL理论外,由于各国的生产活动更加精细化和专业化,国家、行业之间的联系更加复杂,逐渐出现了一些改进的APL理论,从而更加准确地描述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分工。
实证方面主要从微观企业和投入产出法两个方面来展开,微观数据适用于分析价值链治理安排的形式及其对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通过投入产出表来描绘价值链时,可以发现增加值在各产业间变动的趋势,并从系统层面捕捉广阔背景下价值链配置全貌,其最大的挑战可能还是在微观数据的获取和处理上。目前与全球价值链相关的宏观研究数据库较为丰富,如TiVA-dabase(OEDC-WTO),WIOD数据库、亚洲开发银行ADB-MRIO数据库、世界银行WDI数据库等。全球价值链治理模型的实证研究工作依赖于官方货物贸易统计数据。这些数据反映了关联方和非关联方的交易信息,并可以较为清晰反映跨国公司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但也存在一些不足,Antràs(2011)(12)Antràs P. Grossman-Hart(1986) Goes Global: Incomplete Contracts Property Rights, and th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of Production. NBER Working Paper, 2011,No.17470.提出了四个方面的问题:首先,产品层面的数据加总了多个企业的采购决策,这使得在测试企业层面的采购行为时只能进行估计;其次,贸易数据无法提供交易双方的信息,因此无法确定增加值的具体流入部门;第三,关联交易信息也没有反映企业所有权状况;最后,贸易数据大多从本国角度报告进出口信息,而跨国公司大多通过全球供应链进行采购。因此,通过微观企业数据来对全球价值链进行实证研究,可能会是更加合适的选择。
总之,全球价值链的分析框架是在不断完善和发展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会逐渐演化出新的内涵,研究方法的多样性正是由经济现象中参与主体的差异性和不确定性导致的。如何尽量用恰当的方式,将相关框架与具体的问题相结合,从而让模型有更好的解释力,这是在后续研究中需要深入考虑的问题。
(二)研究展望
当前全球价值链研究分析的重点主要还是贸易伙伴之间特定供应-使用关系,特别是企业对中间投入品“制造还是购买”的选择,其主要分析模式仍然主要依赖理论分析。Antràs和Chor(2013)[22]考虑了生产阶段的技术排序问题,这为序列实证分析开辟了新的途径。无论是传统的国际贸易模型还是最新的价值链长度模型,投入产出法本质上还是关注生产流通的序列问题。随着智能算法、网络图模型等新兴算法的出现,逐渐有一些学者开始将网络中心性的概念引入到投入产出模型中。价值链的研究从一维转向了二维,网络分析将会使全球价值链在多国生产分工的描述中更为细致和精确。通过使具有产业关联的价值链之间相互连接而形成系统的价值网络,这对未来产业和国际贸易理论的研究都是有一定借鉴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