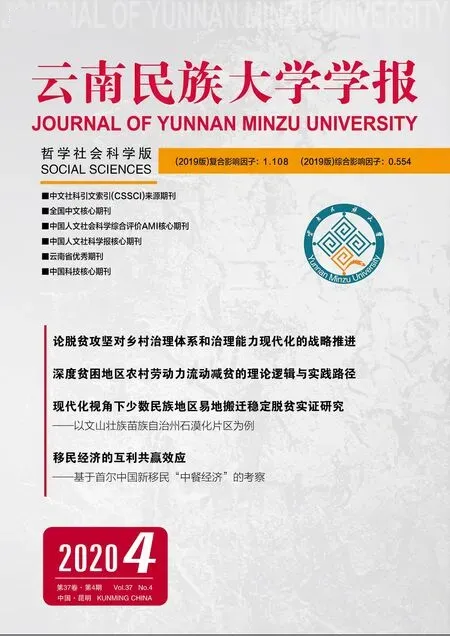明清时期乌江流域民族关系影响因素研究
2020-12-16马率帅
马率帅
(陕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 陕西 西安 710119)
乌江流域涵盖了贵州、云南、湖北、重庆等三省一市,面积广阔,自然环境复杂,苗族、土家族、彝族等数十个少数民族的先民们杂居于这一区域,相关历史文献中称他们为“土民”。在他们各自的社会生产和生活中,这些后来分属于不同民族的先民之间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产生了交叉多元的民族关系。在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建构过程中,乌江流域各民族以其多样性和独特性参与到了这一进程之中。笔者立足于深入考察该区域民族关系的发展变化,聚焦探讨影响乌江流域民族关系的重要因素,弄清楚该地区民族关系生成、发展与变化的原因和过程,以期获得有利于建构和谐民族关系的地方智慧与经验,丰富当代加强民族团结,促进文化交流,构建和谐共生的良好民族关系的知识,为实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目标提供借鉴。
一、乌江流域民族关系概述
位于西南地区多民族聚居的乌江流域,民族关系十分复杂。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就类型而言,各类民族关系错综复杂。例如有中央王朝与少数民族政权的交流,早在西汉武帝时,已有遣唐蒙通使夜郎,并设吏令的行为;各少数民族地方政权之间的关系,如唐代时期乌江流域就有南诏、大理、罗殿国、罗氏鬼国、毗那、乌撒等政权相互来往;有中央王朝与各民族民间之间的互动,如东汉明帝时的益州西部都尉郑纯,因为清正廉洁,以德感化当地土民,民众赠予他特产物资,传颂其美德,从而达到保境安民的效果;也有少数民族地方政权与各民族民间的关系,如水西安氏土司政权与彝民的地方社会治理;还有汉族民间与各少数民族民间的关系,如改土归流策略带来的汉族迁移与当地少数民族发生的矛盾现象,部分地区有时因为客民涌入,不断吞噬苗民土地,引发苗人驱逐移民的现象;以及各少数民族民间内部关系,如乌江流域世居苗族、土家族等多民族民间往来等。由此可见,乌江流域民族关系是一个多层次、多内容的区域网,它链接着中央王朝、地方政府、民族民间等多方势力。
二是就状态而言,乌江流域民族地区的民族关系则颇有代表性。评价一种民族关系的标准通常是“好”与“坏”或者“和谐”与“冲突”,但在考察乌江流域的民族关系时,单一的标准很难奏效。究其原因,难点有二:时间跨度长,空间范围广。以中央王朝与乌江流域地方政权的关系为例,秦汉至今,各有特点,同一时期的乌江流域内部的民族关系状态可能也会不同,如明万历年间播州土司的“叛乱”与其它土司政权的“分分合合”就体现了当时复杂的民族关系。因此,单纯地以“好”“坏”论乌江流域乃至中国西南的民族关系都会有失偏颇,必须以辩证的眼光探讨影响民族关系发展变化的重要因素,唯有如此,才有利于客观、全面地认识民族关系问题。
民族关系的复杂性源自于影响因素的多样。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诸如政治制度、经济行为、文化教育、移民等皆起着重要作用,它们互相交织,互相影响,在历史和现实中逐渐形成相互依赖的整体。
二、政治因素对乌江流域民族关系的影响
影响民族关系的因素纷繁复杂,其中政治因素既是“因”也是“果”。中央王朝处理与地方民族关系的所有方式和手段无不是以“统一”为目标,为此而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民族政治策略以治理边疆民族地区。以西南地区看,从“羁縻制”到土司制度都充分展现了封建王朝统治者治理边疆民族地区的高明之处。他们始终以诸如“以夷治夷”“以夷制夷”“以夷攻夷”等作为中原王朝处理民族关系的重要方式和重要模式。(1)崔明德:《中国古代中原王朝处理民族关系的方式》,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4年第4期。就中央王朝与乌江流域地区的民族关系而言,明清以来实施的土司制度深刻地影响着该流域内民族关系的发展。在乌江流域民族地区,中央王朝先后实施了羁縻制、土司制度、改土归流等政治统治政策,乌江流域与中央王朝的关系也经历了从早期的“宗主国”与“附属国”到纳入统一中央王朝政治体系,再到有清一代“改土归流”的变化。历经此过程后,乌江流域地方与中央王朝之间形成一个内在关联的整体,乌江流域各民族也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一关系的演变过程在时而对立、时而统一的反反复复矛盾中变化前行。
从乌江流域的历史看,政治制度变化带来的最显著和最积极的影响是少数民族地方政权和民众对中央王朝的认同与归属。明朝时期,乌江流域石砫土家族土司秦良玉出于国家与文化认同,积极响应中央王朝的系列策略,在明朝泰昌、天启年间多次“北上援辽”,多次参与明王朝“平播”“讨奢”等地方军事行动。秦良玉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表达了对明王朝的忠诚,维护了国家统一和西南地区的稳定,强化了石砫土司与明王朝中央政权的关系,表现了强烈的国家认同意识。(2)彭福荣,谭清宣:《国家、民族认同视野下秦良玉军征研究》,载《贵州民族研究》2015年第9期。这种良性的互动为构建和谐的中央王朝与地方民族关系奠定了基础,秦良玉本人也得到中央王朝认可,最后官至太子少保太傅、都督总兵、诰封忠贞侯一品夫人,“秦良玉文武双全,是历史上唯一一位被 《二十五史》载入将相列传的女将军。”(3)徐志奇:《我国古代唯一被正式列入国家编制的女将军秦良玉》,载《文史月刊》2011年第5期。由此成为少数民族稳定民族关系和维护国家统一的典范。
水西(今贵州省毕节市大方县)彝族安氏土司奢香夫人处理地方少数民族与中原王朝的关系亦是一典型案例。据《大定府志》记载:“(明都指挥使)马烨素恶奢香,又思尽灭诸罗代以流官,苦无间,会香为他罗所讦,烨欲辱香激诸罗怒,俟其反而后加之兵。……香曰‘反非吾愿,且反则歹得借天兵以临我,中歹计矣!我之所以报歹者,别有在也。’”最终奢香夫人奔赴京城面见皇帝朱元璋告御状,并以开辟驿站为承诺,粉碎了马烨的阴谋,维护了民族的稳定和国家的统一。在整个水西彝族土司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彝族土司政权发挥了重要作用,如协助明王朝平定播州宣慰使杨应龙的叛乱等。此外,水西土司政权还代替中央王朝行使基层控制、保境安民等功能,诸如奉旨征讨西堡蛮、水东蛮、乜香叛苗等征蛮军事活动,有效地维护了地方民族关系的和谐稳定。这类由地方民族政权首领推动的国家认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有明一代中央王朝统治者对地方采取柔和的政治制度所致。
但是,政治因素对民族关系产生的并非全都是积极影响,有时也会产生消极作用,如明万历年间播州土司杨应龙发动的“播州之乱”,天启至崇祯间四川永宁宣抚使奢崇明以及贵州宣慰同知安邦彦发动的“奢安之乱”等都是典型案例。有研究者指出,“播州之乱”源于后期土司治理的诸多缺失,如兼制措施导致事权不一,抚剿不定致使土官骄纵日甚,辗转会勘致使纷争久拖不决,官员腐败致使土官有恃无恐等。(4)颜丙震:《杨应龙议处纷争与明代土司治理的缺失》,载《长江师范学院学报》2018年第8期。“奢安之乱”则因为明王朝连年征战(如“万历三大征”),人力物力财力匮乏,加上因卫所制度崩坏导致过度依赖土兵引发的“尾大不掉”之患。从结果上来看,明王朝后期对西南地区民族的控制力极大下降,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明王朝的覆灭。(5)颜丙震:《明代“播州之乱”与“奢安之乱”比较研究》,载《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年第10期。及至清代,中央王朝加强了对乌江流域地方政治的控制,比较显著的是清康熙年间平叛宣慰使安坤发动的“安坤之乱”与“播州之乱”“奢安之乱”之间存在性质差异,清代“安坤之乱”属于“被迫”“造反”。
三、经济因素对乌江流域民族关系的影响
经济因素既包括经济制度,也包括经济活动,它们共同影响着明清时期乌江流域的各类民族关系,尤其是影响着中央王朝、地方少数民族政权、少数民族民间三者之间的朝贡制度、贡赋与地租、互市贸易等关系。朝贡体现了各民族之间和平交往、相互交流的民族关系。赋税和地租则是象征统治的经济方式,它标志着一种自上而下的社会控制状态。“改土归流”前乌江流域民族地区的赋税主要发生在地方政权与少数民族之间,民族地区向中央王朝纳赋税更多是一种象征性的政治行为,地租则是普遍存在于乌江流域民族地区,成为地方政权控制少数民族成员的重要手段;民族民间贸易的主要形式是互市,如在乌江流域司属境内开设会馆、商贸场所、开设各类交易市场等。以上多种经济行为往往作为改善民族关系、促进各民族间交流的媒介存在。
朝贡是一种政治和经济的双向制度,意味着地方民族政权向中央王朝的认同与臣服,其稳定性影响着中央王朝与地方民族政权的关系。同时,朝贡又是一种包含贸易属性的经济制度。明清时期的地方民族首领及贡使的朝贡行为带来了中央王朝与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交流,践行孔子所言“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的文化理念,促使民族地区对国家产生文化认同和归属感,从而推动中华民族的交融。对于乌江流域的民族而言,经济上因为朝贡而获得许多回赐财物,从而完成地方与中央的贸易行为,谋得实利;政治上则因为臣服的朝贡行为,在合法状态下保持高度自治,还能获得中央王朝的庇护,促成中央与地方民族的互惠共赢关系。史载乌江流域民族地区朝贡次数频繁、种类繁多,多以当地特产为主,如明永乐十二年(公元1414年),位于乌江流域黔东北的思南府丹砂开采和冶炼较为发达,当地分设多个水银局,以便于朱砂、水银的开采,因此地方也将水银、朱砂作为朝贡之物献予朝廷。万历十三年 ( 1585年),播州宣慰使将大木作为朝贡物品进献朝廷从而得到赏赐,贵阳宣慰使安国享则马上效仿,以谎报进献大木的形式也获得中央王朝赏赐的飞鱼服。西南土司进献大木与接受中央朝廷的赏赐仅是象征性和程式化的,但它却是西南土司表示忠顺大明王朝的一种表象,也是明代统治者显示中央王权的一种招牌。(6)李良品:《明代西南地区土司进献大木研究》,载《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8年第9期。从材料可以看出,朝贡行为给双方带来的意义是有区别的,对地方民族政权意味着荣誉和贸易实利,对中央王朝而言更多的是归顺的象征。
明清时期,中央王朝对乌江流域民族地区大多采取宽松的赋税政策。由于明清时期乌江流域地区发展较为落后,中央大多只是收取象征性的赋税,以明清施州卫对土司的税赋规定为例,“无论田地多少,每年固定纳银七十三两六钱四分”;更有特殊情况会完全免除赋税,特别是遇到灾荒情况,如明洪武二十二年(1388年),听闻贵州租税道负,朱元璋曾有“蠲免”之举。过去的传统农业赋税给百姓带来沉重的负担,而朝廷对土司地区的宽松税收政策则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当地农业生产的压力,(7)段超:《古代土家族地区开发简论》,载《江汉论坛》2001年第11期。客观上减轻了各少数民族民众的赋税负担,缓和了中央王朝与地方民族的紧张关系。
互市是民族地区根据自身特点和情况设立的集市。例如贵州比较著名的“十二场”:“贸易以十二支所肖该市名,如子日则曰鼠场,丑日则曰牛场之类。”(8)沈庠:《贵州图经新志》卷一《贵州宣慰司上: 风俗》,清弘治年间刻本。“场”的设置主要是为稳定当地贸易秩序,保证互市的正常开展,随着地区互市的繁荣,也会逐渐增加“场”。清康熙年间,位于乌江流域的鄂西容美土司境内已呈现繁荣的互市景象,“江、浙、秦、鲁人俱有,或以贸易至,或以技艺来”(9)鹤峰,五峰县史志编篡办公室:《容美土司史料汇编》,鹤峰:鹤峰县史志办,1983年印刷,第316页。。早在元代,施州(今湖北恩施一带)就已经设立互市场所并成为当地商业贸易中的中心。及至明代,较大的民族地区都有商业繁荣的中心,如思南府成为“上接乌江,下通蜀楚,舟楫往来,商贾鳞集”之地。(10)李良品:《乌江流域土家族地区土司时期的经济发展及启示》,载《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黔东镇远府因四通八达,交通来往便利成为各类互市的集中场所,来自各地各行各业的人在此贸易,并且明确规定固定互市期限,每月逢三、七赶场,1年共有72次集市,乌江流域民族地区的互市繁荣程度在清朝可见一斑。(11)张世友:《清代乌江流域的移民活动及其对民族关系的影响》,载《重庆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客商络绎不绝的往来和侨居必然带动乌江流域地区互市,促进民族民间交流交往。
四、移民与教育因素对乌江流域民族关系的影响
明清时期乌江流域民族地区的移民主要有以下几类:第一类是军屯。以清代而言,清王朝恪守“羁縻”之道,为维护对乌江流域民族地区的统治,朝廷派遣的军队驻扎于此,后来允许部分军士屯田开垦,移民增加,史载“有屯兵者惟湖南、贵州”(12)赵尔巽:《清史稿》卷一三一《兵志二·绿营》,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8页。。第二类是民屯。明清以来,乌江流域一带发生了播州叛乱、“三藩之乱”等几次重要战争,及至清末,战争造成的人口流失及其对社会发展的阻碍,再加上乌江流域地区资源丰富,吸引了诸多流域以外的人口前来,移民来此的人口数量迅速增长。为缓解资源分配和民众生计等社会矛盾,清朝政府对乌江流域施行募民开荒的策略,客观上也加快了乌江流域民族地区移民人口的增长,特别是汉族移民数量有所扩大。乾隆时,乌江流域中上游的黔西州已有“汉庄”246 处,计28669户、124325口;苗寨仅有209处,计11223户、45263口,附居苗寨的客民有1019户、5260口。(13)爱必达:《黔南识略》卷二十五《黔西州》,清道光二十七年( 1847)重刻本。第三类是客商侨居者。明清以来的手工业经济带来了“商贾”繁荣,乌江流域成为客商侨居的集中地之一。以黔东北的松桃厅为例,由于该地区贸易发达,使得四川、湖北、江西等地的商人落居于此,“年久便为土著”。(14)爱必达:《黔南识略》卷二十《松桃直隶同知》,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 重刻本。位于黔西的威宁州地区,由于铜、铅等矿产资源丰富,引得诸多客民来此务工,造成“汉人多江南、湖广、江西、四川等处流寓”(15)爱必达:《黔南识略》卷二十六《威宁州》,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 重刻本。的侨居景象。其它如乌江流域下游的酉阳州一带,也随着客商侨居者的涌入,当地土著居民已经较少,多数成为贵州、湖北等客民的聚居地,“五方杂处”(16)王鳞飞:《(同治) 增修酉阳直隶州总志》卷十九《风俗志》,清同治三年(1864) 刻本。是这一时期各民族杂居的状态。第四类是官宦子弟。即各个时期赴乌江流域上任的各类流官及其家眷相关人等。据统计,乌江流域仅贵州地区省级文职官员即有567人,(17)刘显世等:《贵州通志·职官表四》,民国三十七年(1948)铅印本,流官等带来的客观影响是教育的兴起与文化的交流。最后一类是流民,即那些因各种原因自发迁居于乌江流域民族地区的移民成员,如流落、犯罪、逃荒等各类人员。数据显示,清初全国人口6千余万,到清末为3亿6千多万,增长6倍;而流域之中仅贵州一省人口则从清初的50~60万增加到清末的870余万,为原来的14倍。(18)李振刚等:《贵州六百年经济史》,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81页。各种类型的移民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移居地区的民族关系产生复杂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促进乌江流域汉族与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往。外来移民不仅极大地增加了当地的劳动力,而且带来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多种农作物,从而促进乌江流域民族地区农业经济的发展。据统计,明清以来乌江流域中的一些地区已广泛使用水磨和铁犁等先进农具,逐渐使用汉族地区流行的育秧插田法。(19)张世友:《清代乌江流域的移民活动及其对民族关系的影响》,载《重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从商业经济角度看,客商移民为乌江流域商贸经济的繁荣作出了积极贡献。有清一代乌江流域中游的遵义地区早有贩卖棉织的贸易现象,并且以遵义为中心,形成了一套完整成熟的生产加工贸易流程。商业的繁荣促进了民族间经济的友好交流,为文化的交流创造了条件。正是在诸如民屯、客商等移民的推动下,民族交往才愈发频繁,从而形成“共同体意识”的环境。当然,大量移民的涌入也增强了这一地区人民谋取生存发展中的竞争力,各民族之间因为争夺生存与发展所需的社会、自然资源,不可避免地产生地方民族矛盾,甚至引发大规模械斗,影响到当地各民族之间和谐关系的建构。但总体而言,移民对乌江流域地区的民族关系的影响是利大于弊。
移民涌入促进并丰富了乌江流域社会发展的同时,中央王朝还在此地推行文化教育策略,提高了各民族成员的文化素质,加快了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与交融,对这一地区的民族关系产生了深远影响,为后来推行改土归流创造了条件。明清时期这一地区主要存在着官学、书院、社学、私塾等教育机构。官学是受汉族地区教育模式影响,教育机构和教官设置都与汉族密切相关,施教者多是受中原文化影响的知识分子,使用的教材多以中原王朝的经典为主,教学以汉语、汉字为主。以明代土司时期的贵州为例,明代乌江流域设立官学37所……位于乌江流域民族地区的州县中,只有普定、余庆、瓮安等九县未设儒学。(20)李良品:《乌江流域民族地区明代学校教育的发展、特点与深远影响》,载《重庆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建在这一地区的书院较多,比较著名的俗称“贵阳三书院”的贵山书院、正习书院和正本书院。清代以来,贵州书院分布较为集中的有:黎平府20所,遵义府15所,贵阳14所,思南府12所,大定府11所,安顺府11所,镇远府11所,兴义府10所和都匀府10所。(21)刘显世等:《贵州通志·学校志三》,民国三十七年(1948)铅印本。其中黎平府、遵义府、大定府、镇远府等都是土司辖制的民族聚居区。在乌江流域中下游地区,主要是今渝东南一带,第一家书院由彭水知县朱雷创于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一直到清末已有15所书院分布在不同的州县。(22)崔莉等:《乌江下游民族地区清代书院的管理》,载《涪陵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6期。社学是兴起于元、明、清时期的启蒙教育模式,社学为各民族成员的基础教育奠定了基础。明代中央王朝为达到“变夷俗,敷教化”的宗旨,明确要求乌江流域民族地区的土司土目们必须在当地创办社学,向广大少数民族民众施教,社学施教的内容主要是教劝农桑,读汉学经典,促进了汉文化在当地的传播。弘治十八年 (1505年),位于乌江流域中游的贵阳各地已经设置24处社学,受教育儿童已有700多人;雍正八年(1730年)起,清政府开始在苗疆地区大量开设义学,施秉、安顺和永丰等地都有办学记载。(23)方铁:《西南通史》,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485页。私塾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私人教育模式,乌江流域一带亦有开办私塾的现象。如毕节县撒拉溪镇顾氏就曾在龙井创办私塾,收徒教礼,亦有康熙时贵州毕节人罗英任清平县训导,晚年于家授学的情形。(24)刘显世等:《贵州通志·人物志五》,民国三十七年(1948)铅印本。
文化教育既是文化得以突破时空限制实现代际传递和空间扩布的重要手段,也是实现人类共享智慧发展成果的重要渠道,还是促进不同人群之间借以相互了解、认识并建构相互关系的重要方式。明清时期乌江流域各种形式的教育发展,促进了中原文化在这一地区的传播和影响,丰富并提高了这一地区各民族的文化知识与素质,增强了这一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技术力量,增进了乌江流域各民族与中原及其他经济文化发展水平较高地区人民的相互了解,进一步密切了不同地区人们彼此之间相互依赖的关系,对于增强乌江流域各民族的国家认同和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成员的意识发挥了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