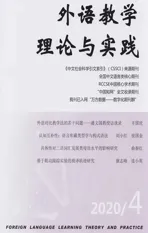大学英语教师实践性知识构建:一项自我研究*
2020-12-14孙钦美
张 惠 孙钦美
青岛大学公共外语教育学院 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提 要: 本文以“可能自我”为理论视角,运用自我研究法探究一名大学英语教师实践性知识构建特征以及自我认知对构建过程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1) 该教师实践性知识的构建呈现内容上的阶段性侧重和路径上的合作学习倾向;2) 缩减“希望成为的自我”和现实自我的差距并远离“害怕成为的自我”是教师构建实践性知识的动机,教师在各阶段为弥合现有实践性知识与“希望成为的教师”所需知识之间的差异而进行的实践是其知识构建的重要手段。
1. 引言
教师实践性知识作为教师专业发展的主要知识基础(陈向明,2003),是国内外教师知识研究的一个重要取向。Elbaz(1981)率先提出“实践性知识”这一概念,认为它是根植于个体内心和外在体验的动态知识。Clandinin(1985)提出教师“个人实践性知识”的概念,并运用叙事法对其展开研究。此后,该领域的研究日益细化,内容涉及学科教学(Meijer et al., 1999)、教师身份认同(Beijaard et al., 2000)、课堂管理(Tartwijk et al., 2009)、实习教师实践性知识的构建(Leijen et al., 2015)等。
在我国,教师实践性知识研究(陈向明,2003;陈向明等,2011;姜美玲,2009;魏戈、陈向明,2017)经历了从理论构建到实证研究的过程,内容涉及其概念和生成途径等。其中,陈向明等(2011:77)在前人研究(Elbaz, 1981; Meijer et al., 1999)的基础上,结合本土研究提出教师实践性知识的内容。本文借鉴该分类方法,即教师实践性知识包括关于科目、学生、自我和教育情境四方面知识,其中关于科目的知识又包括学科知识、课程知识和学科教学知识等,关于自我的知识包括自我认同和自我效能感等。
在高等外语教育领域,研究者多借鉴国内外理论框架,探究外语教师实践性知识的内涵和特点(王艳,2011;徐锦芬等,2014;赵晓光、马云鹏,2015)、生成途径(吴鹏,2011;谢佩纭、邹为诚,2015;杨维嘉,2016)、具体学科教学(张庆华,2015)等。其中,王艳(2011)探究了两名优秀外语教师实践性知识的内涵、特征、影响因素。徐锦芬等(2014)研究了三名优秀教师构建个人实践性知识时呈现的实践性、反思性、互动性等特点以及个人因素和社会语境对构建过程的影响。这些学者的研究思路、方法和发现为相关研究提供了十分有益的借鉴。
上述研究就内容而言,对教师实践性知识的动态发展过程关注不足。就视角而言,对影响因素的探讨较少聚焦心理学视角,挖掘教师自我认知的作用。自我认知即个体对“自我”的知识,其中与未来自我相关的知识也被称为可能自我。Markus & Nurius(1986)认为它包括个体未来渴望成为的理想自我、能够成为的自我和害怕成为的自我,它的形成受到个体所在的社会文化背景和社会经历等的影响,会影响到个体对未来行为的选择。可能自我理论已成为当前国外教师研究的新焦点,但在国内外语教师研究领域尚无应用(徐锦芬、文灵玲,2013)。就方法而言,这些研究多为研究者对他人的探究,鲜有研究者的自我研究,而自我研究可以帮助研究者走入自己的内心世界,“获取关于自身教学的内隐知识”(萨马拉斯,2015:iii)。但当前国内相关研究以理论介绍(如荀渊,2012;范晓慧、朱志勇,2015)为主,实证研究相对匮乏。鉴于此,本文以可能自我为理论视角,采用自我研究法探讨“我”在17年教学生涯中实践性知识构建的特征并挖掘自我认知对整体构建过程的影响,以期对大学英语教师特别是中青年英语教师深入理解教师学习、科学规划个人职业发展以及教师教育研究者有所启发。
2. 研究设计
自我研究作为教师专业发展的方式之一,本质上是有关教师个人和专业成长的自传式叙事(Bullough & Pinnegar, 2001),其独特优势在于教师个人的声音可以被听到(Zeichner, 1999)。依据萨马拉斯(2015),自我研究是通过个人情境化探究和批判性协同探究,在透明、系统化的研究过程中,提高学识,实现知识生产与陈述。研究者“我”既是研究工具,又是研究对象。需要强调的是,自我研究是“我”与合作研究者——“诤友”(critical friends)的协同探究。诤友的质疑和评审帮助“我”清晰阐释该研究、获得不同视角、提高研究的透明度和可信度。通过自我研究,研究者能够系统地评估、重构教学实践,增进教学知识,提升自我效能感,推动教师可持续发展。
1) 研究问题
自我研究者“我”旨在通过个人生活史,反思、审视、建构和重构教师职业身份;该过程中,逐渐聚焦两个研究问题:
(1) 教师实践性知识构建具有怎样的特征?
(2) 自我认知如何影响教师实践性知识的构建?
2) 研究参与者
本研究的参与者包括自我研究者“我”和合作研究者向阳。
“我”2000年研究生毕业后成为大学英语教师。教学中,除了短暂的职业倦怠外,我一直尽心尽责,尝试通过丰富授课内容、改变教学策略等方式提高课堂教学质量,但学生评价和自我效能感时高时低;科研上,我经历了从逃避到接受再到教研结合的过程。我的经历在大学英语教师中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向阳2006年研究生毕业后就职于上海某高校,任专职英语教师;2012—2016年分别在中美两国(国家留学基金委“联合培养”博士)接受较为系统的科研训练,方向为教育语言学和教师教育,具有独立思考和批判思维的习惯。
“我”和向阳在第四届全国外语教师教育与发展专题研讨会上认识,对自我研究和教师专业成长的共同关注促成我们之间的坦诚交流和通力合作。
3) 研究环节
依据自我研究的准则(萨马拉斯,2015),本研究经历以下环节:(1) 自我研究者整理并反复阅读个人日记、教学反思日志、学生问卷、读书笔记等原始资料,围绕实践性知识发展撰写个人生活史(Cole & Knowles, 2001),形成研究文本;合作研究者阅读该文本,并对自我研究者进行电话访谈,澄清实践性知识构建过程中的“关键事件”和“重要他人”(Tripp,1994)。(2) 自我研究者运用主题分析法,依据实践性知识的内容框架(陈向明,2011)对文本信息编码、归类,初步回答研究问题。其中,“科目”、“学生”、“自我”和“教育情境”为一级类属;学科知识、课程知识、学科教学知识为“科目”的二级类属。(3) 合作研究者使用故事分析法(Barkhuizen, 2016),以人物——时间——地点和事件——方式——原因为维度,逐句阅读并依据上述主题系统地分析文本,对初步研究发现提出质疑和建议。(4) “我”获取不同视角后,丰富或重构之前的分析,例如,技术要素是在诤友建议下进入“我”的分析视野(以下图片截自微信和文章批注)。与诤友的批判性协同探究主要通过微信和电子邮件实现。研究共生成1000多条微信短消息和92封邮件。

图1. 第一作者与诤友的批判性协同探究示例
3. 教师生活史
下文以时间为序简述我从教17年的经历。其间,个人专业成长虽无明晰的分水岭,但依据教学理念变化和心路历程大致分为四个阶段:“个体经验为中心”的混沌教学、“以学生为中心”的技巧教学、自我危机侵扰的“懈怠”教学以及自我认同增强的自主教学和研究。
第一阶段:“个体经验为中心”的混沌教学(2000—2002)
我1997年本科毕业,专业为英语教育;2000年研究生毕业,专业为翻译理论与实践;工作后,主讲大学英语阅读和听力。本科期间心理学、教育学、英语教学法等课程均以理论知识为主,大四的实习经历早已淡忘;研究生期间虽教过英语阅读,可忙于学习和论文,对教学并无深入思考。所以刚工作时,除了词汇、句法、文化等学科知识和短暂的授课经历,我茫然无着。备课主要参照自己精读老师和一名英语考级培训名师的课堂以及四级题型,着眼于详细讲解教材中的词汇、长难句和文章结构。除了提问,基本没有其他课堂活动。但学生似乎接受这样的方法,给我很高的评教分数。
其间印象最深的事件是由于学生不分succeed,success和successful的词性,我在课上第一次大发脾气,批评他们的学习态度。后来发现类似错误比比皆是,我才开始有意识地引导学生关注词性。
本阶段,作为新手教师,我主要通过学徒式观察(Lortie, 1975)和考试要求构建课堂。这种依据个人学习体验、培训课堂和应试需求建立的教学模式,注重将学科知识转化为以教材为基础、以课程大纲和个人语言学习观为指导的课程知识。但由于缺乏对学科教学知识及学生知识的了解,我更关注“自己能够传授什么”,而非“学生能接受多少”,因此难以理解他们的学习困难。
第二阶段:“以学生为中心”的技巧教学(2003—2008)
为解答教学困惑,我开始关注《英语教学面面观》(AspectsofLanguageTeaching)等专业书籍。“以学生为中心”、“聚焦意义”、“交际教学法”等教学理念随之进入视野,我当时对这些思想全盘接受,因为它们似乎正是解决备受社会诟病的“哑巴英语”的“对症良药”。
在这些理念的影响下,我尝试通过阅读《怎样教英语》(HowtoTeachEnglish)等著作改变教学方法、培养学生的语言运用能力。其中印象最深的是开展协商课程实验。Nunan(2001:13, 16)指出,在选择教学任务和活动时,教师与学生存在明显差异,提议由师生“讨论和妥协”共同决定教学内容和方法。我认为这可以解决学生课堂参与度低的问题,于是展开围绕学生兴趣选取教学内容、以课堂讨论和展示为主的教学改革。试验中我逐渐摸索出在大班开展交际性教学的思路。尽管获得多数学生的认可,仍有学生认为“活动浪费时间”、“对考四级没有用”。对于这些负面反馈,我认为是学生“功利心太强”,但也开始质疑“以学生为中心”和“聚焦意义”是否在我国水土不服。
本阶段,教学中的问题促使我阅读文献,希望追随先进的教学理念,找到“放之四海皆准”的教学技巧。实践表明,我积累了较为丰富的学科教学知识和学生知识,并形成一定的教学常规,但理论基础薄弱,文献阅读流于“拿来主义”,教学实验也浅尝辄止,因此教学常规难以融会贯通,教学水平的提高进入瓶颈期;此外,有些学生对教学实验做出负面评价,评教结果有时甚至不如传统课堂。这些因素形成合力,不断冲击着我正在形成的教学信念。
第三阶段:自我危机侵扰的“懈怠”教学(2009—2012)
随着教龄增长,我积累起一定量的教学资源和经验,但教学热情越来越低。我意识到:作为外语教师,我的语言功底并不十分扎实,也缺少对英语文化的切身体验,回答学生问题有时底气不足;教学法知识缺乏系统性,应用时难以融会贯通。更重要的是,随着年龄增长,一直逃避的职称问题日益凸显,而我缺少科研成果。与此同时,如火如荼的大学英语教学改革让我倍感焦虑,“会不会因为学时减少而无课可上?ESP蓬勃发展,而我缺少专业知识,ESP的方向在哪里?”我开始怀疑自己在未来做老师的可能和能力。这时同事陆续考博,而我的生活似乎陷入僵局,我问自己“未来一眼可见,这样的人生意义何在?”
在这种情绪下,我无心寻求教学技巧,只是根据学生的课堂表现从积累的教学资源中“剪切复制粘贴”,课堂上“相机而用”。以前备课的时间则留给英文小说和报刊,偶尔也浏览教学文献。回顾这段时间,我的课堂似乎并未受太大影响,因为英文阅读丰富了教学内容、提升了教学语言质量,从而增强了我的教学自信;文献阅读中关于职业倦怠的研究则缓解了我的焦虑。一定程度上,正是这个“懈怠”期提醒我“影响教学效果的因素多元,教学技巧不是万能钥匙”。
本阶段,我并未刻意构建实践性知识,但选择并“相机而用”教学资源的过程丰富了教学情境知识和学生知识。阅读英文小说和文献则增长了学科知识和教师自我(主要是有关情绪)知识。就教师专业成长而言,这是一个自我怀疑的阶段,也是一个沉淀思考期。放下对教学技巧的追逐,进入自我否定,是关注点从外在转向内心的转折阶段,也是自我意识的萌发阶段。
第四阶段:自我认同增强的自主教学和研究(2013至今)
我有意识地思考自我是在一次教学比赛后。比较一等奖获得者,我认为缺少激情或许正是自己课堂沉闷的原因,于是尝试模仿她的风格,几节课后“总觉得站在讲台上的不是自己……教学似乎走入死胡同”。一天浏览微信时,有公众号推荐《教学勇气——漫步教师心灵》。当我读到“教学不论好坏都发自内心世界……就优秀教学而言,认识自我与认识其学生和学科是同等重要的……事实上,认识学生和学科主要依赖于关于自我的知识”(帕尔默,2005:3)时,“我忽然明白自己之所以纠结于教学技巧,甚至盲目模仿他人,正是因为缺乏清晰的自我认识”(第一作者教学日志)。
我开始梳理自我认识,并认识到“自己缺少激情,但课堂内容逻辑清晰;亲和力不足,但对学生耐心包容……”(第一作者教学日志)。日渐清晰的自我认识促使我重新审视自己在教学中的角色并理性看待与学生的关系。此外,我问自己“到底想成为和不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并逐渐找到答案:我希望成为一名不纠结短期现实利益、实践终身学习的学者型教师。这样的明确定位缓减了我挟裹于教学改革、职称评定等洪流中产生的焦虑感。与此同时,学校对教师的科研要求愈来愈高,院领导努力营造科研氛围,鼓励我们教研结合。内外力交互影响下,我开始参加各类教学和科研活动,如研修班和学术会议等。
2015年,我参加了Bonny Norton以“身份认同”为主题的研修班。除讲座内容外,她的研究经历对我触动颇深:“成长需要方向。Norton教授数年如一日潜心研究,而我却盲目追随热点。我应该回到自己搁置的研究方向:教师身份认同,像教授那样认真准备会议论文”。2016年,我第一次通过提交论文摘要参加学术会议,发言得到大家的共鸣和鼓励,不仅收获了自我认同感,还认识许多同行,并与向阳成为合作研究者。
本阶段,实践性知识的构建主要体现于通过文献阅读、自我反思和同行交流而不断形成的自我认识。自我认识看似与教学无关,但它是我对未来期许的基石,这份期许促使我为教学和科研投入更多精力:MOOC出现后,我参加了学院的在线课程建设,课程负责人对我工作的肯定进一步增强我的自信和学习热情。之后,我自费学习“外语教学理念与实践”等多门在线课程。这些课程促使我教研并行,并于2017年春开设公选课《新闻英语视听说》(学生评教进入全校课程前30%,以其为基础,获批校级项目),在教学中提升了以“整合技术的学科教学知识”为核心的实践性知识。(1)“整合技术的学科教学知识”指信息化时代下,教师运用技术进行教学的知识,其特点是高度整合学科内容、教学法知识和技术知识(Mishra & Koehler,2006)。
4. 发现与讨论
1) 中青年大学英语教师实践性知识构建特征
梳理自我研究者的专业成长经历,可以看出其实践性知识构建在内容和路径上分别呈现以下特征。
(1) 内容上呈现阶段性侧重
文本显示,“我”在不同的职业阶段对实践性知识内容的关注点不同。
入职初期,实践性知识的构建主要表现为从学习时期积累的学科知识向课程知识转化,尤其是细化和选择教学内容。在基本把握课程知识后,关注点转向明晰教学信念、提升学科教学知识和增进学生知识,其中教学技巧是重点。当学科教学知识的积累难以提高教学效果时,“我”进入职业发展瓶颈,进而受困于职业倦怠,甚至产生自我危机。这一时期是教师发展的转折期。如果无法以积极的态度应对危机,职业生涯可能就此停滞,导致“未来一眼可见”;反之则可能从不同角度构建实践性知识,如“我”虽然“懈怠”于技巧探究,但并未真正放弃行动,而是在不自觉中转向情境知识和学科知识,并萌发自我意识。对自我的内省引领“我”重新评估自己,形成并不断更新自我概念,进入下一阶段。此时,相对全面的自我认识促使“我”平衡工作环境的限制和教师的自我需求,形成积极的自我认同,进而增强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的意愿,并采取行动拓展学科教学知识等实践性知识,促成教师专业发展的良性循环。在此,需要强调的是,由于信息技术在高校外语教学中广泛应用,我们将学科教学知识定义为“整合技术的学科教学知识”(Mishra & Koehler, 2006)。
纵观上述阶段性特点可以看出,虽然“我”在科目、学生、自我、教育情境等方面的知识在不同时期都得到提升,但呈现出聚焦教学——关注自我——回归教学、教研一体的趋势。这一构建历程很大程度上契合于Richards(2016)提出的语言教师成长四阶段:知识丰富、技能全面的基础阶段;认同自我、关注学生的进阶阶段;寻求同伴、创造理论的飞跃阶段;成为专业人才的终极阶段。不同的是,后者是一个线性过程,是语言教师专业成长的理想路径,并未涉及教师职业倦怠等可能的问题。同时也有必要指出,“实践性知识的生成和发展是一个个体与环境、实践与理论之间不断交互、相互推动的过程”(陈向明,2011:232),不同的教育教学经历、工作环境、社会语境以及个人对理论的不同理解和践行都决定了大学英语教师实践性知识的构建具有较为鲜明的个性化特征。
(2) 路径上呈现个体学习向合作学习的转向
教师实践性知识的增长是教师学习研究的主要关注点,也是教师学习的结果(崔琳琳,2013)。故事中“我”在构建实践性知识的过程中,采取的学习途径主要包括:学徒式观察、自我反思、文献阅读、教学实践、师生交流、同事交流、网络课程、校外同行交流(如学术会议)等。纵观“我”在职业生涯中不同阶段的实践可知,在自我反思的促动下,实践性知识的构建途径不断丰富,整体路径上呈现从个体学习向合作学习的转向。
入职初期,与自我的互动是“我”构建实践性知识的主要途径,即调动自身学习经历和学徒式观察。该途径无法解决教学中多元复杂的问题时,“我”转向文献阅读,从而建立概念上的教学知识资源库。在文献与课堂教学的影响下,“我”日益注重师生互动,逐步构建实践性知识。随着个人教学理论的丰富,“我”逐渐建立起教学自信,开始与同事积极互动,如参加教学团队建设在线课程等。之后,提升自我的需求促使我自主参加线上、线下培训和各类学术会议、与校际同行积极互动,进一步扩大了实践共同体的范围。这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孙钦美和郑新民(2015)有关教师个性化学习共同体构建的发现,同时,也呼应了Louws et al. (2017)的研究结果,即教师在不同职业阶段的学习方式不同。但就学习途径的阶段性差异而言,“我”的历程与他的发现不同。在“我”17年职业生涯中,如果按发展特征划分,早中期(前三个阶段)倾向于文献阅读,后期(第四阶段)才重视培训。Louws et al. (2017)比较处于职业生涯的早期、中后期的教师后,发现前者更愿意采用教学实验,但职龄不影响对培训和阅读文献的运用。上述差异一方面反映教师实践性知识构建途径的个体性差异,另一方面也充分表明教师实践性知识的构建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自我调节型学习。该过程中,教师作为学习者在学习认知观、经验和客观环境等因素的交互影响下,能够依据自身需求和实际情况设定个人目标并自主地选择学习途径(Louws et al., 2017),并通过自我和外在评价调整目标和策略。这种对目标、行为的自主权可以给教师带来满足感和自我效能感,成为教师构建实践性知识、实现自主发展的内在动机,促进教师自我反思、自我研究,进而促成实践性知识构建的良性循环。
2) 自我认知对教师实践性知识构建的影响
上述“聚焦教学——关注自我——回归教学、教研一体”的职业发展历程和个体学习到合作学习的转向表明,教师实践性知识构建受到国家教育政策、课程标准、学校及院系环境、学生需求等外在因素和个人经历、自我认知、教育信念、自我反思等内在因素的影响。Knowles et al. (2005:68)指出成人学习最有力的动机是内在压力(如提升工作满意感、自尊、生活质量等),本节重点探讨可能自我理论框架下,教师的自我认知如何与上述外因相交织,对实践性知识构建产生影响。
本文中的可能自我借鉴了Markus & Nurius(1986)的观点,但是将它依据个体发展的方向概括为两类:一类是“希望成为的自我”,因为对个体而言,“未来渴望成为的理想自我” 和 “能够成为的自我”都属于正向发展,是个体对于未来自我的期许;另一类是“害怕成为的自我”。可能自我将个体目标与行为相互衔接,具有明确的动机功能,关系到个体如何选择未来的行为(Markus & Nurius, 1986)。由此,我们认为弥补“希望成为的自我”与现实自我的差异、远离“害怕成为的自我”是教师发挥能动性采取行动构建实践性知识的主要动力。
可能自我的社会性和个体性决定教师“希望成为的自我”受到国家政策、学校和院系环境、学术职业标准、学科成果、学生期待、同事表现、个人经历和信念的影响。故事中,这些因素交互作用,共同影响着“我”可能自我的构建,即“我”希望成为什么样的教师和害怕成为什么样的教师,进而辐射到实践性知识内容的构建。
具体而言,任职初期“我”以他人的课堂为规范,希望成为教学内容明确、丰富的老师,实践性知识构建因此侧重学科知识向课程知识的转化。之后,在文献理念和学生反馈的影响下,“我”希望成为提高学生语言运用能力的老师,实践性知识的构建转向教学信念、学科教学知识和学生知识等。随后,在自我发展陷入困境后,“我”担心成为无力胜任工作、失去职业成就感的老师。为了远离“害怕成为的自我”,“我”本能地转向自我充实,通过阅读丰富学科知识。之后,通过阅读文献和反思形成新的“希望的可能自我”,即成为获得自我认同、教研融合的教师。对“希望成为的自我”的追求和对“害怕成为的自我”的回避促使“我”通过参加课程团队、学术会议、课程培训、同行交流等途径丰富以自我知识为主,教研结合的实践性知识。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教学实践促使教师反思自己的实践性知识与“希望成为的教师”所需要的知识存在差异,由此产生困惑、职业倦怠、自我认同危机等情感。为消除这些负面情感,提升自我效能感,教师会采取各种途径缩小差异。同时,为远离“害怕成为的自我”,教师也会促使自己采取恰当的行动。简言之,教师对“希望成为的自我”的追求和对“害怕成为的自我”的规避为教师实践性知识的构建提供了动机,同时导致构建内容上的阶段性侧重和建构途径的转向。这与Kubanyiova(2009)的发现一同印证了Oyserman & Markus(1990)的观点——“平衡的可能自我”,即对积极自我的追求和对消极自我的恐惧可以提供双重动力,最大限度地发挥动机作用。
5. 结语
本文运用自我研究法探究一名大学英语教师在17年职业生涯中实践性知识构建的特征和自我认知对这一过程的影响。研究发现,中青年大学英语教师为缩小“希望成为的自我”与现实自我的差异并远离“害怕成为的自我”,通过学徒式观察、自我反思、文献阅读、师生交流、同行交流等多种途径构建实践性知识,整体上具有从个体学习转向合作学习的倾向;内容上则呈现聚焦教学——关注自我——回归教学、教研一体的阶段性侧重。
该发现表明:教师专业发展过程中,教学实践、教师培训、文献阅读、实践共同体都是构建实践性知识的重要途径,但最根本的是教师要打破对权威的简单迷信、突破教学惯性的拘囿,通过教育启蒙实现自我觉醒,转变观念,产生自我发展的动机。各级教育主管部门也要通过政策激发教师的发展需求,创造条件维持教师的发展动机。而教师以自身作为研究资源,也为实现教研一体、实践智慧的生成提供了路径。
需要指出的是,本研究主要语料来源为自我研究者个人日记、教学反思日志,未来研究可通过课堂观察、定时追踪访谈等方式进一步提高研究的客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