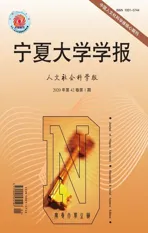元代文人的休闲与闲适心态
2020-12-14王硕
王 硕
(南开大学 文学院,天津 300071)
元代文人的心态是复杂的,蒙古族掌权,他们的内心深处有一种压抑之感。加之社会变动和科举阻断,文人的社会地位急剧下降,似乎在这样的社会中,文人的心态只有苦闷。然而,当我们细读元代诗文与散曲发现并非如此,元代文人反而多在休闲中表现出安闲自适的心理状态。
休闲是人的身心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状态,是不为外物所扰,精神上的悠闲与安逸。休闲是人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休闲作为人的生命的自觉,经历了从生理体能的要求,到生存消费的需求,再到文化精神诉求的过程,即从物质的需要进入精神的需要。生命的自觉既是对生命的关怀,也是对生命的享受;既是对生命自身的一次觉醒,也是对生命意义的一次追求,所以它是一种心之乐,是精神的愉悦和快乐”[1]。元代文人的休闲,更多的是从身的自由到心的清闲舒适。同样是不断获得“精神的愉悦与快乐”。无论是隐居林泉,还是身在朝廷,休闲是大部分文人自觉追求的生活与心理状态。
一 回归自然,心的清闲与安逸
生活在元代的文人,他们不幸的同时也是幸运的。不幸的是他们失去了优越的仕进之路,幸运的是他们仕进之路受阻后,在文学艺术上获得新的发展。历朝皆有文人走进自然,而元人的回归更具彻底性,与“有目的归隐”不同,他们完全沉浸自然之中,体悟山林带给人的清闲与安乐。
山水田园为文人营造了一个隔绝尘世的舒心场所,他们选择自然的生活,从而拥有自然的人生与休闲的心态。查洪德先生提到“元人观念是多元的,元人的生活态度也是多元取向的。就大的时代倾向说,元代文人没有唐代文人那样强烈的功名意识,也没有宋代文人那样沉重的历史使命意识。在元代比较宽松的社会环境中,多数文人愿意自然地活着。”[2]自然地活着,无拘无束,展现自我的真实情感,便拥有自然之人生。什么是自然的人生?如查先生言:“一是真实而不粉饰,二是自适而无拘束”[3]。元代文人这样的人生追求,反映出他们内心的坦然与悠闲。因此,出现众多的“闲适”“清幽”之曲也就不足为奇。张养浩〔双调·落梅引〕“野水明于月,沙鸥闲似云,喜村深地偏人静。带烟霞半山斜照影,都变做满川诗兴”。“入室琴书伴,出门山水围,别人不能够尽皆如意。每日乐陶陶辋川图画里,与安期羡门何异!”[4]清幽的环境引发作诗之兴,所写诗歌也必定是自然悠闲的。“安期”亦称“安期生”,是黄老哲学与仙道文化的传人,“羡门”亦为传说中的仙人,此处之喻,言自身生活在自然之中,与琴书为伴,生活悠闲自在,如“安期”“羡门”这样的仙人一般。自然山水给人带来的内心舒闲,是其他环境所不能相比的。身在自然之中,心欲慢慢释放,心也变得自然,自然的人生是休闲心态的外在体现。
元代文人多以“休”“闲”等相关的语词命名自己的住所。一方面,是标记文人住所,体现文人内在的文化素养;另一方面,也是文人对休闲生活的向往。经历过人世的沧桑,才能懂得清闲的可贵。在不同的记叙文中,也可以看到元人的休闲描写:
近辟山为重屋以眺远,又屋其后,为楹十有八,其位置区画,类隐者所为。括人吴善父名之曰“乐闲山房”。夫天地间,云岚木石,崇丘绝壑,足以发奇潜老,多人迹所不到。故畸人静者,得与世相忘而自乐其乐……饮食滋味之养,而悠闲之适,吟眺之美,一踰足越限而兼有之,可谓乐矣。今君年益老,见益定。虽不绝物,不害为闲且乐。心有外驰,虽闭户坐,不与人世接,乐亦未至。——谢翱《乐闲山房记》[5]
辟山而居,远离尘世,名为“乐闲山房”,能够“与世相忘而自乐其乐”,环境饮食,悠然适之,“为闲且乐”实属难得,闲容易得,但闲中之乐并不是所有人都有,“心有外驰,虽闭户坐,不与人世接,乐亦未至”。只有心内安然,不为外物所动,才能真正做到“闲且乐”。
顺应自然天性而活,不汲汲于荣华,以求心的安闲。有些文人甘愿自“拙”,而不取巧于世。陈旅《拙休堂记》所记,写山水环境清幽,文人生活于此,“吾于其闻以耕、以渔、以读吾书,而遂老于斯矣。盖造物者赋我以拙,不足以有为于世,吾又安能违物以闯闯然于有为者之途?故以拙休名堂”。又言拙与巧相对,世之取巧者可便捷得利,可一旦失足,“忽若飘瓦赴地”,故言“人不能用巧,为巧所用,不至于颠坠不已”[6]。可见,休闲心态也是一种自然而然之适,不必“强为用巧”,本性为拙,便可以拙待世。元代文人深知此理,拙而能朴,便能体现真我之性情,耕、渔与读书,成为悠闲生活的重要内容,不必刻意而为,一切皆出于本心,自然天成。
闲逸需用拙。用拙以藏巧,是人生大智慧。大儒吴澄对此有深刻的认识。他在《拙闲堂记》中言,“人之情莫不耻于拙而慕巧,喜闲而恶劳,是知闲之胜于劳,而不知拙之胜于巧也。巧于利者营营于货殖,巧于名者汲汲于权要……自少至老,虽欲求斯须顷刻之闲,而不可得。无他,巧累之也。拙则不如是矣……故夫世所谓拙者,往往非真拙也。或以拙用其巧,或以拙藏其巧。如是而拙,巧之尤者也。”[7]另外,他在《拙逸斋庐记》中又提到,拙与巧为君子与小人不同的选择,“君子廉于取名,啬于取利,似若拙矣;要其终,则有福无祸,安安无危,未尝拙也。小人巧图爵禄,巧贪货赂,似若巧矣;计其后,则人祸立见,天刑徐及,巧固如是乎?……享逸之实,逸则真逸矣,拙非真拙也。”[8]拙与巧似非为真正之拙与巧,拙者反而能够静享清闲,不为“巧之为累”而“营营于货殖”。君子能够明理,拙而能逸,享受安闲之乐。小人则不能体会其中奥妙,“巧图爵禄,巧贪货赂”而后“天刑徐及”,拙与巧的结果显而易见。元代文人宁愿为“拙”,不求名利,看似为时人所笑,但日后便会懂得,“拙”才能获得身的安闲与心的愉悦。
另一方面,拙也是对自然的喜爱,在元曲中有所体现。元曲家闲居林泉,尽享山水田园之乐。张可久〔双调·折桂令〕《村庵即事》云:“掩柴门啸傲烟霞,隐隐林峦,小小仙家。楼外白云,窗前翠竹,井底朱砂。五亩宅无人种瓜,一村庵有客分茶。春色无多,开到蔷薇,落尽梨花。”[9]小村茅舍,环境清雅,融入自然之中,林峦、白云、翠竹一切都是那样悠闲,山间林下成为闲居的好去处。“选知音,日相寻,山间林下官无禁。闲后读书困后吟,醉时睡足醒时饮,不狂图甚”(吴弘道〔双调·拨不断〕《闲乐》)[10]。闲中可适意读书,读书没有功利目的,生活自然随性,饮醉后便可大睡,醒后接着饮酒,完全按自己喜欢的方式生活。值得注意的是,元曲中常提到“红日三竿未起”,人只有在身心自由,无烦事叨扰的情况下才能舒心酣睡。吕止庵〔商调·集贤宾〕《逍遥乐》云“有何拘系,则不如一枕安然,直睡到红日三竿未起。乐吾心诗酒琴棋,守团圆稚子山妻。富贵功名身外礼,懒营求免受驱驰。则不如放怀遣兴,悦性怡情,展眼舒眉。”[11]安然而睡,诗酒琴棋,愉悦性情,放怀遣兴,这一切都是从自然中来,让身心获得清闲与安逸。酣睡只是身心自由舒适的外化,山水田园给人清闲之感,回归自然是元代文人共同的心理选择。
二 不与物竞,心闲自适
人皆知清闲之难得,亲近自然,无利欲驱使,才能心闲。但更为重要的是真正做到不与物争,追求内心的适然。因此,无论身处何地,让自己保持“心闲”,才能获得精神上的自由与安适。
身在官场,内心淡然,亦可有安闲之乐。元代文人仕进机会减少,但在他们的观念中,即便为官也可拥有清闲,关键就是为官者的内心能否安然行事。吴澄在《乐闲堂记》中指出,“夫心所快悦之谓乐,身得暇逸之谓闲。而世之人但以不在位、不任事为闲者,其义未该遍也……孰不谓公虽在官,而不忘在野之乐也?”身在官,而心在野,同样能有在野之乐。又进一步提出“予独以为闲之义非专指隐退而言,何也?闲也者,安安不劳力也,绰绰有余裕也。隐退固闲,仕进亦闲也。处繁剧而优优简易,应纷纠而秩秩修理,非闲乎?邵子云‘虽忙意自闲,’此之谓也。”身忙意闲,处繁居简,仕进同样可有闲。有闲后便可有闲之乐,“无时而不闲,则无时而不乐,岂必隐退不仕,然后为闲而可乐哉?仕可也,止可也,仕、止不同,而闲一也。”[12]隐退之闲众人皆知,仕进之闲便很难得。理学家吴澄不仅为自己做官找到合理的解释,同时成为大部分文人共同的心理期待。为官亦可有闲,闲之乐在自身,在于心之不争。但进入官场,真能如此的人是很少的,官场之利诱远比山林中多,真正做到居官有闲,守住内心的安适,确实难能可贵。
隐退有闲,如鱼得水,乐在其中。有关归“隐”之大小,前人有“小隐隐于野,大隐隐于市”之说,元人对此也有不同观点。身在朝市同样有隐者,李庭《林泉归隐图序》云:“朝亦可隐,市亦可隐,隐初在我,不在于物。子但专心致志,益治子之术,浮湛闾里,潜心积德,不求声名,固不害其为隐也。又何必高谢人间,窜伏岩壑,亲鱼禽而友麋鹿,然后为隐哉!”[13]隐之心在于自我,不必非要隐居深山之中。方回在《隐乐堂诗序》中也指出:“所谓小隐者,谓身在山林而未能无意于斯世,索水北之高阶,指终南之捷径,其隐小矣。其所谓大隐者,谓身在朝市而不敢萌穹爵厚禄之心。”[14]小隐者求“终南捷径”是有求名之心,而在朝市者有不为利禄所诱,泰然处之,是可为大隐。若有利欲之心,即便身在高林,亦不必为隐也。文坛盟主元好问在《市隐斋记》中指出:“前人所以有大小隐之辩者,谓初机之士,信道未笃,不见可欲,使心不乱,故以山林为小隐。能定能应,不为物诱,出处一致,喧寂两忘,故以朝市为大隐耳。以予观之,小隐于山林则容或有之;而在朝市者未必皆大隐也。”[15]元人的不同观点,体现出对于“隐”的不同态度。大小隐之辩,可以看出元代归隐盛行,但对于归隐方式却存有分歧。那么,这种大隐、小隐的争论与元人的休闲有何关系?我们在元人这种争论中可以看出,真正之归隐不在身而在于心。无论大隐小隐,在官在野,只要内心安然,便可享有清闲,这种心闲也是一种精神上的自由,不受外物拘束。在元人看来,所谓“大隐”“小隐”之辩,可以由心是否“闲”来剖判。
视富贵如浮云,不慕名利,得闲中真趣。名利富贵使人劳累,争逐不断,会失去本心。只有内心淡然,才能拥有清闲,体会生命之真趣。杨维桢在《廛隐志》中提出:“名之所争者朝也,利之所争者廛也。名争而祸必至,利争而害必生。居朝与廛者,能以不争处之,则虽一日九迁,祸无得而至,一货百倍,害无得而生也。况又脱去其所争者耶?若是者,非古德君子居之不能也。”[16]名利本身并无祸患,主要在于如何对待它,以“不争处之”,虽“一日九迁”“一货百倍”也可无祸而安。对于富贵不必过分看重,如朱善在《怡云诗集序》中所云:“夫以浮云视富贵,则千金之重犹敝帚也,万乘之尊犹敝屣也。荣辱不足以累其心,得丧不足以乱其志,终日吟哦,惟白云之为侣。”[17]荣辱不累人心,白云相伴,心领神会,是可得天然之趣。
不与物争,自适而为,得隐中之乐。释来复《云牧山房记》云:“凡物,无心则无竞,无竞则无仇。物即无心矣,人岂独留意于物哉?盖物以无心而应,我以无心而遇,此其牧之善者欤?”[18]以无心而处世,外物之无心与人之无心相和。朱右在《清华樵隐记》中也提到,“然其心则澹然不为声利之移,泊然不为荣禄之累,而托意于山樵野牧之归。其迹若出,而心实隐也。”[19]抛开声利荣禄,心则澹然,才能算为“心隐”,天下隐者众矣,“惟无所系累于名迹者,能充其隐之至。”[20]只有这种真隐才能有心闲,文人处闲,居而乐之,乐有真假之分,“天下无真乐,随所遇而得者乃真乐也。”[21]这种真乐,才是闲中真趣。既然已有空闲,在这空闲中文人所为同样以自适为主,王袆《云林小隐记》云:“于是吾居焉而乐之。朝出耕,夜归读古人书,或钓或游,以适吾适。”[22]这种自适的人生,建立在休闲心态之上,隐居为休闲提供便利,心的放松与坦然又帮助人有安适之趣。隐居的真正乐趣,也就成为休闲给人的自适之感,“诚能得夫隐居之趣,是与造物者游,逍遥乎尘埃之外,仿徨乎山水之滨,功名富贵何曾足以动其心哉?”[23]可见,这种逍遥之趣,要有不恋富贵之心才能获得。元人明白富贵只能带来灾祸,都不如以休闲之心处世,简单而快乐的生活,心闲而外物不扰,安然度过一生。
三 绘画自娱,适意抒怀
元代的“文人画”达到高潮,与唐、宋繁密工整之技巧相比,元人绘画一大特点即为“尚意”。元代的绘画、赏画活动,需要两个方面的条件,一是有一定的物质基础与闲暇时间,二是要有一定的兴趣与休闲心态。元代文人以画写心,直抒胸臆,自娱性情,他们在山水画中塑造出“世外桃源”,构建想象中安闲适意的休闲空间。
元画在宋画的基础上继续发展,从注重写实到崇尚意趣。宋代流行“院体画”,多为宫中职业画家所为,绘画技巧成熟,注重写实,描摹物态极其逼真,但他们主要是为宫廷服务,难以表现个人情感。元代业余画家成为文坛主流,创作风格与品位发生转变,“将创作演变为个人抒怀明志的手段,所以缘心立意、以情结境、讲究笔情墨韵、去除刻画之习便成为元代绘画的重要的创作倾向”[24]。元人绘画极其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够自由表达真正的自我,而这一点是由元代社会所决定的。“元代乃是失去了艺术‘监护人’的时代,尤其是当创作不再是直接的求取仕进的手段时,或者说大多数文人画家不肯这样做时,绘画便成为一种纯属自娱性质的个人的文化行为了。画什么、怎么画、为什么画都不再受他人的指使,每个画家,尤其是文人画家们都可以依据个人的好尚去选取题材和表现手法,至于社会怎么评价,对画家来讲变得不重要了”[25]。可见,元人绘画更多的是“为己而作”,没有功名意识导引,内心适然,任意而画,纯粹只为自我娱乐而已。这样绘画艺术的“表意”方面更加突出,失去了政府的主导,反而能让元画“旁逸斜出”,可谓绘画史上一件幸事。文人们没有了前代科举之业的束缚,将自身才能专注于此,借画写心,为元画注入新的生机。
元人绘画追求精神自由,寓意山水,自乐性情。绘画并非易事,既要深入研习,又要胸中磊落,心宽意适,悠闲而为。宋人郭熙就已经有所注意,“世人只知吾落笔作画,却不知画非易事。庄子曰:‘画史解衣盤礡’,此真得画家之法。人须养得胸中宽快,意思悦适,如所谓易直于谅,油然之心生,则人之笑啼情状,物之尖斜偃侧,自然布列于心中,不觉见之于笔下。”[26]释华光作画也要有外静而内闲的状态,“华光每写时,必焚香禅定,意适则一扫而成”[27]。绘画之身心都要有所准备,在心闲意适的状态下落笔,则如行云流水,自然天成。郭思也提出“意存笔先”,以画寄意,画之上品要做到画已尽而意有余,“意存笔先,笔周意内,画尽意在,像应神全。夫内自足,然后神闲意定。神闲意定则思不竭而笔不困也”[28]。“神闲意定”指精神上之自由与悠闲,而文人心意专一笃定。这种休闲心态对绘画极为重要,能够决定绘画艺术水平的高低。
元人绘画的一大特色就是它的“自娱性”。这种自娱有两方面体现,一是文人绘画写自我真意。二是文人心闲赏画,寄意抒怀。元代画家多为自我娱乐而画,不用过多考虑绘画的社会功名意识。宋代画家李成已提出以画自娱,不求功利,“营丘李成,世业儒,胸次磊落有大志,寓意工于山水……盖成平生所画,只自娱耳,即势不可逼,利不可取,宜传于世者不多”[29]。倪瓒为“元四家”之一,擅画山水与墨竹,更是直言“余之竹聊以写胸中逸气耳,岂复较其似与非,叶之繁与疏,枝之斜与直哉?”又言“仆之所谓画者,不过逸笔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娱耳”[30]。绘画只是一种“自娱”形式,不管所画竹之形态如何,重在写情寄兴而已。同为“元四家”之一的吴镇也提出,“墨戏之作,盖士大夫词翰之余,适一时之兴趣”[31]。绘画作为闲暇兴趣,适性而为,乐在其中。正如潘天寿先生所说,“盖吾国绘画,至元全入于文人余事之范围,纯为士大夫词翰之余,消遣自娱之具,故墨戏画中之梅兰竹菊,孤姿清致,殊有契于士夫之怀抱,尤见兴盛。”[32]文人的绘画自娱,正是元画一个突出的特点。
再看元人的赏画活动,同样有“自娱”性,这种自娱主要为意趣相合。元人汤垕所著《画鉴》中有论述鉴赏的相关问题,提出“看画本士大夫适兴寄意而已。有力收购,有目力鉴赏,遇胜日有好怀,彼此出示,较量高下,政欲相与夸奇斗墨博物耳”[33]。赏画也是“适兴寄意”而为。“画梅谓之写梅,画竹谓之写竹,画兰谓之写兰,何哉?盖花卉之至清,画者当以意写之,初不在形似耳。陈去非诗云:‘意足不求颜色似,前身相马九方皋。’其斯之谓欤?”[34]元人作画以意为先,赏画也关注画之深意。“观画之法,先观气韵,次观笔意,骨法、位置、傅染,然后形似……高人胜士寄兴写意者,慎不可以形似求之。先观天真,次观意趣,相对忘笔墨之迹,方为得之”[35]。作画有意,赏画亦为寄意,二意相合,便能自得其乐。如查洪德先生所指,“在元代文人看来,作画是心灵的寄托,观画则是与画家心灵的沟通,画家的人格、精神、意趣,都贯注于画面;赏画者通过画面,可感悟这些人格、精神意趣。”[36]作画与赏画都要有闲心才能为之,这两种文人活动是元人休闲心态的外化,不仅体现在活动本身,更是休闲与绘画的相互助益,才能促使元代“文人画”发展到高潮,同时又展现出元人休闲心态基础上“文人画”的自娱特色。
四 自在饮酒,悠闲快活
中国文化传统中,文人与酒有不解的情缘。文人喜爱饮酒,酒不仅能给人带来精神上的愉悦,而且能帮助文人释放才华。元代文人的血脉中流淌着“酒”分子,饮酒成为休闲生活的又一特色,醉酒后的自在快活是文人闲适心态的体现。
快活饮酒,不理人间是非,闲中自为乐。元散曲中有很多描写饮酒场面,活泼悠闲,文人享受沉醉其中的乐趣。以醉酒的方式追求精神的自由,元人更注重自我内心的体验,生活的价值就在于实现“真我”的快活。关汉卿的〔南吕·四块玉〕《闲适》云“适意行,安心坐。渴时饮饥时餐醉时歌,困来时就向莎茵卧。日月长,天地阔,闲快活!”“旧酒投,新醅泼,老瓦盆边笑呵呵,共山僧野叟闲吟和。他出一对鸡,我出一个鹅,闲快活!”[37]安心适意,相伴饮酒,尽享清闲快活。“沉醉也更深恰到家,不记的谁扶上马”(卢挚〔双调·沉醉东风〕《适兴》)[38]。有时也写环境清幽,与庄家一起饮酒闲话,“雨过分畦种瓜,旱时引水浇麻。共几个田舍翁,说几句庄家话,瓦盆边浊酒生涯。醉里乾坤大,任他高柳清风睡煞”(卢挚〔双调·沉醉东风〕《闲居》)[39]。这种田家饮酒场面比较温和,还有更为狂放自由、自在欢快的场面。“宾也醉主也醉仆也醉,唱一会舞一会笑一会。管甚么三十岁五十岁八十岁,你也跪他也跪恁也跪。无甚繁弦急管催,吃到红轮日西坠。打的那盘也碎碟也碎碗也碎”(无名氏〔正宫·塞鸿秋〕《村夫饮》)[40]。这种场面在元曲中能表现得酣畅淋漓,在元代前还未见到“自在”到这种程度。场面混乱,盘碎碗碎,没有长幼的区分,没有礼仪的束缚,饮酒唯一的目的就是欢笑快活。题为写村夫饮酒,实际也可视为文人对自由生活的向往,醉酒忘却世事,获得内心的闲暇与精神上的悠闲。饮酒帮助文人内心豁达,是文人走向休闲的一种外在方式。
酒助诗兴,散淡逍遥,笑谈高歌沉醉乐闲。元代文人开始拥有一种新的价值取向,他们从历史中总结出人生真理,只有自我真正的闲适快活才是人生所求。这种快活是遇知音后的畅饮,“酒杯深,故人心,相逢且莫推辞饮”(马致远〔双调·拨不断〕)[41]。“荣华富贵皆虚幻,觑功名如等闲,任逍遥绿水青山。寻几个知心伴,酿村醪饮数碗,直吃的老瓦盆干”(贯云石〔双调·水仙子〕《田家》)[42]。知音饮酒,无忧无虑,醉在其中,内心轻松愉悦。高文秀〔双调·行香子〕云:“〔搅筝琶〕时复饮浊醪,且吃的沉醉陶陶。把人间万事都忘,到大来散诞逍遥。”[43]喝醉后的散诞逍遥,能够释放真正的自我。文人离不开诗,常常饮酒赋诗,“不因酒困因诗困,常被吟魂恼醉魂。四时风月一闲身。无用人,诗酒乐天真”(白朴〔中吕·阳春曲〕《知几》)[44]。闲身一人,诗酒为乐。薛昂夫〔双调·庆东原〕《西皋亭适兴》云“兴为催租败,欢因送酒来,酒酣时诗兴依然在。”[45]送酒而欢,酒酣诗兴在,“酒酣时乘兴吟,花开时对景题”(王爱山〔中吕·上小楼〕《自适》)[46]。“酒旋沽,鱼新买,满眼云山画图开,清风明月还诗债”(马致远〔南吕·四块玉〕《恬退》)[47]。山间幽静,买鱼饮酒,以诗为乐,写诗只是情感的自然流露,不需掺杂外在事物,顺心而为,是身处清闲时的一种自我安乐。“〔离亭宴煞〕闲来溪上横琴坐,醉时节林下和衣卧,畅好快活,乐天知命随缘过”(王实甫〔双调·失牌名〕)[48]。弹琴作诗,随缘而乐闲,文人洒脱欢快。
还有些文人干脆不理诗书,在“安乐窝”中沉醉。阿里西瑛〔双调·殿前欢〕《懒云窝》云“懒云窝,醒时诗酒醉时歌。瑶琴不理抛书卧,尽自磨陀。想人生待则么?富贵比花开落,日月似撺梭过。呵呵笑我,我笑呵呵。”[49]无论是饮酒赋诗,还是自我沉醉,都是自我闲心的舒展,闲适的人生是快活的。元人的饮酒是休闲心态的外在表现,沉醉可以得到精神上的自由与快乐,清醒时外物的压抑有了释放的空间。这种休闲正是元人新的人生价值追求所必备的心理状态,也是元代文学艺术发展的重要体现。
休闲是人思想和精神上的一种追求,元代少了功名意识的牵绊,文人的休闲心态也有着自身的独特性。文人走进自然的山林泉水,享受心的清闲与安逸,他们融入自然之中,真正体会自然给人的欢乐。休闲还应有一颗平淡之心,不与他物相争,不慕名利,归隐田园,能够心闲而自适。元人绘画同样有自娱特色,自乐性情,借画写心适意相合。文人与知音饮酒,沉醉自得,酒助诗兴,宽闲自适而快活逍遥。元代文人的休闲心态,是元代文人生活的重要方面,为元代文学的发展注入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