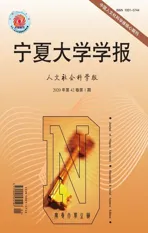百年汉语量词研究述评
2020-12-14王博,王军
王 博,王 军
(辽宁大学 文学院,辽宁 沈阳 110036)
现代汉语语法体系对进入“数词+X+名词”或“动词+数词+X”结构中的“X”成分统称为“量词”。汉语量词的产生大约已有三千年的历史了。“殷商时期,是汉语名量词的萌芽期,度量词开始出现。先秦是量词的发展时期,一方面,名量词纷繁复杂,使用频率高,而又呈系列性发展”[1]。此时,标志汉语显著特点的个体量词已经出现,并且有了一定的发展。“另一方面,动量词的产生,不仅丰富了量词,并且使量词这一门类趋于完善”[2]。秦一代,受到政治、经济生活的影响,量词体量逐渐庞大起来。汉魏六朝以后量词开始广泛使用。随后,经过隋唐至明清近一千五百年的更迭扩展,到现代汉语阶段,量词已经发展成为汉语词类体系中的显赫词类,大体上名词或动词的使用都有与之相应的量词搭配。
汉语量词的研究开展较早,20 世纪20 年代开始,一些专注于现代汉语语法体系建立的教学语法专著相继对量词展开研究。黎锦熙首次给量词定名[3];吕叔湘首次指出单位词表示数量范畴这一本质属性[4];王力首次指出单位名词(即“个体量词”)的性质[5];高名凯首次将量词独立成类[6];张志公首次将量词划分为物量词与动量词两类[7];丁声树等学者也相继对量词进行了研究[8]。20 世纪50 年代以后,刘世儒相继发表了有关量词研究的若干文章[9-13],其《魏晋南北朝量词研究》一书更是揭开了量词断代研究的序幕,对接下来的量词研究产生了较大影响[14]。20 世纪70 年代起,学术界掀起了一场有关量词性质大讨论的热潮,陈望道和黎锦熙、刘世儒各自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此后,参与汉语量词研究的学者队伍愈加庞大起来,陆续有学者开展了量词断代史以及量词专书、专题的研究工作。针对个别代表性通用量词以及方言量词的研究工作也在有序进行。
本文将近百年来的汉语量词研究成果分为基本问题的讨论和量词的具体研究两个方面:基本问题的讨论主要涉及汉语量词词类归属、次类划分、定名、性质四个内容;量词的具体研究则集中关注了个别量词、方言量词、专书量词、断代量词、量词专题研究五个领域。在对汉语量词既有研究成果系统梳理的基础上,针对一些至今仍存在争议的问题提出笔者的看法,最后谈一谈时下量词研究的总体趋向以及研究中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
一 关于汉语量词基本问题的讨论
(一)词类归属
自《马氏文通》[15]以至20 世纪60 年代以前,针对汉语量词研究的学者,主要集中关注了量词的词类归属问题。意见共有两种:一,作为名词的附属词类;二,独立成类。
1.归入名词
真正的汉语量词研究始于黎锦熙。黎锦熙认为:“量词就是表数量的名词,添加在数词之后,用来作所计数的事物之单位。”这是国内语法学界首次给“量词”命名,并将其作为名词的附属词类进行研究。持同样观点的还有王力。这一时期,以黎氏、王氏为代表的学者们认为量词是表示所要计数的事物之单位,其主要功用是辅助计算名词。因此,学者们主张将量词划归为名词附属之一类。
2.独立成类
高明凯首次将量词独立成类,但高氏对于量词次类的划分完全不同于今人之说,该书所言“量词”实际包含了今人所谓副词、数词两类;今所言“量词”则独立为“数位词”“次数词”两类。直到张志公才真正开创了现代语言学意义上的汉语量词研究。张氏将量词独立成类的同时,对量词次类进行了清晰的划分,现代汉语语法体系中对于名量词和动量词这两大次类的划分正始于张氏。丁声树之后的学者在量词次类划分的问题上基本都沿袭了高氏、张氏的观点。随着汉语教学语法体系对量词作为独立词类观点的普及,量词这一现代汉语语法体系中的显赫词类在语法研究中也越来越受到重视。
(二)次类划分
关于量词的次类划分问题从表面看仅仅是粗略与细致之分,但实际上不同的分类方式代表了学者们对量词性质的不同认识。
20 世纪50 年代以前的量词研究还都只注意到名量词,少有学者涉及动量词的研究。直到张志公《语法和语法教学——介绍“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一书的出现才填补了这一空白,全面、系统的量词研究进程随之展开。随后,王力在介绍“单位词”时,也依张氏二者兼而论之的做法,将“东方语言(包括日本语)所特有的天然单位词分为表示人、物的单位与表示行为的单位两类”[16](王力此说弥补了其《中国现代语法》的不足)。总的说来,20 世纪60 年代以前的量词次类划分还比较粗略,通常只笼统分为名量词和动量词两类。
20 世纪60 年代以后,刘世儒在进行量词断代研究时,对名量词和动量词作出进一步细分(名量词分为陪伴词、陪伴·称量词、称量词三类,动量词分为专用动量词、借用动量词两类。刘氏所谓“陪伴词”即今之“个体量词”,“陪伴·称量词”即今之“集合量词”,“称量词”即今之“度量词”)。朱德熙根据名量搭配以及量词功能的不同,进一步将名量词分为个体量词、集合量词、度量词、不定量词、临时量词以及准量词六类,将动量词分为专用动量词、借用名词以及重复动词的动量词三类[17]。现行的汉语教学语法体系基本沿用朱氏这一分类。以通行本《现代汉语》教材为例,量词下辖名量词和动量词两类,名量词具体分为个体量词、集体量词、度量衡量词以及借自名词、动词的名量词共计五类;动量词则包括表动作数和表动作时量的专用动量词,借用名词以及借用动词的动量词共计四类[18]。
与教学语法体系相对,专家语法体系对于量词次类划分的争论近年来愈演愈烈,间或有学者指出国内汉语学界一向将类别词与量词混而不分的问题,如洪波。李葆嘉则提出现代汉语量词应分为“类别词”和“单位词”两种,甚至主张取消名不副实的“量词”这一术语[19]。
(三)定名问题
量词,还有一个定名问题。对于“数词+X+名词”或“动词+数词+X”结构中的“X”成分,有人称之为“量词”,还有人叫作“单位词”“陪伴词”以及“类别词”等等。术语称谓上的歧异,有的时候是异名同实,有的时候可能涉及对词类范围的不同理解,在一定程度上既反映了研究对象本身的复杂性,也间接说明了学者们对量词性质认识的不断深化。
现代汉语教学语法专著对“X”成分的命名基本都遵循黎锦熙的提法。所不同的是,相同名称下,对该成分性质的认识略有不同。黎锦熙认为该成分实乃辅助数词进行数量计算的名词,因而将其划归到名词附属之一类。如今,对作为汉语独立词类的“量词”的认识,已有的说法较为模糊,仍以通行本《现代汉语》教材为例,该书指出“量词表示计算单位。名量词表示人和事物的计算单位,动量词表示动作次数和发生的时间总量”。这种“计算单位”实际上就是一种“计数的标准”,所以无论是否将“X”成分独立为一类,对该成分的性质界定基本上也都认为是辅助计数的,至于是辅助名词计数,还是辅助数词计数,诸家观点又有所不同。而“单位词”“类别词”最初都为王力所使用,王力指出“单位词……经常和数目字一起用,所以又叫作量词。不同类的事物有不同的单位词,所以又叫作类别词”。近来,不断有学者就“量词”下辖之“个体量词”一类词表事物类别的性质提出对“X”成分进行重新分类的必要性,甚至是重新命名,以此消除由于名称所带来的对于该成分性质认识的误导。至于“陪伴词”的提法最初始于日本文法界,《支那语文法》指出“连接于数词之后表示事物种类性质的那种词叫作陪伴词”,根据其后例句可以看出,该书所言“陪伴词”实际上包含了今人所谓个体量词、集体量词、借用名词的量词三类。随后黎锦熙、刘世儒在与陈望道的量词性质争论中继续征引了“陪伴词”的提法,但内容却发生了改变,黎氏、刘氏只把“件”“张”一类“表个体的量词”看作陪伴词。
(四)量词性质
量词的使用究竟有什么作用,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学界对于量词的争论也多集中在其性质以及与性质相关的量词分类上。20 世纪70 年代,陈望道与黎锦熙、刘世儒展开了一场关于量词性质的大讨论[20-21]。40 年过去了,语法学界对于汉语量词的研究愈加深入,但对量词性质的认识至今仍没有一致的意见。总的说来,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统共持有计数、计量以及表类别三种不同的看法。
1.计数
《马氏文通》是最早明确提出汉语量词性质的语法学著作。马建忠说:“凡物之公名有别称以计数者,如车乘马匹之类,必先之。有有称,有无称,而连记者,则有者称之,无者第数之,然要皆后乎公名。”马氏认为“以计数”是汉语量词的性质。持相同观点的还有黎锦熙、王力、高明凯、太田辰夫。太田辰夫认为“量词是数词的附属词,作名词修饰语的名量词计算事物的数量,作动词修饰语的动量词计算动作的次数”[22]。接下来,他继续指出名量词具有计数和计量两种不同的性质,计数如“革车千乘”“千足羊”;计量如长度“尺”“寸”、容量“斗”、重量“斤”等等。另外他还指出量词的形态性以及由于形态性进一步发展而来的类别性特征,并且由于时代的发展,最初原意较为明确的量词渐趋模糊,而且用法也产生了一定的变化。
我们认为马建忠提出“X”辅助“以计数”以及太田辰夫“量词是数词的附属词”的看法是正确的。但马氏、太田氏之后所举的具体实例,如“车乘”“千足羊”之类,则与前面的性质界定相抵牾,导致后学对量词的性质产生了错误认识。这类“X”实际分为两类,最初出现在物质名词之前的一类“X”实际上是为了辅助数词对物质名词进行计算,而在个体名词之前出现的一类“X”则是受到“数词+X+物质名词”结构类推影响的产物,因此,后一类出现的“X”成分的性质并非为了辅助数词对名词进行计算。
2.计量
吕叔湘将“意义不及名词、动词、形容词那样实在的,一概称为辅助词”,并进一步指出“‘量词’在辅助词中是表示数量范畴的”。吕氏对“量词”性质的认识是从表示数量范畴这一角度着眼的。黄载君以甲骨文、金文材料为依托,进一步指出“在量词萌芽的先秦时期,汉语中表示量的这一范畴多用数词表示,秦汉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数词与量词并用表示量范畴,后来随着汉语量词体系的逐渐庞大和词类分工的日趋严密,数词表示量范畴的用法才全部转移到量词上”[23]。袁晖与张帜的看法与黄文不谋而合[24]。其后,陈小明则从名词到量词的转化过程中,名词语义经过“投影”沉淀到量词身上这一角度入手,认为个体量词也都具有表量的性质[25]。与前说相比,严扣凤的观点最为严谨,严文从量词产生的源头谈起,指出量词的出现就是为了计量,但其并未因此否定量词具有的表类别的性质,严氏认为该类别性质的产生源于量词性质的扩散。卢屋认为“量词有表量以外的功能特征,如果量词和数词一样地表量,就根本没有必要另立词类,数词、量词还是合为一体比较简便”[26]。
实际上,“计数”与“计量”两种观点都是着眼于名词的可数性与否来说的,当“数词+X”结构所修饰的名词是个体名词(即可数名词)时,“X”被认为是辅助数词对名词进行“计数”,而当“数词+X”结构所修饰的名词是物质名词(即不可数名词)时,“X”被认为是辅助数词对名词进行“计量”。总之,无论“计数”或是“计量”,其名虽异,但其实都认为“X”乃辅助数词对名词计算之成分。
根据以上诸家说法,我们认为“X”可以从所修饰名词的可数性与否上分为辅助计算具体数(即个体名词)与计算抽象量(即物质名词)两种,但两类“X”的产生有先后顺序。数词在计算具体数时是完全够用的,并不需要额外在“数名”结构中插入“X”来辅助数词对个体名词进行计算,而物质名词所代表的抽象量则有大小、长短、多少、轻重之分,如“水”“米”之类的物质名词(即不可数名词),有时也有对其进行计算的必要,于是便开始借用与其相关的盛物器来辅助数词计算。起初,度量词的出现正是为了弥补数词在计算这类物质名词时的局限。由于借以辅助数词对物质名词进行计算的物体在形体上的差异,导致“数词+X+物质名词”组合显示出了抽象的“量”的差异,如“一碗水”与“一桶水”,“一碗米”与“一缸米”,这种“量”的“多少”差异是通过“数词+X+物质名词”中的“X”成分体现出来的。
3.表类别
量词可表示“类别”,这一提法始于王力。王力指出“单位词是名词的一种……不同类的事物有不同的单位词(如马称“匹”,车称“乘”),所以又叫作类别词”。王氏的观点很有代表性。
王力以后,不断有学者提出量词在名量搭配时所体现的名词的类别性特征。朱安义认为量词在数词之后起到了修饰名词的作用,而汉语量词的显著特点正是其在修饰名词的同时所具有的分类功能[27-28]。董振邦、李玉红随后对这一说法进行了回应和补充,董氏、李氏认为“数词存在的目的是为了表现名词的多少,而量词在一定情况下可以认为是名词的辅助语,从而起到对名词的补充说明作用”[29]。洪波也曾针对国内汉语学界将类别词与量词混而不分的情况,从意义功能和结构两个方面对二者进行了区别[30]。胡琳、何万顺、林坤翰也相继撰文支持洪说[31-32]。李治平则对比了汉英两种语言在描述事物时的不同,从认知角度分析了汉语量词对所言事物或现象的“类”的区分的功能[33]。
以上是学术界对于汉语量词性质认识的主要三种观点。
我们认为对汉语量词性质的界定要从量词体系的发展过程出发,不把量词的性质看作一成不变的凝固体,而要从历时角度仔细爬梳量词在各个阶段的发展演变情况,从而能够以动态、发展的眼光来看待汉语量词性质的扩散。因此我们主张从汉语量词各个次类产生先后顺序的角度,秉承量词性质存在动态变化的可能性的原则上重新认识汉语量词的性质。
回顾汉语量词产生、发展、演变的全部过程,简单来说可以概括为:名量词的产生先于动量词,度量词的产生先于集体量词、个体量词。语言类型学的研究成果已经证明“世界上的语言都具备度量词”[34]。我们认为世界各民族语言中度量词的普遍存在一定有某些共性的特征。比如,在商代汉语中,甲骨卜辞有“牛一”“羊一”“豕一”这样的用例,数词“一”存在的目的显然是为了计数。既然牛、羊、豕之类的个体名词需要计数,那么殷商时期在祭祀活动中充当重要作用的“酒”之类的物质名词同样也需要计“数”,此时,数词在计算这类名词时显现出自身的局限性,因此便开始产生了借用与物质名词相关联的名词辅助计数的用法,如“鬯二升一卣”(这是借用表示盛物器名称的普通名词作度量词)。度量词的产生使得人们可以更为便捷地对物质名词进行计数,由“量词对物质名词操作后产生可读数的集合,即可计数的单位,而选择多少个这样的单位则由数词决定”,在表示物质名词的量词结构中,度量词的出现主要起到称数便宜的作用。这种较为简便的辅助计数方式使得“数量”组合逐渐固定下来。而后,经过强大的语法类推作用,个体名词也逐渐确立起这样的组合规则。起初,“量词(即度量词)的出现并不是为了分类。只是在不断的认识过程中,人们根据事物之间的相似或相关性”选用一些在语义上与所饰名词关联性比较强的词去充当量词[35],于是,标志着汉藏语系语言显著特点的个体量词便产生了。这类量词的使用或隐含兼表形体[36];或涵盖分类、情感评价以及兼有指涉、回指功能[37]。尔后,随着量词体系的逐渐庞大,名量组合中量词与名词在语义特征方面呈现出多种多样的联系,二者之间的关系也变得愈加扑朔迷离,对量词性质的认识也更加复杂起来了。
二 汉语量词的具体研究
历史文献中出现的量词的情况比较复杂,有的使用范围很广,属于官话方言,有的使用范围很有限,属于非官话方言。从建构汉语量词史的角度出发,我们既要将现存的各个具体的官话方言量词和非官话方言量词的来龙去脉搞清楚,同时也要对汉语历史发展过程中曾经出现但现已消亡的量词发展演变情况进行系统梳理。这是一个极其庞大且繁复的工作,需要一代又一代学人不断努力。下面我们将从个别量词、方言量词、专书量词、断代量词、量词专题研究五个方面入手,对现阶段量词个案研究的现状进行一个总的概说。
(一)个别量词研究
汉语庞大的量词系统是由一个又一个具体的量词支撑起来的。对单个量词的发展过程进行历时梳理,是建构汉语量词史的基础工作。
现阶段对个别量词的研究还集中在如“个”“条”“般”“道”“块”等少数几个通用量词上[38-46],更大范围的量词梳理工作亟待进行。
但是,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新的研究材料不断被发现,学者们的研究视野也逐渐由国内走向国外,由传世文献走向出土文献、域外汉籍,如史文磊就对范崇峰《谈敦煌卷子中的量词“掘”》一文提出了不同意见[47-48],并运用多重证据法证明汉语中并不存在指“握、把”的量词“掘”,“掘”实为“握”字之讹。覃继红、李建平、时冰等学者都针对出土文献材料中的量词展开了研究[49-52]。程亚恒则对大约成书于清代后期的域外汉籍《中华正音》中的量词“没”进行了系统研究[53],指出该量词“没(儿)”实际上只是量词“磨(儿)”的另一种记音符号。我们认为程亚恒的研究结论会给量词研究者带来一些新的启发,由于中国错综复杂的方言区存在,汉语中许多方言量词的书写形式很有可能只是官话方言中某一量词的记音符号,后来随着使用频率的提高,影响范围逐渐扩大,这些起初仅作为记音符号“借用”量词的用法渐趋固定下来,最终在量词体系中占据一席之位。
(二)方言量词研究
由于历史、现实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非官话方言量词可能会在某一历史时期(方言地位的升降主要跟该地区经济或者文化影响力的升降有密切关系)上升到官话方言层面,为全民使用。同样,官话方言量词也可能因为地位衰落而成为非官话方言量词,只在某些局部地区使用。对这类非官话方言量词的发展状况进行历时梳理,是量词史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目前,方言量词研究的成果极为丰硕,专著、学位论文、期刊论文涵盖了汉语七大方言区的诸多方言点。陈小明、叶丹分别针对粤方言以及黄石方言中一些特殊的量词,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较为细致的描写和解释[54-55],比较全面地揭示了该地方言量词系统的特点。郑兴敏则运用了横向比较和纵向考察的方法[56],对方言特殊量词及量词特殊用法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论析,郑文认为造成方言量词差异的原因是由于量词来源途径的不同和语言继承、语言接触、语言认知的不同所导致的。另外,还有个别学者在针对一些比较有特点的方言量词以及与量词使用相关的特殊用法方面进行研究,如张淑敏就从兰州话量词重叠式的句法功能、语法意义,以及与数词、指示代词的组合情况、组合后的使用情况入手,比较兰州话量词与普通话量词在各种语境中的具体用法的不同点[57]。张海媚则从林州方言量词“嘴”“口”入手,通过不同方言点中二者在使用方面存在的差异来说明同一种语言现象,在方言和普通话中的发展并非同步[58];就同一种语言系统而言,同一个词的不同用法之间的发展也是不平衡的。王双成、俞易利、王兆燕、李昇虹、聂志军等学者还对一些地域性色彩极强的方言量词进行了研究[59-63]。值得欣喜的是,有学者在进行学术研究的同时,还针对现代汉语中量词误用的情况,编纂了量词词典,对普及量词知识起到了重要作用[64]。
(三)专书量词研究
不同的著者可能受到时代变迁、语言借用(残留)、地域迁徙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在其作品中保存了较为丰富的官话方言量词以及非官话方言量词的使用情况,对这些语言材料进行深入挖掘,可以充实断代量词研究的成果。
在既有的专书量词研究成果中,进行独立的、专门的专书量词研究还不很多,多数学者通常是在全面的专书语法研究中部分涵盖了量词的研究内容,如何乐士就对《左传》中的量词使用情况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分类和描写[65]。诸如此类的研究工作还有李崇兴、祖生利《〈元典章·刑部〉语法研究》[66],曹广顺、梁银峰、龙国富《〈祖堂集〉语法研究》等等[67]。
专门的专书量词研究成果以学位论文为主,如魏丽梅《〈红楼梦〉量词研究》[68],方琴《〈史记〉量词研究》[69],刘玉朝《〈元刊全相平话五种〉量词研究》[70]等等。
总的来看,专书量词的研究成果相较于其他词类来说少且零散,并且,近十年来从事专书量词研究的学者数量也在不断减少。究其原因,我们认为由于专书语法研究不适应当今的学科氛围,在普遍求“创新”风气的驱动下,相比而言较为老套死板的专书研究因水土不服,故而逐渐被忽视。
(四)断代量词研究
断代研究有利于揭示该研究对象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呈现出的阶段性特点。刘世儒《魏晋南北朝量词研究》拉开了量词断代研究的序幕,其后各种断代量词研究专著层出不穷。魏晋南北朝是汉语词类系统大变革、大发展的时期,这一阶段由于战争导致的土地兼并、大规模的民族迁徙致使汉语和其他民族语言不断接触、融合,使得汉语词类系统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一巨变现象直到隋统一之后才逐渐稳定下来,魏晋时期也正是由于这样的一些历史原因,不仅成为语言研究的热点,更是语言研究的难点。虽间或有学者涉足,但系统的断代量词研究除刘氏外,也就仅有极个别断代语法专著以及语法通史论著谈到这一时期的量词使用情况,如柳士镇[71]、向熹[72]。
在量词断代研究的各个阶段,首先,隋唐五代时期的量词研究成果最多,如游黎、李建平、王绍新等学者都运用了共时描写与历时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对这一时期的量词增长和消亡情况进行了系统的梳理[73-75]。其次是先秦两汉时期,这一时期是汉语量词体系逐渐建立、发展、完善的时期,由于研究材料比较匮乏、研究难度较大,目前仅有李建平等少数学者对这一时期的量词使用情况进行了系统的研究[76]。再次是明代及现代阶段的量词研究,如叶桂郴、何杰[77-78]。元代、清代、清末民初阶段的成果最少,量词研究目前还没有系统的成果,只有少数期刊论文和学位论文涉及这几个时期的量词研究情况,如彭文芳、邓帮云等[79-80]。究其原因,我们认为元代、清代都是外民族统治中国的时期,蒙满语分别属于阿尔泰语系中的蒙古语族和满洲—通古斯语族,由于两朝统治者都施行较为积极的语言政策,蒙汉、满汉语言密切接触导致的语言变异现象尤甚,很多语言现象的演变除了需要考察语言内部的因素外,还需要考虑语言接触等外部因素,仅具备单一汉语习得的研究者难以胜任这样复杂的研究工作,给这两个时期的语言研究带来了很大的障碍。至于清末民初一段,则是由于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强势入侵导致这一时期汉语词类系统变化剧烈,同样给研究工作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五)量词专题研究
专题语法研究可以从共时与历时两个角度入手,调查、分析某一问题在共时层面上的特点以及历时演变过程中的发展变化。断代和专书研究的深入也可以为专题研究提供重要的立论依据。
在汉语量词专题研究中,论著较少,论文较多。历时方面,如金桂桃、麻爱民分别以动量词和个体量词作研究对象进行历时研究[81-82]。金文在对近代汉语宋、元、明、清四个时代大量产生的动量词进行细致描写的同时,还集中讨论了动量词的虚化问题,总结了动量词的发展规律。麻文则主要探讨了汉语个体量词系统的产生以及发展规律,并对前辈学者的研究失误进行了更正。共时方面,如徐正考、郑邵琳、张显成、李建平等学者都选取了近些年来新发现的出土文献材料(如铜器铭文、石刻、简帛)作为研究基础[83-85],这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规避因传世文献传抄错误而导致的结论错误情况。张显成、李建平更是从语言类型学的角度对量词的起源进行了考察,得出汉语双音化的发展是汉语量词起源的根本原因这一认识。
此外,还有一些学者致力于从量词结构、量词系统的建立为出发点,探讨汉语量词的产生及功能演变的相关问题,如安丰存、程工指出“量词的产生与发展需要有内在的语言基础以及外在的认知条件”,并认为“量词是在受不可数名词表量结构的类推作用下产生与发展的”[86]。相关研究成果还有安丰存、吴宇偲、程工以及麻爱民[87-88]等文。
三 量词研究的趋向
(一)定性问题尚未解决
究竟该对量词如何定性,这个问题几乎贯穿量词研究的始终,是每一位进行量词研究的学者首先要面临的基本问题,但对这个问题的探讨,迄今为止仍没有一致的看法。实际上,诸家所言量词可“计数”“计量”“表类别”这三种认识都不无道理,这并非“和稀泥”的折中观点,以上三种认识我们都可以列举语言事实来证明。所不同的是,我们认为这些性质是量词在发展过程中逐渐产生的,而非“与生俱来”。因此,我们主张从量词体系发展的角度动态地看待量词性质的扩散问题,并在上文中提出了相对具体的意见。学术争鸣有利于推动学术的发展,我们希望能有更多的学者加入量词性质的讨论中,从而更好地推动量词的研究进程,为量词史的建构打下坚实的立论基础。
(二)个案研究有待进一步完善
量词系统的建立和完善是通过各个具体量词用法的完善表现出来的。通过对各个具体量词源流嬗变情况的梳理,进而厘清整个汉语量词体系的发展演变情况。
个别量词研究和方言量词研究相结合,从而整理出单个量词使用和演变的脉络。分别从断代、专书、专题三个角度入手,通过不同角度的量词研究,逐步廓清量词在各个时期、各个地域的真实使用情况。其中,断代量词研究通过仔细爬梳各类共时语料,细致描写汉语量词在各个历史阶段的基本面貌,帮助我们了解量词的时代性特点,为系统的量词史建构做好穿针引线的工作。专书量词研究作为汉语量词史研究的基石,对各个时期具有代表性的著作进行穷尽式考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断代研究的不足,厘清不同地域、不同时代具体量词的增长以及消亡情况。专题研究涉及面相对较广,其研究语料除传世文献之外,还可能涉及出土文献、域外汉籍,其研究范围除量词次类研究之外,还包括量词结构等等。
但目前,对个别量词、方言量词的研究,还仅仅停留在几个较为通行的通用量词以及地域特点性较强、争议性较大的量词上,更大范围的个案量词研究工作有待进一步展开。断代、专书、专题研究也有待进一步深耕。
(三)新角度、新方法的应用
新时期的量词研究呈现出不同以往的显著特点。新方法的引进、新角度的应用,极大地推动了量词研究的进程。
近年来,运用认知语言学、语言类型学理论对量词进行研究的学者越来越多。一方面,学者们开始尝试从人类认知的角度研究量词系统设立的原则,以及人们在选择与名词适配的量词时的认知基础等等。另一方面,学者们又尝试从更大范围的世界语言角度进行量词的对比研究,使我们认识到不同民族在运用量词表达思想时具有的共性,进而更好地了解汉语个体量词的独特性。
新理论、新方法的应用固然能帮助我们从新的角度重新思考、认识汉语量词,但我们也应该避免进入唯西方语言理论至上的误区,把跟汉语事实毫不相关的理论照搬过来,搞出各种各样的新名词、新花样,使人不知所言,这样的语言研究是我们所反对的。王力先生早先就批判过这种做法。
四 结语
总体说来,自《马氏文通》起,一百多年来的汉语量词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宽加深,取得了极为丰硕的成果。无论是语法通史,抑或是断代史、专书、专题量词研究都有不少学者涉足,致力于量词史建构的学者也持续发力。但迄今为止,学术界对于汉语量词性质的认识仍未趋统一;对于个别量词的研究还集中在少数几个通用量词身上,更大范围的量词个案研究亟待进行;断代量词研究在元代、清代以及清末民初这几个阶段的成果仍乏善可陈,其他几个阶段的量词断代研究虽间有成果,但我们认为仍有继续深耕的余地;专书和量词专题研究也需要更多的学者投入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