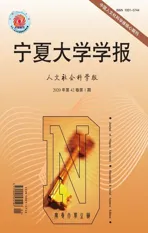从“写心”到“论世”
——清末案头戏抒情风格的嬗变
2020-12-14袁睿
袁 睿
(浙江工业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杭州 310000)
戏曲以曲韵结撰故事,本身兼具了叙事文学和抒情文学的双重特征,在表情达意上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所谓“诗不如词,词不如曲,故是渐近人情”[1]。随着明清戏曲文人化、案头化的加剧,“情”的强调已经超过“事”的建构,戏曲的抒情功能愈加显现。戏曲承载了作者内心的喜乐忧愤,以或隐或现的形式倾吐着他们心中的“块垒”,真正做到了“快人情者,要毋过于曲也”[2]。在“情”与“事”的取舍间,文人曲家逐渐偏离了结撰故事、塑造人物的基本叙事准则,将创作重心全部投射到书写内心、倾吐胸臆以及照见社会等方面,使抒情风格逐渐成为创作主流。而案头戏抒情风格的发展过程,也经历了从“写心”到“论世”的嬗变。
一 “情”的复杂化与符号性人物登场
关于案头戏的抒情特征,杜桂萍教授曾提出“‘自喻’性表达”的概念,认为“借助与剧中人物、事件的某种对应关系,暗示或者映照作家自我的生活经历或某种私人性情感”[3],简单来说,就是“自我”与“艺术形象”之间属于二元对应的关系。这种情况在清初杂剧,尤其是写心杂剧中体现得非常明显,深刻地摹写出文士心中的易代之悲和恋情之恸。
但是这种二元对应的创作原则在清代后期发生了变化,体现为“个体对应→群体对应”的发展轨迹。作家赋予在作品中的“情”也出现了从“写心”到“论世”的复杂化与扩大化转型。
清初杂剧的“个体对应”是将作家个人的心理和遭遇反映在戏曲作品中,所抒之情仅以个人的爱恨情仇为主,这种创作模式一直延续到乾嘉时期。清末的案头戏则逐渐抛弃了作者和主角之间以“人物”为纽带的对应关系,将剧中人物作为情感和思想的传声筒。剧中人物成为一种符号,或象征女权主义(如武则天),或象征爱情(如杨玉环),成为一个群体或者一类情感的代言。因之,曲中此时所抒之“情”也不再局限于个人的情爱、不满等,而是升华为对人生、对爱情、对社会的一种宏观性哲思,即“论世”。
符号性人物与“论世”需求相辅相成,当代表某个特定文化意象的角色出场,观众很快会感知到其背后的象征意义,从而对剧中所论之事,乃至作者的观点、态度作出准确的预判。由于提前接受了作者的观点设定,观众们对接下来的论述就比较容易理解和认同了。这些符号性人物多为历史名人,他们的事迹广为人知,这些人物所带来的认同感远大于作者本人的个体经验。以往的“写心”杂剧重在抒发个人情绪,角色由作者本人代入担当足以满足创作需要;而以“论世”为目的的作品则需要具有普遍感召力的形象——符号化人物出场,才能将更复杂、扩大的情感浓缩为剧本的先验背景,在有限的篇幅中表达深远的意境。因此,符号性人物是戏曲家“论世”诉求下的必然选择,“情”的复杂化和扩大化(“论世”的基础)则是符号性人物出现的根本原因。
比如武则天形象就在道光间戏曲家严廷中的作品中反复出现,成为其表达“论世”诉求的代言人。作为中国古代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代表了女性对权利平等的追求,是古代女性解放的杰出人物。严廷中《秋声谱》中的《判艳》《洛城殿》二剧,均以武则天为主角,正是借用了其形象中的女权意义。
武氏身为女权解放的先锋,在男女关系上比较开放任性,对封建道德进行了大胆反叛。《判艳》一剧并没有如道学家一般对武氏的行为予以批判,而是通过温和的开释、说理为“情”与“欲”划定一个合理的度,使世间女性既拥有追寻爱情的权利,又不至于陷入淫乱,反映出作者对男女之情开明豁达的态度。
作品开篇点明武则天死后封为如意妃子,掌管奈何司中风流怨鬼,生前宠爱的女官上官婉儿亦从旁随侍。这种设定保留了历史上武则天拥有尊崇地位和无限权利的身份属性,以及男女平等的用人原则。武氏开场的唱词【一剪梅半】直陈主题,歌云:
竟把唐家改作周,衮也风流,冕也风流。红颜似此足千秋,生也风流,死也风流[4]。
这位风流女帝死后被上帝评为“虽乱春宫,尚谙国政”,表现了作者对历史人物公正的评价。当然,武氏自己也对生前的淫乱行为有反思之意,并发出“怎奈众生万念可灰,只有这色欲关头,不能打破。则这大千世界一日十二时内,不知有多少迷死的冤魂。因此九幽地府,六道十八层中,便添了无数贪淫的乐鬼”[5]之感叹。
时逢中元节,武则天遂发放众女鬼,为其指点迷津。剧中安排了六位女鬼出场,分别代表六种死因:少女伤春之死、欢淫过度之死、小妾受虐之死、青春守寡之死、改嫁羞愧之死、受辱怀孕之死。这六种悲剧情死,均受到外界的压迫所致。少女伤春、青春守寡以及改嫁羞愧,主要是受到了封建社会舆论压力的迫害,女性丧失了追求自由恋爱、改嫁再婚的权利,成为封建礼教的牺牲品。
小妾受虐、欢淫过度则反映了封建婚姻制度对女性的戕害。在古代婚姻中,妾的地位极其低下,正妻可以对其任意凌辱,甚至处死、买卖,因此姬妾不仅承担着沉重的家务劳动,而且经常成为夫妻相争、妒恨的出气筒,受到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然而无论正妻、姬妾,最终都要在“夫为妻纲”“出嫁从夫”的伦理要求下,成为男性的玩物。欢淫过度而死的女子因美貌遭到丈夫的无度索取,最终一命呜呼。对于这种畸形的夫妻关系,作者借上官婉儿之口一针见血地指出:“错将淫态当温柔”。这一观点反驳了“夫为妻纲”“一夫多妻”的封建传统,从女性尊严的角度出发,为女子张目。这样反传统的言论与女权代表武氏、上官氏的形象相呼应,使作者的“论世”观点更加鲜明。
与上述五种情况相比,女子受辱自尽一案更直击男尊女卑的社会陋习。通过女鬼之口,讲述了其受到坏人迷奸怀孕,只能忍气吞声、投河自尽,而施暴者却逍遥法外的悲惨遭遇。这样的恶性事件在当今的落后国家依然存在,追根溯源,还是性别歧视和畸形的贞操观作祟。反观严廷中的作品,在几百年前就已经为女性权益积极发声。这种先进的观念和深沉的社会责任感早已超脱“写心”剧时代的个人格局和私人情调,体现出清末思想涌动的时代意识和“论世”积极性。
作者以六种“情死”为表象,揭开了封建时代婚姻制度、伦理制度,甚至法治制度的腐朽和丑恶,将千百年来女性的不幸遭遇暴露于众。虽然没有激越的批判之语,但六位女鬼凄怨的哭诉足以唤起世人的同情。最后,作者安排武则天以法力度脱,使她们“来世遂意如心,各偕匹偶”,为全剧留下一个光明的结尾。
《洛城殿》则借用了武则天开科取女才子的传说,表达了对世间才子才女的怜爱之情以及渴望科举制度改革的理想。剧中加入来俊臣、傅游艺等贪官酷吏染指科举舞弊弄权,为子女牟利等情节,最终武则天公正地选取了真正的才学之士,佞臣子女不仅落第且当众出丑。剧本直指明清以来的科举黑暗,抒发愤恨不平之气。武氏的“古今未有之奇恩”反映出儒林群体对朝廷公平取士的渴求。
历史上,武周一朝并没有女科举之事,也没有在朝中任命女性官员,但武后称帝的事实给男权社会造成了根本性的打击。皇权女性化成为卫道士们无法接受的奇耻大辱,而对于女性来说却是扬眉吐气的壮举。尽管武氏称帝期间还未能实现女科举的理想,但宫中女官们却得到了施展才华和抱负的机会,涌现出以上官婉儿为首的一大批才能女子;皇室贵妇们也以武氏为榜样,太平公主、韦皇后都试图成为女皇,展示了高超的政治手腕。因此,武周时代成为文人、才媛向往的理想国。他们幻想在这里一展所长,慰藉现实中仕途不遇、深闺困守的精神苦痛。无论是《镜花缘》小说中的武则天开女科,还是《谢瑶环》戏曲中的女巡按代天子巡狩,都借用了武周时代作为女性崛起的大背景。
施展才华、得配佳偶一直以来是名士、才女追求的最高理想。在清末黑暗腐朽的统治下,不仅女性没有尊严和自由,就连男子也难免科场困顿。凋敝的时代造成了普遍的低落情绪和颓废心理,但在内心最深处,文人们仍然保留着对家国、对理想的拳拳之心。这份深挚的情感使他们通过创作与玄想在历史的旧梦中获得心灵的抚慰。“中试后各按名次,两相婚配,使才子佳人,都成眷属”[6]的科举规定寄托了他们对事业生活兼美的追求。
总之,武则天的形象较其他明君更为复杂、多面,她不仅象征着煊赫盛世,还代表了女权崛起、人性解放以及功业理想等更崇高的追求。这样的人物出场,天然地为剧本奠定了评说人性、指摘政治的“论世”基调。而卷首程莲题诗所云“科名簿与鸳鸯谱,只有先生合主持”[7]之语道出作者指点世事的创作愿景,证明了剧中武则天形象对作品主旨的符号意义,显示出清末“论世”剧与清初“写心”剧相比更为复杂的创作心态和抒情范式。
二 “公共写作”的回归与戏曲功能扩展
清末案头戏从“写心”到“论世”的风格转变,促进了戏曲功能的扩展,其外在表现为“私人领域”向“公共空间”的回归。
戏曲诞生之初,作为一种公共性艺术,或高台教化、或娱乐大众。自明清鼎革之际,文人创作开始了案头化、雅化的风潮,“写心”之曲不断涌现。作品不再向公众搬演,而是在文人圈内部交流,这使得曲家得以在私人的写作空间内恣意舒展,而不必考略观众的欣赏感受。戏曲逐渐成为排遣个人情绪的工具,这是戏曲文体功能的第一次转型。
清末以来,曲家在宣泄个人情感的同时,将视野扩大到社会、政治领域,完成了从“私人写作”向“公共写作”的复归。但他们恣意地在剧中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又使作品带有浓厚的个人色彩和主观情绪。因此,此时的案头戏可以说是私人情愫与公共意识相融合的产物,在传统的教化、娱乐、写心的曲体功能之上,又增加了社会评论功能。戏曲在作者心目中的地位也愈加提升,成为诗、文以外评说世事的重要文体。
“诗言志”“文载道”,戏曲此时也与诗文一样,可以“言志”“载道”。完成了从“写心”到“论世”嬗变的清末案头戏,不仅可以传达个体心声,还能参与评议世事。无论伦理道德,还是儿女私情,都成为作品评说的对象。作者的思想也从以往借事喻理的寓言式表达转变为酣畅淋漓的倾吐式宣泄。在曲家笔下,戏曲已经成为展现情绪、显示才华,甚至评点人生的重要文体。况且与诗文相比,戏曲文体亦庄亦谐的包容文风、人物增减的自由设计,以及曲辞音律的铿锵节奏,都更有利于作者的发挥。因此,承载着“论世”功能的戏曲更加受到文学家的青睐。
以私人化属性较为突出的爱情剧为例,在写心作品中,作者所思所感通常只局限于自身经历;而论世作品则在追忆个人情感之外,生发出对缘分、宿命、爱情的议论,以表达作者对世情的感悟。
严保庸的《盂兰梦》本为悼念爱妾张佩珊所作,作者在表达个人的思念情绪之余,还对世间薄情女子作了一番评点。尽管安排这些人物的出场的目的是为了衬托张氏的贤良淑德,但是作者对她们的精辟评论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其思想价值反而遮蔽了原本的悼亡主题。
剧本以盂兰盆会为背景,描写了地藏菩萨发放众女鬼的场面。这些女鬼皆为前代历史传说中的人物,作者借此对前人公案进行评论。朱买臣妻崔氏,“悍恶不仁,忘廉丧耻”;冯麟如妻罗氏,“抛夫撇子,背义忘恩”;秦桧妻王氏,“助夫作恶,误国殃民,尤为可恶”;柳梦梅妻杜氏,“虽堕情魔,尚无恶孽,准予超度”[8]。在对这四人的评价中,可以看出作者的三个态度:首先,崔、罗二妇背弃了夫妻之道,薄情寡义,为作者唾弃。其次,在对王氏的评价中,强调了祸国殃民“尤为可恶”,看出作者国事重于家事的思想。最后,杜丽娘为情而死,在封建礼教的规则下,本属不贞之女,但严廷中却不认为她的行为有罪,而是寄予“叹梅边柳边,若不是短命能延,枉杀你痴情忒坚”的无限同情。
由此观之,严氏一方面秉持着家国大义、夫妇之道等传统礼教观,另一方面也强调“情”对婚姻生活的重要意义——夫妻间不能薄情,支持自由恋爱。这段热场虽然篇幅不长,但却包含了作者对婚姻和社会的独特感受,使剧本的思想内涵更加充盈丰满。
无独有偶,顾太清的《桃园记》旨在追忆往昔恋情、凭吊丈夫奕绘。其中《遇佛·谈因》一出却宕开一笔,借观音菩萨之口,评点世间男女之情。作者认为男女用情各异,以“岔路”谓之。曲云:
【刮北地风】为片刻欢娱不久长,作一霎比翼鸳鸯,算生前勾了风流账。有因他男子荒唐、有因他女子轻狂,这其间多生怨望。到头来各自悲伤,落得个谁可怜、痛哀哀装模作样。怎知道、赋同心双栖玳瑁梁,只贪图、喜孜孜过眼风光。(白)这便是那俗人浮情的勾当。(生)请问还有何来?(正旦)听者。(唱)
【南滴滴金】有一般缥缈成虚谎,那怨魄愁魂无分两。假因缘却是非非想。(生)难道汉皋解佩、巫峡行云不算因缘不成?(正旦)这根由更渺茫,不过是烟波影响,哪能够效于飞成和唱。暂作个魂魄相交,好梦不长。(白)这便是那精诚所感的幻情了。(唱)
【北四门子】一般儿上了文章,当逞风流、凤欲求凰,竟不知口孽遭天网。谤闺门、不自防,作的那人渺茫、情渺茫,仿佛是镜难圆、天不长。写的那花解语、玉有香,只因他无所得、造成形状。(白)那曹子建的《洛神赋》、元微之的《会真记》,皆因是有所慕而无所得,才写的那样迷离惝恍。这便是痴情了。(生)请问菩萨,还有何情?一发指教弟子。(正旦)听来。(唱)
【南鲍老催】两情并长,真心蜜意商且量,温柔软款禁怎当。这便是连理枝、鸳鸯伴、鹣鹣样、并头莲,却不怕风飘荡。(生)如此讲来,这便是真情的了。(正旦)才堪树个情坛幌,断不比天涯草,两下里相抛忘。(白)这才是那真情的呢[9]。
这四段联唱,直指男子的轻狂孟浪与女子的荒唐任性行为。两者不仅有违礼教约束,而且造成了许多恋爱悲剧,对青年男女的身心健康和女性的名节都造成了巨大伤害。文人墨客艳羡歌颂的巫山云雨、西厢拜月,在作者看来,都是男子污蔑女性的意淫行为。这种略显偏激的观点虽然与太清本人受到谣言毁谤(即“丁香花”公案)的心境有关,但也客观地表达了封建时代女性的艰难地位——既要循规蹈矩,又要防人口舌。而女性本身无法控制后者的发生,却要受到余论责难,反证了性别歧视带来的恶果。
上述两剧均以描写作者自身经历为主,论世的部分只作为铺垫、衬托出现,却显现出不凡的见地。这些深思以普泛化的社会意义和独辟蹊径的思维视角,在剧本中脱颖而出,超越了中心事件的魅力。可见,清末案头戏在功能上已经超出前代的“写心”范畴,将“论世”的拓展化思考融入作品,形成了具有一定社会意义的公共文学。
简言之,戏曲文体功能的两次变迁——从大众娱乐到写心、从写心到论世,促进了作品内涵的不断深化。文人曲家在个体创作之余重拾社会责任,此时他们不再以观众的态度、世俗的观念为转移,而是以精英阶层的独特思维评点世事,具有思辨性和先进性。因之,“论世”作为案头戏的新功能并没有完全取代“写心”功能,二者是并存的,大多数情况下仍以“写心”为主。作者的“公共空间”创作在情感上关注社会,在思想上和表达形式上却依然保留着典雅、写意的审美取向。
三 写意化与颠覆叙事原则
由于“论世”的部分为作者思辨心理的集中阐发,大多数与作品的主线情节几乎没有关联,因此经常造成审美上的脱节,破坏叙事连贯性。不仅如此,个别以“论世”为主要内容的剧本还会采用更为纯粹的抒情方式,完全颠覆最基本的叙事原则,表现出鲜明的写意化特征。
根据作品“论世”成分多寡的不同需要,作者对叙事原则的破坏程度也有强弱之别,大体可分为三个层级,由弱到强依次为:忽视情节构思的平板化叙事;破坏叙事连贯性的插入式评论;放弃完整性叙事,以人物的独白、对白等充斥全剧。三种模式反映出清末曲家对戏曲抒情风格的探索和实验,表现了戏曲文体写意化的创作时尚。
第一种模式保留了故事叙述的完整性和基本要素,仍属于传统的叙事性作品。但是在讲求情节曲折与构思巧妙的戏曲叙事规范之下,这类作品显得较为平板无聊,缺乏生动激荡的戏剧情绪。比如汤贻汾的《逍遥巾》杂剧,全篇充满归隐修道的意味。虽然也讲述了一个文人身着道装访友的完整故事,但并没有强烈的戏剧冲突,甚至连反面角色也没有安排。这部平和飘逸的出尘之曲满足了文人雅士的精神追求,却没有照顾到普通观众的欣赏感受。全剧文辞雅洁,充满哲思玄想。欣赏者必须了解汤氏的遭际,与他具有同样遗世独立的高洁品质,对现实社会具有厌倦之情,才能真正体会剧本平淡表象下的内涵与所指。这显然不符合传统的叙事原则和戏曲结构技巧。
第二种模式则以插入式的“论世”桥段割裂故事主线,打破叙事的连贯性。虽然“论世”的部分语言较为精彩、思维较为深邃,但从全剧统领观之,这种旁逸一枝的写法与主要情节严重脱节。如果这样的唱段作为折子戏演出,可能会耀人夺目,但作为长篇传奇中的一环,却并不符合叙事原则的基本要求。尽管如此,清末案头戏中仍大量出现此类片段。
张梦祺的《玉指环传奇》第十九出有杨玉环评判女鬼一段,就借这位“爱情”代言人之口,表达作者对爱情的看法。剧写杨玉环死后为蓬莱女仙,因怜悯世间痴男怨女,将他们发落重生。被发落的鬼魂中除了本剧的女主人公玉箫之外,还有三对情侣:乔知之与窈娘、赵象与步非烟、李益与霍小玉。前两对都分配托生富贵人家、重结姻缘。就连李益,也为其换了一副心肠,与小玉再携鸳鸯。这样的结局饱含作者“佳人才子真堪并,教第一风流重认”的美好理想。
张梦祺在剧前点明此剧以《云溪友议》《唐宋遗史》中的韦皋和玉箫女故事为蓝本,并摘录了原文作为引证。无论是两篇引证,还是元人乔吉的《玉箫女两世姻缘》杂剧,均未提及杨玉环判案一段,可以说这个片段是作者的再度创作。与前代同题作品相比,这段情节突出了才子佳人大团圆的爱情观,在故事发展的主线之外,形成了较为独立的部分。
这种插入式论述甚至出现在题材和叙事风格都比较传统的教化剧里,江义田的《丹桂传》中就有这样的桥段。《丹桂传》讲述了王华、王守仁父子两代人忠孝节义、善有善报的故事。第五出,王华坐馆于员外富胡行家,富妾朝霞欲向王华借种生子,王华坚拒。朝霞列举了前人风流之事以挑之,王则以“荒唐事”反驳。一问一答中涉及了历史上许多有名的浪漫爱情故事,包括相如琴挑文君、红拂夜奔李靖等。这些香艳传奇历来为读者津津乐道,但作者却对其进行了彻底的否定,表达了批判态度。这段批驳全盘否定爱情自由,显得过于严苛,使得主人公的形象沾染了一些道学气,并不利于塑造人物。
上述两处桥段,或偏离主线,或僵化主人公形象。总之,都只是满足了作者自己倾诉观点的需要,而没有充分考虑艺术表现的需求。这种情况与叙事文学的基本要求背道而驰。实际上,这类突兀的论述语段是作者思维火花的输出,在创作过程中,作者经常会就本事迸发和联想出一些哲理性的思考。以往的曲家讲求“立主脑”等主次分明的叙事原则,并不会将这些杂感加入作品。但清末文人似乎更加重视这种偶发性、碎片化的思考结果,因此这些议论被生硬地安插在叙事中间,形成了一种随性而发的抒情小段。
至于最后一种模式,将其视为叙事传统的彻底颠覆性创作亦未尝不可。严廷中《秋声谱》之《谱秋》以妓女沈媚娘、书生商金锡的一场倾谈演绎全剧。迟暮的名妓、赴试的举子,相逢相知,却没有上演风流情缘,反而如知己般进行了一场讨论世事和人生的深度对话。听罢媚娘的琵琶絮语,二人同伤今昔(“商金锡”之名暗喻此意)。这首凄凉的秋日悲歌,唱出了《琵琶行》里的“天涯沦落”,唱出了“美人名士,一例飘流,古今同恨”[10]的感伤心曲。
吴藻的《乔影》在内容的编排上更是完全放弃了情节的起伏推进,以一场、一景、一人完成了全剧的表演,看似简单突兀的设计实际上剧本展现的孤寂、幽愤情绪相得益彰。主人公的变装行为、歇斯底里的宣泄,以及与古人的思绪碰撞无不充满荒诞意味,毫不逊色于西方流行的后现代主义独幕话剧。可以说,全剧的氛围、言语、布景、情节与传统的古典戏曲作品截然不同,在戏曲文体发展史上独树一帜。
这些写意化的表达丝毫没有顾及叙事方面的平衡,将清末案头戏的抒情特征推向极致。在写心剧大量涌现的乾嘉时期,这种颠覆叙事原则的写法也曾偶尔出现。如石韫玉的《花间九奏》杂剧集,由九种一折短剧组成,每剧均为截取某个故事片段敷演而来,不以叙述故事、摹写人物为主,专为表达作者当下闲适、高洁的心境。与之相比,清末的案头戏思想更加深刻,内涵更加丰富,风格也更加成熟。《谱秋》《乔影》都以一二个角色出场,而且以谈心或独白的形式支撑了整部戏曲的演出。没有完整的情节,没有前因后果,没有情节发展,只有黄昏平康巷里娓娓清谈的天涯知己和深夜孤寂闺中喁喁细语的郁闷佳人。这样幽暗、朦胧的场景,充满沧桑感、略带神经质的主角,有如一场晦涩的文艺电影,在苍白的画面里隐藏着作者内心绚烂的世界。这些情感不仅代表了作者的内心,也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甚至反映了当时普遍的社会情绪。《谱秋》中美人迟暮、文人落魄之悲与“黄昏”的时间意象都表达出浓重的末世情绪,暗喻了清末社会的迷惘与悲观。《乔影》中的女子身着男装,对着屈原的画像,发出“恨不速变作男儿身”的感慨,既是吴藻个人的精神诉求,更是清末才媛渴望自由和机遇的集体心愿。因此,尽管“写心”“论世”都以颠覆叙事为表象,但“论世”作品写意化场景背后传递的信息和意义要远大于前者。
四 结论
案头戏的“写心”抒情风格随着明清鼎革之际遗民群体的自我剖白开始确立,成为私人领域的自我书写。乾嘉时期,更是出现了大批摹写风月情怀、排遣闲情逸致的精致短剧。尽管这些绮丽典雅的作品情感真挚,但由于所写之情囿于一人一事的小情怀里,难以带来大范围的审美影响和社会意义。随着清末的时代风云,整个中国社会陷入变革和恐慌之中。文人雅士以敏锐的思想意识和自觉的责任担当,体察社会、评说现实,将诗文中“载道”“言志”的创作传统融入戏曲创作中,扩展出“论世”的抒情范式和文体功能,使戏曲的抒情风格更加成熟、内涵更加丰富。清末案头戏抒情风格的变迁过程不仅体现了戏曲文体本身的超越与演变,而且反映了文人群体对社会人生关照与反思,以及时代与文学的复杂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