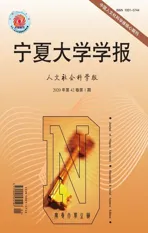试论谭献经世致用的诗文思想
2020-12-14刘红红
刘红红
(内蒙古科技大学 文法学院,内蒙古 包头 014010)
谭献是晚清著名学者, 常州词派的代表人物,晚清词学家,其诗文理论亦颇有建树。 然学界对谭献的研究多集中于词学方面,对谭献诗文理论的研究关注较少, 笔者试图从谭献的学术思想出发,分析其经世致用的诗文思想。
谭献的学术思想与他所处的风云变幻、动荡不安的晚清政局有十分密切的联系。 谭献所处的晚清社会, 内有持续十多年的太平天国运动及捻军起义;外有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中日战争、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等事件。 谭献作为传统知识分子,试图从儒家思想中寻求治乱之方。 谭献的学术思想以经世致用为出发点, 其诗文思想受其学术思想影响,也具有经世致用的特点。
一 谭献经世致用诗文思想的学术来源
《复堂日记》言:“献束发以来,亦欲寻求治乱之本,约之六经。 徵之万物,纵横之三古之陈迹、万里之风会,出其所测识者,拟撰《学论》。 ”[1]谭献自15岁束发之年起,即试图从儒家思想中寻求经世致用的治国方略。 大致说来,谭献从常州今文经学、章学诚史学、颜李实学等传统儒家学说中取资。 谭献《师儒表》首列庄存与、汪中、章学诚、龚自珍四人为绝学门。“今海内多事,前五十年之文章,已可测识。盖贤者如汪容甫、龚定庵、周保绪诸君子,智足以知微也。”[2]谭献认为龚自珍等人致力于讲求微言大义的今文经学,这种学问有益于社会政治。 这是谭献将绝学列于经师、文儒之上的缘由。 下面从四个方面分析谭献经世致用的学术思想。
(一)心折常州学派今文经学
谭献生于道光十二年(1832)。 道光、咸丰年间,今文经学蔚然成风。 谭献治经亦讲求微言大义,推尚今文经学。 吴怀珍《复堂诗序》言谭献为学“能通古今治乱,言天下得失如指诸其掌,国家大政刑大典礼,能讲求其义”[3]。《清史稿·谭廷献传》云:“少负志节,通知时事。 国家政制典礼,能讲求其义。 治经必求西汉诸儒微言大义,不屑屑章句。 ”[4]谭献治经蕲向西京, 归宗常州庄氏, 论学每以微言大义为准则。 谭献对常州今文经学的学者极为推崇:“吾于古人无所偏嗜,于今人之经学,嗜庄方耕、葆琛二家。”[5]这里的庄方耕、庄葆琛分别指庄存与、庄述祖。 庄存与(1719—1788),字方耕,江苏武进(今常州)人。 清代经学家,尤精于春秋公羊学,常州学派的开创者。庄述祖(1750—1816),庄存与之侄,字葆琛,江苏武进人。 于今文经学研究精密。
自咸丰七年游学京师之后,谭献对经史诸子之学一直潜研不辍,学术上倾向于讲微言大义的今文经学,对常州庄氏之学推崇备至。 他认为“方耕(庄存与)侍郎之《春秋》冠绝古今无二”[6]。 谭献从十五岁开始阅读张惠言之弟张琦所编的《宛邻书屋古诗录》, 他对常州学派私淑已久,“庄中白尝以常州学派目我。 谐笑之言,而予且愧不敢当也。 盖庄氏一门,张氏昆季,申耆、晋卿、方立、稚存、渊如,皆当私淑,即仲则之诗篇,又岂易抗颜行乎?”[7]庄棫视谭献为常州学派中人,谭献虽谦称愧不敢当,但却心折常州学派学说。 除了此处提到私淑庄氏一门、张惠言、张琦、李兆洛、董士锡、董佑诚、洪亮吉、孙星衍、黄景仁之外,《复堂日记》中多次出现谭献对常州经学、文学的阅读和评论,私淑之意,跃然纸上。
(二)服膺章学诚史学
钱基博《〈复堂日记〉补录序》言及谭献的学术思想:“以吾观于复堂,就学术论,经义治事,蕲向在西京,扬常州庄氏之学;类族辨物,究心于流别,承会稽章氏之绪。”[8]可见,谭献认同常州庄存与、庄述祖、庄绶甲的经术文章与章学诚的通识古今。除了对常州学派今文经学的推崇之外, 谭献对章学诚的史学服膺最深。“章氏之识冠绝古今,予服膺最深。”[9]谭献在《章先生家传》一文中肯定了章学诚“六经皆史” 说及其在方志学方面的建树:“先生学长于史,尝谓六经皆史,《书》与《春秋》同原,《诗》教最广,太史陈之,官礼制作,与《大易》之制宪,明时圣王经世之大,皆所以为史也。 ”[10]认为其《方志立三书议》具有重要意义。 同时说明章学诚学术的渊源,得益于刘向、刘歆父子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目录学的影响:“先生文不空作,探原官礼,而有得于向、歆父子之传。 ”[11]谭献将章学诚《文史通义》奉为鸿宝,时置案头,表明自己的愿望:“治经史未竟之业,得一卷书,附庸于胡石庄 (胡承诺)、 章实斋两先生, 于愿足矣。 ”[12]于此亦可见出谭献对章学诚的服膺之深。
(三)推崇清初颜李实学及胡承诺学说
谭献《师儒表》列颜元、李塨入大儒门,位居第三。 列胡承诺、黄宗羲、顾炎武入通儒门。 谭献讲求实用,反对桐城派空谈义理。 因同治、光绪年间,内忧外患严重,空谈心性无益于治国安邦,于是谭献主张颜李学派的实学,以实学救弊时世。 钱穆先生曾指出颜元、李塨与章学诚学说的相同点是都“重事功而抑著述”[13]“重践履而轻诵说”[14]。 谭献认为“颜李学说”高于顾炎武、黄宗羲之处在于其能实践朴学,折衷六艺,“李刚主(李塨)承颜氏学,不事空言心性,以六艺三物为教,近世之巨儒”[15]。 颜李学派强调真知力践,以经世致用为宗旨,这是谭献推崇其说的主要原因。
谭献对清初学者胡承诺极为推许, 认为顾炎武、黄宗羲与之相比,大有不如。 如言:“读(胡承诺)《绎志》六日一过。 胡先生粹然一出于正,可见施行。视亭林(顾炎武)更大,视潜斋(应撝谦)更实,视梨洲(黄宗羲)更确,视习斋(颜元)更文。 ”[16]谭献对胡承诺学说的推崇着眼于其体用之学。 有清一代,究心胡氏之学者,始于乾嘉间常州兼学者文人于一身的张惠言与李兆洛。 谭献既心仪常州学派,则欣赏胡承诺固然。 胡承诺为明代崇祯举人,入清不仕,究心学术。 谭献称其为“楚学之大宗”[17],“通经致用,命世儒者”[18]。 其《绎志》一书,谭献评之为“通儒之言,有体有用,足以信今垂后者也”[19]。 称赞是书“言性道者,朴属微至,推究本末;言治理者,黄钟大镛,重规叠矩。 诚经国大业、不朽盛事也”[20]。 而叹其学说“生当阳九,未见施行”[21]。 可谓推崇备至。
(四)吸纳西学
晚清之际,列强入侵,国家内忧外患不绝,故谭献接受“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理念,学习西方的各种长处,不仅局限于形而下的器物层面,也学习形而上的制度层面,试图通过学习西方来寻找御侮安邦之策。 谭献在安徽为官期间,与李鸿章的老师徐子苓有交往。 晚年应洋务派代表人物张之洞之邀担任湖北经心书院院长,也接触到洋务派“中体西用”的思想。 正如萧华荣所言:“根植于特殊的时事之变,洋务运动开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经世致用的新路向。 ”[22]谭献留心西学,着眼点在于“师夷长技以制夷”, 通过吸纳西方的进步学说试图使国家富强。 《复堂日记》中有多则有关谭献对西学态度的条目,现择要列之如下:
假蔼人行箧《天演论》读毕。 西学中之微言大义殊有精邃,不敢易视。[23]
重检《时务报》所载《盛世元音》及重译《富国策》,此皆有实有用者。[24]
阅《瀛海新论》上中下三篇,粤人张君(张自牧)撰。文气渊茂,持论明通,有识之士,有用之文。[25]
高仲瀛来谈艺。究心实学,有志于天文律算,乃欲通西人之术,以求制夷,可谓大义凛然。[26]
南皮张芗涛(张之洞)先生,予举主也。 视学蜀中,撰《书目答问》,可谓学海之津梁、书肆之揭橥,固今日一大师。[27]
这几条资料表明,谭献曾阅读《天演论》《富国策》《瀛海新论》等书,这些著作具有经世致用的功能,为有用之文。 复堂对究心实学的高仲瀛加以赞同,表明他学习、吸纳西学的目的是寻求制夷之方。张之洞是谭献的座师,其所撰《书目答问》以“经世致用”为指导思想,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准则,谭献对此书的评价极高,说明他对中体西用之学的认同。 值得注意的是,甲午战争失败之后,谭献更多从制度层面关注西学,表现出对西方经济学及进化论等先进理念的关注,“呈现出鸦片战争以来知识分子思索中国前途时,由‘器物’到‘精神’的现代性追求的轨迹”[28]。 此外,《谭献日记》中“有用”一词反复出现:
同治九年(1870)十二月十三日:借得沈石渠《诗铎》。 是书二十六卷,为张仲甫丈纂辑;以有用之言为宗旨,于诗教颇见其大。[29]
光绪二年(1876):阅《诗铎》……其义以有用为主。[30]
光绪五年(1879):杨惺吾寄《历代地理沿革图》至……颇有益于世用。[31]
可见,谭献的学术思想既扎根于传统,又紧密联系时代。 无论是传统思想中的今文经学、史学、实学,还是“中体西用”的新型思想,谭献吸纳这些思想的原因在于欲以此解决晚清社会所面临的严峻的现实问题和社会矛盾。
二 谭献经世致用诗文思想的具体表现
谭献曾言:“明以来文学士心光埋没于场屋殆尽,苟无摧廓之日,则江河日下,天可倚杵。 予自知薄植,窃欲主张胡石庄、章实斋之书,辅以容甫、定庵,略用挽救。 ”[32]谭献不满于士人为文只知八股制艺,而倡导实学,试图用胡承诺、章学诚、汪中、龚自珍的经世致用之学改变士人埋头八股制艺的不良文风。 受经世致用学术思想影响,谭献的文学思想也主张有实有用, 这从他自己的表述中可窥一二。《复堂日记》载:“予治文字,窃以有用为体,有余为诣,有我为归,取华落实。 二十余年,耳目差不眩变。 ”[33]光绪十三年谭献撰写的《虚白室集序》言:“往日妄言文章,辄曰有实,曰有用。 ”[34]这表明,谭献认为文章的宗旨是有实有用。 “有实”即重视作品的思想内容,反对空言无事实之文。 “有用”即文章要有益于社会政治。 有实有用成为谭献文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谭献诗文的“有实有用”思想可从两方面来考量:一是从形式而言,反对片面追求语言的华丽而言之无物。 如《虚白室集序》言:“若夫抑扬措注而言家法,侔色选声而号名家,匪用掎摭,心窃耻之。 ”[35]谭献反对“藻绘为文章”,否定空谈“体势”“声病”,造成文章的“华而不实”[36]。 他认为诗文应“植体经训,原本忠孝”[37]。 “诗也者,根柢乎王政,端绪乎人心,章句纂组,盖其末也。 ”[38]认为章句辞采的形式为诗歌之末,王政人心的内容是诗歌之本。 二是从内容而言,认为文章可以观风会,诗可以观化。 其一, 文章要与政治教化相关,“文章之事知政知化,夙昔持论如是”[39]。 《复堂文录甲叙》表明其选录文章的原则是立言经教, 推究世用:“古者学以为治,陈言朝廷之上,荦荦大者,贯五德之运,通万国之情。 其次因事纳忠,一简有一简之益,一篇有一篇之用……”[40]其二,谭献认为“以诗为教”包含诗歌以温柔敦厚为本,以兴观群怨为用两部分。 具体说来包括以诗观时代风尚、观政教得失的诗歌功能及温柔敦厚含蓄蕴藉的诗歌风貌两方面。
首先,重视以诗观政。 诗歌是反映政治和世运的晴雨表, 通过诗歌可以感知政治的清明与昏暗。谭献《明诗》云:
献尝服膺会稽章先生之言曰:“诗教至广, 其用至多。 ”而又师其论文之言,持以论诗。 求夫辞有体要,万变而不离其宗。进退古今,以求其合,盖千一而绌。然而一代政教,一时风尚,则可以观焉。 世盛则草野皆和平之音,世乱则衣冠皆噍杀之音。 流连风月,奔走声气,虽甚繁鄙,而可觇灵长。 悲悼感愤,穷蹙酸嘶,虽甚迫狭,而可识兵凶。 严刑峻法,世变日亟,则群乐放废,家家自以为老庄。 放辟邪侈,名实不副,而不耻干进,人人自以为屈贾。 之数者几相感召,如环无端。 无病而呻与乐忧者,非人情耳。 有道术者,依仁据义,履中蹈和,则上合六义;怀才抱朴,言志永言,则旁通九流,卓矣茂矣。[41]
蔡长林对这段文字解释说:“文章求其体要,在万变不离其宗。 亦即不论形式如何变化,内容所载,仍是一代政教、一时风尚,而后可从中观其风会,识其盛衰,可谓皆有与乎世运也……所以流连风月之鄙辞,可以觇性灵之寡长;悲悼穷蹙之嘶吼,可以识兵凶之迫狭。 而严刑峻法之治,放辟邪侈之时,各有其特殊之显相,皆所以为观风会盛衰之所资。 由是文章之业,非仅关乎诗之靡丽,非徒与于文之排比,而在于求其体要,寓盛衰于几微之际。 谭献所谓‘诗可以观化者’以此。 ”[42]
诗文可观世运的又一体现是谭献对友朋王咏霓、薛福成等描绘世界局势的文字加以赞扬。 谭献认为出使英、法、美等国的王咏霓,其诗能够反映当时世界局势的变化:“王子裳比部同年 《函雅堂诗》蓄思隐轸,而吐音高亮,可以形四方之风,洞当世之变者。 表海壮游,开昔人未有之诗境。 ”[43]谭献为王咏霓所作《六潭文集叙》云:“吾同年友黄岩王咏霓子裳者……从使臣于来宾之国,所以联邦交而洞情伪,身所经历,而神明识量又足以贯终始而握机。 以故先后数年,述事穷理之文,多有古昔所未具。 ”[44]王咏霓因出使邦国而见识广博,其文在内容表现上对传统题材有所突破。 谭献对王咏霓诗文所表现出的新内容持肯定态度。 谭献还曾阅读薛福成《出使日记》并称赞之:“所载能举其大,于欧洲形势及其所学与船车、火器、阿芙蓉均有确当之论。 ”[45]这些评价体现了谭献以诗文观世变的思想。
其次,作诗要符合温柔敦厚的蕴藉之美。 谭献反对诗歌无病呻吟,认为诗人应“依仁据义,履中蹈和”来言志永言,如此方能合乎六义、旁通九流。 其实质是讲究诗歌要温柔敦厚。 谭献对诗歌的这一功能深信不疑。 《复堂日记》记载他对诗歌的看法:“言诗之旨,推本六义,曰温柔敦厚,曰思无邪。 所谓老生者见不生,常谈者见不谈,持此以进退百代,即非一己之爱憎,否则刻画唐突,应声吠影而已。 ”[46]谭献认为诗歌的主旨应该体现诗六义,具有温柔敦厚的诗教精神。 尽管这些说法看似老生常谈,但谭献认为这是诗歌的根本所在。
《唐诗录序》云:“折衷诗教,匪用爱憎,庶闳达方雅,与为商榷云尔。 ”[47]“折衷诗教”即重视诗歌的教化作用及诗歌温柔敦厚的含蓄之美,这是谭献编选《唐诗录》的宗旨所在。 “诗教”一词最早出自《礼记·经解》。 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 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 ”孔颖达《毛诗正义》释云:“《诗》 依违讽谏, 不指切事情, 故云温柔敦厚,是《诗》教也。 ”这里,温柔敦厚是通过“依违讽谏,不指切事情”的言说方式实现的。何为“依违讽谏”?孔颖达曰:“依违谲谏,不直言君之过失。 故言之者无罪,人君不怒其作主而罪戮之;闻之者足以自戒,人君不自知其过而悔之。 ”可见通过“依违谲谏”的委婉方式言说人君过失,从而规劝统治者,体现了温柔敦厚的诗教。 具体到谭献讲的“折衷诗教”,主要表现在变而不失其正的诗歌中。 《金亚匏遗诗叙》云:“献窃闻之,《诗》有《风》有《雅》,则有正有变。 庙堂之制,雍容揄扬,箸后嗣者,正雅尚已。 天人迁革,三事忧危,变雅之作,用等谏书,流而为《春秋》家者,非亡位者之事。 ”[48]这里,谭献提到《诗经》的风雅有正变之分。 正风正雅,以歌颂为主;变风变雅,为乱世之作,以讽谏为主。 “变风变雅”的表述最早见于《诗大序》:“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故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 ”变风变雅是王道衰微、礼义废弛的乱世产物,诗人在乱世抒发感情要合乎礼义,用委婉方式表达对统治者的规劝,是变而不失其正,符合温柔敦厚的诗教精神。 谭献认同这样的创作方式:
《学宛堂诗序》:而忧生念乱,则不能无悲悼感愤之辞,然其中之舂容而夷愉者如故也……世治则可以歌咏功德,扬盛烈于无穷。 世乱则又托微物以极时变,风论政教之失得,绸缪婉笃于伦理之中。[49]
《东埭文稿序》:处乎平世,弹琴以乐先王之风,稽古载笔,发挥名义,以告安雅之君子。 又或不幸阳九兵甲,所见闻多激昂,时复憔悴,易感于怀抱。 叔季之风教,且稍稍远于先王,于是婉笃其辞而不伤,条鬯其旨而不矫,惟有道之人,乃能为有道之文。[50]
正风正雅多为治世的歌功颂德之作,变风变雅是乱世之音,它应托微物以极时变,所谓“绸缪婉笃于伦理之中”“婉笃其辞而不伤”即用委婉方式对政治得失作出评价——讽政教以谏得失,但又须不失雅诗怨悱不乱的风度。 谭献认同用比兴手法委婉讽谏时政,表现忧生念乱,有悲悼感愤之辞却能做到舂容夷愉,无噍杀之音。 谭献赋予诗教以调和治乱盛衰的政治功能,“以诗教来敦厚人品,保证儒家纲纪之不坠”[51]。
三 结语
基于经世致用的诗文思想,谭献提出如下三点看法:
其一,谭献强调言之有物,肯定意内言外之文。《徐先生遗文跋》云:“徐仲平先生盖洞乎艺必达道,儒非空言,与会稽章氏《文史通义》同笙磬之音,但使学于古人者,优柔餍饫。 读徐先生此篇,意内言外,可以摧陷廓清剽贼之文、虚憍之文、空言无事实之文、谐笑酬酢俳优之文,皆如大风之吹垢……献平生之言文章二要,曰有实,曰有用,庶几质诸先生而无疑。 ”[52]这里谭献肯定了徐仲平文章言必有物,讲求实用,与章学诚《文史通义》的写作宗旨相契合。 谭献将“意内言外”之文与剽贼之文、虚憍之文、空言无事实之文、谐笑酬酢俳优之文相对,言下之意是好的文章是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结合,意内指文章的思想性,言外指文章的艺术性。
其二,谭献反对“张皇幽眇,为性道之空言”[53]。受经世致用思想影响,谭献鄙薄理学,反对桐城派空言心性。 关于谭献对待桐城派的态度,《复堂日记》有所交代:“少交袁凤桐敬民,严事邵位西丈,入都以后朱伯韩、王少鹤、孙琴西、冯鲁川诸先生皆附文游之末。诸君固学宋儒之学,传桐城之文。予亦究心方、姚二集,私心有所折衷,不苟同,亦不立异也。 ”[54]这条资料表明谭献在二十多岁入京师期间,交游中多有主张桐城派者,谭献对桐城派的观点有所折衷,不苟同亦不立异。 钱基博在《〈复堂日记〉补录序》中言:“谭氏论文章以有用为体、有馀为诣、有我为归,不尚桐城方、姚之论,而主张胡承诺、章学诚之书,辅以容甫、定庵。 ”[55]可见谭献对桐城派的观点有所疏离。谭献不喜桐城派的原因有二。第一,桐城派空谈宋学义理,不如西汉今文经学的微言大义之学有补于世。 第二,桐城派主张古文,而谭献主张骈散合一。 邓濂写给谭献的书信中谈及谭献独立于桐城派之外的文学宗尚。 邓濂言:“道咸以来,论文者多主张桐城,自一二巨子为之倡,海内学者靡然从之。 其宗法之正,选词之严,诚无可议。 然学者囿于其中,知其正而不知其变,其弊也多失之弱,而矫其弊者,肆其鸿博藻艳之才,□□无所不有。 而驳杂之弊又生,其于文章之大本大原则皆焜乎未有闻也, 独先生以淡雅之才, 明通之识, 刬刮俗学,振□其衰,虽单文片辞,莫不持之有故,言之成理。 简文云,‘斯文未坠,必有英绝而领袖也者’,非先生谁与任此哉? ”[56]这里谈及桐城派的流弊,而谭献为文持之有故、言之成理。 纠正了晚清桐城派空言性理的不良文风,邓濂高度肯定了谭献对扭转桐城派不良文风的功绩。
其三,从诗教出发,谭献批判李渔、袁枚、俞樾等人的“轻佻”之作,认为其书为“支离无用之书”。《复堂日记》记录了谭献对这些文人的批驳之词:“偶借《笠翁一家言》翻阅一过。 鄙猥之言,芜秽艺林。 前有李渔,后又袁枚,杭州之垢也。 ”[57]“经生有俞樾,犹文苑之有袁枚矣,若俞之诗义,则又袁枚之舆台。 ”[58]其中谭献对袁枚的批评,言辞最为激烈:
《古诗一首呈孙先生思澧仁渊》:吾乡溯前辈,杭厉高颉颃。 西江近兀奡,美媛乏老苍。 一从袁枚出,邪说何猖狂。 俳优语嘲诙,鲍老舞郎当。[59]
《复堂日记》:其(袁枚)全集罅漏百出,世多达者,不待哓哓。独其诗之失,大似明季钟、谭,败坏风教……总之率天下人不读书、不求理、不师古、不循规矩,皆《五行志》所谓文妖也。 钟、谭阴幽,近鬼,袁吊诡,近狐。 洪亮吉评之,良有悬解。钟、谭纯阴,遂兆亡国,袁阴战场,亦兆东南大乱,非文章细故也。[60]
《明诗录序》:袁氏非通变之材,一脔知味,钟、谭为亡国之妖,去之若浼。 极盛而衰,亦足知政。[61]
杭世骏、厉鹗、袁枚为清代杭州有名的诗人,与谭献是同乡, 但谭献对这三位诗人评价截然不同。谭献肯定了杭世骏、厉鹗的诗歌成就,而批评袁枚诗歌为猖狂之邪说,风格诙谐调笑似俳优。 袁枚为诗主张性灵,追求个性自由解放,对儒家诗教提出异议。 谭献视袁枚为“文妖”,批评袁枚诗歌有违诗教。 不仅批评袁枚,对与袁枚有相似文学追求的明末竟陵诗派钟惺、谭元春也嗤之以鼻,批评其诗为鬼为狐。 正是因为其诗歌不讲究诗教,于事无补,所以才兆端了明代的灭亡。 谭献对诗教的推崇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谭献批评袁枚诗背离诗教,而对与袁枚同时代能够写诗关乎诗教之人,则大加赞扬:“阅《稼书堂诗》。雍容夷愉,所谓诗可以观化者。当袁枚时,颇不染其恶习,信乎君子人也。 ”[62]与袁枚诗歌不同,潘惺庵《稼书堂诗》可以观政教得失,是故谭献对其评价很高。 又如谭献盛赞王士禛诗“论本朝诗,终当以渔洋为第一”[63]。 个中原因是因为王士禛诗符合谭献的诗学取向,其诗中和敦厚,可以观政化:“予服渔洋中和敦厚,可觇世运,所谓诗可以观化者在此。 ”[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