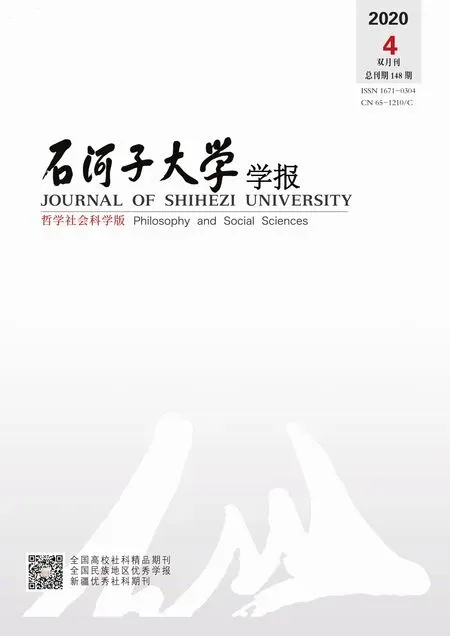受让方不具有资质的矿业权转让合同效力认定之探究
2020-12-09江钦辉
江钦辉
(新疆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新疆乌鲁木齐830011)
一、问题的提出
当前,矿业权转让合同纠纷已成为重要的民事案件类型,司法实践中发生了大量的矿业权转让合同纠纷案件。虽然矿业权具有民事物权属性,但矿产资源的开采涉及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等问题,故国家对矿业权的转让给予了严格的规范,包括对矿业权受让人设定资质条件的限制。然而,由于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矿业权转让合同违反“矿业权受让人资质条件”这一限制条款的私法后果,故受让方不具有资质的矿业权转让合同之效力问题,成为了司法实践争议的焦点。
司法实践中,不同法院对于受让方不具有资质的矿业权转让合同的效力认定问题,由于寻找的请求权基础不同,导致了“同案不同判”,有损法律的权威和司法的公信力。总体而言,对于合同效力的认定,主要有两种不同的裁判意见。第一种裁判意见认为,对于受让方不具有资质的矿业权转让合同,由于合同未经行政机关批准,故认定为成立未生效①七台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七民商初字第2号民事判决书;陇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陇民一初字第10号民事判决书;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常民二终字第78号民事判决书。。第二种裁判意见认为,对于受让方不具有资质的矿业权转让合同,应认定为无效②浙江省义乌市人民法院〔2018〕浙0782民初8058号民事判决书;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015〕黔南民商终字第123号民事判决书;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黑高商终字第83号民事判决书;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民申1077号民事裁定书;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2013〕甘民二终字第91号民事判决书;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川民终字第574号民事判决书;湖南省石门县人民法院〔2012〕石民二初字第9号民事判决书;四川省宜宾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宜民初字第99号民事判决。。而司法实践中之所以出现这两种不同的裁判意见,究其原因,要么忽略了《矿产资源法》第3条③《矿产资源法》第3条规定:“矿产资源属于国家所有,由国务院行使国家对矿产资源的所有权。地表或者地下的矿产资源的国家所有权,不因其所依附的土地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不同而改变。国家保障矿产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坏矿产资源。各级人民政府必须加强矿产资源的保护工作。勘查、开采矿产资源,必须依法分别申请、经批准取得探矿权、采矿权,并办理登记;但是,已经依法申请取得采矿权的矿山企业在划定的矿区范围内为本企业的生产而进行的勘查除外。国家保护探矿权和采矿权不受侵犯,保障矿区和勘查作业区的生产秩序、工作秩序不受影响和破坏。从事矿产资源勘查和开采的,必须符合规定的资质条件。”以及《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管理办法》(以下简称《转让管理办法》)第7条④《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管理办法》第7条规定:“探矿权或者采矿权转让的受让人,应当符合《矿产资源勘查区块登记管理办法》或者《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法》规定的有关探矿权申请人或者采矿权申请人的条件。”有关“矿业权受让人资质条件”之规定的适用,要么对《矿产资源法》第3条以及《转让管理办法》第7条有关“矿业权受让人资质条件”规定的规范性质认识不一。
二、两种不同裁判意见的争辩
(一)矿业权转让合同成立未生效论
该种裁判意见认为,根据《合同法》第44条⑤《合同法》第44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转让管理办法》第10条⑥《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管理办法》第10条规定:“申请转让探矿权、采矿权的,审批管理机关应当自收到转让申请之日起40日内,作出准予转让或者不准转让的决定,并通知转让人和受让人。准予转让的,转让人和受让人应当自收到批准转让通知之日起60日内,到原发证机关办理变更登记手续;受让人按照国家规定缴纳有关费用后,领取勘查许可证或者采矿许可证,成为探矿权人或者采矿权人。批准转让的,转让合同自批准之日起生效。不准转让的,审批管理机关应当说明理由。”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以下简称《合同法解释一》)第9条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9条规定:“依照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合同应当办理批准手续,或者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才生效,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当事人仍未办理批准手续的,或者仍未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未生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合同应当办理登记手续,但未规定登记后生效的,当事人未办理登记手续不影响合同的效力,合同标的物所有权及其他物权不能转移。合同法第七十七条第二款、第八十七条、第九十六条第二款所列合同变更、转让、解除等情形,依照前款规定处理。”规定,因矿业权转让行为属于须报有权机关批准才能生效的法律行为,故受让方不具有资质之矿业权转让合同如未经有权机关批准,则处于成立但未生效状态。
如在“七台河市双利煤焦有限责任公司等与七台河市宏伟煤矿四井采矿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中,一审法院依据《合同法》第44条第2款、《合同法解释一》第9条及《转让管理办法》第10条第3款的规定,认为虽然闫新春将宏伟煤矿四井转让给双利公司后,双利公司实际接收了煤矿,并组织进行了生产,但双方一直未办理煤矿转让的审批手续,也未办理过户手续,后煤矿被关闭,至煤矿整合前,该煤矿的所有权人仍是闫新春,故诉争“采矿权转让协议”未生效⑧七台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七民商初字第2号民事判决书。。又如在“康县山川矿业开发有限公司与刘旗探矿权转让纠纷”一案中,一审法院依据《合同法》第32条⑨《合同法》第32条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第44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以下简称《合同法解释二》)第8条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8条规定:“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经批准或者登记才能生效的合同成立后,有义务办理申请批准或者申请登记等手续的一方当事人未按照法律规定或者合同约定办理申请批准或者未申请登记的,属于合同法第四十二条第(三)项规定的“其他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和相对人的请求,判决相对人自己办理有关手续;对方当事人对由此产生的费用和给相对人造成的实际损失,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规定,刘旗与山川公司签订的“探矿权转让协议”是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的法律行为,因该“探矿权转让协议”未报甘肃省国土资源厅批准,应为成立但未生效的合同。按照该“探矿权转让协议”第4条的约定,山川公司有义务协助刘旗办理矿权变更手续,相关费用由乙方承担。合同成立后,在刘旗依约履行了120万元的主要给付义务后,山川公司仍以刘旗未完全履行协议为由拒绝履行其协助报批义务,导致合同未生效②陇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陇民一初字第10号民事判决书。。再如在“匡鸿与杜亮谋等采矿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中,二审法院依据《矿产资源法》第6条第1款第(二)项的规定,采矿权须经依法批准后,才可转让给他人。案涉《石门县磨市九条岭石灰厂转卖协议》是当事人匡鸿与刘玉红、刘玉治、杜亮谋、周乃军、陈位菊五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转卖协议所涉标的物包括石灰岩采矿权和石煤采矿权。而采矿权转让未经相关审批管理机关批准,应认定采矿权转让合同未生效。但不影响当事人履行报批义务条款及因该报批义务而设定的相关条款的生效。并认为,《矿产资源法》第3条以及《转让管理办法》第7条有关“矿业权受让人资质条件”之规定属于管理性强制规定,即便上诉人匡鸿不具有采矿权受让人的资质条件,也不宜认定采矿权转让合同无效③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常民二终字第78号民事判决书。。
对此,学界有学者也持有该种观点,认为采矿权受让方的资质条件规定仅是“对采矿权人的行为能力和实质条件的限制”,受让方是否符合资质条件属于行政机关的管理职责范畴,故该矿业权受让人资质条款的规定属于管理性强制规定,不会影响到转让合同的效力。如受让方不具备资质条件之采矿权转让合同未经有权机关批准,则应认定为未生效[1]75-77。笔者认为,该司法进路和学者观点不具妥当性,不可取。
其一,从合同效力的认定路径来看,在合同成立后,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对合同进行法律上的价值评价,即对合同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有效要件、有无违反《合同法》第52条④《合同法》第52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规定进行审查。如合同存在《合同法》第52条规定的合同无效之情形,则合同应认定为无效。如合同不存在《合同法》第52条规定的合同无效之情形,则还须进一步判断合同是否存在法定或约定的生效条件。如合同不存在法定或约定的生效条件,则合同生效,当事人双方依照合同的约定享有权利履行义务。如合同存在法定或约定的生效条件,则在不具备法定或约定的生效条件时,合同不发生履行效力,当事人双方不能依照合同的约定享有权利履行义务。对此,最高人民法院也持有该种认识⑤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民申1077号民事裁定书。,值得肯定。而该司法进路,在判断矿业权转让合同成立后,并没有对受让方不具有资质的矿业权转让合同是否违反《合同法》第52条之规定进行审查的情况下,即基于矿业权转让合同未经有权机关的批准,而直接依据《合同法》第44条第2款、《转让管理办法》第10条第3款及《合同法解释一》第9条的规定,认定矿业权转让合同不具备法定的生效条件,处于成立但未生效状态,显然发生了法律适用上的逻辑跳跃,忽略了《矿产资源法》第3条以及《转让管理办法》第7条有关“矿业权受让人资质条件”之规定的适用。
其二,该观点将《矿产资源法》第3条以及《转让管理办法》第7条有关“矿业权受让人资质条件”之规定的规范性质识别为“管理性强制规定”,进而得出“即便当事人不具有矿业权受让人的资质条件,也不会导致矿业权转让合同无效”的结论,从而为直接适用《合同法》第44条第2款、《转让管理办法》第10条第3款及《合同法解释一》第9条之规定提供依据。但将法律、行政法规有关“矿业权受让人资质条件”之规定的规范性质识别为“管理性强制规定”,在认识上却有检讨的余地,具体理由下文将予以说明。
其三,这种将受让方不具有资质之矿业权转让合同的效力认定为成立未生效,但又认为当事人有关报批义务条款以及违反报批义务条款应承担之责任条款的生效并不受影响的做法,也有检讨的余地。一方面,在合同效力层次分为“成立—生效”的传统理论下,将合同认定为“未生效”无法为未经批准之矿业权转让合同的当事人负有报批义务提供法律的正当性基础;另一方面,这种做法将矿业权转让合同效力定性为“未生效”的同时,又将“当事人不履行报批义务的责任指向了违约责任的范畴,导致了责任定性与责任承担认识上的不同”,凸显了司法实践逻辑的混乱[2]113-119。
(二)矿业权转让合同无效论
关于受让方不具有资质的矿业权转让合同无效的观点,司法实践中有五种不同的司法进路。
第一种进路根据《合同法》第44条、《转让管理办法》第10条的规定,以“矿业权转让合同”未获有权机关批准为由,认定该转让合同无效。即“未获有权机关批准——合同无效”的司法进路。笔者认为,该种进路在转让合同的效力认定上是妥当的,但其寻找的请求权基础却不具有妥当性,不可取。其一,如上所述,该进路在没有对受让方不具备资质条件的矿业权转让合同是否违反《合同法》第52条之规定进行审查的情况下,却直接依据《合同法》第44条第2款、《转让管理办法》第10条第3款的规定,基于矿业权转让合同未获有权机关的批准而认定该转让合同无效,同样忽略了《矿产资源法》第3条以及《转让管理办法》第7条有关“矿业权受让人资质条件”之规定的适用,发生了法律适用上的逻辑跳跃。其二,将未获有权机关批准的矿业权转让合同认定为无效,使得行政审批成为影响合同是否有效的决定要件。但该种做法一方面混淆了《合同法》第52条与第44条不同规定在功能和作用的不同,另一方面也使得行政权有不当僭越司法权之嫌。因为合同的价值评价专属于裁判机关,而行政机关则无此权限。因此,如果矿业权转让合同存在《合同法》第52条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情形,即便获得行政机关的批准,该转让合同也不会因为有权机关的批准而有效,裁判机关仍有权认定合同无效。正如日本学者美浓部达吉指出,当事人之间的合同即使“已取得行政官厅的认可”,但如对合同本身的效力发生了争议,法院也得“审查该合同的效力”[3]187。
第二种进路根据《合同法》第52条第(三)项的规定,基于“矿业权转让合同”签订后当事人不积极履行报批义务,在合同未经批准的情况下受让方即行开采,属于“非法转让采矿权”,从而认定合同当事人“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得出“矿业权转让合同”无效的结论。即“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合同无效”的司法进路。如在“七台河市双利煤焦有限责任公司等与七台河市宏伟煤矿四井采矿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中,二审法院认为,宏伟煤矿与双利公司签订的诉争“采矿权转让协议”约定,“闫新春将其投资的包括资源价款、井巷工程等在内的宏伟煤矿四井全部转让给双利公司,并将该矿井证照、印章全部交付给双利公司”,“双利公司给付全部转让款后,宏伟煤矿四井协助双利公司办理转让手续”。因该协议签订后,闫新春即将涉案煤矿交付给双利公司,同时双利公司接收案涉煤矿后,在未办理采矿权审批手续的情况下即行生产,且直至案涉煤矿被关闭时仍未办理采矿权审批手续,故双方当事人虽签订了“采矿权转让协议”,但却通过合同约定不积极办理采矿权审批手续,并在未办理采矿权审批手续的情况下即行生产,该行为应属非法开采,构成非法转让采矿权,应认定诉争“采矿权转让协议”系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根据《合同法》第52条的规定,该转让协议无效①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黑高商终字第83号民事判决书。。
笔者认为,该种进路在转让合同的效力认定上是妥当的,但其寻找的请求权基础也不具有妥当性,不可取。而该请求权基础之所以不具有妥当性,其根源在于对事实认定不准确。该进路将“矿业权转让合同”签订后受让人不积极办理报批手续却在转让方交付案涉煤矿后进行非法开采,定性为“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显然有欠妥当。因为根据《合同法》第44条第2款、《转让管理办法》第10条第3款及《合同法解释一》第9条的规定,当事人之间的“矿业权转让合同”未经批准仅是成立但未生效,难谓“合法形式”,矿产资源主管部门对矿产资源的勘探、开发进行监督,本就是其职责范围之内的事务,“不积极办理报批手续”也不能就此认为其有实现“非法开采”不受矿产资源主管部门监督的“非法目的”。更何况,该进路也忽略了《矿产资源法》第3条以及《转让管理办法》第7条有关“矿业权受让人资质条件”之规定的适用,而法律、行政法规有关“矿业权受让人资质条件”之规定的规范性质是否应识别为“管理性强制规定”,从而不对合同的效力产生影响,在认识上也有检讨的余地,具体理由下文将予以说明。
第三种进路将《矿产资源法》第6条①《矿产资源法》第6条规定:“除按下列规定可以转让外,探矿权、采矿权不得转让:(一)探矿权人有权在划定的勘查作业区内进行规定的勘查作业,有权优先取得勘查作业区内矿产资源的采矿权。探矿权人在完成规定的最低勘查投入后,经依法批准,可以将探矿权转让他人。(二)已取得采矿权的矿山企业,因企业合并、分立,与他人合资、合作经营,或者因企业资产出售以及有其他变更企业资产产权的情形而需要变更采矿权主体的,经依法批准可以将采矿权转让他人采矿。前款规定的具体办法和实施步骤由国务院规定。禁止将探矿权、采矿权倒卖牟利。”、《转让管理办法》第5条②《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管理办法》第5条规定:“转让探矿权,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一)自颁发勘查许可证之日起满2年,或者在勘查作业区内发现可供进一步勘查或者开采的矿产资源;(二)完成规定的最低勘查投入;(三)探矿权属无争议;(四)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已经缴纳探矿权使用费、探矿权价款;(五)国务院地质矿产主管部门规定的其他条件。”的规定识别为效力性强制规定,因“矿业权转让合同”违反了该转让限制条件的规定,应认定为无效。并基于双方当事人均明知矿业权受让方须具备法定的资质条件,认定双方当事人都有主观上的过错,应对由此造成的损失承担相应的责任,即“违反矿业权转让限制条件——合同无效”的司法进路。如在“康县山川矿业开发有限公司与刘旗探矿权转让纠纷”一案中,二审法院认为,山川公司与刘旗签订的《探矿权转让协议》违反了《矿产资源法》第6条、《转让管理办法》第5条的强制性规定,该转让协议被认定为无效,并因“山川公司与刘旗均明知转让受让探矿权须有一定资质,且不能转让给个人”,故认定山川公司与刘旗对《探矿权转让协议》的无效均有过错,对由此造成的损失双方应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③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2013〕甘民二终字第91号民事判决书。。笔者认为,该种进路对合同效力的认定是妥当的,但该合同无效的认定是基于“矿业权转让合同”违反《矿产资源法》第6条、《转让管理办法》第5条的规定而得出,显然是建立在将《矿产资源法》第6条、《转让管理办法》第5条的规定识别为“效力性强制规定”的基础上。然而,将《矿产资源法》第6条、《转让管理办法》第5条的规定识别为“效力性强制规定”,在认识上却有检讨的余地,不具妥当性。从强制性规定的识别上看,如果“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范明确规定对其的违反将导致合同的无效”,那么“该规定就属于效力性强制规范”;如果“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范并没有规定对其的违反将导致合同的无效”,但“违反该规定如使合同继续有效将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也应当认定“该规定为效力性强制规定”[4]112。可见,对于《矿产资源法》第6条、《转让管理办法》第5条的规定而言,要判断其是否属于“效力性强制规定”,首先要看相关法律、行政法规是否明确规定违反有关“矿业权转让限制条件”的规范将导致合同无效。从《矿产资源法》第42条④《矿产资源法》第42条规定:“买卖、出租或者以其他形式转让矿产资源的,没收违法所得,处以罚款。违反本法第六条的规定将探矿权、采矿权倒卖牟利的,吊销勘查许可证、采矿许可证,没收违法所得,处以罚款。”的规定来看,对于违反“矿业权转让限制条件”之规范的行为,行政机关可以给予行政处罚。而《转让管理办法》则未对违反“矿业权转让限制条件”之规范的行为法律后果作出规定。因此,从法律规定的违反“矿业权转让限制条件”之规范的行为后果上看,无法得出《矿产资源法》第6条以及《转让管理办法》第5条有关“矿业权转让限制条件”的规定属于效力性强制规定。其次还要看法律、行政法规有关“矿业权转让限制条件”之规范的立法目的到底是为了维护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还是纯粹为维护矿业权的勘探、开采秩序和转让秩序而基于行政管理的需要。从《矿产资源法》第6条以及《转让管理办法》第5条的立法目的来看,法律之所以规定矿业权转让的限制条件,主要是基于行政机关纯粹为“维护矿业权转让秩序、实现矿业权有序流转”的需要,以为行政机关进行管理提供法律上的依据。因此,不宜将《矿产资源法》第6条以及《转让管理办法》第5条有关“矿业权转让限制条件”的规定认定为效力性强制规定,而应认定为管理性强制规范,矿业权转让合同违反《矿产资源法》第6条以及《转让管理办法》第5条的规定,并不会导致合同的无效。对此,最高人民法院也持有该种见解①最高人民法院〔2011〕民申字第512号民事裁定书;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民申344号民事裁定书。,值得肯定。当然,该进路基于矿业权受让方不具备法定的资质条件而认定双方当事人对合同的无效均有过错,应对由此造成的损失承担相应责任的做法,是值得肯定的。
第四种进路根据法律、行政法规有关“矿业权受让人资质条件”的规定,以受让人不具有资质不能获准转让进而取得采矿权许可证,否则将可能危及矿山生产安全、资源环境安全,从而损及社会公共利益为由,依据《合同法》第52条第(四)项关于“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合同无效”的规定,认定“矿业权转让合同”无效,即“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合同无效”的司法进路。如在“何涛、杨淋与张华清采矿权转让纠纷”一案中,二审法院认为,《转让管理办法》第7条、《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法》第5条②《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法》第5条规定:“采矿权申请人申请办理采矿许可证时,应当向登记管理机关提交下列资料:(一)申请登记书和矿区范围图;(二)采矿权申请人资质条件的证明;(三)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四)依法设立矿山企业的批准文件;(五)开采矿产资源的环境影响评价报告;(六)国务院地质矿产主管部门规定提交的其他资料。申请开采国家规划矿区或者对国民经济具有重要价值的矿区内的矿产资源和国家实行保护性开采的特定矿种的,还应当提交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的批准文件。申请开采石油、天然气的,还应当提交国务院批准设立石油公司或者同意进行石油、天然气开采的批准文件以及采矿企业法人资格证明。”的规定明确了法律对“采矿权的市场准入”采取了严格标准,对采矿权转让的受让人的资质条件亦予以严格的限制。而根据国土资源部国土资发〔2011〕14号《关于进一步完善采矿权登记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第13条③《国土资源部关于进一步完善采矿权登记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第13条规定:“申请采矿权应具有独立企业法人资格,企业注册资本应不少于经审定的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测算的矿山建设投资总额的百分之三十,外商投资企业申请限制类矿种采矿权的,应出具有关部门的项目核准文件。申请人在取得采矿许可证后,必须具备其他有关法定条件后方可实施开采作业。采矿权人应当严格按照经审查批准的相关要件实施开采作业,接受相关部门的监督管理。”、第19条④《国土资源部关于进一步完善采矿权登记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第19条规定:“转让采矿权受让人应具备本通知第十三条规定的采矿权申请人条件,并承继该采矿权的权利、义务。”以及国土资源部国土资发〔2000〕309号《矿业权出让转让管理暂行规定》第19条⑤《矿业权出让转让管理暂行规定》第19条:“矿业权申请人应是出资人或由其出资设立的法人。但是,国家出资勘查的,由出资的机构指定探矿权申请人。两个以上出资人设立合资或合作企业进行勘查、开采矿产资源的,企业是矿业权申请人;不设立合作企业进行勘查、开采矿产资源的,则由出资人共同出具书面文件指定矿业权申请人。采矿权申请人应为企业法人,个体采矿的应依法设立个人独资企业。”的规定可知,采矿权受让人须为企业法人,个体采矿的应依法设立个人独资企业,自然人主体作为受让主体申请办理采矿权许可证将不能获准。而上述内容是国土资源部根据《转让管理办法》第7条、《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法》第5条第1款第(六)项的授权,对采矿权申请人应具备的条件作出的具体规定,上述内容亦是采矿权转让的受让人申请办理采矿权许可证必备的条件之一,任一条件不具备,均不能获准转让进而取得采矿权许可证。据此,根据《合同法》第52条第(四)项有关“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合同无效”的规定,何涛、杨淋因不具备采矿权受让人主体资质,应认定诉争《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系无效合同⑥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川民终字第574号民事判决书。。
对此,学界有学者也持有该观点,认为法律之所以对主体设定严格的市场准入制度和资质条件,其目的在于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因此,受让方不具有资质的矿业权转让合同因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违反了《合同法》第52条第(四)项的规定,应认定为无效[5]70-80。笔者认为,该种进路和学者观点对合同效力的认定是妥当的,其以“矿业权转让给不具有资质的受让人”,将损害到社会公共利益作为认定合同无效的理由,也是妥当的。但在法律、行政法规对“矿业权受让方的资质条件”作出强制性规定的情形下,并认为该规定的立法目的在于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时,选择适用《合同法》第52条第(四)项的规定,而不选择适用《合同法》第52条第(五)项的规定,在法律适用的优先顺位上有检讨的余地。从法律的适用逻辑来看,在法律、行政法规对“矿业权受让方资质条件”作出强制性规定的情况下,应优先适用“违反强制性规定”对合同效力进行判断,即应优先适用《合同法》第52条第(五)项的规定来判定“矿业权转让合同”的效力。而在无“强制性规定”时,才可以适用“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对合同效力进行判断。即在矿业权转让行为损害到社会公共利益,但又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时,方可适用《合同法》第52条第(四)项的规定来判定“矿业权转让合同”的效力。故《合同法》第52条第(五)项规定乃是第(四)项规定的具体化,属于特别法与一般法的关系,前者优先适用[6]113-122。其理由在于“社会公共利益”的概念过于抽象,容易导致司法权的滥用。正如有学者指出:“公序良俗在对法律行为的控制中可能蜕变为以维护道德之名而滥用公众授予的权力,立法上所保障的个人自由可能在司法的层面因公权力的销蚀而化为乌有。”[7]95-102因此,对于《合同法》第52条第(四)项的规定,仅在《合同法》第52条第(五)项的规定无法适用时,起到补充适用的作用,以避免司法权的滥用。
第五种进路将《矿产资源法》第3条以及《转让管理办法》第7条的强制性规定识别为《合同法》第52条第(五)项规定的效力性强制规范,以受让人不具有资质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为由,依据《合同法》第52条第(五)项关于“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的规定,认定受让人不具有资质的矿业权转让合同无效,即“违反矿业权受让人资质条件——合同无效”的司法进路。如在“闫新春等诉七台河市双利煤焦有限责任公司采矿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中,再审法院经审查认为,根据《矿产资源法》第3条第4款的规定,从事矿产资源勘探、开采的主体,必须具有相应的资质。而案涉“煤矿转让协议”受让方双利公司不仅不具有采矿权资质,而且闫新春与双利公司未经批准擅自转让采矿权,并在未办理采矿权转让手续的情况下非法开采,严重扰乱了国家矿产资源管理秩序,损害了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因此,闫新春与双利公司签订的“煤矿转让协议”因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被认定为无效①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民申1077号民事裁定书。。如在“匡鸿与杜亮谋等采矿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中,一审法院认为,《矿产资源法》第3条、《转让管理办法》第7条对采矿权的受让人资质条件的强制性规定,属于涉及矿产资源开采保护和安全生产等社会公共利益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案涉转卖协议所涉及石灰岩和石煤采矿权均以石灰厂的名义申办,虽然石煤采矿许可证上记载的经济类型为私营独资企业,但石灰厂的工商登记性质为个体工商户,故匡鸿不能因石灰厂的整体受让而承继取得采矿权申请人应具备的独立企业法人主体资质,且匡鸿在本案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也未设立具有法人资格的矿山企业。故因匡鸿不具有申请采矿权的资质条件,根据《合同法》第52条第(五)项的规定以及《合同法解释二》第14条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14条规定:“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规定,案涉转卖协议应认定为无效③湖南省石门县人民法院〔2012〕石民二初字第9号民事判决书。。对于该种司法进路,笔者基本表示赞同。但该司法进路允许合同效力的补正之做法在理论上却有检讨的余地。因为按照民法的理论,合同的无效是自始的、绝对的、确定的无效,是无法予以补正的[8]302。
三、“违反矿业权受让人资质条件——合同无效”之进路证成
对于受让方不具有资质的矿业权转让合同的效力认定问题,应采取何种司法进路,才能正确适用法律,以维护国家的经济秩序。笔者认为,对于合同的效力认定路径而言,在合同成立后,首先涉及到对合同进行法律上的价值评价问题,即审查合同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有效要件,有无《合同法》第52条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情形。只有在作出合同有效的判断后,才需进一步审查合同是否存在法定或约定的生效条件。因此,对于矿业权转让合同,在受让方不具备资质条件的情况下,如何认定合同的效力,首先涉及到《矿产资源法》第3条以及《转让管理办法》7条有关“矿业权受让人资质条件”规定之规范性质的识别问题,以妥当寻找请求权基础,实现法律设立矿业权市场准入制度的立法目的。而对《矿产资源法》第3条以及《转让管理办法》7条有关“矿业权受让人资质条件”的规定之规范性质进行识别,就是要解决法律、行政法规有关“矿业权受让人资质条件”的强制性规定是否属于《合同法》第52条第(五)项规定的“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范畴的问题。
对于《合同法》第52条第(五)项关于“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之规定的适用,《合同法解释一》第4条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4条规定:“合同法实施以后,人民法院确认合同无效,应当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为依据,不得以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为依据。”进一步明确了,在《合同法》实施以后,人民法院只能依据“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范,确认合同无效。而对于是否意味着合同行为违反“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规定的所有强制性规范,人民法院都应当确认合同无效呢?《合同法解释二》第14条则进一步将《合同法》第52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限缩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由此可见,人民法院依据《合同法》第52条第(五)项的规定来认定合同无效,应以合同行为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规定”为准。
那么,“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规定”应如何判断呢?如上所述,如果“强制性规定明确了违反其将导致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则该强制性规定属于“效力性强制规定”,没有疑义。但如果“强制性规定没有明确违反其将导致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时,应如何判断该强制性规定是否属于“效力性强制规定”呢?对此,有学者指出,区分强制性规定是“效力性强制规定”还是“管理性强制规定”,可从强制性规定所保护的利益不同进行判断。如果强制性规定所保护的是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那么该强制性规定属于“效力性强制规定”;如果强制性规定所保护的不是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而只是保护民事主体的利益,那么该强制性规定则属于“管理性强制规定”[9]67-71。还有学者指出,区分强制性规定是“效力性强制规定”还是“管理性强制规定”,可“运用历史解释和目的解释方法去分析和判断”强制性规定的规范目的。如果强制性规定经过“运用历史解释和目的解释的方法,我们发现它是以直接维护公共利益为目的的”,那么该强制性规定就属于“效力性强制规范”;但如果发现其规范目的是为了“维护管理秩序”,那么该强制性规定则属于“管理性强制规定”[10]151-160。笔者表示赞同。因为要判断某强制性规定是否属于“效力性强制规定”,实质上涉及到对该规定之规范性质的判定,而法律规定的规范性质须以规范意旨为判断标准[11]153-174。从本质上看,《合同法》第52条第(五)项之规定作为引介条款,其功能和价值在于为国家公权力适度干预和管制私法自治提供基本的途径和手段。而国家公权力适度干预和管制私法自治的正当性则在于国家基于对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保护的需要。正如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中提出,认定强制性规定的类型应通过法律法规的意旨加以判断。因此,“效力性强制规定”的判断路径在于通过直接考察该具体法律规范的立法目的,是否在于保护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加以判别。如果该法律规范的立法目的在于保护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那么违反该“强制性规定”的合同将有损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应当认定合同无效;如果该法律规范的立法目的不在于保护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而仅在于维护纯粹的管理秩序,那么违反该“强制性规定”的合同并没有损害到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就不宜认定为无效。当然,对于违反纯粹维护管理秩序的强制性规范的行为,有关行政机关可以给予行政处罚。正如史尚宽先生指出,识别“强制性规定”,“在我民法尚不能全依条文方式以为决定,应依条文之体裁及法律规定本身之目的,以定之”[12]329。也如日本学者我妻荣先生认为,识别“强制性规定”,只能是“分别对管制法规的立法宗旨、对违反社会行为的伦理非难程度、对一般交易的影响、当事人间的信用、公正等进行仔细探讨加以决定。”[13]248
而纵观《矿产资源法》《转让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因法律、行政法规并未明确违反“矿业权受让人资质条件的强制性规范”将导致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故无法从法律、行政法规之规定本身来判断《矿产资源法》第3条以及《转让管理办法》第7条有关“矿业权受让人资质条件”的强制性规定是否属于效力性强制规定。因此,要判断《矿产资源法》第3条以及《转让管理办法》第7条有关“矿业权受让人资质条件”的强制性规定,是否属于《合同法》第52条第(五)项规定的“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规定”,关键在于考察《矿产资源法》第3条以及《转让管理办法》第7条有关“矿业权受让人资质条件”条款的立法目的是否在于保护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如是则属于“效力性强制规定”,如不是则属于“管理性强制规定”。
从《矿产资源法》第3条以及《转让管理办法》第7条的立法目的来看,立法上之所以对矿业权市场设立严格的准入条件,就是因为矿业权人的资质条件设置不仅涉及到“矿产资源的可持续开发利用”问题,也涉及到“生态环境的保护”问题以及“矿山企业的生产安全”问题,是为了维护国家的经济秩序而作出的制度安排。可见,法律、行政法规有关“矿业权受让人资质要求”的条款设置,其立法目的并非为了维护纯粹的管理秩序,而是为了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由此,应将《矿产资源法》第3条以及《转让管理办法》第7条有关“矿业权受让人资质条件”的强制性规定识别为“效力性强制规范”,而非“管理性强制规范”。
因此,对于“受让方不具有资质”的矿业权转让合同,因违反了《矿产资源法》第3条以及《转让管理办法》第7条有关“矿业权受让人资质条件”之规定这一“效力性强制规范”,依据《合同法》第52条第(五)项的规定,应认定为无效。对此,最高人民法院也持该种观点①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民申1077号民事裁定书。,值得肯定。
四、结语
对于“受让方不具有资质”的矿业权转让合同的效力认定问题,因司法实践中不同法官寻找的请求权基础不同而导致了“同案不同判”,主要有合同成立未生效和合同无效两种不同的观点。而矿业权转让合同无效论又有“未获有权机关批准——合同无效”“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合同无效”“违反矿业权转让限制条件——合同无效”“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合同无效”“违反矿业权受让人资质条件——合同无效”的不同司法进路。因“受让方不具有资质”的矿业权转让行为违反了《矿产资源法》第3条以及《转让管理办法》第7条有关“矿业权受让人资质条件”的强制性规定,而法律、行政法规有关“矿业权受让人资质条件”之强制性规定又属于“效力性强制规范”的范畴,故应采取“违反矿业权受让人资质条件——合同无效”的裁判路径,依据《合同法》第52条第(五)项关于“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的规定,认定受让方不具备资质条件的“矿业权转让合同”无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