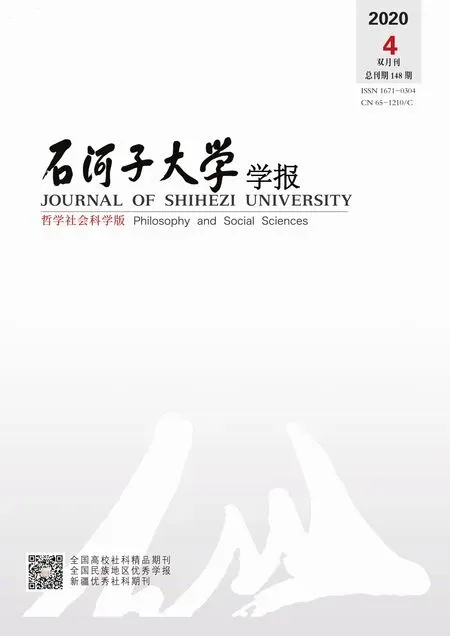丝绸之路:东西方文明交流融汇的创新之路
——以敦煌文化的创新发展为中心
2020-12-09李并成
李并成
(西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甘肃 兰州730070)
以往的有些研究中,在论证和评价丝绸之路的历史作用时,学者们大多关注的是丝绸之路作为东西方世界之间的重要通道、在传播和沟通东西方经济文化中发挥的重大作用和贡献等方面问题,自然这是没有疑义的。然而笔者认为,丝绸之路对于世界历史的作用和贡献并不仅仅体现在“通道”上,如果只是将其看作“通道”的话,那就会大大低估和矮化其应有的历史意义和价值。而其更重要的作用和贡献在于这条道路还是东西方文化交流、整合、融汇及其创生衍化和发展嬗变的加工场、孵化器和大舞台,是文化创新的高地。毫无疑问丝绸之路可称之为名副其实的创新之路。
就拿丝绸之路文化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敦煌文化来说,其交融创新的特点就十分突出和明显。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枢纽和吐纳口,为“华戎所交”的都会,西方文化传入中国后,大多要通过敦煌、河西等地进行中国“本土化”过程,或与中国传统文化碰撞、交流、整合后再继续东传。同样中原文化向西传播亦是经过河西、敦煌发生文化的交流融汇。敦煌在整合东西方文化资源、创新文化智慧方面有着独具特色的优势,这也从一个方面生动地体现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的胸怀与应有的文化自信。
一、敦煌文化呈现出东西方文化融合创新的亮丽底色与崭新格局
笔者认为,敦煌文化是一种在中原传统文化主导下的多元开放文化,敦煌文化中融入了不少来自中亚、西亚、印度和我国西域、青藏、蒙古等地的民族文化成分和营养,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化融合发展的亮丽底色与崭新格局,绽放出一种开放性、多元性、浑融性、创新性的斑斓色彩。例如,敦煌遗书中不仅保存了5万多件汉文文献,而且还汇聚有大量中国国内少数民族文字以及一批西方国家民族文字的写本。又如西方传入的“胡文化”,对于敦煌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即有着十分深刻的影响。
(一)敦煌遗书中汇聚有中外诸多民族文字文献的新史料
敦煌文书中保存的我国少数民族文字以及西方国家民族文字的写本,有吐蕃文、回鹘文、粟特文、于阗文、突厥文、梵文、婆罗迷字母写梵文、佉卢文、希腊文等语言文字的文本。此外莫高窟北区还发现西夏文、蒙古文、八思巴文、叙利亚文等文书,可谓兼收并蓄,应有尽有①荣新江:《敦煌学十八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80-282页。。这么多古代东西方民族、国家的文献汇集一地,本身即表明敦煌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的重要地位。这些文献大多为我们以前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新资料,它们对于丝绸路上的文化交流交融和民族关系,以及中古时期的民族学、语音学、文字学的研究贡献重大。
例如,敦煌少数民族语言文献中,以吐蕃文即古藏文文献为最多,其内容除大量与佛教有关的经典、疏释、愿文祷词外,还有相当多的世俗文献,涉及到吐蕃历史上一系列重大问题。由于吐蕃人自己所写的吐蕃时代的文献非常少,而敦煌出土的近万件吐蕃文写本,则反映了整个藏人早期的经历和吐蕃王朝的历史进程。如所出《吐蕃大事纪年》《吐蕃赞普传记》等,按年代顺序记载吐蕃王朝会盟、征战、颁赏、联姻、狩猎、税收等大事,可填补研究中的一大片空白②王尧,陈践译注《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北京:民族出版社,1980年,第8-10页。。敦煌本回鹘文文书虽是劫后余孤,但数量仍不少,内容包括各种经文、笔记、医学、天文学、文学作品以及从甘州回鹘和西州回鹘带到敦煌的公私文书、信件等,弥足珍贵③杨富学:《回鹘文献与回鹘文化》,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年,第29-31页。。于阗语是新疆和田地区古代民族使用的语言,公元11世纪以后逐渐消失,成为“死文字”,敦煌于阗语文献大部分已获解读,内容主要有佛教经典、文学作品、医药文书、使河西记、双语词表等,对于于阗历史、语言文化以及于阗与敦煌的交往和民族关系的研究意义重大④张广达,荣新江:《于阗史丛考》,上海:上海书店,1993年,第15-19页。。粟特语又称作“窣利语”,为古代中亚粟特地区民族使用的语言,敦煌粟特语文献大多为粟特人来到敦煌后留下的文字材料,内容有信札、账单、诗歌、占卜书、医药文书、译自汉文的佛典、经书等,实为宝贵⑤黄振华:《粟特文及其文献》,《中国史研究动态》,1981年第9期,第28-33页。。突厥文为公元7—10世纪突厥、黠戛斯等族使用的文字,曾流行于我国西域、河西以及中亚、西亚等地。敦煌文书中保存有突厥文格言残篇、占卜书、军事文书等⑥陈宗振:《突厥文及其文献》,《中国史研究动态》,1981年第11期,第26-30页。。
敦煌发现的外来民族文字的文献亦不少。如梵文文献除佛经外,尚有《梵文—于阗文双语对照会话练习簿》、梵字陀罗尼、梵文《观音三字咒》等。又如,莫高窟北区B53窟出土两页四面完整的叙利亚文《圣经·诗篇》,据之可大大增加我们对蒙元时期景教(基督教聂斯脱利派)传播的认识⑦彭金章:《敦煌考古大揭秘》,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33-138页。。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敦煌文献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是丝路沿线国家共同历史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
除藏经洞和莫高窟北区庋存的众多民族文字的文献外,莫高窟等石窟中还留下了吐蕃文、西夏文、回鹘文、蒙古文等不少民族文字的题记,敦煌汉代烽燧遗址出土佉卢文帛书,莫高窟北区B105窟出土青铜铸造的十字架,表明宋代敦煌地区景教徒的存在。莫高窟还先后4次出土回鹘文木活字1 152枚,为目前所知世界上现存最多、最古老的用于印刷的木活字实物,具有十分重要的研究价值。
(二)敦煌文化中融入了诸多西方文化的新元素
西方传入的“胡文化”,对于敦煌文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古代敦煌的赛祆胡俗、服饰胡风、饮食胡风、乐舞胡风、婚丧胡风,敦煌画塑艺术中所融入的西方元素,以及医药学文化、科技文化、体育健身文化等所体现出的中西文化交流融汇等。
以赛祆胡俗为例。赛祆,即祈赛祆神的民俗,为“赛神”活动的一种,唐宋时期的敦煌尤为盛行。所谓“赛神”,即以祭祀来报答神明所降的福泽之意。祆教,即琐罗亚斯德教,又称“拜火教”,为萨珊波斯的国教,约在魏晋时传入我国。由敦煌遗书《沙州都督府图经》(P.2005)等见,唐代敦煌城东一里处专门建有安置粟特人的聚落——安城及从化乡,该乡辖3个里,750年时全乡约有300户、1400口人,其中大部分居民来自康、安、石、曹、罗、何、米、贺、史等姓的中亚昭武九姓王国①[日]池田温:《八世纪中叶敦煌的粟特人聚落》,《唐研究论文选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3-67页。。安城中建有祆庙,其规模多达20龛,专门供奉祆神。敦煌归义军官府的《布、纸破用历》(P.4640v)等文书中经常记载为了举办赛祆活动而支出的画纸、灯油、酒、麨面、灌肠及其他食品等,且数额不菲。并且祆祠赛神已被纳入到敦煌当地的传统祭祀习俗中,从官府到普通百姓,无论粟特人,还是汉人和其他少数民族,无不祀祆赛神,藏经洞中亦保存有祆教图像,可见祆教对敦煌文化的重要影响。敦煌赛祆活动的主要仪式有,“祆寺燃灯,沿路作福”,供奉神食及酒,幻术表演,雩祭求雨等,反映了外来宗教文化传入中国后融入中国传统文化的状况,经过中国传统文化消化、改造了的祆教,已与中亚本土的祆教有诸多不同,呈现出一派新的景象。
又如饮食胡风。作为中国古代国际性都市,敦煌的饮食习俗具有浓郁的汉食胡风特色,来自中亚、西亚、中国西域等地的饮食习惯融入敦煌当地传统的饮食风俗中,成为敦煌饮食文化中新的有机组成部分,体现了丝绸之路上中西饮食文化交流融汇的生动场景。笔者曾将敦煌饮食文化的特点概括为:包罗宏大、美味俱全,中西饮食习俗汇聚交融,多民族饮食习俗汇聚交融,僧俗饮食习俗汇聚交融,饮食与医疗卫生、保健养生有机结合,饮食与岁时文化密切结合,饮食与歌舞艺术相结合②李并成:《敦煌饮食文化的若干特点论略》,《丝绸之路民族文献与文化研究》,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15年,第263-264页。。据不完全检索,仅敦煌遗书中出现的食物品种名称就达60多种,其中源于“胡食”,又经敦煌当地传统饮食习俗影响和改造过的饮食品种即有不少,如各类胡饼、炉饼、炊饼、饩饼、饸饼、餢飳、饆饠、餺飥、胡酒、诃梨勒酒等,不一而足。敦煌还有来自吐蕃的糌粑和灌肠面,至今它们仍是藏族和蒙古族的主要食物之一。至于饮食炊具、餐具,亦有不少是从“胡地”传入的,如鍮石盏、金叵罗、注瓶、垒子、犀角杯、珊瑚勺、食刀、胡铁镬子等。饮食礼仪中的胡跪、垂腿坐、列坐而食等,亦深受胡风影响③高启安:《唐五代敦煌饮食文化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年,第227-257页。。
再如,敦煌艺术表现手法中的胡风。敦煌艺术就其品类而言,包括壁画、彩塑、石窟建筑、绢画、版画、纸本画、墓画等,内容十分丰富,数量极其巨大。著名学者姜亮夫先生评价:“敦煌千壁万塑,至今仍能巍然独存,而且还有远在北魏的作品,无一躯一壁不是中国流传的最古的宝迹。一幅顾恺之的《女史箴》引得艺术界如痴如醉;数十躯杨惠之的塑像,使人赞叹欣赏,不可名状。这样大的场面,这样多的种色,这样丰富的画派,安能不令世人惊赏!它是世界第一座壁画塑像的宝库,是中国人骄傲的遗产,也是艺术界的宝典,史学上的第一等活材料。总之,以艺术来说,敦煌的唐代美术,是融合了中国的象征写意图案趣味的古典艺术与印度的写实手法,而发挥出其交融后最美丽的光彩,是中土美术得了新养分成长最为壮健的一个时代……它包罗了中国传统的艺术精神,也包罗了中西艺术接触后所发的光辉,表现了高度的技术,及吸收类化的精沉的方式方法,成为人类思想领域中的一种最高表现。它总结了中国自先史以来的艺术创造意识,也吸收了印度艺术的精金美玉,类化之,发恢之,成为中国伟大传统的最高标准,它是人类精神的最高发扬。”④姜亮夫:《敦煌——伟大的文化宝藏》,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0-41页。
二、敦煌文化中突出体现了佛教“中国化”的创新成就
作为外来宗教,佛教欲在中华故土上传播发展,欲融入中国的传统文化,就必须要适应中国原有的文化氛围,适应中国人的思想观念与审美意识,运用中国的语言表达方式,这就需要首先进行一番“中国化”的改造与更新过程。史实表明,敦煌作为佛教进入我国内地的第一站,率先形成了佛经翻译、传播中心,率先成为佛教“中国化”的创新之地。此外,敦煌文献中还保存了大量原已散佚失传的佛教典籍,从中可获得许多新发现、新收获。敦煌文化突出体现了佛教“中国化”的创新成就。
据《高僧传》卷1记载,月氏高僧竺法护,世居敦煌,曾事外国沙门竺高座为师,游历西域诸国,通晓多种语言,率领一批弟子首先在敦煌组织了自己的译场,被人们称为“敦煌菩萨”。竺法护被认为是当时最博学的佛教学者,是佛教东渐时期伟大的佛教翻译家,开创了大乘佛教中国化的新局面,奠定了汉传佛教信仰的基本特色①李尚全:《竺法护传略》,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页。。他“孜孜所务,唯以弘通为业,终身写译,劳不告倦。法经所以广流中华者,护之功也。”《开元录》载其共译经175部354卷。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第2卷载,竺法护“一生往来于敦煌、长安之间,先后47年(266—313),译经150余部,除小乘《阿含》中的部分单行本外,大部分是大乘经典……早期大乘佛教各部类的有代表性的经典,都有译介……在沟通西域同内地的早期文化上,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正是由于竺法护开创性的贡献,使敦煌实际上成为大乘佛教的发祥地。
又据《高僧传》卷4《晋敦煌竺法乘传》载,竺法护的弟子竺法乘承其师之衣钵,继续在敦煌“立寺延学,忘身为道,诲而不倦”,颇有影响。尔后敦煌僧人竺昙猷继续研习光大,成为东晋时代的著名高僧、浙江佛教的六大创始人之一。《高僧传》卷11记载:“竺昙猷,或云法猷,敦煌人。少苦行,习禅定。后游江左,止剡之石城山,乞食坐禅……自遗教东移,禅道亦授,先是世高、法护译出禅经,僧先、昙猷等并依教修心,终成胜业。”可见,竺法护、法乘、昙猷等前后相继,译出并创立大乘佛教的禅学理论,又付诸实践禅修弘法,成就胜业。马德先生认为,昙猷实际上就是中国佛教禅修的创始人②马德:《敦煌文化杂谈三题》,杨利民、范鹏主编《敦煌哲学》(第四辑),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56页。。
敦煌遗书中约90%的卷帙为佛教典籍,总数超过5万件,包括正藏、别藏、天台教典、毗尼藏、禅藏、宣教通俗文书、寺院文书、疑伪经等,具有十分重要的补苴佛典、校勘版本和历史研究价值。例如,禅宗为彻底中国化的佛教,且简单易行,8世纪以来成为中国佛教的主流,受到唐代士大夫及普通民众的欢迎和热衷信仰。然而由于战乱及“会昌灭法”的打击等原因,以至于许多早期的禅籍遗失,其教法也逐渐失传,使我们无法全面了解唐代禅宗发展状况,也难以真正了解中国思想史和中国社会史。欣喜的是敦煌遗书中保存了大量8世纪前后禅宗的典籍,主要有初期禅宗思想的语录、禅宗灯史等。例如,据说是禅宗初祖达摩的《二人四行论》,三祖僧璨的《信心铭》,卧伦的《看心法》,法融的《绝命观》《无心论》,五祖弘忍的《修心要论》,北宗六祖神秀的《大乘五方便》《大乘北宗论》《观心论》,南宗六祖慧能的《坛经》,南宗七祖神会的《菩提达摩南宗定是非论》,以及杜胐的《传法宝记》、净觉《楞伽师资记》,保唐宗(净众宗)的《历代法宝记》,等等③[日]田中良昭:《禅学研究入门》,东京:大东出版社,1994年。。这些著述填补了禅宗思想史的诸多空白。
又如别藏,是专收中华佛教撰写的中国佛教典籍的集成,但在大多数佛僧眼中其地位远远比不上由域外传入翻译的正藏,故而使大批中华佛教撰著散佚无存,殊为可惜。敦煌藏经洞中则保存了相当多的古逸中华佛教论著,包括经律论疏部、法苑法集部、诸宗部、史传部、礼忏赞颂部、感应兴敬部、目录音义部、释氏杂文部等,从而为我们研究印度佛教是怎样一步步演化为中国佛教的,中国佛教是如何发展演变的等问题,提供了十分丰富的新史料。
再如,疑伪经即非佛祖口授而又妄称为经者,或一时无法确定其真伪的经典,亦大多无存。但这些经典均可反映出中国佛教的某一发展断面,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它们在敦煌遗书中保存了相当多的数量,十分值得庆幸。如《高王观世音经》,反映了观世音信仰在中国发展和流传的状况;《大方广华严十恶品经》,反映了梁武帝提倡断屠食素背景下汉传佛教素食传统的形成过程;《十王经》反映了中国人地狱观念的演变,等等①方广锠:《敦煌遗书中的佛教文献及其价值》,《西域研究》,1996年第1期,第45-48页。。这些资料已使佛教“中国化”的研究呈现出诸多新的面貌。
三、敦煌壁画中的飞天——极富创新的艺术形象
敦煌石窟,包括莫高窟、榆林窟、西千佛洞、东千佛洞、五个庙石窟、昌马石窟等,保存了公元4世纪至14世纪的佛窟约900座、壁画50 000多平方米、彩塑3 000余身,用艺术的图像生动地记录了古代千余年来的历史场景与社会风貌,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历史文化艺术宝库。石窟的营造者们从一开始就进行着再创造,他们适应中国人的审美情趣和艺术追求,按照中国人自己的观念来理解佛教教义,描绘天国的理想境界,创作佛教的神祇;以中国人喜闻乐见的形式宣传佛教思想,以中国民族形式表达佛教内容。他们在创作中发挥出杰出的聪明才智,体现出卓越的创造精神。
就拿敦煌壁画中的飞天来说,其艺术形象源自印度,又名乾闼婆、紧那罗,是佛教天国中的香神和音神,即专施香花和音乐的佛教专职神灵,莫高窟中的飞天多达6 000余身。飞天形象传入敦煌后,经不断地交融发展、脱胎换骨、艺术创新,完全摆脱了印度石雕飞天原有的样式,以全新的面貌展现于世人面前,美不胜收,与印度的石雕飞天已非同日而语。
早期洞窟(如北凉275窟等)中的飞天,头有圆光,戴印度五珠宝冠;或头束圆髻,上体半裸,身体呈“U”形,大多双脚上翘,作飞舞状,姿势显得笨拙,形体略呈僵硬,似有下沉之感,尚带有印度石雕飞天的较多痕迹。北魏时期飞天加快向中国化方向转变,但仍有较明显的域外样式和风格,其体态普遍较为健壮,略显男性特征,飞动感不强。西魏到隋代是飞天艺术各种风格交融发展的时期,完全中国化意义上的飞天艺术逐渐形成。如西魏285窟飞天形象已趋向于中原秀骨清像形,其身材修长,裸露上身,直鼻秀眼,微笑含情,脖有项链,腰系长裙,肩披彩带,手持各种乐器凌空飞舞。四周天花旋转,云气飘荡,颇显身轻如燕、自由欢乐之状。
隋朝飞天艺术得到进一步发展,一扫呆板拘谨的造型姿态,由于画师工匠不断吸收、摹仿中外舞蹈、伎乐、百戏等的精华,进行再创新,克服了早期飞天中蹲踞形和“U”字形的弱点,使得飞天的身姿与飘带完全伸展,体态轻盈、流畅自如,完成了中国化、民族化、女性化、世俗化、歌舞化的历程。如第427窟内四壁天宫栏墙内绕窟一周的飞天,共计108身,皆头戴宝冠,上体半裸,项饰璎珞,手带环镯,腰系长裙,肩披彩带。有的双手合十,有的手持莲花,有的手捧法器,有的扬手散花,有的欢快地演奏着琵琶、长笛等乐器,朝着同一方向(逆时针方向)飞去。飘逸的衣裙、长长的彩带,迎风舒卷。飞天四周流云飞动,天花四散,充满了动感和生气。
唐代是敦煌飞天艺术发展的最高峰,也是其定型化的时代。初盛唐的飞天具有奋发向上、轻盈潇洒、千姿百态、自由奔放的飞动之美,这与唐代前期开明的政治、强大的国力、丰富的文化和奋发进取的时代精神是一致的。例如初唐321窟西壁佛龛两侧飞天,姿态格外优雅,身材修长,昂首挺胸,双腿上扬,双手散花,衣裙巾带随风舒展,由上而下,徐徐飘落,充分表现出其潇洒轻盈的飞行之美。又如盛唐320窟南壁西方净土变中的阿弥陀佛头顶华盖上方两侧的4身飞天,身轻如燕,对称出现,相互追逐,前呼后应,灵动活跃,表现出一种既昂扬向上又轻松自如的精神境界与美感。
唐代大诗人李白描写的“素手把芙蓉,虚步蹑太清。霓裳曳广带,飘拂升天行”,正可用来吟哦赞叹敦煌飞天。敦煌飞天不生羽毛,不长翅膀,借助彩云却不依靠彩云,通过长长的飘带,舒展的身姿、欢快的舞动,在鲜花和流云的衬托下翱翔天空,翩翩起舞,把洞窟装扮得满壁风动。诚如著名学者段文杰先生所论:“敦煌飞天不是印度飞天的翻版,也不是中国羽人的完全继承。以歌伎为蓝本,大胆吸收外来艺术营养,促进传统艺术的变改,创造出的表达中国思想意识、风土人情和审美思想的中国飞天,充分展现了新的民族风格。”①段文杰:《飞天——乾闼婆与紧那罗》,载于《段文杰敦煌艺术论文集》,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438页。敦煌飞天堪称人类艺术的天才创造,是中国美术史上的一个奇迹,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不断突破自我、勇于创新的精神品格。有人说敦煌飞天寄托了人类征服自然、飞跃太空、翱翔宇宙的伟大梦想;也有人认为,敦煌飞天是当代载人航天、宇宙飞船等人类尖端科技的最初灵感来源。
四、敦煌歌舞艺术——融汇中西菁华的全新艺术形象
莫高窟中保存了历时千余年的极其丰富的舞蹈形象,在北区的492个洞窟中,几乎每一窟都有舞蹈绘画。舞蹈是转瞬即逝的时空艺术,在没有古代舞蹈动态资料的情况下,那些凝固在敦煌洞窟壁画中的历代舞蹈图像就成为十分罕见的珍贵舞蹈史料。早在北朝时期许多西域乐舞,包括龟兹(今新疆库车)、高昌(今吐鲁番)、疏勒(今喀什)、安国(今乌兹别克斯坦布哈拉一带)、康国(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一带)、悦般国(今阿富汗北部)等的乐舞,即首先经由敦煌而传入中原。这些乐舞与中国传统乐舞交流荟萃,展现出丰富多彩的崭新形象,使得敦煌壁画绚丽多姿,美不胜收。
例如,敦煌壁画中十分引人注目的舞蹈形象天宫伎乐,即壁画中天宫圆券门内奏乐歌舞的天人,计有4 000余身,源自印度佛教所描绘的西方极乐世界中供养佛的音乐舞蹈之神。其动作特点是大幅度的扭腰出胯,伸臂扬掌,体态舒展,挺拔昂扬,手指变化也颇为丰富。那些怀抱琵琶、手执管弦等外来乐器边弹边舞的伎乐,吹奏的虽是外来乐器,舞姿却蕴含我国古典舞韵,为中外舞蹈交融的生动表现。在绘画技法上,既有圆券形宫门、服饰和表现主体感的西域式明暗法等,更有满实的构图、遒劲的线描,以动态传神、鲜明的色彩和中原传统晕染法②万庚育:《敦煌早期壁画中的天宫伎乐》,《敦煌研究》,1988年第2期,第24-26页。。敦煌天宫伎乐不仅是反映佛教内容的优美的艺术形象,而且具有生活的真实性和观赏性。
迨及隋唐,进入各民族、各地区乐舞文化大交流、大融合、大发展、大创新的时代。隋炀帝置九部乐,唐太宗时又增为十部乐,其中西凉乐、龟兹乐、天竺乐、康国乐、疏勒乐、安国乐、高昌乐,皆是经由敦煌传入中原而盛行于宫廷的。西域百戏、胡旋舞、胡腾舞、柘枝舞、高昌舞等,也是首先在敦煌流行发展继而风靡于内地的。这些舞蹈具有浓厚的西域、中亚风情,传入敦煌后开创一代新风,矫健、明快、活泼、俊俏,舞风优美,气氛热烈,与当时开放、向上的时代精神相吻合③王克芬:《多元荟萃,归根中华——敦煌舞蹈壁画研究》,《敦煌研究》,2005年第3期,第41-50页。。
就拿西域传入的胡旋舞来说,其源于康国,故而又名康国舞,约北周时传入中原,隋唐时大盛。白居易长诗《胡旋女》描绘其舞蹈场景:“胡旋女,胡旋女,心应弦,手应鼓。弦歌一声双袖举,回雪飘摇转蓬舞。左旋右转不知疲,千匝万周无已时。人间物类无可比,奔车轮缓旋风迟。曲终再拜谢天子,天子为之微启齿。胡旋女,出康居,徒劳东来万里余……”胡旋舞的场景在莫高窟壁画中比比可见。例如220窟北壁药师经变中的两对伎乐天所跳胡旋舞姿十分优美。第一对舞伎均头戴珠冠,上身着短袄,下身穿裤裙,裸臂着钏,跣足,手舞长巾,一腿立于圆毯上,一腿弯曲抬起,一手举过头顶,一手弯曲下垂,给人以飞速旋转的强烈感觉。第二对舞伎展臂旋转,所着长巾、佩饰卷扬飘绕,动感极强,似乎是同一舞伎两个连续旋转动作的绘制。其舞蹈动势,颇有“蓬断霜根羊角疾,竿戴朱盘火轮炫,骊珠迸珥逐飞星,虹晕轻巾掣流电……万过其谁辨始终,四座安能分背面”的胡旋舞飞旋优雅的姿态。在12窟、146窟、108窟等窟壁画中还有男性表演的着长袖衣、旋转踏跃的胡腾舞。
又如,著名的《西凉乐》就是以龟兹为主的各族乐舞与流行河西一带的“中原旧乐”(包括清商乐)融合而成的,为西域音乐传入之后融合西方少数民族音乐的代表,是古代敦煌、河西(凉州)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乐舞艺术。唯庆善乐“独用西凉乐,最为闲雅”。乐舞表演离不开乐器伴奏,于敦煌壁画中见,主要乐器有琵琶、曲项琵琶、五弦、胡琴、葫芦琴、弯颈琴、阮、花边阮、答腊鼓、腰鼓、羯鼓、毛员鼓、都昙鼓、鸡娄鼓、节鼓、齐鼓、擔鼓、军鼓、手鼓、鼗鼓、扁鼓、竖笛、横笛、凤笛、异型笛、筚篥、笙、竽、筝、角、画角、铜角、箜篌、凤首箜篌、方响、排箫、串铃、金刚铃、拍板、钟、钹、铙、海螺等,它们大多出自西域①郑汝中:《壁画乐器》,季羡林主编《敦煌学大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年,第250-261页。。如《隋书·音乐志》:“今曲项琵琶、竖箜篌之徒,并出自西域,非华夏旧器。”《破阵乐》《大定乐》等,“皆擂大鼓,杂以龟兹之乐”。长寿乐、天授乐等也“皆用龟兹乐”。
著名舞蹈艺术家王克芬研究员认为,唐代频繁的乐舞交流为创作新的舞蹈作品提供了取之不竭的素材,唐舞以传统舞蹈为基础,广泛吸纳许多国家、地区民族的舞蹈艺术,广采博纳,撷取菁华,融化再创,成为当时舞蹈发展的主流,开创中国古代舞蹈艺术的一代新风,取得辉煌成就。其中,许多舞蹈就是以中原乐舞为基础,广泛吸取中外各民族民间乐舞的菁华创作而成的②王克芬:《天上人间舞蹁跹》,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75-83页。。
综上可见,丝绸之路上的敦煌文化在其长期的历史演进中“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形成了极强的包容性,它并不排斥外来的同质或异质文化,包容不是简单的混合,也不是取消差异,取消民族特色,文化的认同并不等于文化的同化,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是以我为主对外来文化进行的改造与融合,是在更高层次上和更广范围内的优势互补和创新发展。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自由交流,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的交融汇合,使得敦煌文化绝非仅仅是本乡本土的产物,而成为整个丝绸之路上东西方文化交流融汇、创新转化的典型代表。敦煌文化的创新发展生动地表明,丝绸之路并非仅仅是一条简单的东西方之间的通道,而是东西方文化交流融汇的创新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