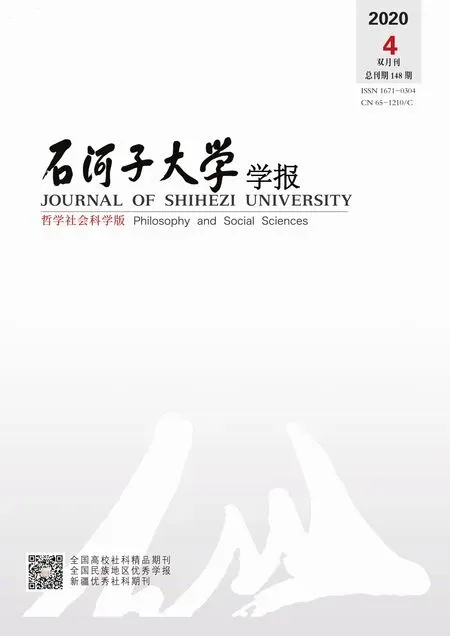论建安时代偏才论的兴起
2020-12-09徐昌盛
徐昌盛
(山东大学文学院,山东济南250100)
“偏至之材”来源于刘劭的《人物志》,是对以曹丕《典论·论文》为代表的作家论进行理论总结的成果,因此曹丕、刘劭等人共同开创了中国文学批评中的偏才论。目前的研究,虽然敏锐地关注到曹丕、刘劭提及偏才问题①如王运熙、杨明指出《典论·论文》描述了作家的才能长短问题,追溯了东汉讨论人性的渊源,发现与《人物志》的才能各有偏至的观点相通。参见《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36-37页。,但尚属于一般性的背景介绍,既未能揭示出偏才论这一建安文学批评的重要命题,又未能系统梳理偏才论兴起的实践来源、理论基础、思想背景和政治需要等一整套体系。
一、清谈风气与偏才论的提出
曹丕《典论·论文》写成于建安末期,以“品藻人才”为主要内容,属于典型的人物论,是汉末清谈风气的产物。汉末清谈的内容,“主要部分是具体的人物批评”[1]278。郭泰、许劭、许靖等是汉末人物批评的权威,具有重要的影响力。风气所及,曹操也很重视名士的评价,曾厚礼拜谒许劭“求为己目”[2]2234,对桥玄的识见之恩念念不忘。曹丕熟悉人物批评,自然受到了曹操的影响。鱼豢《魏略》载:
孙权称臣,斩送关羽。太子书报繇,繇答书曰:“臣同郡故司空荀爽言:‘人当道情,爱我者一何可爱!憎我者一何可憎!’顾念孙权,了更妩媚。”太子又书曰:“得报,知喜南方。至于荀公之清谈,孙权之妩媚,执书嗢噱,不能离手。若权复黠,当折以汝南许劭月旦之评。权优游二国,俯仰荀、许,亦已足矣。”[3]395
唐长孺指出,曹丕认为荀爽的话属于清谈中人物批评标准,孙权属于荀爽“爱我者一何可爱”的范畴,如果“权复黠”,情况发生了变化,还须按汝南月旦之法重行评定,总之“曹丕以之(荀爽言)为清谈,便是与人物批评有关的例证”[1]279。
曹丕人物论的主要成就是作家论,而作家论的核心是偏才论。《典论·论文》是偏才论提出的经典文献。东汉的王充、延笃、仲长统等也注意到偏才的问题[4]36,但他们既没有专门进行论述,也没有与文学相联系。《典论·论文》开篇说:“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傅毅之于班固,伯仲之间耳,而固小之,与弟超书曰:‘武仲以能属文为兰台令史,下笔不能自休。’夫人善于自见,而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是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5]720曹丕提出了“文人相轻”的问题,以傅毅和班固才能相侔而班固轻视傅毅的事情进行立论,交代了人的才能各有长短,很少能擅长各体文章。曹丕论证了偏才存在的缘由,也说明文体论最早从属于作家论,又说:“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5]720。根据蔡邕《独断》可知,汉末文体甚为丰富[6],当然不止“四科八体”,曹丕采取了举例的形式,旨在说明文体类别和风格的不同是偏才出现的原因。曹丕对当时颇具影响力的七子的长短处进行了介绍:“王粲长于辞赋,徐幹时有齐气,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楼》《槐赋》《征思》,幹之《玄猿》《漏卮》《圆扇》《橘赋》,虽张、蔡不过也。然于他文,未能称是。琳、瑀之章表书记,今之隽也。应玚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词,至乎杂以嘲戏;及其所善,扬、班俦也。”[5]720曹丕说王粲、徐幹善于作赋,而不擅长其他文体;陈琳、阮瑀善于章表书记等应用文体;应玚、刘桢和孔融也皆擅长一端,在其他方面也非所长。总之,曹丕不仅指出了人才皆有偏至的事实,而且对各个作家的创作或气质进行了评论。
曹丕在其他场合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给吴质写信说:“观古今文人,类不护细行,鲜能以名节自立。而伟长独怀文抱质,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谓彬彬君子者矣。著《中论》二十余篇,成一家之言,辞义典雅,足传于后,此子为不朽矣。德琏常斐然有述作之意,其才学足以著书,美志不遂,良可痛惜。间者历览诸子之文,对之抆泪,既痛逝者,行自念也。孔璋章表殊健,微为繁富。公干有逸气,但未遒耳。其五言诗之善者,妙绝时人。元瑜书记翩翩,致足乐也。仲宣独自善于辞赋,惜其体弱,不足起其文;至于所善,古人无以远过。昔伯牙绝弦于钟期,仲尼覆醢于子路,痛知音之难遇,伤门人之莫逮。诸子但为未及古人,自一时之儁也。今之存者,已不逮矣。后生可畏,来者难诬,然恐吾与足下不及见也。”[5]591-592曹丕分析了徐幹、应玚、陈琳、刘桢、阮瑀和王粲的特点:有人格的,如徐幹的“怀文抱质,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谓彬彬君子者矣”;有著述才能的,如徐幹的《中论》和应玚的“有述作之意,其才学足以著书”;也有对陈琳和刘桢善于某一文体的表彰和评价,如陈琳“章表殊健,微为繁富”,刘桢“有逸气,但未遒耳。其五言诗之善者,妙绝时人”,阮瑀“书记翩翩”,王粲“善于辞赋,惜其体弱,不足起其文;至于所善,古人无以远过”。曹丕注意到不同人的气质不同、才能迥异,只能在某些擅长的文体上成绩斐然,从而提出了文学批评上的偏才论。
偏才论并非曹丕的一家之言,是当时作家评论风气的反映,曹植、鱼豢等都有类似的讨论。曹植面对杨修批评陈琳说:“以孔璋之才,不娴辞赋,而多自谓与司马长卿同风,譬画虎不成反还为狗者也。前为书啁之,反作论盛道仆赞其文。夫钟期不失听,于今称之。吾亦不敢妄叹者,畏后之嗤余也。”[5]593曹丕说陈琳“章表书记,今之隽也”,又说“孔璋章表殊健,微为繁富”。据知陈琳是偏才,擅长章表,而不娴辞赋。但陈琳自己对辞赋十分看重,认为作品与司马相如赋作风貌相同,曹植曾就此写信戏谑,或是过于隐晦,陈琳未能明白,反而以为曹植欣赏他的辞赋,这与曹丕所指责的“患于自见,谓己为贤”的弊病同出一辙。鱼豢《魏略》说:“寻省往者,鲁连、邹阳之徒,援譬引类,以解缔结,诚彼时文辩之俊也。今览王、繁、阮、陈、路诸人前后文旨,亦何曾不若哉?其所以不论者,时世异耳。余又窃怪其不甚见用,以问大鸿胪卿韦仲将。仲将云:‘仲宣伤于肥戆,休伯都无格检,元瑜病于体弱,孔璋实自粗疏,文蔚性颇忿鸷。如是彼为,非徒以脂烛自煎糜也,其不高蹈,盖有由矣。然君子不责备于一人,譬之朱漆,虽无桢幹,其为光亦壮观也。’”[3]603鱼豢认为王粲、繁钦、阮瑀、陈琳、路粹诸人的文章意旨,不逊于鲁连、邹阳等前代俊才,但因为时代不同,没有引起重视。他又为诸人不得进用而请韦仲将解释原因,韦氏从性格方面入手分析了诸人的缺陷,指出“仲宣伤于肥戆,休伯都无格检,元瑜病于体弱,孔璋实自粗疏,文尉性颇忿鸷”,最后说“不责备于一人”,即承认人的才华有所偏擅,偏才也自有其价值。另外,同时代的应璩《百一诗》说“人才不能备,各有偏短长”[7]471。此诗应作于魏时,仍属于建安时代偏才论的流风余韵。
二、《人物志》与偏才论的理论总结
刘劭是曹魏著名的文士,其《人物志》对偏才论进行了理论总结。建安二十年(215),刘劭受御史大夫郗虑辟举,不久被拜为太子舍人,属于曹丕的近臣。本传说刘劭“受诏集五经群书,以类相从,作《皇览》”[3]617,《皇览》是曹丕即位后实施的重大文化工程,《世语》称“合四十余部,部有数十篇,通合八百余万字”[3]664,由“京师归美,称为儒宗”的皇象主持,刘劭受命参与,亦可窥见曹丕对他才能的重视[8]。黄初元年(220),曹丕立九品官人法,由各州郡县的大小中正考察选拔并举荐本地人才,意在取得世家大族对其称帝的支持。曹丕称帝后因政治需要开始推行儒家道德,必然要改变曹操的“唯才是举”政策,而《人物志》重点突出才性,遵循的是曹操的理念,则此书应该写成于建安时期。
《人物志》是汉魏时期人物评议中最重要的著作,目的是“专门探讨人物评议的原理、方法、内容以及汉魏间人物评议得失”[9],其中的《九征》《体别》《材能》《英雄》《八观》[10]等篇系统阐述了偏才理论,通过对偏才能力长短的原因分析,提出“人才各有所宜”的观点。
第一,讨论了偏才和中庸的关系。《九征》罗列了“偏至之材”的几个表现并分别予以命名,即“直而不柔则木,劲而不精则力,固而不端则愚,气而不清则越,畅而不平则荡”,而中庸之材是“五常既备,包以澹味,五质内充,五精外章。是以目彩五晖之光也”。“中庸”是最高的标准,是圣王那样理想的君主。然后对“九质之征”分别定义,指出“九征皆至”的人物是“质素平淡,中睿外朗,筋劲植固,声清色怿,仪正容直”,是作者心目中的典型,如果违背了九征就是“偏杂之材”,在人才序列中次于“兼德而至”的中庸和“具体而微”的德行。《体别》篇强调“中庸之德”是区分衡量各种人才的标准,并将人才分为“拘”“抗”两类,即“拘抗违中,故善有所章,而理有所失”,继而着重分析了这两类人才各自的特长,同时区分了十二种不同的偏才,分析各自的长短处,讨论扬长避短的办法。文中说:“夫学,所以成材也。恕,所以推情也。偏材之性,不可移转矣。虽教之以学,材成而随之以失;虽训之以恕,推情各从其心。信者逆信,诈者逆诈,故学不道,恕不周物,此偏材之益失也。”“偏材之性”比较顽固,“固守性分,闻义不徙”(刘昞注),无论是“教之以学”,还是“训之以恕”,都不能改变他的立场,这是偏才的短处。《体别》篇在文学批评方法论上的意义是,提供了判断作家或作品的标准即中庸,又细分成具体的性格或文体特征,并讨论该性格或文体的长短之处,利用各自的长处,发挥最擅长的部分。
第二,分析了偏才能力长短的原因。《八观》说:“何谓观其所短以知所长?夫偏材之人,皆有所短。故直之失也讦,刚之失也厉,和之失也懦,介之失也拘。夫直者不讦,无以成其直;既悦其直,不可非其讦;讦也者,直之征也。刚者不厉,无以济其刚;既悦其刚,不可非其厉;厉也者,刚之征也。和者不懦,无以保其和;既悦其和,不可非其懦;懦也者,和之征也。介者不拘,无以守其介;既悦其介,不可非其拘;拘也者,介之征也。然有短者,未必能长也;有长者必以短为征。是故观其征之所短,而其材之所长可知也。”既是偏才,自然会有一些短处,要承认短处是偏才的特点,通过短处来发现长处,然后加以充分利用,因此提出“材能既殊,任政亦异”的原则。至于偏才能力长短的原因,《材能》说:“凡偏材之人,皆一味之美;故长于办一官,而短于为一国。何者?夫一官之任,以一味协五味;一国之政,以无味和五味。又国有俗化,民有剧易;而人材不同,故政有得失。是以王化之政,宜于统大,以之治小则迂。辨护之政,宜于治烦,以之治易则无易。策术之政,宜于治难,以之治平则无奇。矫抗之政,宜于治侈,以之治弊则残。谐和之政,宜于治新,以之治旧则虚。公刻之政,宜于紏奸,以之治边则失众。威猛之政,宜于讨乱,以之治善则暴。伎俩之政,宜于治富,以之治贫则劳而下困。”“人材不同,故政有得失”,人才的使用是由具体的政事情况决定的,因此“量能授官,不可不审”,只有国体之人,即“兼有三材,三材皆备,其德足以厉风俗,其法足以正天下,其术足以谋庙胜,是谓国体,伊尹、吕望是也”(《流业》),才是“众材之隽”,为最理想的对象。《流业》和《材能》给文学批评提供的价值是:兼善众体者是最理想的大作家,如政事中的伊尹、吕望,是非常难得的;很多作家只是偏至之材,各人的才能和习性不一样,所擅长的文体自然有所不同,因此要妥善发挥他们在擅长领域中的作用,如陈琳善于章表、王粲长于辞赋等,要务使各有所宜,各尽所用。
第三,在偏才的使用上,提出“人材各有所宜”,要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材能》篇说“人材不同,能各有异”,并举例称“有自任之能;月立法使人从之之能;有消息辩护之能;有德教师人之能;有行事使人谴让之能;有司察纪摘之能;有权奇之能;有威猛之能”。人才能力不同,所担任的职责也要有所差别,如:“自任之能,清节之材也,故在朝也,则冢宰之任;为国则矫直之政。立法之能,治家之材也,故在朝也,则司寇之任;为国,则公正之政。计策之能,术家之材也,故在朝也,则三孤之任;为国,则变化之政。人事之能,智意之材也,故在朝也,则冢宰之佐;为国,则谐合之政。行事之能,谴让之材也,故在朝也,则司寇之佐;为国,则督责之政。权奇之能,伎俩之材也,故在朝也,则司空之任;为国,则艺事之政。司察之能,臧否之材也,故在朝也,则师氏之佐;为国,则刻削之政。威猛之能,豪杰之材也,故在朝也,则将帅之任;为国,则严厉之政。”这事实上就是量能授政,使人才各尽其用、各有所宜,因此要将不同的人才放置于不同的位置来发挥他们的特长。刘昞注《流业》说“三材为源,习者为流。流渐失源,其业各异”,以德、法、术作为各种才能的源头,以德、法、术兼备为最高人才,而学习和掌握三种才能中的一部分,可以区分成十二种人才类型,“有清节家,有法家,有术家,有国体,有器能,有臧否,有伎俩,有智意,有文章,有儒学,有口辩,有雄杰”,又说“凡此十二材,皆人臣之任也,主德不预焉”,刘昞注称“各抗其材,不能兼备,保守一官居,故为人臣之任也”,而“主德者,聪明平淡,总达众材,而不以事自任者也。是故主道立,则十二材各得其任也”,就是说君主的责任是根据不同的才能,将他们放置不同的位置以便发挥他们的作用,而且不能有所偏好:“清节之德,师氏之任也。法家之材,司寇之任也。术家之材,三孤之任也。三材纯备,三公之任也。三材而微,冢宰之任也。臧否之材,师氏之佐也。智意之材,冢宰之佐也。伎俩之材,司空之任也。儒学之材,安民之任也。文章之材,国史之任也。辩给之材,行人之任也。骁雄之材,将帅之任也。是谓主道得而臣道序,官不易方,而太平用成。若道不平淡,与一材同好,则一材处权,而众材失任矣。”
刘劭有关偏才理论的一系列论述与当时新兴的名理学中的才性理论密切相关。
三、名理学与偏才论的思想背景
传统儒家以德性为标准对人物进行分类,刘劭《人物志》第一次以才性为标准区分人物,从而完成了人才理论从重德性向重才性的转化。
班固《古今人表》[11]863将古今人物区分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等,《史通》说“班氏之《古今人表》者,唯以品藻贤愚、激扬善恶为务尔”[12]437。这虽是较早的系统人物分类,但以“品藻贤愚、激扬善恶”为标准,强调道德功用,反映了重视德性的思想。《人物志·序》说:“是故仲尼不试,无所援升,犹序门人以为四科,泛论众材以辨三等。又叹中庸,以殊圣人之德,尚德以劝庶几之论,训六蔽以戒偏材之失,思狂狷以通拘抗之材,疾悾悾而无信,以明为似之难保。”刘劭熟悉儒家的德性分类,“四科”“三等”“中庸”等俱出于孔子之手。孔子根据门徒才能的不同区分为四类,即“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论语·先进》),又将众人划分为三个等级,即“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论语·季氏》),以“中庸”为最高的道德规范,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论语·雍也》)。孔子根据门徒才能的异同区总分成四类,各类之中归进才能相类的几个人,这是先有“实”的依据,再赋予不同“名”的方法,属于逻辑上的归纳法。刘劭的分类方法与此不同,《人物志》有意识地区分人物为若干品类,钱穆《略述刘劭人物志》说“《人物志》主要在讨论人物。物是品类之义。将人分成许多品类,遂称之为‘人物’”[13]57,如《流业》分人物为十二种并归入不同品第,这种分类的方式显然受到了班固《汉书·古今人表》的启发,但在分类前先确定一个规定性的“名”,这种分类的标准则是名理学影响的结果。刘劭将人才类型分为十二种,说“盖人流之业十有二焉:有清节家,有法家,有术家,有国体,有器能,有臧否,有伎俩,有智意,有文章,有儒学,有口辨,有雄杰”,这是对儒家“四科”的重大发展;又对每一种人才都进行界定,如“若夫德行高妙,容止可法,是谓清节之家,延陵、晏婴是也。建法立制,强国富人,是谓法家,管仲、商鞅是也。思通道化,策谋奇妙,是谓术家,范蠡、张良是也”,“清节家”“法家”“术家”构成了“三材”。兹以清节家为例,先说清节家的构成条件,再列举出代表性人物,这是典型的辨名析理的方法:先列出“名”及其规定性,然后再检核人物获得相应的“实”。刘劭再根据“三材”残备的不同又进行了品第,如果“兼有三材”,那么“三材皆备”为“国体”,“三材皆微”为“器能”;如果只有三材之一种,则分为“臧否”“伎俩”和“智意”,以上通称“八业”,“皆以三材为本,故虽波流分别,皆为轻事之材也”。刘昞注《人物志》说“八业之建,常以三材之本”,说明了“三材”与“八业”的源流关系。《人物志》不评议具体人物,所讨论的抽象才性问题与钟会《才性四本论》一起被称为“清议变相之最著或仅存之作也”[14]。
《人物志》是“汉代品鉴风气之结果”[15]11,宗旨是“以名实为归”[15]11,是魏晋时期“名理学的一部总结性的著作”[16]45。《人物志》不仅是名学思想和名实观念发展的产物,而且是魏晋名理学的典范,在玄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刘劭与名理学的关系密切。刘劭曾负责政策法令的制定,其中鲜明地体现了名理思想的影响。明帝景初(238—239)中,他受诏作《都官考课》七十二条,上疏说“百官考课,王政之大较”[3]619,这是在魏明帝在罢黜诸葛诞和邓飏等以浮华派人物后,体现了注意名实、注重考绩的思想;又作《新律》十八篇,著《律略论》五卷,汤用彤《读人物志》说“魏律以刑名为首篇,盖亦深察名实之表现也”15]12。刘劭的名理才能,在当时就赢得了很高的评价,夏侯惠推荐他说:“深忠笃思,体周于数。凡所错综,源流弘远。是以群才大小,咸取所同而斟酌焉。故性实之士,服其平和良正;清静之人,慕其玄虚退让;文学之士,嘉其推步详密;法理之士,明其分数精比;意思之士,知其沈深笃固;文章之士,爱其著论属辞;制度之士,贵其化略较要;策谋之士,赞其明思通微。凡此诸论,皆取适己所长而举其支流者也。臣数听其清谈,览其笃论,渐渍历年,服膺弥久,实为朝廷奇其器量。以为若此人者,宜辅翼机事,纳谋帏幄,当与国道俱隆,非世俗所常有也。惟陛下垂优游之听,使劭承清闲之欢,得自尽于前,则德音上通,煇燿日新矣。”[3]619刘劭的学术研究“推步详密”,“著论属辞”为世所嘉,处世玄虚退让,且善于清谈著论。据此可知,刘劭著《人物志》接受了当时渐兴的名理学影响。
《人物志》反映了刘劭对名理的深入思考。《材理》说:“夫辩有理胜,有辞胜。理胜者,正白黑以广论,释微妙而通之。辞胜者,破正理以求异,求异则失正矣。夫九偏之材,有同、有反、有杂。同则相解,反则相非,杂则相恢。故善接论者,度所长而论之。历之不动,则不说也。傍无听达,则不难也。不善接论者,说之以杂、反;说之以杂、反,则不入矣。善喻者,以一言明数事。不善喻者,百言不明一意;百言不明一意,则不听也。是说之三失也。善难者,务释事本;不善难者,舍本而理末。舍本而理末,则辞构矣。善攻强者,下其盛锐,扶其本指以渐攻之;不善攻强者,引其误辞以挫其锐意。挫其锐意,则气构矣。”刘劭意在区分辩论中明理和强辞的不同,并表达了鲜明的意见,即对说理的支持。刘昞注说“理胜”者“说事分明,有如粉黛,朗然区别,辞不溃杂”,而“辞胜”者“以白马非白马,一朝而服千人,及其至开禁锢,直而后过也”。刘劭又对比了“善接论者”“善难者”“善攻强者”和“不善接论者”“不善难者”“不善攻强者”论辩的方法,分析了论辩上的失误,指示了论辩取胜的途径。《材理》篇又说“是故聪能听序,谓之名物之材。……辞能辩意,谓之赡给之才。……与通人言,则同解而心喻。与众人言,则察色而顺性。……善言出已,理足则止。鄙误在人,过而不迫”,能够辨别细微声音差别的人是名物之材,“名”即是显示差别特征的概念。而言辞能够辩明实际的意旨,是谓善辩之才。刘劭又强调与通人及众人言说的不同表达艺术。刘劭正是对名辩有过缜密的思考,因此《人物志》的分类观体现出深刻的思辨性。
《英雄》是刘劭辨名析理的最佳代表。通篇先有名词的溯源如“草之精秀者为英”“兽之特群者为雄”,继有名词的定义,如“聪明秀出谓之英”“胆力过人谓之雄”,尤其注意“英”“雄”之间的密切联系,如“夫聪明者,英之分也,不得雄之胆,则说不行;胆力者,雄之分也,不得英之智,则事不立。是故英以其聪谋始,以其明见机,待雄之胆行之;雄以其力服众,以其勇排难,待英之智成之;然后乃能各济其所长也”,指出“英”的聪、明、智和“雄”的胆、力、勇要发挥所长、互相配合。随后以真实的历史人物为例,张良属于“英才”,是“聪能谋始,明能见机,胆能决之”,韩信属于“雄才”,是“气力过人,勇能行之,智足断事”,尽管如此,“英”“雄”都是“偏至之材”,只能担任人臣的职位,即“英可以为相,雄可以为将”,而集“英”“雄”于一身的则是刘邦和项羽这样的帝王。尽管如此,在这两者之中,“英”“雄”的分布也有不同,项羽英分少,故谋士去之,而高祖英分多,群雄服、英材归,两全其美。因此最理想的是“英”“雄”兼于一身,然后役使或“英”或“雄”的偏至之材,最终成就大业。在本篇里,刘劭是注意先规范“名”的概念,再步入细腻的析理,既有理论的阐析,也有事实的印证,环环相扣,很有说服力。
曹丕对当时的名理学也很熟悉。曹丕有《士操》一书,应该是人物品评的专书,与《人物志》同列《隋书·经籍志》的子部名家。《典论·论文》提出:“常人贵远贱近,向声背实,又患于自见,谓己为贤。”[5]720“向声背实”指一般人信从名声而不检核实际才能,这里突出了名实问题,而名实关系是名理学的基本内容。吴质《答魏太子笺》说:“伏惟所天,优游典籍之场,休息篇章之囿。发言抗论,穷理尽微;摛藻下笔,鸾龙之文奋矣。虽年齐萧王,才实百之,此众议所以归高,远近所以同声。”[5]566所谓“发言抗论,穷理尽微”,说明建安年间曹丕组织文学活动的时候,彼此之间有所辩论,反复回还,也促进了对名理学的了解。因此说,曹丕的偏才论体现了新兴的名理思想的影响。
四、“孟德三令”与偏才论的政治背景
刘劭《人物志》的才性理论,察其本意,应是为曹操的人才政策张本。刘劭曾入曹操幕府,于建安中担任计吏,又在尚书令荀彧处讨论礼制得到赞赏,荀彧在建安初曹操迎献帝都许时进为侍中、守尚书令,卒于212年,可知建安初年刘劭已追随曹操。
曹操明确提出了“唯才是举”的口号,颁布了一系列人才政策,简称为“孟德三令”:一是建安十五年(210)发布《求贤令》说“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又得无有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17]41;二是建安十九年(214)发布《敕有司取士毋废偏短令》宣示“夫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陈平岂笃行,苏秦岂守信邪?而陈平定汉业,苏秦济弱燕。由此言之,士有偏短,庸可废乎”[17]46;三是建安二十二年(217)发布《举贤勿拘品行令》要求“今天下得无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间,及果勇不顾,临敌力战;若文俗之吏,高才异质,或堪为将守;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17]48-49。陈寅恪《书世说新语文学类钟会撰四本论始毕条后》指出“孟德三令,非仅一时求才之旨意,实标明其政策所在,而为一政治社会道德思想上之大变革”[18]45,可知是为当时的学术和社会思潮的解放提供了政策依据。汉代的察举和征辟制度,注重士子的品行,以此敦励人们的道德崇尚。汉末大乱,军阀割据,社会政治陷于混乱,冲击了儒学独尊的地位,中央政府已难以号令天下,军阀竞相网罗人才,作为政治和军事的智力资本①非但曹操说“丧乱已来,风教凋薄,谤议之言,难用褒贬。自建安五年已前,一切勿论”(《三国志·魏书·陈矫传》注引《魏氏春秋》),孙权也秉承“忘过记功”“以功覆过”的选士宗旨,暨艳主管选曹,不解此旨,清浊甚明,而获罪自杀。参见田余庆《暨艳案及相关问题》,《秦汉魏晋史探微》(重订本),中华书局2011年。。因此,以勉励社会风气为目的的奖掖道德品行的举动,在这个时候显然不再适用。当时的主政者,要革新士人的旧观念,说服他们容忍传统意义上品行恶劣的人进入中枢,并希求他们同心同德、共赴时艰,那么急切需要在思想理论和历史事实上获得支持。汉末清谈渐渐流于名实乖离,曹操对名实不副的现象深为不满,又时值用武之际,迫切需要延揽人才;曹操是寒族出身,没有世家大族的道德束缚,又崇尚简易佻达,因此敢于延请有一技之长却背负污辱之行的人才。这是身为政治家和军事家的曹操指出才有偏短的出发点。
汉末社会实际存在着才德之争,代表了党汉党魏两种不同的取向。荀悦《申鉴·杂言下》载“或问:‘圣人所以为贵者,才乎?’曰:‘合而用之,以才为贵。分而行之,以行为贵。舜禹之才而不为邪,甚于(亡)矣。舜禹之仁,虽亡其才,不失为良人哉”[19]187,荀悦主张德才兼备,才德之间,以德为贵。徐幹《中论·智行》载:“或问曰:‘士或明哲穷理,或志行纯笃,二者不可兼,圣人将何取?’对曰:‘明其哲乎。夫明哲之为用也,乃能殷民阜利,使万物无不尽其极者也……’”[20]144荀悦曾任秘书监,献《申鉴》于汉献帝,则与汉室关系密切,徐幹曾任曹操的“司空军谋祭酒掾属”,后任曹丕的“五官将文学”,属于魏臣,荀、徐两人的观点不同,说明当时存在着代表汉魏不同倾向的才德之争。刘劭《人物志》在才德之争中更加突出了才性的作用,也是为曹操的人才政策张本。
曹丕是邺下文学活动的组织者和活动者,响应曹操的用人理念,也开始思考身边僚友的文学特长。建安十三年,曹操平定荆州后,天下士人辐辏邺下,曹植说:“昔仲宣独步于汉南,孔璋鹰扬于河朔,伟长擅名于青土,公干振藻于海隅,德琏发迹于大魏,足下高视于上京。当此之时,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吾王于是设天网以该之,顿八纮以掩之,今悉集兹国矣!”(《与杨德祖书》)[5]593钟嵘《诗品序》说“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笃好斯文,平原兄弟,郁为文栋;刘桢、王粲,为其羽翼。次有攀龙讬风,自致于属车者,盖将百计,彬彬之盛,大备于时矣”[21]12。邺下时期是建安文学的高峰,文学集会盛行,有南皮之游、西园(后园)之会、北园及东阁讲堂赋诗等,曹丕是邺下文学领袖,身边聚集了一大批当时最优秀的文人,又编纂了汇聚众人作品的总集“邺下集”和别集《孔融集》等,对当时的作家作品有深刻的认识,因此完全有能力有条件对建安七子的才能长短作出评论。因此《典论·论文》的偏才论,是曹丕在丰富的文学实践基础上经过深思熟虑而提出的论点。《典论·论文》写定于建安二十二年冬天以后,应是吸收了“孟德三令”的理念。曹操提出“士有偏短,庸可废乎”,放弃了汉儒主张的道德标准,强调的是治国用兵的一技之长。曹丕通过对自己领导的邺下文学的研判,强调了文体创作上的偏擅之才,实际上是对曹操人才政策的呼应。
五、余论
汉末建安时期的思想解放,和学术上清谈向名理的发展,以及曹操唯才是举的政策推动,促进了士人的观念变化,才性超越德性得到了重视,为偏才论的产生提供了实践和理论的土壤。曹丕与同时人的文学活动和理论总结是偏才论的实践来源,而刘劭《人物志》为偏才论提供了理论支持。随着经史分离和史学发展,东汉以来的文章体裁日益丰富,当时作家难以擅长全部的文体,却又自以为是,甚至互相讥讽,曹丕以太子之尊纵览全局、直击问题,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因此说,偏才论是建安时期作家论的核心。曹丕提出的“四科八体”,在文体分类和文体风格上取得了重要的成就,向来认为是开创了文体论的新纪元,但在建安时期仍属于作家论的副产品。随着文体论的发展,皇甫谧的《三都赋序》开始关注文体的源流辨析,直到西晋末年的挚虞《文章流别论》,融分类、风格和源流为一体,从而确立了文体论的基本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