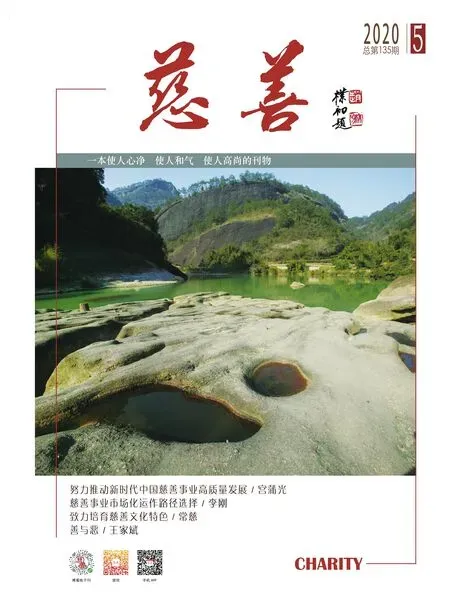文学殿堂
2020-12-08
这地方曾经有名,文学圈或喜欢过文学的人里很多人知道它,中国,上海。这并非意味着它多么伟大,只是因为,有一个新中国最早创刊的青年文学刊物——《萌芽》杂志——曾长期在这里办公。在文学青年千军万马浩浩荡荡的年代,有多少人向它投稿时写过这个地址啊:上海,延安西路200号,萌芽杂志社,邮编200040。
这是1996年以前的事。更早以前,我还没调到《萌芽》时,我也在信封上这么写过,怀着恭敬,忐忑不安。这地方对我遥远而神圣,我鼓足了勇气,才从写在笔记本上的诗歌习作里挑了两首寄给《萌芽》。一首有关灯光,大意是,灯光从灯罩下如水一般流泻,洒在爱人伏案工作的身影上,形成一个光的轮廓,让我温暖和安然,因为我正在注视他。另一首有关阳光——我和我的表姐,在清晨的一个公交车站上等车,谈她的画,我的诗,我们共同的理想,而阳光正在此时从远处铺来,一片淡金色笼罩了我们。现在我找不到这两首诗了。现在读到它们,我肯定会脸红,因它只对一丁点儿的表面美加以渲染,以此作为陶醉的依据,而对更复杂的生活躲闪回避。汤茂林老师却肯定了它并采用。后来我见到汤老师,感觉她就像一个慈爱的母亲(年龄上也接近)。她说,她喜欢我诗里的美,这美透露出一个人对生活的爱和渴望。
她坐在她的办公桌后面,说着就站了起来。她个子不高,两手撑在桌面上。她身后是一扇打开的窗,窗外天空衬着绿树,像一幅春天的画。她非常朴素,短发,灰色两用衫,白衬衫,像极了一位教书的老师,而不是我先前从名字上猜测的一个严肃的、高的、瘦的男人。在萌芽杂志社这间最里面、最小的办公室里,我一点也没觉得它逼仄。
作为作者,我第一次来这里开座谈会。我穿了一条咖啡色呢裙,手脚紧张到僵硬。我感觉这里的每个人,编辑、作者,都是好看的,有气质有风度。这也正像是我那时的诗,或我对文学的爱屋及乌的感情。
来过的人都知道,这地方不是一幢楼,是一个大院子,名叫文艺会堂。萌芽杂志社是在院子深处左角的一幢小楼里。小楼简陋,约建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楼梯拐角处总堆着一个个边角磨烂的纸板箱,里面是看过不用的弃稿。拐弯上去,三楼,就到了杂志社的玻璃门前。进门是通联组的办公室,再里面一个窄道,通往编辑部的大小办公室。天花板是一方方连接起来的
纸质材料,带着一个个小孔,新的时候也许漂亮,旧了却泛出一摊摊水渍来,有几块甚至耷拉下来,露出一只只大窟窿,黑乎乎的,深不可测。
到后来,我对这地方的印象,全被这些水渍和大窟窿取代了。
1986年12月,我进入萌芽杂志社,做了一个编辑。当时这本杂志的鼎盛期刚过,但还在整个文学的兴盛期内。盖着各地邮戳的稿件每天都来好大一摞,编辑们的办公桌旁,堆满一捆捆写着地区名的稿件:华东,华中,西南,东北,边疆……每个编辑都俨然成了“军区司令”,管辖着五六个省的文学青年。为一篇重点稿件,编辑会专门从上海跑到外省,盯着作者写稿,当场批阅当场修改再带回来,要不,就请作者来上海,住在隔壁文艺会堂招待所里,定定心心地写和改。为了稿件质量,花费多少一概不计。
后几年经济上有点紧了,可每年春暖花开时,编辑部仍会走出上海,和某个省市的作家协会联合举办青春笔会。编辑们和年轻作者们住在一地,“过堂”似的,对一个个作者的稿件会诊,提修改方案,让作者一遍遍改,直改到“通过”。
那是兴奋和新奇的日子。陌生的人,陌生的地域和素材,湖光山色,发亮的眼睛,跳荡在这一切之上的文学和人生的话题。大家像忘了一切,像在度假——一个和文学有关的轻松愉快的长假,说不定还在此结下友情,邂逅爱情。脱离了各自的生活背景,这群年轻人看上去个个优秀而有个性,他们都相信文学能够让生活放出异彩,能把自己从黯淡的凡俗生活中解救出来。
这样的聚会从一九九二、一九九三年以后突然消失。商品经济的大潮冲来,文学青年们如梦初醒,忽然意识到文学对于实际生存的无用或者无力,物质和金钱才是一切之基础。文人们纷纷下海——真的,在1993年上海的新民晚报上,“文学角” 曾开出一个由本市众多作家参与的接龙小说专栏,小说的主人公就叫“夏海”(“下海”)。《萌芽》来稿量骤减,发行量更是滑坡,编辑部里人心浮动。偶有昔日作者来访,名片上的身份,大多已变成“经理”“总裁”。
编辑部的天花板,好像就是从那时开始破出洞的。一到下午,办公室就没什么人上班了,仿佛都跑出去“找方向”了。我有时会坐在那里,盯着天花板发呆。再也没有人会在开会时为一篇稿子该不该发、打不打头条争得面红耳赤了。有两个不知文学为何物的生意人面孔的人,某一天忽然走进来,要每个编辑都出去拉广告,完成一定量的广告额。后经大家质问:经营部干什么吃的?这才没有实行下去。
我刚来这里上班时,文艺会堂的大院子宽敞,宁静,有很多树,树下摆着仿古的陶瓷圆桌和圆凳,男编辑们爱在这里喝茶,下棋,聊天。树后面一排平房是小卖部,柜台不大,店堂里摆了几张小圆桌,罩着洁白的桌布,可以让人坐下来喝一杯咖啡。作者、朋友来了,我喜欢带他们来这里坐坐。咖啡虽是速溶的雀巢,但盛在小白瓷杯里,放在小白瓷碟上,杯前搁一把不锈钢小勺,感觉还是很正式。小卖部旁有个礼堂,曾一度放映“内部观摩”的外国片,凡文艺会堂的工作人员每人一张观摩卡,贴着照片,以示非本人不得享有此特权,不过我拿到这张卡时,这类电影差不多外面都有放的了。
变化仿佛在一夜之间。对着华东医院的大门一侧,先是改成食堂,紧接着改成餐厅。《萌芽》楼旁的招待所也改建成一个餐厅,楼上楼下过道里全是养着鱼虾鳖的玻璃缸,楼上还有卡拉OK房。大门另一侧,一座现代化的“文艺宾馆”拔地而起,底楼由台湾人经营成一家“老爷车鱼翅餐厅”,也卖过牛肉面,35元一碗。我们开窗,就闻到混杂在一起的食物煎炒、红烧、清炖的气味。而我们后期因没了食堂,有的就在办公室泡面解决,偶有一人跑出去买肉馒头,大家都托他带,于是中午就一起在办公桌前大口吞咽冷了的馒头。
树只剩下院中央一棵。轿车围着它进进出出。有个长久不来的“文学中年”一次来看我,竟找不到《萌芽》,以为跑错了地方。《萌芽》栖身的小楼,缩在最里面小小的一角,黯淡,破旧,在近旁豪华的楼堂中完全不起眼。它的容身已岌岌可危。
从我来这里上班,到随《萌芽》迁走,前后共有十年。十年,很长,一场战争都可以结束,一个孩子会长成大人。儿子当年跟我第一次来这里时,还是个不懂事的小不点儿,指着一个男编辑身上的“梦特娇”T恤没来由地说“假的”“大兴的”(冒牌货之意),然后一溜烟跑下楼钻进院子的树丛里没了影。他第二次来到文艺会堂,是跟着我来参加《萌芽》举办的青年诗歌朗诵会并兼作服务,当这个一米八的初中生拿着节目单在新建的礼堂门口向到会者散发时,有个矮个子高中生上前叫了他一声“老师”,把他闹了个大红脸。那个中学生也是紧张的吧,来参加一个文学活动,他是否也紧张到把所有人都当成大人,好看的人,有风度有气质的人,就像当初的我?
十年是一个历程。我却无法细说。就像我对文学的态度和感情一样,不能用一句话概括。对它,这十年,这地方,我经历了从向往、膜拜到怀疑、失望的转变,有过沮丧,也有新的认识产生,那是往下沉了,而不是向上飘去,从虚无和缥缈中寻找慰藉。其中也有反复——浮躁、 焦虑、痛苦、恍惚、徘徊……文学之路如人生之路,是无法预期,只能摸索体会着慢慢走。大量的阅读帮助了我,不仅阅读稿件,作品,他人的生活和思想,也阅读自己,自己的人生和内心。文学或许就在这一点上和人生连在了一起。然后人有了一个稍高的开阔的立足点,能看见天空、远方,也看见近前的地面上发生的事情。
文艺会堂在延安西路的开端,门前的马路曾幽静美丽。它所处的地区,叫“美丽园”。它斜对面的马路上,有上海戏剧学院的一个后门。在它东面,就是我熟悉的静安寺了。由此我相信世界对一个具体的人来说并不很大,转来转去的,她仍在命运给出的范围内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