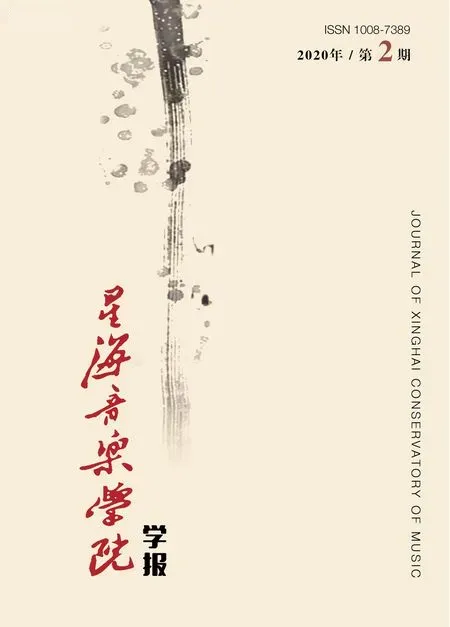文化非本质主义·主体性·自我民族志
——民族音乐学研究的三个重要学术观念
2020-12-05赵书峰
赵书峰
民族音乐学研究就是跨学科方法论交叉互动思维语境对于田野工作的审视与观照,只有将上述两者之间展开“接通”性思考,才能更加圆融地、相对合理与接近真实的描述与分析音乐形态特征以及独特的音乐文化隐喻。民族音乐学研究者的田野工作反思不但是对研究者的田野过程的学术反思,也是研究者长期研究观念的一种自我批判与学术观照。任何一位民族音乐学学者只有时刻保持敏锐的学术思维与自醒的学术研究理念,才能使自己的学术研究不断开拓与创新。在文化人类学研究领域,对于田野与学术研究自我反思的经典个案较多,具有代表性的有美国著名人类学家保罗·拉比诺《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1)[美]保罗·拉比诺:《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高丙中、康敏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和英国著名人类学家奈杰尔·巴利《天真的人类学家——小泥屋笔记》(2)[英]奈杰尔·巴利:《天真的人类学家——小泥屋笔记》,何颖怡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年。,结合自己的田野工作经历与学术研究展开了深入的学术自我反思,可以说是当下民族音乐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必读的经典个案。受上述学者研究理念的深刻影响,笔者就多年来的瑶族传统音乐研究心得与田野工作经历,结合当下世界民族音乐学学术语境,针对民族音乐学田野工作与案头工作中应坚持的“文化非本质主义”(3)“非本质主义”又称“反本质主义”,主要是指真理或身份(认同)并非自然、普遍通用之物,而是受特定时空限制的文化产物:发生的主体,必须先有所谓话语或论述位置的存在;与其说真理是被发现的,倒不如说是被制造的,而认同(身份)是话语论述建构出来的。参见[澳大利亚]Chris Barker,Emma A.Jane:《文化研究理论与实践》,罗世宏译,台北: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8年,第23页。与文化“主体性”两种重要的研究观念展开讨论。
一、如何看待“传统的发明”问题
有关“传统的发明”(4)[英]E·霍布斯鲍姆、T·兰格:《传统的发明》,顾杭、庞冠群译,北京:译林出版社,2004年。的概念提出主要来自于英国著名的后现代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的研究,他在其《传统的发明》一书中认为:
“被发明的传统”意味着一整套通常由已被公开或私下接受的规则所控制的实践活动,具有一种仪式或象征特性,试图通过重复来灌输一定的价值和行为规范,而且必然暗含与过去的连续性。(5)[英]E·霍布斯鲍姆、T·兰格:《传统的发明》“第一章 导论:发明传统”,顾杭、庞冠群译,北京:译林出版社,2004年,第2页。
可以看出,霍氏提出的上述概念与当下中国传统音乐学研究中某些学者的研究理念格格不入,属于非常典型的“文化非本质主义”思维。笔者认为,霍氏概念的核心观念是:传统文化的身份不是固定的、静止不变的,而是随着所处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中的变迁,会被操纵文化权力者的政府与民间艺人进行不断地发明与创造,同时也说明文化身份是一个持续性建构过程。所以,“传统的发明”在长期的社会历史发展背景中一直在持续,而且像泉水一样源源不断,因为文化的互渗、互融现象会随着人在跨区域、跨国界流动与传媒信息迅捷的现实世界中不可阻挡。任何追求“文化本质主义”的思维都是乌托邦。部分研究者认为越古老的文化越值得研究,一看到改变的、创新的东西就视而不见,认为毫无研究价值,这其实是学者的研究观念陷入了“文化本质主义”思维。若结合后结构主义、后现代理论去看待传统音乐文化的发展与变迁,传承与创新的时候,我们的研究思维或许又打开了一扇明亮的窗户。黄翔鹏认为“传统是一条河流”(6)黄翔鹏:《传统是一条河流》,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0年。,这其实是黄先生对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传承与发展问题的最为形象的比喻,即在强调中国传统音乐文化是一条源源不断的河水,在从长江的源头一直流到上海的吴淞口进入东海。作为长江主干道的文化是其传承母体,在流过数千公里流域过程中,途径诸如岷江、嘉陵江、汉江、沅江、湘江、赣江等等支流为代表的新鲜活水注入长江主干道,最后流入吴淞口,然后注入东海。因此,我们不仅要问:吴淞口的水与长江源头的水难道是完全一样的吗?答案其实是否定的。所以,这是对传统音乐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以及跨文化互动交流语境下的“传统的发明”的最好诠释,即任何传统音乐文化绝不是原样的纵向传承的,而是在吸收跨文化元素基础上的一种发明与创造。因为,“传统继承不是原样的继承而是创造性的继承。传统继承不是模仿和重现,不能仅仅停留在文本的背诵和训诂层次,而是在新时代面向新问题的新的理解,是对传统文本在新的视域下的参与和诠释”(7)洪汉鼎:《诠释学:它的历史与当代发展》“再版序”,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13页。。
当下受“非遗”运动的影响,地方政府对民间文化进行了重建,将用乐语境,表演方式、表演内容进行了发明与再造,这一切都是为了适应现实多样化的审美语境的需要,随着历史积淀与审美受众的走向趋同性(或形成某种文化认知“共识”),进而也就成为了一种新的地方文化“传统”。随着“非遗”音乐表演的用乐语境、用乐方式、表演内容的重建,经过国家文化部门与“专家系统”对其进行界定后,成为了一种具有发明性质的“非遗”项目,这种被重构的民间文化就是“传统的发明与本土音乐文化的重建”(8)赵书峰:《传统的发明与本土音乐文化的重建——基于中国少数民族音乐身份认同变迁问题的思考》,《音乐研究》2019年第1期,第67—78页。。这种被发明的文化传统首先包括纵向“传承链”(“传承主题”或文化母体)与“时间链”“变体链”三者之间的互文关系。其中包含有地方民间艺人与学者(或者专家系统)多方音乐话语实践下的一种创造性思维,是一种发明的民俗仪式音乐表演传统。比如过山瑶的“盘王节”民俗仪式展演,是在瑶族民间“还盘王愿”仪式的基础上,加入了很多当代元素的一种文化重构,在“非遗”运动的影响下,现在被政府打造成一种新的传统文化,也成功申报为一种国家级“非遗”项目。(9)赵书峰:《传统的延续与身份的再造——瑶族“盘王节”音乐文化身份研究》,《中国音乐》2020年第1期,第25—32页。又如2018年开始在每年农历秋分日举办的“中国农民丰收节”,就是国家政治话语建构的现代节庆活动,是农民直接参与的一种反映全国亿万农民庆祝农业丰收节庆的一种盛大节日,于2017年在全国两会期间由人大代表提出议案,2018年由国务院正式审批通过。整个节日活动分为农事竞赛与文化展演。其实,中央政府成立“中国农民丰收节”也是充分基于各民族传统的丰收节庆基础上的具有政府行为的民俗节庆的当代重建产物。这种节日重建,若干年之后也就成为了一种真正的文化传统。所以,对于“传统”的认知必须以动态的眼光看问题,即今天由政府建构而成的“中国农民丰收节”也是保持在历史的连续性基础上的一种文化新传统。
二、如何看待文化“本真性”问题
“文化非本质主义”思维是人文社科研究中秉承的学术理念,它强调动态的眼光看事物的形成与发展。当下,中国民族音乐学研究理念应坚持“文化非本质主义”思维来看待研究对象的发展与变迁问题,而不是一味地用“本质主义”思维追求研究对象身份属性的“本真性”(“原生态”“原汁原味”)特征。
当下追求传统音乐文化“本真性”的思考本身就是一种“本质主义”思维。目前,有关文化的“本真性”问题的研究,以刘晓春、刘正爱(10)刘正爱:《谁的文化,谁的认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中的认知困境与理性回归》,《民俗研究》2013年第1期,第10—18页。、姚慧(11)姚慧:《何以“原生态”?——对全球化时代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反思》,《文艺研究》2019年第5期,第143—151页。等为代表的人类学与民俗学研究者分别撰写文章进行了深入论述。当下在中国民族音乐学的田野工作中也时常碰到上述问题,比如笔者在瑶族音乐的田野工作中经常看到某些学者抱怨说,很难看到他们自认为是古老的“传统”的音乐,尤其碰到改编过或者加入流行元素的表演,这些学者总是觉得不值得研究,甚至表现出很失望。因为,有的学者怀着美好的期待进入田野,当自己置身于田野现场时看到的多是创新的或者改编的东西,他们/她们变得心灰意冷,甚至有曾放弃研究的念头。笔者认为,这就是“文化本质主义”思维在作怪,因为他们追求的是所谓“本真性”的传统音乐文化,或者是原汁原味(“原生态”)的东西,当看到变了味的音乐文化表演时,却表现得不屑一顾。这些学者一味地认为,传统的东西是不允许变化的,是需要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的。所以,当他们看到田野中改变的元素,就主观地认为这些传统是“伪民俗”(12)有关“伪民俗”问题的讨论,参见赵书峰:《传统的发明与本土音乐文化的重建——基于中国少数民族音乐身份认同变迁问题的思考》,《音乐研究》2019年第1期,第76—77页。。因为他们看不到传统的变迁与身份重构的研究价值,而是一味追求传统的“本真性”(“原汁原味”)的特点。鉴于此,笔者认为,当下学者的田野观念的转变非常必要,我们要坚持“文化非本质主义”思维看待研究对象。因为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永远是历朝历代一个永恒的主题,文化的变迁与音乐的重建都是为了适应其所处社会文化认同与审美的需要。若是传统音乐文化在其起源之际就亘古不变,我相信,这种文化的生命力就不会长久,因为它不会“随波逐流”“与时俱进”,换言之,就无法适应其特定的审美语境的需求。传统也是这样的,经过数千年的传承与创新以及历史积淀,一直流传到当下,在不断地保持“历史连续性”(传承主题)的首要前提下,不断地“与时俱进”的产物就是文化的“变体链”,即特定社会语境中的多元文化互动交流后的融合与创新。所以,田野观念的转变也是学术思维的更新,没有上述前提,我们的学术研究就会止步不前,永远在“炒剩饭”或做重复研究。因为,“‘传统’事实上只是今人的一种文化建构,而远远不是什么远古或原始部落的规范习俗”(13)陈定家主编:《全球化与身份危机》,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10页。。
其次,当下传统仪式音乐的重建问题其实就是强调回到历史原生语境的表演,或者追求表演的“本真性”问题。比如模仿与仿造传统古乐器进行表演,希望回到历史时空语境,虽然乐器仿造了古代的做法,但是由于社会语境的时空变迁,充其量是其乐音形态的时空穿越,但是其表演语境与音乐的表征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甚至是经过数百年的地理气象环境的变迁,乐器的物理学现象也发生了变化,导致乐器的“原生”的声音形态发生改变。虽然强调再现历史声音语境,充其量就是乐器制造工艺与乐器配置的再现,而不是其声音景观的一种历史重现。因为,再现的是声音形态,不可能还原其音声场域与表演语境。比如,古典雅乐重建行为就是要寻求一种重回原生性表演历史时空语境,其实只要是文化重建就会与“原生”时空表演场域不一样,甚至是一种再造、创新。因为声音景观是一种历史建构。某些学者追求音乐文化的“本真性”问题本身就是对传统文化声音形态与表演语境的一种“原生”诉求。结合美国著名民俗学家理查德·鲍曼的表演民族志理论可以看出,任何的一场表演都具有“新生性”(14)[美]理查德·鲍曼:《作为表演的口头艺术》,杨利慧、安德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79页。,都是“去语境化”与“再语境化”的过程。所以,民族音乐学强调传统音乐文化研究的“本真性”问题无形中却陷入了“本质主义”思维。因为音乐重建的是声音形态而不可能再现原生性的表演语境。正如英国当代文化研究之父、学者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认为:
文化身份根本就不是固定的本质,即毫无改变地置身于历史和文化之外的东西,它不是我们内在的,历史未给它打上任何根本标记的某种普遍和超验精神,它不是一层不变的,不是我们可以最终绝对回归的固定源头。(15)转引自汪安民主编:《身体的文化政治学》,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96页。
再次,目前在民族音乐学界(或者传统音乐研究中)仍有部分学者坚持“文化本质主义”思维,孰不想,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社会与当下多元化的中国社会语境能一样吗?社会语境的变迁给传统音乐文化的发展带来哪些问题值得我们思考。因为,语境变迁将会导致生于斯、长于斯的传统音乐的生存与叙事语境发生变化。当我们看到“非遗”被打造、包装后为地方旅游经济文化的发展做贡献的时候,难道还是“本真性”的民俗节庆叙事的传统文化吗?即便其音乐形态没有变化,但是传承人、表演者的审美思维已经发生改变,这难道不会影响传统音乐文化的传承吗?尤其是以人为主体性建构而成的传统音乐,虽然在传承方式与传承制度上一直坚持封闭性、规范化、正统化原则,但是由于用乐者审美语境的变迁,也会导致其音乐表演文本理解与建构的潜在逻辑思维观念发生变迁,由此造成其音乐与表演形态的风格与内在气质发生变化。所以,追求传统音乐文化的“本真性”思维,根本忽略了社会语境的综合变迁以及音乐传承主体——传承人对于音乐表演风格的理解与传承人本身性格、世界观、价值观、教育背景、传承流派、经济利益等等综合因素的影响。因为,面对当下急剧变革的社会,我们逐渐发现:“乡愁文化”正在被现代化的城市生活所遮蔽,“乡愁”只能保留在儿时的记忆中。因为社会语境变化了,硬是要我们继续追求传统文化的“不变”,那是乌托邦思维。当下传统音乐文化正在经历一个文化身份重建的过程,它不但是表演形态的持续性变迁,同时也是文化象征功能的改变。所以,民族音乐学田野工作中的“文化本质主义”思维既不利于重新认识传统音乐的身份重建与文化变迁问题,又无助于审视多元化社会语境中传统音乐变迁的内在逻辑结构。因为,传统音乐是长期的社会历史积淀的文化产物,是跨文化互动与交融语境中不断地、持续性地建构与变迁的产物。传统音乐的建构是一个历史积淀之后形成的“惯习”,当然保持与“历史连续性”是首要的,因为这是“传承主题”不变,而“变体链”就是一种特定社会语境中的多元文化互动交流后的融合与创新。所以,任何传统音乐文化都是在不断地传承与创造、采借与发明基础上的一种文化重建,强调对于文化的“本真性”研究的诉求,实质上也就是陷入了一种文化的“本质主义”思维。(16)同时有必要说明的是:笔者并不全盘否定学者们在学术研究中所坚持的“文化本质主义”思维,因为这要视研究对象的文化特性而定。
三、 少数民族音乐文化“主体性”观念反思
民族音乐学者的田野工作观念尤其要关注少数民族音乐文化的主体性问题,尊重音乐“文化持有者”的文化主体性,用“他者”的观点理解“他者”,这同时也是田野民族志书写的一个基本原则。有学者认为:
在一个民主的多民族国家中,对于不同的具体民族文化,首先需要的不是先进与落后、文明与愚昧的简单比较,而是一种平等、尊重的态度。平等地对待其他民族,真诚地视为平等主体,并尊重其他民族的民族文化。尊重少数民族,尊重少数民族的主体性地位,尊重少数民族文化,这是少数民族文化保护活动中的基石。(17)高兆明:《多民族国家中少数民族文化保护的主体问题》,《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0期,第2页。
美国著名人类学家卢克·拉斯特认为:
若我们怀着敬意去真正了解其他人(即使是野蛮人)的基本观点……我们无疑会拓展自己的眼光。如果我们不能摆脱我们生来便接受的风俗、信仰和偏见的束缚,我们便不可能最终达到苏格拉底那种“认识自己”的智慧。就这一最要紧的事情而言,养成能用他人的眼光去看他们的信仰和价值的习惯,比什么都更能给我们以启迪。(18)[美]卢克·拉斯特:《人类学的邀请》,王媛、徐默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87页。
所以,尊重少数民族音乐文化的“主体性”原则是民族音乐学研究者必须要遵守的田野伦理。坚持文化的“主体性”原则也是为了更加客观地描述研究对象真实的音乐生活。仔细回想,从当初进入田野的“青涩”中多次违反田野禁忌到如今尊重田野伦理等学术自觉,这一切都是笔者多年田野实践中得出的学术反思。因为少数民族音乐文化的“主体性”是其民间生活语境中自然发生的一种文化样态,因此,强调文化的“主体性”是要求针对其音乐表演语境有一个基本的尊重,用“文化持有者”的局内观去理解和研究他们的文化,即用“他者”的观点去研究他者的音乐文化,而不能忽略被研究者真实的生活样态去主观建构我们的田野思维。所以我们会经常发现:部分研究者对当地文化的价值判断先入为主,对音乐表演者“指手画脚”,甚至要求表演者按照他们的指导进行表演,这种做法明显地忽略了少数民族音乐文化的“主体性”原则,因为“主体性”是作为“文化持有者”的“他者”对其拥有的族群传统文化的一种主位表达(“自表述”),它是对当地人民俗音乐文化生活的真实写照。
其次,缺乏对于少数民族音乐文化“主体性”认识。当下国内各级别的人才项目培训,不考虑少数民族音乐文化的“主体性”特点,一味地用同质化标准(或欧洲音乐文化中心论思维)来审视和规范少数民族音乐的审美。比如,少数民族歌唱的培训中,用专业音乐学院的标准来规范其别具个性的唱法。这种做法明显导致少数民族音乐文化的“主体性”丧失,用一种标准规范不同文化中具有个性的歌唱,由此造成文化主体与客体的本末倒置。比如,国内某高校国家艺术基金项目的培训中,汇集了国内众多少数民族歌手,主办方用西方古典音乐的音高概念与歌唱思维来“训练”他们。我们知道,少数民族音乐的音高概念与西方古典音乐相差很大,这是用“欧洲音乐文化中心论”思维来规范他们别具个性的歌唱风格与音高概念,其做法忽视了少数民族音乐文化的“主体性”认知,这不利于中国少数民族音乐文化多样性的可持续发展。因为用文化的标准化、同质化去抹平传统音乐的多样性、个性化特征,丧失了各具特色的少数民族音乐的“主体性”认知。因此,只有建立田野工作者与研究对象的文化身份与话语权力的平等原则,用“他者”的文化价值观去理解“他者”,我们的传统音乐文化的教育与传承,民族音乐学学者搜集到的田野资料才相对接近真实,才真正体现传统音乐文化的“主体性”原则,同时这样的学术理念才真正符合田野工作的基本伦理规范。
四、自我民族志思维与民族音乐学研究者学术观念反思
自我民族志研究属于民族志研究的后现代思维,当下在文化人类学研究领域已经有比较成熟的研究基础,其代表性研究成果主要有:蒋逸民《自我民族志 :质性研究方法的新探索》(19)蒋逸民:《自我民族志 :质性研究方法的新探索》,《浙江社会科学》2011年第4期,第11—18页。、徐新建《自我民族志:整体人类学的路径反思》(20)徐新建:《自我民族志:整体人类学的路径反思》,《民族研究》2018年第5期,第68—77页。。当下,受到后现代人类学与现代民族音乐学研究观念的影响,部分学者开始结合人类学的“自我民族志”研究理念,展开学术自我反思与批判性研究。自我民族志研究就是基于阐释人类学背景下的(深描),从传统民族志书写(他表述)走向以研究者作为研究对象或研究主体的,并对研究者亲身学术经历和学术观念进行学术反思的一种后现代民族志书写范式(“自表述”)。也就是说,民族音乐学的自我民族志是基于长期深入的田野经验基础上,研究者从对“他者”音乐的研究中跳出来针对自我学术研究经历与研究观念转变进行反思的一种“非虚构性写作”。(21)赵书峰:《改革开放40年中国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民族艺术研究》2019年第1期,第34页。通过自我民族志的书写,可以观照作为研究者的自我在反观自己研究对象的时候,所经历的种种学术观念反思与研究对象的文化变迁过程。以2008年以来笔者的瑶族音乐研究的体会为例,逐渐认识到自己学术观念的不足与局限性,因此近些年学习了诸多与民族音乐学研究相关的跨学科知识。尤其是近5年(2015年至今)以来,笔者受到“华南学派”(22)王传:《华南学派史学理论溯源》,《文史哲》2018年第5期,第23—37页历史人类学思维、结构主义与符号学理论(如互文性理论(23)[法]蒂费纳·萨莫瓦约:《互文性研究》,邵伟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 年。)、后结构主义人类学(如弗雷德里克·巴斯的族群边界理论(24)[挪威]弗雷德里克·巴斯主编:《族群与边界——文化差异下的社会组织》,李丽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年。)、文化与身份认同(如斯图亚特·霍尔的文化研究理论(25)[英]斯图亚特·霍尔、保罗·杜盖伊编著:《文化身份问题研究》,庞璃译,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 年。),后现代史学理论(如霍布斯鲍姆的“传统的发明”理论),以及民俗学的“表演民族志”(如理查德·鲍曼的理论(26)[美]理查德·鲍曼:《作为表演的口头艺术》,杨利慧、安德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等诸多跨学科理论的深刻影响,极大地丰富了本人的田野实践与理论思考。因为,任何一位学者都应该进行自我学术反思与批判。民族音乐学研究中的自我民族志研究就是将学者的学术反思与批评,以及个人的学术经历与田野工作展开“文化非本质主义”思维,而不是一味地针对任何田野研究对象坚持“本质主义”思考。只有不断地进行自我反思与批判,每个人的学术研究才会有持续性地进步与创新。因为,作为研究者的研究对象在长期的时空转换语境中的文化身份与音乐形态的变迁现象,也直接影响作为研究者的自我学术观念的调整和转型。比如,在笔者多年来的过山瑶音乐的学术研究历程中,由于早期缺乏对于瑶族传统音乐文化历史的深度认知,致使自己的学术研究缺少更多的历时性研究(27)这种现象在当下的部分民族音乐学研究中仍然存在,虽然目前有所改变,但是很多学者仍坚持以共时性研究为主的学术路径。,因此导致对瑶族传统音乐文化的历史文献全面、深度挖掘,梳理与总结不够。因此,近些年笔者结合诸多历史文献资料(官方历史文献、民间历史文献等)与大量的田野工作材料,针对瑶族音乐的历史与当下展开了初步的历史民族音乐学研究,期间发表了诸多相关问题的学术成果(28)代表成果主要有赵书峰:《历史民族音乐学研究的新思考》,《音乐研究》2015年第6期,第86—94页;赵书峰:《瑶族婚俗仪式音乐的历史与变迁》,《中国音乐学》2017年第2期,第12—20页;赵书峰:《关于中国历史民族音乐学中几个关键问题的思考》,《中国音乐》2019年第1期,第55—60页。。其次,在看待瑶族音乐的“本真性”等问题上,受到霍布斯鲍姆“传统的发明”的理论以及斯图亚特·霍尔的“文化身份持续建构论”深刻影响,不再固执地一味坚持瑶族音乐文化的“原生性”研究,而是结合全球化与地方化语境中的瑶族音乐文化身份的重建问题展开动态地审视与观照。上述学术研究理念的转型是笔者长期的田野实践与不断地学术自我反思与批判的产物。
结语
首先,当下的中国民族音乐学研究对于传统音乐文化的认知不能完全停留在“文化本质主义”思维层面,或者一味地追求传统音乐文化的“本真性”问题,而是要结合“文化非本质主义”思维,针对“传统的发明”与音乐文化身份的持续性建构问题进行动态地深入思考。其次,民族音乐学田野工作中的“主体性”原则,不但是为了培养研究者尊重音乐“文化持有者”的局内表演观,而且是为了相对真实地把握与认知“他者”音乐文化所拥有的“地方性知识”。最后,开展自我民族志研究不但可以洞悉民族音乐学研究者学术理念转型的历史轨迹,而且有助于研究者更好地展开学术自我反思与批判工作,这对于提升民族音乐学学者的实际研究水平具有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