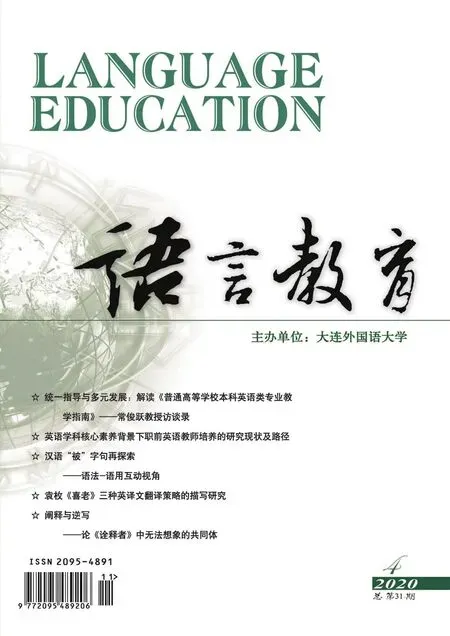阐释与逆写
——论《诠释者》中无法想象的共同体
2020-11-25胡燕姚峰
胡 燕 姚 峰
(1.北京外国语大学非洲学院,北京;2. 上海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上海)
《诠释者》①一译《痴心与浊水》。(The Interpreters)系非洲首位诺奖桂冠作家沃莱·索因卡(Wole Soyinka)创作的第一部小说,成书于1963年。该书于1965年出版时,尼日利亚独立仅有5年,新生的政权根基未稳,正处于飘摇欲坠之中;国家内部冲突频起、危机四伏。在这种语境中创作的《诠释者》带有深刻的民族隐喻。小说叙述了五位留美归国的知识分子对尼日利亚国家前途、个人命运、社会发展的焦虑与探求,他们以不同的方式对民族传统、当代现实、国家建设及其解决方案进行了各自不同的阐释,共同勾勒出一幅万花筒般斑驳陆离、分裂失序的时代画面。知识分子群体对当下价值认同的分歧投射出一个关于现代民族国家的重大命题——想象的共同体,这种想象在亚非民族主义思潮持续高涨的1960年代却难以促使尼日利亚形成一个紧密的共同体。
根据安德森的解释,在最后一波民族主义——即亚非殖民地民族主义——中,殖民当局利用同化政策培养了一批双语精英,不同部族的成员得以使用同一种语言;同时,殖民教育使这一小部分精英接解了欧洲历史,包括18世纪以来的民族主义思想(本尼迪克特·安德森,2003:134-158)。亚非殖民地民族主义参照、模仿了此前的欧美民族主义模式,遂使民族共同体的想象之花开遍亚非大陆。在非洲,自1947年坦桑尼亚取得民族独立以来,大多数国家于1960年代相继独立。然而,许多独立后的非洲国家在民族一体化进程中乱象丛生。就尼日利亚而言,共同体想象的断裂发生于1967-1970年的内战期间。《诠释者》极富预见性地反映了民族想象的破灭。问题在于,索因卡为何要在民族独立情绪高涨的1960年代初创作一部预示民族分裂的作品?
本文拟通过对《诠释者》的转喻式阅读,探究尼日利亚后独立时期知识分子与民族建构的关系,试图阐明1960年代尼日利亚共同体难以想象的原因,论证知识分子群体的疏离隐喻了民族共同体的分裂;同时,索因卡对民族想象进程断裂的前瞻性书写,既是对当时社会现实的鞭笞,也是致力于建构“非洲世界”和非洲文学文化主体性的努力。此外,本文通过借用“想象的共同体”这一学界所共喻的概念,为重访该小说提供一种新的思想资源,并以此管窥索因卡复杂的文学世界。
1. 知识分子的殊异阐释与幻灭
本·奥布姆塞路(Ben Obumselu)指出,《诠释者》问世之初,多以作者未建构文学想象的统一体(imaginative unity)而被误读(Obumselu, 2018: 167)。帕尔墨(Palmer, 1972: xiii xiv)的批评更为直白,“语言的灵活性和复杂性本身几乎成为目的……说《阐释者》具有精心构思的整体结构,或者说仅凭叙事部分成就了小说的紧凑结构与整体性感觉,这种赞誉显然是言过其实了。《阐释者》给人留下的主要印象是沉闷乏味、形式不够完整”。这种批评显然并没有考虑和理解索因卡在非洲民族独立之初对时政的警醒意识和对民族分裂的预感。早在尼日利亚独立初期,索因卡就对国家政权潜藏的独裁、腐败等失序倾向感到忧惧。这在其独立之际创作的预言式戏剧《森林之舞》中早有揭示。1960年代见证了这个羽翼未丰的国家遭逢政治变革与民情动荡。暗流汹涌的政治危机似乎在显示一个新生的现代民族国家正走向分崩离析,并预示内战的威胁。在这种充斥着暴动、抗议、冲突的氛围中问世的《诠释者》,“充满了不祥的预兆”(索因卡,1987:4)。
索因卡的笔触并未直接涉及当时的政治危局,但瓦解分裂的基调贯穿小说始终。作品采用现代主义的手法,显示出作家大胆挪用西方文学形态的尝试;更重要的是,如此挪用目的在于呈现行将分裂的民族隐喻图景。非线性叙事打破了时间的连续性,在现在、过去、未来之间任意快速地穿梭;故事主线缺失;主要人物的过往经历与记忆片段通过“闪回”呈现,打破了空间的连续性,却突出了人物的流动意识;人物行为与事件场面的表达常常因出自不同诠释者的视角且机锋暗藏而显得暧昧不明(Maduakor, 1986: 81-82)。这种试验性叙事,加上索因卡晦涩的语言,将文本结构变成一个层次繁复的迷宫,使小说在形式上显得混乱、不完整。正是在这种看似残缺散碎的结构中,嵌入了五位主要人物在现代社会中的遭际以及各自的阐释,新生的民族国家也在他们与传统、现实、理想的交汇中获得呈现,显示知识分子群体遭遇的精神危机。
工程师兼雕塑家塞孔尼(Sekoni)患有口吃,似乎隐喻了他的阐释之路难以顺畅,更隐喻了他实现科技建国梦想的艰辛。他渴望用自已掌握的现代科技知识和经验使祖国山河日新、大地焕颜,为她修桥、铺路、兴水利、建电站。为了将梦想付诸实践,他向政府申请建立了一座实验小电站,以期造福一方民众。电站尚未开工就被公司董事长注销,因为“注销工程比完成工程还能赚钱”(索因卡,1987:37)。他那带着口吃的解释终究未能敌过白人“专家”的不合规“指控”。他因此进了疯人院,最终惨死于一场车祸。塞孔尼的命运显然指向一个罹患疾病的社会中知识分子群体命运的不确定性。发电站工程的夭折和他的精神失常与死亡,正是知识分子壮志难酬的厄运,也是难以言说的民族失序的悲剧。
艾格博(Egbo)的部落贵族出身和现代教育经历决定了他必定要在传统与现代之间作出抉择。与传统连带的部落贵族特权使他产生回归的欲望,令他望而却步的是,传统在他看来已丧失活力,但拒绝传统、回到现代世界,又只是把他变成一个“絮絮叨叨的奴隶”(索因卡,1987:14),仍算不得是一个好的选择。因此传统的诱惑始终如影随形,使他无所适从。这种选择的困境恰当地隐喻在他与三位女性的关系中。胖女人阿沃利比(Owolebi)象征传统的母体引力,但又代表着女权社会,平静得出奇。喜媚(Simi)孤傲冷艳,对他保持长久的吸引力,但其神性般的存在中,同样隐含着难讨艾格博欢心的“死水”意象。而代表新时代知识女性的女大学生扰乱了他与传统的关系;同时,这股力量又显示出他难以把控的、极强的独立自主性。他最终对女大学生求而未得,暗示了他对现代社会的无力诉求和对责任的无力承担。如果说艾格博本人隐喻了独立后的尼日利亚民族,那么这个民族此时尚未处理好继承传统与拥抱现代的关系。既无力完成传统的期望,又无力承担现代的责任,正是建国之初部分知识分子在传统与现代之间难以取舍的矛盾心境。
萨戈(Sagoe)是活跃的社会批评家和黑幕揭发者。新闻报道工作把他带往拉各斯乱象丛生的各个角落。他显然明白,自身所处的社会正罹患疾病,亟需救治。然而,面对被腐败侵蚀的现代国家机器,他能否抵挡它对个体的异化,真正履行记者的职责,帮助社会排泄污浊?似乎都成了问题。他将塞孔尼被诬陷的事件诉诸笔端,却成为报馆与当事机构之间暗中交易的砝码,而他本人也不得不接受“你是我们雇佣的。你用的是我们的时间,这是我们的财产”这一套说辞(索因卡,1987:139)。从一开始,他就让自己相信,德林诺拉爵士(Sir Derinola)所代表的腐败传统无法改变。充斥在他脑子里的排泄理论(Voidance)是他对尼日利亚的不卫生和恶劣现象的迂回批判,但这种伪哲学却暗示这一群阐释者难逃异化的混乱处境。毕竟他走街窜巷,出入于上层社会的聚会,无不是为了在这个“制度”下,“利用别人挣钱过日子”(索因卡,1987:266)。
本德尔(Bendele)提醒读者注意尼日利亚现代社会中的道德沦丧。他以敏感的洞察力看穿一切骗局和伪善:艾格博对女学生的侵犯以及对喜媚的不忠、科拉的绘画创作和萨戈的新闻报道可能成为另一个有害“神话”(索因卡,1987:265)的宣传、拉撒路(Lazarus)把小偷变成信徒背后的图谋、鲁莫耶(Lumoye)医生对生命的随意和奥古阿左教授以体面为名的伪善,等等。其批判直指其他阐释者的良知。与萨戈的新闻披露相比,他对伪知识分子——法塞尤、奥古阿左、鲁莫耶等受西式文化腐化的精英群体的谴责更为猛烈,但又如艾格博在故事展开未久所质疑的,本德尔身为大学教授,仍默认了这个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生存则意味着“助长”了它(索因卡,1987:13)。
科拉(Kola)的阐释聚焦于对《众神像》(“Pantheon”)的表达。一直以来,索因卡努力在哲学与现实层面建构一个和谐的“非洲世界”,他认为当下的世界已然失序,因与神祗世界断裂而陷入了混乱。艺术的功能是创造一座桥梁连接“转换的深渊”,使分离的神祗世界与现实世界、传统世界与现代世界相接,复原宇宙、生命的循环与和谐。《众神像》的创作意图便在于实现这种连接功能。但科拉似乎并未成功掌握连接传统与当下所需的力量,他“知道自己的双手是有力量的,并且有转化力量的愿望……中庸是微不足道的,而要有行动,在画面上或者在人的肉体上展开行动……但他对完成这一历程产生了强烈的恐惧感……他肘部有一个无形的制动闸,在最后的行进中,它把他从行动中拉了回来”(索因卡,1987:328)。这一象征性动作分明表示,画家科拉履行艺术的社会职责时有许多迟疑和无力。尽管科拉“力求洞观一切”(索因卡,1987:368),他仍旧缺乏一股力量,以便把众多的事情一件件抖开,并将它们置于创世之初那种调和的静止之中(索因卡,1987:369)。受失序混乱所困的现代尼日利亚民族需要的正是这股哲学层面的力量。
以上解读显示,五位主人公在各自的阐释中都显得捉襟见肘。无论是谁,他们实事上都在讲述1960年代尼日利亚的同一种困境——一个经历了殖民、尚未完成现代民族整合的共同体的“想象”困境,表现为政治、教育、媒体等社会领域的腐败失序、社会民众的堕落麻木、知识群体的萎靡不振。在这种境遇中,曾经领导民族政治独立的知识分子阶层,正在经历梦想破碎的精神危机,以至对于隐喻民族想象的议题难以达成认同。
2. 无法想象的共同体
《阐释者》出版后两年,尼日利亚政局急转直下,内战骤然爆发,这是地区间和各族群间矛盾分化持续加剧造成的灾难性后果,似乎也是索因卡笔下的阐释者们共同经历并想象的尼日利亚必然要经历的分裂阶段。如果说“民族是想象的共同体”一说如今看来已成为真知灼见,那么对于内战时期的尼日利亚而言,这个共同体的想象是失败的。是什么促使尼日利亚独立6年后陷入了分裂的战争,从而使得一个共同体变得无法想象?其中的原因既有历史根源,又有裹挟其中的政治、文化因素。
尼日利亚作为现代民族国家,是殖民统治的人为产物。就国家版图形成的机制而言,尼日利亚的疆土界限最早来自殖民帝国的征服想象,而对于本土人士而言,共同体想象原本限于各自的部落之内。自19世纪中期西方列强入侵,直到1914年尼日利亚国家版图的确定,该国地理边界形成经历了英国对南、北方的占领、征服及合并过程。此后,英国在尼日利亚的殖民治理采用以“分而治之”、“界而治之”为理论基础的间接统治体系。时任尼日利亚总督弗里德里克·卢加德(Frederic Lugard)以尊重非洲传统习俗为由,发明了一套由中央管理体系与地方管理体系组成的双重统治制度。这一统治术的实施推广以服务帝国利益为目的,并不顾及本土人的真实关切与尼日利亚社会的内在差异,其恶果直接影响了独立后尼日利亚政局的稳定。法洛拉对间接统治导致的民族分裂,作了如下总结:“中央和地方两级政府助推了分裂和种族间的敌视。南方和北方被尽可能地保持分裂……土著管理局培养了种族意识;殖民政府把每个族群都看做是一个独立的共同体……一个族群与另一个族群为福利设施和财政收入展开了竞争”(托因·法洛拉,2015:71)。1960年尼日利亚取得了独立,1963年成立第一共和国,但1965年却垮台了,之后迎来军人执政。但军队作为殖民遗产之一,其政权不仅未能解决种族问题、少数民族问题、地区政治和经济问题。相反,独裁政权所掌握的暴力手段为施行部族大屠杀提供了便利。1966年发生了两次政变,北方城市爆发大屠杀,北部、西部、东部均要求脱离联邦。1967年,内战爆发。
尼日利亚的近现代历史表明,尽管作为多民族国家,其地区文化有内在性差异,但独立后民族国家的一体化进程遭遇危机,重要根源仍在于殖民统治遗留的历史问题。甚至在独立以前,主导民族独立的民族主义者已经变成了地区主义者,只为寻求狭隘的地方利益(托因·法洛拉,2015:87-88)。掌权精英似乎更热衷于“想象”本族人的狭小共同体,故对多民族构成的国家之边界“想象”不够。到1960年代中期,尼日利亚政变突起,即是地区主义和种族主义所致。“事实上,没有多少政治人士热衷于统一的尼日利亚”(托因·法洛拉,2015:101)。种族问题、少数族群不满、腐败和暴力日益严重、政治问题突出等一系列乱象成为索因卡创作《阐释者》的基本历史背景。当萨戈的女友德享娃(Dehinwa)受母亲责备非要找一个“豪萨佬”(索因卡,1987:50)时,南北方之间的矛盾仍像一道鸿沟横亘在这个新近独立的国家实体中。
另外,从殖民主义文化遗产来看,殖民教育培养了非洲的政治精英与知识分子,传播民族主义意识与共同体想象的主导力量有赖于二者。在寻求政治独立时,精英阶层倾向于利用民众的反殖情感,而很少从历史、文化和语言中寻求共鸣,难以与普通大众达成共同体的“同志爱”。独立后,相当一部分西化的非洲知识分子“血管里流淌的已经是欧洲文化的血液”(蒋晖,2016)。非洲对西方文化遗产的继承,最突出地表现为宗主国语言的使用。在欧洲民族主义的起源中,拉丁语作为真理语言的神圣性式微,英语、法语等民族语言及其出版物方能成为现代世俗民族共同体的想象媒介,印刷资本主义创造出一群群单一语言的阅读大众,并成就了英语、法语等方言的地位、权力(本尼迪克特·安德森,2013:46-55)。与此不同,在多语言的尼日利亚,英语作为外来语言,是以其已经牢固树立的殖民霸权姿态出现的。独立后,英语的主导地位非但没有衰弱,反而成为尼日利亚的“国家语言”(Achebe, 1997: 343),作为书写、交流的通用媒介,并使许多部族语言边缘化。
客观而论,英语使原本难以或无法沟通的、不同部族的成员变得能够相互理解,少数通双语的精英能够向各自部族成员传播民族意识。虽然安德森认为现代传媒科技和双语精英能够超越单一语言的限制,传递想象的连带感(sense of solidarity),但在非洲,语言问题的复杂性却远胜于此。就共同体的想象而言,非洲的语言问题不仅在于某种语言能否传递意象,更在于语言作为文化价值载体所携带的政治性造成的权力之争。殖民政权瓦解后,语言成为文化“去殖民化”进程的重大议题,一部分知识精英质疑作为殖民遗产的英语裹挟着西方文化价值,能否成为共同体想象的载体。现代非洲文学的语言在尼日利亚独立后未久便被问题化。相当一部分作家与学者主张,非洲国家的书写语言——即民族想象媒介应为本土语言,因此提出选择一门本土通用语替代英语。这种主张极易被种族主义者和地区主义者所利用,使语言问题带上浓重的政治色彩。而一旦语言问题被政治化为权力因素,那么,它作为政治媒介的功能将大于作为传播手段的功能。这也正是大多数非洲国家,包括尼日利亚,在独立后面临的境况。1962年非洲作家大会引发的、关于语言问题的持续论争显示,用宗主国语言进行文学与民族想象,实则包涵了许多无奈,英语作为国家语言终究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权宜之计。索因卡、阿契贝等英语作家接受殖民遗产,使用宗主国语言进行想象性书写,多数受众却并非本国读者。另外,索因卡对英语的复杂运用和对西方传统中神话意象、写作手法的混用,使得共同体想象的横向关联更为困难,他用隐晦语言传达的意象难以在极有限的本土受众中呼唤共同的想象。奥比阿均瓦·瓦(Obiajunwa Wali)曾指出,能读懂《森林之舞》的尼日利亚读者竟不到百分之一(Wali, 1963: 13-15)。
基于以上思考,本文认为,殖民主义间接统治的分化余毒弥漫在独立后非洲国家的知识空间与艺术创作中。由此,我们回过头来,通过转喻式阅读,审视《阐释者》如何因无处不在的殖民遗产的影响,再现了民族分裂意象,又如何预言性地表述了共同体想象的不可能。此前的分析已论证这部意识流小说在形式上所采用的片段式现代主义风格与民族分裂的隐喻关系。与此相似,作者从社会观察中挖掘的意象——从肮脏的街景到报社业务处长那摆满各国新奇发明的办公室,从报社的“高级厕所”到“低级厕所”,从报社董事长德林诺拉爵士的盛大葬礼到复兴教会使者的惨淡出殡,这一切使社会景象呈现失序破碎的样态。连小偷巴拉巴斯(Barabbas)——即后来的诺亚(Noah)——在行窃后,被同为弱势群体的民众追击,也完全是为了满足暴力的狂热,而非为了唤起正义想象的道德惩罚与教育。借用安德森的表述方式,读者并不能从这些文学意象中确认单一的,并且函盖了小说人物、作者、尼日利亚及非洲读者,并在时空中前进的共同体的坚固的存在。
以五名阐释者为核心的知识分子群体看似一个整体——他们集体接受过西式教育,共同出入于上层社交聚会,定期在酒吧相聚,但事实上,这个阶层内部是分离的。这不仅指阐释者们在基本观念和价值取向上的分歧,而且涵盖更多知识分子在内的集体异化。艾格博的一段哀叹式内省极具代表性,他感觉“人性就像一个废坑里的污水一样”(索因卡,1987:332)。这一情节发生在塞孔尼死后,其余四人共同参加拉撒路皈依诺亚的宗教仪式,驱车离开时,他们在被洪水肆虐的伊布特梅塔海滨迷了路。在极具象征意义的黑暗、混乱、迷失当中,他想起萨戈“痛嗟往日可以向之吐露真情的朋友,如今多已疏远,形同路人”(索因卡,1987:333),于是叩问,“难道他们不是都受到了镀金空想的伤害,受到了害人精的困扰,因而都坠入了同一个离心器?”(索因卡,1987:333)。正如奥比(Obi Maduakor)所言,这些“阐释者们都受到一种压抑的疏离感与无归属感的折磨。他们从各自就职的学术与文职机构疏离,最后与他们自已疏离”(Maduakor, 1986: 88)。
内部分裂趋向集中体现在阐释者们对《众神像》的解读分歧上。画作以科拉周边的现实人物为原型,再现了约鲁巴创世神话。就众神的形象与现实人物的关联而言,这部作品应归于集体创作。但创作者对神话原型及现实人物的选择性理解,常常与小说中现实人物的个体意识,以及其他阐释者对画作的解读相去甚远。
艾格博并不满意自己被画成以嗜血者的“蠢像”出现的奥贡神(Ogun),甚至对这种呈现感到愤怒。显然他并不认为自己代表了奥贡的负面形象。科拉最初欲将诺亚视为叛教者耶稣,即背叛旧教、建立新教的救世耶稣。但诺亚显然无法履行救世的职能,萨戈对这一点有着清醒的认识,他看到诺亚“到了拉撒路手里,就成了一团湿泥巴了”(索因卡,1987:264)。诺亚最后被画成一个没有面孔的家伙,即用石头砸主人后背的背叛者阿屯德(Atunda)。艾格博对此仍不赞同,原因在于,约鲁巴神话的第一位叛教者阿屯德出于嫉妒背叛主神奥里撒-恩拉(Orisa-nla),但与他不同,从小偷转化为新使徒的诺亚无力表达主体意志,这种转化只是拉撒路别有用心的操纵,况且这种转化还是失败的。至于画作的收官之笔,科拉最后选择拉撒路承担伊苏麦尔(Esumare)的角色来完成连接的使命,但这个白化病患者显露的病容却叫人难以忽略。以他的病态与他对权力地位的热望,将难以成为受上帝之命,拯救苍生万物的使者。他救赎窃贼、杀人犯的目的也是为了让他们变成心甘情愿的殉道者,正如被他架上十字架的诺亚并未得到真正的拯救。归根到底,如本德尔所言,他是个“宗教贩子”。
本·奥布姆塞路指出,科拉的问题在于,他未能意识到,模仿现实并非创造性艺术,不朽的神祗是只能在画布上捕捉的、作为创造力的精神。从这个意义上看,《众神像》对现实人物的模仿未能成功再现约鲁巴众神所启示的精神,这部画作的社会功用显然是缺失的。换言之,画面显然隐喻了民族意象与精神,却未能唤起观看者共同的想象。
对阐释者们精神状态与相关意象的分析表明,无论是一个知识分子的共同体、还是一个民族的共同体,在这里都是无法想象的,更难以在小说以外的横向世界中产生民族想象的连带感。当然,对于这样一部内容丰富的作品而言,通过意象分裂预示民族想象失败仅为其中的一个方面。奥拉克昆勒·乔治(Olakunle George, 2008)分析了索因卡作品表征的民族主义本质,他认为索因卡的民族认同倾向于超越界限分明的民族主义(nationalism)与本土主义(nativism),是一种混杂了种族、民族、部族(race,nation,ethnicity)认同的跨国主义(transnationalism)或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因此他的作家身份既是约鲁巴人的,也是尼日利亚人的,更是非洲人的。这种分析是极富洞见的,从这个意义上而言,索因卡对独立后尼日利亚知识分子群体分裂与幻灭的批判,事实上在后殖民语境中表现为更为复杂的逆写尝试与主体性建构,这在其文论思想以及对他的批评中或可见一斑。
3. 后殖民语境中的逆写
与《阐释者》相似,索因卡的多数文学作品语言隐晦,象征意象复杂难以捉摸,常常将本土经验、多种文化中的神话仪式以及西方经典交织融汇。因此,无论是非洲读者还是全球受众,对其作品进行解读都是一件费力的事情。自1960年代至1970年代初,索因卡因语言风格与创作理念的复杂性持续引来批评界的诸多争议与指责。就《阐释者》而言,批评的声音在1973年发生转向,马克·金克赫德-威克斯(Mark Kinkhead-Weekes)详细考察了约鲁巴神话与《奥德赛》在小说中的有机关联与作用,认为此作品具有整体连贯性(Obumselu, 2018: 168-169)。此后对索因卡的批判有所减弱,至20世纪90年代末后殖民理论兴起时,索因卡受到指责的缘由恰成为其获得称许的砝码。后殖民理论认为后殖民作家们通过对语言与文本的重置——如对西方语言、文类、写作技巧与经典文本的挪用与改写,对写作权力的挪用等策略——创造出不同于西方文学的、独特的后殖民文学,以此达到颠覆固有权力概念的目的。将索因卡的文学作品作为后殖民文本阅读,同时考察其在特定社会历史语境中的作用,会发现其在后殖民批评语境中如鱼得水。就《阐释者》而言,无论是其对英语语言,还是对《圣经》故事、意识流的挪用改写都足以产生后殖民理论论证的“逆写”效果。后殖民解读揭示了《阐释者》在初期尼日利亚民族文学与文化建构,或者从更宽泛的意义上说,在非洲文学与文化建构中的积极作用。
那么,《阐释者》如何在无法唤起共同体想象的情况下,仍成为一种民族文化与文学建构的力量,以及索因卡缘何在此后的想象性书写中秉持一贯的创作风格?要回答这些问题,需从学界对索因卡文学的批评话语发生转向的过程进行探究。因为,索因卡本人兼具作家与批评家的角色,其总体的文学实践是在与非洲文学批评话语的动态交互中进行的。这一转向的过程,不仅伴随着非洲现代文学与西方文学之间的话语交锋,同时伴随着非洲本土批评的内部争论,并见证了索因卡创作理念的坚持。
如同大多数非洲“民族国家”一样,非洲现代文学也是殖民主义的产物,本土文学批评形成以前,西方早已攫占先机,将非洲文学纳入批评观察视野。自1950年代末开始变得活跃的非洲文学生产主体,均为殖民教育培养的精英,其文学活动,包括创作、出版、阅读,均受制于西方的赞助体系;西方的非洲文学研究肇始于此,研究者们将非洲英语文学划归于“新英语文学”“英语新文学”和“英联邦文学”的附属范畴(蒋晖,2019:120)。非洲高校(包括伊巴丹大学、拉各斯大学、马凯雷雷大学)英语文学系的文学批评遵循欧洲模式,视非洲作品为西方经典的模仿(比尔·阿希克洛夫特,格瑞斯·格里菲斯,海伦·蒂芬,2014:122)。因此非洲的文学生产整体处于边缘地位,索因卡在其1976年出版的文学批评专著——《神话、仪式与非洲世界》的序中指出,英国某大学迟至1973年,尚不认可存在着“非洲文学这样一个神奇的怪兽”(Soyinka, 1976: vii)。其附庸地位直至今日仍未彻底改变。
与西方批评话语相伴而生的是本土作家与批评家在文学理论上的发展。独立后繁荣的英语文学创作同时鼓励了本土文学批评,但批评主张因意识形态的差异而成众声喧哗之势。发端于1920-30年代的黑人性主义(Negritudism)最早尝试建构现代非洲创作理论,起初以鲜明的黑人种族认同肯定了一种特定的黑非洲本质与心理,但渐渐演化为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甚至种族主义,1950-60年代以后受到诸多本土批评家的诟病。索因卡是黑人性主义的坚实反对者之一,他指出,其结构是抄袭和仿冒的,并没有像它宣称的那样区别于殖民文化类别与特性,反而依赖于殖民文化(转引自比尔·阿希克洛夫特,格瑞斯·格里菲斯,海伦·蒂芬,2014:118)。黑人性运动试图通过实现民族化,乃至种族化达到与欧洲文学的完全隔离,使非洲文学重回僵化的二元对立。
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初,出现了以非洲文化“去殖民化”为目标的、“拒绝创作之文化融合的力量”(比尔·阿希克洛夫特,格瑞斯·格里菲斯,海伦·蒂芬,2014:121),即由钦维祖(Chinweizu)、杰米(Onwuchewka Jemie)和马杜别克(Ihechukwu Madubuike)组成的波勒卡佳批评家和马克思主义左派作家恩古吉·瓦·提安哥(Ngugi Wa Thiong’o)。他们的文学批评对于索因卡文学中的精英文化与西方传统因素颇有微词。恩古吉认为索因卡专注于批判知识分子阶层而忽视工人、农民等普通大众,并寄希望于艺术家来改变独立后腐败的非洲社会现状。在恩古吉看来,塞孔尼由于发电站项目受挫,转向《摔跤者》的雕塑创作,实为知识分子无力参与社会改革的一种退避行为(Thiong’o,1972: 66)。波勒卡佳批评家们则指责索因卡用绕口的英语、晦涩的修辞和外来的意象创造非洲读者难以阅读的作品,实则是对本土文化的背叛(Chinweizu, Jemie & Madubuike, 1975)。他们强调非洲文学自身的传统、模式和规范,拒绝承认殖民主义不可避免地导向文学杂糅化的历史事实,对此索因卡对钦维祖等人批评中的简约化倾向作了有效地反击(索因卡,1987:123)。双方论争甚至持续了整个20世纪70年代。
索因卡与本土各派批评家之间虽然存在激烈论争,但多数批评家的共同认知是,非洲本土文学仍受西方话语的宰制,因此,非洲学界在1970年代开始质疑异己的(alien)批评标准以及内部的异化者(the alienated)对此标准的参照,主张从内部寻找参照点理解自身文化,实现自我接受(Self-appreciation)。而这种对非洲价值与观念的重申很快又招致新殖民主义①就独立后的尼日利亚而言,英国成功地控制了其非殖民化进程,仍掌握着尼日利亚的国家经济权力。殖民因素的影响转化为新殖民主义结构,通过国家政权与跨国公司进行政治、经济、文化渗透。势力的否定,他们从“他们的世界,他们的历史、他们的社会心理(social neurosis)和他们的价值系统”出发,“公然邀请非洲人屈服于第二个殖民化时代”(Soyinka, 1976: x)。
面对这种在新殖民主义语境中被再度他者化的事实,索因卡提出,“为了传达一个种族、一个文化的自我接受,有时候必须从他者的价值观中解放出来,并将这种集体意识与他者的价值观联系起来”(Soyinka, 1976: viii)。基于这种对自我文化的认知以及对新殖民主义政治意图的警惕,索因卡主张非洲作家应创作一种“社会观念”(social vision)文学(Soyinka, 1976: 66)。他认为,文学的功能不仅在于现实经验的反映,更重要的是经验反应的延伸;能够解放作家想象力的意象蕴含在非洲传统神话中。这也是为什么索因卡总是将其现实主义创作诉诸本土神话与仪式的原因。
纵观其创作实践,从戏剧到小说,多以非洲神话为框架揭露现实,以避免对现实的机械摹写。在《阐释者》中,索因卡借助约鲁巴创世神话为参照,讨论尼日利亚独立后的民族国家建构问题,且敏锐地察觉了在此进程中国家肌体结构的脆弱。《众神像》对现实人物的失败模仿,既反应了社会的混乱现实与知识分子的无力担当,也揭示出画家未能将神话意象转化为真正的创造力。如果说,小说中科拉作为艺术家未能达到模仿“功能”的效果,那么索因卡借助约鲁巴神话的真实目的则在于“阐释个人的艺术理念与社会-政治观点”(George,2008: 284),以此实现艺术创作的社会功能。
索因卡对传统的诉求并不与其文学中的现代主义因素相抵牾。从非洲现实政治、社会、文化和文学发展的角度看,非洲现代文学的创作语境极为复杂,而对于使用(前)殖民语言进行书写的非洲作家而言,其创作处境则更为矛盾甚至困难。“去殖民化”大潮中回归传统的呼声、现代性发展浪潮中西方文化的诱惑以及不同思想流派的影响汇成汹涌的洪流,使得像索因卡这样的作家难以就某一个单一价值进行取舍判断,极度的多元性、复杂性必然成为其作品的本质特征。这是艾格博难以在传统与现代之间进行选择的原因;这是塞孔尼在实干经验受挫后转向艺术创作的原因;这是科拉的画布上即有约鲁巴神话又混合着《圣经》元素的原因;这是本德尔在挑明拉撒路是宗教贩子的同时,又承认他把某种意义带入人们的生活的原因;这甚至是年青医生法塞依(Faseiyi)怀揣扎实的专业技能,仍亦步亦趋地寻找异化的伪知识分子上层社会认同的原因;这当然也是索因卡选择混杂意识流、神话意象来表征混乱的社会现实和非洲经验的原因。这为《阐释者》中太多的复杂现象提供了中肯的解释。正如《逆写帝国》的分析所示,在非洲文学杂糅化的语境中,“文学赞助和生产体系的制度化会深刻地改变并决定后殖民环境中所有写作的本质(语言、形式特征和文化效忠的分裂问题)”(比尔·阿希克洛夫特,格瑞斯·格里菲斯,海伦·蒂芬,2014:123)。
独立后的非洲作家处于本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交叉路口”。此时,非洲作家如同译者(interpreters),(比尔·阿希克洛夫特,格瑞斯·格里菲斯,海伦·蒂芬,2014:77)挣扎于“分裂”的困境,不可能在二者之间择其一。索因卡在《阐释者》中探讨的正是这一分裂背景下,阐释者们的“翻译”(阐释)行为。作家本人正是因为繁复的语言运用和对西方经典的肆意征引,成就了他作为“西非的莎士比亚”之声名。如果说他从西方传统中攫取了巨大的创造力,这丝毫不为过。同时也必须承认,这种创造力最终效力于非洲文学与文化的主体性话语建构。
4. 结语
尽管《阐释者》未能成功地召唤想象的共同体,但这部作品和索因卡在非洲及尼日利亚民族文化建构中的重要性与作用是不可否认的。索因卡作为一个具有鲜明的政治与社会关怀的作家,其想象性创作书写从未脱离尼日利亚与非洲的社会母体与传统;其民族斗士的角色从未像有些评论家所怀疑的那样有丝毫不坚定;他致力于建构非洲文学主体性地位所做的努力从未有丝毫懈怠。1970年,尼日利亚内战结束,比夫拉分裂告终,国家重启民族整合计划,尽管此后的社会矛盾与政治危机仍迟迟悬置未决,但民族国家建构的努力一直在进行。而索因卡作为一个激进的社会活动家与文学创作者,其反对腐败与霸权政治、寻求建构“非洲世界”的决心与实践从未停止。或许我们可以在他的许多回忆录中寻找唤起共同体想象的强大意象。而非洲各国的共同体想象如何持续应是当前非洲文学研究值得探讨的重要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