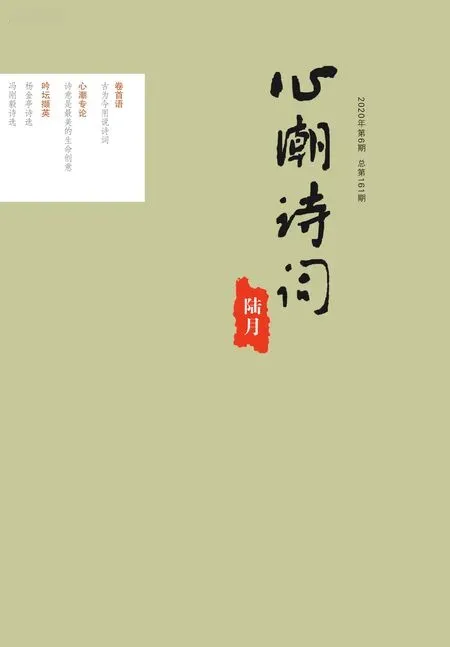同光体:流光何辉赫
2020-11-18
胡迎建(江西省社科院研究员(二级),中华诗词学会副会长,江西省诗词学会会长):清末民初诗坛极为活跃,有汉魏诗派、中晚唐诗派、西昆派、诗界革命派、南社,流派众多,是诗坛繁荣的重要标志。其中影响最大的则为同光体诗派。其领军人物是陈三立、郑孝胥,各人身后又有众多效法者。
同光体的形成与近代张之洞密切相关,正是他,使武汉成为当时著名诗人的舞台。光绪十六年(1890)四月,张之洞就任湖广总督后,创办两湖书院(武汉大学前身),礼聘海内学者名师。张本人也是一位重量级的诗人,时常邀请诗人们在一起唱和。
光绪十七年(1891),著名诗人陈三立来武昌侍其父——时任湖北按察使的陈宝箴。与两湖书院主讲梁鼎芬唱和最多。光绪二十年(1894)冬与次年春,黄遵宪两次赴武昌公事之余,与陈三立切磋诗艺。一个是同光体首领,一个是诗界革命派旗手,两人在武昌声气相求,推心置腹。光绪二十二年(1896),陈三立离开武昌往长沙,助其父湖南巡抚陈宝箴推行新法。
张之洞还先后聘陈衍、沈曾植在两湖书院主持教席,两人同住一院。还邀郑孝胥来办理新政,受命为芦汉铁路南段总办兼办汉口铁路学堂,住在汉口,常渡江而来,与沈曾植、陈衍论诗不倦,相约作诗。有共同爱好与旨趣,激发诗兴,切磋诗艺,热烈的探讨,明确了认识,提出同光体的诗学观,同光体核心层因而形成并举帜扬旗。①胡迎建:《论同光体的形成、特征与时代背景》,《中国文化》,2019年秋季号,第135页。如果不是张之洞,没有文人在武昌的风流际会,也许就没有近代诗史上影响最大的同光体诗派。
当代诗界大多数诗人对同光体不了解,只有少部分学习,并从中悟入,成就较高。我个人认为,同光体一是让人知道,学诗须重门径,着重学哪几家;二是求奇求变,求厚重,避流滑,避俗避熟,对当代创作尤有借鉴意义;三是由于时代近,他们的典范作品值得今人学习,钻研。
关于同光体诗派,有许多说不完的话题,特别是同光体与当代诗词创作有何关系,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今特邀请八位专家、学者诗人就这一话题作谈谈各自的见解。
马卫中(苏州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近代文学学会副会长):同光体是离我们时代最近的古典主义诗歌流派。钱仲联先生《论同光体》的结语谈到:“同光体诗的艺术,对我们今天怎样做到诗是精炼的语言方面,还是可以借鉴的。”可以陈三立为例稍加阐述。
陈衍《石遗室诗话》讨论同光体代表诗人的创作特点,说是“散原奇字,乙庵益以僻典”。刘禺生《世载堂杂忆》所言,可视作注脚:“陈散老作诗,有换字秘本。新诗作成,必取秘本中相等相似之字,择其合格最新颖者,评量而出之,故其诗多有他家未发之言。”他自称在陈三立处亲见,“如‘骑’字下,缕列‘驾’‘乘’等字类”。所以,过去褒贬陈三立诗,多与用字之奇相关。其《园居看微雪》有“冻压千街静,愁明万象前”一联,郑逸梅《艺林散叶》说“王蘧常于同光体中,极推陈散原用字之新奇,如‘冻压千街静’,此‘压’字为人意想不到”。而《石遗室诗话》则记述了易顺鼎所见闻:“伯严(陈三立字)在武昌,重九日张文襄(张之洞)招同登高,伯严有诗,末二句云:‘作健逢辰领元老,夕阳城郭万鸦沈。’元老自指文襄,文襄批驳‘领’字,谓何以反见领于伯严也?”对此,陈三立“笑文襄说诗之固”,谓“领元老岂吾领之哉”?这正是用字之奇才让读者解诗有不同的答案。
陈三立用字之奇,继承了江西诗派“夺胎换骨”法。惠洪《冷斋夜话》引黄庭坚语云:“诗意无穷而人之才有限,以有限之才追无穷之意,虽渊明、少陵不得工也。然不易其意而造其语,谓之换骨法;窥入其意而形容之,谓之夺胎法。”也有人对此不以为然。宋代魏泰《临汉隐居诗话》便说:“黄庭坚作诗得名,好用南朝人语,专求古人未使之事,又一二奇字,缀葺而成诗。自以为工,其实所见之癖也。”陈三立作为维新派的重要人物,在戊戌以后的处境使其诗表达情志比较隐晦曲折,用字之奇也有这方面的考量。不过,陈三立并未畏缩,其《漫题豫章四贤像搨本》咏陶渊明有“想见咏荆轲,了了漉巾影”句,钱仲联《论同光体》据此以为陈三立“把江西诗派的渊源,上推到陶渊明。特别强调陶诗于平淡中郁风雷之声的特点,诗作与政治紧密结合的特点”。而《石遗室诗话》也谓:“散原为诗,不肯作一习见语……盖其恶俗恶熟者至矣。少时学昌黎、学山谷,后则直逼薛浪语……然其佳处,可以泣鬼神、诉真宰者,未尝不在文从字顺中也。”
钟振振(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导,中华诗词学会原副会长,现为顾问):“同光体”对当下的诗词创作有没有作用?当然有,但不可能有太大的作用。因为当代绝大多数诗词作者不知道“同光体”为何物。既不知,“同光体”还能对他们起什么作用呢?退一步说,即便他们知道“同光体”为何物,也学不来的。因为“同光体”崇尚宋诗。宋诗与唐诗,特别是盛唐诗,最大的不同在于盛唐诗重在“气象”,而宋诗重在讲学问,讲气象,似乎没什么学问也不打紧,有胸襟即可;而要讲学问则光有胸襟是不够的,还得有“腹笥”,肚子里要有文史类古籍的万卷书。当代诗词作者读过三五百首古典诗词,就很不错了。许多人只热衷于“写”,却不怎么读古典诗词的,更别说“读书破万卷”了。不读书,或读书不多,便知道“同光体”为何物,又怎样?它只是鲁智深那六十二斤重的浑铁禅杖,看得使不得。
现在有些诗友很推崇并很努力地学作“同光体”诗,尽管人数不太多。可见,“同光体”对当下的诗词创作也还是有些作用的。他们的作品我读过一些,确有学问好,诗也写得好的。当然也有欠火候,写得吃力的。但不要紧,有勇气去耍鲁智深那六十二斤重的浑铁禅杖就好,谁能一下子便舞得像风扇一般?总要有个操练的过程。比起“同光体”来,笔者更喜欢它的老师——宋诗。但我也不反对那些诗友从“同光体”入手,只希望他们不要以“同光体”为止境,为终极目标。此外,笔者还想说,诗坛亦如歌坛,无论什么“体”,都不过只是一个流派而已,不好说“美声唱法”一定就比“通俗唱法”高贵,唱得好不好才是最重要的。唱得好,永远是硬道理。要之,笔者主张当代诗人应多读书。南宋严羽《沧浪诗话》说:“夫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然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学“同光体”最大的好处是逼自己多读书。对于精力充沛的年轻诗人来说,严羽这段充满辩证法的论述应全面领会并付诸实践。至于年纪较大、去日苦多的诗人,我们只能用严羽的前半段话去鼓励他们:书读得不多,就在“别材”二字上下功夫吧。十八般兵器样样都会固然是好,但一根少林棍耍熟了也能打遍天下!
曹辛华(上海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大学中华诗词创作研究院院长):同光体诗风在晚清民国尤为风行。由于新中国成立后诸多诗坛耆宿凋零以及新诗、新文学的强势等影响,同光体诗风在一定时期内处于被贬斥状态。随着上世纪80年代传统文学、文化的日复苏,旧体诗写作日益流行,时至今日更是蔚为大观。当前人们对同光体研究的成果较多,胡迎建先生《同光体诗派研究》尤显功力。于此,本人欲就同光体诗风在当代如何扬弃问题来谈下,以有益于优秀传统文化的良性发展与继承。
对同光体诗风的较早揭示者为易宗夔。其《新世说·文学》云:“若同光体诗人,出入南北宋,郑苏龛、陈伯潜、陈伯严、沈子培,为其宗之魁杰。其中又分二派:一派清苍幽峭,体会渊微,思精笔炼。苏龛、伯潜优为之;一派生涩奥衍,语必惊人,字忌习见。伯严、子培优为之。范肯堂、林畏庐、陈石遗、李拔可,皆此宗之健者。至罗瘿公、黄秋岳、梁仲异、夏剑丞,则后起之秀也。”此处将同光体分为两派,并将各派诗风指明。今观其为诗追求,其中“生涩奥衍”“字忌习见”二者当为我们避免者。虽然当时同光体诗人这种诗风是为了规避流易直白的诗风。但一旦运用修辞过度、过于精巧、以学问为诗,就会导致读者的阅读障碍。以前的读诗环境是文言文占主流的,其读者与作者素养基本对等。这就要求当前为诗词者弄清楚读者的品味与需求。如果写诗为一己之娱乐,有以学问为诗、以文字为诗的爱好不妨。倘若要让当代更多读者理解与接受,此二者当力避。同光体所追求的“思精笔炼”“语必惊人”诗风在当代应大力发扬。当前诗家众多,总体观之,合格中式者多,但能以“思精笔炼”“语必惊人”创作者少。笔者以为,如果当代诗人都能以同光体诗派这一精神来要求自己,就不会出现劣作、平庸之作泛滥的情形。同光体所强调的“思精笔炼”“语必惊人”实际上也是对杜甫“语不惊人死不休”“晚节渐于诗律细”等诗学主张的继承。
张煜(上海外国语大学副教授,博士):同光体诗派是晚清民国最大的一个古典诗歌流派,也是中国古典诗学在封建时代名副其实的大结局,但其实对于我们当今的诗词创作,仍然有着很多的借鉴意义。首先,文学是人学,同光体诗人中,不乏人格高尚者。如江西义宁陈三立,吴宓《读散原精舍诗笔记》称“先生一家三世,宓夙敬佩,尊之为中国近世之模范人家。……先生父子秉清纯之门风,学问识解,惟取其上。而无锦衣纨袴之习。……故义宁陈氏一门,实握世运之枢轴,含时代之消息,而为中国文化与学术道教所托命者也”。此种对于人伦纲纪的笃实坚守,形之于立身处世,发而为至情至性,正是陈三立诗作品格高洁的文化底蕴。
其次,同光体主张才情与学问相济。陈衍《近代诗钞》开篇即云“学人诗人之诗二而一之”。这方面最具代表的当然是嘉兴沈曾植。他提出“谢文靖之‘訏谟定命,远犹辰告’,所谓‘雅人深致’者,为诗家第一义谛;而车骑所称‘昔我往矣,杨柳依依’者,为胜义谛。”才情与学问,两者没有优劣之分,是同等的重要。只有两者相结合,既有文学形象,又有思想内涵,写出来的才是一首好诗。他觉得己作之所以高于湖湘派的王闿运,正是因为诗中有玄理,而不仅仅是“缘情绮靡”。
最后,同光体一些诗作既忧时伤世,在诗歌意象的承继上,也绵延今古。我想举闽派陈宝琛诗为例。《感春四首》:“一春谁道是芳时?未及飞红已暗悲。雨甚犹思吹笛验,风来始悔树旛迟。蜂衙撩乱声无准,鸟使逡巡事可知。输却玉尘三万斛,天公不语对枯棋。”(其一)此诗作于1895年甲午战败、《马关条约》签订之时。又如《次韵逊敏斋主人落花四首》,作于1919年,其三云:“生灭元知色是空,可堪倾国付东风。唤醒绮梦憎啼鸟,罥入情丝奈网虫。雨里罗衾寒不耐,春阑金缕曲初终。返生香岂人间有,除奏通明问碧翁。”其四云:“流水前溪去不留,余香骀荡碧池头。燕衔鱼唼能相厚,泥污苔遮各有由。委蜕大难求净土,伤心最是近高楼。庇根枝叶从来重,长夏阴成且小休。”写得典雅精工,怨而不怒。诗人笔下的落花,不仅仅是寄寓对时局的感慨,也可以说是对于中国古典文化花果飘零的一曲无尽的挽歌。
龚喜平(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流行于清末民初的同光体是古典诗歌向现代新诗流变与转型时期具有重要地位和影响的诗人群体和创作流派,其代表作家达数十人之多,又因个人风格的差异和地域风貌的不同而细分为赣派、闽派和浙派。深入探讨同光体的特点、成就及局限,既有助于深化近代诗歌的学术研究,亦有益于当今旧体诗词的创作实践。现代白话新诗已经走过了一百年的历程,与新诗蓬勃发展的同时,旧体诗词依然受到人们的喜爱并拥有众多的读者和作者。反思当年同光体的历史经验和时代局限,或许对当今的旧体诗创作有所启示。在内容题材层面,同光体虽不乏时代特色鲜明、现实内容厚重的诗人诗作,但整体而言较之南社等同时代的诗派又似有不足,这就启示我们今天的旧诗写作在内容题材上力求丰富性和多样化的同时,亦当重视诗作内容的时代性和现实感。在风格基调层面,同光体作为清代宋诗运动的最后阶段,倡导“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合”,虽“不墨守盛唐”但尤重宋诗,注重学问学识,诚然不免偏颇,但亦说明学问学识对旧体诗创作的作用。当今旧诗写作在充分发挥才情灵感的同时,亦须重学识理趣,以期兼取唐宋诗之长而为今天的旧体诗写作助力,情韵与理趣兼胜,诗情和哲思并存。在艺术技巧层面,同光体诗人普遍重视写作技巧的探索和诗歌意境的创新,虽然难免因刻意求新而导致了生涩险怪的弊端,但也积累了一定的艺术经验和创作教训,或正或反,都可为今天的旧体诗词写作提供借鉴,启示今人充分重视旧诗的写作技巧,努力提高旧诗创作的艺术水平。
张寅彭(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国家社科重大项目《清诗话全编》主持人):陈衍溯源“同光体”诗派的产生,一般比较耳熟能详的是他所揭示的道光以来程恩泽、祁寯藻、郑珍、曾国藩倡导的宗宋“变风”。但实际上他心目中的上限还不止此,他又曾说过:“有清一代诗宗杜韩者,嘉道以前推一钱萚石。”而“程春海侍郎几欲方驾萚石斋”,可惜“天不假年,而由子尹与道州从而光大之”,这样就前推到乾隆时期了。我最近为《萚石斋诗集》的整理出版写了一篇四万字长序,详论了钱载“以文为诗”的质实诗风,他与袁枚一起,全面扭转了清诗前半期由王渔洋主导的“神韵”诗风,彻底摆脱了与明诗的藕断丝连,清诗的自家风格至此才算真正树立。也就是说,乾隆以后直至清末,钱载、郑珍直至“同光体”的质实诗风,成为清诗的主流,故陈衍这一论述是极具清诗全史的眼识的。
但还不止此。在《石遗室诗话》中,陈衍还有一个更大的论述,最终也归结于同光体。由于弯子绕得比较远,则一般不易被觉察。我指的是他在诗话中,曾就梅圣俞名言“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所发的高论:“宛陵此四句,前二句实难于后二句。”“前二句惟老杜能之,东坡则有能有不能。后二句阮、陶能之,韦、孟、柳则有能有不能。至能兼此四语者,殆惟有《三百篇》。汉魏以下则须易一字,曰:状‘易’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乍读之下,口气似大而怪。《三百篇》以下的一部诗史,被分出对象的“难写”与“易写”,表达的“尽”与“不尽”;而推慕“难写”尚在情理之中,贬损“不尽”则令人大跌眼镜矣。他在此也是有针对性的抑王渔洋,批评《沧浪诗话》及托名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等为“渔洋所表章者”的趣味,而为“同光体”诗人张目。这就把清诗及“同光体”推而及于汉魏以下的全部诗史了。如此一来,以“质实”为主要特征,以“同光体”为结穴的清诗,理所当然在唐宋诗之后,成为中国传统诗史的又一个当之无愧的高峰。这才是陈石遗关于“同光体”诗派的完全定位,而揆诸清诗的实际,也是站得住脚的。
赵家晨(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博士):上世纪三十年代,陈衍在《近代诗钞》卷首标举“学人之言与诗人之言合”,倡导诗歌熔铸学问、性情、襟抱于一,并标举祁寯藻诗为典范,作为诗坛学诗宗旨。其实同光体与道咸之际的宋诗运动主将们所标举的“学问”内涵迥异:在程恩泽、祁寯藻、郑珍、莫友芝、何绍基等主张汉宋调和者眼中,诗中容纳经史名物制度考据才能称为“学人诗”;而同光体诗人除沈曾植精通考据外,大部分诗人对朴学并不精深,陈衍所标举的学问乃是关于“朝章国故治乱贤不肖,以至山川风土草木鸟兽虫鱼”,恰如钱锺书所云乃是“诗人之学”。然作为变风变雅之作,同光体诗人标举诗中融入真性情、讲求炼字锻句与宋诗运动主将提出的“真诗”“不俗”论趣旨是一脉相承的。
在同光体内部,针对“学人之诗”问题,沈曾植和陈衍分别提出“三关说”“三元说”。前者从传统学术理路论述诗中所蕴含的学问,试图和融元嘉之玄言与元和之佛禅和元祐之天理,再揉进本朝之考据,接续的是道咸宋诗派一路;后者则以开元盛唐诗之格律典范、元和韩孟诗派之奇崛、诡谲调剂元祐宋诗纯粹“重理趣”之单调,以诗人之视域走以宋调为主、唐音调剂宋调之融合道路。
清末民初之际,西学东渐风潮大盛,国人对中国传统知识的划分有了重新认识,四库之学转变为七科之学。随着现当代学术分科制度的确立以及大学教育的普及,陈衍开拓的“诗人之学”为主要内核的“学人诗”对民国诗坛影响巨大。诸多大学教授跟随同光体领袖学诗,他们将擅长的专业学识融进诗作,不再关乎经史,不以考据、阐发义理为作诗目的,而是在现代学科范围内将诗歌与现代学术紧密结合在一起,形成“教授诗”,开创“学人之诗”的另一范式。
房舫(诗人,金陵诗社、哈军工北京校友诗社社员)同光体诗歌在沉寂七八十年后再次以“八风恣搴扬”的姿态受到不少诗词爱好者的大力追捧,是由其“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合一”的独特魅力决定的,是有识之士面对诗坛乱象的正确选择。
当前诗词流水线上的“产品”多如牛毛却乏善可陈,许多作者腹笥贫乏、毫无风骨。清人批判的“不讲格律,不贵学问,空疏易于效颦”的现象愈演愈烈,长此以往,非为昌诗,实乃亡诗。在此背景下,师法“炼字奇警,句法新奇”的同光之路才是振衰起敝的不二法门。以陈三立、郑孝胥、陈洐、沈曾植为代表的同光体诗人都是科举时代的王者和“鱼龙光怪百千吞”的饱学之士,正如当代刘士林所言:“同光体诗歌中,学者的‘才、学、识’与诗人的‘审美直观’第一次得到相当完美的融合。”有人批评同光体诗爱用“冷僻故实”,认为若无相当深厚抑或驳杂的文史功底做基础,字面含义都难读懂,更遑论窥其堂奥,其实这是理解上的一种障碍,不能怪古人的典故难懂,只能怪自己读书太少。古人的“必修课”四书五经若干史,凡是读书人势必熟悉,用了其中的典,怎么算是冷僻隐晦?
后人文史知识有限,见了古人视若平常的典故不懂,反而抱怨古人用典生僻,这是反历史的思想方法。白居易诗当时号称“老妪能解”,但他家的老妪何尝不是“郑玄家婢”之流亚?试问当代老妪,《长恨歌》第一句“汉皇重色思倾国”的“倾国”为何意,几人能知?我们总不能要求当代的白居易们再次降低艺术标准以“徒博下愚无知之人一日之称誉”(郑孝胥语)吧!
此外,诗人之间的交谊、相互砥砺,也是同光体诗派发扬光大的重要原因之一。胡迎建先生的《同光体诗派研究》堪称是一部同光体诗人的友谊史,即使其中郑孝胥、陈洐晚年交恶,也不掩其整体上文人相重的光芒。海量的诸如“秋半有怀凭海客,太虚明月近谁圆”“不觉肺肝生白露,空怜河汉失流晖”“觥觥群彦集京国,万口诗伯交相推”之类的名句正是在他们惺惺相惜的交游中产生的,这对于文人相轻、山头林立的当代诗坛无疑具有榜样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