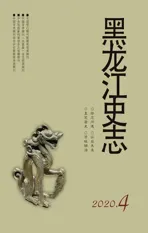辽代宁江州城考
2020-11-17王东峰
王东峰
(大庆市直机关工委 黑龙江 大庆 163000)
疫情期间读《松漠纪闻》,发现一个叫冷山的地名,著者洪皓在这里住了十年,据他讲“冷山去宁江州百七十里”,这是考证冷山的一条重要线索。考冷山必先考宁江州,于是又读了李健才先生《辽代宁江州考》,刘少江先生《伯都讷古城考》,很受启发。
宁江州的价值有两点,一方面它是金太祖完颜阿骨打首战之地,记录了一个王朝的起点;另一方面,它又是找到相关地名的一把钥匙。
李健才先生是研究东北史的前辈,1983 年出版了《辽代宁江州考》,从此宁江州城在松原伯都讷古城的结论被广泛接受。2016 年,刘少江先生在考证后提出了异议,他认为宁江州城不在伯都讷古城,而在扶余市三井子镇四道门古城,文章论据充分,有说服力。
在李健才、刘少江考证的基础上,笔者想说一点自己的看法。
史料中关于宁江州的词条不算少,可信度高低有别,区分一下是有必要的。《许亢宗行程录》《松漠纪闻》多是宋人许亢宗、洪皓出使金国亲身经历、亲眼所见写出来的,两人都是高官,又是文人,官品和文才广受好评,宋史对洪皓评价尤高,所以相对来说他们写的东西更可靠一些。《辽史》《金史》取材于《实录》,真实性自不必说,是写史的主要依靠,但史官不见得事事都去详究,难免有年代上系统考虑不周的问题,何况跟亲历者的第一手材料相比也差了一层。至于《契丹国志》《大金国志》之类,大都取自杂史、逸闻或笔记,用来参考、补证、互证可以,作为支撑证据来引用,慎重一些比较妥当。
关于宁江州城,笔者觉得在六个方面是比较清楚的 :
一、宁江州在界壕以西
《金史·太祖本纪》: “……将至辽界,先使宗幹督士卒夷堑。”
《许亢宗行程录》第三十六程:“自合里间寨东行五里,即有溃堰断堑,自北而南,莫知远近,界隔甚明,乃契丹昔与女真两国古界也。”
大连大学王禹浪先生认为,合里间寨在扶余市大三家子乡半拉子古城。许亢宗和洪皓出使金国间隔五年,在扶余段记载大体相当,这段路程与今天京哈线几乎重叠,可称千年古道,王禹浪先生说的应该可信。那么按许亢宗的记载,契丹与女真界壕当在大三家子乡附近。许亢宗当时是路过,只看出南北走向,有多长不知道。实际上前面第一条《太祖本纪》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阿骨打在去宁江州途中填过界壕,它就在起兵地以西。阿骨打起兵是在扶余德胜镇石碑崴子,那里有大金得胜陀颂碑为证。可见界壕从大三家子乡向北一直延伸到石碑崴子,而且以经验看,它不会就此止步,还要继续一路往北,直抵东流松花江南岸才到尽头。从大三家子乡往南也是同样的道理,直到西流松花江北岸 为止。
边界划分是大事,要遵循一定的原则,从地图上看,拉林河的走向和位置,决定了契丹与女真的分界只能大体平行于拉林河,如果往东偏,界壕无法途径石碑崴子;如果向西偏,等于多给了女真一方土地,契丹作为一个大国不会答应。
契丹与女真的界壕在两个松花江之间,大体南北走向偏往西北。
按这个分界,宁江州属于契丹人,一定在界壕以西,而在界壕以东处在女真地的古城都应被排除,包括曾经呼声很高的扶余石头城子古城、榆树沟王家屯古城。
二、宁江州靠近女真地
《辽史·地理志二》记载,宁江州“清宁中置”。清宁是道宗第一个年号,他是辽代倒数第二个皇帝,此前女真已经有过多次犯边的记录,宁江州的设置,就是为了防御女真。
《辽史·道宗本纪二》载,咸雍七年三月“以讨五国功,加知黄龙府事蒲延、怀化军节度使高元纪为上将军……宁江州防御使大荣为静江军节度使”。咸雍也是道宗年号,此时已是宁江置州13 年以后的事了,因何去征讨五国部?一定是对女真屡次寇边的报复,否则不必动用那么大的力量,府、节度州、防御州的兵力悉数上阵。同时也能看出宁江州与黄龙府、宾州之间必定存在着某种渊源(怀化军驻宾州),下文要专门说到这个问题。另外更重要的一点是,宁江州参与了此次征讨,它在三个府州中行政级别最低,军制级别也最低,显然充当了马前卒的角色,这是宁江州靠近女真地的又一力证。
伯都讷古城地处两个松花江东南夹角的位置,距石碑崴子有八九十公里远,宁江州既是为防御女真而置,如此远的距离很难起到防御作用。
三、宁江州在混同江北
史料中混同江的记载比较混乱,从辽太宗改粟末水为混同江之后,到道宗、天祚两朝,西流松花江至少在扶余以西的下游江段称混同江。
李健才、刘少江相继引用了《辽史》第98 卷中的一句话,“清宁四年,置鸭子、混同二水间”。笔者仔细看了两遍,书中并没有交代此城的名称,可能是通过清宁四年来推断的,当然有可能是宁江州,但不好说它一定就是。《辽史·地理志二》说宁江州下辖一县,名混同。混同县,从名称上看,是县以水名,应该离混同江不远,但也未必一定在江北。
刘少江先生在文中引用两条记载,一条来自《三朝北盟会编》,一条来自《契丹国志》,大体都是说“女真地在混同江以北,宁江州以东”。两部史书虽非正史,由于可以互证,所以比较可信。
“混同江以北,宁江州以东”,这句话很值得玩味。混同江大体可视为东西流向,说在混同江以北,本身已经包含了宁江州,否则逻辑上说不通。从另一方面看,宾州在混同江南岸(下文提及),离女真地不远,宾州以西还有长春州,两个州都是节度,比宁江州的观察高一个等级,规模、名声更大,说在宾州或长春州以东似乎更为适当。之所以不这样说,只能理解成宁江州所处位置更利于辨别女真方位,而这个位置只有一种可能,就是位于混同江以北,离女真地更近。
实际上还有一点可证,就是反过来看,宁江州如果不在混同江以北,防范女真的价值就小了,置州也失去了意义。
四、宁江州离宾州近
宁江州和长春州兵事同属于东北统军司,李健才先生认为这是两州相近的证据。但是《辽史》地理志一、二同时还提到了一点,宁江州和宾州同属于东京道,而长春州却隶属上京道,这点与兵事隶属看起来是矛盾的。实际上行政隶属关系比兵事隶属关系更能体现出距离和方位,而军事隶属不见得一定按区域统辖,在某些特殊时期,打破区域界限有利于统一指挥,快速反应。宁江州处在防御女真第一线,兵事归东北统军司直管,只是反映了它军事地位的特殊性。
进一步从道一级行政区划看,长春州隶属治在巴林左旗的上京道,宾州、宁江州隶属治在辽阳的东京道,这一定是从区位上划分的。
宾州治在混同江南岸,洪皓《松漠纪闻》“契丹自宾州、混同江北八十里建寨以守,予尝自宾州涉江过其寨”,即可证明。它的具体位置,李健才先生认为在农安靠山镇西北的混同江南岸,许亢宗当年也曾路过这里,且提到了宾州,应该是可靠的。
长春州治向来争议很大,一说在松原前郭塔虎城,一说在白城德顺城四家子古城。白城2013 年出土过一块铭文方砖,上面刻有“长春县”几个字,但由于方砖出处存疑,所以目前还不能定论。《辽史·地理志一》载,长春州“统县一,长春县,本混同江地”。这个“本”字令人费解。本来、原来都是“本”的词意,如果按“本来”理解,长春县应该在混同江流域,城四家子古城远在德顺的洮儿河,就不大可能;如果按“原来”理解,意味着长春县是从别处迁移而来,这样城四家子古城的可能性就增大了。在没有定论的情况下,长春州治的位置,可以姑且看成在查干湖一带。
宾州在农安靠山镇,长春州在查干湖,因为长春州偏西,宾州偏东,所以它们划为不同的两道管辖。宁江州和宾州一样隶属东京道,如果它不处在偏东的位置而是偏西,这种划分就无法解释。这样看来,宁江州与宾州的距离,无疑要比长春州更近。
五、首战南下
李健才先生认为,阿骨打起兵是往西走的,依据是往西要路过夹津沟,这条河沟正好与《金史·太祖本纪》中提到的扎只水相合,所以得出在伯都讷古城的结论。
阿骨打起兵是以弱对强,心里不会有多大底数,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历史上造反成功的人都是这么过来的。所以首战阿骨打一定慎之又慎,最优选择是捡近处打,一出便是八九十公里,路程太远了不说,南面还有混同江边的宾州,不能不担心被抄后路。据《太祖本纪》,起兵前契丹已经探到了风声,军事上有所准备,这点阿骨打是清楚的。另外从距离上看,混同江以北诸城,伯都讷古城离石碑崴子肯定是最远的,不打近而打远,道理上解释不通。
西去不成,阿骨打就只有南下一条路了。
六、宁江州规模中下等
《辽史·地理志二》载“宁江州,观察……初防御,后升”。在辽代,州分五个等级,宁江州初建时只是防御,接近于中等州,州城规模应该比排在前两位的节度、观察要小。
据大连大学东北史研究中心一篇文章的统计,在嫩江流域的138 座辽金古城中,周长5 公里以上的3 座,4—5 公里的2 座,2—4 公里的12 座,1—2 公里的36 座,1 公里以下的85 座。可惜的是,文章没有对古城所对应的军政建制作出分析。
依照这个统计及行政区划的平衡,粗略区分一下,大概是周长4 公里以上的5 座属于节度州,2—4 公里的12 座属于节度以下诸州,1—2 公里的36座可能是县。考虑到宁江州作为边城,离战争最近,存废无常,不见得一定按正常州制建城,周长可能在2—4 公里之间,也可能小于2 公里。
文章对每座古城的形制都有记录,归纳一下,周长2 公里以下的绝大多数只有一个城门,2 公里左右的至多两个城门,四城门只出现在四五公里的大城中。角楼几为标配,连周长三四百米的小城都有,瓮城也很普遍。但护城河无规律可循,如前郭周长2040 米的哈朋店、2140 米的土城子没有护城河,而洮南569 米的海城子则是护城河,角楼、马面、瓮门诸样齐备。由此可以看出,除了周长以外,城门数也可作为衡量州城规模的尺子。
宁江州有东城门,《金史·太祖本纪》里面讲了,是不是还有西城门,从边城军事功能的角度考虑,有的可能性更大。按东西两个城门算,加上前面的统计和分析,宁江州城应该在周长2 公里左右。
综合以上六个方面,宁江州城的位置可以锁定在扶余境内,具体为大三家子乡以西,五家站以北,三井子镇、弓棚子镇以南,以新万发镇为中心的区域内,重点勘察周长2 公里左右的古城遗址。但是从考证本身来说,这个范围有些过大,能不能把它限定在更小的区域或某一个点上?
洪皓说“契丹自宾州、混同江以北八十里建寨以守,予尝自宾州涉江过其寨,守御已废,所存者,数十家耳” 。我曾怀疑这里所说的寨就是宁江州城,但洪皓何以没有提及,按宋金使者往来的成例,洪皓进了金国国境,会有接伴使全程陪同,宁江州是大金国的起点,倍感荣耀,不可能无人向洪皓讲起。
《松漠纪闻》是洪皓回到南宋被秦桧贬官赋闲养老时写的,其时已六十多岁,如果是由于身体原因记不起来,书中却又两次提到宁江州,而且描述比较细致,所以绝不可能是无心的疏漏。
许亢宗在《行程录》中提到了宾州、益州,却没有提及分量更重的宁江州,说明宁江州并不在驿路上,这也间接印证了洪皓所说的寨不可能是宁江州城。
《松漠纪闻》对于宁江州的描述是这样的:“宁江州去冷山百七十里,地苦寒,多草木。如桃李之类,皆成园,至八月,则倒置地中,封土数尺,覆其枝干,季春出之。厚培其根,否则冻死。”我一直疑惑桃李怎么能倒置地中,这段话其实是不准确的。我问了扶余新万发镇的人,他说不是桃李而是葡萄,到了冬季,须把葡萄的枝条深埋地下,根部也要培土防冻,这样来年才能早熟。洪皓是江西上饶人,上饶不产葡萄,他应该不太了解,所以闹了张冠李戴的笑话。据这个人讲,现在在新万发镇一带,种桃李和葡萄的农户很多,这与洪皓的记载吻合,不排除乃为世代相因而来。
《许亢宗行程录》曾提到,从大三家子乡往东北“行终日无寸木,地不产泉”。据说那一带属风沙区,即便今天依然如此,但是从大三家子乡往西到新万发镇,这种情况发生变化,绿色逐渐多了起来。
最后的结论 : 宁江州城在五家站镇—新万发镇—三井子镇一线,具体在新万发镇附近,可能略微偏东。
宁江州从建城伊始到现在961 年,不敢说一定还有遗迹可寻,历史上像宋太宗毁太原城、隋文帝毁邺城这样的例子不少。州城地处两个松花江之间,战略位置重要,从辽末到清末七八百年,这里免不了杀伐征战,更有被洪水漫灌的可能,很难说会像其他古城那样留给我们一些残墙碎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