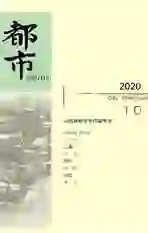眼角的亮光
2020-10-30秦海智
秦海智
最后一节网课还有十多分钟就下课了,母亲打来电话说药引子准备好了,让我往牛场走。我在QQ上通知了舍友小A,让他签退的时候通知我,便将电脑扣住,开始洗漱穿戴。
今年的春天格外冷,加上刚刚下过雨路上坑坑洼洼不说还满是泥泞。说来也奇怪,我由于流鼻血找村里的赤脚医生看了一下,医生居然要我喝中药。而且药引很是奇怪,需要还在哺乳期的男婴的尿和他母亲的奶水。
走在路上不少人跟我打招呼,當然我知道这一切都是源于父亲。父亲前些年办了个养殖场,专门养牛。牛场里面现在有一百多头牛,用句比较得意的话说父亲现在也算得上是养牛大户了。不过有很多人打招呼难免有些尴尬。好在妹妹及时给我发了条微信让我有些事做。
妹妹给我发了三张照片,照片中,一只小牛犊卧在地上,它腰间系着的一条白布很是显眼。
从爷爷家到牛场的路说长也不长,没用多少工夫就到了。推开门,我直接坐在沙发上,将手中一味我也不知道是什么的药扔在茶几上,跟母亲说:“医生让把这个药在砂锅上炒黑,泡好药后,把那个尿和奶滴在药里面,再滴上一点儿酒。”
母亲拿起茶几上的药,放在鼻子前闻了好一会儿,说道:“这个引子好奇怪啊。”
“谁晓得呢,反正医生说这是个经验方子,叫什么引火归原,喝了以后肯定不会再流鼻血了,我看到他是从一个小本子上抄下来的,应该有用吧。”
“行,我给你先炒,炒完泡上过一会儿喝。”
突然,母亲把脑袋凑在我脸旁边,把我吓了一跳。我以为母亲又闻到了我身上的烟味,心中顿时就不安起来,心想又免不了一顿唠叨。
母亲看着我,两只胳膊环抱在胸前,“你不去看看那牛犊?可真是个好牛犊。”
见母亲没说烟味,我心中放松了不少。跷起二郎腿,跷着的那条腿胡乱摇着,我看着手机,“有啥好看的,不就是个牛犊?”
母亲听到我的话,直接揪着我的耳朵把我拉起来,“看去,这一家老的少的辛辛苦苦不就是为了你,这牛场迟早要给你接手的,连个牛犊都不愿看,成啥了?”
迫于母亲的压力和耳朵的疼痛,我走到卧室拉起妹妹往牛圈里走去。
牛场里一共有三个大棚,还有一大片场地用来供牛活动,只不过那片场地现在都被牛粪所覆盖。大棚旁边有几十块白色小圆台一样的东西,是豆腐渣,是给产后的母牛吃的。通过大棚再往里面走,有三间窑洞,以前是场里的工人住着的,后来整个场子都翻新了一下,工人们重新有了住的地方,三间土窑洞便成了牛的产房。
窑洞前挂有重重的门帘,为了防风。掀起门帘,泛黄的灯光将窑洞照亮。母牛卧在地上,前蹄曲在肚子下,鼻子里“哼哧哼哧”地发出声响,牛犊卧在母牛旁边,静静地看着自己的母亲。母牛伸出它粗大的舌头在牛犊脑袋上时不时舔一下,牛犊似乎很享受这种感觉,时不时也伸出舌头舔一下母牛,两头牛很是和谐。
我看着妹妹,“这牛犊多少斤?”
“这牛犊大得厉害呢,八十斤呢。喂牛的那两个人说。”
“八十斤!”
“你以为呢,要不然往下生它这么麻烦呢,比养了一个月的牛犊都大。”
妹妹这话着实把我惊了一下,我走到牛犊面前,伸手想在牛犊脑袋上摸一下,却又怕母牛顶我一角,一只手停在了空中。看着母牛的眼神没有什么恶意,我慢慢地把手挪向牛犊的脑袋,它突然脑袋一转,没有让我摸到,这让我很是尴尬。
我也不敢强行上去摸它,不知为何,我天生就对动物很是害怕。看了好一会儿后,便觉得无聊,回到了母亲住的屋子。
我换上拖鞋,盘腿坐在沙发上,母亲端着一大一小两个碗走到我面前,“我刚刚打电话问了那个医生,你这孩子,自己的事也多少不上心,医生说还有捣碎了的阿胶说是让你用开水冲开,先喝了阿胶再喝那碗药,好在我问了下,你真是。”
我讪讪地笑了下,“忘了和你说了。”
“牛犊看了吧?这牛犊好吧?”
我喝着冲开的阿胶道:“不错,就是腰上的白布是干啥用的?”
“那不是因为它舔自己的脐带舔得流血了。”
我拿起那碗药,想着掺杂着尿、奶和酒,心中难免恶心,我看着母亲,“这喝了会不会有化学反应,我真怕自己喝死。”
“赶紧喝吧。我睡一会儿,昨晚两点多生的,我一直忙活到生完,牛犊站起来。”
“我爸呢,他没上手?”
“就他?靠他的话,这牛场里的牛早死干净了,你看我这日子过得,我一个妇道人家,天天在牛圈里,鞋底上都是牛粪……”
“牛生麒麟,猪生象,我还以为这两三天生不下是准备给我生个麒麟哪。”这时父亲笑呵呵地走了进来,“这日子怎么了,天天和牛玩还不行?”
母亲白了父亲一眼,“反正昨晚是我在后面看着,你后生是在床上睡了,打呼打得房顶都快塌下来了。”
“那还是没塌下来呀,有你就行了,我去能咋,我又没生过孩子。”
“来,儿,你岁数也不小了,你听听你爸那话,明天开始我也不管了。”
“行,不管,雇下喂牛的就是让他们干活呢,你自己不会享受,现在怪我?”
“儿,你听听你爸这话。”
父亲走到母亲旁边,拍了母亲肩膀:“老刘做几个菜去,我和咱儿子喝一点。”
“没菜。”母亲抖了下肩膀,看着我说道:“老大,你想吃啥?”
父亲抢先说道:“随便做几个菜就行了。”
母亲白了父亲一眼:“我问我儿子呢,你是我儿子?”
“妈,妈。”妹妹人还没到,声音就传到了屋子里,推门进来看着我们说道:“赶紧进去看看母牛吧,屁股上晓不得吊着个啥,看着挺吓人的。”
母亲站起来,往门外走去,“是牛衣吧。”
我看了眼父亲,“你不去看看?”
“有你妈就行了。”
这时妹妹看着父亲,脸上笑意越来越重,“那次家里进来老鼠,妈妈让爸爸去抓,爸爸在床上睡着,一下用被子把脑袋盖住了,死活不去,还是妈妈用钳子把老鼠夹住的。”
父亲脸上露着笑容,手在妹妹面前虚晃了两下,“再说小心打你。赶紧去帮你妈去吧。”
我看着父亲,“那你干吗?”
“我给你们叫人,让那个刘国庆上来看看。”
窑洞内,母亲站在窑洞最里面,泛黄的灯光照在她的脸上,脸上眉头皱成一团,原本就有点黄的脸上此刻不知是灯光还是什么的缘故更加黄了。母亲手拿着手机,蹲在母牛的屁股处,时不时抓起母牛粗壮的尾巴,看看屁股。
“怎么样了?”
“這谁能知道呀,国庆来了没?”
“应该快了。”
母亲指着妹妹说道:“慧慧,赶紧去把那两个喂牛的老头叫过来,出了这么大的事,他们人在哪里?”说完母亲又蹲在母牛旁边。
我两步走过去,想着能帮些什么。母亲把母牛尾巴抓起来,一个猩红的肉块登时出现在我面前,只这么一眼就把我惊住了。小牛犊在旁边“哞哞”地叫着,母牛鼻子里依旧“哼哧哼哧”的,自打我这次进来后,母牛便不再舔小牛犊了,小牛犊在母牛脑袋上蹭着,母牛硕大的脑袋仿佛定格住了,只有鼻子不停地发出“哼哧哼哧”的出气声。
很快一个白头发高个老头和两个身形矮小的老头进来了。
母亲两步走过去,把白发老头拽到母牛屁股处,抓起牛尾巴,“国庆你看看,这是啥,是不是牛衣?”
刘国庆嘴里嘬着烟,拍了拍两只手,便向母牛屁股上的那块肉抓去。良久后,把烟头扔在地上,踩灭说道:“怕不是牛衣,是不是胎盘?”
“不知道啊,是不是还有个牛犊,上次,有个双胞胎出生时,也是这么一团,后来把那块肉撕开里面是个牛犊。”
“应该不是,是牛犊早下来了,这么长时间了,这个牛犊是昨晚两点生下的,现在下午六点了,不可能。”
“不是啊,怕还是个牛犊的话,闷死了怎么办。”
“晓不得啊,这个牛肚子还好大啊,有可能是。”一个喂牛的老头说道。
刘国庆又点了一根烟,嘬了一口说道:“老杜看了没,他说是啥?”
母亲站起来,长出了口气,“老杜说没事啊,把他给的草药吃上就行了。”
“牛犊吃奶了没,先说牛犊吧。”
“今天吃了两口,没奶水啊,你看奶头子干成啥了。”喂牛老头说道。
“没奶水,你先把牛犊抱过去,不是有个母牛前几天生了,让过去吃上点那个母牛的。”刘国庆站起来说道。
只见喂牛的老头两步走到牛犊面前,一把将牛犊抱了起来,牛犊四条腿不知是卧得太久还是没吃奶的缘故,腿竟然展不开,刚抱起来就跌倒了。
“轻点啊。”我淡淡地说了句。
“这少东家说话了,牛犊子你多少给点面子啊。”说着那老头上手帮牛犊把腿展开,从屁股后推着它往另一间窑洞走去。
母亲时不时拿手指戳一下母牛屁股上的红色肉块,然后看看国庆,“你说它一直哼哧是怎么了?感冒了,还是牛衣下不来疼?”
刘国庆蹲在地上,左手将烟屁股放到嘴边嘬了一口后说道:“我感觉是疼了,你应该晓得婆姨们生完孩子后的那个疙瘩疼,我认为和疙瘩疼一样。”
母牛鼻子依旧哼哧不停,突然母亲喊道:“国庆你看,又出来一道。”我顺着母亲指的方向看去是一条很长的暗红色带子。
刘国庆上手将那条红色带子抓在手中,摊开手看了好一会,“牛衣吧,这是。”
“要不让人掏一下牛衣,让它好受一点?”
“行,掏一下,要是还有只牛犊就真赚了。”
母亲看着我,“你赶紧跑过去让你爸给兽医站那个常振国打个电话,让赶紧下来。”
闻言,我急忙往屋子里跑。推门进去,发现父亲低着头坐在沙发上,夹着烟的一只手在没有几根头发的脑袋上拍着。父亲许是听到开门声,抬起了头,看着我,“没事吧?”
父亲本来就很黑的面庞上没有一点表情,我急忙说道:“我妈让赶紧给兽医站的常振国打电话,说让下来掏一下牛衣。”
父亲将烟叼在嘴上,开始打电话,只听到他说:“我,国雄,你赶紧来我牛场里一下,我让人接你去,有啥事了啊,用不了多少工夫,真的,我,你也晓得,几年了你见我什么时候求过人了,给个面子,我准备了几瓶子‘三十年,赶紧。”接着又打了个电话,“去兽医站接上常振国下来喝酒,两瓶子‘三十年啊。嗯,快点啊。”
听着父亲打电话的声音,我推开门走到了院子里。天已经完全黑了下来,月亮并不怎么亮,旁边有几颗星星若有若无地点缀在月亮旁边。夜间的风有点冷,我长出了口气,往那间窑洞里面走去,途经大棚发现牛已经进圈了。我走到去年生的双胞胎跟前蹲下。小双胞胎已经长得很是健壮,其中一个从栅栏下伸出脑袋,我将一片干草叶子送到他脑袋旁边,只见它舌头一卷吃了下去。
“真好。”我摸了摸它的脑袋,说完后往窑洞里走去。
母牛“哼哧”声越来越重,仔细一看,还是在不停地发抖。我将手放在它的身上,发现它抖得就像拖拉机一样。我将手放在它脑袋上,心中暗暗说道:没事的,肯定没事的。
“你爸打电话了没?”
“打了,应该快了,牛犊吃奶了没?”
母亲叹了口气,“唉,不吃啊,把它推到奶头跟前都不嘬。”
我摸着母牛的脑袋,感受着它鼻子里哼出来的气,听着它的“哼哧”声说道:“不是它妈,肯定不吃。”
刘国庆和两个喂牛的老头交谈了起来,母亲依旧看着母牛屁股。大概过了二十多分钟,一个三十岁左右的男子掀起门帘走了进来。
只见他从兜里摸出一副塑胶手套戴上,几步走到母牛屁股处看了看,“让这头牛站起来掏吧。”
他一说完,窑洞里的几个人立刻动了起来。母亲嘴里吆喝着,两只手在母牛头旁边不停地上来下去。
“不行啊,要不就这样掏吧。”母亲看着那人说道。
“这样怎么掏?把牛赶起来。”
两个喂牛的老头拿了两根竹条走了进来,“起,赶紧起。”母牛依旧不动,只有一颗硕大的脑袋上下动一下,两个老头拿着竹条一下下地抽着母牛。小牛犊颤颤巍巍地站了起来抬起脑袋,用它的小嘴尖尖地叫着。小牛犊摇摇晃晃地走到母牛旁边卧下,伸出舌头舔了一下母牛,然后“哞哞”地叫着。老头手里的竹条不停,打了几下后,一个走到门口拿起了一个铁环套在母牛鼻子上,另一个将牛犊抱到门口,“你妈现在病了,得给你妈看病,你让它起来就不打它了。”
牛犊趁人不注意,又走到母牛身后。一个喂牛老头一只手拽着鼻环,一条腿弯曲,另一条腿在地上蹬直,一直手朝着门口那边,另一个老头拿着竹条一下下抽着,母亲嘴里“呦呵”着,牛犊“哞哞”地叫着,母牛脑袋横着,朝着门口挪动。泛黄的光照在每个人脸上,拽着鼻环的老头动作一改,双腿蹬地,双手拽着鼻环,我分明看到母牛硕大的眼睛正盯着我。
“要不别掏了。”我淡淡地说了句就走出了窑洞。
回到屋里,烟灰缸里的烟屁股数量着实把我吓了一跳。父亲倚在沙发上,手上夹着的烟,烟灰都有半截烟长了。父亲闭着眼问道:“怎么样了?”
“人来了,牛不站起来。”
“哦。”父亲夹着的烟不堪重负,烟灰掉了下来,在他的裤子上形成了一个小圆柱。
“爸,烟灰。”
父亲睁开眼看了一下,将烟头在烟灰缸里戳灭,又点燃了一根,放到了嘴边,“山峰和慧慧去你爷爷家做了几个菜,一会就回来了。”说着起身拍了拍烟灰,往门外走去。
“你干吗去?”
“我去看看那头牛。”
“不怕了?”
“怕又能怎么办。”
屋子里的烟味很重,我从烟盒里抽出一根烟,抓起一个打火机往厕所里走去。身上的牛粪味、厕所的臭味,都随着“嘀嗒”一声,让我嘬入了嘴里。一口烟入肺,掺杂着许多心事从口中吐了出去。许是我心事很重,嘬了三四口,一支烟就抽完了。
我再次掀起门帘走进窑洞里面时,父亲远远地站在门口看着里面。整个窑洞静得出奇,只有母牛“哼哧”的声音。常振国正在掏牛衣。一条胳膊从牛屁股里伸进去,过一会儿手上多了一些血色丝带,然后甩在地上。一个老头在牛前面拽着鼻环,母牛越抖越厉害了,不过站起之后,屁股上的那块肉也不见了。常振国手上有时候掏出来一些透明的东西,如同透明塑料布一样。
我踮着脚尽量不发出声音,走到母亲跟前,发现母亲眼角有一点亮光闪过,小声问道:“怎么站起来的?”
母亲揉了下眼睛,脑袋靠在我的肩上,声音很是微弱,“硬生生打起来的。”
我实在看不下去了,转身回到了屋子里。再次从烟盒中抽出一根烟点燃,一连抽了两根后,我突然干呕了起来,眼中有些泪水出现,眼睛生疼。我急忙摁灭烟头,袖子在眼上擦个不停。
这时,父亲的声音在门外响起,我心中咯噔一下。只见父亲身后跟了好几个人,常振国进了屋子说:“不敢掏了,牛抖得太厉害了,我怕这牛是不行了,一直是只出气,气还都是凉的。”
父亲坐下脸上笑嘻嘻道:“本来就是急病乱投医,没事。”
常振国抽了口烟说道:“有温度计没,我量一下体温。”
“有,听诊器要不。”母亲一边说,一边在柜子里翻找着,拿出来递给了常振国后两人又走出门外。
“狗屁,一直出气早死了,什么本事没有,瞎说,是吧儿子?”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转身走到卧室扑在床上。可一闭眼,满脑子都是母牛的那双眼睛。
“给我拿过来一盒烟。”
我从床上跳了下去,走出卧室,父亲呆呆地坐在沙发上抽着烟。见我把烟扔在桌子上,父亲将咬着的烟屁股吐在地上,拆开烟盒又点了一根叼在嘴上。
我和父亲一人坐在一个沙发上,一句话不说。良久后,母亲他们回来了。
父亲嘴角动了动,看着常振国。
常振国将听诊器扔在沙发上,“不行了这牛,脱水脱得厉害了,我刚刚听了下心跳,第一次九十多,第二次一百多,体温才三十七度二,我打电话给我的朋友,他们都说这牛危险了。”
“脱水是要补水啊,有病就治,反正这头牛看你了,不管怎么样都不怪你,脱水,不行的话输液?”父亲咬着烟说道,烟从他的嘴边不停地往上飘,让人很难看清他的表情。
“是怕拿药也来不及呢,这太危险了。”
“这样,你往路上走,我给山峰打电话,让他路上接你,快点的话二十分钟打个电话应该能行。酒的话咱把牛安顿好再喝。”
说着父亲掏出了电话朝着卧室里面走了过去,常振国转身走向门外。母亲两只手放在脸上,发出吸鼻子的声音,“国庆,你认为这牛怎么样。”
刘国庆左手夹着烟,“我感觉没他说得那么厉害,不懂牛,咱们对比人,我感觉是像婆姨们生完孩子一样疙瘩疼呢,脱水,今天就饮了不少了,红糖水,还有老杜開的药。”
母亲拍了下茶几,“对,我感觉那人本身就不行,我刚刚看到他在那儿查东西了,还问东问西的。我给老杜打个电话,问问。”
接着母亲掏出电话,把牛的状况和老杜说了一下,显然这个电话让母亲放松了不少。
“老杜说没事,把地米和林可打上,再拿上二百克黄芪拌在他给的药里,再打上五支肾上腺素就行了,我就说,那个常振国屁用不顶。”
刘国庆接过话柄,“就是,和人一样呀,肯定是疙瘩疼呢,不过我认为还有点感冒了,地米、林可咱们这儿有,黄芪……”
父亲从里屋出来,摁着我,“我去医院拿,二十分钟打个来回没问题。”
母亲瞪了父亲一眼,“你那是飞呢?外面黑成啥了,慢点,牛成了那个样,你不要再……”
父亲双手从我肩膀上抬起,“说的那是啥话,牛怎么了,牛没事,赶紧打那些针去吧,我十来分钟就回来了。”
在父亲的大嗓门下,几个人相继走出了房门,空荡荡的房间里只剩下我一个人了。我屏着呼吸,两根手指从烟盒中夹出一支烟放在嘴上。我打开水龙头,一根手指放在水柱上好让水流发出更大的声音,“嘀嗒”一声,打火机亮起,点燃了我嘴里的烟。一根烟灭了,又续上一根,连着两根吸入肺中,我又干呕了起来。
推门出去,几颗星星点缀在漆黑的幕布上,我低着头往大棚里走去。刚一进去便看到喂牛的老头一只手拽着鼻环,另一只手拽着一根铁柱子,一颗白头在牛嘴旁边,母亲背对着他们。我慢慢走过去,看到国庆左手拽着牛舌头,右手中指在牛舌头上反复摩擦着。突然,国庆眉头一皱,取下嘴上叼着的针头,对着牛舌头上的一根黑黑的血管一样的东西扎了下去。
“我就说嘛,这牛肯定感冒了。”说着,他伸出一根中指把牛舌头上冒出来的血抹开,“你们看,这血都是黑的。”
母亲转过身来,“老刘,还是你厉害,这要不你去兽医站怎么样?”
“老头了,看不上,比那常振国强吧,哈哈。”
“笑啥呢?”父亲本来就有点胖,现在双手端着一个绿盆,宛如熊二捧着蜂蜜罐很是滑稽。
刘国庆接过绿盆,“能笑啥了,这牛和我想的一样,来,把喂药了。”说着就拿起盆里的调羹,将盆子里稠稠的深褐色药汤给牛嘴里放。
父亲看了两眼后转身走出了大棚,我紧跟着父亲回到家里,坐在沙发上。父亲径直走向里屋,踩着一个板凳从衣柜顶上取下了一个黑色的塑料袋摆在茶几上。父亲皱着眉头从黑塑料袋取出一沓黄纸和几捆香。
“拿上个打火机跟我来。”
出了屋子,只见父亲在牛圈外面跪了下来,将黄纸整理好,“打火机。”
父亲接过打火机点燃黄纸,嘴里小声说着一些“顺顺利利,平平安安”的话语。说完之后父亲磕了三个头站了起来,“磕上个头。”
等我磕完头,父亲又往大门口去了,这次我没有跟过去,提前回屋里等着他。
没多久,父亲和母亲前后脚进来了。
父亲边往沙发上坐边说,“刚刚山峰打电话说常振国不下来了,一路上说两万的牛成四千了,他回了兽医站说他老婆打电话让他回家。”
母亲往厨房里走去,“常振国,我看是怕糟蹋了他的名声了,屁本事没有,在那儿查东西了,这兽医我也能当。”
父亲点着一根烟,“做饭去吧,慧慧今晚肯定就在她爷爷家睡,都没吃饭,煮上几块方便面吧。”
母亲摆弄着电磁炉,“我不吃,你们看你们是吃多少。”
“煮上两块,再煮上点菜叶子、鸡蛋,我再去看看牛。”
说着父亲便转身出去了,我紧紧跟在父亲后面。夜深了,风不是很大,却很凉。许是受了父亲的影响,我心中竟然也默念着:“临兵斗者皆阵列前行。世间有正气,杂然赋流形。”
掀起厚厚的门帘,泛黄的灯光照在这一对牛母子身上。母牛卧在地上,鼻子里依旧哼哧个不停,小牛犊缩成一团靠在母牛身边。
父亲走到母牛旁边,慢慢地伸出手摸了下牛角很快又缩了回来。接着又慢慢伸出手放在母牛脖子处抚摸,“没事,别哼哧,真没事,我在这儿,你能有什么事,你看这医生一个个给你找,都是救你来了,没事啊,听话。你看啊,每次出事我眼皮都跳了,这次我都没有跳,肯定没事。不要哼了,知道你难受了啊,你看这药刚吃了,发挥作用也要一会儿,不要哼了。你不信别人你还不信老杜,老杜都说没事你肯定没事。不要哼了,听话。你再哼我可就火了啊,就不管你啦。没事,都说你没事啊,听话,不要哼了。”
看着父亲的样子,我心中默默地念道:佛祖,上帝,玉皇大帝,只要谁能让这个牛没事,我以后就信哪个。
许是父亲的话,或是我的祈祷起作用了,母牛颤颤巍巍地站了起来。一只前蹄似乎无处安放,朝左朝右胡乱迈着。
“没事吧,我就说嘛,我眼皮都没跳。回吧,吃饭。”
“真没事了,爸?”
“能有啥事,站都站起来了。”
回到屋子里,父亲一进门就喊着:“没事了,站起来了,自己站起来的。”
母亲一只手托着下巴,“我就说没事吧,那常振国真是。”
听着两人的话,我胡乱扒拉了两口便不吃了,走进里屋将自己扔在了床上。许是心累了一天,没多久就睡着了。
我再醒来是被母亲杂乱的话语吵醒的。母亲慌乱地说着,“老杜,昨晚还好好的,吃了药还自己站了起来,你看要不再来一趟?牛现在侧躺着一直用牛角在地上磕,看得我怕死了。”
听了母亲的话,我立刻翻了个身下床,胡乱将脚踏在拖鞋里,便往窑洞里跑。
快到窑洞的时候我看到穿着军绿色棉袄的父亲用袖子在眼角蹭了一下。
“没事吧。”
“不顶事了,这事终于算过去了,以前是牛伺候人,现在,人伺候牛还……”
听着父亲的胡话,我没有搭理他,径直走到窑洞里。一个喂牛的老头抱着脑袋坐在门口放着的一只桶上,另一个老头蹲在母牛旁边。整个窑洞里面静得出奇,我踮着脚走到母牛旁边。母牛果真如同母亲说的一般侧躺着,四条腿如同木棍一般直直的。母牛眼眶旁边还有一些没有干的泪水,牛嘴旁边的地上还有許多白沫。
整个窑洞很是压抑,我没待多久就回到了屋子里。
“老杜,我早上看的时候,母牛侧躺着,四只蹄子来回蹬,牛头在地上一下下磕。”父亲说着,两只手在空中比画着。
茶几上的手机传出一个中年男人的声音,“疼死的,活活疼死的,你们知道撕心裂肺这个词吧,就和那个词一样。掏牛衣掏坏了,本来牛犊大,生下就疼,还伸进胳膊掏牛衣。掏牛衣当场死了的也不少,掏坏了,你们看这么好的牛没了,七十二小时内就不能掏。”
父亲挂了电话,头低着,马上就能塞在裤裆里面。许是脖子累了,父亲慢慢地抬起了头,看了眼旁边的母亲,“咱们自己杀了卤牛肉吧,现在卖也卖不了多少,卖个四五千,还不如自己杀了送人,老子通人情,可就不止四五千的了。”
母亲环抱胳膊,低着头,时不时用右手在脸上抹一下,她叹了口气,“唉,自来了咱们家……别的不说,要吃你自己吃去。”
父亲又点起了一根烟,我努了努嘴,“爸,要不咱埋了它吧。”
父亲将烟戳进了烟灰缸,“你懂个屁,人情世故屁都晓不得,少瞎说。”
说完父亲就开门往外面走了,应该是去处理那头牛了。
我抬头看了看母亲,“自己家的牛,自己杀了吃,我真……妈,我看见那头牛眼角里有泪,就像哭来着。”
“肯定哭了,这生下来就注定以后是啥了,咱这下辈子还不知道转个啥胎,说的只养不杀,你看这……”
母亲的右手依旧在脸上一下下抹着,屋子里很闷,也很安静。终于,她眼角的泪似乎流干了,开始给自认为是领导的人打电话,说一些邀请他们第二天来吃正宗牛肉的话。
责任编辑杨睿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