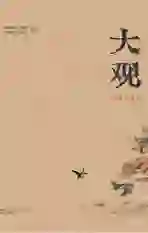新媒体时代中国绘画展示与传播方式的新策略
2020-10-20代晓蕾崔强
代晓蕾 崔强
摘 要:在中华文明几千年的发展进程中,绘画图像与社会信息的传播息息相关,图像传播是古代社会信息传播的重要类型之一。绘画作品在信息传播中具有独特的直观性和形象性,是传达中国传统文化和精神内涵的重要信息载体,而美术展览会是绘画作品进行展示、欣赏、交流的重要方式。在信息发达的新媒体时代,探索适应社会文化现实语境的绘画作品展示与传播方式势在必行。
关键词:新媒体;中国绘画;传播方式;展览模式
注:本文系河北省社科基金项目“新媒体艺术发展条件下中国绘画展示方式研究”(HB17YS039);河北省第二批青年拔尖人才资助项目阶段性成果。
传统的中国绘画展示与传播在很长的一段历史发展过程中,都局限于小范围的传统知识分子阶层之间的人际传播模式。20世纪初,西方的美术展览会得以引入中国并推广,这种公开化、社会化、规模化的作品展示与交流的形式改变了中国绘画作品在传统意义上的欣赏与品鉴方式,并逐渐成为中国绘画作品实体性展示与传播的主要方式。在信息发达的新媒体时代,全新的艺术展示创意和技术手段为中国绘画作品展示注入现代的艺术观念,也给观者带来了新的视觉感受形式和艺术作品的传播交流、感知模式,将我国绘画作品的展示与传播推向了一个全新的高度。
一、展示与传播方式的新视角
2019年9月至12月,苏州博物馆举办的特展“画屏:传统与未来”,以全方位、多角度的形式对屏风这一独特的艺术媒介进行了展示,为中国绘画作品的展示与传播方式的创新提供了诸多的可借鉴之处。
(一)多重角色的展示与传播媒介
屏风既是中国传统建筑空间中起隔断作用的一种结构因素,是作为家具的实物,又是一种绘画媒材,是最古老的绘画形制之一,更是中国绘画艺术中备受青睐的一种绘画图像。特展以严谨科学的学术理论依据为支撑,将各种与屏风相关的实物和艺术品进行了有机组合,呈现了不同时期的画屏和以屏入画的传统绘画作品,展示了一批与画屏形式或观念有关的当代艺术作品。展览为古代和当代的中国艺术搭建了桥梁,促成两者间的深层对话,是一场高水平的学术型展览,其展示与传播的理念、方式、成效更是值得分析研究和借鉴。
(二)新颖的策划角度和切入点
展览从屏与礼仪空间、物的画屏、屏风入画三个角度还原了艺术作品以外的场景,将绘画与社会生活、文化习俗联系起来,展示了中国传统文化与艺术中的屏风,直观而立体地描绘了画屏从生活走向艺术又回归生活的轨迹,向观者立体全面地展示了屏风的多重角色以及屏风绘画的多个主题,具有非常直观强烈的传播作用。通过屏风这个媒介使大众从一个新的角度把建筑、器具、绘画放在一起来讨论研究,从而传播中国传统文化、古代生活、古代美学。以屏风为契机将当代艺术家以屏风为元素所创作的作品进行展示,让观者体会到传统文化元素在现代乃至未来艺术中的延续。
二、构建全新的展览模式,促成传统与未来的多重对话
此次展览尝试用一种新的方式研究传统的延续和继承问题,以屏风为契机,创造一个传统与未来对话的平台。
(一)多元化:作为实物、绘画媒材和绘画图像的画屏
丰富而多元的展品为观者提供了一个层层叠进的多重视角,全方位地展示了屏风的多重身份。展览中作为物的屏风,包括战国错金银铜虎噬鹿屏风座、东魏武定元年的翟门生围屏石床、繁峙南关村金代壁画等考古材料,以及清宫所藏的各式挂屏、插屏,充分强调了屏风从最初就具有多样的功能、设计与物质性。在临展厅中清乾隆剔红围屏、宝座与东魏武定元年的翟门生围屏石床相对而立。前者置于朝堂之上,使处于屏风环绕之中的人物成为引领观者视线的焦点。屏风在这种礼仪中,为统治者构造了一个与国家政治结构相契合的象征性空间。后者作为独特的葬具形制埋藏于地下,其基本的功能也是分隔空间。而展品中清宫的各式挂屏当属紫檀木边嵌牙骨珐琅大吉葫芦春屏彩胜的工艺最为复杂,且其材质多样,并以具有吉祥寓意的图案为装饰。这件挂屏展示了屏风在发展过程中的另一种含义,即具有短暂时效性与节庆内涵的装饰品。
在当代艺术厅中,艺术家展望将关注点进一步投向了对屏风多元形制与物质性的探索。他的作品《山水镜》和《不锈钢木家具》在保留原本木质穿衣镜框架的基础上,用不锈钢山石替换了镜面。这种立式穿衣镜在某种程度上与屏风的分隔空间功能有着相似之处,特殊材质的不锈钢既赋予了穿衣镜一种雕塑的立体感,同时又形成了独特的绘画感,周围环境作为一种元素入画、入屏,而又与镜像有所不同。
(二)画中幻象:从古代绘画空间到现代艺术中的画屏
画屏作为中国绘画中的一种重要意象,被不同时代的画家充分运用来构造图画中的空间,叙事性地表现人物之间的关系,屏风本身的内涵与本质被不断深化和丰富。
《重屏会棋图》是最具代表性的“重屏”作品,也是本次展览的一大亮点。画面中,对弈男性背后的床榻上有一扇立屏,屏中描绘了侍女备榻的场景,床后另有一榻,而榻后立有一扇山水折屏。画屏入画、屏中有屏的层叠设计将多重空间不断递进地呈现在观众眼前。唐寅的《临韩熙载夜宴图》在基本保留原作的构图和人物形象的基础上,将画面顺序做了调整,增加了屏风数量,室内空间的装饰也替换成了明代流行的设计,并融入了明代的审美意趣,画家在画面中制造了一个新的视觉游戏。画中的屏风,既界定了绘画空间与情节片段,也模糊了室内与室外的界限。
当代艺术中,新媒体表现形式为幻象的营造提供了进一步的可能。杨福东创作的《善恶的彼岸·第一章》和《明日早朝》,以多屏影像裝置为媒介,呈现于忠王府楠木厅三个独立的建筑空间中,流动的影像画面与特设的古典壁纸相映成趣,从视觉到听觉,从古代建筑空间到当代艺术表现,为观者呈现出了来自不同时空中的文化、历史和艺术的摩擦与碰撞,制造了多重幻境。屏幕上的花卉纹样与唐寅《临韩熙载夜宴图》中各类纹样,屏内的古装场景与《重屏会棋图》发生了多重联系与对话,而电子荧屏从某种意义上来看,成为了当代的新式立屏。
(三)寻寻觅觅:在遮挡与显露之间若影若现
屏风本身造成了一种在遮挡与显露之间若影若现的寻觅,在明清时期的戏曲版画与小说插图中,屏风时常带有一定的“窥视”。展览中所展出的陈洪绶绘《西厢记》第十出“玉台窥简”,表现了崔莺莺阅读张生来信的场景。画家采用了正面的视角,将人物和屏风作为插图中的两个图像,一块折屏分隔了前景中读信的崔莺莺和屏风后偷窥其读信的红娘。作为观众,我们无法得知信中内容,反而是屏风上的装饰象征性地暗示了一些无法言传的信息,四折花鸟屏风的右侧双蝶纷飞,象征了浪漫的爱情。屏风自身的形态在其流传过程中逐渐改变或消失,而被赋予了新的生命,书画展厅正中央的三幅题为《雍正妃行乐图》的立轴便是说明了这一点。这三幅立轴是从一架十二折围屏上拆下,后被重新装裱成立轴的。作品表现出了屏风所传递的信息:在展品其中的一幅上的美人端坐桌前,手持书籍,其身后的屏风上是雍正的歌咏美人的亲笔提诗。通过这种隐晦的形式,雍正得与画中的美人进行对话。
三、画屏特展中展示与传播方式的创新价值
特展从实物的屏风、图像的屏风、文献中的屏风等多个维度,全方位、多角度地发掘、研究、欣赏画屏,建立了古代和当代艺术的多重对话,建构艺术展览中的一个新型展示模式,引入一个新的角度来阐述和理解当代艺术,呈现中国艺术传统的连续性以及中国本土艺术传统的持续的活力。同时,将精心选择的一批与画屏有着密切关系的作品和艺术家,系统地展示给公众,深刻清晰地揭示了画屏在中国传统文化和艺术发展中的关键作用,呈现了其跨越书画、建筑和器物的综合性能,从一个更加全面丰富的角度传播了屏风这一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媒介。画屏特展立足当下,回顾传统,面向未来,有效地向大众、向世界传播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髓。
参考文献:
[1]巫鸿.重屏·中国绘画中的媒材与再现[M].文丹,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
[2]李喆,何依萍.奇妙的屏中世界:苏州博物馆“画屏:传统与未来”特展概述[J].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9(3).
[3]朱亮亮.“展示”与“传播”:民国时期美术展览会研究之新视角探析[J].艺术百家,2013(6).
[4]张莉岚.广州艺术博物院书画展览传播效果研究[D].广州大学,2019.
作者簡介:
代晓蕾,衡水学院美术学院讲师。研究方向:美术学。
崔强,河北师范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美术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