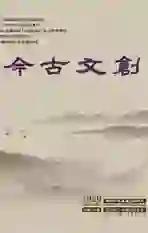《莳萝泡菜》中薇拉的逃离
2020-09-10郭冬林
郭冬林
【摘要】短篇小说《莳萝泡菜》由一对昔日恋人的对话和回忆构成。通过文本细读和话语分析发现,对话中女主人公薇拉在权力关系中处于明显弱势,主要体现在薇拉频繁被男人打断,主要承担倾听者的角色而没有话语权,其声音被男人视为审美对象加以凝视。薇拉的权力弱势象征着社会结构层面女性的弱势地位。在男权社会中,女性的主体性受到压抑,掌握话语权的男性将女性对自由的渴望定义为自私,要求女性牺牲自我,无私为男性奉献。拥有独立意识的薇拉不愿接受规训,主动离开以男主人公为代表的男性,以此抵抗和逃离不公平的性别结构。
【关键词】话语;女性;权力弱势;性别结构;逃离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0)36-0011-03
一、导言
凯瑟琳·曼斯菲尔德的短篇小说《莳萝泡菜》讲述了一对昔日恋人在分手六年后偶然相逢、短暂交谈又再度分开的故事。小说叙事方式独特,内容含蓄深刻。女性主义的解读中,认为作者对女性视角的运用展示了女性生存经验 (张闻琦,2009),或分析女主人公薇拉觉醒的女性意识(牛雪莲,2015),而不少研究试图对此进行解构,认为文本自相矛盾,未达到讽刺男性人物的创作目的 (曾霞,2010),或认为作者意图双轨反讽,通过隐性叙事暗示薇拉的自我中心主义(申丹,2019)。也有学者曾通过会话分析,指出男人与薇拉在关系中的地位差别(姚晓东,2013)。现存研究富有启发性,却也存在诉诸道德谴责、忽略关键细节和过分解读等问题,不够有说服力。本文运用话语分析的方法,聚焦语言使用,分析主人公之间的权力关系,阐释结构性的性别不平等,以便说明故事最后薇拉再次离开的原因。
二、薇拉的权力弱势
小说讲述了一个无情节故事,由对话和回忆构成,但对话双方权力地位并不平等,相对男人,薇拉处于权力弱势。语言不只是中立或透明的交流工具,而更是“实现权力运作的重要手段”,因此分析话语“也可以揭示支配者与服从者之间的权力关系”(蓝纯,116-117)。
(一)频繁的打断
对话中,男人对薇拉的频繁打断反映出薇拉的弱势地位和男人的主导地位。打断常被认为是不礼貌或缺乏尊重的体现,这却忽视了谈话者之间潜在的权力结构。“话语中的权力体现为强势参与者对弱势参与者的言语的控制和制约”(Fairclough,46)。换言之,打断的背后是权力的强弱,强势方打断弱势方,而很少被后者打断。强势方以此排除其认为无关的内容,使对话按其想要的方向进行。因此,打断发生的方向可以揭示权力关系的强弱。
故事开头,薇拉说起她不喜欢冷天气时被男人打断,这让她想起 “他那个伎俩——打断她的伎俩——以前时常惹得她很生气”(Mansfield,182)。男人的打断并非偶尔无意为之,而是频繁发生。习惯性的打断显示了男人对于薇拉的权力优势。薇拉“那时常常觉得,在她话正说到一半时,他好像突然用手捂住了她的嘴,不理她,转身去注意些其他的事”(Mansfield,182)。被打断的薇拉被男人剥夺了说话的机会,被迫沉默。因此,认为男人打断薇拉是因为内向的薇拉不愿意向他人敞开心扉,以致男人必须寻找新的话题让对话继续下去(姚晓东,61),无意中忽略了文本事实。频繁打断反映出的是权力关系,权力强势方的男人不想听薇拉谈论她自己,认为薇拉的声音是可忽略的,因此打断她,控制谈话方向。弱势方的薇拉则不曾打断男人来抢夺话语权。部分学者将男人提到俄罗斯时薇拉的插嘴理解为打断,这值得商榷。薇拉的插嘴并不构成典型的打断。一方面,她急于发起的问题与男人之前的谈话内容密切相关,因此更多体现出她对男人的专注倾听和强烈兴趣;另一方面,薇拉发问并非意图阻止男人说话,抢夺话轮,而是邀请男人接着讲述自己的旅行经历。这不能证明她的自私和无礼,也没有实质性地改变权力关系。
(二)薇拉——沉默的倾听者
对话中的不平等还体现于角色分配。薇拉地角色是顺从的倾听者,而男人则始终是说话人,这体现出薇拉相對于男人的弱势地位。说话的机会本就是权力的象征。在平等的对话中,参与者在不同的话论中交替扮演说话者和倾听者的角色。在不平等的关系中,通常是强势参与者说话,而弱势参与者倾听。角色分配和话论转换,正是“在对话中行使权力”的策略(蓝纯,134),是权力关系的表现。男人称赞薇拉,“你真是个很棒的倾听者”(Mansfield,186)。薇拉内心敏感细腻,因此善于理解男人的话。她自己的声音却被压制,处于沉默,承担着倾听者的角色,这并不是自愿的选择,而是处于权力弱势的结果。
话论转换方面,薇拉很少主动发起新的话题,几乎不谈论自己。谈话虽然由男人和薇拉共同完成,但双方的贡献并不平等。强势方的男人控制着对话进程,他发起新的回合,转换话题,提出问题。薇拉则顺从地跟随男人的思路,听他说话,或是回答男人提出的问题,配合男人。对话基本是男人在讲述自己,薇拉是沉默的配角。男人的生活经历和旅行见闻都出现在他的话语中,薇拉过往的具体生活则几乎不曾被谈起。仅有的一处细节是男人问起她的钢琴,薇拉简短地说很久前就卖掉了。显然薇拉的生活发生了变故,过得比较艰难。尽管读者出于好奇或关心可能希望了解更多,但此处男人没有就此问下去,“他就这样算了”(Mansfield,185)。这也暗示出一个更普遍的假设,即发起话题的主动权属于男人。当男人忽视此话题时,薇拉没有试图多说,而是任由男人回头谈论自己。总之,男人是发起者,是说话者,起主导作用;薇拉是配角,是没有话语权的听话人。
(三)薇拉声音的客体化
薇拉在他们的关系中的弱势地位还表现在,她的声音即使被听到,也被视为一个客体,被简化为一个被观看和凝视的审美对象。男人听到她的声音时,关注到的是声音的形式,而不是内容。除总体上的话语权缺失外,薇拉即使发出自己的声音,也没有真正被男人听到。男人赞美薇拉有 “美妙的声音”,“迷人的说话方式”, 他可以轻易从众人的声音中辨认出她的,因为她的声音是“挥之不去的记忆”(Mansfield,182)。这似乎反映出男人对薇拉的深情,时隔多年依然念念不忘。但正是这种赞美,才体现出对薇拉声音的客体化。男人记得薇拉曾经告诉他各种花的名字,实际上却没有听懂薇拉。对各种花名的熟悉显示出薇拉对美丽事物的热爱,男人忽略了她的内在品质,只注意到她的说话方式。他记得当时的场景是因为她很迷人,而不是因为她的内在。他的赞美是一种微妙的男性凝视。薇拉变成被观赏的对象和客体,而不是独立的主体,这进一步体现出薇拉的失语和弱势。
三、女性的权力弱势
薇拉与男人在话语使用中的权力不平等并非偶然,而是社会层面性别不平等的具体展现。话语不只是孤立的个人行为,也反映公共的社会规范,是“由社会结构决定的社会实践”(Fairclough,17)。在男权社会的两性关系中,男人是主体,女人是被边缘化的他者,是男人的附属品。如波伏瓦在《第二性》中说,“他是主体,他是绝对者——她是他者”(Beauvoir,16)。女性被要求依附于男性,以男性为中心,为男性做出牺牲,满足男性的主体幻想。姚晓东分析了薇拉与男人的地位差异,但是认为在对话中不应该“沉溺于想象,仅仅扮演倾听者的角色”,而应该“采取行动,努力争取话语权”(姚晓东,63),有建设性意义,却无形中将责任归咎于薇拉的不反抗,忽略了深层的结构性问题,使不公平的结构隐形化。实际上,薇拉的失语正说明面对结构性不公时个体的无能为力,女性整体处于权力弱势地位。女性的弱势在于女性的主体性受到压抑。薇拉热爱自由,渴望探索世界,但困于现实,无法像男人一样去完成当年计划的旅行。当她听到男人谈论旅行经历时,感到“内心那沉睡至今的奇怪的野兽骚动起来”(Mansfield,184)。“野兽”比喻薇拉对自由的强烈渴望,“沉睡至今”表明受到现实环境的压抑而无法实现,同时她始终不曾彻底接受现实,放弃自我。内心的“野兽”是“奇怪的”,因为薇拉对自由的渴望是不同于主流话语,是未被驯化的异类,存在于结构之外,陌生而无法被理解。换言之,薇拉内心既渴望自由又压抑自我的矛盾,正体现出社会结构对女性的压抑和规训。薇拉“也许是世界上唯一真正活着的人,生不逢时,困于宿命”(Mansfield,188)。薇拉与众不同,其个体的独立意识与外部压迫性的性别关系之间的冲突难以调和,她所面临的困境不是私人的,而是其身处的社会结构性压迫的体现。在男性主导的社会中,女性的独立意识自然格格不入。
男性运用话语来控制和压抑女性,将女性对自由的渴望定义为自私,要求女性无私地牺牲自我,维持男性的中心地位。薇拉听到男人说“希望变成魔毯带你去看你想去的远方”(Mansfield,188)时,感动到想要留下来。看起来,男人已经意识到薇拉被时代与命运所束缚的现实,并愿意做出努力去改变现状。僵硬的结构在此刻似乎有所松动,女性的自由仿佛即将受到认可与尊重。然而,他又说道:“但是……我们是这样的利己主义者,如此地自我陶醉,如此地陷于自我,以至于我们心里没有一个角落可以容纳别人。”(Mansfield,188)“我们”似乎同时指涉男人和薇拉,看上去男人是在剖析和反思自我,但他已经说过自己只是想帮助薇拉实现她的愿望,塑造了自己无私的形象,因此他其实是说,自己并不自私,薇拉才是以自我中心,此处的“我们”实际单方面指代薇拉。男人使用“我们”一词营造出共同体的表象,更容易赢得薇拉的认同,令薇拉失去自己的立场,认为自己追求自我即是自私,产生道德的内疚,接受男人的视角。男人试圖用话语来重塑薇拉的意识和观念,使她放弃自我,做一个所谓无私的人,照顾男人。男性掌握着话语权,借用话语来压抑女性,塑造没有独立意识的女性,使其牺牲自己的主体性以为男性而服务。
四、薇拉的逃离
面对要求女性牺牲自我的不平等性别关系,薇拉的离开即是拒绝和抵抗,以此保持自我。薇拉“没有朋友,不和人们交朋友”,“一如既往地孤独”(Mansfield,188),是她主动的选择。分手六年,薇拉不曾和其他男人交往,因为她清楚性别关系对女性的不公,明白社会结构中的男性中心主义。爱情固然要求个体走出自我,“打破一人视角,让世界从他者、从别处的视角中重生”(韩炳哲,69),但这种改变应是平等和双向的。否则,要求女性无私只能是维持现有不平等结构。作者没有为故事中的男人赋予具体的名字,因为他是普遍男性的象征,是能指符号,指代性别结构中的普遍男性。薇拉拒绝的并不是男性个体,而是男权社会下的男性整体或结构。
男权社会单方面要求女性做出奉献,女性缺乏话语权,处于弱势地位,无法有效维护自身的主体性,爱情关系主要基于对女性的压抑。爱情与自由发生矛盾,薇拉的离开是拒绝了爱情和关系,选择了自由和孤独。她的孤独并非是因为她的自私自恋,而是身处男权社会的自我保护,是对不平等关系的拒绝和逃离。个体的薇拉无力反抗性别结构,又不愿屈服或接受,因此用离开作为自己的抵抗,通过逃离体现出其顽强的主体性。薇拉的逃离是对男性话语霸权和男性压迫的抵抗。
五、结论
通过文本细读与话语分析发现,薇拉在与男人的对话中经常被突然打断,缺乏话语权,被迫充当沉默的倾听者,即使发出声音也不能被真正听到,只是成为被男人凝视的客体,因此始终处于权力弱势地位。从个体层面上升到结构层面,薇拉相对男人的弱势是不平等性别结构的具体体现。在男权社会中,女性的主体性受到压抑,掌握话语权的男性将女性对自由的追求定义为自私,意图塑造无私的女性以满足男性的需要。文中的薇拉拥有强烈的独立意识,无法接受男权社会对女性的规训,离开了男人及其代表的男性群体,自愿游离于爱情关系之外。孤独是她的主动选择,以此抵抗和逃离不公平的性别结构。
参考文献:
[1]Beauvoir,Simone De.The Second Sex[M].H.P. Parshley,trans. London:Lowe and Brydone,1956.
[2]Fairclough,Norman.Language and Power[M].New York:Longman Inc.,1996.
[3]Mansfield,Katherine.Bliss,and Other Short Stories[M].Harmondsworth:Penguin Books,1977.
[4](德)韩炳哲.爱欲之死[M].宋娀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
[5]蓝纯编.语言导论[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7.
[6]牛雪莲. 《莳萝泡菜》中的自我主义与女权主义[J].作家,2015,(9):96-97.
[7]申丹.明暗相映的双重叙事进程—— 《莳萝泡菜》单轨反讽背后的双轨反讽[J].外国文学研究,2019,(1):17-27.
[8]姚晓东.解构与重构:话语分析视角下的《莳萝泡菜》解读[J].当代外语研究,2013,(6):60-63.
[9]曾霞.从女权主义的角度解构《莳萝泡菜》中的男性形象[J].小说评论,2010,(4):271-275.
[10]张闻琦.《莳萝泡菜》中的女性视角叙事手法[J].湖北成人教育学院学报,2009,(5):78-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