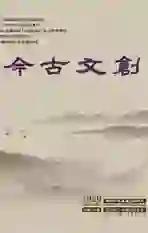《鲁滨孙漂流记》中的田园理想研究
2020-09-10吴森
吴森
【摘要】作为欧美小说的开山之作,关于《鲁滨孙漂流记》的研究不胜枚举,而却鲜有人以田园理想为切入点剖析小说意涵。本文立足于英美田园文学批评理论,通过对时代背景的分析和对文本的解读,阐述本文中多层次的田园理想,并剖析小说所展现的作者对于社会发展的思考。
【关键词】《鲁滨孙漂流记》;田园理想;城乡冲突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0)36-0019-04
基金项目:本项目由“华中农业大学‘国家级/省级大学生创新創业训练计划’资助”,项目研究成果属于华中农业大学所有。
17、18世纪的欧洲,随着人们对于海洋以及新大陆的不断探索,游记文学盛行一时。1719年,年近古稀的英国作家丹尼尔·笛福完成并发表了他的回忆录式小说《鲁滨孙漂流记》,该小说以一个被放逐到荒岛的水手为原型,讲述了一个名叫鲁滨孙·克鲁索的英国人,在流落荒岛后顽强生存,历经28年最终得以返乡的故事。小说一经发表便引起了剧烈的反响,在出版后的四个月内再版了五次,在当时可以说是人手一本。至今三百年来,已经衍生出数百种不同的译本、剧作以及仿作,不仅引得各个时代的学者对于其丰富的文学意涵进行深刻剖析,也为笛福博得了英国小说之父的赞誉。
文学批判界对于《鲁滨孙漂流记》的研究不胜枚举,其集中聚焦于早期的个人英雄主义分析和现当代的后殖民主义研究。在18世纪,对小说的解读更多地倾向于突出个人经验的重要性。
18世纪是资本主义蓬勃发展的时期,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下,也让文学作品响应时代号召,莎士比亚式的宫廷贵族被逐渐摈弃,取而代之的是克鲁索式的来自中产阶级的积极开拓、顽强拼搏的形象。伊恩·瓦特(Ian Watt)在著作《小说的兴起》中指出,鲁滨孙·克鲁索和笛福笔下的其他任务一样,是“经济个人主义的化身”[1]63。而安德鲁·桑德斯在《牛津简明英国文学史》中,认为克鲁索是一个“孤独的流亡者而非原始殖民主义者”,他所体现的是一种“普通人对抗陌生环境的英雄主义”[2]304。
到了20世纪中期,随着后殖民主义思潮的兴起,对小说的研究逐渐转向后殖民主义。后殖民主义用全新的视角,将鲁宾孙与荒岛的关系解读为殖民与被殖民的关系,鲁宾孙个人英雄的形象被解构为早期殖民者形象,其贩卖黑奴、占有荒岛的行为被解读为欧洲早期殖民经验。而他对星期五居高临下式的教化与奴役,更被视作“西方种族歧视的集体无意识”[3]54。
然而,却鲜有学者以田园理想为切入点剖析小说意涵。田园理想作为英美文学田园批评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发端于文艺复兴时期,并在20世纪60年代随着生态批评的出现重回批判界。
本文将立足于英美田园批评理论,从田园理想的角度深入剖析小说中深厚的田园主题。通过分析鲁滨孙流落荒岛前、流落荒岛之初以及荒岛求生三个时间段的种种作为,分析小说如何以主人公身上所体现的田园冲动展现其对于社会发展的思考,并详细阐述小说中多层次的田园理想。
一、田园理想与《鲁滨孙漂流记》
20世纪60年代末,英美田园批评的领军人物利奥·马克斯(Leo Marx) 在其代表作《花园里的机器:美国的技术与田园理想》(1968)中对于田园理想给出了明晰的区分:大众的情感型田园理想(Sentimental Pastoralism)和想象的复杂型田园理想(Complex Pastoralism),他认为前者是对乡村生活的过度理想化、诗化的书写,是一种从复杂的城市文明“退避到原始美好或乡村幸福的感伤情趣”,从而“掩盖了城市化、工业化真正问题”[4]3-4。而后者则对乡村生活进行写实的书写和揭露,并且“不希望我们对宜人的田园风光持完全的肯定态度”。[4]17-18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5]”这样一派宁静和谐的乡野风景正是情感型田园理想的吸引力所在。从世故嘈杂的资本主义世界,走向纯真和谐的田园风景,代表的正是大众心理对于原始美好的憧憬与渴望。但如果这样的一种田园冲动脱离了理性的桎梏,一如小说中鲁滨孙对于探索未知的狂热冲动,就会产生愚蠢的不切实际的愿望,产生浪漫怪异的思想和感情,也就是情感型的田园理想。这种将乡村生活方式理想化的倾向曾一度导致了思想的含混,也阻碍了社会的进步,掩盖了工业文明真正的问题。
但工业文明带来的现实问题,往往会将这样一种含混的田园冲动消弭于无形,深刻的文学作品常常通过讽刺或质疑这样不切实际的田园幻想,来展现更理性、写实的复杂型田园理想。当理想中的“快乐的英格兰”(Merrie England)深陷“伦敦雾”(London Fog)的泥沼,虚幻与真实的界限便被打破,对和谐田园逃避式的向往便沾上了讽刺的意味。
《鲁滨孙漂流记》是一部生动的资本主义发展史,也是现代化文明进程种种问题的折射。以田园理想为切入点,下文将继续研究《鲁滨孙漂流记》如何对资本主义社会转型进行伦理批判。
二、逃离故乡:《鲁滨孙漂流记》 中的田园冲动
利奥·马克斯在《花园里的机器》中认为,情感型的田园理想是一种“逃离城市”的“退避到原始美好或乡村幸福的感伤情趣”,是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蒙着的“一层温柔的怀旧面纱”。这样的一种田园情结自大发现时代延续至今,这样的朦胧情感从莎士比亚、马克·吐温、厄内斯特·海明威以及罗伯特·弗罗斯特的作品中都或多或少有所体现。
这样的一种田园情结在笛福的笔下有强烈而自然的流露。在《鲁滨孙漂流记》中,主人公鲁滨孙从小说的一开始就流露出强烈的离开家乡出海的意愿:
“我是家里的第三个儿子,没学任何手艺,从小就满脑袋的胡思乱想。我的父亲非常传统,他让我享受到好的教育,甚至送我进寄宿学校和上普遍的义务村学,他热切希望我学法律。但我对这一切不感兴趣,一心想漂洋过海。[6]”
在小说中,鲁滨孙出生于体面的家庭。他本可以通过接受教育,进入社会的中上阶层,但他却对离开欧洲出海有着强烈的执念,同时并没有提及出海的明确目的地,仿佛欧洲之外的海洋之上的某种存在有着致命的吸引力,以至于现有社会的一切都变得索然无味。
值得注意的是,这样的一种田园冲动并不是从一而终的。在小说的第一章,鲁滨孙在每一次出海遭遇风险后,都会对自己的行为懊悔不已,其反差之大,和他的田园冲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这种惶恐不安的心情下,我多次发誓,如果上帝愿意在这次航行中留我一条性命,如果我能再一次脚踏干燥的土地,我就径直回家见我的父亲今生今世再也不涉足海船了,我将听从父亲的劝告,再也不像这样自讨苦吃了。[6]”
看似突兀又矛盾的意愿,其实暗含着时代背景下资本主义发展的混乱与失序。随着圈地运动、工业革命相继在英国展开,英国开启了高速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一方面资本主义力量快速崛起,另一方面人与自然的失和也进一步加剧。加州学派代表人物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在其著作《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中指出,十八世纪的英格兰和中国南方地区同样面临着“马尔萨斯陷阱”(过快的人口增长抵消了经济发展成果),而英格兰之所以能在十九世纪跳出马尔萨斯陷阱,并在之后成为欧洲乃至世界经济中心,对外进行殖民扩张是核心原因之一[7]。这意味着,资本主义的制度性缺陷决定了其早期的原始积累不可避免地要与大自然发生冲突,而仅仅是欧洲本土的自然资源显然无法满足其需要,于是资本主义的发展毫不犹豫地指向攫取全球资源。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城乡之间的对立难免让人对宁静和谐的乡野风光产生向往之情,这样的朦胧冲动在十八世纪的小说中不乏笔墨。无论是菲尔丁的《汤姆·琼斯》中,充满着伦理与秩序的乡村同邪恶的伦敦之间强烈的对比,还是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中,作者借大人国国王之口对英格兰的讽刺,都足以证明在十八世纪的英国,“逃离伦敦”俨然已经成为一种时尚。然而,在大机器生产的铁蹄下,整个欧洲已经很难再寻找到一片如此高度理想化的乡村净土,昔日“快乐的英格兰”也只是超越物质存在的虚影。
既然欧洲已经再难找到诗化的乡村,那么这片处女地究竟在哪?笛福笔下的鲁滨孙一次又一次地“逃离欧洲”,正是受这样一种情感型田园理想的驱使。戏剧化的是,鲁滨孙真的来到了一座从未被人踏足的荒岛,荒岛在文中并没有给出具体的方位,这样的场景设计和莎士比亚的戏剧《暴风雨》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荒岛是具体实有的,然而地理位置却是虚无缥缈的,进一步增强了这样一种情感型田园理想所给人带来的幻灭感。
然而感性的冲动在残酷的现实前是如此不堪一击。荒岛严峻的生存条件显然与鲁滨孙向往的宝地落差甚大,但主人公并未就此沉溺于幻灭的虚妄当中,而是代表着城市文明的铁蹄,向荒岛这片处女地吹响了征服的号角。
从渴望逃离到流落荒岛,从征服荒岛到改造荒岛,田园冲动驱使着鲁滨孙逃离故乡,而他本人就是马克斯笔下闯入“花园”的“机器”,他对荒岛的征服不仅仅象征着资本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与征服,更象征着城市文明向乡村文明的进军。
三、由故乡到他乡:《鲁滨孙漂流记》 中闯入“花园”的“机器”
在小说中,鲁滨孙对荒岛的闯入是一个关键的转折点,是其田园理想由表及里的过渡。如果说流落荒岛前鲁滨孙还仍对于出海探索心存幻想的话,那么从他踏上荒岛的那一刻起,含混的感伤情趣就在冰冷的现实面前消弭于无形了。
荒岛像一座巨大的“花园”,表面上一派安宁祥和,其实暗流汹涌——变幻莫测的恶劣天气、岛中猛兽、匮乏的物资以及不知藏身何处的食人部落无不严重威胁着主人公的生存,自其闯入的那一刻起,他就必须抛下感性的桎梏,去认识田园世界的本质,重塑文明的和谐。
值得一提的是,这样的一种“闯入”暗含深意,文学作品中也经常出现意象的闯入,以传达耐人寻味的意涵。利奥·马克斯认为,经典文学作品中反复出现的现代机器闯入田园风景的意象,事实上是作者不得不承认诗化的田园理想同现实世界格格不入的关系,简单退隐的感伤情趣在现实世界中站不住脚,而“由于机器的打扰而转化为更加复杂的心境”。[8]9正是这些闯入的“机器”的意象将文本中表象平面的“情感型”的田园幻境升华成令人寻味的“复杂型田园理想”。
在小说《鲁滨孙漂流记》中,笛福同样巧妙地设计了闯入的“机器”意象。从宏观角度来看,鲁滨孙来到荒岛本身就是城市文明闯入乡野之地的隐喻;从微观叙事来看,笛福详细描绘了鲁滨孙“闯入”乡野田园的情形:
“我还发现,我所在的这座海岛非常荒凉,我有充足的理由相信这里没有人住……回来的路上,我看见一只大鸟停在森林边上的一棵树上,就向它开了一枪。我相信,自上帝创造这世界以来,第一次有人在这个岛上开枪。我刚开枪,从森林的各个部分飞出无数的各种鸟类,鸟声此起彼伏,混成一片,但我却叫不出任何一种鸟来。[6]”
多么意义非凡的一枪!鲁滨孙用这一枪向整个荒岛宣告他的到来,也昭示了接下来他对荒岛所进行的一系列人为改造。鲁滨孙作为一个闯入者的意象,打断了荒岛表面上的一派和谐,成为了一股“闯入”田园风光的反作用力,粗鲁地进入荒岛上原有的乡野田园,给予读者以强烈的反差感受。
如果说情感型的田园理想是一种含混的感伤情趣,那么由外部世界强行闯入的意象则成了惊醒世人的警钟——警告这样朦胧的意识形态只不过会掩盖工业文明的真正问题。事实上,无论是霍桑和梭罗笔下“尖啸的火车汽笛”的意象,抑或是鲁滨孙打响的枪声意象,其背后都暗含著一个隐喻——技术向田园进军。
“机器”闯入“花园”,是毁灭“机器”,回归原始主义,还是征服“花园”,再造一个海外的英格兰?鲁滨孙把技术带进了田园,却跳脱出了二者的束缚,选择了中间路线——既不满足于简单的田园退隐,空发提屠鲁式的田园牧歌,也不全然抛弃田园理想,而是在介于技术和自然之间重塑了一种中间风景。
四、反把他乡作故乡:《鲁滨孙漂流记》 中的复杂型田园理想
叹惋田园风光的消逝无济于事,直面并解决文明的复杂性和冲突性则是解决问题的唯一渠道,这就是复杂型田园理想有别于情感型田园理想的核心本质。
18世纪的英国,资本主义社会不仅摧毁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并且异化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资本主义让少数人占有生产技术并赋予城市和工业以绝对优先权,其代价就是社会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恶化,人类异化成为“机器的单纯的附属品”[9],同时“割断了子女与父母、人与人、男人与女人之间的联系”[10]48。不断加深的工业文明危机,激起了人们对城市和工业的境况的担忧和反思,对解决城乡冲突的思考以及实践,复杂型的田园理想正是人们对此历史进程的一种反应。
如何调和城乡冲突,不同的作家有不同的答案。善于剖析的莎士比亚找到了技术和田园之间的一种天然的联结,利奥·马克思认为莎士比亚在剧作《冬天的故事》中表达出这样一种立场:既然技术是人类的产物,而人类又是自然的产物,那么技术也是自然的产物,人类作为技术和自然之间天然的桥梁,必然能调和技术和自然之间的冲突。[8]178
而笛福给出了不同的答案:技术带来物质的丰裕,而自然带来精神的自由。主人公鲁滨孙改造荒岛的过程中,主要运用了两种方式来实现其田园理想:从物质世界的改造来看,他运用工业文明的技术实现了物质的丰裕;从精神世界的改造来看,他用宗教来调和伦理困境。
从改造物质世界的角度来看,鲁滨孙将一座自然的岛屿改造成了一个与世隔绝的王国,技术的力量带来丰裕的物质生活,从而构成了和谐田园的稳定基础。当鲁滨孙流落荒岛时,风暴和海浪将船骸驱离到荒岛附近,船骸上残存的来自欧洲世界技术生产的生活物质,让鲁滨孙“活了下来,并一直活到今天[6]”。可见技术的产物构成了鲁滨孙生存的基础,没有物质基础,实现田园理想便无从谈起。
解决了生存的问题,技术的力量转而解决生活的问题。鲁滨孙依靠掌握的技艺,“完全靠劳动和发明制造出各种合适的工具[6]”,靠着这些工具,鲁滨孙不仅实现了生活水平的提升,并且在荒岛上再现了一片自给自足的乡村田园。
当物质生活达到一定的水平,技术的力量转而关注精神需要。鲁滨孙依靠绝对的技术优势,不仅过上了衣食无虞的生活,并自诩为全岛的君王,“绝对掌握着自己臣民的生命,说一不二[6]”。这种精神需要建立在物质的稳定基础之上,正如文中引用的圣经典故:“以色列的子民们虽然当初被救出埃及时高兴了一阵,但在旷野里缺乏面包时,他们甚至反叛了拯救他们的上帝。[6]”
从改造精神世界的角度来看,小说肯定了宗教在维护社会稳定上的积极作用,并指出自然的力量能够引领人的理性,而宗教的存在则是“大自然的必然后果[6]”。这种想法将宗教与自然联结在一起,以人的理性作为媒介,发挥着调和伦理困境的作用。
鲁滨孙以一个新教徒的宗教身份对仆人星期五进行教化,实现了道德观念重建的作用。星期五本是一个野人,通过鲁滨孙对其灌输宗教观念,星期五不仅改变了星期五吃人的野蛮习俗,并且使其坚定信仰基督教的道德观念,星期五的转变是这片田园世界道德观念重建的具体体现,伦理困境的解决也使这座荒岛脱离了野蛮的氛围,拥有了属于自己的文明秩序。
在文明秩序的基础上,鲁滨孙进一步发挥意识形态的作用,巩固田园的和谐与宁静。“我虽然只有三个臣民,但他们属于三个不同的宗教。我的仆人星期五是新教徒;他的父亲是异教徒;而西班牙人是个天主教徒。可是,在我的领土上,我允许信仰自由。[6]”鲁滨孙允许信仰自由,他构建的田园世界不再局限于一种意识形态的束缚,宗教从而可以以最大限度发挥其社会稳定作用,维持田园的和谐风光。
鲁滨孙在荒岛上塑造了一个充满着秩序与伦理的田园世界,田园的和谐也反过来对鲁滨孙施加着影响。在小说的开头,“鲁滨孙的冒险意愿毫不含糊地指向快速发财”[11]43,而他为了达成这一目标,可以违逆父母背井离乡,也可以毫不犹豫地卖掉他的救命恩人佐立。
然而落难荒岛的经历,使他纯粹的“经济人”身份重新注入了人性的光辉。在小说的前半部,温情脉脉的家庭关系与和谐无私的人际关系是缺席的,人与人之间不过是冰冷的契约关系,与其说他是被命运抛弃到了荒岛,不如说他是主动与社会“脱钩”:当他诀别父母,出卖朋友,他的灵魂已经早肉体一步流落精神的“荒岛”。而真正流落荒岛之后,所有的利益往来反而失去了意义,“这使他和“物”的关系蒙上一层朴素而亲切的田园色彩”[11]44。當他逃出生天之后,不仅重新同社会建立起联系,更是步入婚姻组建了家庭,在他身上我们看到了经济利益本位色彩的褪去,以及人性的复归。
总而言之,鲁滨孙不仅在荒岛上实现了技术和自然之间的和谐,将荒岛这座“他乡”改造为“故乡”,而这样的一种和谐也反过来投射到他的精神世界里,让远在异乡的他重新建立起与故乡的联系,正可谓是反把他乡作故乡。
五、结语
鲁宾孙的冒险历程,正是小说中田园理想的嬗变过程。在田园冲动的驱使之下,他像闯入“花园”的“机器”一般来到荒岛,象征着工业文明向田园风景的进军。
但野蛮、原始的荒岛将其田园情结朦胧含混的情感消弭于无形,理性与反思见证了小说中田园理想由表及里的转变。
鲁滨孙的“闯入”彻底改变了荒岛,这种改变不是破坏,而是基于理性与反思的改良,在理性的调和下,原始的荒岛形成了一种中间风景,让天工与人工和谐并置。这便是复杂型田园理想的深刻意涵,既不崇拜原始主义,亦不放任工业文明野蛮生长,而是在理性的指导下,有序地、和谐地推进社会转型进程。
作为欧美小说的开山之作,《鲁滨孙漂流记》自问世便承担着厚重的时代责任。今天,当把小说重新放入十八世纪的时代背景下,不难体会到作者对英国乃至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社会转型的伦理批判,值此小说发表三百年之际,重读《鲁滨孙漂流记》,新的意涵油然而生。
参考文献:
[1]Ian Watt.The Rise of Novel[M].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Berkeley and Los Angeles,1957:63.
[2]Andrew Sanders.The Short Oxford History of English Literature[M].Oxford University Press:New York,2004:304.
[3]陈岚.《鲁滨孙漂流记》与后殖民主义[J].长沙铁道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04):53-54.
[4]利奥·马克斯.花园里的机器:美国的技术与田园理想[M].马海良,雷月梅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5]滕王阁序[EB/OL].古诗文网,https://so.gushiwen.org/search.aspx?value=%E6%BB%95%E7%8E%8B%E9%98%81%E5%BA%8F.
[6](英)丹尼尔·笛福.鲁滨孙漂流记[M].曾冲明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1.
[7](美)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M].史建云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
[8]利奥·马克斯.花园里的机器:美国的技术与田园理想[M].马海良,雷月梅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9](德)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M].中共中央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10]乔治·奥威尔.一九八四[M].董乐山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
[11]黄梅.推敲“自我”:小说在18世纪的英国[M].北京:三联书店,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