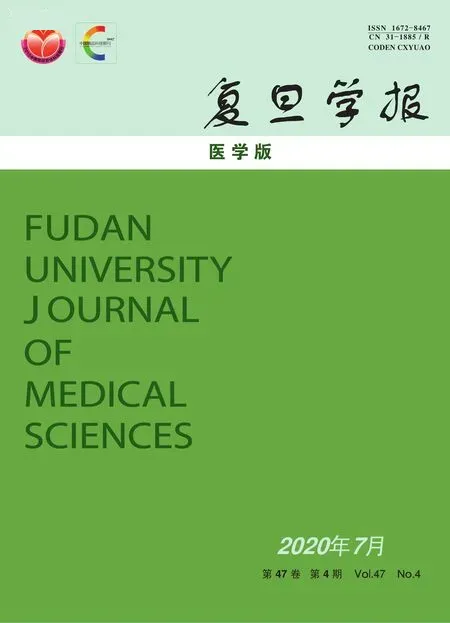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ITP)合并胸闷1 例
2020-09-04郑杭萍熊楠青李念夷王小钦罗心平
周 鹏 郑杭萍 熊楠青 李念夷 王小钦 罗心平 李 剑△
(1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心内科,2血液科 上海 200040)
免疫性血小板减少(immune thrombocytopenia,ITP)是一种因免疫系统介导的血小板破坏过多进而导致血小板减少的疾病,可继发皮肤黏膜、内脏出血[1]。既往认为,血小板增多是冠心病(coronary artery disease,CAD)和急性心肌梗死的危险因素之一[2-3],但Chandan 等[4]的队列研究提示,ITP 患者的心血管疾病风险是非ITP 者的1.38 倍,行脾切除治疗的ITP 患者的心血管疾病风险更高。Meta 分析也提示,ITP 患者发生动脉栓塞事件的风险是非ITP 者的1.5 倍,发生静脉血栓栓塞事件的风险是非ITP 者的1.9 倍[5]。这可能与ITP 患 者 的血小板体积大、黏附能力强相关,体积大的血小板具有更强的止血作用,有血栓形成的倾向,具有潜在的心肌梗死风险[6];自身抗体可能在损伤血小板的同时,对血管内皮也具有损伤作用[7];而激素等治疗方式可能导致血液的高凝状态,同时继发的代谢改变也可能促进动脉粥样硬化的进展,与心血管事件的发生相 关[8]。Rodeghiero[9]总 结 了 数个ITP 合 并 血 栓栓塞事件的研究,认为ITP 是静脉血栓栓塞事件的危险因素,而对动脉血栓的影响较小。Ekstrand 等[10]的队列研究提示,年龄增加和男性是ITP 患者发生动脉血栓事件最主要的危险因素,同时年龄增长也增加了静脉血栓的风险。本文报道1 例ITP 合并胸闷患者的诊治过程。
病例资料患者,男性,77 岁,因“血小板减少30 年,PCI 术后9 年,再发阵发性胸闷6 月”入院。患者30 年前因自发鼻出血不止于外院就诊,查血小板10×109/L,完善骨髓细胞学等检查,诊断为“原发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予以激素(剂量不详)治疗后好转,后长期服用泼尼松5 mg(qd),随访血小板波动于20×109/L 左右。患者2010 年2 月活动后出现胸闷,当时至外院行胸部CT 未见明显异常,此后时有活动后胸闷,伴胸骨后绞痛,一般持续2~3 min,休息后缓解,无放射痛及出冷汗等。遂至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门诊,给予美托洛尔25 mg(bid)、单硝酸异山梨酯40 mg(qd)治疗。2010 年6 月初患者休息时出现胸痛,放射至左臂,伴出冷汗,无头晕、恶心、呕吐、视物模糊等,持续近半小时后缓解,未含服硝酸甘油。后胸痛明显加重,发作次数增加,夜晚不能平卧入睡,伴痛醒。后因胸部疼痛剧烈、不能缓解至我院急诊,以“急性冠脉综合征(acute coronary syndrome,ACS)”收住心内科。患者GRACE 评分120 分,TIMI 评分3 分,予对症治疗后,于2010 年6 月上旬在局麻下行冠状动脉造影(coronary angiography,CAG)术,术中见左前降支(left anterior descending,LAD):近中段长病变,最窄处95%~99%,因患者血小板较低(8×109/L),未行经皮冠状动脉介入(percutaneous coronary intervention,PCI)术。术后请血液科会诊,完善骨髓穿刺术:骨髓有核细胞增生活跃,全片巨核细胞8个,产板型1 个,颗粒型6 个,裸核1 个,片上散在极小簇血小板易见。结合既往病史,考虑为ITP 可能,予甲泼尼龙60 mg 静滴3 天后改为泼尼松30 mg(bid)口服治疗,血小板回升至93×109/L。给予患者西洛他唑50 mg(qd)、氯吡格雷50 mg(qd)抗血小板治疗后,于2010 年6 月下旬在局麻下行PCI 术:植入Multi-Linkφ 3.0 mm×23 mm支架于LAD中段,植入Multi-Linkφ 3.5 mm×23 mm 支架于LAD 近段,术后3 个月即停用抗血小板药物,泼尼松规律减量至5 mg(qd),患者无出血事件。
2013 年9 月初,患者上呼吸道感染后出现全身散在瘀斑又至我院急诊就诊,血小板14×109/L,予输注单采血小板1 U,予甲泼尼龙60 mg 静滴3 天后改为泼尼松30 mg(bid)口服治疗,症状明显缓解,2013 年9 月下旬复查血小板为17×109/L,遂收入血液科进一步诊治。入院后完善骨髓穿刺术提示:增生性骨髓象,巨核细胞成熟障碍;骨髓活检见造血组织占30%~40%,巨核细胞可见,各系造血细胞未见明显异常,遂诊断为ITP。予地塞米松40 mg(qd,d1~4)+促血小板生成素15 000 IU(qd,d1~14)方案治疗,治疗后复查血小板升至172×109/L。出院后规律服用泼尼松15 mg(qod)+10 mg(qod)。
患者出院后偶有阵发性胸闷、胸痛,2017 年8 月因胸痛就诊于外院,2017 年8 月下旬行CAG+经皮冠状动脉腔内成形术(percutaneous transluminal coronary angioplasty,PTCA):左 主 干(left main coronary artery,LM)远段30%狭窄,LAD 中段支架内闭塞,左旋支(left circumflex artery,LCX)远段40%~50%狭窄,右冠状动脉(right coronary artery,RCA)中段50%狭窄,远段60%狭窄。于LAD 病变处行PTCA 术,置入Thrombuster Ii 抽吸导管,由远及近抽吸1 次,复查造影,TIMI 血流0~1 级,遂置入球囊Hiryu 2.5 mm×15 mm,LAD 中段以压力12 Atm×10 s 扩张球囊,再置入球囊NC sprinter 3.0 mm×9 mm 于LAD 中段支架内行后扩张,以压力16 Atm×10 s 扩张球囊,复查造影,残余狭窄<30%,远段TIMI 血流3 级。出院后患者服用阿司匹林100 mg(qd)和氯吡格雷75 mg(qd),3 个月后因血小板减少停药。
患者自诉2019 年1 月起阵发性胸闷不适,胸闷后即服用麝香保心丸,服药后2 min 症状即缓解,症状发作次数渐频繁,遂再次收入我院。
患者有高血压病史11 年,否认糖尿病史,否认吸烟史、饮酒史。
入院后处理 2019 年6 月下旬,血小板计数为16×109/L。诊断为CAD PCI术后ITP 合并高血压。
血液科医师予甲泼尼龙40 mg(qd)治疗,并输注血小板1 U,2019 年6 月下旬复查血小板计数为85×109/L,排除禁忌后于2019 年7 月上旬行CAG术,术中LM 未见明显狭窄;LAD 近段狭窄40%,中段起全闭塞(图1);LCX 中段管壁毛糙,远段提供侧枝使LAD 远段显影;RCA 开口狭窄50%,近段管壁毛糙,狭窄30%。 遂于原支架远段串联植入Resolute 2.75 mm×30 mm 及Resoulute 2.75 mm×18 mm 支架各一枚。复查DSA 见支架贴壁良好,未见残余狭窄(图2)。术后予泼尼松15 mg(qod)+10 mg(qod)治疗ITP,常规予阿司匹林100 mg(qd)和氯吡格雷75 mg(qd)双联抗血小板治疗,未因血小板减少而停药,术后随访偶有双下肢瘀点,无大出血事件,患者无胸痛等不适主诉。
讨论本文报道1 例ITP 合并胸闷患者的诊治过程。
ITP 患者中CAD 的比例高于非ITP 者,而ITP合并CAD 的治疗是临床难题之一。CAD 患者需要接受抗血小板治疗,其可进一步降低血小板功能,增加患者的出血风险,与ITP 的治疗相矛盾。目前,对于ITP 合并CAD 的治疗尚无统一的标准。
Russo 等[11]分析了PCI 和冠状动脉移植旁路术(coronary artery bypass surgery,CABG)治疗ITP 合并CAD 患者的预后,发现两种治疗方式均比较安全,虽然出血风险均高于不合并ITP 的CAD 患者,但总体并发症发生率仍较低。在围手术期,大手术(如CABG)需保障血小板计数不低于80×109/L,小手术(如PCI)需维持血小板计数在50×109/L 以上,也有报道称血小板在30×109/L 以上时即可安全进行PCI 术[12]。术后长期的抗血小板治疗也是安全的,有研究者认为血小板计数高于50×109/L 时可正常应用抗凝、抗血小板治疗[13]。有研究者提出ITP 患者PCI 术后需长期抗血小板治疗,仅当血小板计数低20×109/L 或发生出血事件时才需考虑停药[14]。
当术前血小板计数低于手术下限时,可应用激素或丙种球蛋白冲击治疗,直至可耐受手术的程度,虽然丙种球蛋白可以增加血小板计数,但也增加了血栓栓塞事件的风险[15]。应用球囊血管成形术治疗ITP 合并急性心肌梗死的患者,避免了支架植入,从而降低出血风险[15]。
本病例证明虽然ITP 患者的血小板低,出血风险大,但仍有发生血栓栓塞事件的风险。ITP 合并CAD 的患者可安全接受PCI 术,术后在平衡出血和栓塞的风险以后,考虑更加激进的抗栓策略,即尽可能长期行抗血小板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