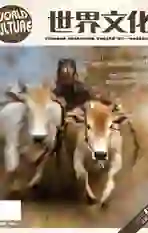追寻逝去的时光
2020-08-20王文
王文
代尔夫特距离海牙市中心不过半个小时的车程,但确实是完全不同的内陆小镇风情。这座小镇被贴上了“欧洲蓝陶之乡”的标签,据说时至今日欧洲宫廷所使用的大部分精美陶瓷仍来自代尔夫特。但我对蓝陶并没有什么兴趣,我在海牙街头的橱窗里看到过蓝陶,类似青花瓷的造型,瓶身上绘制着欧洲人心目中典型的东方人形象——身穿朝服、拖着大辫子的清朝官员,因为那蓝得发黑的釉彩竟然有些林正英操刀的港产僵尸片的味道,令人倍感困惑。尽管同行的伙伴一再抛出一起去蓝陶博物馆的提议,仍然被我拒绝了。“那你来代尔夫特看什么呢?”这是一个严肃的问题,就像去景德镇却不看瓷器一样。我犹豫了一下,没有告诉她,此行最感兴趣的其实是探寻一位17世纪的荷兰画家在故乡留下的痕迹——那个叫维米尔的艺术天才一辈子都住在这座小城。很多年前第一次看到他的画作,就惊讶于那美轮美奂的构图与光线……
从电车站台步行3分钟拐入一道镌刻城市名字的铁门内,马上就进入了代尔夫特的老城区,丝毫没有时间供你想象或酝酿情绪。
古朴的城门之上露出老教堂的尖顶,走过城门之后可以看到教堂就在一条护城河的对岸,四座哥特式尖塔护卫着中间的高塔,高塔的四面各有一面大钟。买了门票进入老教堂内部寻找维米尔的墓,从门口一直到布道台的地砖上刻满了安葬者的名字,因为全都是荷兰文,唯一能读懂的就是时间。弯着腰来回寻找着,好像在玩跳格子的游戏,但几个格子就轻松跨越了几个世纪。高大的花窗上绘着《圣经》故事中的场景,正午的光线射进即刻弥漫开来,幽幽的,像是沾染了逝去时光的气息。
维米尔的墓砖在教堂深处的角落里,只有小小的一格刻着他的生卒年:1632—1675。作为荷兰艺术“黄金时代”最重要的画家,维米尔一生都生活在这座运河边的小城,在身前身后很长时间维米尔及其画作都默默无闻,几乎要湮没于艺术史泥沙俱下的河流中,直至19世纪50年代才被批评家重新“发掘”出来。

第一次看维米尔的画当然是他的那幅代表作《戴珍珠耳环的少女》,一个少女侧身回首、欲言又止的神情攝人魂魄,这是一个所谓的“决定性瞬间”。少女披着精致的蓝黄相间的头巾,戴着一个泪珠状的大珍珠耳环。全黑的背景下人物沐浴着柔光,光线在身上流走,让你不得不注视她的眼睛。她到底美在哪里?这不是对一个美人提出的问题,对于真正的美人大家更关心的是,她是谁?所以才会有几百年来对蒙娜丽莎身份的猜测和争论。

后来我在海牙的莫瑞泰斯皇家美术馆看到了这幅画的真迹。冬天的博物馆几乎没有什么游客,一个人在展厅中心的沙发上坐着,与微笑的少女对视。在彼得·韦伯执导的同名电影中,维米尔一如所有庸俗文艺故事中的艺术家那样产生了婚外情,爱上了家中新来的除了美貌一无所有的女佣,但由于妻子和丈母娘的虎视眈眈和巨大的经济压力,只得隐忍自己的感情。在赞助人不怀好意的提议下,他终于有机会为他心爱的葛莉叶创作了这幅充满柔情的杰作,但随即就永远失去了她。在原著作者看来,画家一定是爱自己的主人公的,也正因如此才能把她描绘得那么美。
从老教堂出来,沿着运河往深处走,大片流云徘徊在天空与河堤之间,风很大,略有些寒意。沿途看到整饬的民居矗立在河边,刷着鲜艳的漆。每走一会儿就能看到一座石拱桥,路面并不宽阔,只容步行。在小城的码头站立片刻,眼前的情景总是让我想起维米尔的《代尔夫特远眺》,那是在当时堪称巨幅的油画:蓝天与浓云底下是代尔夫特小镇,环绕的运河,运河上的小桥,城门口的船和吊桥,斑驳的城墙,黑色的和红色的屋顶,并不高耸的尖塔,运河上的倒影,河对岸的行人……让人感觉这个小镇安静极了。
根据艺术史专家的研究,维米尔当初可能是在De Kolk港口远眺城内画出的这幅作品,但令人困惑的是他并非一五一十地反映了现实的景象,例如他将岸上的新教堂置于光辉下,而略去了其在水中的倒影,据说是“隐晦地寄托了自己的天主教信仰,同时象征着崭新的荷兰共和国,更代表了历经灾难后浴火重生的代尔夫特城市精神”。
河堤走到尽头就到了由昔日画家公会改造成的“维米尔之家”,是的,在代尔夫特处处可以看到维米尔的痕迹。买了10多欧元的门票进入这座三层小楼,你看不到维米尔的任何真迹,因为他传世的37幅作品绝大部分都被世界各大博物馆所收藏,作为一位穷其一生也没有离开过小城的贫穷画家,这大概是他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出的境况。
在三楼的展厅里布置了光学实验室,用特定角度的灯光模拟出了维米尔画作中的神秘“打光”。维米尔作品中的光线一直是欣赏者们津津乐道的话题,据说他的“秘密武器”是显微镜发明者列文虎克亲自为他打造的黑箱,透过黑箱的镜片就可以得到一个绝佳的构图视角。
从“维米尔之家”出来步行几百米就到了市政广场,这里的格局似乎是在1000年前就已经形成。广场上视野非常开阔,南面是市政厅,维米尔不愿描绘其倒影的新教堂就与之遥遥相对。
说起来“新教堂”这个名字非常吃亏,让人以为是近现代的建筑,其实它已有了七八百年的历史,但无奈刚才去过的老教堂建于更早的13世纪,抢走了前辈的身份。好在新教堂凭借着100多米高的钟楼扳回了一局。
顺着新教堂塔楼异常逼仄的楼梯盘旋而上,一共379级台阶,光线幽暗,木板踏上去吱吱作响,有许多处似乎已经损毁,须小心绕过。我曾爬过北京中轴线上的钟鼓楼,75级台阶的钟楼当然高度要差一些,登楼通道也远没有教堂塔楼那么狭窄。在此处爬楼时我一直感觉前面游客的皮鞋掠过我头顶,像一种神秘的宗教仪式。由于上下楼通道仅此一条,随时有可能与下楼游客狭路相逢。一直爬到109米的平台,高度几乎与鹿特丹的EUROMAST(“欧洲之桅”瞭望塔)相当,而后者则是1960年代兴建的现代城市地标,令人不禁想象在漫长的中世纪,人们如何看待这座高耸入云的摩天塔楼,是否真的相信它能直达天听?



推开最高一层平台的木门,大风立刻在耳边呼啸,走上只可单人通行的甬道,视线开阔。这是代尔夫特数百年来的最高点,眼前景象一如影片 《戴珍珠耳环的少女》中所展示的17世纪的市景,到现在竟然没有什么变化。
脚下是市政广场,空旷得显出洁净,因为是冬天,跳蚤市场也没有开,可以清晰地看到对面市政厅的玫红色窗格。小城的红墙黛瓦沐浴在午后日光下,笔直的运河穿行其中,像一条动脉血管缓缓流淌。
环视四周,另一个制高点则是老教堂,五座哥特式塔楼耸立于不远处,但相比之下还是矮了一些。木心先生在《素履之往》中虚构了充满禅意的对话场景:深夜闲谈,托尔斯泰欲言又止,“我们到陌生城市,还不是凭几个建筑物的尖顶来识别的么,日后离开了,记得起的也就只几个尖顶”。接着木心总结道,地图是平的,历史是长的,艺术是尖的。漫步欧洲城市,这一点应该体会尤为深刻,因为但凡是有人文气质的古老城镇,市中心总会有几个尖顶,宣告此处是信仰的领地,而那风吹日晒的玫瑰窗间则回荡着艺术“黄金时代”的余音。
城市边缘的草场是一抹连绵的绿色,风车悠悠转动,周围当是风吹草低见牛羊的风光。目力所及是楼宇广厦的影子,但海市蜃楼一般模糊,分不清究竟是海牙还是鹿特丹。想必维米尔在世的时候一定曾在楼上踟蹰,在地势一马平川且无高楼阻碍的古代,他应该能俯视几乎在海平线以下的整个低地王国。
步行出新教堂时太阳已然偏西,我在市政广场附近寻找吃午饭的地方,跟着导航钻入运河边的一条小巷。也许我迷了路,道路越来越窄,游客越来越稀少,最后站在两堵红墙之间无路可走,眼前画面有点像维米尔的另一幅代表作《小街》。维米尔在画中描绘了再寻常不过的巷弄生活场景,两家相邻的弄堂房间陈旧而洁净,门帘敞开,隐隐露出洗衣的女人,还有坐在门前缝补的妇女和玩耍的小孩儿。这是一幅岁月静好的画面,甚至能让人想起那句隽永的古诗——“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恰好打开的那兩扇门几乎是通向逝去时光的窗口。
和维米尔笔下的少女一样,关于这条巷道是否真实存在的争论从未停止。最新资料是,阿姆斯特丹大学的一位教授从1667年代尔夫特小城的一份财政档案中查到,在整个小城中只有两家弄堂房是相邻而建的,也就是现在Vlamingstraat街的40号和42号。进一步的研究表明,这应该就是维米尔作品中所描绘街景的原型。
我没有刻意去寻找谜底所显示的地点,即便小街真的有原型,也早已湮没于历史长河中,更何况维米尔从来不是风景的真实记录者。在1654年,代尔夫特城中的火药库发生了大爆炸,一半城市被夷为废墟,伤亡人数上千,包括后世认为可能是维米尔老师的人选之一的法布里迪乌斯及其全部画作,都在那次大爆炸中化为乌有。仅仅几年之后,维米尔就创作出了《小街》,看不出空气中有任何波澜。前面提到的那幅《代尔夫特远眺》创作时间也非常接近,同样是如此的岁月静好,让人疑惑那场惊天动地的大爆炸真的发生过吗?它确实造成过什么影响吗?维米尔似乎刻意用画笔保存了他记忆中宁静美好的小城,它因而得以克服岁月的蚀刻,抵抗灾难与意外的降临。然而记忆并不可靠,那保存下来的不是任何一个年代的代尔夫特,而是属于维米尔一人的代尔夫特。
终于找到了那家人气颇高的汉堡店,坐在靠窗的位置可以看到外面静静流淌的运河,水草丛生的河面呈现出幽深的墨绿色,倒映出那些沿河民居,还有老教堂塔楼的一角,在荡漾的水波中明明灭灭,它们几乎是永恒不变的。还有一些匆匆的过路客如我般在某年某月某日低头看水的瞬间留下了自己的影像,破碎的,模糊的,短暂的,却无比真实。如果水真的有记忆,它应该会记下这一刻,并显然比爱憎分明的画家更令人信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