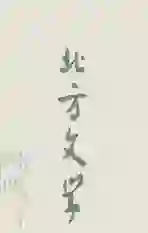孤鸟
2020-08-10王鸿达
王鸿达
宋福刚开始见到宋影时,感觉她并不是那么漂亮。当时就想,干那種事的女人咋会不漂亮呢?那会儿,宋福正和张云处朋友,情人眼里出西施……怎么看也觉得张云好看。宋福心里就时不时地想着张云,把一副挺垂怜挺复杂的目光,落在了这个女人的身上。屋里的光线有些暗淡。暗淡的屋子中间,是一把埋进水泥地里的铁腿圆椅。椅子又高又大,宋影坐在里面,身子小了一圈儿,像一个孱弱的婴儿,坐进一个铁制的洗澡盆里。她有五天没洗脸啦。这是进屋前,这里陪同的女同行告诉他的。女人观察女人最细心的莫过于仪表外貌了。说这话时,女同行脸上带着说不清的鄙夷还是嘲弄。果然,她的脸灰兮兮的,头发披散着,掩着半边脸;眼睛黯淡淡的,失去了光泽。若不是从鼻角游移出一丝若隐若现的白雾气儿,谁都会以为那是一团凝固的影子。三个人的屋里,一开始就成了无声无息的世界。屋里有点冷,宋福就把手抄进袄袖去。冰凉的水泥地面,挂霜的墙角返着潮气,还有一点发了霉的怪味。这中间,女同行出去了一次。回来,拎了一暖瓶滚烫的开水,给宋福倒了一杯,自己也倒了一杯。借水驱寒,身上稍稍有了暖意。宋福示意给她也倒一杯。女同行没有动。宋福也知道,给她,她也不会要的。就这样,不知过了多久,打小窗外跳进来一块风尘仆仆的阳光,成平行四边形落到地面上。屋里一亮!渐渐又成正方形状移上圆椅,像一束聚光灯,将圆椅里的影子照得清清楚楚。
后来,宋影就开口说话了,说:“我要出去走走。”
宋福拿眼睛瞅瞅女同行。女同行似有迟疑,但还是带她出去了。一同来到了大院里……
一下子完全暴露在阳光下,就觉得外边比屋里暖和。已是初春时节了,宋福想。高高的大墙背阴处,星星点点有未化净的雪堆,上面浮了一层脏污污的黑迹;下面是白花花的玉般冰雪化开的地方,就见有捂了一冬的蓬蓬草露出,在春风的吹拂下,摇动着枯黄的叶子。
院子里电线杆上,有几只晒阳阳的麻雀,蹦来跳去,挲着羽毛,悠闲地“啁啁啾啾”嬉戏着。见有人走到电线杆下,便“扑”地纷纷飞到附近的平砖房上。两只从大墙外面飞回来的麻雀,嘴上好像叼着什么东西,悠悠地落在了房檐上。又蹦跳了两下,钻进一块瓦里,不见了……宋影的两眼一直向天上望着。乍暖还寒,刚才,她虚弱的身子好像抖动了一下,宋福想不出,一个人绝食五天会是什么滋味。
“我想见见孩子……”宋影喃喃地自言自语,又像是对宋福提出要求。
按规定,被审对象未判刑之前,一般情况下是不准亲属探视的。想到她儿子还是一个不懂事的孩子。宋福就答应了。他看见她从天空中放下的目光亮了一下,苍白的脸上被阳光照得也有了一点血色。
下午,宋福去孤儿院领宋影的孩子。保育员喊了一声:“宋小军!”无人应声。看来他还没有学会怎样回答保育员的点名,或者压根就把自己的名字忘了。保育员只得走过去,在一群东张西望的孩子堆里,扯着衣领,带出一个五六岁的男孩来。男孩细细的脖颈支棱着一颗大脑袋,吃惊的眼睛怯生生地望着宋福。宋福见他脸上、脖子上挺黑挺脏,就把他领进屋去,打来一盆温水给他洗了。又叫保育员给他找一套干净一点儿的衣服换上。保育员不太情愿地,嘟哝了一句什么找去了。宋福当时只想着带孩子去见宋影,也没有去注意保育员嘟哝了一句什么。衣服换好了,宋福就带他走了。
他们一走进看守所大院,那个女看守就跑过来,告诉宋福,宋影中午开始吃东西了。说着,她眼里禁不住流露出惊喜的神色。宋福理解她此刻的心情,一种同行对同行的理解。宋福没有说什么,径自朝号子里走去。
半倚半靠在床上的宋影,突然睁大了眼睛!发疯似的赤脚冲过来,一把夺去了宋福手中的孩子。宋小军有些害怕,欲往外挣脱。宋福走上前去,说:“她是你妈妈,别怕,她是你妈妈呀。”宋小军就不动了,听任宋影搂在怀里低声号啕大哭……号子里还有两个女号,年纪都比宋影大。看到蹲在地上痛泣的宋影,她们露出鄙夷不屑的嘲笑,并不时向宋福打来淫欲流气的飞眼。过了一会儿,宋小军也跟着哭了起来。宋影便止住了哭泣,一边用衣袖为他擦去泪水,一边颤抖着嗓音说:“别哭,孩子,别哭,好孩子……”说着,抽搐着身子走到床边。从床被底下摸出两块巧克力糖来(真不知她怎么得来的这东西!);酱紫色的糖纸,揉搓得皱皱巴巴的,糖纸和糖块粘在了一起。她一点一点,小心翼翼地把糖纸抠去,塞进了孩子嘴里:“吃吧,孩子,别哭了啊。”小军停住了哭声,嘴腮一鼓一鼓地吮吸着糖块。宋影静静地流着泪,看着小军贪婪地吮吸……宋福觉得心头有点闷热,就走到了门外等着。分别时,小军又哭了。他紧紧拉着宋影的手不松开。女看守只好进去抱小军……“当”,铁门关上了。宋福的背后,能感觉到有张扭曲的脸,在小窗栏杆上拚命挣扎。
第二天,宋福又去了那间阴冷潮湿的审讯室。女同行眼里的目光由惊奇变为敬佩了……想不到这个又黑又瘦的小个子刑警还真有两下子。“……我是为了孩子,才做出那种事的……”每个人说到犯罪动机,都好像是出于迫不得已。因此,宋福也并没有往心里去……可渐渐的,他觉得她目光里有些异样,她交待完了,就用那种异样的目光期待什么似的望着他。“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宋福例行公事地问了一句。“我有个请求……”她犹犹豫豫地说了一句。“说吧。”“……希望政府能帮我照顾一下孩子……”她嗫嚅了半天这样说道。“你放心吧,我们会照顾好你的孩子的。”这是每个办案人员到这时都会说的一句话。宋福当时也这样说了。那双异样的目光闪了闪,就一直目送着他走出了小屋,目送着他走出了大墙门外。
墙外,阳光正好。宋福的身心顿时轻松起来。
在案卷送达检察院的前一天下午,宋福又来到了孤儿院。不知为什么,他忽然觉得应该到这里来看看。于是就进了一家商店,买了二斤巧克力糖果和一盒奶油饼干。买糖果时女营业员认识这个常在这里转悠的“老便”,就开他的玩笑:“给女朋友买?”宋福不好意思地笑笑,不作解释。宋福的女朋友张云,就在对面一家蔬菜商店上班,她们彼此认识。
马路两旁栽植的人工杨树林,已返青了,生出新绿的树叶。和煦的风儿吹来,哗啦啦,一路唱着歌儿。
暮春的午后,给人们的感觉,太阳总是暖洋洋的。沙滩上,一群戏耍的孩子,正在奔跑着打沙仗,沙土弥漫。宋福走过去时,看见两个男孩按倒了一个男孩。其余的孩子便往倒在沙坑里的男孩子身上纷纷扬沙子。“打,打他!”“他是杂种。……宋福拎小鸡状拎去两个男孩,别的孩子也停止了攻击,站在一边傻傻地看。宋福扶起被沙埋住的男孩,他是宋小军。
宋福领着小军去找保育员。“他们欺负他,你怎么不管呢?”宋福认认真真地问。那个年轻的女保育员正忙着织毛衣,头也不抬地答:“管不过来么。”宋福茫然地扫视了一下四周。
“怎么会是这样呢?”
“要么会是咋样呢?”
保育员仍旧头也不抬地织毛衣。他就站在旁边呆呆地看。保育员织错了两针,显得不耐烦,瞥了他一眼,认出他是上次公安局来的那人;上次本以为他们领走不会送来,谁知……不免有了难看的脸色:“谁能管,咋不管咧。”
宋福听了,愣怔了半晌,说:
“那么,我领走了。”
来这里领养孩子的多是些结婚多年无子女夫妇,看他也不像成家的样儿,她是想激他走开。一见他当了真,保育员有些发慌,领走孩子要经过院里,怕他……赶紧织出一副笑脸:
“何必当真呢,我们哪能要你管哟。”
“是我自愿要求领走的。”
他说得真诚。保育员不得不领他去办手续……见他没当人说三道四,也就放心了,直陪送到门口。“怪事。”望着一大一小远去的背影,保育员心里嘀咕了一句。
宋福把小军领到单身宿舍。宿舍的人见了,就问:“谁家的孩子?”
“宋影的孩子。”
宿舍的人知道他最近在办宋影的案子,便没再多问什么。宋福不知打哪儿弄来了一张折叠行军床,支在了他自己的床边。
宋福领小军到区机关食堂吃饭。机关食堂在分局后院,走七八分钟就到了。在这里吃饭的除了区政府干部,还有附近的公、检、法单身职工。吃饭的人多,就要排挺长的队,等半天。每回公、检、法来的人多,看见前头有穿制服的,就叫他(她)给大伙带出来。常常一人带十几个人的饭来,要后边的人等挺长时间,就有人翻白眼。大伙装做没看见,围在一起,你说我笑地热热闹闹吃。有时“三长”们(局长、检察长、院长)中午不回去,也加入到这个行列来凑热闹,倒也吃得痛快。叫那些整日坐在办公室里的人羡慕。宋福带了小军后,就不再叫别人打饭了。自己站在队里慢慢地排,然后陪他慢慢地吃。吃完也就是最后一个了。
“这是谁的孩子?”区机关里,有和宋福见面打招呼的人问。
“宋影的孩子。”
别人以为宋影是他的什么亲戚,开始没人去注意。带的时间长了,总还是叫人觉得有些奇怪。就向宋福的同事打听。宋福的同事就说了。吃饭时,排队的人群里,就有人直瞅宋福。还有的女干部指指点点小军……宋福被人瞅得不自然,就等人吃完了再去食堂。这样常常是十有八九没热炒菜了,只好啃咸罗卜条。看着小军吃得挺香的劲儿,宋福觉得长了也不是办法。
有一天,局长把他叫进办公室,对他说:“宋影的案子结案了,法院已判刑啦……”
宋福明白局长的意思。宋影因卖淫罪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他总不能领着小军在分局楼里住上五年。他也觉得很不方便。宋福就去找房产科要房子。区房产科在离区政府大院挺远的一座二层楼里。中区房子特别紧张,宋福早就听说了。他还是抱着试一试的心理去了。那个姓张的房管员倒挺实在,收下他的两条“大重九”后,就挺哥们儿挺神秘地对他说:“现在等房子结婚的排成一个加强团啦。要不这样好啦,等你登记结婚时,哥们儿就是头拱地,怎么也想法给你解决一间房子呵。”宋福当然说明白了他还没有登记,他是想现在要一间房子。听他这样说,心中有点生疑,会不会是虚晃一枪?“放心,到时你就来找我好啦。”他把宋福送到外门口,手握得有点生痛。宋福还是有点感动,放心地去了。
宋福和张云处朋友,见面的机会不多。因为宋福的工作没有规律,常常是没黑没白地连轴转。有时张云去宿舍找他,他不在。张云就叫宋福去找她。宋福就去了。都是赶在张云在班上的时间去的。其实,宋福也在班上,单帮跑“便衣”,就溜进了张云的蔬菜商店。
柜台里的张云,穿著一件青蓝大褂,头上扎着方方正正的白巾帽。宋福觉得挺好看,就呆呆地躲在人群中看上半天。直到买菜的人少了,他才走上前去,“你挺忙啊。”张云抬头见是他,眼睛一热,脸颊也不觉微微红了下。“每天都这么多人买菜吗?”“嗯,每天都是这么多人来买菜。”正说着,又过来买菜的人。张云就过去给人家称菜。称完菜又转身过来,镇定了许多。“你今天休息吗?”“没,我也在班上。”宋福含含蓄蓄地说,眼睛躲闪进了菜床上的大玻璃镜子里,瞥见有两个蓝大褂在窃窃笑语……“你们也挺忙呢。”“啊,挺忙的……”又有人过来买菜,宋福就说:“你忙吧,我走了。”……匆匆告辞。张云站在柜台里,端着秤盘欲言又止。宋福走后,同一个柜台里的姑娘就问:“那人是谁?”张云笑而不语,姑娘们就明白了。那人再来,她们就主动承担了张云的柜台,叫张云到后边柜台的出口处,同那人说话。张云就放下秤盘子去了,和宋福站在了一起。“你们挺忙啊。”宋福没话找话。“嗯。”张云看了他一眼,不再脸红了。“每天都是这么多人来买菜吗?”“嗯,每天都是这么多人来买菜。”空空两只细巧的手不知往哪里放好,就忸怩地绞手指头。“你还待在班上吗?”“在……”宋福就把目光往柜台里寻。三个人的柜台,突然少了一个人,柜台前就涌满了等着称菜的人。还有人向这边指指点点,小声议论。宋福便觉不自在,就说:“你忙去吧,我走啦。”就匆匆逃也似的离开了。她想再说一句什么,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走过去称菜了,脸上无可奈何地歉意地笑笑。
宋福带了小军后,局里不再安排他值夜班了。张云下了班,就去他宿舍。去时也不空着手,有时拿刚上市的红苹果有时拿从家新煮出锅的饺子。说是给孩子的,宋福就跟着“借光”。看着他们两人吃得狼吞虎咽,张云就跟着抿嘴乐。小军的衣服穿得久了,宋福也想不起洗。他的衣服从来都是家住附近的同事拿回去代劳的。张云见了,就说:“该洗洗了。”动手去解小军身上的衣服,脱完又对宋福说:“你的也顺便洗洗吧。”宋福就把积存的脏衣服拿出来。同宿舍的其他人上夜班去了。窗外的夜幕拉上了,室内安然、静谧。白炽炽的日光灯下,张云熟练地揉搓着衣服;小军趴在床上看给他买的儿童画册。宋福心头暖融融地涌起一股从来没有过的感觉……一种奇妙、温馨的家庭感觉。只是这感觉有点太突然了……
当张云接到电话,着实有点激动,连声调都变得有点语无伦次:“……下班以后,什么地方……公园……”那边电话已经撂了,她还紧紧握着话筒不放。这是她第一次接到约会的电话……下班以后,她着意打扮了一下。
宋福也是头一次约女朋友到公园来。他拣了个幽暗僻静的林荫处站下了。夕阳沉落进了人工湖里。湖面上有几对呢喃的倩影,悠闲地荡来荡去……当一个身穿白色连衣裙的纤纤身影,翩翩向他飘来时,他竟一时没有认出来。张云站住了,侧着脸,瀑布般的黑发随意飘散开来:“怎么,不认识啦?”宋福脸一红道:“你换裙子啦。”张云“扑哧”一乐。宋福也觉得说了一句废话。“好看吗?”张云红着脸问。“……”宋福一时也说不清楚。在他印象里张云总是穿着蓝大褂,去他宿舍也是穿一件宽松的蓝格罩衣。现在一换上薄薄透明的连衣裙,显得腰身很纤细,他就和张云坐到一条石凳上。石凳晒了一天,刚一坐上去就觉得热乎乎的。张云拿出一块手绢,要给他垫上。他慌忙摇手叫她自己垫上,他说他穿得厚。张云就自己垫上了。张云坐下以后,眼光就向湖里撒去,脸上现出和湖中人一样的舒适、惬意神色来。宋福一直想着那事,也就说了。
“张云,我想跟你商量个事。”
张云就收回目光,眯缝着眼睛看着他。
“张云,我们……结婚吧。”
张云睁大了眼睛,有点惊奇。
张云不说话……他就自管自顾地说起了他自己的想法。说到他负责的那起案子……说了他向那个女人说过的话。本来他可以不说,可是还是情不自禁地说了……直到这时他才忽觉有点明白,他之所以照顾小军,原来是在履行自己保证过的“诺言”。当时随意说出的一句话,不知不觉中沉进了他的潜意识中去。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清晰地浮了上来。说到房子,他说得很肯定很有把握,张云听到最后,低下了头,想了想说:“你看着办吧。”
……燃烧的晚霞退去,墨水一样的夜幕遮住了一切。石凳上的两个大龄男女的身影,热烈地相拥在一起……
那天,他们在公园里呆到很晚才离去。走时,张云还有点恋恋不舍,频频回头热望……对对情侣留在黑影里,旁若无人地相依相吻。张云就满脸羡慕和遗憾……他们这样的恋爱时光太短暂了,短暂得就像夜空中刚刚划去的流星,转瞬即逝。谁说的,恋爱是鲜花,结婚是坟墓。未免有些悲壮……走出公园大门口,宋福觉得有点对不起张云。后悔不多带她来这里几趟……
宋福把结婚登记证放在姓张的房管员办公桌上。张房管员吃了一惊。他没想到这个小警察办事这么利索。他以为结婚这种事情哪能说办就办呢?他一边叼着“喜烟”,一边连声道:“恭喜!恭喜!”便也没再含糊,从抽屉里拿出一把带锈迹的钥匙。分房子的高峰在秋天,如果等到那时,这把钥匙不知要属于谁的了。走出房产科大门,宋福想。
房子在西下洼子。是一间只有十五平方米的单屋。一进门,用板壁隔开了个小厨房;再进去就是稍大一点儿的里间。从墙上斑剥的墙皮,能够看出房子有些年头了。由于急着住,搬进来也没修理一下,墙壁也没刷,屋里有些暗。他和张云睡的床是从宿舍临时搬来的两张单人铁床,拼在一起的。搬小军的帆布折叠床时,宿舍里的人不让搬,说是头一宿,让他俩儿好好亲热亲热……让小军先在宿舍里住两天,再搬过去。但宋福还是执意一同搬过来了。
早晨,宋福先醒了。穿鞋下地,看看那边地上行军床里的小军还在睡,就又回到床前穿衬衣去了。昨天夜里,他没敢太任性用劲,铁床腿“吱呀吱呀”地叫唤,他怕惊醒了小军。尽管这样,张云还是感到兴奋。醒来,两眼奕奕地望着他。他用眼神示意该起床了。张云就兴幽幽地说:“你给我找条衬裤吧。”宋福就去找了。回身看见张云的一条白细的腿伸出被外,就一阵热热地往上涌。他放下花衬裤,侧卧上床,手伸在了张云光滑的身子上。张云用眼睛看了看地下。宋福顷刻间控制住了自己,下床走出门去。晨风一吹,他觉得凉爽多了。
宋福打量着屋前。屋前是一块不大的菜园子,周围还用板条圈上了。园子里没种什么,黑土硬硬的,只长着一棵沙果树。上面不见有果子,大概被搬走的那家摘去了。绿绿的叶子还挺密,晨風一吹,就欢欢地摇,像是在欢迎这家新换的主人。宋福懒赖地伸了个腰,觉得舒服极了。心想,毕竟有个自己的家了。
第二年,屋前的沙果树开花时,宋福领着小军去学校报名。宋小军已经八岁了,该让他上学了。宋福这样想。经过一年多的营养,小军长胖了,皮肤变得白白净净,眼睛黑黑的,挺招人喜欢的。
在教导处,每个领孩子来报名的家长都聚集在这里,等着填报名登记表。轮到他时,负责填写登记的人就问:“宋小军的家长叫什么名字?”他迟愣了一下,所有的人便都瞅他。“您是宋小军的父亲吗?”那人这样问了一句。“嗯……是。”“请问您姓名?”“宋福。”“工作单位?”“区上公安分局。”就见有人投来羡慕的目光。“他母亲姓名?”“张云。”“工作单位?”“……。”卸去了包围的目光,宋福就松了口气。
回到家里,他对张云说:“以后叫小军管你叫妈妈吧,管我叫爸爸吧。”以前小军只管他叫“叔叔”,管张云叫“大妈”。从这天起,小军就管他叫“爸爸”。叫得真真切切,他听了也觉得比以前亲切些。叫“妈妈”时,张云听了,愣了一会儿神,半天不大自然地答应了。宋福看见了,就说:“还是叫大妈吧。”小军就叫“大妈!”,张云很快就答应了。
宋小军每天放学,宋福都去学校接他。没到下课时间,就在门口等一会儿。有熟人碰上了问:“你的孩子也上学啦?”“嗯,上学啦。”他答。问的人就一脸猜疑。
回来,张云已做好饭了。一家人就团坐在一起吃饭。饭桌上,宋福边吃边问:“今天老师教了几个什么字?”“做、人、爸、妈、年……”小军就边吃边答。张云也把从别人那里学来的智力开发“测试题”,拿来问小军:“一棵树上有十只鸟,一枪打下来一只,还剩下几只鸟?”小军歪头想了想答:“没有啦。”张云就高兴了:“真聪明!”宋福想起小时候,也有人这样问他,他当时算了半天才回答:“还剩下九只鸟。”别人就笑他傻。他问人家为什么?别人就说:“还不都飞啦。”他还憨乎乎地问:“要是不飞走呢?”别人愈加笑他痴:“哪有不飞走等着送死的鸟啊。”……是啊,想想,就觉得好笑,自己那时真的没有小军这样聪明。他不由得傻傻地笑了……
知道底细的人,悄悄地问张云:“你们不打算自己生一个?”张云听了,觉得不好回答,就笑笑,没作声。回到家里,小军不在跟前,张云就跟宋福说了:“别人总问,我们也生一个吧。”宋福听了,想了想说:“等等吧,要不再生一个小孩,事情就多啦,怕你照顾不过来。”宋福望着她单薄的身骨说。张云也知道他“等等”的意思……就没有再说什么。
好像真的说中了,说不要就不要。就真的没有出现过“意外”。其实他们并没有认真地采取什么重要防范措施,只不过是心理犯禁罢了。有时宋福连上几个夜班,回来难免会进犯“禁区”的……倒也相安无事。听人讲,体格弱的女人,做一次“人流”会死去活来,恐怕再也难怀上孕的。因此,也不觉着有什么压力……
树上的沙果熟透了。红红的,染红了树叶,把枝头都压弯了。小军就去摘。他蹦了几蹦,没够着。就回屋取出一只方凳来,踩了上去。这回够着了,他用力拉过一个树枝,一只手握住枝头,一只手往下摘沙果。……手里的沙果拿不住了,刚要往兜里放,握着的枝头猛地挣脱了他的手,他一闪从凳子上摔了下来……
中午下班回家的宋福看见了,赶紧抱起他上医院。医生给他看了X光,说:“左胳膊骨折啦,得需要住院治疗。”刚从商店下班的张云,也满头大汗地跑来了。她推开房门,就听宋福自悔地说道:“……怨我,早摘下来好啦。”“爸爸别难过,是我自己不小心的。我是想摘给大妈吃的。”张云听了,这才猛地想起早上说过的一句话。早上,她一出门看见满树的红沙果,有的都裂了缝,就咂咂嘴说了句:“真馋人哪……”看看表,上班时间到了,就急急忙忙上班去了。想不到她随意说出的一句话,却被小军听到了,放了学就……她眼圈一红,扑上前去,把小军的头搂在怀里。
张云向单位请了假,在醫院里护理小军。宋福白天抽时间跑到学校去,问老师当天讲了哪些内容,然后晚上再到医院里照着书本给小军补上。小孩的骨头长得快,一个月后就好了。这样课也没耽误。
小军上到三年级时,宋影被提前释放了回来。局长把宋福找到办公室,告诉了他。宋福听后竟呆头呆脑地说了一句:“怎么会是这么快呢。”当时,局长很古怪地看了他一眼。
不管怎么说,小军要离开他和张云,这是事实。
在司法局刑满释放人员安置办公室,他把小军领了去,与那女人见了面。从家来时,小军还不知道将要发生的是什么。宋福和张云都不太忍心向他详细说明这一切。四年多过去了,小军不认识那个女人了。那女人也有点变样。听说她在北安革志监狱被服厂服刑,工作得挺不错的。司法局的人宣布完后,那女人就向他和小军走过来。小军听到自己名字时,似乎明白了眼前将要发生的是什么。他紧紧拉住宋福的手。那女人先是感激地看了他一眼,恭恭敬敬地向他行了个鞠躬礼。然后就急不可待地去拉小军的胳膊,并轻轻地急切呼唤小军的名字:“小军,小军,我的孩子。”
他本能地蹲下身去,抱紧了小军。那女人有点儿惊讶地看着他,张着两手不知所措……
“小军,去吧,她是你妈妈……”
“不,我不去,我不要!我要跟爸爸回家。”
小军“哇”地大哭起来。引得所有的人都向这边看来。那女人含着泪水,向他投来艾怨嫉妒的目光……
他的眼圈也红了,一时说不出话来,深深埋下了头……
那女人又过来拉小军。宋福感觉到胳膊上,小军的指甲深深地嵌进了他的肉里。他麻木了,听凭那女人将小军抱起。趁小军没转身的工夫,他“噌”地站起身跑了出去。
远远地,还能听到背后传来的小军的哭声,两行无声的泪水,从他脸上哗哗流了下来。
一连几天,他回到家中,觉得空落落的。干什么都没劲,眼睛老往那张空空的行军床上落,一看就是半天。张云叫他吃饭,他嘴里答应着,身子却不动,还在等。张云拿着两只碗,两双筷子上桌;他就好奇地看上张云一眼。看得张云心里也怵怵的。张云忙不过来,叫他拿碗拿筷,他就拿三只碗、三双筷子来,还习惯地按三个不同的位置摆上。引得张云想发笑,又笑不出来。她心里,也有点想……
过了些日子,张云就把行军床撤了,折叠起来放在了床底下。宋福的眼睛还总爱往那块空地瞅。家里少了些话语,闷闷的。张云就想,该有个孩子啦,有了孩子也许就会好的。
想着,也就对宋福说了,张云本想他听了能够开心的。“该有个孩子了……?”他听了,半晌才茫然地说了一句。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询问张云。以后几天,也并不见他怎么开心……行动也迟迟的。张云也不管不顾,一心一意地做着自己想做的事情。把原来每月周期中的“禁区”,变成了“选区”。月月盼着“选区”的到来,这样日子也就不知不觉过得很快。
有一天,他去宋影家看小军。小军还没有放学,他就站了一会儿。在这之前,他曾去过两次,见是见到啦,只是小军一见面,就跑过来喊他“爸爸!”他就惶惶然的,看那女人。她也一脸惶惶然。“这孩子……”他不知说什么好,就匆匆告辞走了。
“小军这段时间还好吗?”
“还好。”女人低着头回答。
他又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女人叫他进屋里坐,他就进屋去坐了。炕上有他熟悉的被褥,刚拆过,干干净净的,散发着浆洗的气味。
“他还常起夜吗?”
“大啦,不常起夜了。就是……”
“就是什么?”
“就是……夜里常做梦哭醒喊爸爸……”女人欲言又止。
宋福听了,心里怪热得慌,忙移去了眼光。
“这孩子。”
“叫习惯啦。”
“嗯,叫习惯啦。”
宋福感到轻松了点儿,就细细打量着屋里。这是一间平顶土屋,屋中间盘着土炕。是街道上给盖的。他转了话题:
“街道上有活儿干吗?”
“没,还没有。”女人脸上隐隐浮着愁云。
“要不,摆个台球案子吧。”宋福想起在区上文化部门有个熟人,这类执照归他们管。
天在外面不知不觉地黑了下来。屋里灯泡明晃晃的。小军听着、听着……就睡着了,脸上凝着兴奋的光晕。小巧的鼻翼、微微上翘的嘴唇,送出均匀的鼾声……看着,看着,他又坠入了一种熟悉的幻觉中……
模糊的视线里,出现了高挺挺的胸部……她不知道什么时候走了进来,正愣怔怔地立在那儿,看着他。目光有些异样……莫名其妙的感觉碰在一起,他浑身燥热,引起一股强烈的冲动,顿时头晕目眩了起来……
“我,我该走了。”他跌跌撞撞地说。
从她身边走过,一股粗重的酒气,热烈地扑来。摇晃了两下,她扶住了将要跌倒的他。
“醒醒酒,再走,好吗?”她柔柔地关切说。刚才,她忘了给他倒茶水了。
燥热得难受,他怕控制不住自己,没有应声,挣脱了直直地往外闯。冷风一吹,好了点。
她跟在他后面,送了好远,夜幕裹去了他的身影。她还在路边远远地望着,内心涌起一股说不出的热潮,眼窝也热涟涟地湿润了。她在那里站了很久、很久。
回到家,张云还在等他。桌上的饭菜热了几次……摆久了,就懒懒地没有了热汽。
“……小军今天得了100分。”
“我以为你今晚有任务……”
“那孩子又长高了。”
“我出去给你们单位打过电话啦。”
“你吃饭吧。”他有些过意不去。
“不太想吃了……”张云说着,就恹恹地吃了两口,放下筷子,草草地收拾了。
然后,就早早地铺好床被,早早地躺下了。宋福的酒劲还没有退去,身子还热热的。他就把手向张云身上摸去。
“她挺漂亮的吧?”
“谁……”
“宋影。”
“……”他放在张云身上的手停住不动了。
“她比我好看,是吧。”张云拿去他的手。
“别说啦……”他低低地有些哀求。
“你不让我说,心里就是那样想的,她比我漂亮……”
“我求求你,别说啦……”他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你就是那样想的……”张云嘤嘤地哭了,瘦削的肩头和被子一起抽动。
他的脑袋发涨、发痛,一针、一针扎得似的,就扯过自己的棉被,蒙头盖上了。
早上起来,他和张云都觉得有点儿不自然。慌慌的,面面相觑了一眼。想说点儿什么,又谁都没开口先说。如果说话,就好啦……遗憾,各自匆匆忙着上班去了。
上午,宋福一直没离开过办公室。他坐在办公桌前的靠背椅子上,眼睛向外望去……显得有些发呆。办公室里谁和他开了一句什么玩笑,他也没注意去听。下班的时候到了,人都走了。誰走在最后还问了他一句:“中午不回去了?”他听见了……他当时并没有打算中午不回去。只是想一个人静静地呆一会儿,再回去。这样就看着太阳从正中的窗格子里射进来,照在黑色的桌面上。他就想再等一会儿。
小刘喊他时,他刚看过表不大一会儿。看表时正好是中午十二点。
值班的小刘在空荡荡的走廊里跑,急急的。看见敞着一个门,也没停下,冲他侧影喊了一声:“老宋,快!前天省厅通缉的持枪杀人抢劫犯,有人在铁东看见了……”他门也没关,就跟着跑去了。
……在铁东一处未施工完的楼房建筑工地上,就看见那人了。那人顺着楼外面没安装扶手的楼梯磴往上跑,窗户也没安窗框,那人跑进一个最上面的窗洞里,就拿枪往下瞄。宋福也拿枪往上瞄。“啪!”枪就响了。在枪响的同时,宋福顺着枪口准星,清楚地看见,有两团黑影箭一般从窗洞射出。一前一后,前边的黑影就撞在了宋福射击的弹头上。炸出一团伞状的羽毛来,飘飘悠悠落下。刹时,后边的那团黑影像钉在了半空中,冲着落下的黑影“啾啾”哀哀地叫。正午的太阳很亮,亮得有些刺目。就在宋福觉得奇怪空中那团黑影为什么不飞走的四分之一秒时间里,胸口被烫了似的一热!太阳晃了几晃,没有掉下来。掉下来的却是一个张牙舞爪的黑影,喷着黑红的血,重重地压在那只弱小可怜的黑影上。他的思维就定格了。“老宋,老宋,你怎么啦?老宋!……”小刘拼命地喊,他也没听见。留在他最后记忆里的是:落在地上的麻雀,是他无意打掉的。落在地上的男人,是小刘有意打掉的……鸟为什么不飞走?看来鸟并不是都怕死的……
火葬场里,穿着孝服的宋小军,抱着一只精制的骨灰盒走了出来。他嗓子哭哑了,哀哀地张着嘴号噎着。
“他是个好男人。”宋影凄凄惨惨抽泣着。
“……都怪我……他要是不生气……中午就会早回来的……一定会早回来的……”张云两眼失神地望着高高的熏黑了的烟囱,怅惘地念叨着,“他走了,他走了……”那上面,刚刚冒出过一股黑烟,化作一块黑云;停了一下,就悄无声息地轻轻飘逝了……
地上,对着骨灰盒,小军垂着头,在烧他一张一张积攒下来的,打着红红100分的试卷。片片纸灰,轻盈旋舞着飞向天空。两个女人跪在地上,抱头恸哭在一起。
局长叫政工科长把宋福的材料整理一下,按烈士往上报。政工科长整理完了,就拿给局长过目审批。……局长的目光久久地停留在一份履历表上:宋福。男。40岁。“父母”一栏空白着,出身:孤儿院……
(原载《北方文学》1991年第3期,责任编辑:孙苏)
作者简介:王鸿达,笔名洪荒。一级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黑龙江省作协签约作家,鲁院高研班十三期学员,黑龙江省作家协会副主席。1982年开始创作,已在《人民文学》《当代》《中国作家》等刊发表长、中、短篇小说四百多万字。作品多次被《小说选刊》《小说月报》《人民日报》海外版转载。作品曾获东北文学奖、金盾文学奖、中国人口文化奖,多次获得黑龙江省文艺大奖。部分作品被译成英、法文介绍到国外。
《孤鸟》被《人民文学》1991年7-8期合刊选载,获首届东北文学奖,并被改编成电视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