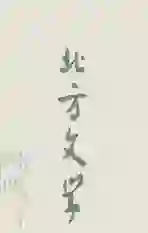空谷手记
2020-08-10包临轩
包临轩
逆 光
当黎子在我面前停下脚步时,我意识到这不是一个人的出现,而是往昔出现了。
往昔不再遥远模糊,而是清晰得可以触摸,当我握住他的手,甚至想要扶住他微微颤动的肩膀时,我觉得往事正在抖落时间的织物和灰尘,露出了久违的面容。
黎子是我初中时的学长,大我一岁,高我一个年级。我足足有二十多年不曾见过他,不是我们相见不易,也不是我不想见他,而是他不肯与我相见。
在我的少年时代,黎子的作文出类拔萃,人也帅气,一头卷发。讲话时,语气和音色皆雅致,彬彬有礼,在我们学校是一个传说。据说他本人也很骄傲,一般人是靠不上前的。但是我从未读过他的作文,不知道优秀到何种程度,但是也和其他同学一样,觉得他肯定厉害,所以也不免有了结识的愿望。正好有一个机会,学校搞一次演讲解说活动,一共选四个人,我也入选其中。我记得当时他笑吟吟地向我走来,和我打招呼,我俩就成了要好的朋友。
共同的志趣和愛好,使我们无话不谈。但是那时刚刚恢复高考,中学生们都开始磨刀霍霍地准备考大学了,黎子也开始陷入忙乱,一头扎到对高考的准备中去了,这样我俩就无暇见面了。后来,我从初中考到县重点高中去了,离开老家,奔赴县城。从那时起,好多年过去了,我上大学,毕业后参加工作,我们就再也没见过面。但是我一直惦念着他,时常想起他,想起风华正茂、一心一意想在文学上有所成就的黎子,他过得怎么样了,活得还好吗?
黎子活得不好,我是从其他同学和老乡这些间接渠道得知的,他们讲得零零碎碎,我只能自己把这些信息碎片拼接起来。黎子参加了高考,但是很不顺,他的语文成绩特别好,但是数学零分,这样他的总分就被拉下来了,仅以一分之差,未能达到录取线而名落孙山。不知是什么原因,他未再继续复读,而是参加了工作,不久又结了婚。婚后他的妻子得了一场大病,卧床不起,好像直到如今仍是如此。他在最难的时候,不得不去蹬三轮,给妻子治病买药,补贴家用。我想,蹬三轮对这个当年心高气傲的英俊少年来说,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单是那一个“蹬”字,就会令他的自尊心碎了一地。后来他和我说过,蹬三轮可以在平地上飞也似的前进,但是遇到陡坡就很吃力,下坡的时候还得控制好速度,避免翻车。控制下坡的技巧,和滑雪下山时的控制奥秘差不多。他居然想到了与滑雪的类比,令我吃了一惊。就我所知,我的老家处于松嫩平原的核心地带,可谓一马平川,连个山的影子都看不到,绝大多数当地人不可能知道滑雪是怎么回事儿。难道黎子会滑雪?但是我没敢问,我也不认为滑雪下山与蹬三轮下坡真的能有一比,我更倾向于这是黎子的一个主观想象。我不可能去问他蹬三轮的酸甜苦辣,那一定是他心中的隐痛,他也不会在这段情节里过久地停留,虽然他对我并不怎么避讳这一经历。他说,我不可能抛弃妻子,不仅仅我们的恋爱过程是美好的,还在于后来她病得最重的时候,已经不怎么认人了,但是却始终能认出我,只有我在她身边,在她面前出现,她才会安静下来。甚至只要听见我的声音,她也会从惊慌不安中挣脱出来,变成小鸟依人,紧紧依靠着我。我感觉他是深爱着妻子的,这份不离不弃、始终坚贞如一的状态,在他那里是极为自然的事情。这位当年的英俊少年,成了爱情世界里的一个白马王子。
黎子打了很多工,也一直在寻找着一份适合自己的工作。蹬三轮不可能是他干得很长的活儿,他将自己的文学爱好放在何处呢?他是否写过小说散文之类呢?我一直没敢问他,他也从不提起。但是他的这份热爱还是在小小县城派上了用场,慢慢地,他成了一名婚庆司仪,主持大大小小的婚礼,他的儒雅风度,他卓异的文采,使得他的婚庆主持在当地名声大噪,生意最火的时候,连周边的市县、大庆、齐齐哈尔都有人慕名来请他,他的经济状况和生活也慢慢好了起来。
但是一件看似偶然的事情改变了黎子的事业轨迹。一天,他交往甚密的一位好朋友,因为一场车祸意外去世了,朋友的家人陷入巨大悲痛之中,整个丧事就全权交给他来办。他自己当然也觉得责无旁贷,怀着同样的悲痛心情,他忙前跑后,还在朋友的葬礼上致了一段告别辞。令他没想到的是,他的致辞打动了在场的所有人。的确不可能有人比他表达得更好。从那以后,遇到白事,找他的人越来越多,一传十,十传百,起初他只是帮忙,有时也却不开情面,也没收过什么费用。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红事司仪的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他就转到了这一行,虽然内心并不怎么愿意,但是同样又很快做得名头越来越响,远近闻名。人们似乎忘了他出道时本是红事司仪,如今不得不成了专事白事的司仪了。
黎子后来说,成为白事司仪,虽然并非本意,当时觉得谁家里遇到这类事,不仅悲痛不已,而且往往都陷入茫然之中,这时不施以援手,也说不过去。做司仪多年,对行业熟悉,虽然红事白事是人生的两个极端,挨不到一起,所涉行业完全不同,但是这事情毕竟都涉及场面,他对场面是能够把控的。所以一开始客串、帮忙,并未想将其当作一份职业,感觉是被推着走进这一行,及至入行,他便很认真地做了。
我后来终于知道黎子在我的老家及其周边地区,成了一个著名的白事司仪了,这样我们反而更不好见面了,因为我从未忘记他的少年时代,从未忘记他对自己文学梦的那份痴迷,如今他阴差阳错干上了这一行,绝非他的本意。一找他,总会不免触及他的旧伤和隐痛。如果他想联系我,其实是很简单的事情,因为我们共同的同学不少,但是他没有和我联系,他的心情一定是极其复杂的。我也听同学说,黎子一直斯斯文文的,但也相当洒脱健谈,他的谈吐魅力是大家公认的。但是他对每一个事主,每一次白事,又都是极其认真负责的,在小小县城,巴掌大的地方,只有一条主街,人们大都是熟悉的,所以当某一个人不幸离世,黎子往往对他们的生前是略知一二的,但是他从不因此敷衍,每次都会赶到逝者家中,和家属进行适当的交流。他在主持告别会上,那份凝重和严肃,不是表演,他的主持词都是个性化的,没有套路,没有装腔作势,每一个逝者,似乎都是他熟悉的故交和亲友,他不是简单地代替家属说话,他是在讲述一个人曾经的生活,他经历的事情,他给这个世界留下的痕迹,他最美好的心愿和祝福是什么。他的致辞有代入感,但是不会有职业化的煽情。在同学的讲述中,我能够看见黎子在那种肃穆场合的样子,他的一头卷发依旧,但他的英俊之气已被时光所侵袭,因而多了几分沉郁,他的语气已不再是清亮激越,而是和缓如深秋山涧的溪水,下面站着的那些逝者的家人亲友,静默如夕照下深黑色的石林,冷峭凄清中却有一股难以诉说的温情从心底流过,而黎子的声音,正是那温情的源头。
黎子想对我说的或许是,我看尽了人生的另一面,消逝,但却从未习惯过那种消逝。每一次人的消逝,都不是重演,也不是重复,而是一次又一次的全新事件,是一件事情的再度发生。每一次主角都不同,观众也不同。每一个即使最卑微的生命,从未站在舞台中央,或者压根就不曾登上舞台,但是当他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就是主角。不仅仅在他的亲人当中是这样,不仅仅在葬礼上是这样,在我黎子的心中,也是这样。当然,在婚礼上,人也会成为主角,所以,人的一生,无论贵贱,大约都有两次成为主角的机会。但是婚礼上的主角,是两个人,你的伴侣在,你非但不孤独,反而是幸福;而葬礼,则只能是一个人成为主角,成为最后的孤独前往未知世界的主角。所以,两次做主角,第一次是喜剧,第二次是悲剧。但最成为人生憾事的,是鳏寡孤独者,生前死后,似乎都不曾得到过眷顾,甚至人们都不知道他们来过这个世上,他或他们没有最后的时刻,因为那一时刻已经永远失传。所以,每一场葬礼,我都是怀着一颗对生命的虔敬之心,去做好本该做好的事儿,而这,也应该是一个职业司仪的分内事。司仪,假如用心去做,他就不只是一种程序的代言人。
真实的黎子现在来到我这里了,和我见面。他说你不知道我有很多次来到你的办公楼下,向上面张望。我甚至问过门卫,哪一间办公室是你的,或者,你是否就在里面办公。但是我一次也没有走进去。你是我少年时代最好的朋友,你走到今天的每一步我都是了解的,我甚至都不用见你。我觉得你就是我,你已代替了我,你写作,就是我写作,你谈诗歌,就是我在谈论诗歌,你延续着我少年时代的梦,一直是这样。而我则留在原地,代替着当年的我们。文学是我的梦,也许我从未实现它,也许我是换了一种方式,我把对它的一腔赤诚,写在了许多人的生死关头,写在了人生悲剧的时刻,悲催的时刻。它们不是散文、小说,只是一篇篇悼文,一篇篇告别辞,但是,它们是至真至纯的。但是担心你不能理解这些,我自己也常常不能理解我自己。我就是一个白事司仪嘛。
那今天为什么来见我呢?我有些困惑了。黎子说,不来找你不行了,需要你帮忙。这时,黎子那清秀的面容,浮上来的是焦虑的表情。是的,焦虑。黎子说的情况是,他的业务遭遇了重大挑战,挑战者是几个年轻人,他们组建了一家与白事相关的公司,采取低价位、强公关等方式,大肆掠夺黎子的固有市场。黎子一开始没怎么重视,但是后来不行了,他实在无计可施,便下定决心来找我了。黎子如果不走投无路,是不会来找我的,他是用尽了一生的气力来见我的。我明白,黎子老了,时代变了,后浪要把前浪黎子拍在沙滩上,黎子的时代就要被结束了。
但是黎子不服,他当然不服,但这是大势所趋,我没法讲什么大道理,只能尽自己所能。我开始打电话,找朋友,给黎子出主意。我不是在帮他,我是在帮我自己。我和他共同的往昔,是那样纯粹而美好,让我出手拯救我们共同的少年岁月,勉为其难。但是想想吧,在时光开始的地方,那两个怀揣美好梦想的少年,走在小镇破败的土路上,惺惺相惜。我们都把自己定格在那里了,我用回忆,黎子用的,却是一生。
黎子的事业无论怎样都不可能重返往昔了。他回到县城继续度日,身体每况愈下。他需要的是事业上切实的帮助,而我却做不了更多,心中同样是焦虑的。但是我们都不可能坐下来再像小时候那样交谈了,我后来驱车回去看过他,但两人只能是默默地坐一会儿,开始说一些无关紧要的话。这时我感觉他家宽大的窗子,正在被夕照慢慢染红,让兄弟两个,都成了剪影。
黄房子
色彩已经变得极为斑驳,不再柔和,不再协调。甚至也不再是房子,而只是房子的轮廓,是断壁残垣的前奏,是废墟的初始形态。然而,摄影家还是在它的身前身后徘徊,不时地把相机举起,他还能拍到些什么呢?
他是慢慢注意到黄房子的,那时他还年轻,刚刚来到这座城市。他在大街上闲逛时,累了,走进街边一家冷饮厅,坐下来。起初他并未觉得有何异样,但是在他座位面对着的木刻楞墙壁上,挂着一幅俄罗斯风格的老照片,一位异国女郎也是像他这样坐着,正在端着一杯咖啡,目光望向窗外,一缕黄昏的余晖飘落在她姣好的面庞。而画面里的桌椅,和他此时享用着的桌椅,颇为相似,这一发现引起了他的注意。他叫来女服务员,一位胖胖的阿姨,问这幅老照片的来历。对方说,照片拍的就是这里,是她老父亲一直保存下来的,然后放大了挂到了那上面。岂止是照片里的桌椅,照片的里里外外,都是这座老黄房子的故事在延续,他忽然悟到了。他于是从冷饮厅出来,到外面打量这座建筑的外立面。这时他才发现,这是一栋俄式米黄色小楼,精巧别致,但是窗棂和大屋顶则是绿色的。这黄绿相间的楼体,与周围的那些高楼大厦的庞大灰色、千篇一律构成了巨大的不和谐,这栋小楼显得形单影只,仿佛随时可能被轻轻抹掉。
后來的事实也越来越证明是这样,摄影师从他的拍摄经历中慢慢懂得了这一点。他便开始拼命拍,不间断地拍,开始搞专场摄影展,开始四处奔走呼号。但是黄房子却越来越破败,越来越减少。他自己和黄房子,和自己的老相机,老去的速度似乎有点快。正逢四月,谷雨已经过去了两天,不见雨下来,却下起了漫天大雪,仿佛正值隆冬一般。黄房子和整个城市一样,也陷在大雪里面,而且它比那些高楼大厦陷得更深,雪中的黄房子,甚至不如不远处那些埋在雪中的汽车,人们一边哭笑不得地清雪,把汽车从雪堆里扒出来,一边堆着雪人。但是没有谁向废弃多年的黄房子这边投来一瞥,不会有人上这边来清雪的,只能任它在大雪中独自煎熬。
摄影师在停止拍摄的时候,会默默想到许多。他想,这些住过人的房子,曾经多么美,现在没有人住在里面了,只剩下孤零零的墙体,没有人在了,没有了烟火和灯火,但是房子还站在这里,它就是一种提示,这里面,曾经有过喜怒哀乐,悲欢离合,房子就是往事的纪念碑和遗物。一百多年前,这些当年的黄房子,作为中东铁路的伴生物,星罗棋布般出现,不是作为风景,而是生活的居所,是铁路高级职员的一栋栋家宅,是人们的日常。为什么随着时光的流动,它们变成了稀罕物呢?
稀缺。
壁炉还在,里面燃烧过的木炭已经熄灭,而且无迹可寻。走到院子里,房前屋后各有一个花园,种植着果树,木桩子被削得尖尖的,排成高度在一米左右的篱笆,圈出一个整齐精致的小世界,一个独立自足不受干扰的居家生活。可是这样的场景,只可能存在于遥远的旧日子里。摄影师想,像他这样怀念这些的人都在哪里呢?除了他自己。
他看到黄房子的院落里,杂草丛生,废弃物遍地都是,无人清理。也不可能看到完整的老房子,因为一直有灰铁皮围拢着,这块特殊材料制成的超级遮羞物,像一条勉为其难的短裤头,无法真正挡住墙面出现的一道道裂隙,那裂隙是越来越大了。他觉得这灰铁皮不仅遮挡不住老房子走向破败的颓势,也遮挡不住试图提供保护者的那份勉强、无奈和耻辱,虽然他们误以为自己似乎是做了点什么。摄影师有些恨恨地想,他们不过是在尽量拖延罢了。
摄影师接待过一些从外地赶来的黄房子爱好者,和喜欢画点什么拍点什么的慕名者,他们在网上发图发文发视频,有一些微弱的呼吁和建议,像他做过的那样。他们因为黄房子的因缘聚在一起,成为朋友,但是或热烈或忧心的谈论之后,就只剩下唏嘘。他们发现本地的一些机构也不是什么都不想做,公道地说,他们在做,但是他们却把事情弄得更加复杂,思维变得越来越奇特,就好像忘了为什么要干这件事。不是说要保护黄房子吗?他们给它命名,花园街区、老城1898、历史建筑文化街区,等等。但是多年过去,却迟迟没有下文。
黄房子是个不正规的名字,是一群少不更事的小青年给起的,也不能说不对,他们说出了这些为数不多的老房子的大致颜色,这米黄色甚至也是这座城市的色彩基调,但是这种说法遗漏了许多,譬如除了黄色,与其搭配的绿色,那也是相当醒目的,不可以忽略的。甚至,房子本身的提法也过于简陋,那不是简单的房子,那是建筑,不但有着居住功能,而且是立体艺术,是这块土地上很少能见到的一小段凝固的音乐,是一幅安静的画,类似水彩或者油画。甚至也不光是房子本身的事儿,那是个由房子、栅栏、花园和门组合到一起的院落,房子不过是中心点,院落才是它完整的格局。但是也不只是院落,这些房子不是一栋两栋,而是成行成排的,是一大片街区。和机构相比,摄影师觉得自愧弗如,他不过是转转悠悠,拎着相机,东拍西拍而已,机构的眼光当然是更高的,更全面的,他们雄心勃勃,他们从黄房子构成的街区看见了机会,尤其是商业机会,他们更乐意将其称为城市升级改造,更喜欢超级大手笔,于是有了宏阔的规划,搞出了招商引资大项目。最重要的是,他们把黄房子里的住户清空了,把私建滥建、违章建筑一股脑清空了,动作非常快。这时,黄房子们得以从建材大市场的乌烟瘴气中挣脱出来,裸露出来,它们不是一个两个,而是一个群落。但是它们只能各自呆在各自的老地方,彼此已经无法发出重又相见的欢喜叫声,一百多岁的它们,再没有那样的力气了。它们中的每一个,都身负沉疴,颤颤巍巍,时间的烟尘过于浓重了,它们气喘吁吁,等着神医来施行手术,妙手回春。但是等得太久了,它们除了在无数次的落日余晖中苦苦等待之外,还是等待。
摄影师最初是喜出望外的,见到这些黄房子,就仿佛见到了故人,他为它们拍照,他和它们合影。大地上一下子冒出来这么多令他心仪的黄房子,这应该是这座城市的一个节日,而不单单是他自己的。但是,这些从棚户区和违章建筑里被解救出来的黄房子,蓬头垢面,还不曾梳洗打扮一番,就重又变成孤立无援的了,只是这一次挣脱了拥挤,但却是站在了四处透风的空旷之中,在一片暴露状态中承受着更大的雨雪风霜。其他的建筑群落和街区离它们远远的,与这边十分的隔膜。摄影师反复举起相机的一双手臂,也疲累不堪,成了枯枝了。
不久,城市图书馆里多了一个读书人,那人在故纸堆中翻拣,老旧报章杂志、画册、回忆录等等。他想知道当年都有谁住在这些黄房子里,这座金色的宅子内部,藏着些什么样的生活,这是他仅仅用相机所寻觅不到的。他发现,最初宅子的主人是来自另一片土地,他们在东方的新土地上复制了他们西式的那一切,而这些宅子,是一条著名铁路的附属品,镶嵌在铁轨和枕木、站房之外的不远处,当他们工作结束之后,这里就是安放他们疲惫身心的所在。等到他们被命运赶走之后,这里开始接纳又一代国籍和身份完全不同的人物,这些老房子,除了发挥住宅的功能,它们有的还成为战时的指挥所,许多决胜千里之外的战事,是在这里运筹的。再后来,当炮火沉寂,和平的日子来临,另一大批穿着蓝制服的职员和他们的家属,沿着从不同方向延伸过来的铁路线,从车厢里跳下来,涌向这里。这里的从前是他们从未深究过的,这里只是成了聚集平民狂欢的无数家庭的汇集地,与任何别的地方的聚集地,也没有多大区别。但是这里的人口越来越多,原来的黄房子住不下了,紧贴着老墙体,后来是在院子里,大批的棚子、平房,开始见缝插针,随后遍地开花,再随后,是废品收购站、食杂店、饭馆、小作坊,出现在临街,挡住了后面或者侧面的黄房子,直至出现了一个超级体量的建材大市场。这个大市场不仅垄断了这里的空间,也彻底遮蔽了这一带的老宅,将它们矮化直至令其沉入匿名之中,往昔的历史被遮断了,黄色不是被挤对得愈发局促的问题,而是彻底的面目全非。同时进行着的,是绿色栅栏被拔掉,当柴烧了,果树们齐刷刷地死去,代之以酱缸和坛坛罐罐,以及黑黑的煤棚子。是住在房子里的主人的一代代演变,是不同的人群的不断更替,黄房子的命运就已经注定了。在它颓然倒下之前,就已经不再是原来的那个它了,它成了一个空洞的躯壳,但是它一直在顽强地呼吸,虽然那呼吸是越来越急促了。
当摄影师在图书馆里东翻西找的时候,黄房子的命运终将怎样,他似乎是有些明白了。房子不仅是个实体,即使今后修缮得再好,恐怕也不适合现代人居住了。事實也是如此,一些老房子已经变成了酒吧、咖啡吧和冷饮厅,还有的变成了小型专题博物馆,但很难再还原为住宅了。他本人和它的初相识,不就是因为它已经变成了一个公共场所了吗?昔日的私人空间,其中的物事,慢慢转化为后来者心目中的传说和故事,并且可以被讲述起来,讲得好的,还能出售,进入公共空间,而它最初到底是什么样子,有着怎样的谜底,反而无人关心了,黄房子和它的物事,成为了故事得以贩卖的背景。
当然,黄房子的价值不止这些,它还可以是影像,是照片,是画。而他作为一个拍摄者,已经身体力行,为老房子留下了那么多层层叠叠的倩影或者丽影,似乎也尽了他的力量了。但是现在他又觉得这还是远远不够的,老房子的价值是淘不完的,它分明还是一种符号,一组密码,他常常抚摸着斑驳的墙体,然而如何发问,如何能得到它的应答?对它的奥秘和基因的破译,要花更深的功夫,于他而言,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这样想的时候,他感到有些疲倦。
摄影师现在不怎么经常去黄房子街区那里走动了,他的老式相机和黄房子一样,变得不太合时宜,和手机比,也显得笨重了些。有时,他和老伴一起坐公共汽车路过那里,黄房子从车窗上快速闪过,像老朋友和他打招呼一样。那种米黄色像金子,闪闪发光的样子,令他有些睁不开眼。他就细细地眯起眼睛,不再往那个方向看了,但是他的眼里是酸涩的。
责任编辑 韦健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