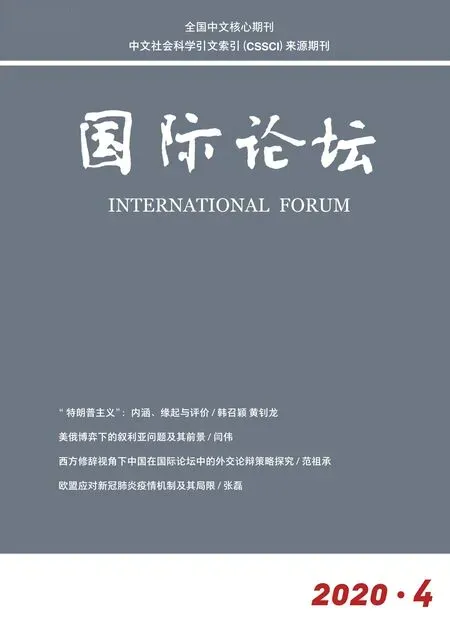“特朗普主义”:内涵、缘起与评价
2020-08-04韩召颖黄钊龙
韩召颖 黄钊龙
【内容提要】2016年当选美国总统以来,特朗普对美国对外政策传统进行了众多变革和颠覆,美国自身和国际社会都受到了巨大冲击。在特朗普政府的对外政策被各种词汇不断“标签化”的背后,弄清何种“主义”支撑和指导着特朗普政府的对外战略、明确此种“主义”成型的原因、研判其自身的局限和对中美关系的影响成为各界讨论的热点。本文通过对特朗普政府执政三年多发布的官方文件及其实际战略作为进行剖析,认为“特朗普主义”具有如下基本内涵:大国竞争的基本战略判断、美国优先的具体政策指针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单边主义与强制主义外交风格。此外,由于复杂的国内政治因素影响,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原则还体现出“铁锈带优先”和“白人优先”两项特点。国际格局的持续变化,政党政治和社会主流认知变迁等美国国内政治因素与特朗普个人特质的综合作用是“特朗普主义”最终成型的原因。“特朗普主义”除对国际秩序造成诸多负面冲击外,对中美关系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本身受到美国内部的广泛批评。
2016年,国际政治诸多“黑天鹅”事件中最大和最有影响力的莫过于反建制派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当选为美国第45任总统。其自恋、自负、争强好斗、不羁善变的鲜明个性给国际社会判断美国对外政策走向增加了太多的不确定性。①尹继武、郑建君、李宏洲:《特朗普的政治人格特质及其政策偏好分析》,《现代国际关系》2017年第2期,第15—22页。执政三年多来,特朗普对美国的国内、国际政策做出了众多颠覆性调整,美国自身和国际社会都受到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使人疑惑的是,频繁被各种“标签化”的特朗普政府是否存在某种一以贯之的政策理念或“主义”(Doctrine)?其有什么内涵?如何形成?影响和局限何在?诸多问题接踵而出,让国际社会不得不始终对此保持密切关注。
实际上,是否存在“特朗普主义”(Trump Doctrine),学界还存在争论。持怀疑论者认为,根本不存在什么“特朗普主义”,更遑论其行为有何逻辑可循。例如,美国著名政治评论家法里德·扎卡利亚(Fareed Zakaria)认为,理解特朗普的外交政策是一个挑战,因为他很少针对这一主题发表文章或谈话,换言之,是否存在“特朗普主义”本身就是一个疑问?②Fareed Zakaria,“Does a Trump Doctrine on Foreign Policy Exist? Ask John Bolton,”The Washington Post,May 3,2019,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opinions/does-a-trump-doctrine-onforeign-policy-exist-ask-john-bolton/2019/05/02/6d209220-6d1c-11e9-a66d-a82d3f3d96d5_story.html.专栏作家迈克尔·托马斯基(Michael Tomasky)也认为,“你听说过杜鲁门主义、里根主义、布什主义、奥巴马主义,也许你喜欢它们,也许你不喜欢,但它们是存在的,你可以大致定义它们是什么。然而,特朗普主义到底是什么?”③Michael Tomasky,“The Trump Doctrine Is Sicker and More Terrifying Than Ever,”The Daily Beast,August 22,2019,https://www.thedailybeast.com/the-trump-doctrine-is-sicker-and-more-terrifyingthan-ever?ref=scroll.尽管如此,随着特朗普执政时间的增加,一些学者也开始探讨特朗普政府行为的一般模式,以求从这一模式背后剖析出其所遵循的基本理念。例如,美国著名政治学家查尔斯·库普乾(Charles Kupchan)就认为,“美国优先、民族主义、单边主义、反移民的热情、对中国的抨击,这些都是‘特朗普主义’的标志,它们已成为新常态。”④Charles Kupchan,“America First:Means a Retreat From Foreign Conflicts,”Foreign Affairs,September 26,2019,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2019-09-26/america-first-means-retreat-foreignconflicts.也有学者观察到,“就过去两年多来看,特朗普政府对外政策的逻辑基本体现为‘大国竞争’的战略框架、‘美国优先’的政策目标”。①刁大明:《特朗普政府对外政策的逻辑、成因与影响》,《现代国际关系》2019年第6期,第19页。
鉴于学界还对上述诸多问题存在争论,本文尝试对“特朗普主义”的内涵、成因和评价进行更深入的分析,并据此探讨“特朗普主义”对中美关系的具体影响和中国的应对之策。
一、“特朗普主义”的内涵
在美国对外政策研究中,“主义”一词常被用来形容美国总统对外政策制订的指导原则和在某一原则指导下展现出的行为特征。②参见王鸣鸣:《奥巴马主义:内涵、缘起与背景》,《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9期,第109页。美国虽然是个政治制度完善的法治国家,但由于其宪法和制度本身赋予了总统巨大的决策权,因而美国外交一直具有强烈和明显的总统个人特征。③楚树龙、周兰君:《特朗普政府外交特性及其影响》,《现代国际关系》2018年第8期,第23页。尤其当遇到像特朗普这样极具个性的领导人,美国对外政策注定会出现不同以往的鲜明变化,与特朗普本人个性相称的“主义”也必然会出现。事实上,美国《大西洋月刊》主编、曾提出“奥巴马主义”(Obama Doctrine)一词的杰弗里·戈德伯格(Jeffrey Goldberg)早在2018年6月就提出了“特朗普主义”的概念,戈德伯格认为,“没有敌人,没有朋友”构成了“特朗普主义”的基本内涵。④Jeffrey Goldberg,“A Senior White House Official Defines the Trump Doctrine:We’re America,Bitch,”The Atlantic,June 11,2018,https://www.theatlantic.com/politics/archive/2018/06/a-senior-whitehouse-official-defines-the-trump-doctrine-were-america-bitch/562511/.就此来说,“特朗普主义”毫无疑问是存在的。本文通过对特朗普执政三年多的官方文件,尤其对其实际战略行为进行剖析后,发现“特朗普主义”具有如下内涵:大国竞争的基本战略判断、美国优先的具体政策指针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单边主义与强制主义外交风格。
(一)大国竞争的基本战略判断
认为国际政治进入了新一轮大国博弈、大国竞争的时代是特朗普政府最基本的战略判断,也是“特朗普主义”的首要原则,这一判断从宏观和大战略层面指导特朗普政府战略调整的整体方向。
从冷战结束到2017年特朗普当选总统前,就官方层面而言,美国对国际政治的基本判断是,虽然国际社会存在诸如恐怖主义、核扩散和新兴力量崛起等威胁,但美国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没有受到根本挑战。因而,美国在对外目标设定上历来以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为主,对威胁判断也比较模糊。①韩召颖、黄钊龙:《对冷战后美国大战略的考察:目标设置、威胁界定与战略实践》,《当代亚太》2019年第5期,第30页。例如,奥巴马政府2010年出台的《国家安全战略》就美国所面临的威胁写道,“美国面对的不是一个敌对的扩张主义帝国”,“对美国人民来说,没有比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更大的威胁”。②The White House,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Washington,2010,p.17,p.4,http://nssarchive.us/.就算是在推出“亚太再平衡”政策以后,美国官方对大国威胁的判断也没有出现性质差异,2015年奥巴马政府出台的第二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在威胁范围的界定上与2010年保持了大体一致,关于大国崛起仅提出“权力转移的变化给未来的合作既带来了机会也带来了危险”。③The White House,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Washington,2015,p.4.
但以2017年12月特朗普政府发布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为转折标志,美国官方对国际政治环境性质的判断发生了根本变化。这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大肆渲染中国崛起对美国主导地位的威胁,并依此认为,国际政治的发展在冷战结束三十年后正式重回大国竞争的时代。④The White House,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Washington,2017,p.2.2018年1月出台的《美国国防战略》报告进一步指出:“国家间的战略竞争,而不是恐怖主义者,现在成为美国国家安全的主要担忧。”美国繁荣与安全面临的核心挑战是再一次出现的“修正主义大国”。⑤“Summary of the 2018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Sharpening the American Military’s Competitive Edge,”February 19,2018,pp.1-2,https://www.defense.gov/Portals/1/Documents/pubs/2018-National-Defense-Strategy-Summary.pdf.《2019 财年国防授权法案》则明确强调,“与中国的长期战略竞争是美国的最高优先”。⑥The 115th Congress,“H.R.5515,John S.McCain National Defense Authorization Act for Fiscal Year 2019,”August 13,2018,https://www.congress.gov/bill/115th-congress/house-bill/5515/text.正是受此理念的指导,在全球地缘战略重心的调整上,特朗普政府延续了奥巴马政府在中东进行“战略收缩”而在亚太进行“战略平衡”的态势,在《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直言要寻求与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的四方合作,夯实以“菱形同盟”为基石的“印太战略”。⑦The White House,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Washington,2017,p.46.2020年2月29日,特朗普政府更是走出了通过与塔利班和解以从阿富汗脱身这关键一步。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不仅直接向中国发动贸易战,还不惜大力动员广布世界的盟友在高科技领域,尤其是5G网络通信、芯片合作等项目上封杀华为等中国 企业。①张一飞:《特朗普政府“联欧制华”战略的形成与评估》,《国际展望》2020年第2期,第103—125页。
从对冷战结束后三十年美国大战略的根本性变革来看,官方层面正式判定国际政治重回大国竞争时代,是特朗普政府对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做出的重大调整,也是“特朗普主义”的首要内涵,将指导特朗普政府甚至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内美国对外战略调整的整体方向。有学者就此判断到,强调大国竞争,正是特朗普外交在理论上成型的标志。②沈雅梅:《特朗普“美国优先”的诉求与制约》,《国际问题研究》2018年第2期,第101页。
(二)美国优先的具体政策指针
美国重回大国竞争时代是特朗普政府的基本战略判断,美国优先(America First)则是在这一基本战略判断的基础上,饱含特朗普个人色彩的具体对外政策指针。所谓美国优先,强调美国对外政策的首要甚至唯一目标就是维护美国利益。展开大国战略竞争,只强调自身利益的优先性而忽视其它国家的利益关切并不是唯一的战略选择,就此意义来说,“美国优先”就成为“特朗普主义”的一个特点鲜明的核心理念。
2017年特朗普政府的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就明确表示这是一项美国优先的国家安全战略。③The White House,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Washington,2017,p.3.特朗普本人更是在多种场合表示了类似看法,例如,在第72届联合国大会进行演讲时,特朗普就直言,“作为美利坚合众国总统,我将永远把美国利益放在第一位”,大力宣扬其美国优先理念。④The White House,“Remarks by President Trump to the 72nd Sess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September 19,2017,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s-statements/remarks-presidenttrump-72nd-session-united-nations-general-assembly/.美国前国务院官员米歇尔·安东(Michael Anton)认为,如果说有“特朗普主义”,那就是美国优先。⑤Michael Anton,“The Trump Doctrine,”Foreign Policy,April 20,2019,https://foreignpolicy.com/2019/04/20/the-trump-doctrine-big-think-america-first-nationalism/.有学者判断,如果说“特朗普上任以来诸多行为的背后有一套完整的理念在驱使,美国优先正是这套理念的灵魂”,①王玮:《从“优势论”到“优先论”:冷战后美国对外政策思想的演进》,《美国研究》2018年第5期,第69页。也是特朗普外交政策的核心原则,构成正在形成中的“特朗普主义”的关键内容。②沈雅梅:《特朗普“美国优先”的诉求与制约》,《国际问题研究》2018年第2期,第96页。
假如仅强调美国利益优先于其它国家的利益在美国外交历史上并不算“独一无二”的话,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由于夹杂着美国国内政治因素,尤其是特朗普政府的选举政治利益考虑,使其具有了真正的“独一无二性”,即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具有“铁锈带优先”和“白人优先”两个特征。有学者认为,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理念实际上体现的是“铁锈带优先”,③张文宗:《美国“铁锈带”及其政治影响》,《美国研究》2018年第6期,第110页。也就是说,特朗普政府对国家利益的界定和追求优先以支持自己的关键选民的偏好为主要根据。2016年特朗普击败希拉里的关键正是由于传统上属于民主党“基本盘”的“铁锈带”(五大湖地区)倒向了共和党,④沈雅梅:《特朗普“美国优先”的诉求与制约》,《国际问题研究》2018年第2期,第102页;张文宗:《美国“铁锈带”及其政治影响》,《美国研究》2018年第6期,第117页。因此,特朗普要想连选连任,必须“讨好”助其当选的这群“功臣”。从另一个角度而言,特朗普执意推行“禁穆令”,不顾和国会决裂,以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的极端方式修建美墨边境墙,收紧美国移民政策等一系列措施都旨在讨好白人中下层选民,又具有明显的“白人至上主义”特征。有学者就特朗普政府采取如此措施的根源分析道,“特朗普政府在移民问题上的一系列动作契合了其大选时的选举承诺,呼应了美国白人尤其是中下层白人的诉求,巩固了其在共和党选民中的民意基础”。⑤张文宗:《美国特朗普政府的移民政策及其影响》,《当代世界》2019年第11期,第62页;李庆四、翟迈云:《特朗普时代美国“白人至上主义”的泛起》,《美国研究》2019年第5期,第106页。
(三)单边主义、强制主义的外交风格
美国优先是特朗普政府的具体政策指针,单边主义和强制主义则是在这一具体行事原则指导下,特朗普政府在执行对外政策过程中所展现出的两项行为特征和“处事风格”,换言之,单边主义和强制主义本身不是指导美国对外政策的原则理念,而是实现和践行美国优先原则的具体体现。
1.单边主义。所谓单边主义是相较多边主义而言的,多边主义又近似国际主义,强调在维护自身利益时与其他国家的利益协商以采取多边行动的方式;单边主义与此相反,其在自身利益优先的理念指导下,多以单边行动的方式维护自身利益。①王玉主、蒋芳菲:《特朗普政府的经济单边主义及其影响》,《国际问题研究》2019年第4期,第111页。特朗普政府的单边主义在三个方面体现最为突出:一是经贸领域,二是国际机制、国际制度领域,三是国际热点问题领域。
在经贸领域,特朗普政府频繁运用与多边贸易规则相抵触的国内法律(“232”“201”“301”条款)对包括美国盟友在内的众多国家展开调查,同时放弃了奥巴马政府对更新多边贸易规则的追求,转而采取美国直接与当事国双边谈判的方式,放弃《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的同时,重谈了北美自贸协定和与韩、日等国的双边贸易协定。有学者就认为,特朗普政府在经济领域,尤其是国际贸易领域采取了一系列举措,是一种典型的“经济单边主义”(economic unilateralism)。②王玉主、蒋芳菲:《特朗普政府的经济单边主义及其影响》,《国际问题研究》2019年第4期,第111页。
在以多边规则为基础的国际制度领域,特朗普政府具有明显的推卸责任、拒绝承担国际义务的倾向。特朗普政府首先对以联合国为主要标志的国际制度采取了极其实用的单边主义态度,不断以资金相要挟,强调联合国的各项政策必须体现美国意志、维护美国利益。③毛瑞鹏:《特朗普政府的联合国政策》,《国际问题研究》2019年第3期,第35—41页。此外,特朗普政府不断退出国际机制和国际组织,成了世界上退出国际组织最多的“退出国家”,④楚树龙、周兰君:《特朗普政府外交特性及其影响》,《现代国际关系》2018年第8期,第26页。其先后退出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巴黎气候协定》、联合国人权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中导条约》等。在2019年底新型冠状肺炎开始肆虐全球需要各国合力应对的关键时刻,美国不仅对世界卫生组织的合理建议置若罔闻,而且不时指责世界卫生组织偏向中国;相较中俄等国对疫情严重国家的大力援助,美国政府除了口惠而实不至的1亿美元对外援助外基本无所作为;2020年5月30日,特朗普更是直接宣布终止美国与世界卫生组织的关系。这表明特朗普政府不仅在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等比较传统的全球治理领域一意孤行地采取单边主义,就算是在全球公共安全这种政治意义最淡薄的全球治理议题上也是丝毫不热心。⑤有学者将特朗普政府屡屡退出国际组织的行为视为其反制度化国际战略的一部分,认为特朗普政府对国际组织的“选择性退出”正是“美国优先”国家安全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参见:王明国:《选择性退出、多边间竞争与特朗普的反制度化国际战略》,《国际论坛》2020年第1期,第20页。
在热点问题领域,不顾既有国际共识的约束,完全以美国利益,甚至是自己决策小圈子的局部利益为考量激化热点问题。巴以问题是困扰国际社会的难题,“两国方案”得到全球大部分国家的支持和理解,特朗普由于受到犹太利益集团的影响,将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迁至耶路撒冷,并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的首都。这无疑会激起巴勒斯坦甚至中东伊斯兰国家大部分人民的不满,使巴以问题更难解决,恐怖主义更难消除。特朗普政府还在伊核问题上一意孤行地“开倒车”,致使伊朗重启核计划,让中东时不时就成为全球安全的焦点。此外,在古巴、委内瑞拉、军控等诸多全球热点议题上,由于特朗普政府在美国优先理念指导下采取单边主义做法,使诸多问题由冷转热,国际社会更不太平。
2.强制主义。在美国优先的政策理念指导下,以极限施压为主要内容的强制主义成为与单边主义相辅相成、相伴而生的另一项“特朗普主义”的重要特征。所谓强制主义,就是以经济制裁、外交施压、武力威胁为后盾,力图使别国屈服于自己的意志,接受自己的要求。特朗普政府执政三年多,针对众多国家和议题,采取了令人眼花缭乱的强制主义外交。
2017年3月17日,美国时任国务卿雷克斯·蒂勒森(Rex Tillerson)在访问韩国时宣布“战略忍耐”结束,所有选择都摆在桌面,①Rex W.Tillerson,“Remarks With Foreign Minister Yun Byung-se Before Their Meeting,”March 17,2017,https://kr.usembassy.gov/031717-remarks-foreign-minister-yun-byung-se-meeting/.由此开启了对朝“战略强制”和“极限施压”的进程。②沈文辉、江佳唯:《美国对朝“极限施压”政策的内涵、逻辑与困境》,《美国研究》2019年第1期,第26—48页;朱锋:《特朗普政府对朝鲜的强制外交》,《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年第6期,第60—76页。此后一年多,美国对朝鲜采取了强度空前的“极限施压”。2017年4月,美国在朝鲜周边海域集结了两个航母战斗群,从实战层面对朝鲜进行挑衅和威慑,制造了朝鲜半岛的“四月危机”。在韩美联合军演中,美国甚至直接将对朝鲜最高领导人的“斩首行动”列为演习科目以最大程度上威慑朝鲜。
特朗普政府一改奥巴马政府的对古巴缓和政策从而使美古关系重回对抗的轨道。2017年8月因“声波袭击”事件,美国撤走了驻古巴大使馆的相关人员,并驱逐了15名古巴驻美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无限期停止向古巴公民发放签证,出台相关政策法令限制美国企业、公民与古巴公司开展商业往来。③曹廷:《试析特朗普对古巴的强硬政策》,《现代国际关系》2019年第1期,第55页。
美国还对伊朗采取强制外交和极限施压的方式,主要体现在大量任用对伊强硬人士、退出《伊核协议》重启制裁、煽动伊朗内部动乱,①迟永:《特朗普政府的伊朗政策及其影响》,《现代国际关系》2018年第9期,第44—47页。将伊斯兰革命卫队划为恐怖组织,派驻航母战斗群进驻波斯湾,甚至直接斩杀伊朗强硬派的高官。2019年7月22日,在伊朗打下美国无人机以后,特朗普一度下达了空袭和向伊朗发射导弹的命令,只是在最后关头取消了。2020年初美国又在伊拉克境内击杀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部队指挥官卡西姆·苏莱曼尼(Qasem Soleimani),一度使美伊面临开战的局面。此后,特朗普政府又不顾欧洲盟友的异议,继续推行致使《伊核协议》基本“流产”的敌对政策,即使在面临新冠肺炎这种严重公共卫生安全事件时,美国也丝毫不愿放松对伊朗的各种严厉制裁。
自从2019年年初委内瑞拉发生政变以来,美国自愿为反政府人士胡安·瓜伊多(Juan Guaido)撑腰,以军事打击相威胁,让马杜罗政府向反对派交权,纠结利马集团和众多盟友对委内瑞拉展开了强度空前的金融、贸易、外交和政治制裁。
除上述在安全领域的强制性外交举措,特朗普政府在涉及经贸议题等非传统安全问题上,也大肆挥动“大棒”,对包括美国盟友在内的众多国家进行加征关税等“讹诈”外交。其中影响最大、受到关注最多的莫过于从2018年3月开始的对华贸易战。特朗普政府针对多个国家、多个议题采取的强制主义外交,目的无疑是在试图逼迫相关国家向美国让步,背后的理念支撑正是美国优先。
此外,在分析特朗普政府的强制外交时还能看到,美国在执行强制主义外交政策的过程中,存在将不同议题挂钩,进而讨价还价的特点,而这也证明了特朗普政府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实用主义、现实主义价值取向。在特朗普初登总统宝座后,就试图将台湾问题和贸易问题挂钩,迫使中国在后一问题上让步。2019年,特朗普又以加征关税为威胁,迫使墨西哥在管控难民议题上向美国的要求做出重大妥协。在特朗普执政三年多时间里,时不时就以美国所提供的安全保证为手段,向欧盟、日韩等盟友施压,使其在经贸问题上让步。有学者就此认为,经贸议题与安全议题挂钩、不同安全议题之间挂钩,成为“特朗普主义”的核心支柱之一。②左希迎 :《特朗普政府亚太安全战略的调整》,《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年第5期,第43页。
二、“特朗普主义”的缘起
通过上文的分析可以发现,“特朗普主义”的内涵包括:大国竞争、美国优先、单边主义、强制主义,其中大国竞争是基本战略判断,美国优先是具体政策指针,单边主义、强制主义则是在二者尤其是在美国优先的政策指针下展现出的实际行事风格。此外,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原则还体现出“铁锈带优先”和“白人优先”的特点。众所周知,一国对外政策的制定和由此形成的风格既受到国际格局等外部环境的影响,也受到本国国内政治、领导人自身等单元和个人层次变量的塑造。毫无疑问,“特朗普主义”的形成也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且不同层次的因素对不同内涵的形成所起的作用存在差异。
国际格局的变迁和共和、民主两党的共识是大国竞争这一基本战略判断形成的主要原因。印太战略作为对大国竞争这一基本战略判断的政策回应,力图投入更多资源、拉拢更多国家以抗衡中国崛起,推动这一战略出台的直接和首要原因正是新兴力量与美国实力对比出现的显著变化。①韩召颖、黄钊龙:《对冷战后美国大战略的考察:目标设置、威胁界定与战略实践》,第56—65页。如表1所示,从冷战结束至今,中美实力差距出现了根本性变化,中国不论是经济实力还是军事实力所占美国实力的比重都增长了约10倍,如简单按经济、军事实力平均计算的“综合国力”看,中国占美国实力的比重已由1993年的5%增长到了2017年特朗普上台时的50%,且这一差距仍在不断缩小。除去国际格局本身的变迁外,美国国内就此形成的强烈共识也有力地推动了大国竞争基本战略判断的形成和印太战略的出台。有学者就此分析道,这一战略出台的原因正是在于两党对21世纪的未来属于亚太或印太这一认知并无实质分歧。②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课题组:《中期选举后特朗普政府内外政策走向》,《现代国际关系》2018年第12期,第32页。总而言之,印太战略正是国际格局变迁这一结构性矛盾和美国国内因素及特朗普个人共同作用的产物。③吕虹、孙西辉:《“结构性矛盾”与“特朗普主义”——特朗普政府“印太战略”的双重动因》,《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8年第6期,第1页。
从现实来看,作为印太战略的核心内容,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变体现了上述逻辑。有学者对此分析道,“当前中美关系正在发生重大变化,这种变化的背后既有特朗普执政的个性因素,更有美国对华政策演变的趋势性因素”,①吴心伯:《特朗普执政与美国对华政策的新阶段》,《国际问题研究》2018年第3期,第93页。同时还受到美国工商业界、社会精英、普通民众、国会议员对特朗普政府执行有关对华政策强烈支持的影响。②刘卫东:《特朗普政府对华施压的国内动因》,《现代国际关系》2018年第7期,第32页。

表1 冷战后中国占美国实力对比变化
国内公众偏好、主流认知变迁和特朗普本人的性格特征、经商背景等单元和个人层次因素是美国优先的具体行事原则,以及在此基础上展现出的单边主义和强制主义风格形成的主要原因。从美国国内因素来看,特朗普政府对美国优先和单边主义的追捧,既有选举利益的考量,也受美国国内主流认知变迁的影响。有学者就认识到,特朗普推进美国优先和单边主义对外政策的指向性很明显,即回馈共和党基础选民,尤其是助其上位的中西部中下层白人、蓝领工人。③钱立伟:《特朗普治下的美国:内外政策特点及前景》,《现代国际关系》2017年第12期,第11页;张文宗:《美国“铁锈带”及其政治影响》,第117页。可以说,这是美国政党政治的工具,是共和党和特朗普谋取两党力量比较优势和总统选举的重要抓手。④李杨、孙俊成:《特朗普政府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基于政党政治的研究视角》,《美国研究》2019年第3期,第43页。从主流认知变迁这一更深层视角来看,美国优先和单边主义的出现是因为美国国内兴起了全面质疑全球化的社会思潮,其根源在于“全球化时代收入分配不均恶化激发了受益不多或者无从受益者的民粹主义观点,使‘慷慨’‘包容’‘协作’的自由主义国际观不再具有说服力。”⑤王玮:《从“优势论”到“优先论”:冷战后美国对外政策思想的演进》,《美国研究》2018年第5期,第67页。有学者就认为,以文化、民族和国家为核心的本土主义兴起是促成特朗普政府在对外政策上出现经济功利主义、安全单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层面单向孤立主义的原因。①周鑫宇:《美国外交中的本土主义:历史传统与新发展》,《国际问题研究》2017年第6期,第96—108页。
从特朗普个人层面来看,“逐利自我”的人格特质,决定特朗普更加自私,喜好以美国自身利益作为政策出发点,而不顾及国际义务和责任。“精干有为”和“好胜执着”的人格特质,则塑造了其好斗、强硬的政策追求。②尹继武、郑建君、李宏渊:《特朗普的政治人格特质及其政策偏好分析》,《现代国际关系》2017年第2期,第17—19页。由此可见,美国优先、单边主义、强制主义理念与风格的形成,既受到美国国内主流思潮变迁和共和、民主两党的选举博弈推动的影响,也与特朗普个人因素密切相关。
从实际政策出台来看,特朗普政府对古巴强硬政策的出台就混合了保守派理念、执政需要、商人利益计算等各种原因。共和党在古巴问题上历来是持保守态度,里根、布什父子都是对古巴强硬人士,特朗普对古巴强硬符合共和党的传统。此外,特朗普还从商人的视角认为,奥巴马在美古关系正常化中,对古巴让步太多,而美国得到的太少,不符合成本收益的期望。同时,支持对古巴强硬的多为古巴裔选民,他们多居住在关键摇摆州佛罗里达,为了拉拢关键摇摆州佛罗里达的选民支持,特朗普采取了对古巴强硬的政策。③曹廷:《试析特朗普对古巴的强硬政策》,《现代国际关系》2019年第1期,第56—57页。同样,特朗普政府之所以采取敌视伊朗的政策,既有特朗普个人因素的作用,又受美国国内政治环境的影响。④迟永:《特朗普政府的伊朗政策及其影响》,《现代国际关系》2018年第9期,第47页。
三、共识与分歧:美国国内对“特朗普主义”的评价
美国对外政策历来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尤其是在“特朗普主义”所带来的颠覆后,已有很多研究者从其对国际秩序、全球治理、热点问题和一系列双边关系所造成的巨大影响等方面进行了分析,本文更多从美国国内的视角,来看美国国内精英对“特朗普主义”的评价。
从美国国内来看,不能说对“特朗普主义”毫无共识,对其首要原则,即国际政治重回大国竞争时代的基本战略判断,美国国内各界并无多大争议,得到了两党和部分社会精英的赞成。例如,美国著名战略家赫尔·布让兹(Hal Brands)就认为,“公平地说,特朗普应该因他的一些更具建设性的政策而受到赞誉,他的基本直觉,即中国对美国利益构成严重威胁,美国同盟需要更新,不受束缚的经济一体化不一定是毫无害处的,绝非疯狂。”①Hal Brands,“Reckless Choice,Bad Deals,and Dangerous Provocations,”Foreign Affairs,September 27,2019,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2019-09-26/reckless-choices-bad-deals-and-dangerousprovocations.兰德公司高级研究员阿里·韦恩(Ali Wyne)和詹姆斯·多宾斯(James Dobbins)也认为,对特朗普将中国视为最大竞争者这一事实,没有人持批评态度。②Ali Wyne and James Dobbins,“How Not to Confront China,”National Interest,September 29,2019,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how-not-confront-china-82356.
然而,从现实来看,美国国内对“特朗普主义”的批评声远大于赞成的声音,而批评的声音主要聚焦于美国优先、单边主义和强制主义。
首先,对美国优先和单边主义的批评。美国国内很多人首先批评了特朗普对国际制度和一些已经达成共识协议的单边主义做法,认为其从根基上腐蚀了美国主导国际秩序的能力和合法性。③Abby Bard,“Trump’s UN Speech Hurts America and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National Interest,September 22,2018,https://nationalinterest.org/blog/skeptics/trumps-un-speech-hurts-america-andinternational-system-32057.针对特朗普政府在移民、难民问题上极其富有争议的单边主义做法,有评论家批评道这标志着自由主义基本原则的终结,也标志着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正在崩溃。④Nanjala Nyabola,“The End of Asylum,”Foreign Affairs,October 10,2019,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2019-10-10/end-asylum.相较政治偏好倾向于自由主义的学者,美国较保守的知识分子对美国优先和单边主义的批评,更多不是在批评这一理念和政策本身,而是批评其适用的范围。他们认为,特朗普不分敌友的单边主义会破坏美国和盟友之间的关系,致使美国无法将有限的资源集中起来处理最优先的事项,破坏了战略集中性原则,反而更有利于敌对势力影响力的增长。布让兹就此批评到:“在动荡时期,即使是超级大国也需要盟友。但是特朗普对盟国领导人公开攻击、单方面放弃国际协议,削弱了华盛顿应对波斯湾这样的短期危机以及来自中国和俄罗斯的严重长期威胁所需要的关系。”“近三年来,特朗普政府仍未制定全面的与中国竞争的方法,部分是因为华盛顿的注意力在委内瑞拉、朝鲜和伊朗等其它地方。”⑤Hal Brands,“Reckless Choice,Bad Deals,and Dangerous Provocations,”Foreign Affairs,September 27,2019,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2019-09-26/reckless-choices-bad-deals-and-dangerousprovocations.韦恩和多宾斯也批评道,特朗普放弃了以盟友和伙伴为主的联合遏制,在选择单边遏制的同时,还对抗自己的盟友,这极不明智。①Ali Wyne and James Dobbins,“How Not to Confront China,”National Interest,September 29,2019,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how-not-confront-china-82356.
其次,对强制主义和极限施压的批评。在对华政策上,批评者认为特朗普政府过于夸大中国威胁,更严重的是采取了错误的应对方式。例如,里根总统特别助理、卡托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道格·班多(Doug Bandow)就认为,“北京对美国的价值观和利益是构成了严峻挑战,但中国不是敌人,不是无与伦比的,华盛顿夸大了这一切。孤立与对抗将是愚蠢的反应,这只能导致中国以及中国人民的敌对情绪。华盛顿应该继续与中国保持和扩大接触,接纳更多的中国学生进入美国大学,欢迎学术交流,吸引游客。”②Doug Bandow,“Is China or Fear of China the Greater Threat?”National Interest,September 29,2019,https://nationalinterest.org/blog/skeptics/china-or-fear-china-greater-threat-84021?page=0%2C1.针对特朗普对华发动的贸易战,《国家利益》杂志特约编辑米尔顿·埃兹拉蒂(Milton Ezrati)就批评道,特朗普的好战态度和完全缺乏谨慎行事的作风决定其处理贸易问题的整个方案都使美国和世界处于衰退甚至更糟的风险中,特朗普的方针即使能取得成功,也是弊大于利。③Milton Ezrati,“In Defense of Free Trade,”National Interest,No.164,Nov/Dec.2019,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defense-free-trade-87836.针对美国对伊朗的极限施压政策,《洛杉矶时报》专栏作家道尔·麦克马纳斯(Doyle McManus)略带调侃地批评道:“特朗普在许多事情上一直前后矛盾,但他的这种矛盾性却一直保持一致:他宁愿讲话也不愿打架。他一次又一次地以血腥的方式威胁和挑衅其他国家,但随后又表示他更愿意进行谈判。”④Doyle McManus,“Column:The‘Trump Doctrine’:He’d Rather Talk Than Fight,”Los Angeles Times,June 23,2019,https://www.latimes.com/politics/la-na-pol-trump-iran-war-doctrine-20190623-story.html.由此导致美国的威胁可信性降低,使美国对外战略更难获得成功。
四、结语:“特朗普主义”的影响与应对
对国际秩序而言,“特朗普主义”的冲击无疑是巨大的,尤其是美国的经济单边主义将对国际贸易和投资环境带来较大的负面作用,⑤潘晓明、陈佳雯:《特朗普经济安全战略及其影响》,《国际问题研究》2018年第5期,第98页。而特朗普政府的“反制度主义”对多边主义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冲击,⑥王明国:《选择性退出、多边间竞争与特朗普的反制度化国际战略》,《国际论坛》2020年第1期,第36页。更重要的是其经常使用的极限施压和强制主义外交政策有可能使地区热点问题的局势变得不可控制。总之,“特朗普主义”不仅加剧了国际局势的动荡,恶化了全球经济形势,而且从各个维度增加了全球治理的难度,①王一民、肖刚:《特朗普政府对多边主义的消极影响及其限度》,《战略决策研究》2019年第6期,第44页。一系列新的问题对世界各国而言都是艰巨的挑战。
对中美关系而言,由于大国竞争成为特朗普政府的首要战略原则,中美关系的发展势必受此影响进入战略竞争的新阶段。首当其冲的是中美经贸关系尤其是有关高科技的商业往来,尽管目前中美已经签署了解决两国贸易战的第一阶段协议文本,但正如有学者所认为的,中美经贸谈判取得进展,可能无法解决美国对中国的所有抱怨,双方在高科技和社会文化领域的摩擦难以避免。②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课题组:《中期选举后特朗普政府内外政策走向》,第27页;Riley Walters,“Is a U.S.-China Trade Deal Possible?”National Interest,September 29,2019,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us-china-trade-deal-possible-84071.2020年1月15日双方暂时“休战”后,美国一刻也没有放松对中国高科技产业的打压,尤其在打压华为开展5G网络通信业务时,美国可以说无所不用其极。除此之外,特朗普政府正不遗余力地推进其以美日印澳合作为基础的“印太战略”,以确保地缘战略重心转移至西太平洋。③仵胜奇、陶文钊:《特朗普政府“印太战略”前瞻》,《国际论坛》2018年第5期,第29—38页。同时,美国继2019年末通过所谓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和“2019年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后,2020年3月26日特朗普又签署批准了所谓的“台湾友邦国际保护及加强倡议法案”(也称“2019年台北法案”),利用中国国内问题钳制中国的力度可能在未来会更大。
另一方面,也应该看到中美关系经过四十年的发展,在众多领域存在利益的互补性,同时国际社会面临的各种困难都离不开中美的合作。虽然美国国内对中国是美国最有潜力竞争者的身份认知越来越没有分歧,但在如何应对的问题上,美国并未形成一致的共识,强调美国优先并对中国采取全面敌视的战略并非唯一选择,这也是特朗普政府对华发起贸易战后遭受国内批评的原因。例如,新美国安全中心首席执行官理查德·方丹(Richard Fontaine)就指出,根据民调显示,美国公众在如何应对中国挑战的问题上,2/3的人主张通过友好的合作与接触方式,只有30%的人主张强硬的方式。④Richard Fontaine,“Great-Power Competition Is Washington’s Top Priority—but Not the Public’s,”Foreign Affairs,September 9,2019,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china/2019-09-09/great-power-competition-washingtons-top-priority-not-publics.美国鹰派学者、前国防部顾问埃利奥特·科恩(Eliot Cohen)也就美国国内提倡遏制中国的声音批评道,“简单地把遏制政策重复用于不同对象,例如拥核的伊朗,或者崛起的中国,都忽视了全然不同的背景”,①埃利奥特·科恩:《大棒:软实力的局限和军事力量的必要性》,刘白云、郭骏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8年,第205页。换句话说,美国“遏制”中国并不是顺理成章的,套用冷战思维也存在很大的不合理性。
面对这种复杂局势,中国势必要及时调整对美政策以适应新的挑战,为尽力维护中美关系的总体平稳以更有利于追求国家利益,中国应当优先做好两点:一是,中国需要从战略和心理层面做好长期与美国进行战略竞争的准备,随着中美结构矛盾的凸显,美国打压中国的议题、手段可能越来越多,越来越新。对此,中国需要做好长期应对的战略准备,既要有“平常心”,又要严肃应对。②林利民、林东晓:《中美关系“新常态”析论》,《国际论坛》2019年第3期,第77页。就中近期在面对美国打压中国的高科技企业和产业时,既要坚定自己扩大开放、追求发展的坚定意志,还要真正下决心、下力气、下功夫提升本国产品质量,使核心科技永远掌握在自己手中。③楚树龙、周兰君:《特朗普政府外交特性及其影响》,《现代国际关系》2018年第8期,第29页。二是,应继续强调对“稳定、协调、合作”的中美关系的追求,④吴心伯:《竞争导向的美国对华政策与中美关系转型》,《国际问题研究》2019年第3期,第20页。坚持强调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两伤”的战略判断,使中美关系保持基本稳定既符合中国的战略利益,也符合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实际来看,中国在做好斗争准备的同时,仍有很大的空间去继续保持中美关系的整体稳定,四十年的发展使两国利益的交融程度得到空前深化,美国国内不乏力主对华友好的合作派,只是在特朗普政府执政的政治气候下难以发出有力的声音,中国需要做的是主动调动和影响美国国内、国际社会的积极力量,使美国国内的“遏制派”在出台相关极端政策时面临更大的阻力,以压缩其破坏中美关系的行动空间,尽可能维持中美关系“有限竞争”与“合作—竞争”共存的大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