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之鸟与牢笼:二战后十年间荷兰建筑期刊考
2020-07-24赫尔曼贝赫艾克
[荷] 赫尔曼·凡·贝赫艾克 文
潘一婷 译
译者按:一战中作为中立国的荷兰,成为战时欧洲艺术家、建筑师人才的避难所。荷兰的自由精神和氛围,也为20 世纪初世界现代建筑史留下了独树一帜的艺术主张,例如由设计师特奥· 凡· 杜斯伯格(Theo van Doesburg,1883— 1931)、皮特·蒙德里安(Piet Mondrian,1872—1944)等人创立的荷兰“风格派”。其同名期刊《风格》,作为重要的思想发声器,表达当时一部分艺术家和建筑师的理念和精神,掀起了一股风格派纯抽象的现代艺术运动,对包豪斯学院体系的建立乃至对世界现代建筑理论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然而到了二战,荷兰虽仍宣布中立,但德国不宣而战,在1940 年5 月10 日凌晨发起的“闪电战”中击垮了荷兰的防线,荷兰被迫宣布投降,直到1945 年5 月5 日在盟军的协助下,荷兰才终于赢得了解放,结束了被德军攻占的5 年黑暗。但蕴藏在内、蓄势待发的自由精神并没有被战火浇灭,荷兰出版业随即复苏,荷兰建筑期刊在战后继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成为战后重建时期建筑界多元思想交锋的平台。这些思想不仅体现在文字上——包括期刊的期刊名称、方向定位、编委会宣言、论战话题,也延伸到建筑期刊的方方面面,包括作品收录,封面设计和排版设计。原文作者赫尔曼·凡·贝赫艾克(Herman van Bergeijk),是荷兰代尔夫特理工大学历史与理论教授,不仅是《建筑工程师扬·杜伊克尔(1890—1935)》(Jan Duiker,bouwkundig ingenieur 1890—1935)等多部荷兰“风格派”、包豪斯相关历史研究专著的作者,同时也是荷兰知名出版人,现任荷兰当代期刊《自己的建造者》(Eigenbouwer)的主编。他通过挖掘荷兰建筑期刊文史资料,带我们穿越到二战前后,重温那段从战争炮火中挣脱后的历史,了解荷兰建筑师、艺术家、学者和出版人如何重塑精神家园,并重建战后被毁的城市。本文标题中的“自由之鸟”,隐喻荷兰建筑师追求自由本质含义的探索精神,而“牢笼”,除了暗指二战期间的压迫,更隐喻了荷兰建筑师试图挑战与突破的历史传统之枷锁、固有思想之束缚,以及外来影响之困境,最终使得荷兰的创新思想在反复检验中前进。有意思的是,文中讨论的荷兰自由精神,也在某种程度体现在原文作者凡·贝赫艾克教授本人主创的《自己的建造者》期刊具有实验性的当代建筑话语实践里,呈现在其内容和版面的前卫探索中,这或许可以看作本文主旨在今日荷兰的印证与延续吧。
一、荷兰的多元思想竞争
国土面积狭小是荷兰的重要特征,这导致了荷兰不同设计集团的竞争意识也非常强,其结果是荷兰设计的多元思想和阵地意识[1]。这反映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每个建筑期刊都有明确界定的兴趣范畴,不同派别都有属于自己的专业机构和对自己出版物的独特构想。
一方面,荷兰有明确走现代主义路线的期刊:例如荷兰“风格派”团体(“De Stijl”)在1917 年创立的《风格派》(1917—1931),表达一种将艺术、建筑、产品设计联系起来,试图创造新的秩序和新的世界的现代主义愿景[2];又如由阿姆斯特丹建筑“8 人”团体(“De Acht”)与鹿特丹“建造”团体(“Ophouw”)在1932 年联合创立的《de 8 En Opbouw》期刊(1932—1943),旨在对新建筑技术作为工具如何创造新形式等建筑实际问题的深入探讨。[3]另一方面,荷兰亦有仍带着浓重宗教色彩的期刊:如《罗马天主教建筑期刊》(Rooms Katholiek Bouwblad)。在激进与保守之间,“荷兰建筑师协会”(Bond van Nederlandse Architecten,简称:BNA)作为一个守护着对建筑的普遍兴趣和荷兰建筑师权益的行业性质团体,其官刊《建造周刊》(Bouwkundig Weekblad,简称:BW),稳固地占据着建筑思想领域的中间地带。此外,许多其他建筑期刊也找到了自己的定位,亦或联系某一具体产业,亦或与某些建筑师的具体愿景有关。
然而,二战作为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和时间节点,又给荷兰设计思想发展和建筑期刊格局带来什么呢?[4]
二、德军占领期荷兰期刊业的重挫
在德国占领荷兰期间,由于受德方控制,荷兰建筑活动普遍遭遇阻滞,许多建筑期刊被迫中止了出版。其中,荷兰建筑师协会于1942 年被更名为“建筑行会”, 并受德国占领者成立的文化商会(Kultuurkamer)的监督。德方不仅限制了建筑行会的大部分活动, 其行业期刊《建造周刊》也在不久后停刊。
二战期间,瑞士平面设计师汉斯·诺伊堡·科雷(Hans Neuburg-Coray)在一本瑞士期刊《作品》(Werk)上评论道:“法国、英国、德国、土耳其、荷兰、和斯拉夫期刊几乎都是无聊和无趣的。”[5]这看似一个寻常观点,起初也未引起什么争议,其背后的支点到底是什么并不清楚,但关于荷兰,这个严厉的批判很难成立。阿姆斯特丹建筑师协会的期刊《扭转》(Wendingen),很多年来在很多方面都曾是一本独树一帜的出版物。[6]此外,荷兰艺术家保罗·舒特马(Paul Schuitema)在《De 8 en Ophouw》的版面设计也同样地具有创新性,尤其是在日益保守的欧洲。舒特马是荷兰“风格派”和俄国“构成派”(Constructivism)的追随者,当时也是鹿特丹“建造”团体“Ophouw”的成员,他为该期刊封面创造了一种以字体排版为突出印象的基本设计,其他设计师只需要在每期封面上填充剩下的部分,就使得各期封面既统一又富有变化[7](图1)。只可惜,在二战期间,这些平面设计的技能无从施展。这样的问题即便到了战争结束后的短期内,由于纸张的限供,也未能立即改观。
三、团结的愿景与战后联合刊
然而,战争对荷兰建筑活动和出版物的重挫,并不意味着荷兰建筑师们都顺势消沉、自我孤立。相反,战争的束缚激发了很多设计团体渴望突破自己的阵地、增进交流的愿望。他们在二战期间非法秘密聚会,交流思想,并谋划计策,因为他们深信战争一旦结束一切都会复苏。这项共识最突出地反映在了“多恩会议”的创立—— 取名为“建筑与友谊”(拉丁文:Architectura et Amicitia,简称:A. et A.)的阿姆斯特丹建筑师协会创立了一个位于多恩市(Doorn)马滕·马丁之家(Maartenmaartenshuis)的会议系列。其第一讲的议题是 “荷兰建筑特征”,引发了大家浓厚的兴趣,激发了不同阵营的建筑师们去保卫一种统一的荷兰民族身份,也促进了不同派别间兄弟般的对话。[8]

图1:《De 8 en Ophouw》封面(1935年3月第7期)
二战结束前夕,1945 年4 月,年轻建筑师科奥克·梅瑟(Auke Komter,1904— 1982)当选上阿姆斯特丹建筑师协会的主席。科梅瑟曾参与过“多恩会议”,深刻认识到派别间团结合作的重要意义。他在上任开幕词中提出,战后的阿姆斯特丹建筑师协会应当延续协会在1930 年之前试图促进不同的建筑思潮相互交流的政策。[9]二战一结束,科梅瑟就立即联合了当时一些重要的建筑师,一起开始谋划一部新期刊。[10]他们的共同愿景,是创立一部在国际语境下能够经受得起批判的期刊,核心目的是追求合作而不是争端。
与此同时,在二战结束的同一年底,1945年12 月,荷兰建筑师协会、荷兰皇家建筑师学会下的“建筑艺术促进会”(Maatschappij ter Bevordering van de Bouwkunst, 简 称:BvB), 以及阿姆斯特丹建筑师协会三方合作的联合刊《Bouwkundig Weekblad Architectura》( 简 称:BWA)63 卷第一期出版。
四、战后荷兰传统主义对联合刊的影响
受到战后荷兰传统主义思潮的影响,战后重新出版的联合刊第一期封面照片选择了荷兰传统主义运动(Traditionalism) 影响 下 重 建 后 的 雷 宁 市(Rehenen)( 图2)。 主持重建规划的是“代尔夫特学派”的追随者、建筑师库奈尔·帕尔默(Cunera Pouderoyen),而他也在这期期刊里被特别介绍。朗普雷·莫里哀(M. J. Granpré Molière,1883—1972) 从20 世 纪20年代开始在代尔夫特任教授,创立了以传统主义为精神内核的“代尔夫特学派”(Delftse School),帕尔默深受其影响,在重建中重视保护雷宁市的历史风貌与传统建筑的特征。联合刊第一期的第一页也充满了严肃而怀旧的气氛,内容是对战争中逝去的人的致敬,尤其是对那些在1941 年6月15 日以来逝世的建筑师的崇敬。
期刊接下来是联合刊编辑委员会的声明,其主笔人是联合刊最重要的负责人、编辑秘书长——建筑师兼作家J·P· 米拉斯(J. P. Mieras,1888—1956)[11]。(图3)米拉斯在二战前已是荷兰建筑师协会的主席,也是一位知名的宣传家和评论家。米拉斯发表在联合刊上的第一篇社论强调:
“我们肩负着艰巨的责任。如此多的地方已被摧毁、被严重破坏,以至于一个涉及广大区域的城市新面貌正等待着我们去塑造。这是一份责任极大的工作。这需要大量的合作,需要了解各种民意,需要特别努力的工作。”
愿景是美好的,但事实证明合作很难。各派观点各执一词,导致了不可避免的冲突。1946 年初,阿姆斯特丹建筑师协会就宣布从联合刊退出,同时开始出版自己的独立期刊《论坛》,并声明道:
“他们(荷兰建筑师协会和荷兰‘建筑艺术促进会’)应该意识到,阿姆斯特丹建筑师协会从‘组合阵营’中离席,并没有给双方带来一丝不满。相反,战争德方占领期间加强的只有荷兰建筑师协会与阿姆斯特丹建筑师协会间的联结。我们单独出版期刊的动机,只是想要建筑出版物在效率和标准上都更好地契合已设定的目标。”

图2:《Bouwkundig Weekblad Architectura》封面(1945年12月第1期)

图3:米拉斯的画像(1948年)
五、《建造周刊》回应战后现代主义
阿姆斯特丹建筑师协会退出后,荷兰建筑师协会还是继续与建筑艺术促进会合作出版,统一发声。[12]米拉斯带领的编辑委员会在《建造周刊》改版后第一期的序言中,强调了脚踏实地的折中发展路线:
“同时期出现的各式各样的期刊,营造了一种躁动不安的氛围……我们必须保持谦逊的姿态, 摒弃采用那些生涩的词语,不再制造我们明知道是幻象的幻觉……我们准备好了致力于我们期刊的重建,旨在展现建成事实而不制造追随时势的评论……”[13]
中间路线意味着,《建造周刊》对所有新的设计趋势持开放但是谨慎的态度:期刊会对多样化的当代建筑进行介绍,并报道在建项目等事实性的消息,但不会轻易评论某种思潮或为其造势。[14]这种态度的一个生动例子,是一篇米拉斯对“现代建筑的代表”所做的评论文章。[15]
米拉斯指出,二战后新的现代主义设计探索是有益的,但是要注意不要落入只重现代主义形式转抄、不重现代主义精神内核的误区。他说,事实上,“这一系列所谓‘现代建筑的代表’的外形,给人的印象是它们是从一种随意的选择中发展出来的,随意得如同从一袋弹珠中随机翻找而来的选择”。米拉斯进而指出,“如果建筑师意识到这点就会很不一样:只看重建筑外表形式是肤浅的,因为建筑内在精神的内容对我们的影响才是更大的”。因此,必须寻求“好的内在形式”,“探索最大的敌人是庸俗;而其最好的朋友是发现。建筑师是发现者,他们应该最清楚这一点,如果他们自认为已经找到了(这种内在 形式)”。[16]
六、《建造周刊》回应美国现代主义影响的返流
米拉斯带领的《建造周刊》编委会在改版后第一期的序言又继续说道:
“(我们)绝不采用任何关于美国想要告诉我们什么的特别文章,对俄国、伊朗、刚果同样如此。我们会将那些矫揉造作的、以‘你们应该知道……’开头的(文章), 留给那些热衷于此的人。这些就是你们需要知道的全部。”[17]
这意味着《建造周刊》除了仔细辨析来自国内的声音,也对外来影响保持警惕,拒绝不加筛选地对外来思潮全盘接受。[18]其中一个生动例子是米拉斯在《建造周刊》上发表的一篇针对美国五角大楼的评论,反对荷兰建筑师对美国现代建筑的盲目崇拜。
当二战结束后,美国成为许多荷兰建筑师的榜样[19],不少学习团体被派往美国。然而,荷兰建筑师们也注意到,美国的现代建筑体量巨大,成为其随处可见的主导特征和美国国家印象,这样的尺度令一些荷兰建筑师感到困扰。于是,米拉斯在他的“五角大楼”评论文章里,先肯定了这座建筑是美国人生活方式与建筑师挑战和技能间微妙关系的结晶,然后批判了美国现代建筑的巨大尺度对荷兰的“不适”:
“如果我们牢记这种关系,美国建筑师为美国社会的‘作为’,不会比荷兰建筑师为荷兰社会的作为更多。如果我们置身美国,面对像设计五角大楼那样的挑战,我们会感到生疏与信心不足。五角大楼的体量,很明显是布鲁塞尔司法宫、巴黎歌剧院、伦敦议会大厦、斯德哥尔摩市政厅以及罗马圣彼得大教堂的总和。但同样的,如果美国建筑师不得不在我们这样一个像蚂蚁般拧成一团的社会环境里做设计,他们很可能也会如坐针毡,而这却是我们的本性使然。一个宏观宇宙和一个微观宇宙,它们各自都有自己的内在体系,然而并不因此而在本质上有太大的不同。”[20]
米拉斯指出,只有认识到社会间的差异并了解需要解决的实际性问题后,才能理解这样一座建筑:“应该记住这一点以便我们避免被误导,五角大楼这座‘让我们真切地看到未来’(讽刺)的建筑,在我们自己的重建期间,致使我们丧失了平衡。”
七、《建造周刊》中间路线的利与弊
米拉斯带领《建造周刊》选择的中间路线意味着,更多激进的建筑师极少有机会被倾听,而《建造周刊》中占据主导的都是温和派建筑师的作品。米拉斯通常会选择这样一些建筑师:他们以“中间路线”的建筑为标识,并且非常谨慎不要处于过于激进的位置。米拉斯对建筑各种新的思潮没有特别的偏好,也几乎不会给还尚未成熟、但急于成功的新一代年轻建筑师们铺平道路。
当先锋视觉设计期刊《开眼》(Open Oog)于1947 年冬成立时,米拉斯用尖锐的批评迎击它:
“随着《开眼》的到来,这本几十年来一直被需要的期刊最终出现了,即一本纯粹的、尽是胡话的期刊。《开眼》成功地呈现了这种纯度和无懈可击, 如同纯酒精的品质,几乎极致的精神性。《开眼》是一部前卫的小册子,它所谓的国际编委会,就像过去的骑士先驱一样,无所畏惧地闯入战场试图战胜保守势力。(讽刺)”[21]
令人惊讶的是,像米拉斯这样通常温文尔雅的人,竟会瞄准这本对现状几乎没有任何真正威胁的期刊。就像战前的《国际10》期刊(i10)(“i”这里指“international”,i10 指“国际10 人组”)一样,《开眼》几乎没有吸引到什么读者,因此被证明是无害的。但米拉斯对这本薄薄的先锋期刊无丝毫赏识,即使该期刊争取到了左翼人士马特·斯塔姆(Mart Stam)和威廉·桑德伯格(Willem Sandberg)的支持。后者为期刊进行了夺人眼球的平面设计,他还是年轻建筑师阿尔多·凡·艾克(Aldo. E. van Eyck,1918-1999)的朋友。凡·艾克后来成为战后荷兰重要的“结构主义”运动的发起人。《开眼》的第二期,采用了同样有动感的封面,以宣言的形式严厉批判了秉持传统主义的“代尔夫特学派”的教条(图4)。米拉斯忍无可忍地再次瞄准该期刊进行讽刺,但没有指名道姓。他具有讽刺意味的、标题为“进步”(Progressief)的文章,嘲笑了“进步”的真正含义。[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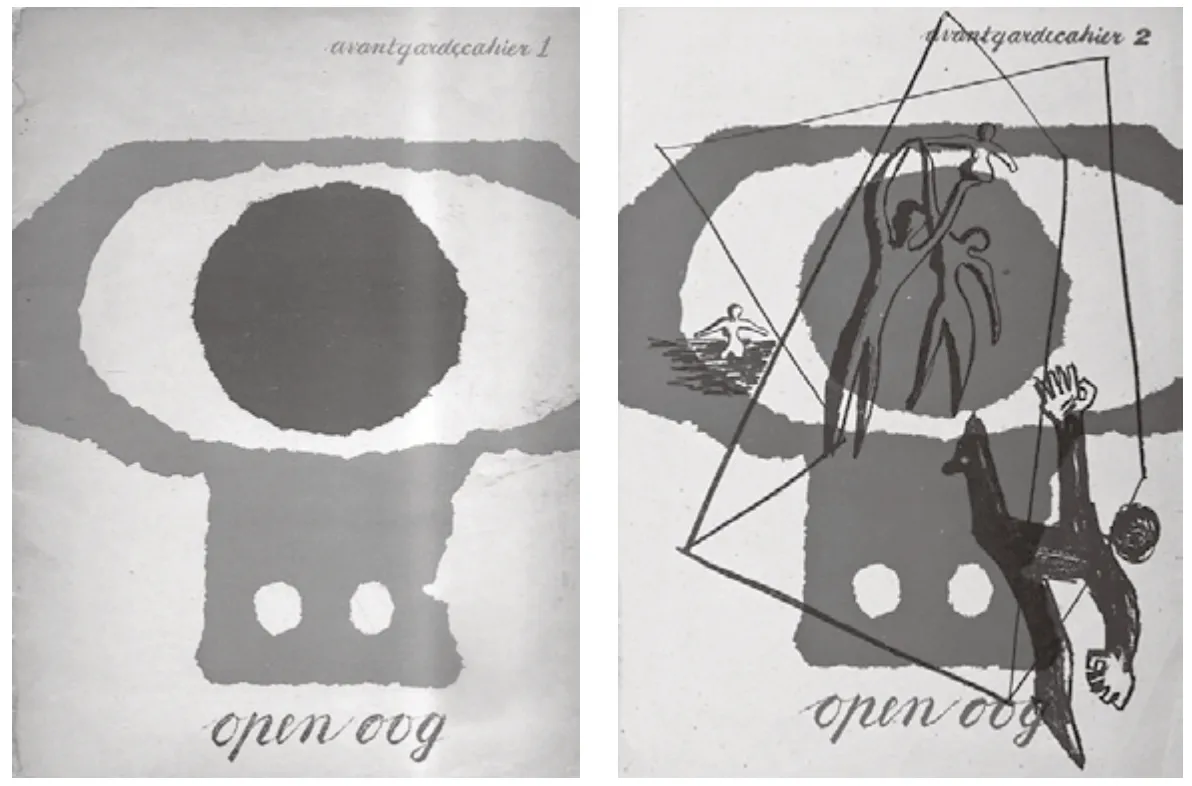
图4:《开眼》期刊封面(1946年第1、2期)
不久以后,这本前卫期刊就在沉默中真的消亡了。
在某种意义上,米拉斯的中间路线,在平衡战后荷兰纷繁复杂的多元思想竞争、在反对现代主义形式的肤浅模仿、在分辨外来影响的适与不适、在纠正激进而空洞的思想方面,是起到了积极的作用。[23]正是由于米拉斯的立场始终居于中间地带,他也赢得了各个阵营的青睐。这可以从他去世两年后专门为他出版的《米拉斯:一 个 朋 友》(Liber Amicorum J. P. Mieras)中得到验证。在这本书中,W·M· 杜多克(W. M. Dudok),S·凡·拉夫斯泰恩(S. van Ravesteyn),莫 里 哀 和 凡· 登· 布 鲁克(J. H. van den Broek,1898—1978)等不同阵营的荷兰建筑师都各自就“建筑师的艺术和社会地位”的问题贡献了自己的观点。[24]
但与此同时,对于拒绝秉持传统主义视角的战后先锋建筑师,米拉斯的中间路线又变成了一种束缚。[25]《建造周刊》通常避免有争议或极端的作品,也几乎不去关心其他艺术种类的重要性。那些新一代荷兰建筑师直率地坚持自己的道路才是正确的,在意识到《建造周刊》编委会不会接受他们的观点后,便继续寻找其他表达他们设计思想途径。于是,他们找到了阿姆斯特丹建筑师协会从联合刊退出后于1946 年创立的期刊《论坛》(Forum)。
八、《论坛》成为荷兰先锋思想的新阵地
《开眼》短暂的生命,绝不意味着激进的建筑师都沉寂了。1947 年,《论坛》期刊发表了一群不知名的荷兰年轻建筑师的观点,他们渴望“突破他们在荷兰建筑中观察到的保守势力的包围”。他们认为,建筑不仅应满足常规的需求,它本身还应该肩负起一种与社会正义、自由、合作相关的新责任。[26]
虽然《论坛》期刊最初的编委会并不比《建造周刊》期刊更前卫,但《论坛》给了年轻建筑师自由讨论更多的空间。例如《论坛》发表了一篇S·J·凡·恩登(S. J. van Embden)当时颇有“争议”的关于鹿特丹(Rotterdam)新城市规划案例的文章,该文章给出了一个城市应该如何进行现代性重建的范例。[27]
战前,每种运动都是孤立前行的,阿姆斯特丹建筑师协会决定这种状态现在要改变。《论坛》在其创刊号引言中写道:“《论坛》应该将‘多恩会议’的参与者聚集在一起:加深对建筑的洞察力,并共同研究什么是最好的观点和表达方式……允许建筑领域里的所有潮流不带任何偏见地、自由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为了做到这一点,《论坛》试图把其他相关“艺术门类”也涵盖在内,以提升期刊内容的丰富性,并开辟可能的新视角。在这种自由与包容政策的实践下,《论坛》的订阅量取得了稳定的增长。
但《论坛》核心领导人内部也有立场较为保守的一派。[28]例如,科梅瑟认为《论坛》对各种思想阵营的无分别接纳,导致期刊“时常以无整体性观点的大杂烩的面貌出现”,而他认为《论坛》 “缺一位给期刊指引方向的人,就像《建造周刊》的米拉斯”。[29]在历史学家兼评论家R· 比利斯特拉(R. Blijstra)于1951 年加入《论坛》编委会后,这一争论有所缓解,而期刊的地位也持续提升。从1952 年起,《论坛》增加了英文摘要,并因此提升了国际影响力(图5)。
尽管如此,在1950 年代,《论坛》总体而言仍是一本温和的期刊,既不随波逐流,也不挑起争端。期刊每年会出版一期,由荷兰先锋建筑师J·B·巴克马(J. B. Bakema,1914—1981)(图6)和 凡· 艾克主持编辑,关注国际现代建筑会议及其活动。1959 年,《论坛》进行了改组,巴克马和凡·艾克等人成为期刊核心人物。[30]《论坛》新一代的领导人与前辈们观点完全不同,后起之秀对期刊的版面设计进行了彻底的改造,以适应新的视觉文化。改版后的《论坛》专注于文本和插图之间更巧妙且动态的配合,每一期的主题都要传达得更强烈有力。凡· 艾克想通过更少、但是更有针对性的图片,来突出特征和强化表现力。当出版商质疑这是否会使期刊的“专业性”减弱,凡·艾克的回答是这更可能提升期刊的批判性。
除了版面设计的革新,更重要的,是期刊的新定位——《论坛》明确地将自己定位为一个实验性的文化期刊,把“建筑环境”的整体作为出发点。那些《论坛》介绍过的、最有影响力的荷兰年轻建筑师,后来参与到CIAM(“国际现代建筑协会”,英 文: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Modern Architecture)中。在1956 年CIAM 第十次会议中,包括巴克马、凡·艾克、凡·登·布鲁克[31](图7)等荷兰建筑师在内的一群筹备会议的年轻的欧洲建筑师(后来也因此被称为“第十小组” Team X),公开反对CIAM 僵化的“功能主义”,主张场所的精神性和个性,以及人与其生活环境之间的互动和认同感。[32]1959 年,《论坛》发表了凡·艾克著名的“结构主义运动宣言”(Manifesto for the Structuralist movement)。[33]在《论坛》的助推下,凡·艾克等人在随后的1960—1970 年代,在欧洲引领一股新的“结构主义”潮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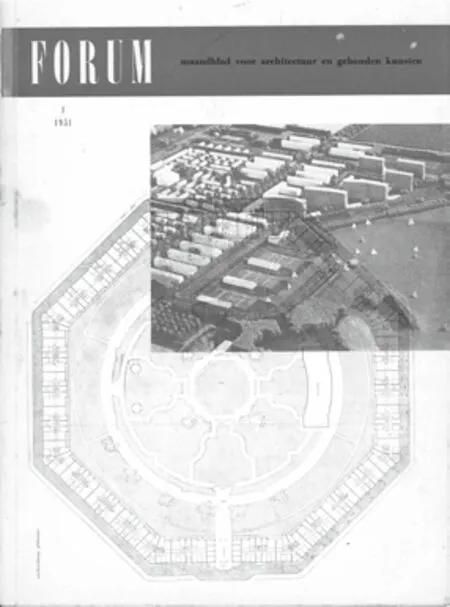
图5:《论坛》期刊封面(1951年第1期)

图6:工作中的巴克玛(J. B. Bakema)
九、《天主教建筑期刊》作为战后传统主义的阵地
荷兰有先锋而激进的一面,也有其传统而怀旧的一面。前文提到的格朗普雷·莫里哀教授(图8)和他创立的“代尔夫特学派”,这里有必要作进一步背景介绍。[34]“代尔夫特学派”得名于莫里哀1925—1955 年期间在荷兰代尔夫特理工大学任教授时创立的一支秉持传统主义的流派,可以看成是“贝尔拉格(H. P. Berlage)式理性主义”的一种延续。[35]二战后,莫里哀领导的“代尔夫特学派”运动,反对当时的现代建筑“功能主义”,以及“阿姆斯特丹学派”(Amsterdamse School)的“表现主义”(Expressionism)。其目的是为了复兴乡土的、传统的、民族的建筑风格,喜欢采用清水砖墙,极简的、“真实”(即传统和自然)的材料。这种思潮深刻影响了二战后教堂的设计,尤其是天主教建筑。在城市规划方面,除了前文提到的雷宁的重建,米德尔堡(Middelburg)重建也是受到了“代尔夫特学派”的影响,在战后重建规划中按照战前的传统形式,保持了历史的、如画的特色。二战后重新出版的《天主教建筑期刊》(图9),成了莫里哀 “代尔夫特学派”思潮的重要阵地。
1946 年10 月,《天主教建筑期刊》战后创刊号中回顾了其战争前后的出版历程:
“我们的期刊名称在战前是《罗马天主教建筑期刊》(R. K. Bouwblad),之后我们考虑到期刊应该不仅为罗马天主教利益服务,也为更广泛地治愈建筑和视觉艺术服务,于是我们把标题中的‘罗马天主教’几字去掉了……二战结束后的第三阶段,我们决定再次以《天主教建筑期刊》(Katholiek Bouwbiad)为期刊名称出版,但我们的目标仍保持不变。”[36]
毫无疑问,二战的结束对所有期刊都意味着一个新的开始。《天主教建筑期刊》把“天主教”加回的原因,是希望体现“每次重生都只能来自基督”的信仰,以及“对于艺术,每一次更新和复兴都只能产生于来自神圣艺术的冲动”的理念。[37]虽然《天主教建筑期刊》的声明强调了这本具有浓郁宗教色彩的建筑期刊得以重生的凭信,但这样的声明未留给其他阵营可以沟通的余地。
表面上看这似乎是带来了分裂,实际上《天主教建筑期刊》是渴望另一种他们理解的“团结”,即基督徒建筑师选择主动走出去,和专业领域的其他人分享自己信仰和实践[38]:
“许多人问自己……为什么除了《论坛》之外,这本(天主教的)建筑期刊仍在出版,他们认为这意味着分裂精神再次在我国这一文化生活的重要部分中出现。这完全不是事实。正如阿姆斯特丹建筑师协会所做的那样,当《论坛》试图团结这个在很多层面上分裂的社会内部所有的积极力量,从而执行一个国家级的任务,同样有必要从更高的视角来看待建筑……我们相信《天主教建筑期刊》有它的位置,所基于的立场是,一个基督徒可以隐居在教堂建筑的四面高墙内来实践他的信仰,但他的基督徒生活更应该对他生命的每一部分产生影响,因此这也应该包含他的专业实践。”[39]

图7:凡·登·布鲁克(J. H. van den Broek)像

图8:格朗普雷·莫里哀(M. J. Granpré Molière)画像(1941年)

图9:《天主教建筑期刊》封面(1950年6月第18期)
然而,许多人并不赞同这一观点,而是将《天主教建筑期刊》的重新出版视为一种宣战。二战后的荷兰,不乏来自现代主义反对“代尔夫特学派”的声音。例如J·弗兰德(J. Vriend)一篇文章题为“代尔夫特建筑的独裁”(Dictatuur van het Delftsche bouwen)的文章,认为许多城市用保守的方式进行着重建,而忽视了新的社会发展。弗兰德的批判直指莫里哀以及他传统主义追随者们进行的城市规划。又例如J·J·P·乌德(J. J. P. Oud)在《建造周刊》上发表的题为“代尔夫特学派:建筑与艺术的综合性 ”(De Delftsche school en de synthese in de architectuur)的批判文章。乌德反对任何关于建筑与艺术间的综合性,认为追求妥协将分散对本质的注意力,因此“必须默默地专注于自己的目标:建造良好与纯粹的建筑形式, 使其表达得尽善尽美,专注于当代的本质”。[40]
莫里哀通过深入而详细地回应这两篇文章,随后发起了对“新建筑”(Nieuwe Bouwen)的全面攻击。他攻击那些过分强调技巧的人:“为了获得和谐,一个人有时需要放弃那种专一的完美主义追求,尤其是当这种追求是贸然的、是在对美感缺乏正确的衡量标准的情况下进行的”。[41]莫里哀还撰写了一篇文章,阐述了“代尔夫特学派”与“新建筑”之间的区别。莫里哀自然对《论坛》里讨论米德尔堡重建计划的方式感到沮丧。但他当然也已经留意到了代尔夫特正经历一股转变之风,虽然他依然是那里最有权威的声音。这所技术性的学院需要现代化。对于莫里哀,代尔夫特是“推动技术进步的丰富血脉”。但他也期望“技术与艺术之间和谐关系的破裂”能在代尔夫特 愈合。[42]
巴克马、凡·登·布鲁克后来也加入到了与莫里哀之间有关现代主义和传统主义的论战[43],甚至上升为有关宇宙观与信仰的辩论[44],专业期刊领域的震荡也因此从一个时刻进入到另一个时刻,但这里也不再作长篇叙述了。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巴克马在他文章“新建筑及其他”(Het nieuwe bouwen en verder)对“自由”本质的解读,或许对任何一方都具有启发性:
“让我们认识到,民主是一种社会形式,宗教主义者和人道主义艺术家都可以在这种形式下工作,只要他们愿意合作并创造条件,使社会的每个成员都有尽可能多的机会成为一个完整的人,或者,换一种方式陈述就是,以他自己的方式渴望着无限和谐。在我看来,这就是自由的目的——这也是为什么乌德诉诸写作的原因,即使他用另一种的方式陈述了这个论点。”[45]
十、结语:思考,建筑,写作——皆是建构
二战后荷兰期刊,是在不同流派和团体的竞争与合作中,在他们寻求的各自发展与自我革新中,在建筑师、编辑、设计师的新老交替中,在理念和观点的不断辩论中,在期刊名称和内容的连续变化中,探索着自己的身份和前进的方向。正如《天主教建筑期刊》这个奇特的例子:不久之后,它先是改名为《建筑与视觉杂志》(Tijdschriftvoor Architectuur en Beeldende Kunsten),随后改成《生活建筑与视觉杂志》(Wonen TA / BK),之后又改为《Archis》(“Archis”这里是一个发明词,表示Arch-is,即探讨建筑是什么),在很久之后最终改名为《体量》(Volume)。通过这种方式,一本重要的专业期刊,发展出了自己的新动力,并充当了文化的测震仪。这种根据不断变化的环境而进行的不断更新,在荷兰建筑期刊的发展历程中成为一种常态。然而,这又是另一个奇妙的故事了。
译者后记:
原文是作为一个针对荷兰期刊的章节,以英文形式(转译自荷兰文)发表在由托斯坦· 施米德克内希特(Torsten Schmiedeknecht) 和 安 德 鲁· 佩 卡 姆(Andrew Peckham)主编的《现代主义与专业建筑期刊:战后欧洲之报道,编辑与 重 建》(Modernism and the Professional Architecture Journal:Reporting,Editing and Reconstructing in Postwar Europe,Routledge,2018)中。2019 年7 月10 日~ 13 日,凡·贝赫艾克教授访问苏州大学,并作关于荷兰“风格派”有关的学术演讲,之后与译者就本文内容进行了交流。为了方便中国读者的阅读,本文译者在全文翻译的基础上,进行了适当的调整、删节(部分删节内容放入注释中)和有关背景的补充。
注释
[1] [译者注] 王受之. 现代建筑史,第二版[M].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2:232.[2] [译者注] 王受之,2012:130.
[3] [译者注] 关于《de 8 En Opbouw》的兴趣范畴为译者补充。
[4] 相对其他国家,关于1945年以后的荷兰建筑期刊的研究较少。例如在英美,有两本针对英国期刊的专题论文展开研讨,参见:Erten,E. Shaping‘The Second Half Century’:the Architectural Review,1947-1971 [D]. MIT,MA:Cambridge,2004; Parnell,S. Architectural Design 1954-1972 [D]. Sheffield University,2011.
[5] NEUB URG-CO R AY,H. Die ausländis chen Fachzeitungen vom Gesichtspunkt des Grafikers aus betrachtet. Das Werk [J]. 30(8),1943:13.
[6] 关于阿姆斯特丹建筑师协会,参见:SCHILT,J. and VAN DER WERF,J. Genootschap Architectura et Amicitia 1855-1990[M]. Rotterdam:010 Publishers,1992. 关于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艺术期刊,参见:FREIJSER,V. “De kunsttijdschriften en de receptie van de modern kunst 1945-1951”,in Willemijn Stok vis(Ed.),De doorbraak van de modern kunst in Nederland. Vernieuwingen na 1945 [M]. Amsterdam:Meulenhoff,1990:173-191,219-222.
[7] 关于舒特马背景介绍为译者补充。
[8] Wendt,D. Academie van Bouwkunst Amsterdam 1908-2008 [M]. Rotterdam:010 Publishers,2008:96.关于1950 年荷兰社会现实的有趣图景,见:SCHUYT,K. and TAVERNE,E. 1951:Wealth in Black and White. Dutch Culture in European Context [M]. Den Haag:SDU,2000.
[9]但在该政策下,当时的交流合作最后并未成功。因为1929 年随着金融危机到来,意见分成了几派,不同观点通过不同期刊发声进行论战。
[10]科梅瑟联合了贝尔戈耶夫(J. F. Berghoef)、霍尔特(G. H. Holt)和斯蒂尔(A. Staal)一起想要构思一本新期刊,他们先是与军方当局进行谈判,然后在1945年6月申请到了出版许可。参见信件:The New Institute,Archive of the Association Architectura et Amicitia,ARAM 180. [译者注] 这本新期刊指后文将提到的《论坛》,贝尔戈耶夫、斯蒂尔等后来成为《论坛》的编辑。
[11] 该编辑委员会由几乎不知名的建筑师兼工程师谢林(H. G. J. Schelling,1888-1978)任主席。谢林的名声主要在荷兰的铁路建筑领域里。显然,编辑秘书长米拉斯才是联合刊最重要的负责人。
[12] [译者注] 译者根据上下文和其他相关资料的补充。
[13] Editorial Board. Preface [J]. Bouwkundig Weekblad,1(1),1946:1.
[14] [译者注] 译者根据上下文的归纳。
[15]这篇文章是米拉斯为建筑师凡·蒂钦(W. van Tijen)和马斯坎特(H. A. Maaskant)写的一篇关于国家航空实验室的文章做后记,凡·蒂钦等将这些当下的建筑视为 “现代建筑的代表”。
[16] MIER A S,J.P. Naschrif t [J]. Bouwkundig Weekblad,64(6),1946:69.
[17] Editorial Board. Preface [J]. Bouwkundig Weekblad,1(1),1946:1.
[18] [译者注] 译者根据上下文的归纳。
[19] [译者注] 这里不得不先简要提及美国现代主义建筑影响返流的背景。1920 年代初,荷兰“风格派”核心领袖杜斯伯格通过到包豪斯讲学,对包豪斯学院体系的建立产生了重要的影响。1930 年代,包豪斯被纳粹政府关闭后,包豪斯主要领导人和大批学生为躲避战火而移居美国,并把集欧洲现代主义设计探索之成果带到了美国。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国际主义风格”(International Style)成为包豪斯的影响在美国的土壤上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现代主义设计风格,在二战后迅速成为全世界效仿的标准。参见:王受之,2012:182,190,233,245。
[20] MIERAS,J.P. Het Pentagon-gebouw te Arlington bij Washington [J]. Bouwkundig Weekblad,64(4),1946:45.
[21] MIER A S,J.P. Ee n nie u w tijds chrif t [J]. Bouwkundig Weekblad,65(7),1947:57.
[22] MIER AS,J.P. Progressief [J]. Bouwkundig Weekblad,65(16),1947:127.
[23] [译者注] 译者整理补充。
[24] VAN DEN BROEK,J. H.‘De artistieke en sociale positive van de architect’,in J. P. Mieras,Liber Amicorum J. P. Mieras [M]. Amsterdam:B. N. A.,1958.
[25] [译者注] 译者整理补充。
[26] Jongeren en nieuwe architectuur [J]. Forum,2(4),1947:103.
[27] VAN EMBDEN,S. J. Wanordelijk artikel bij Rotterdam’s stadsplan [J]. Forum,2,1946:33-47.
[28]在 西 里 蒙 斯(K. L. Sijmons)对 米 德 尔 堡(Middelburg)重建规划进行批评之后,他就与他的合作编辑贝尔戈耶夫(J. F. Berghoef)就设计原则发生争执。其结果是贝尔戈耶夫后来从编委会退休,他的位置由博肯(A. Boeken)取代,后者所持的立场不那么保守。但期刊随后的发展方向也几乎没有改变,主要是因为米拉斯作为荷兰建筑师协会的代表也加入了编委会。然而,米拉斯在《论坛》期刊中的影响是有限的,因为他不是编辑秘书长。这个职位由艺术史学家、荷兰国立博物馆馆长施利尔(Th. H. Lunsingh Scheurleer)担任。
[29] 参 见 会 议 记 录:Het Nieuwe Instituut,Archief van het Genootschap Architectura et Amicitia,ARAM 179。
[30] [译者注] 参见:褚冬竹. 荷兰的密码:建筑师视野下的城市与设计 [M].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2:186.
[31] 凡·登·布鲁克有多重职责,并活跃在多个方面:他是各种咨询委员会的成员,也积极参与建筑师国际联合会(Union Internationale des Architectes,简称:UIA)的工作,并在建筑中心(Bouwcentrum)和《建筑》期刊的建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他还参与“美好生活消费基金会”(Consumentenstichting Goed Wonen)及其同名期刊的工作。这是抵制劣质住房的宣传运动,通过具有吸引力的设计拓展受众。期刊采用有着家具和家居内饰的插图,散发出现代生活方式的气息。1959年它已拥有6000订阅量,此时期刊决定将重点从设计和材料方面的建议,转变为对一般和特定住房策略的关注。范登布鲁克在其中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力,并偶尔为期刊撰稿。毫无疑问,凡·登·布鲁克是荷兰战后建筑文化中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此外,他参与了许多实际建造项目,并从1948年起与巴克马合作。他们一起在鹿特丹林班街(Lijnbaan)留下了自己的印记,该项目也获得了世界范围的认可。
[32] [译者注] 1959 年,CIAM内部由于新老两派的分歧激化而宣告解散。参见:刘先觉,汪晓茜. 外国建筑简史[M].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0:211; 关于荷兰“结构主义”,参见:朱亦民. 迷宫式的清晰:荷兰结构主义建筑[EB/OL]. [2016-06-28]. https://www.archiposition.com/items/20180525100545
[33] [译者注] 这个重大事件的背景是,当时一些建筑师对CIAM的“功能主义”(Functionalism)的不满。CIAM成立于1928 年,提倡建筑设计和城市规划以功能为设计的中心和目的,而不再以形式作为设计的出发点,对荷兰战后重建影响很大。虽然这种“功能主义”的根源是社会主义立场的,是主张设计为大众而非少数权贵服务的,其精神核心是民主,这成为它创立早期的内在驱动力和生命力,然而,强调物质功能和结构合理性的规划方法,也在荷兰战后重建中,制造了一批基于清晰的功能区划、但脱离生活习俗,和缺乏人情味的功能城市。这招致具有独立见解的新一代荷兰建筑师的怀疑。参见:王受之,2002:133,233.
[34] [译者注] 关于“代尔夫特学派”的背景介绍为译者整理补充。
[35] [译者注] 贝尔拉格(H. P. Berlage)在20 世纪初进行的一系列传统形式的“理性主义”实验,以阿姆斯特丹证券交易市场为其代表作。关于贝尔拉格传统形式的“理性主义”实验、关于阿姆斯特丹学派“表现主义”,参见:[荷] J. J. P. 奥德,刘忆(译). J. J. P. 奥德谈荷兰建筑 [M]. 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9:25-54.
[36] Editorial Board. Het Bouwblad herrezen [J]. Katholiek Bouwblad,1(1/2),1946:1.
[37] 同上。
[38] [译者注] 译者整理补充。
[39] Editorial Board. Onze plaats te midden van de vakbladen [J]. Katholiek Bouwblad,1,(1/2),1946:0.
[40] OUD,J.J.P. De Delftsche school en synthesis in de architectuur [J]. Bouwkundig Weekblad,64(24),1946:222; Oud,J.J.P. Durven en niet durven in de architectuur [J]. Bouw,1(29),1946:613-615,620.
[41](原文:“One sometimes has to move away from single-minded perfection for the sake of harmony especially when this is not identified with the correct measure of beauty,but rather prematurely determined.”)Molière,M. J. G. Ter inIeiding [J]. Katholiek Bouwblad,1(1/2). 1946:8.
[42] 在莫里哀看来,“新建筑”试图消除艺术、建筑和城市规划之间的界限,是走过了头:“我并不是说代尔夫特的思想家是独裁者,他们(自己)的信条谴责这一点。我也没有说‘新建筑’的大师们是暴君,而是他们的教义要求他们如此。均一化(译者注:‘均一化’这里指该‘新建筑’思潮只认同现代建筑,不认同其他类型的建筑,缺乏宽容性)作为‘新建筑’的本质属性,应当严格地强加给建筑师们; 然而,等级和多样性的信条,则自然应当宽容自由。”(原文:"I am not saying that Delft thinkers are dictators,but their [own] doctrine condemns this. Nor do I claim that the masters of the Nieuwe Bouwen are tyrants,but their doctrine commands them to be so. The uniformity,which is inherent to the Nieuwe Bouwen,should stringently impose this on architects; yet the doctrine of hierarchy and variety naturally should allow for freedom.”)Molière,M. J. G. Delft en het nieuwe bouwen [J]. Katholiek Bouwblad,14(4),1947:156.
[43] 凡·登·布鲁克发表了一篇题为“建筑的目标和本质”的论文,对此作出了简洁回应,他于1947年1月15日在阿姆斯特丹以此为题做过一个演讲,见:Van den Broek. Doel en wezen van de architectuur [J]. Forum,2(2/3),1947:69-70.
[44] 后来巴克马用莫里哀自己的推理方式来迎击他:“什么比基本的人类-宇宙关系更强大? 什么能比一个无声的星夜或一个遥远海岸的暴暴风雨,或儿童的眼睛和向日葵更能说明我们的想象力,甚至超越时间?什么可以带来更多的融合与启发?是基督信仰吗? 在一个充满教会和教会官员的世界中发生过两次世界大战之后? 有且只有一个空间概念,仍然是不可触碰。我们的空间只能是宇宙。”(Bakema,1947)(原文:“What is stronger than the primary Human---Cosmos relationship? What speaks more to our imagination,and even transcends time,than a silent starry night or a violent storm over far-away shores,or the eyes of children and sunflowers? What can integrate and inspire more? Christianity? After two world wars in a world full of Churches and Church officials? There is but one spatial conception,that which remains untouchable. Our space can only be Cosmic.”)这 极尽含蓄的话语,是巴克马在意识地嘲笑他的对手。这场战斗已进一步白热化—— 凡·恩登在文章里写道:“争执又重新开始了——但没有由鲁道夫·施瓦茨等人在德国发起的‘包豪斯之辩’那么激烈。”见:VAN EMBDEN,S. J. IJdel dispuut:De oorlog is voorbij:het krakeel herleeft [J]. Bouw,1(29),1946:617-621.
[45]原 文:“Let us realise that Democracy is a societal form in which both religious dogmatists and humanitarian artists can work,provided they show a willingness to cooperate and create conditions in which every member of society has the biggest possible chance of being a complete human being or,stated differently,to in his own way aspire to harmony with the infinite. And that,in my opinion,is the purpose of freedom—and the reason that Oud reached for the pen even if he stated it [the argument] differentl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