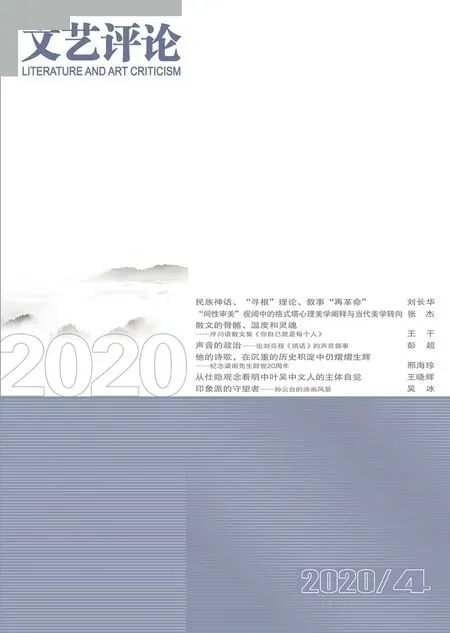从仕隐观念看明中叶吴中文人的主体自觉
2020-04-18王晓辉
○王晓辉
汉代刘向在《说苑》中对“士”下定义道:“辨然否,通古今,谓之士。”“士”,作为我国古代社会阶层的一个特殊群体,他们学识渊博,贯通古今;作为我国古代知识分子阶层的精英部分,他们胸怀天下,以道自任。无论世事如何变幻,他们始终秉承儒家“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的传统教义,执着地奔波于庙堂与江湖之间。对他们而言,能够跻身庙堂,行辅佑君王、经世安邦之责,是最大的幸事。但当这种“幸运”被现实的种种困境阻断时,他们往往会走向反面,选择隐居于林泉,持守于江湖。“誓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齐,“每辄言佳”的司马徽,“采菊东篱下”的陶渊明,“仰天大笑出门去”的李白都是此类士人的代表。尽管他们选择的隐逸方式有所不同,但他们在隐逸中所表现出的高洁品性和超脱之姿却是一致的。或许正是有了这些隐逸高士的召唤和启迪,历代失意士人才能够在“献身政教、至死靡它”的入仕法则外觅得一条全身而退的道路,并在进退出处的磨砺间形成一种特有的隐逸文化。
一、袭与变:吴中文人的隐逸观
吴中文人的隐逸传统是具有广泛传承性质的。祝允明在《金孟愚先生家传》中论述了吴中隐逸的传承性特征:
吴最多隐君子,若杜公者,函中蹈靖,何其凤德之盛与!其一于狷独者,邢氏与故沈诚希明。有名隐而专与世事者,赵同鲁与哲,顾亮亦然,而金孟愚乃略同之。亦各从其志也。今杜、赵之后,乃涉荣途,邢、顾、沈皆无闻。金之子成性,守素慕文,不令家声委地,辑述先事甚勤,又乞余特传之,亦孝矣哉!①
这段论述涉及了杜琼、邢量、沈诚、赵同鲁、顾亮等多位隐逸之士,其中杜琼、赵同鲁为沈周的师傅,沈周的祖父沈澄、父亲沈恒、伯父沈贞也是远近闻名的隐士。可见吴中文人的隐逸行为并不仅仅局限于个人,有的是家族性的甚至是区域性的。
明中叶吴中文人的隐居传统,大多延续元末吴人隐逸的流风余波。为逃避无可救药的乱世,元末士人大都无心仕进,终日优游于清泉林石之间,论文赋诗,挥麈谈玄。其中,最为当时士大夫称赏的是昆山顾瑛主持的文士雅集。据顾氏自编《玉山名胜集》记载,从至正八年到二十年,在其私家园林“玉山草堂”中举行的大小集会就达五十余次,参与人员达一百四十余名,其中有诗人、古文家、书画家、乐师、鉴古家、歌姬舞女乃至艺人墨工等。这种集会常常是文学、艺术的交流活动,规模之大、内容之丰富远远超过历史上的文士雅集,被后人称为“风流文采,照映一世”。
这些集会的组织者——顾瑛,既是一位豁达大度、豪侠慷慨的富商,又是一位颇具自省意识和哲学思维的隐逸高士。在他的《玉山纪游》中记载着这样一幕:至正十一年正月初四,他独自乘舟,停泊在苏州垂虹桥下,面对着寒冬:“蓬窗独坐,静思世情,真堕幻境,更欲如‘雪巢’之清会不可得也。”②这种静谧和惆怅,既是对喧嚣繁杂的世情的沉淀,亦是对人生进退出处的深层思考。顾瑛《自题摘阮小像》一诗,抒写的正是这样一种萧朗静谧的隐逸境界:
自家面目晋衣冠,写入林泉又一般。手摘阮琴秋寂寞,断鸿飞处水漫漫。
此诗极具画面感。画面中的诗人独处在寥阔秋色之中,远处一派澹荡的水,长空里飞鸿远翔。这样阔大的自然空间,幽邃的意境,映衬出诗人寂寥的情怀,充盈着无限的情思。这使人联想到晋人那种萧朗、悠远的风韵,但“自家面目晋衣冠”,诗人指出,这不是历史的一个摹本,与晋人优雅的风度相比,“自家面目”别具一种自信、高妙的风韵。
元末以“隐”著称的高士还有高启。高启的隐逸生活不像顾瑛那样潇洒而安逸,而是始终交织着焦虑、忧郁、渴望、痛苦、惊惶等种种复杂的心绪。纵观历代隐逸文人,谁也不曾像高启那样表现出精神上的矛盾和困惑。他暂借其岳父住宅隐居青丘,惬意于田园的静美:“远见帆度川,高闻鸟鸣柳。孰云非吾庐?居止亦可久。”(《初开北窗晚酌,时寓江上外舅周隐君宅》)而强烈的自尊心又使他萌生“客中常耻受人怜”(《秋日江居写怀七首》之六)之感;他喜爱闲暇和孤独,却时而又有“虽欣远物累,终悲寡交亲”(《答宋南宫间寄》)的孤独落寞;他渴望忘却忧愁:“日暮欲忘忧,搴芳转伤抱”(《萱草》),可对自我的不满却时时袭上心头:“进无适时材,退乏负郭田。”(《始迁西宅》)这种时而欢欣、时而悲伤,时而希望、时而绝望的情绪几乎伴随高启的一生。而导致此种心境的原因一方面来自于乱世中刀光剑影的恫吓,另一方面来自于内心深处渴望出仕却生不逢时的苦痛。
不论是顾瑛的适意型隐逸,还是高启的痛苦式隐逸,比之于明初的吴中文人,他们还是比较幸运的,因为元末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使他们可以超脱政治之外,尽情地享受聚会雅集的欢畅,反复地舔舐身心的悲伤。从另一个角度看,元末文人又是悲哀的,风云变化的乱世剥夺了他们经邦济世的权利。面对摇摇欲坠的昏聩王朝,他们只能将救世之志压制到内心深处,并将其小心翼翼地保存下来,等待“盛世明君”的开启。高启《野潜稿序》云:
夫鱼潜于渊,兽潜于薮,常也;士而潜于野,岂常也哉?盖潜非君子之所欲也,不得已焉尔。当时泰,则行其道,以膏泽于人民,端冕委佩,立于朝庙之上,光宠煊赫,为众之所具仰,而潜云乎哉!时否,故全其道以自乐,耦来耜之夫,谢干旄之使,匿耀伏迹于畎亩之间,惟恐世之知己也,而显云乎哉?故君子之潜于野者,时也,非常也……《传》曰:“君子在野。”《书》曰:“野无遗贤。”是时不同,而君于之有潜显也。然时可潜类,而欲求乎显,则将枉道以殉物;时可显矣,而欲事乎潜,则将洁身而乱伦!故君子不必于潜,亦不必于显,惟其时而已尔。凡知潜、显之时者,可以语夫道:不然,难乎其免矣。③
非常明显,元末文人的隐逸是待时而动的。“隐”并不是他们的人生目标,而是因为“时否”而做出的“不得已焉尔”的无奈之举,目的是为“养其材以待作乐者之用”。客观而言,身处血雨腥风的乱世,“潜于野”以“全其道以自乐”的举动是元末文人自保的最佳方式,但这种方式的选择多少带有些无奈与悲凉的意味。
有明一朝是推翻元蒙统治后建立起来的以汉人为主体的政权,此种形式的改朝换代为国家和民族带来了统一和安定,更给隐居林泉的文人带来了出仕的机遇和希望。明朝的开国之君朱元璋是一个礼贤下士、爱才亲贤的开明君王。早在渡江前后,他已四方搜罗香儒文士,创礼贤馆处之。立国之初,又多次下诏求贤。但同时他又是一位嗜杀成性、守旧偏激的狭隘君王。对于那些不愿出仕、不肯合作的文人士子,他的态度是“诛其身而没其家”,在这种霸气十足、残酷十足的屠杀政策下,不肯出仕或者已经出仕的文人都鲜有善终者。赵翼记曰:
文人学士,一授官职,亦罕有善终者。宋濂以儒者侍帷闼十余年,重以皇太子师傅,尚不免茂州之行,何况疏逖素无恩眷者。如苏伯衡两被徵,皆辞疾,寻为处州教授,坐表笺误死。郭奎参朱文正军事;张孟兼修史成,仕至佥事;傅恕修史毕,授博野令,后俱坐事死。高启为户部侍郎,已放归,以魏观上梁文腰斩。张羽为太常丞,投江死。徐贲仕布政,下狱死。孙荬仕经历,王蒙知泰安州,皆坐党死。其不死者,张宣修史成,受官,谪驿丞。杨基仕安察,谪输作。乌斯道授石龙令,谪役定远。此皆在《文苑传》中。当时以文学授官,而卒不免于祸,宜维祯等之不敢受职也。④
作为一个对历史进程发生影响的人物,在对待人才问题上,朱元璋的历史视界过于狭隘,缺少一代君王应有的宽容与大度。他的那些残酷的惩罚措施,只能证明其君主力量的权威与强硬,但永远不可能征服文人士大夫坚毅而倔强的内心。面对“茅庐三顾”的知遇之恩,他们或许会俯首称臣,并为之鞠躬尽瘁;但面对残酷无情的杀戮,他们所能做的只能是抗争或抗争不得后的冷漠、压抑进而麻木。
在朱元璋的高压政策下,吴中文人自然也难逃杀戮之灾。洪武年间,吴中文士因政治原因致死的有顾瑛、陈汝言、申屠衡、高启、王彝、徐贲、张羽、杨基、王行、卢熊……其中被后世誉为“吴中四杰”的高启、杨基、张羽、徐贲,因为少才高,又因高启、张羽死得极惨,后人把他们比作“初唐四杰”,深加挽悼。
在明初先辈们血的教训的震吓下,明中叶的吴中士人在仕隐问题上,视野和心态逐渐变得理性且和缓。他们睿智地认识到,明朝险恶的政治环境已经不允许他们像元末文人那样完全隐居,但是出仕为官又遭受杀身之祸,这一“仕”与“隐”之间的矛盾促使他们形成了更加圆通的生存状态。他们一改前人那种不肯合作的态度,以一种更加通达的心态对待出仕。得之,可也;不得之,亦可也。在他们看来,那种献身政教、至死靡它的执着固然可敬,但身家性命的保全和世俗之乐的获得也是人生中值得追求之事。于是,面对君主的征召,他们不再坚决推辞,而是婉言以拒;面对政治之争,他们不再直声廷杖,而是以融通的心态接纳或者回避。朝堂之上,吴中文人不再锋芒毕露、咄咄逼人;朝堂之下,他们也不再党同伐异,相互倾轧。他们开始以一种置身事外的冷静来看待世事的纷争,以一种近乎冷漠的回避来保全身家性命。在谈到“以死劝谏”这一现象时,文徵明的看法是:“若夫矫抗直前,靡所顾藉,而慷慨激烈,以阶祸首,难以求必胜。夫刚此足以收其名而已,天下之事何赖哉?”⑤反对激进,厌烦争斗,主张平和,文徵明的这种平和自保的心态在吴中文人中极具代表性。严迪昌认为,这种心态在吴中文人中辐射成浓重的文化“场”,到了明中叶以后成化、弘治、正德、嘉靖四朝得以充分发展。稳定成地域的文化精神,即特定空间群体性趋从的一种意识形态。受此影响,吴中文人在隐逸方式的选择上也呈现出一种“群体性的趋从意识”。即,不再看重是否做官,是否隐居山林这一外表形式,而是看重内心是否得到自由、生活是否适意这一实质。
明中叶的吴中士人那里,隐逸的形态和地点是可以随意选择的。寄身名山、栖息山林可也;隐于乡间、居于闹市可也;隐于庙堂、献身朝廷亦可也。隐逸不必与仕隐相关,不必与时俱变,不再由时之泰否决定,只要内心有隐逸之想,便可不拘形迹,触处皆隐。“隐”,既可以付诸实践,也可以只是心中之想,关键是要保持一种圆融冲和、乐观豁达的心态。
隐居山林丘壑者,其志高远,其行超逸。如王宠、桑悦辈。王宠《隐》诗云:
心与迹俱隐,且随云恣行。江湖元自阔,笼槛任须争。山意犹含雪,林歌稍灭莺。天涯望春色,醉倚越王城。
桑悦《入山》诗云:
幽子寻幽兴,随云入乱山。清秋兴不极,尽日影俱闲。灵籁追长啸,残霞映醉颜。脱身尘土外,心静是真还。
王宠与桑悦之“隐”,乃是藏身山林丘壑、息心灭迹之隐。轻车肥马、功名富贵非其所慕,超脱尘世之外,或“清吟”为乐、或把酒而歌,才是他们的志向所在。
隐于闹市乡间者,其志淡泊,其行潇洒。杜琼诗曰:
每求贤诏下,有司辄首举,郡守况钟两荐之,固辞不出……戴鹿皮冠,持方竹杖,出游朋旧,逍遥移日,归而菜羹粝食,怡怡如也。
⑥沈周诗曰:
有竹居,耕读其间,佳时胜日,必具酒肴,合近局,从容谈笑,出所蓄古图书器物,相与抚题品玩以为乐。晚岁益盛,客至益多,户屦常满。⑦
虽言隐居,却不拘于平淡。与一二友人聚会、听琴、品茗、游览……你来我往,酬唱赠答,诗酒宴笑,乐此不疲。此种隐居生活虽无山林高士的高雅,但也因生活的多彩而别具韵味。
隐于庙堂府邸者,其志超然,其行独立。如吴宽:
公(吴宽)好古力学,至老不倦,于权势荣利则退避如畏然。在翰林时,于所居之东治园亭,杂莳花木,退朝执一卷,日哦其中;每良辰佳节,为具,召客分题联句为乐,若不知有官者。⑧
吴中文人的这种“自由随意,不拘形迹”的隐居形态,沈周将其定义为“市隐”。沈周《市隐》云:
英言嘉遯独终南,即此城中住亦甘。浩荡开门心自静,滑稽玩世估仍堪。壶公溷世无人识,周令移文好自惭。酷爱林泉图上见,生嫌官府酒边谈。经车过马尝无数,埽地焚香日载三。市脯不教供座客,户墉还喜走丁男。檐头沐发风初到,楼角摊书月半含。蜗壁雨深留篆看,燕巢春暖忌僮探。时来卜肆听论易,偏见邻家问养茧。为报山公休荐达,只今双髩已毿毿。
杨循吉《叶氏南隐记》以散文笔法对此诗进行了解析:
盖吴城之外,清丽之佳地也,有南濠焉,带□(原字不清)通村,而君居之。以不仕称隐也。是地也,深无山,密无林,远无江湖,日扰扰乎与人迹相逐也。况君之家肆临通衢,有一客及门,则必以衣冠见。虽欲隐也,无由矣。噫嘻,山林江湖能生躁心,古不有神放乎?如其隐者,门如市,心如水耳。人在善藏,藏则其生也完矣。妻子室家人之有也,乌能逃之?世之仕者,则既不能藏矣。然不仕者,又岂皆能藏哉!何所无事,逐之则生;何所无人,上之则争。事不能皆却,人不能皆谢,在乎共貌独怀,心山林,身城郭而已。
“心山林、身城郭”,杨循吉用简单的六个字便精确地概括出了明中叶吴中士人的多样隐逸形态。其实,沈周、杨循吉所谓的“市隐”即是“处处皆可隐”之意。可以藏之名山、隐于大川,可以居于闹市、身藏通衢,也可以隐于庙堂、心存江湖。所谓的“隐者”乃是一个“可官可民”的多面性人物。既可以是采菊东篱的适者,也可以是诗酒宴笑的闲者,好古力学的智者。不管隐逸的环境怎样,隐者的身份如何,这些皆不重要,重要的是心灵是否真正得到了解脱、净化,身体是否得到了休息、享受。
明中叶吴人的“市隐”思想表明:与同时代的他域士人相比,吴中文人是较为现实的,铁马金戈、大漠江山、仙风道骨、高山流水等他们都不感兴趣,因为这与他们的现实生活相距太过遥远。他们更愿意从实在的世俗生活中体会人生乐趣,享受生活的自在。因为在这种真实的生活中,他们能够找回真正的自我,而这个“自我”才是他们生之所系的真谛。
二、进与退:吴中文人的参政观
吴中文人是乐于隐逸的,但隐逸之乐并不能掩盖他们关注时政、忧心庙堂的议政意识。尽管身处林泉,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如沈周、文徵明、祝允明等仍对政治有着相当的热情;尽管不愿投身复杂政坛,但他们仍时刻关注着时事及时局的变化,并表现出自己或主观或客观、或冷静或激烈的态度。身在江湖,心仍存魏阙,只是这种“存魏阙”的成分会随着朝政的清明或黑暗而有所增减。
沈氏家族以多出隐士而闻名吴中,沈周更是吴中文人隐逸的典范。但即便如沈周这样立志终生不仕的乡野文人,内心仍时刻关注时局,忧心朝政。文徵明的《沈先生行状》记载王鏊和沈周讨论讽谏还是直谏一事,其中的一段对话表明了沈周的政治态度:“‘彼以南面临我,我北面事之,安能尽其情哉?君子思不出其位,吾尽吾事而己。’然先生每闻时政得失,辄忧喜形于色。人以是知先生非终于忘世者。”⑨沈周的“非终于忘世”,首先表现在对国家政事的关注上。《己巳秋兴》云:
灯火郊居耿暮秋,北风迢递入边愁。三更珠斗随天转,万里银河接海流。筹笔简书何日见,新亭冠盖几人游。侧身自信江湖远,一夜哀吟到白头。
此诗沉郁顿挫,颇具伤时忧国之思。《沈周年谱》认为该诗作于“土木堡之变”之后。沈周此诗正是闻“土木堡之变”后所作。“一夜哀吟到白头”,一个“哀”字,说尽了诗人挂念君王、忧心朝政的良苦之心。
为一个生于市井又隐于市井的隐者,沈周的政治观念更多地表现在对民生疾苦的关心上,体现着“天下归仁”的情怀。其他诗作《割稻》《低田妇》《堤决行》等表达了对底层百姓生活悲惨的关心和悲悯。《十八邻》一诗写尽了遭受水患后百姓生活的凄惨,让人不忍卒读:
嚼草草亦尽,仰面呼高天……浑舍相抱哭,泪行间饥涎。日夜立水中,浊浪排胸肩。大儿换斗粟,女小不论钱。驱妻亦从人,减口日苟延。风雨寻塌屋,各各亦为船。
沈周“非能忘世”的心态在明中叶文人圈中极具典型性,其弟子文徵明便明显受到了他的影响。与其师相同,文徵明也对“土木堡事变”进行了记载;与其师不同,文徵明是通过对民族英雄于谦的褒扬侧面反映此事的。其《读于肃愍旌功录有感》二首云:
南迁议起共仓皇,一疏支倾万弩强。既以安危系天下,曾无羽翼悟君王。莫嫌久假非真有,只觉中兴未耿光。浅薄晚生何敢异,百年公论自难忘。
老臣自处危疑地,天下遑遑尚握兵。千载计功真足掩,一时起事岂无名?未论时宰能生杀,湏信天王自圣明。地下有知应不恨,万人争看墓门旌。
于谦(1398一1457),明永乐十九年进士,曾任监察御史,兵部右侍郎,后升任兵部尚书。英宗正统十四年,土木堡之变时,英宗被俘,侍讲徐理主张南迁,于谦坚决反对,并拥立英宗弟为景帝,主持军务,击退了也先。景泰元年,也先请和,送返英宗。景泰八年,徐有贞、石亨等发动“夺门之变”,拥立英宗复位,后又诬陷于谦谋逆,将其处死。于谦死后被追谥忠肃。
上面的两首诗对于谦在“土木堡”事件中的表现进行了褒扬。“仓皇”“遑遑”,写出了事件发生后朝廷的慌乱,把议南迁众人的慌乱与于谦一个人的独立支撑大局相对照,表现出他的临危不惧和大智大勇。但全诗的重点却不在于此,而在于对谦惨遭被害原因的探讨上。“曾无羽翼悟君王”,一个“悟”字,指出了于谦悲剧的原因所在。他关心的是国家、人民,而忽视了国家的实际掌控者君王的利益。他没有意识到为国为民抛头颅、洒热血而忽视君主利益的严重后果。在君主眼中,为国亡,可叹也;为君死,可敬也。于谦正是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才招致了“千载计功真足掩”的悲惨结局。诗尾“百年公论自难忘”,“万人争看墓门旌”两句,既鲜明地体现出了文徵明的褒扬好恶,也反映出了百姓对于谦这位民族影响的由衷敬佩。
与此二首作于一时的《因读旌功录有感徐武功事再赋二首》,写的是对徐有贞之过的批评。徐有贞是吴中的阁老前辈,又是祝允明的外祖父,但这并不影响文徵明对他的过失进行客观评价。“白璧微瑕尤惜者,当时无用议迁京”“冤哉一掬江湖血,信史他年未必书”。犀利尖锐,一针见血,由此可以看出文徵明敏锐的政治眼光,亦可看出其刚正不阿的秉性。
与沈周一样,文徵明既有着关注家国大事的政治眼光,又有着体恤天下苍生的儒者情怀。如《采桑图》一首,写采桑女“只愁墙下桑叶稀,不知墙头花乱飞”的忧虑和辛苦,并对她们生活的穷苦表现出深深的同情:“一春辛苦只自知,百年能着几罗衣?”
在明中叶的吴中文人圈中,唐寅是最具特性的。他才华出众,潇洒倜傥。他沐浴着儒家仁爱之风长大,却敢于违背礼教,终日与舞女歌妓为伴;他立志科举入世,却因蒙冤受辱而放弃追求,终日以狂呼豪饮为务;他发愤创作,希冀立言垂世,却因不甘寂寞而半途而废,平生以卖字鬻画为生。就是这样一个狂放不羁、视传统价值观直如破屣的叛逆士人,内心深处竟也有着关心民瘼、系念苍生的仁爱情怀:
天子睿圣,保障必须贤令,赋税今推吴下盛,谁知民已病!以自公临邑政,明照奸豪如镜。敕旨休将亲侍聘,少留安百姓。⑩
此诗是唐寅为送别一位不知名的吴县县令而作。诗中,唐寅直言不讳地道出了吴中赋税繁重、民不堪苦的境况。“九重夜半虚前席,定把疲癃仔细陈”。“九重”指代皇帝,“夜半虚前席”,为垂询意见之意。他希望县令能够在君王面前为民请命,使吴人摆脱赋税之苦。唐寅生性率真正直,卑微的出身和坎坷的遭际使他有机会接近下层民众,体察民间疾苦。目睹民生多艰,便生恻隐之心并发而为诗词,这对倜傥不羁的唐寅而言实在是难能可贵的。
值得注意的是,吴中文人的不能忘世不独体现在诗文作品中,还体现在对科举考试汲汲以求的态度上。与吴人“乐隐”现象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吴地自明代建国一始“科名之盛,特冠海内”,吴人多愿追逐科名,富贵之家自不必说,如文徵明凡九试,祝允明凡七试,蔡羽凡十四试,可谓呕心沥血、旷日持久;平凡布衣家庭稍有盈余者,亦敦促弟子立志科考,博取功名。即便家贫者也执着于科举,无有懈怠。如徐祯卿自幼家贫,无钱蓄书,所阅书皆与人借读。在吴中地区,如徐祯卿者大有人在。
一面积极地倡导并践行隐逸,另一方面又汲汲于科举功名的追求;一面逍遥于山水田园之乐,而另一方面又对庙堂政治念念不忘。在隐逸还是参政的选择上,吴中文人似乎陷入了矛盾的怪圈。其实仔细思考便可发现,“仕”与“隐”在吴中文人这里并不是互相矛盾的,而是彼此补充的。吴中文人并非不愿入仕,只是与同时代的其他士人相较,他们对入仕内涵的理解更加平和、豁达。科场得意,能顺利入仕,自是幸事;科场不顺,入仕不果,他们也能够坦然地接受并自得其乐地隐居自活,且这种隐居生活并不妨碍他们关注并干预时政。在吴中士人的心中,入仕已经不再是实现生命价值的唯一出路,致力于诗文书画的创作并以此为生,满足于平凡的生活并以此为乐,也未尝不是人生幸事。
归结到一点,明中叶吴人的思想观念是通达的,是进步的,他们习惯于进行多维思考,而不是固执地拘泥于一端。他们聪明地意识到,政治上的飞黄腾达与生活上的安逸自足同样重要。正是有了这种通达观念的支撑,吴中文人才能安于隐逸并进而乐于隐逸,而此种通达观的形成,与当时吴中经济的发达及文化氛围的浓厚密切相关。
1.渐为多元的生活
明中叶的吴中,交通便捷、物产丰饶,优越的地理环境和开放的观念带来了经济的发展与商业的繁荣,于此相应,经济的发达又生发和带动了人们世态风俗的改变。对吴中世风的传承与转变,记载较多。范成大《吴郡志》记曰:“吴中自始号繁盛,四野无旷土,随意高下悉为田。人无贵贱,往往皆有常产。以故俗多奢少俭,竞节物,好游遨。”张瀚在《松窗梦语·百工纪》中记载:
至于民间风俗,大都江南奢于江北,而江南之奢莫过于三吴。自昔吴俗习奢华、乐奇异,人情皆观赴焉。吴制服而华,以为非是弗文也;吴制器而美,以为非是弗珍也。四方重吴服,而吴益工于服;四方贵吴器,而吴益工于器。是吴俗之侈者愈侈,而四方之观赴于吴者,又安能挽而之俭也。盖人情自俭而趋于奢也易,自奢而返之俭也难。
经济的繁荣和世风的变化带来了世人心态的转变,“重本抑末”“崇义黜利”的传统观念迅速消解,取而代之的是对物质的追逐和对金钱的崇尚。与奢华膨胀的世风相适应,各种相关产业应运而生,最为突出的就是书画、诗文、古董等的买卖与收藏。这些行业的兴起不仅为士人实现人生价值提供了可能,也为他们在“入仕途、得俸禄”的传统选择之外又拓展了一条谋生之路。在明中叶的吴中,行商坐贾已经不再是羞于启齿之事,靠卖书鬻文以维持生计在文人中已司空见惯。
李诩《戒庵老人漫笔》卷一“文人润笔”条,记载了吴中士人卖书鬻文一事:
嘉定沈练塘龄闲论文士无不重财者,常熟桑思玄曾有人求文,託以亲昵,无润笔。思玄谓曰:“平生未曾白作文字,最败兴。你可暂将银一锭四五两置吾前,发兴后待作完,仍还汝可也。”唐子畏曾在孙思和家有一巨本,录记所作,簿面题二字曰“利市”。马怀德言:曾为人求文字于祝枝山,问曰:“是见精神否?”(俗以取人钱为精神)曰:“然。”又曰:“吾不与他计较,清物也好。”问何清物,则曰:“青羊绒罢。”
这段论述了唐寅、桑悦和祝允明三人,他们饱尝科场落地之苦,皆无官资俸禄可用,但三人的生活却未陷入窘困,因为卖文鬻画所得酬资足够他们日常花费和生活所需。谈到这种自给自足的生活,唐寅颇为自豪地说道:“不炼金丹不坐禅,不为商贾不耕田。闲来写幅青山卖,不使人间造业钱。”不仅科场落败、无俸禄者靠买卖书画度日,那些科举高中、有酬金俸禄者也不乏卖书鬻文者。《续吴中往哲记》记都穆曰:“至太仆少卿,返初服,修郡志,卖墓文为养……凡润笔之资,与异母弟共之,次及二子,或推及杨、李门下者。”
与其他文人相比,文徵明的生活境况较为优裕。但他也卖书画,只不过其卖画的标准并不是金钱的多少。何良俊《四友斋丛说》记其卖画一事:
衡山先生于辞受界限极严。人但见其有里巷小人持饼饵一箬来索书者,欣然纳之,遂以为可凂。尝闻唐王曾以黄金数笏,遣一承奉赉捧来苏,求衡山作画。先生坚拒不纳,竟不见其使,书不肯启封。此承奉逡巡数日而去。
从这则材料可知,文徵明书画的价格具有很大的随意性,贱时只值饼饵一筐,贵时却可换黄金数笏。卖画所得不仅满足了文徵明的生活所需,也成了其接济乡邻、帮扶穷人的一种手段。
卖文鬻画,自适自足;买卖公平,各得其所。吴中特殊的经济环境与文化传统使大多数士人不必依赖官府俸禄而生活,就是在这样一种崇尚物欲、重视利益的大环境中,吴中文人的思想情感逐渐发生了变化。早年那种建德立名的事功思想在他们心中渐趋淡化,对政治权势已经没有那种天然的向往感。他们的人生取向已经开始向世俗化一面倾斜,其考虑更多的是适心任性的自在生活。沈周晚年戒其子曰:
银灯剔尽谩咨嗟,富贵荣华有几家!白日难消头上雪,黄金都是眼前花。时来一似风行草,运退真如浪捲沙。说与吾儿须努力,大家寻个好生涯。⑪
“寻个好生涯”,沈周之语虽质朴无华,却一语道出了吴中文人乐隐且能隐的内在原因。与同时代文人相比,吴中文人思想更为进步、开明、睿智,在生命意义的找寻上,他们较早地领悟到适意自足的生活比功名利禄的苦苦追求更为实惠。
2.日趋艰难的科考
地区经济的繁荣势必会带动其它产业的发展与进步。得益于经济发展的推动,吴中的文化教育事业十分发达,文人士子数不胜数。《姑苏志·风俗》记载:
国朝又升为京辅郡,百余年间礼仪渐摩,而前辈名德又多以身率先……今后生晚学文词动师古昔,而不顾于专经之陋。矜名节、重清议,下至布衣韦带之士皆能擒章染翰。而闾阎田亩之民山歌野唱亦成音节,其俗可谓美矣。
在上者名卿巨公,名驰海内,名震一时;在下者畎亩细民,亦能自谱曲辞,歌唱于山野。吴中文风繁盛、人才辈出的兴盛景象由此可见一斑。
与文教的繁盛发达互为矛盾的是,朝廷的科举名额却非常有限。明朝采取根据不同地区分卷录取的方式,此举是为了保护落后地区士子不至于成为文化发达地区士子的“陪考官”。然而这样做也加剧了同一区域内科考者之间的内部竞争。由于吴中文教水平极高,其生员人群也日益庞大,有限的科举名额远远不能满足众多士子的需要。在吴中,累试不第者比比皆是:钱孔周“自弘治辛酉至正德丙子,凡六试应天,试辄不售”;⑫蔡羽“凡十有四试,阅四十年……而潦倒场屋,曾不得盱衡抗首,一侪诸公间,而以小官困顿死”;⑬祝允明竟“七试不售”。就连盛名威震东南的文徵明亦“九试不售”,他在《三上陆冢宰书》中的一段话就很能代表当时吴中文人因为出仕受阻而产生的不满情绪:
(生员)略以吴苏一郡八州县言之,大约千有五百人。和三年所贡不及二十,乡试所举,不及三十。以千五百人之众,历三年之久,合科贡两途,而所拔才五十人。夫以往时人才鲜少,隘额举之有余,顾宽其额。祖宗之意,诚不欲以此塞进贤之路也。及今人材众多,宽额举之而不足,而又隘焉。几何而不至于沉滞也,固有乡廪三十年不得充贡、增附二十年不得升补者。其人岂皆庸劣驽下,不堪教养者哉!顾使白首青衫,羁穷潦倒,退无营业,进无阶梯,老死牗下,志业两负,岂不诚可痛念哉!⑭
由于科举名额的限制,大量生员的沉滞势所必然,至于普通读书人的正途出身更是困难。人才的过剩现象已十分明显,传统的科举、学校已经不是解决办法。于是,吴中文人不得不背离传统的应考取仕之路,转入它途以开拓生存之道。
3.身居庙堂的尴尬
自建国之初到中叶,明代帝王一直对江南文人特别是吴中文人持一种歧视态度。建国之初,为惩戒江南士民不恭的“抵抗”之举,朱元璋对江南地区实行了特殊的、极其严酷的政策。经济上,明初吴中赋税之重堪称全国之最。王鏊记曰:“考之旧志,宋元岁数在苏者,宋三十馀万石,元八十馀万石。国朝几至三百万石。自古东南财赋又未有若今日之盛也。”⑮在繁重的赋税压制下,吴中居民苦不堪言。政治上,明政府利用“胡蓝”案“空印案”“郭桓案”等举国大案,对江南文人进行迫害,而吴中文人境遇尤为悲惨:洪武七年,高启被害,揭开了吴中文人悲剧命运的序幕。此后,与高启同具“吴中四杰”之名的其他三人亦皆惨遭迫害,,或被流放,或抑郁而终。
至宣宗、英宗二朝,吴人被压制和歧视的态度仍未缓解。《明史·彭时传》说:“帝(英宗)爱时风度,选庶吉士。命贤尽用北人,南人必若时者方可。贤以语时。俄中官牛玉宣旨,时谓玉曰:‘南士出时上者不少,何可抑之?”吴中文人不仅在政治斗争中饱受迫害,在脱离政治外的文学活动中,也备受打压。沈德潜记载:“正统三十三年,选庶常三十人,山东四人,北直六人,河南三人,陕西三人,四川五人,俱江北。而浙、福、湖广,南直隶之江南,以至两广、云贵,俱无一人焉。”⑯
至成化年间,随着王鏊、吴宽等人的入京,吴中文人的庙堂境遇似乎稍有好转,但明中叶的帝王仍然对吴中文人持一种怀疑态度。成化、弘治两朝,吴中进士能入主朝政者几无。吴中官僚的代表王鏊、吴宽、徐有贞等皆未能像“三杨”那样成为政坛上的常青树,而是饱受欺压折磨。徐有贞乃进士、翰林出身,在明英宗复辟上起到了关键作用,因此进入内阁。但此后的政治斗争又让他在短短几个月中落败,流放云南。吴宽入朝三十年未得拜相,最后只担任礼部尚书的闲职。《明史·吴宽传》记曰:“时词臣望重者宽为最,谢迁次之。迁既入阁,尝为刘健言,欲引宽共政,健固不从。他日又曰:‘吴公科第、年齿、闻望皆先于迁,迁实自愧,岂有私于吴公耶。’及迁引退,举宽自代,亦不果用。中外皆为之惜,而宽甚安之,曰:‘吾初望不及此也。’”王鏊虽拜相,却因为遇上“时中外大权悉归(刘)瑾”的独断专权局面,在内阁中掣肘过多而黯然离去。从明初的惨遭迫害,到明中叶的备受怀疑,吴中文人从帝王鄙视的目光中感受到的是不被信任的失望和心寒。试想,在一个缺乏了帝王信任和尊重的朝堂上,吴中文人能做什么?又能做成什么?
经济发展带来了生活道路的多样化,科举制度的不公导致了应试之路的坎坷多艰,帝王的怀疑与冷漠又使得学识无用、抱负难伸。这多种境遇的遇合导致吴中文人变得不再乐“仕”。古人的那种与生俱来的政治责任感,那种以天下为己任的政治使命感和自我牺牲精神已大为减退。他们不再将科举入仕、位列臣班视为生命的唯一寄托,确切说不是最重要的寄托。科举之路对他们来说已经不再是通往理想生活的唯一道路。在此种观念的影响之下,吴中士人逐步接受并融入了世俗的生活。
其实,吴中文人不乐“仕”,但并非不愿入“仕”。只是有的时候,他们的入仕或参政意识常常会被各种外在或内在的因素消融掉。他们的真实心态是,一方面,他们不愿彻底放弃对正统出世道路的选择,以科举出仕、服务帝王为正途;另一方面,他们又在正途之外找到更为丰富的生命归宿。当政治道路偃蹇不达时,他们伤心痛苦,但这种痛苦很快就会被世俗生活的丰富所消解。因为在他们面前,别有一番天地。入仕不成可以从商,从商不成还可以卖画种田。在这些宽广的生活空间中,他们依然能够得到世俗社会的承认。说到底,吴中文人是徘徊于士人的传统人生道路与世俗人生之间的一个群落。他们并非不喜政治,也并非不愿出仕,而是多变的生活环境为他们提供了选择别样生存的权利。因为有选择的权利,所以便不再执着,这或许就是吴中士人能够游离于“仕”与“隐”之间最根本的原因。
①祝允明《怀星堂集》(卷16)[A],《文渊阁本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第1260册)[C],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 594—595页。
②顾瑛《玉山纪游》[A],《文渊阁本四库全书·集部总集类》(第 1369册)[C],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491页。
③高启《高青丘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880-881页。
④赵翼著,王树民校正《廿二史劄记校正》[M],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741页。
⑤⑦⑨⑫⑬⑭文徵明著,周道振辑校《文徵明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482页,第593页,第593页,第756页,第735页,第584-585页。
⑥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216页。
⑧王鏊《震泽集》(卷22)[A],《文渊阁本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第1256册)[C],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353页。
⑩唐寅著,周道振、张月尊辑校《唐伯虎全集》[M],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160页。
⑪罗宗强《弘治、嘉靖年间吴中士风的一个侧面》[J],《中国文化研究》,2002年冬之卷。
⑮王鏊《姑苏志》(卷 15)[A],《文渊阁本四库全书·史部地理类》(第493册)[C],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⑯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 10)[M],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5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