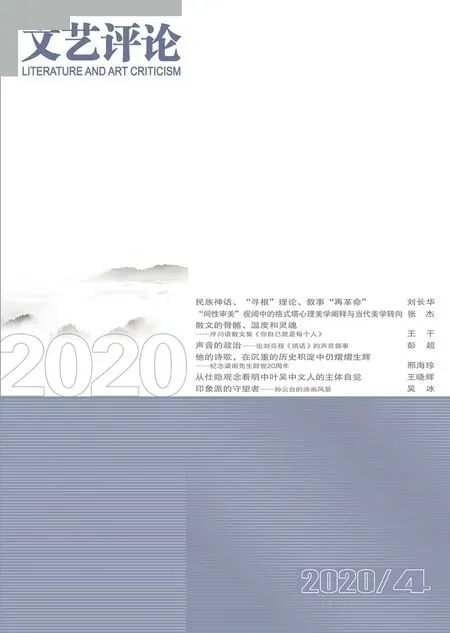他的诗歌,在沉重的历史积淀中仍熠熠生辉
——纪念梁南先生辞世20周年
2020-04-18邢海珍
○邢海珍
一转眼,20年过去了,时光留给人间世界的足迹也正在延伸向远方。20年前,诗人梁南突然离开我们,离开了他所钟爱的诗歌。由于走楼梯摔倒伤及脑干,75岁的诗人于2000年10月12日在医院逝世,终止了他正值旺盛的诗歌创作热情,中国新诗失去了一位特别优秀的诗人。读他的诗,我们看见诗中站着的诗人,一种个性,一种精神,字里行间存储着时间与历史的怀念。
一、文学追梦与命运的歧路
梁南,原名李启纲,四川省峨眉县人,1925年12月20日出生。1940年初中时代即在成都的《新新新闻》“中学生”副刊发表文学小品,1945年秋天的高中读书期间,曾与诗人罗洛、罗介夫编辑《成都晚报》“彼方”新诗周刊,1947年赴北平读书,曾考取北师大外语系、朝阳大学法律系,但因体检认定肺结核而入学未果,经乡友帮助借读北大中文系,后经战乱无法生活、学习而卖文为生。后北平和平解放,1949年2月7日参军。1952年2月,调军委空军政治部任记者。1956年4月加入中国作协。1958年4月被打成右派,发配边疆。1979年3月改正平反,7月被《诗刊》借调半年,1982年3月在56岁之时调入《北方文学》杂志,第二年9月转为专业作家。
从1981年开始,共出版七本著作,其中诗集五部:《野百合》,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1月;《爱的火焰花》,花城出版社,1983年4月;《诱惑与热恋》,漓江出版社,1988年12月;《梁南自选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风雪归来》,哈尔滨出版社,1999年9月。另有随笔集《寸人豆马随笔》,1997年6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诗学理论集《在缪斯伞下》,2000年6月由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
梁南从初中就开始写作,起步于十几岁,而且发表作品较早,是一位少有的早慧型作家和诗人。但是他命途不顺,一路坎坷,没有读成大学,又遇上战乱。后北平和平解放,入伍当兵一直到新中国成立,人生终于有了起色。几年里也算突飞猛进,两次在《人民文学》发表长诗,参加全国青创会,加入中国作协。然而好景不长,1957年风云突变,在“大鸣大放”的潮流裹挟中折戟沉沙,1958年4月被开除党籍、军籍,戴上“右派”帽子,押解到黑龙江省虎林县云山畜牧场监督劳动,他生命中刚刚打开的梦想蓝图就被撕扯得七零八落。
直到1979年3月,梁南的沉冤得以昭雪,诗人重新挥桨扬帆开启了人生的文学航程,此后的二十年诗歌创作路程,为中国新诗留下了许多值得珍视的里程碑式佳作。其中《贝壳·树·我》就是归来早期的代表性作品,组诗由三首短诗组成,第一首《贝壳》:
纵然贝壳遭受惊涛骇浪的袭击,/不变它对海水忠实的爱情,/深沉地,深沉地噙着珍珠泪,没有嫌弃……//记起大海造就它迷人的花纹,/记起大海给它跋涉浩渺的履历,/它紧紧投身于大海的泛滥中,/任磨折与咸苦刺戳它纯爱之心。
诗人以“贝壳”自喻,深沉地描述了大风大浪的苦难过后,仍持守着坚贞之爱。包括《贝壳》在内的一些诗作所涉及的爱情,无论是象征与否,其中都包含着个人遭际的因素。但诗中的意象方式则放大了情感所指的范畴,以“贝壳”“对海水忠实的爱情”,表达了远比个人爱情内涵更为深广的情怀和忧思,是个人遭际与家国情怀相统一的诗意美学境界。诗人所营造的贝壳的“纯爱之心”,是“它紧紧投身于大海的泛滥中”“磨折与咸苦刺戳”所收获的结果。所以贝壳铭记大海曾“造就它迷人的花纹”,铭记大海曾给他“跋涉浩渺的履历”,诗的意象创造使诗的情感走向了思辨的深度。
第二首《树》:
泥土纵然干涸得没有一丝水分,/眷恋它的树枯萎了也站在怀里,/像婴孩依偎于母亲,/落叶是树的眼泪,落满母亲手里。//怀念大地给它织春的碧玉针,/感激大地塑造它健康的胴体,/它们是亲密的母女啊,/一起美丽,死亡时也抱在一起!
记住“泥土”的养育之恩,与“大地”母亲生死相依,是梁南至死不变的诗与人生的理念。在漫长的人生逆境中,他就像一棵行将枯萎的“树”,把落叶的“眼泪”抛洒给大地母亲。虽然泥土曾经干涸,他饱受折磨和委屈,但他没有怨恨,他记住大地母亲曾给他“织春的碧玉针”,曾给他“健康的胴体”。与《贝壳》一诗一样,以另一种意象,表达了内心的深沉之爱。
第三首是《我》:
既有贝壳爱慕大海的深情,/也有山树苦恋大地的真意,/花香而微霜扑地的我的母亲祖国,/我愿做你的爱的奴隶!//我弯下驼峰承受你的一切苦难,/以你给我刻画的容貌走在风沙里;/如果在死生之间有所抉择,/愿毁灭的是我,不是你。//请剖开水囊,我还有甘水几滴,/每一滴,都请交给你的生命!/恨吗?没有;恨有时是爱的顶点——/我怕有人盗窃你的神圣的名义。
如果说前两首是以象征的方式表达了在苦难的生命历程中所具有的“纯爱”,那么《我》则近于直抒胸臆的倾诉,诗的头一节把“贝壳爱慕大海的深情”“山树苦恋大地的真意”明确地指向了“我的母亲祖国”,并作了呼喊式的表白“我愿做你爱的奴隶”“愿毁灭的是我,不是你”,可说是血泪的诉说。诗的后两节又以意象加以寄托,“承受你一切苦难”的骆驼与人合为一体,在“风沙里”,在“死生之间”,一个献身者的意象昭然于纸上。“请剖开水囊,我还有甘水几滴,/每一滴,都请交给你的生命!”在诗中,“爱”已上升为一种信仰,为了所爱的祖国,甘愿献出一切,甚至牺牲生命,这是许多志士仁人的精神选择。结尾两句引进了爱、恨对举的设问,有着更为复杂的反思意味。
诗人梁南不在了,他的血肉之躯已经走进了历史,但是他把自己的诗留在了人间,留给了今天的世界。他的苦难人生历程的底蕴,形成了他诗歌沉郁、苦吟、椎心泣血和刻骨铭心的风格特色,这是一个特定时代之于“这一个”诗人的生命标记。在一首题为《我看见一株草的悲剧》的诗中,诗人这样写道:
一株我熟悉的草茅,悄然逃脱。/冷冷。视线中,几丝碧绿被剥夺。//也许我该望见他迷人的腰肢,/远远地:却传来他生命的哀歌。//他从诞生他的天然草地逃离,/渴望依随花丛顶戴出时花一朵。//当含苞的花乳们敞开关闭的微笑,/他孤独地只得到绝望的衰落。//风来他愁,雨来他哭,/枯瘦憔悴,最终死于寂寞。//秋季的身后是冬,是春,/那草地仍有碧绿的欢乐给我。//我似乎什么也没有失掉,/虽然我的确失掉过什么。
“草的悲剧”就是人的悲剧,诗中浓郁的悲剧氛围,就是人生境遇的写照,命运的歧路让诗人梁南的文学追梦变得分外严峻。就像“一株草”成为异类而“悄然逃脱”,而“逃离”不是甘作逃兵,而是“渴望依随花丛顶戴出时花一朵”,但是当应当开放之时,得到的却是孤独和绝望。“风来他愁,雨来他哭,/枯瘦憔悴,最终死于寂寞”,命运的歧路和悲剧的精神创伤在他的诗意情怀中留下了鲜明的印记,对于诗人个性的形成是不可缺少的心理维度。
二、扩而大之的“苦恋”情结
梁南在青年时代,经历过一场刻骨铭心的恋爱,后因国家动荡、个人生路坎坷,二人无奈分手。这次失败的恋爱,给诗人留下了很重的心灵创伤,对于他后来的诗歌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梁南的许多诗作显现着鲜明的爱情痕迹,这种“爱情”的叙写可以从两个维度来进行体认:一是爱情的写实维度,即对一个人爱慕、思念的抒写,我们可以称为爱情诗;二是把个人的情感作为一种精神底蕴,由个人拓展的人生命运、时代历史、家国情怀,引入对社会政治大情境的认知和抒写。是这两个维度形成了梁南诗歌的基本抒情架构,是个人经历的痛苦之思,是由个体情感向着历史与现实的责任承担的不断放大的“苦恋”情结。
短诗《黄桷树下》所写就是个人爱情经历的感怀:
我在纸上画着难忘的记忆,/永是黄桷树下开花的雨具。/柔淡一瞥,解除我久候的苦凄,/你忙把我欢笑的脸收进伞去。//你踩我的足迹,我踩你的足迹,/不知走向哪里却欢天喜地。/我们好像这样走了一辈子,/尽管你始终在东,我始终在西。
人虽然不在一起,但爱的凝思却深深刻在心中,“黄桷树下”,有一把“伞”撑开,恋人并肩而行,“你踩着我的足迹,你踩着我的足迹”,在“我久候的苦凄”中,爱的“欢天喜地”只是一种诗意的想象和幻觉,因为残酷的现实是“你始终在东,我始终在西”。诗写得典雅、唯美,情感的波澜在深处,沉郁而悠远。而《不知何故,想你》一诗则有几分“壮怀激烈”的意味了,诗人难抑内心的冲动:
想你,就把花枝摘在手里就把星星招引/想你,就散步喝茶注视屋檐目不转睛/就把手不释卷的书打开又关起/就禅意入定,双眼微闭/去咀嚼那个又讨厌又欢乐的雨季/想过千人万事,反复类比/都没有这种美得伤心的意境//世界走过去就不再回头/一步跟不上就落后一个世纪/多少美丽都从指缝间流失了/年过六十尚未研究透一桩世情/尤其是这种难以理喻的少不更事/贝壳那么狂热于海恋,为什么/偏偏在冷冷的沙滩上死去
激情突破了文字的平静,对美好的青春及爱情的追忆让人痛心疾首。诗中的感慨多于写实,可见诗人对于丢失美好机缘的惋惜与悔恨,那“美丽都从指缝间流失了”“难以理喻的少不更事”其中必有更多的不为人知的衷曲。“狂热于海恋”的贝壳,却让爱情死在“冷冷的沙滩上”殊为可惜。这样近于内心独白的爱情诗,应是诗人心路历程的重要阶段。梁南由“苦恋”而“苦吟”,其中个人的爱情悲剧体验是他苦吟诗歌的重要情感底蕴。
在《诱惑与热恋》诗集的序言中,诗人敏歧说:“我不止一次听见读者称梁南为‘苦吟诗人’。这‘苦吟’,除了指艺术上的锲而不舍的追求外,更为重要的,恐怕还在于特定的内涵。因为自风雪泥泞中‘归来’,心上和肩上有着太多的重负,于是,希望凝重的诗篇中,如爝火,总燃烧着深沉的忧患。忧患,是对历史痛定思痛的反思。因为是一个特定历史年代的产物,所以我们在许多诗人的诗篇中都能看到,特别在‘归来’的诗人中。”一方面,在诗歌的艺术追求上,梁南历来是字斟句酌,讲究推敲提炼之功,是典型的“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实践者。他的诗歌语言凝练、干净,没有拖泥带水的乱象,警策简古,可谓掷地有声。另一方面,他的诗充满忧患意识,是对大半生命运歧路的诗意思考与感受,是对于自我人生、时代社会以及历史现实的洞察与反思。
梁南的诗歌常常把经历中的爱情体验与时代社会的政治内容联系起来,把个体的情感经过象喻指涉等诗化处理,在融通中扩而大之,使诗意的内涵获得多元和丰富的可能。
《我这样爱过》是梁南的短诗代表作之一,是组诗《我追随在祖国之后》中的一首,曾荣获1981—1982年《诗刊》优秀作品奖。《我这样爱过》全诗如下:
我在爱恋中痛苦了一辈子/我一辈子都在痛苦中爱恋……/诅咒她,背弃她么?不!/我甘愿沉溺于爱的痛苦,/我宁肯毁灭于痛苦的爱。/我曾怎样浪迹于欢笑之外,/怎样在惟有痛苦、/没有爱的深深底层/蛰伏着,渴念着,长期隐埋。/啊!只有我才知道:/痛苦是爱的必要补充;/爱是痛苦永恒的期待。//当艳阳给了我补充,当春风把期待引来,/又一次我怀着凌霄花般鲜红的爱恋,/含着泪水,焦忧,忍着灼痛和疑猜,/苦苦去追求,去开花,去结果,/经受了千般万般风雨,到底,/我们的心彼此没有离开。/有一对识途的甘美的眸子,/传递着喜讯的温柔,望着我,/从遥远遥远的地方终于回来……//我这样爱过,真的,这样爱过,/从属于祖国的,融化在祖国身上的:/爱的痛苦,痛苦的爱!
此诗是梁南“归来”的早期作品,发表于1982年第1期《诗刊》,是诗人的心血之作。虽然诗中有着明显的理念痕迹,比如“我在爱恋中痛苦了一辈子,/我一辈子都在痛苦中爱恋”“痛苦是爱的必要补充,/爱是痛苦永恒的期待”,都是推断的方式,重视逻辑性,是一种理性的表述。但是,由于诗人的感受是独特的,又加之话语的情感化,而推断的逻辑中有一定的具象性,使其理念的表述散发出强烈的哲思的诗性光芒。毫无疑问,这是一首情感深沉、充沛,是以真情感人的优秀诗作,有深刻的政治内涵,与诗人自我的人生命运融于一处,可以称其为“政治抒情诗”。诗人把祖国比作痛苦追寻的爱人,他以坚贞、执着不改的信念,抒发了对祖国的一腔赤子情怀。“我曾怎样浪迹于欢笑之外,/怎样在惟有痛苦、没有爱的深深底层/蛰伏着,渴念着,长期隐埋。”诗人所表达的“爱恋”是一种刻骨之痛,这种情感像一条从心中流出的河,力度震撼,涛声动人。诗人倾诉心灵深处的“苦恋”情结,把不能遏止的警句式的诗思以情境化的形象加以烘托、衬照,营造了富有强烈但绝不浮泛的诗意感染效果。
把自我的情感扩而大之,心怀忧患,心怀使命,心怀人间道义,心怀天下苍生,梁南的诗歌具有广阔的胸怀和高远的境界。立于众多的“归来”者诗人中,他是特别杰出的一位。
在长期文学和艺术的修炼过程中,梁南的艺术创造虽已达到了极高的境界,但是诗人对自己仍是严格要求,苦苦追求一种诗意的化境,努力而审慎地在“苦吟”的路上一步一步地前行。在《追索红宝石和珍珠》一文中,梁南这样写道:
在创作上,我始终是个失败者。
我还从来没有结过一个成熟的果实,从来没有创作过一篇称得上达到炉火纯青境地的作品。我生怕被自身庸浅的惰力所累赘,每到雕虫涂鸦之时,总以谨严来约束笔头子,渴望“把自己的血化为红宝石,把自己的泪化为珍珠”(卢那察尔斯基语)。令人内疚难堪的是,尽管我在不遗余力追索,缪斯的红宝石和珍珠,却不赐我半粒。
就是这样一位在诗坛几乎被一致公认的优秀诗人,对自己写作的要求竟是如此严苛,其创作的严谨态度真是令人顿生敬意。比起当今感觉始终特别良好的我们之辈,总是满足于“一瓶子不满、半瓶子逛荡”的水平,应该感到脸红心跳,应该知道诗人与诗人的差距。
三、精致独特的风格追求,深刻独到的诗学思考
在75年的生命历程中,不论是顺境还是逆境,梁南都没有忘记诗歌,他是一位把人生命运甚至生命都与诗捆绑在一起的诗人。在流放改造的二十多年中,他历尽艰辛,几乎被剥夺了创作的权力,虽心中有诗,但毕竟自由受限,许多流水年华在岁月中远去。直到56岁时得以回归诗歌,他以不足二十年的时间冲刺诗坛,获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自1979年开始,在《诗刊》发表作品共四十多次,其中诗歌一百多首,诗学论文十几篇。曾连续十四年入选国家级新诗年选本,有十余种当代文学史对梁南的诗歌成就进行了推介、论述,对他的许多作品给予了高度评价。
《我不怨恨》一诗是梁南一生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可称得上是中国新诗的经典之作:
诱惑人的黎明,/以玫瑰色的手/向草地赶来剽悍的马群。/草叶看到了自己的死亡,/亲昵地,仍伸向马的嘴唇。//马蹄踏倒鲜花,/鲜花,/依旧抱住马蹄狂吻;/就像我被抛弃,/却始终爱着抛弃我的人。//啊,爱情太纯洁时产生了坚贞。/不知道:坚贞/可能变为愚昧的天真;/我死死追着我所爱的人,/哪管脊背上鲜血滴下响声……//希望,总控制着我的眼睛。/我在风雨泥泞之途没有跌倒,/我在捶楚笞辱之中没有呻吟,/我在沉痛无边的暗夜,心里/总竖着十字架似的北斗星……//至今我没有怨恨,没有;/我爱得是那么深。/当我忽然被人解开反扣的绳索,/我才回头一看:啊!我的……人民!/两颗眼泪滴下来,谢了声声,声声……
诗的前两节以两组对举的意象来渲染“爱”的悲剧性:“马群”与“草叶”、“马蹄”与“鲜花”。诗中出现了令人陡然一惊的镜头:“草叶看到了自己的死亡,/亲昵地,仍伸向马的嘴唇。//马蹄踏倒鲜花,/鲜花,/依旧抱住马蹄狂吻”,这样的诗表现出一种为“爱”献身的狂热,向我们提供了认识一代人情感历程的可靠证据。即使被所爱的人抛弃,也还是“死死追着我所爱的人”,抒写了“我不怨恨”的谅解,敞开了从大局着眼、排除个人得失的博大情怀。
梁南的“我不怨恨”是历史的文明和坚定的信仰赋予了他宽容的精神,他的巨大的苦痛之中包含着更深层的爱的能量,与那些个人恩恩怨怨的呻吟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在人生经历的坎坷之路上,因为“爱情太纯洁时”的“坚贞”,而使他产生了“愚昧的天真”,诗人没有回避自己在那种特殊的历史阶段所具有的思想局限,这也正表现出诗人的清醒。是错误的政治路线使他蒙冤二十多年,但他没有抱怨祖国和人民,不能因为委屈而迷失,当他回归到正常人的群体中来,他感激人民和历史,他为自己有了“报效”的机缘而激动不已。这就是他作为一个诗人的真实人格,他以自己血肉之躯最真实的体验和感受写诗,而不是故作清醒来神化所处特殊历史境遇中的人格。就像诗圣杜甫,沉郁顿挫,坚忍冷峻,梁南又多了几分生命的硬度。他的诗已经形成了鲜明的风格特色,可以在创作中独领风骚。
《我们给历史雕刻金黄的形象》是梁南新时期以来的长诗代表作,是诗人一生诗歌创作的重要成果。长诗创作于1985年,诗人敏锐地感受到改革开放时代强风的力量,产生了一种发自内心的兴奋和冲动,经过月余的时间,六易其稿,投入了巨大的心力,写下了这首二百多行的抒情长诗。诗人面对蓬勃发展的新时代,把个人的命运与社会政治的风云激荡紧紧地联系起来,从宏观的大角度看取一个新时代的历史性变化,抒写了一个伟大时代的精神风貌。
这是一首独具特色的政治抒情诗,是诗人以诗的方式为历史和时代塑形、造像,诗歌中洋溢着充沛的坚定、感奋的政治热情,既有强烈的情感氛围和鲜明清晰的具象效果,又有丰富的、入木三分的思辨深度。长诗开头两句,以一个前行者的意象开局起兴,为历史和时代雕刻出一个象征性的标志性形象:
脚步抛弃起点老远老远。向远方
前进中,头发永远是风的形象
在关键的历史时刻,中国以一个巨人的伟岸雄姿开启了全新的行程,作为前行者,被诗人置放于开阔、风起云涌的境遇之中,“脚步抛弃起点”,在义无反顾中前进。开拓者,走自己的路,“向远方”的是一个大写的人,不惧任何艰难险阻,“头发永远是风的形象”。诗人对于时代和历史的诗意定位,长诗中反复出现多次,可谓一唱三叹,回环往复,作为独特的抒情主人公形象,始终引领着波澜起伏的激越之情在大时代的潮头中迎风挺立。
全诗的倾诉式的表达注入了诗人对历史和社会现实的深切思考,宏观与微观互融,内心与外物契合,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足迹延续成为风,我们走着/前方一下子被我们抛向后方/没有永恒的前方。没有。语言里/出现两个激动时代的字汇:振兴/或者开拓或者改革或者投降/让我们重新生长一次吧,让我们/再崇高一点,再美丽一点吧/歌哨擦响云朵,焦急地,带走/我们给世界的回答祝福挑战。带走/我们的诚意我们的情思梦想……/我们前进。戴着喜马拉雅帽徽的/伟大民族,在痛失三次兴旺的机遇后/刚毅地,开始向繁荣的大迁徙/在两个世纪交替的手臂之间/在黑玫瑰陷落的地平线之上。摇着/细丝如雨的杨柳枝,寻求知识之光/大自然跟我们迁徙着。山走向水/水走向海。海走向风。风走向香/波涛与波涛,用水花的语言谈论着/海上通路指向星星和月亮的家乡
诗人把诸如“振兴”“开拓”“改革”等政治词语化入诗意的情境之中,把政治情怀与具象的细节和感性描述紧密地结合,形成了磅礴大气、自如舒展的抒情风格。诗的表达不无忧患和沉郁,明确的政治内涵中又具有反省、思辨的生命重量。如“前方一下子被我们抛向后方”,“没有永恒的前方”,重视在发展和进取中找出路,把政治的理念化为诗的意象和情境,既有通透明晰的情感指向,又有深刻悠远的理性关照,既有传统艺术方式的扎实底蕴,又重视探索创新的吸纳和践行。长诗为政治抒情诗的写作提供了有效的经验,拓展了诗与社会、诗与政治关系的途径。
在诗歌创作中,梁南特别重视语言修炼,反复淘洗,精警提纯,绝不放任迁就,绝不拖泥带水。他的诗歌多以短诗为主,在不断地推敲和比较选择中走向精到、深邃、纯美。他重视修改,他不是开闸放水式的一挥而就,而是一字一句地斟酌,经常推倒重来。他在推敲中,几乎达到了忘我的程度。著名作家吕中山在《以诗为生命的人》一文中写到梁南“沉迷于诗,险些丢掉性命”的一件事:1978年的一天早晨,他走在铁道线上,因构思诗篇而陷入“入定”境界之中,没有听见后面火车的呼叫,被火车掀出七米多远,碰得头破血流,肩背多处骨折,差点丢掉了性命。他的诗,不是轻易就出手的,是思之再三的结果。《墓地》一诗,就是他短诗中非常显眼的一首:
我死后绝不乞求一寸墓地。/一边死去,一边/我将立即追索花果的繁荣,/用我的白骨及爱的信息。//倘若硬要赐我墓地一寸,/我将用头颅繁殖玉兰玫瑰,/让其飘飘染出一方清芬,/洗却我占地一席的羞愧。
全诗只有两节八句,文字极为俭省,却有着极大的诗意含量,以“思”拓展了情怀和境界,把崇高的献身精神表达得十分到位。诗人写“死”,没有悲哀的情绪,而是进入了一个“奉献”的世界,用精炼的语言表达了一种向善向美的情怀,“追索花果的繁荣”“用我的白骨及爱的信息”,少少许的语言,表意特别准确。后一节是以假设得到“墓地”的“羞愧”之情抵达了另一番高远的境界,“我将用头颅繁殖玉兰玫瑰”,想象奇崛,把诗推向了高潮。从诗的遣词造句到意象营造,只在方寸之间,却成就了经典之作。
梁南是一位创作态度极其严肃的诗人,是肯于下大功夫、出大力气的“苦吟”派诗人,精雕细刻,独树一帜,他的诗歌具有创新的价值。他除了是一位优秀的诗人,还是具有较高成就的诗歌理论家,他的许多观点深刻地影响了后来的写诗人。
在长期创作实践的基础上,梁南发表了大量的诗学理论、评论文章,曾经引起了诗歌界的广泛关注和反响。他逝世前由北方文艺版社出版了诗学论集《在缪斯伞下》,收入了他大部分诗论文章,包括了他对诗歌本体、诗歌表现、诗歌发展、诗歌传统诸多方面的独特思考,是诗人多年来对于诗歌进行深入研究的心血结晶。
梁南的诗歌理论重视感悟性。他的许多诗学观点,多是来自诗歌创作中的思考,不是那种学院式的研究,不去刻板地追求理论框架的构建,而是采取突破一点的方法,注重探讨某个具体问题,并进而达成尽可能的理论深度。比如在诗是“表现自我”的讨论中,他写出了论文《对诗评诗论的困惑》,他从“诗言志”理论基点出发,把它与今天人们常讲的“表现自我”进行合理的引导和疏通,使古老理论命题的枝条长出了具有现代神韵的哲思生命新芽。他在文中说:“诗言志即表现自我,这是我们的诗歌批评鼻祖总结我国诗歌领域第一次走向成熟期的艺术概括之一。我们的诗论家对此却一概不谈。偏向维护传统的论家视之为异端,不知是搞评论的老祖宗留下来的传统精粹;以反传统自命的诗人诗论家又自视这个‘表现自我’是他们的发现,不知这是两千几百年来老传统里的理论瑰宝之一。维护传统者和反传统者双方都对传统知之甚少,这是耐人寻味的。”梁南对于忽视传统理论积淀的人进行了有理有据的批评。
随着诗歌创作和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梁南从创新意识、语言陌生化、诗家语等方面的辨析中看到了更为复杂的问题,这就是任何创新的努力都不是无限度的,都必须受到一定的规范,因此他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诗要遵循应有的艺术逻辑。在《浅谈诗的逻辑问题》一文中,他针对一些诗人只求新异而不讲逻辑、对语义肆意施暴的现象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剖白。正如《诗刊》在发表此文的“编者按”中所说,梁南“提出了一个比较新鲜的理论问题”,“颇具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他在文中指出:“自然,诗还独具非叙述性不确定性等艺术个性,但都不能构成不讲逻辑的口实。逻辑与诗的血缘关系,远远超出语法文法的范畴,彼此是既依存又有制约。逻辑因诗而得以进入艺术领地,诗因逻辑而更富哲学思辨,即令语言的弹性(实乃弹性思辨的外形),甚至意象与意象之间,都有逻辑保证存在。”这对于有的人写诗违背常识和逻辑,造成伪诗泛滥的现象,有着拨乱反正的意义。
梁南诗学理论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注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入挖掘,把创作中的体验和感受同古代丰厚的文学现象、新诗发展的经验紧密地联系起来,使其理论的内涵建立在深厚的民族传统文化基础之上,更具有一种思辨的从容和稳健。在梁南的诗学理论中,我们看到他对《诗经》《楚辞》《论语》《左传》《史记》《汉书》以及许多古代诗文典籍的研读相当细致深入,他善于对史料进行分析比较、考辨论证,对于历史上的一些定论性观点能够提出自己的看法。
1992年,梁南写出了一篇两万多字的考证性诗学论文《论孔子绝非〈诗经〉选家》,前后费时将近一年,他以翔实的资料论证了孔子不是《诗经》选家的观点,对于《史记》《汉书》等权威史书的定论提出了不同意见。虽然在后来的历史上许多人也提出了不少与司马迁、班固相左的观点,但真正从翔实的史料中严肃考证这个问题,大概梁南是第一人。他通过对《左传》上的引《诗》进行研究,发现孔子出生前即有大量的引《诗》,与今本《诗经》几乎一致,甚至字句亦无出入,于是在大量可信史料的证明下得出了“孔子绝非《诗经》选家”、而真正的选家是“周王朝的有关的权威部门”的结论。他所列举的大量证据体现了极为严肃的态度,在写前曾三遍通读《左传》和《论语》,把《左传》引用的《诗》241篇次摘抄下来,与今本《诗经》反复对照,并对《论语》中孔子论《诗》的内容进行深入研究,他终于用心血写成了足可传世的文章。
古人诗云:跃跃诗情在眼前,聚如风雨散如烟。敢为常语谈何易,百炼功纯始自然。
当梁南离开这个世界二十年的时候,他所热爱的新诗也走过了百年的历史。在这漫漫的风雨途程中,梁南的名字已为新诗的发展留下了令人瞩目的光彩,他作为一位诗人、一位曾经的奋斗者,应当为历史所铭记。
岁月匆匆而逝,时光如风流过。诗人梁南飘然而去,他走向心灵的远方,有文字和纸留下来了,他的诗还在。他在灵性的文字中仍还睁着眼睛,是诗的光芒穿过沉重的历史积淀,照亮了他身后的许多春天。读他的诗,记着他的名字,愿诗情永在、诗人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