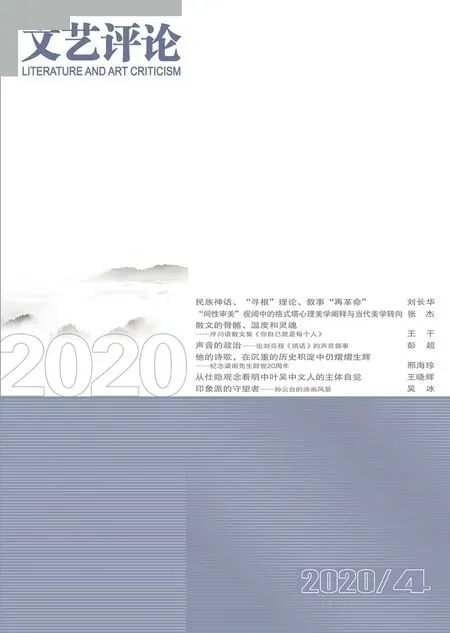声音的政治
——论刘亮程《捎话》的声音叙事
2020-04-18○彭超
○彭 超
在刘亮程的作品中,声音一直都是不可或缺的元素,这源于他所拥有的“悠长的听觉”,他在风声、驴叫、鸡鸣犬吠和人语之间寻找到一个广阔的世界,“那个我早年听见的声音世界,成了我的文学中很重要的背景”①。在他的《捎话》中,他依然将声音作为重要的叙事元素。
在人类文明发展历程中,声音从来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与文化交流、身份认同、权力建构之间存在着内在联系。谁在发出声音,什么样的声音能够被听见,被谁听见,以何种方式听见,这本身是一种话语权力。对于声音的关注,是“把看不见摸不着的声音附着在其‘栖居’的具体的自然、技术和文化空间里,来对声音的构成、形态、历史进行文化分析”②,即“声音的风景”。
《捎话》中,刘亮程是以虚构的毗沙和黑勒两个国家为叙事背景,通过讲述捎话人库和小母驴谢将一句话从毗沙捎到黑勒的故事,勾连起宗教信仰、语言、人与动物等诸般议题,展现了作者对文化冲突的反思。他是通过声音来完成这一系列的高难度动作,将自己对文化冲突的思考呈现出来。
一、诵经
《捎话》中最先出现的声音是诵经的声音。诵经并不是罕见的事情,在有宗教信仰的地方,我们总是能够听到信徒虔诚的诵经声音。可是,在刘亮程这里,声音的发出者、声音的形状、听觉的主体都大有文章,先来看小说对诵经声音的描写:
嗡嗡的诵经声响起来,声是扁的,像浮尘像雾,裹着昆塔一层层攀升,升到金灿灿的塔尖时,整个昆塔被诵经声包裹。那声音经过昆塔有了形,在塔尖上又塑起一层塔。一座声音的塔高高渺渺立在裹金的昆塔之上。诵经声又上升,往声音的塔尖上再层层塑塔。越高处的塔就越扁,越缥缈。③
这段对诵经声音的书写,至少透露出三重信息。第一重,诵经声音的发出者是谁。在小说中,作者虚构了两种不同的宗教,昆和天。位于西边的黑勒国和位于东边的毗沙国,原本都是信仰昆,后来黑勒国改宗信天,自此两国之间战争频发。在这里,“昆塔”的出场解决了诵经主体的问题,是昆门徒在诵经,也交代了小说重要的叙事背景。这是一部和信仰有关的作品,信仰的冲突将是小说重点探讨的议题。
第二重,是关于声音的形状。令人惊讶的是,声音被赋予形状,是“扁的”。通过后文的解释,我们得知这是因为“她”是透过木门上的裂缝来看,所以看到的是扁的声音。
刘亮程对声音的偏爱早已不是秘密,他在《凿空》中就有过经典的表述,“驴叫是红色的”④,声音被赋予颜色,那泣血般的颜色是驴在用自己的方式向古老的农业文明时代告别,传递出刻骨的绝望与悲恸。在《捎话》中,声音具有了新的属性,那就是形态,而且是塔的形态。诵经声音形成塔,不断累积的诵经声音层层塑塔,那么,这塔是否可以到达天庭,那个真理存在的地方?
在上古神话中,天和地之间存在着往来,在昆仑山有天梯存在,在《山海经·大荒西经》记载,颛顼命令重往上托天,黎往下按地,天地分离,不能随便上天下地,即所谓“绝地天通”。在西方创世纪神话中,也有巴别塔的存在,那是人类联合起来修建一座通往天堂的高塔。为了阻止这个计划,上帝让人类说不同的语言,互相之间沟通困难,造塔的计划就失败了。在《捎话》中,诵经的声音也形成了一座塔,这座塔不断地往高处走,越来越缥缈,但是诵经声音无法抵达天庭,诵经的信徒们也无法真正领悟上天的真理。在小说中,只有驴的声音能够抵达上天,不论是昆经,还是天经,都无法实现与上天的真正沟通,这无疑构成了一种反讽。
第三重,是关于听觉主体,究竟是谁在听诵经的声音?“她”不仅能听见声音,还可以“看见”声音的形状。“她”为何具有如此特异功能?在刘亮程的笔下,只有驴才能看见声音的形状,原来“她”是一头小母驴。这头小母驴为什么会出现在昆寺中呢?这又涉及到小说叙事视角的问题。
刘亮程给予驴如此重要的地位,他要在人、动物、上天之间建构一种全新的观察视点,人诵经是为了向上天表明虔诚的信仰,但是并没有真正理解上天要传递的真理,诵经的声音也无法传递到上天;听到诵经的是驴,驴叫声里藏着上天要传给人的真理;但是,人与驴之间没有平等的对话与沟通,人不知道在驴的叫声中能够寻找到真理,驴却将人的行为都看在眼里。
小说中除了昆门徒的诵经声音,还写到了天门徒的诵经声音。残酷的是,杀戮和诵经联系在一起,那是毗沙对黑勒的一次突袭。小说是如此来描述:
叩拜礼后,天门的念诵变得舒缓悠扬,人群默立,能听到尘土在空气里碰撞的声音,仿佛落下的尘土又被念诵声和高捧的手臂扬起。能听见尘土落在刀刃上的声音,落在战马鬓毛上的声音。黑勒士兵的眉毛胡子和头顶上一定都落了厚厚的土,天门的念诵声和重重的浮尘一同落下来,他们的耳朵里肯定也落满土,不然怎么会听不到马队逼近的声音呢。⑤
刘亮程在这里用抒情性的文字来描写天门的念诵,一边是能够听见尘土碰撞的声音,那是在无边的静谧之中,天门徒与他们信仰的上天进行着灵魂的沟通;另一边是尘土堵塞了天门徒的耳朵,让他们对即将到来的袭击一无所知。尘土不仅是堵塞人的耳朵,也将人的心灵蒙蔽,让人变得狭隘,无法实现和平的沟通与交流。所以,战争就出现了。据刘亮程讲,“写《捎话》时,惟一的参考书是成书于11世纪的《突厥语大词典》,跟《捎话》故事背景相近”⑥。《突厥语大词典》是维吾尔族语言学家马赫穆德·喀什噶里于11世纪70年代所编纂的一部阿拉伯文辞典,刘亮程是以词典中记载的喀喇汗于阗战争为参考进行创作,这场历史上著名的宗教战争最终以于阗国的灭亡而结束,然而喀喇汗也损失严重,阿里·阿尔斯兰汗在战争中被于阗军队戕杀。
二、驴叫
这场宗教战争,又可以被称为驴叫声引起的战争。因为昆门徒诵经最讨厌驴叫,“驴叫从空中把诵经声盖住,传不到昆那里”,所以昆门徒修建高院墙来挡住驴叫,但是事情传到黑勒却变了味;西昆寺的高墙挡住了黑勒城的太阳,这被视为对黑勒王朝的严重挑衅,战争一触即发。多么荒诞!
驴叫在小说中有着更为重要的作用,那就是给予人类启示录,什么是上天的真经,什么是真正的沟通。
昆门徒诵经的声音能够形成昆塔,而驴鸣能够形成巨大的昆塔,在由诵经声塑起的重重高塔之上,存在着一座更高、更亮、更缥缈的驴鸣昆塔。驴的声音在天上垒城,“人的天庭为啥塌不下来?驴叫声从下面支撑着。每一声驴叫都是支撑天庭的一根柱子,驴不叫,天会塌”⑦。驴的声音是如此重要,以至于人的天庭需要驴叫来支撑。驴和人的关系在这里被颠倒过来,不是人决定驴的命运,而是驴在用自己的声音支撑着人的精神信仰。
“捎话”本身意味着沟通,将一句话从一个地方代到另一个地方。假如两个地方的人使用不同的语言,那就需要翻译,如此在捎话的过程中,所捎的话可能会走样。但是驴就不会出现这种问题,驴叫声“昂叽昂叽昂”,天底下所有的驴——毗沙、黑勒、沙洲、蕃的驴都叫这一句。当毗沙西昆寺的王大昆门委托库将一头小母驴捎给黑勒桃花寺的买生昆门时,他嘱托库,将小母驴看作是一句话。为何要将一头驴当作一句话捎给买生昆门?那是一部刻在谢身体上的黑勒语昆经。人类语言传递存在着不准确的可能,转而借助驴来传递。当小母驴谢出让自己的身体参与到捎话的过程中时,驴的声音也加入到小说的多声部中。
有两次驴叫是令人震惊的,那并不是真的驴叫,而是人在发出驴叫。人类无法通过语言进行沟通的时候,进入到语言的黑洞中,需要转向动物,转向驴叫。正如德里达在《我所是的动物(更多随后)》中的阐释,对动物的认识折射出对人自我的认识,⑧刘亮程是在通过驴来完成对人的自省。
第一次是库被迫改变信仰的时候,不由得发出了“昂叽昂叽昂叽”的驴叫声。目睹了小母驴谢的死亡,他的心里也住进了一头驴。这种驴叫声在库改宗信天之后,不时地有种要冲出身体的冲动。同样由昆改宗信天的买生劝诫库:“我们的身体里也都有一头倔强的叫驴,谁不想像驴一样放声鸣叫呢?”⑨小说要讨论的是人们如何由信仰昆到被迫信仰天,由此给心灵带来创伤,可是偏偏要说他们的身体内住进了驴。他们从信仰昆向信仰天艰难转变,从而换取生存的机会,这并非是因为他们怜惜自己的生命,而是希望履行自己的职责,把人世还给生者,让更多的人可以有机会活着。
第二次是库在去世之前,他选择以驴叫结束自己的一生,他看见“满天空五彩缤纷的驴鸣”⑩,这是他第一次看见驴鸣是如此有色有形。师傅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叫出无须翻译的驴鸣,库在自己的最后关头也让驴叫冲破他的喉咙。师傅和库都是懂得多种语言的属驴人,为何在生命的终点都以驴叫向这个世界告别?在生命的终点,属驴人才真正领悟驴的智慧,领悟语言的本质。语言原本是用以沟通的,但是使用语言的人夹杂着私心,这就让语言存在着误传与歪曲;唯有不需要翻译的驴叫才是本真的沟通,“上天把真言给过人,被人传歪。唯独驴叫没有走形”⑪,驴叫声是纯粹的。
成为鬼魂的库来到天庭,他见到所有阵亡者的魂,不分彼此,如同兄弟姐妹一般;他向天庭的守门人申请做天庭的翻译,却被告知在天庭,人的灵魂是透明的,无须翻译。上天让库重返人间,投胎为驴,把上天的话用驴叫捎给人,彷佛绕了一大圈,又回到驴这里。人为了宣示、论证自己掌握真言,不断地进行着战争;等到人变成了鬼,又被上天告之,唯有驴叫的真言是准确的;人又要投胎为驴,重新回到人间传递真言。这里至少有两重理解,一重是关于沟通,不同信仰之间的平等对话是何等重要;一重是关于动物,人要如何处理与动物之间的关系,去倾听并善待它们,从它们那里领悟造物主的真言。
三、鬼话
“鬼话连篇”,通常用来形容人讲话满口的胡言乱语,目的是为了蒙骗人。在《捎话》中也有“鬼话”,与鬼相关的话语。黑勒与毗沙之间的这场战争让死亡像阴影一样笼罩着大地,无数士兵在战争中被割头,成为无头鬼。
无头鬼并不会开口说话,但是风声代替他们发出声响。恐怕没有哪位小说家像刘亮程这般残忍,在小说中如此来书写无头鬼吧?士兵们的脑袋如同成熟的庄稼一样被对方收割,然后被抛弃在戈壁上,任风吹着滚动:
光秃秃的戈壁寸草不生,刮西风时成千上万颗人头朝毗沙方向滚动,全滚成骷髅,头骨碰撞的声响,风吹过骷髅眼的声响,刀刃一样扁扁的,一直传到固玛,传到毗沙,被那里的无头鬼听见。⑫
风声在这里构成一种奇特的美学风格。与刘亮程以往对风的抒情描写不同,这里的风声并不指向清新的自然风光、怡人的边塞风情、纯真的田园生活,而是与死亡联系起来。令人惊诧的是,即便是风吹动士兵的头颅,头骨碰撞发出声响;风吹过骷髅眼,发出犀利的声音,你也不会觉得阴森恐怖,反而会产生一种情感上的期待,好像风声被毗沙的无头鬼听见,就可以安慰他们的心灵。虽然无法找回丢掉的头颅,但是至少听到了来自头颅的呼唤。
在中国文学中一直有志怪的传统,自魏晋南北朝起,在小说中讲述鬼神怪异的势头愈盛,出现了《搜神记》《列异传》等作品;发展到清末,更是有《聊斋志异》《阅微草堂笔记》等多种作品传世。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认为这是因为“当时以为幽明虽殊途,而人鬼乃皆实有”⑬,所以叙述鬼怪异事就与记载人间常事一样。新时期以来,诸多作家的笔下又出现了鬼的踪影,“残雪及韩少功早期即擅长处理幽深暧昧的人生情境,其他如苏童、莫言、贾平凹、林白、王安忆及余华,也都曾搬神弄鬼”⑭。这一方面是受到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中国作家们将中国志怪叙事传统激活,另一方面是文学的创新发展,对革命美学进行突破,这也让鬼魂在文学中获得呈现的机会。以莫言为例,他在作品中也写到鬼,被作家阿城称赞“格调情怀是唐以前的,语言却是现在的,心里喜欢”⑮,他对鬼的经验主要来自童年时候从老人们那里听到的“妖精和鬼怪的故事”⑯,他笔下的“怪力乱神”因联系着民间经验而显得淳厚与生机勃勃。
在《捎话》中有大量关于鬼魂的书写,除了无头鬼,还有无眠之师,一种神秘的鬼魂军队。最为人惊叹的是,刘亮程还创造了新的鬼妥觉,在毗沙人觉的身体上错缝了黑勒人妥的头,于是他们重新组合成鬼魂妥觉。作为鬼魂的妥觉在小说叙事中承担了重要的功能。妥与觉的回忆,从黑勒和毗沙不同的视角将战争的全貌呈现出来,以此完成对战争的反思;他们作为战争的亲历者,见证了这场持续多年的战争是怎样改变了两国民众的命运,从物质层面到精神层面,都经历了极大的痛楚。鬼魂妥觉倒骑在小母驴谢身上,随着库穿过两国交战的地带,将激烈的交锋、无情的砍杀都带到读者面前。妥与觉从最初的互相敌视,到进行对话,产生理解和同情的情感,他们之间的对话,算不算是“鬼话”呢?“觉,我要把我的故事讲给你,让身体知道头的事,我头里的这些事情,是另一个身体干的,跟你没关系。可是,你成了我的身体,你要认可这些。”⑰妥与觉都已经成为了鬼,他们之间的对话,是鬼与鬼之间的对话,倒是可以认定为“鬼话”,他们以鬼的视角来讲述他们对这场战争的观察与反思。
小说中最大的鬼话,反而是发生在人与人之间的,那是关于毗沙与黑勒战争的缘由。黑勒人从小被大人告知,是毗沙西昆寺的高墙把太阳挡住了,造成黑勒国的太阳升起的要晚一些。在两国都信仰昆的时候,黑勒国会向毗沙表示敬意,东方的毗沙鸡叫醒了黑勒鸡;待到黑勒国改宗信天之后,所谓的“高墙”成为战争的理由,黑勒要推翻毗沙的高墙,它挡住了太阳,让黑勒国永远要比毗沙国晚一步,这是多么荒唐的理由!鬼与鬼之间能够进行坦诚的交流,说的话是“鬼话”;人与人之间反而不能顺畅的沟通,说的话也是“鬼话”。因为人与人之间的“鬼话”,让更多的人在战争中沦为了鬼,让人生出无线唏嘘,战争的意义何在?倘若成了鬼之后,他们明白战争与高墙无关,上天也没有给过人什么经,经都是人编的;或是知道人把上天给的真言传歪了,那该作何感想?
写鬼魂,实则是在写人。
四、语言的翻译
小说中有不同的语言,所以需要翻译。从事翻译工作的是属驴人,“他们最大的共同处就是除会驴叫外,至少能说三四种语言,多的会几十种,能跟来自东方西方各个地方的人交流”⑱。翻译者还从事着捎话的工作,将一句话从一个地方带到另一个地方,从一种语言翻译为另一种语言。驴也会捎话,但不需要翻译,所有的驴都使用同一种语言,在这一点上,略胜于人。
索绪尔将言语活动分为“语言”(langue)和“言语”(parole)两部分,语言是社会成员所共有的,而言语则是受个人意志所支配的。同一社团的成员之所以能够互相沟通,缘于他们拥有共同的语言,语言发挥着统一的作用。语言研究又分为内部和外部,前者关心语言本身的结构系统,而后者则注重语言与民族、文化、地理、历史等因素的关系。借助于索绪尔关于语言的论述,我们能够更好地剖析小说中关于语言的书写。
语言在翻译的时候,势必会产生文化的交流。了解一种新的语言,实际上是了解一种新鲜的文化和一个陌生的地区。师傅教给库多种语言,给他画出辽阔的语言地图,那是“语言让远处大地一片片明亮起来”⑲。正如索绪尔所说,语言是与民族、文化、地理、历史等多种因素密切联系的,从语言起,进而了解新的民族、新的文化、新的风俗,对于世界的认知范围会随着掌握的语言增加而不断扩大。通过语言,人们认识到陌生文明的存在;借助语言翻译,不同文化得以交流,这也就促进不同民族文化的交融,进而达到和而不同的境界。问题在于,这是不同语言碰撞最理想的状态,现实往往更为复杂。
语言也有无法点亮的地方,反而会带来黑暗,“你每学会一种语言,就多了一个黑夜”⑳。语言是沟通的工具,人们借助语言保存和传递文明,一种语言承载着一个民族的文化;当某一种语言或者说某一种文化试图去征服另外一种语言或文化时,问题就会出现。小说借由库的师傅之口,道出语言的秘密。师傅认为看似被不同语言照亮的地方,其实更黑暗。他以昆经为例,昆经试图照亮世间的黑,可是当经文被翻译成黑勒语、毗沙语、皇语和丘语时,都无一例外被扔进这些语言的黑暗中。
小说中的西昆寺一直进行着昆经的翻译工作,来自各国的译者聚集在西昆寺,将昆经翻译为不同语言版本,致力于昆的传播。昆作为一种宗教信仰,信仰昆的人希望将昆文化传到更多的国家;在昆门徒看来,没有昆的地方是黑暗,只有昆才能驱赶这些地方的黑暗,给这些地方的民众带来光亮。问题是,当昆经被翻译为多种语言的时候,真的能够如同预先设想的那般照亮那些地方吗?答案是否定的。被翻译为其他语言的昆经,反而被带入那些语言的黑暗,比如说黑勒语昆经。这至少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第一层是在单纯的语言层面,当昆经被翻译的时候,可能会出现不准确的地方。所以,西昆寺在翻译的时候,每一部经书至少需要两名译者,在翻译完成之后,还需要再次校对。“他在西昆寺读过原文和译成皇语、丘语、毗沙语、黑勒语的昆经,库读出一部经因为翻译造成的差异,远大于和另一部完全不一样的经书”㉑,这一层仅仅是从语言的层面来阐释,能够做到准确的翻译已属难事,更遑论通达与优雅。第二层是要从语言深入到文化层面。每一种语言都承载着相应的文化,不同语言的交流实则是不同文化之间的碰撞。将昆经翻译为其他的语言,这实际上是在进行一种宗教文化的传播;当一种宗教文化进入到新的语言地区时,势必会对该语言区的本地文化进行冲击,其后果是不可预计的。当黑勒改宗信天的时候,黑勒语昆经不仅无法去照亮黑勒,反而会引起激烈的冲突。
语言原本是用以沟通的,不同的语言通过翻译可以互相交流,进而促进不同的文化交融,这是语言的亮;但当一种语言试图征服另一种语言,一种文化试图取代另一种文化时,这就会带来语言的黑。换言之,语言能点亮的是远处的地方,点不亮的是人心的黑暗。
五、文明冲突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众声喧哗的文本。人语、驴叫、鬼话、风声等多种声音,构成了声音的风景。那么,这些声音究竟在表述怎样的观点?
声音与文化权力是联系在一起,所以诵经的声音不单单是人向上天表明虔诚之意,昆门徒与天门徒都希望征服对方,让对方来诵自己的经。小说在开头就以诵经的声音来暗示读者,即将切入的话题与信仰冲突有关。但是小说是以驴的视角来观察这一切,这就带来丰富的叙事视角,驴获得一种超越性的视野,是最接近上天的存在。只有驴的叫声能够抵达上天,也只有驴明白“上天从没有给过人什么经,都是人编的”㉒。这一下子就戳破了皇帝的新装,既然没有经,那么,因为昆与天之争而爆发的战争意义何在?
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指出,世界冲突的根源,在于文化方面的差异。㉓他认为冷战之后的世界格局是由七大或八大文明决定的,即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还有可能存在的非洲文明;冲突的基本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也不是贫富差异,而是文化差异,即“文明的冲突”。亨廷顿的分析针对的是冷战后的世界形势,自有特定的讨论背景,在此借用亨廷顿文明冲突之观点,希冀以此为参照来察看《捎话》是如何唤起对文明冲突的警惕。
小说名为“捎话”,将一句话从此处捎到彼处,从毗沙捎到黑勒,其用意是在沟通。但是,话虽然捎到了,交流的目的却没有达到。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一从委托的一方来看,捎这句话目的并不单纯。这句话是刻在小母驴身上的一部昆经,而昆经是试图去照亮世间所有的黑暗,这从本质上是传教,是用一种宗教信仰去让另一国的民众皈依。这是一种新的宗教文化进入到另一种宗教文化的领地,这就势必会引起不同宗教文化之间的冲突。其二,从接收的一方来看,捎话的时机是不合时宜的。在一国之内,多种不同的宗教文化是否可以同时并存?答案是可以的。不同的群体拥有不同的宗教信仰,民众有着宗教信仰自由,这是可能的。问题在于,当天上升成为国教,并且要求黑勒民众都信仰这种宗教,没有信仰自由的时候,矛盾就会爆发。
小说中,黑勒和毗沙之间的战争,和历史上喀喇汗于阗战争颇为类似,黑勒由昆改天,将昆寺改为天寺,让民众改信天,并最终将毗沙灭国,将天传播到毗沙。小说中令人哀恸的无眠之师、可悲的人羊、被砍头的民众、毫无生机的村庄、被烧毁的寺庙经书,都是为此付出的代价。亨廷顿所分析冷战后的世界格局,以文明冲突作为战后冲突的重要缘由,而那场发生在10世纪晚期到11世纪初期的宗教战争已给出历史的教训。
语言作为沟通的重要工具,在小说中也是被反思的。掌握多种语言,如同翻译家库那样,并不能带来想象中的文明交流。更重要的是语言使用者的主观意愿。倘若能够反省文化责任,意识到文化和谐相处,即便是跨越界限的人与动物都可以和谐共处。在人类语言无法解决的难题面前,小说家请出了驴作为榜样。在驴的世界里,不存在天与昆之争,它们也不参与战争,就连骑着毛驴的人也不参与战争,但是上天偏偏将真言借助驴叫来传达。不论是天,还是昆,都认为自己是对上天意旨的正确解读,但却都走了形,“唯独驴叫没有走形”㉔。人类不妨去动物那里学习如何领悟真理,返回到人生的本真状态中,去体悟自然赋予人类的经验。
小说为不同文明,尤其是不同宗教文明之间如何相处敲响了警钟。小说对文明冲突的反思是有力的,将矛头直指冲突的源头。小说并没有止步于此,而是进一步构建出蓝图,在天庭重建和谐秩序,“天庭朝上的台阶上走着这场战争的所有阵亡者,他们不分彼此,手牵手,兄弟姐妹一样,往天庭的祥云里走”㉕。在天庭里,地上的一切像梦一样被遗忘,毗沙的将领和黑勒的士兵可以握手谈笑,放下仇杀和怨恨,就连妥与觉都结合得像是一个人。只是,这种被重建的秩序是存在于想象的天庭之中。
①刘亮程、刘予儿《我的语言是黑暗的照亮——〈捎话〉访谈》[A],《捎话》[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8 年版,第322页。
②王敦《声音的风景:国外文化研究的新视野》[J],《文艺争鸣》,2011年第1期。
③⑤⑦⑨⑩⑪⑫⑰⑱⑲⑳㉑㉒㉔㉕ 刘亮程《捎话》[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8年版,第1页,第132页,第27页,第200页,第304页,第310页,第167页,第160页,第175页,第179页,第111页,第149页,第196页,第310页,第308页。
④刘亮程《凿空》[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0年版,第199页。
⑥刘亮程《小说是捎话的艺术》[N],《文艺报》,2019年1月21日。
⑧Jacques Derrida.The Animal That Therefor I am(More to Follow)[J].Critical Inquiry,2002,28(2).
⑬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22页。
⑭王德威《魂兮归来》[J],《当代作家评论》,2004年第 1期。
⑮阿城《魂与魄与鬼及孔子》[J],《收获》,1997年第 4期。
⑯莫言《恐惧与希望——在意大利演讲》[M],深圳:海天出版社,2007年版,第157页。
㉓[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周琪、刘绯、张立平、王圆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228-27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