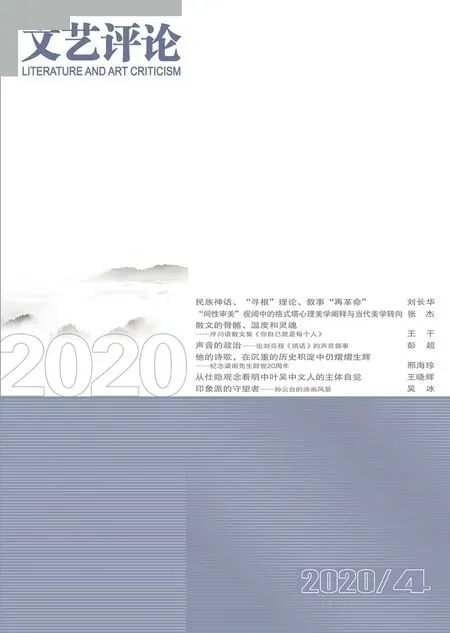民族神话、“寻根”理论、叙事“再革命”
2020-04-18刘长华
○刘长华
言及中国新文学的神话、传说书写,“寻根”文学无论如何是绕不开的议题。“寻根”文学与中国当代文学中其他衮衮文学思潮略有出入的是,它与理论自觉、学术总结之间的直线距离更短近,因为这个时段有作家亲自披挂跃马理论前线。韩少功的《文学的根》(《作家》,1985年第3期)、郑万隆的《我的根》(《上海文学》,1985年第5月期)、郑义的《跨越文化的断裂带》(《文艺报》,1985年“理论与争鸣”专栏第1期)、李杭育的《理一理我们的根》(《作家》,1985年第4期)、阿城的《文化制约着人类》(《文艺报》,1985年7月6日),等等,这些理论大旗是历史的见证,也是后来研究者弘法“寻根”文学的“宝典”。实际上,“寻根”理论不应仅指这几篇文献,阐发神话、传说书写价值更远不止它们所能包囊的。“寻根”文学“欣逢其时”的正是“文化热”高潮到来之际,相关的理论是排山倒海的,“文化寻根思潮,无疑顺应了这股巨大的学术回归运动”①。而这正是相关研究所关注不够的。就“寻根”理论中所包含叙事民族性的启示而言,我们似应扩大视域,旁及相关的民族神话、传说理论,“寻根”理论应该是一个大“寻根”理论,中间还包含相关的文学批评。“寻根”文学作家或多或少亲炙过这些理论,这是不争的。退而言之,就算某些民族神话、传说理论的确没有进入“寻根”文学的精神骨血和时代现场,它们也是历史心声中一个个不曾缺席的音符。对于这份“文化遗产”重新发掘、审视,对导航中国当下文学创作也是有着某些裨益的。
一
文学可拟神话,担待“神圣的世俗事物”②之叙述。在神话研究中,郑凡的《神话结构与功能的独特性——以独龙、怒、佤、景颇神话为例》是一篇学界重视不够的力作。它不仅着力于专业领域,而且与整个时代气候和文化大环境保持着呼吸相通。看似与“寻根”实践无甚瓜葛,却是从本源上梳理了文化之“根”——神话的本质特性;表面与文学研究颇有差池,但在叙事学或“故事学”领域里能给人以清晰扼要的省示。
首先,神话的叙述主体在“求告神灵”与“吟诵人生”之间。③李泽厚1981年撰写的《康德哲学与建立主体性论纲》、1985年撰文《关于主体性的补充说明》为掀起全国范围“主体性热”的大讨论垫埋下了哲学基石。卷身在“文学主体性”讨论热潮中有刘再复、陈涌、何西来、敏泽、杨春时、程代熙、郑伯农等,论争过程尘土飞扬,深度见证了中国思想解放征程上的几分热情、几分艰辛。是某种机缘巧合,也是历史规律的必然,“文学主体性”的大讨论与“寻根”思潮在时间上有叠合,在精神上交集。季红真在1989年的一篇带有“下结论”性的文章中,认为“寻根”思潮留给文学史第一个突出的意义就在于“重主体性认知”④。的确,进入当代文学时期,中国文学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崇尚反映论。另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学在整体上也不曾摆脱“颂圣”⑤的影子,甚至从起步阶段也是与历史、哲学等纠缠在一起。文学的主体性意识在根袛上是稀薄的。主体论的崛起,也是“人”意识复苏和进一步觉醒的互文表达。问题是从一个极端可能走向另一极端,主体的过度膨胀,意味着将外在世界全然客体化的嫌疑,时隔几年后杨春时就借鉴“主体间性”予以纠偏。早在1985年,郑凡在神话的田野考察基础之上,认为神话不类“咒语、祷词,通常都跟神灵拉近乎”,而是“故事之讲述与想象中的神灵之间,具有一定的间接性”⑥,意即多了几分世俗性;比世俗的童话和情歌等更具有宣示性、神秘感,意味着在品格层位上要高,因此“神话的故事主角及其称谓,体现了它与求告神灵和吟诵人生这两种行为方式都不同,可以说它是位于两者之间,架成一座彼岸与此岸之间的桥梁,担当一种神圣的世俗事务”⑦。郑主要立足的是叙述者(也涉及到文学人物形象)这一角度来阐释主体性的,这种“中庸”性的观照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我们都应将其视为对时代的回应,对人既是一种适时的扩张,也是一种必要的审慎。
其次,神话的叙述时态多为“现在完成时”。众所周知,叙述时态的意义支点主要建构在与读者距离之间的把控之上。这除了关涉到写作者的价值姿态选择,也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影响到接受效果。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前期文学语境,是不难发现,“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其叙述时态在总体上是“过去时”,往往包含着一种回忆性的写作底色。问题是,这种“过去时”单从逻辑和学理上就意味着与过去挥别了,事不关“今”。显然,这是对曾经令人刻骨铭心的历史“不负责”,是一种“为了忘却的纪念”。所谓“历史意识”,正如约恩·吕森所说的“是将时间经验通过回忆转化为生活实践导向的精神(包括情感和认知的、审美的、道德的、无意识的和有意识的)活动的总和”⑧。“过去时”与这种“历史意识”在理路上就不大衔接。当然,这里面还牵涉到汉语本身没有“时态”的问题。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不过,由此恰恰显示出叙述方法、叙述策略的重要性。郑凡在《神话结构与功能的独特性——以独龙、怒、佤、景颇神话为例》中梳理出神话的叙述时态一般是“现在完成时”⑨,尽管它的叙述对象与内容都是“过去时”的事件,它也不像:“咒语和祷词是对现时愿望(有时还非常具体)的直截诉说。”⑩换言之,“现在时”或者“现在进行时”往往是与主体(作者与读者)切身利益相关的,带入感和情境意识过于强烈。因此在“出乎其外”这方面是大有缺憾的。神话的“现在完成时”则是将读者置于“入”与“出”的中间地带,文学功能也不再是为“教化”所包办,同时又是“庄严宣告过去留下的传统”⑪,在世俗与神秘之间达成和解。这样的情状正出现在不少“寻根文学”作品之中。
最后,神话的情节叙述中对“母题”的普遍应用。情节是神话不可或缺的质素。不过,与一般意义上的情节有所不同的是,神话的情节具有原发性、恒定性、集结性、单一性等特点,人们因而将其命为母题。在这一点上,荣格、普罗普、汤普森等相关理论是较为深入的。郑凡在《神话结构与功能的独特性——以独龙、怒、佤、景颇神话为例》在一文中,意识到神话的情节与其他类型的故事是不同的,但他只是模糊到神话起到“说明因果的价值”⑫,没有直截了当地提出“母题”这一概念。而这种“说明”是“主角的目的、行动和结果,反映着心理水平上对因果关系的清晰意识。”⑬从中不难看出,其中就与荣格所说的“民族集体无意识”有着不太精准的对应。郑凡在此基础上,比较了神话与童话的不同之处,最终指出:“神话一经形成并在一定限度内完备了,这种解说就成为全社会规范的解说,只要社会背景不变,它也就成了必然的、不容许‘灵活多变’的。”⑭这一说法极其契合母题的特质。图腾是某一母题固化和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母题一方面反映了先民在理解世俗生活和征服宇宙自然时的真实心理,另一方面在某种程度上是“以故事形式出现的社会法规”⑮,具有几分神圣性。因此,不少母题是链接着世俗和神秘两个世界。母题对叙述文体的介入从中能深刻地折射出民族的集体无意识或者原始思维的,这正是“寻根文学”交付给自己的历史使命和时代精神之一。从另一个侧面来看,母题也使得相关的叙述看似多沾溉了一丝“民间化”的味道,实则是更增添了几分文化气息,是对那种所谓呈现化写作的超越。这一点对那些与民族神话、传说书写直接关联不甚紧密的作品而言,尤显明显。
二
神话是非“规范”⑯性叙述。在“寻根”作家李杭育眼里,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原规范文化是“儒臭”,文学创作动辄在“道”的名义之下,“这是政治的、伦理的,而绝非哲学的、美学的”⑰。李杭育和韩少功等在“寻根”文学运动中,对史前文化——神话的推崇是颇为用力的。富有意思的是,李与韩两人在后来的文章中,对神话作为一种艺术生产其“非规范性”的特点有着英雄所见略同般的应合。这大概是在“杭州会议”上所达成的某种共识。以“非规范性”来概括中国神话的突出特点,于学理而言是不大精准的,因为中国古神话中对道德等的弘扬也是尤为其甚的,譬如“尧”“舜”“禹”等其所谓的“神迹”很大部分就是建立在立功立德之上。总体来看,“寻根”作家所持认的神话为“非规范性”叙述,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的表现。
首先,神话的“非规范性”叙述能展现历史心灵的真实。规范的意义在于有序规整,合乎集体、世俗的名义与要求,以外在的、体面的、仪式性的方式表达出来。其所彰显出历史和现实的价值是显而易见的,但规范本身也是具有缺陷与不足的,譬如对个性、差异性和内层的诉求一般采取拒绝或者压抑的态度就位列其中,以至于对某些“不足外人道”的真实存有遮蔽。唐代的格律诗是一种“规范诗学”⑱。它寓示和见证着中国诗歌达到了一定精神成熟度和形式高度,然而它过于“文人化”是不大利于对整个时代某些深层次心理释放的,而“非规范”往往意味着将沦为所谓“痛失雅正”。李杭育在《理一理我们的“根”》中,以伏羲与女娲的故事为例,礼赞“非规范性”叙述第一个突出效能便是它的认识价值。在西南少数民族的神话、传说中,伏羲与女娲是结为夫妻的,人类由此得以再造,是为人祖。这在相关边缘性古籍《三五历纪》中有印证。但到了《太平御览》《独异志》等书中,一些细节被窜改了,从中不断加入了叙述者的伦理评判和思想引导,就此强调了教化功能。先人自认为天经地义、顺乎自然的事情,在后来者看来就是荒诞不经的。这显然是对历史本身的不尊重,是以论带史。古人的原初想法究竟怎样,便不得而知了。因此,文学创作重返神话那种原生态,不仅仅是将文学视为一种反映论,一种旨在无限贴近现实的反映论,甚至是有本体论的味道。神话作为初民全部意识结构的集结,列维·施特劳斯大抵持这样的神话观。返回神话,也就意味着打破各种文体的“规范”,冲破“语言的牢笼”,进入本体层面,相对而言更能反映历史心灵的真实,也将抵达存在之真。所以,李杭育动情地说:“一种真实的文化,质朴的文化,生气勃勃的文化,比起我们的远离生存和信仰、肉体和灵魂的汉民族文化,那一味奢侈、矫饰,处处长起肿瘤、赘疣,动辄僵化、衰落的过分文化的文化,真不知道美丽多少!”⑲
其次,神话的非“规范”性叙述是原始思维美学的绽放。对西方原始文化研究成果的激情拥抱,是20世纪80年代“文化热”的重要有机组成部分。一时间,泰勒、列维-布留尔、列维-斯特劳斯、维柯等人在学术市场上极为行销。“原始思维”等概念在国内学界炙手可热。相对儒家的正统意识,原始思维自不待言属于“非规范性”,属于“怪力乱神”之类。李杭育在《理一理我们的“根”》中引证和肯定“伏羲与女娲的神话被证实起源于湘西的苗蛮集团”,这是个人学术观点的选择问题。他的这般“执意”,与他对“非规范性”文化的神往合二为一。他在转述伏羲与女娲的神话时,说:“雷公发洪水灭绝人类,一对童男女(即伏羲与女娲)入葫芦避水幸免于难。洪水退后,二人有感于蜥蜴交尾,触景生情,以兄妹结为夫妇,再造人类,是为祖先。”其中“有感于”“触景生情”这些细节,正是原始思维的体现。这也就是弗雷泽在《金枝》中所讲的“相似律”⑳。这种“相似律”也表现为浪漫的想象,楚辞和吴越文化是韩少功、李杭育等人极力宣扬的。而这一切很大范围是建立在神话、传说这一文化事象之上,这正是李杭育们是所“会心”的:“楚辞浪漫、奔放,异想天开,且大量地运用了上古的神话传说。”㉑搁置20世纪80年代中前期具体文学语境来看,“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等是现实主义路数的拥趸,且在理解何谓现实主义的视野和胸襟方面都大为扩展。“27年文学”与“红色经典”在写作理路等方面更是严格遵循某种观念。但是,总体上而言,它们都是一种“规范性”的叙述和写作。“两千年来我们的文学观念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而每一次的文学革命都只是以‘道’反‘道’,到头来仍旧归结于‘道’,一个比较合时宜的‘道’,仍旧是政治的、伦理的,而绝非哲学的、美学的。”㉒过度的规范是对文学的主体性背离。从元叙述上来看,原始思维是有对世界原初命名的意味,部分体现了文学的主体性回归。这正是“寻根文学”大潮泛起的初衷和内在动能之一。
最后,神话的非“规范”性叙述是一种有生命力的叙述。韩少功在《文学的“根”》中同样用文学色彩极浓的口吻说道:“这一切,像巨大无比、暧昧不明、炽热翻腾的大地深层,潜伏在地壳之下,承托着地壳——我们的规范文化。在一定的时候,规范的东西总是绝处逢生,依靠对不规范的东西进行批判地吸收。”㉓意即包括“神怪故事”㉔在内的“非规范性”的文化是所谓“规范性”文化的重要精神资源武库,一方面可资开采,一方面能收藏着那些“礼失”的部分。说来说去,“非规范性”文化从根本上就在于它的健旺的生命力。规范性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精致化、专门化、绝对化。相对而言,那种粗朴古越的状态其可塑性、开放性更强,从中所寄寓的是创造者与整个时代的生命坦诚度、元气淋漓感更鲜明。“寻根文学”运动中的重要理论干将李陀曾谈及对霍去病墓前雕塑的观感。对于那些怪诞和充满神话色彩的雕塑,李陀依然认为是因为“与商周文化与楚文化中所共有的‘巫’的传统有关”,“至于社会心理、宗教意识、生活态度、艺术观念等领域,汉人与屈原相去并不很远”㉕。李陀甚至还认为,“汉代方术及谶纬的流行”“造就了汉代人奇异发达的思维,以及汉代人特有的炽热粗放的情感”㉖。李陀所强调的生命力正是与神话那种“非规范”的思维和意识联系在一起。对于过于规范性的写作,李杭育所说的“处处长起肿瘤、赘疣,动辄僵化、衰落的过分文化的文化”,正是针对于生命力而言的。对民族文化生命强力的呼唤,正是“寻根文学”运动所内蕴的一支精神流脉。莫言、贾平凹等人相关作品,叙述方式的确也显得简古朴拙,形式与内容是相称的。
三
从中国神话的历史化反观叙事的“由史返文”。正如前文中已经提及“寻根文学”是一个系统,在一个文学时代的氛围,文学的各方角力都在有意无意地参与现场。董乃斌的《中国叙事文学的演变轨迹》虽然着眼于古代文学中的叙述轨迹梳理,但其着力点与“寻根文学”在寻求理论资源支撑方面上有着精神耦合。在文中,他抛出的一个话题就是:“中国古代神话对于叙事文学的成长发展关系如何呢?”㉗这正与其时整个中国文坛对神话的重视是齐步同行的。董乃斌的一个基本判断就是中国神话的历史化,这是中国神话的独特性,并由此导致中国的叙事特色有二,即“一是文学叙事能力向历史领域转移,二是‘史贵于文’价值观的确立”㉘。在这两个基础之上,《中国叙事文学的演变轨迹》还对中国叙事文学相应的特点做过归纳。回返中国神话本身来看,将中国神话的“祛历史化”,中国当代叙事文学应获得相关的启示。
首先,注重对“第二现实”㉙的创造。关于所谓的“历史事实”,人们是多重看法的。“什么是事实?在这里,日常语言就准备好了一个答案。正常地,我们应该说,任何领域里的事实就是独立于研究者自身之外的东西;在某种意义上,无论任何人想没想到它们,它们都存在着。它们就是我们所描述为‘过硬的’‘顽强的’或‘给定的’东西”㉚,这是兰克史学传统的基本观点之一。饶有意味的是,将历史事实等同于客观性,可以说也是中国普通百姓的集体无意识或者集体“有”意识。“秉笔直书”“信史”等说法就暗含着这样的意向。而且在出于李世民所说的那种“知兴替”的目的之下,历代统治阶层又是高度重视历史的作用。对历史的无限推崇最终演绎成了“六经皆史”的论断。与之同时,为了增强史籍本身的阅读感和最大程度地释放出其精神能量,中国历史也是讲究叙事技巧,即董所说的文学的叙述能力向历史转移;另一方面,中国史籍在写作过程之中或者在后世传布时,可以删,可以改,但是无论如何,它就是不能让人产生虚幻感、想象性、超越意识即“第二现实”的。“所谓文学叙事,它不同于一般的陈述、记载之处,在于它不但是充满感情色彩的,也不但是讲求辞章藻饰之美的,关键是在于它的叙述常常需要突破实事的限制而进入虚构之境。”㉛而神话最为突出的特点之一,就是它能营造“虚构之境”。中国神话的渊薮《山海经》,整部书籍很大程度在书写维度上正是以山为经、海为纬,建筑了一个“虚构之境”。这是对现实生存世界的某种逃逸,不需要接受世俗眼光的挑剔和检验。在中国神话之中,不少的神诸如尧舜禹等,被后世认为是某种现实生活和文化的传始者。这是神话的历史化,不过这恰恰反映了他们本身是生活在“第二现实”之中,为制造“现实”而生、而来。因此,叙事文学创造出“第二现实”,从根本上说文学应该不必拘泥于人们眼前的、日常的世界,在想象等手段中体现出它的超越性。
其次,以“史诗”而非“诗史”的叙事批评标准。正如前文中已经多次提及西方所訾议的中国无“史诗”。确乎,这里面也存在一个基本事实,便是初民“史诗”的发达程度与神话、传说的丰富与否两者是成正比的。从语义来看,“史诗”的重心落在“诗”上,即强调的是文学性、审美性。甚至可以做一个泛化的理解,“史诗”中的“史”不排除历史知识的融入,但它更像是在表达一种条理清晰、富有逻辑、讲究理性的味道。希腊的“史诗”并不承担再现希腊历史的责任。“诗史”则不同,董乃斌进入中国文学批评史,基于大量的史实并以夏志清等现代学者的研究成果做验证,得出“所谓‘诗史’的批评标准,就是说只有达到了或被认可为具有‘史’的水平的文学作品(无论是诗、小说还是又划剐),才是应予高度评价的上乘之作”㉜。实际上,在20世纪中国新文学中,“诗史”的标准是被有意无意地拆解了。首先,“寻根文学”中的“根”与“历史”的含义就不在同一语义场上。“寻根”并不是在追寻、回溯、还原民族的具体生存情境,从中“考古”出某些历史真相,得出考据学的某些认知。在建构形式上,更像是“六经注我”即强调与当下人文精神相互勾连,而非“我注六经”地爬梳剔抉。实际上,“典型”这一范畴在新文学批评史上曾经一度广有影响,几成绝对标准,特别是在现实主义文学这一畛域。按照恩格斯的说法——“除了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㉝,“典型”是个性与普遍性的统一,而历史更多的是“描述已发生的事”㉞,因此相关的叙述一般难以蕴涵普遍性事实的体认,显然这本身更像是对“诗史”的远离,与“史诗”观念的呼应。对于新中国建立后的长篇小说、“红色经典”以及后来一些叙事时间跨度较长的作品,人们基本上都以“史诗”而非“诗史”为批评命题,虽然在具体操作还不免依然存有将“史诗”与“诗史”混同的现象。所以,有学者提出“史”“诗”“思”三者有机结合的原则”㉟,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有淡化“诗史”的践行价值。
强化“史诗”而非“诗史”的批评标准,应对于中国新文学的叙事实践,是有其针对性价值的。报告文学是中国文学史上出现的一个新文类,纪实是它突出的特点。近些年来,纪实文学更是独擅胜场,梁鸿等人的作品无论是批评界还是普通读者都青眼有加。当然,纪实文学的兴起也是一个全球性的话题,譬如2015年阿列克谢耶维奇获得诺贝尔奖。人类亟待用文学来解决现实问题。但文学的本质在于它不能解决任何实际问题,它只是有助于而已,是间接性的,否则是对本质的异化。因此,纪实文学的灵魂还必须是文学的即“诗”的,在批评标准上更应警惕“诗史”的覆盖。
最后,叙事文学应淡化历史经验中所渗透的道德教化。塔西佗说过:“历史的职责即是扬善惩奸,以警后人。”㊱中国史著中对道德教化的器重比希腊等有过之无不及的。当然,“文以教化”,中国传统文学体系在这一点上是不甘示弱的,毕竟“文”“史”“哲”在传统中国长久一段时间都是不分家的。董乃斌对普实克的观点十分认可:“一面也指出重真实、重思想认识功能是中国作家‘具有自觉的严肃态度和文学责任感’的表现,‘使中国文学有一种高度的道德风尚’,观点尚属全面。”㊲就此,“由史反文”似乎存有逻辑上的支绌。推究起来,此“文”正应是原生态的神话、传说所指涉的“文”,沉潜在民间状态的“文”,譬如伏羲女娲兄妹成亲的故事等。叙事文学因此尽可能地绕开道德十字架的绑架,而以美学、人类学等为标准。
四
从神话、传说中抽绎出民族精神,并解码成叙事民族性的某些认识。“寻根文学”运动的初衷在韩少功等人看来,就是要实现一次文化上的涅槃再生。㊳这种涅槃是要回到儒家主流文化之前的那种生气勃勃状态。这点与鲁迅等人对史前文明的推崇,并将其与现代文明的嫁接是英雄所见略同的。“求古源尽者将求方来之泉,将求新源”㊴,最终以期“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㊵。20世纪80年代相关的理论家提出了一个核心概念——民族精神。这个民族精神在外延上,与“五四”时期的国民劣根性批判,与20世纪三四十年代抗日战争之际对百姓精气神的鼓与呼是大有出入的,主要赋予的是民族独特的文化心理、生存密码等意蕴。有关于神话与民族精神之间关系的探讨,谢选骏等人较为投入,虽然此前西方哲学家尼采、赫尔德,包括黑格尔和荣格等都涉足。固然,包括韩少功在内的其相关论述并没有条分缕析出叙事民族性在具体操作实践上的子丑寅卯来。但,从谢选骏和韩少功等人对民族精神的奋力呐喊中,还是能提炼出他们对叙事民族性在宏观上的认识。
首先,叙事上的东方思维与批判现代性相容。韩少功在《文学的“根“》结尾部分不无动情地讲到中国正在“向西方‘拿来’一切我们可用的科学和技术等等,正在走向现代化的生活方式。但阴阳相生,得失相成,新旧相因,万端变化中,中国还是中国,尤其是在文学艺术方面,在民族的深厚精神和文化物质方面,我们有民族的自我”㊶。在此结论之前,该文援引了一些有关西方现代主义向东方文化皈依的事例。现代主义的精髓是对理性的绝对化、一元化的反思和批判。从事理上来讲,理性是对原始思维、非逻辑形态的反动,现代主义是对理性的反动,东方思维与现代主义的应合也就成了某种可能。不过,这不是简单的轮回和复归,西方在理性与非理性上的嬗变还存有黑格尔所说的否定之否定的意思。因此,这种应合只能说有很大部分的交集而已,在根本属性上还是全然不同的。回到文学上来,东方叙事学或者说叙事上的东方思维究竟是什么,韩少功的落脚点似乎并不在此。谢选骏在《神话与民族精神》中是审慎和辩证。他认为,“把现代文化的一个枝桠(科幻小说)与古代文化的乔干(神话)相提并论,是一种容易引起误解的比附”㊷。科幻小说与批判现代性之间的亲密关系毋庸讳言。谢选骏在指出科幻小说与神话之间的“神离”,恰恰又是肯定了两者之间的“貌合”。落实到具体的叙事策略上,谢选骏有过某些散点的认识,但其专业指向并不落在指导文学创造的实践上,因此也只是吉光片羽。叙事上的东方思维与批判现代性相容,这样观念的提出无疑能极大增强中国作家的叙事自信。“寻根文学”与所谓的“魔幻现实主义”结盟,东方思维从中所扮演的纽带角色,或者说中国作家笔下的“魔幻现实主义”从根本上就是东方思维、本土意识的别样演绎,这是不能不引人为之深入思考的问题。在东方思维上,阿城的那种眷恋态度更可堪为深情款款,虽然他并不立足于神话、传说本身,虽然他对批判现代性本身也有些不甚了了。他说过,“若将创作自由限定为首先是作者自身意识的自由,那就不能想象一个对本民族文化和世界文化认识肤浅的人能获得多大自由”㊸。阿城的意旨是在包括叙事在内的整个文艺创作上,不必盲从西方的方法论进而从本体上否定中国文艺、哲学。他是从中西文化的“隔”中看到“不隔”,即强调的是东方思维和西方精神两者的平等与对话——“再譬如易经的空间结构及其表述的语言,超出我们目前对时空的了解,例如光速的可超”㊹。郑万隆在《中国文学要走向世界》一文中也有过类似的看法。
其次,民族精神与神话、传说互为表里,应重视叙事个性。谢选骏认为,“体系神话虽是社会发展、文明出现的必然产物,但不同的民族生活、文化心理和‘民族精神’,却足以给各民族的体系神话打上不同的印记、铸造不同的形态”㊺。这是对尼采、赫尔德、黑格尔和荣格等人理论的发挥和展开。在这个基础之上,谢选骏站在世界体系神话的比较基础之上,并扼要地归纳出了中华民族精神的几个突出特点。而这些特点最终都统摄在“历史化的道路”㊻,因此是“在中国,文学的发展与‘历史’缘分甚深。‘演义’小说在中国异乎寻常地发达,最终形成了一种历史化的小说传统”㊼。就此,谢选骏与董乃斌的结论惊人一致。谢选骏最终进一步给出一个论断:“生物存在与个性的本质,在不同条件下,表现出不同的地域特征、民族特征、时代社会的特征、世界历史的特征,是为神话的种种构成。”㊽总揽起来,在谢选骏看来对民族精神的正视,就是对文化个性的尊重。而个性话题正隶属现代性范畴。作家贾平凹对这一点说得朴素直观,“文学作品就能深入地准确地抓住作为人的最根本的东西,作品的精髓和情调就只能是中国味、民族气派的,而适应内容的形式也就必然是中国味,民族气派的”㊾。贾平凹所说的“中国味”“民族气派”与“二十七年文学”所讲的不一样,它主要侧重于文化立场。韩少功在《文学的“根”》一文中的一个重要落脚点也是谈“自我”:“我们有民族的自我”,“释放现代观念的热能,来重铸和镀亮这种自我”㊿。
小结
通过上文的展开,能看出“寻根”理论不止局限于与文学相关的表述,因为那的确是一个“文化热”的时代。对民族神话、传说铺开充分的认知,这不仅仅只是从中发现某些独到的文化意象和文学母题,而且能促进对叙事民族性的深入把握。叙事民族性的建构一直是中国新文学所关切、所焦虑的问题。“寻根”理论就表现出了与通常文学史视域下总结文学传统、保持文学传统在路径上的不同,暗含着“否定之否定”的“再革命”思想。在信息化、网络化主宰的当下,保持文学的个性、特性无疑尤为重要的。譬如网络文学中的“玄幻”“穿越”等主题作品,如果能真正与民族神话、传说保持文脉上的贯通,其社会价值和文化意义自不待言将会得到更大的认可,在叙事上将会有更强大的文化底蕴、精神气度做支撑。中国当下文学如何从更古老的神话、传说中的井水中汲取营养,又保持生命流脉的开放性,这便是我们再度回
①季红真《文化寻根与当代文学——序〈新时期文艺理论大系〉·文化寻根》[A],《忧郁的灵魂》[M],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264页。
②③⑥⑦⑨⑩⑪⑫⑬⑭⑮郑凡《神话与文化系统》[A],云南省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室编《民族文谈》[M],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151页,第151页,第150页,第151页,第148页,第148页,第148页,第151页,第151页,第153页,第153页。
④季红真《文化“寻根”与当代文学》[J],《文艺研究》,1989年第2期。
⑤资中筠《知识分子对道统的承载与失落——建设新文化任重而道远》[A],梁由之编《梦想与路径:1911-2011 百年文萃(3)》[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1453页。
⑧[德]约恩·吕森《历史思考的新途径》[M],綦甲福、来炯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社,2005年版,第63页。
⑯韩少功《文学的“根”》[J],《作家》,1985 年第 4 期。
⑰⑲㉑㉒李杭育《理一理我们的根》[A],王蒙、王元化编《中国新文学大系:1976-2000文学理论卷(2)》[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201页,第202页,第203页,第200-201页。
⑱[俄]鲍里斯·托马舍夫斯基《诗学的定义》[A],什克洛夫斯基等著《俄国形式主义文论选》[M],方珊译,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80-81页。
⑳[英]弗雷泽《金枝 巫术与宗教之研究上》[M],徐育新译,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19页。
㉓㉔㊶㊿韩少功《文学的“根”》[A],《韩少功作品自选集》[M],桂林:漓江出版社,1997年版,第357页,第357页,第359页,第359页。
㉕㉖李陀《中国文学中的文化意识和审美意识——序贾平凹著《商州三录》》[A],杨扬主编,郜元宝、张冉冉编《贾平凹研究资料》[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93页。
㉗㉘㉛㉜㊲董乃斌《中国文学叙事传统论稿》[M],上顾和审视“寻根”理论的全部意义之所在。海:东方出版中心,2017年版,第316页,第321页,第324—325页,第330页,第333页。
㉙朱玛主编《电影电视辞典》[M],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年版,第8页。
㉚[英]沃尔什《历史哲学——导论》[M],何兆武、张文杰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73页。
㉝[德]恩格斯《致玛·哈克奈斯》,张德厚编《西方文论精解》[M],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684页。
㉞[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诗学》[A],伍蠡甫编《西方文论选》[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64页。
㉟吴培显《诗、史、思的融合与失衡——当代文学的一种反思》[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版,第32页。
㊱[古罗马]塔西佗《编年史》[A],[英]汉默顿《伟大的思想,塑造人类文明的力量》(历史卷)[M],北京:九州出版社,2004年版,第78页。
㊳韩少功《爸爸爸》[A],《故人》[M],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33页-第339页。
㊴鲁迅《摩罗诗力说》[J],《河南》,1908年第 2期(笔名令飞发表)。
㊵鲁迅《文化偏至论》[J],《河南》,1908年第 7期(笔名迅行发表)。
㊸㊹阿城《文化制约着人类》[A],王蒙,王元化编《中国新文学大系:1976-2000 文学理论卷(2)》[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197页,第197页。
㊾贾平凹《四月二十七日寄友人书》,程光炜主编,谢尚发编《寻根文学研究资料》[M],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10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