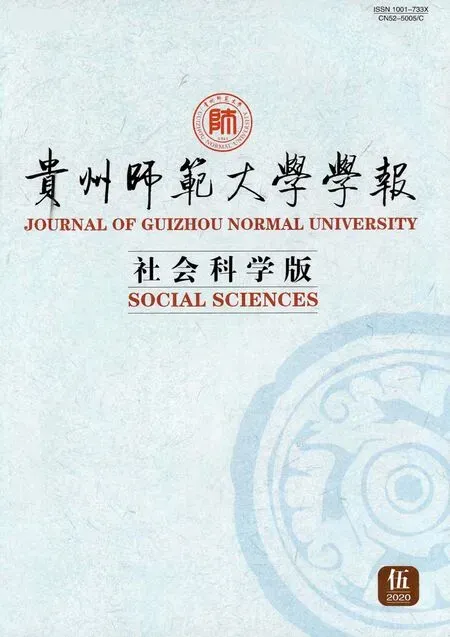论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研究的现状、得失与前景
2020-03-16韩晗
韩 晗
(武汉大学 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湖北 武汉 430000)
文化产业是近年来国内外学界广泛关注的一个领域,关于文化产业历史、理论与对策等各方面的研究已成为学术热门课题。文化产业形成的基础是市场经济。因此,海外特别是西方国家文化产业实践、相关理论的提出以及若干问题的思考均比国内要早。就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研究而言,也是海外学界早于国内,并且在研究方法上曾给予国内学界颇多启发。虽然在形式上形成了国内外两个分支,但受制于目前国际总体学术环境,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研究在话语权力上仍以海外中国研究(Chinese studies)为主导,这是目前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研究的现状。
(1)此处需要厘清两个概念,一个是“中国研究”,另一个就是“汉学(Sinoloy)”,这两个概念均为专有名词,但多数时候会被学界混用。两者虽然有共同点,但也有差异:海外研究中国问题,先后经历了从欧洲向美国的过渡,欧洲多半从敦煌经卷、金石碑版等历史文献来研究古代中国,被称之为“汉学”;20世纪中叶以来,以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为代表的美国学者则开创了关于现代中国的研究,并促使国际中国问题的中心从欧洲转向了美国,这一研究被称之为“中国研究”。(参阅朱政惠:《美国中国学发展史:以历史学为中心》[M].上海:中西书局,2014年,第200-204页)故而除特别说明之外,本文概以“中国研究”称之。哈佛大学王德威教授是海外学界提出“中国现代文化产业”这个概念的学者,早在1997年,在《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Fin-de-siecleSplendor:RepressedModernitiesofLateQingFiction)一书中,他专门提到了“晚清通俗小报与休闲杂志”的“文化产业”(cultural industry)[1];这一提法受到了其他海外学者的认可,譬如周佳荣在其代表作《早期中国的印刷、文化与权力》(Publishing,Culture,andPowerinEarlyModernChina,2004)中多次用到产业(industry)与市场(market)这两个词来定义清季民初的出版活动;史通文(Andreas Steen)在《在娱乐与革命之间:留声机、唱片和上海音乐产业的初期(1878-1937)》(ZwischenUnterhaltungundRevolution:Grammophone,SchallplattenunddieAnfängederMusikindustrieinShanghai, 1878-1937, 2006)一书中论述中国早期唱片产业的发展时,十余次用产业(industrie)来形容当时日渐兴盛的唱片市场,并在标题中用了“音乐产业”(Musikindustrie)这个词。而芮哲非(Christopher A. Reed)则直接以“文化产业(cultural industry)”来指涉晚清以来中国精英阶层消费的文化市场[2]。由此可知,海外主流学界不但认同中国现代文化产业的客观存在性,并形成了稳定的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研究格局,且对国内学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在“海外中国研究热”的作用下,国内学界也开始从不同学科的角度关注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与之有关的各种问题受到了不同程度的重视。最早提出这一问题的是焦润明,他从晚清维新派的文化产业运作与思想启蒙入手,并定义“文化产业是指以生产和销售知识产品为目的的企业”[3],之后李长莉也对晚清具有“时尚型、消费性、商业性”特征并“以市场导向而制作的文化产业”提出了自己的看法[4]。最近十余年,国内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研究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几乎涉及中国现代文化产业的各类样态。但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尚无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的总体研究。事实上,作为一门独立的门类史,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具备总体上的完整性,并系统地反映了中国现代文化的生产、消费、分配与传播等一系列特征[5]。
所谓总体研究,一方面就是对中国现代文化产业的发生、发展与演变规律进行总体性的学理性总结,另一方面就是立足于总体史的视野,从中国现代史的具体国情出发,对中国现代文化产业百年发展、演变的得失进行探讨与思考。本文拟从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研究的现状入手,从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研究发展史的脉络出发,分析海外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研究对国内学界利弊两个方面的影响,从而揭橥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研究的得失,并试图为今后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研究的发展前景提出合理的设想与建议。
一、国内外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研究的现状
历史地看,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研究,次第经历了两个历史阶段。第一个历史阶段可称得上是“海外萌芽”,该阶段大约自1980—1990年代之交至21世纪初。若是将其放置到海外中国现代文化史研究的维度下来观照,可见它实际上是海外中国现代文化研究的第三个时期。
在此之前,海外中国现代文化研究次第经历了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1940—1970年代,当中几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分别是费正清、列文森(Joseph R.levenson)与夏志清。正是费氏的努力,使得中国问题研究的中心从欧洲转向了美国,并且促使海外学界开始从区域研究(Area Studies)与跨学科的角度关注中国现代史;列文森则从儒教的现代命运入手,对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研究进行了填补空白式的研究;夏志清的《现代中国小说史》(AHistoryofModernChineseFiction)被公认为是海外中国现代文化史研究的开山之作。但因冷战时期的特殊性,这一时期的海外中国研究难免被打上强政治弱学术的烙印,而海外中国现代文化史研究也只是萌芽期;第二个时期从1970年代的越南战争结束、中美建交至1980—1990年代之交的苏东剧变,海外中国研究界从社会史、政治史、经济史与思想史等不同角度出发,以中国现代史研究为依托,来预测未来中国的走向与可能出现的变革,当中代表人物是周策纵、周希瑞(Joseph W. Esherick)与魏斐德(Frederic Evans Wakeman, Jr.)等,但这些学者主要将精力放置在中国现代史研究上,同时对中国现代文化史诸问题有所涉猎,进而在客观上推动了海外学界对中国现代文化史的研究,此阶段应是海外中国现代文化史研究的发展期。
因海外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研究是海外中国现代文化史研究的第三个时期,故而这一阶段可以看作是从文化产业的研究视角来观照中国现代文化史诸问题,也是海外中国研究界真正开始自觉地关注中国现代文化。因此,可以看作是海外中国现代文化史研究的成熟期。从学术谱系的角度来看,文化产业研究发源于20世纪中叶兴起的文化研究,如伯明翰学派的大众文化理论、葛兰西(Gramsci Antonio)的“文化—资本”理论、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理论等等,这些理论常被海外学者用以解读20世纪人类在资本主义时代中所呈现出异彩纷呈的文化现象。1980—1990年代之交,文化研究激起了海外中国研究学者们的兴趣,他们也开始借鉴这些新兴理论解读近代以来的中国文化现象,构成了海外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研究的先声。譬如金介甫(Jeffrey C.Kinkley)的沈从文研究、马利安·高利克(Marián Gálik)的茅盾研究、柳存仁的鸳鸯蝴蝶派小说研究、李欧梵的鲁迅研究、圣丹尼(Douglas St Denny)的摄影技术在华传播流变研究与哈利德·萨金特(Harriet Sergeant)的海派文化研究等等。后者在1991年出版的著作《上海:文化碰撞之点(1918-1939)》(Shanghai:CollisionPointofCultures1918—1939)以文化研究中的批判理论为工具,对1918-1939年上海地区中西文化共生并且形成的都市消费文化进行了细致的阐释与研究,可谓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之一。但此时国内学界研究中国现代文化史,仍多半从文化思潮、流派的发展及当中的文本、作家、艺术家与重大事件入手,对于文化产品的生产、消费、交换与分配诸要素依然关注不够。
但需要说明的是,这并非意味着海外中国研究界自发并有意识地研究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此时的海外中国研究者们只是将文化产业作为切入中国现代文化史研究的视角,属于区域研究与文化研究相结合的结果。可以这样说,真正引发海外中国研究界关注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并有意识研究当中诸问题,当从法国文艺理论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文化生产场域”理论对海外学术界的影响谈起。
布迪厄从社会经济学有关理论出发,认为文化资本是资本的一个重要组成,而且文化体现了资本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因此,反映经济、政治关系的文化生产场域(the field of cultural production)是客观存在的。从理论谱系上来说,布迪厄的观点与伯明翰学派、法兰克福学派诸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有着先承后续的关系。但布迪厄的走红恰在1990年代之初,这正是海外中国现代文化史研究进入到第三阶段的转折期。
1990年代,美苏两极结束了对抗,中国因邓小平的南巡讲话而进入到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被确立为中国的经济体制,海外中国研究界也逐渐减少了对中国社会、文化的冷战式批判,并试图从中国现代文化中探索出未来中国社会、经济的变革趋势。这使得一批海外中国研究学者开始用布迪厄的“文化生产场域”来解读中国现代文化,并对中国现代文化的生产、消费、传播机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一阶段具有开辟性的西方学者首推贺麦晓(Michel Hockx),他在1996年主编出版的《二十世纪中国的文学场》(TheLiteraryFieldofTwentieth-CenturyChina)可以看作是运用“文化生产场域”理论解读中国现代文化的开山之作。当然,同一时期较有代表性的研究还有王德威的晚清小说与小报研究、张英进的现代中国电影史研究、耿德华(Edward Gunn)与傅葆石的沦陷区文艺生产研究、李欧梵的现代中国城市文化研究等等。这些为日后海外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研究的蓬勃发展打下了重要的基础。
20、21世纪之交,意大利“微观史学派”特别是文化微观史(Cultural Mierohistory)研究日益受到国际历史学界的推崇,这一关注日常生活细节与具体器物、强调微观研究的范式当然也波及到海外中国研究界,形成了学术研究上的“范式转换”(2)“范式转换”是美国科学史学家托马斯·库恩(Thomas Samuel Kuhn)提出的一个观点,认为任何学科的研究都存在潜在的危机性,一旦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必须要“范式转换”——对理论方法、话语表达、思维观念、视野立场进行彻底的替换,只保留基本研究对象并遵循基本逻辑,否则这一研究就会穷途末路,譬如已故美国中国史学家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ik)曾以此概念来描述当时的中国现代史研究,认为“现代化史学”取代“革命史学”即意味着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范式转换”。此后,学界惯常用“范式转换”来描述人文学术研究在研究方法、话语表达乃至具体研究对象等层面上的嬗变。,进而催生出“文化生产场域”与“微观史学”相结合的中国现代文化史研究范式,此时的相关研究已经明显展现出了开始着重关注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中的细节问题。因为与前沿理论接轨快,取得成果多,并有着跨学科的影响力,这使得海外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研究渐成海外中国研究的中坚。当中以周佳荣的早期现代化出版业研究(2004年)、史通文的留声机在华技术转移研究(2006年)、安德烈·戴维(Andrew David Field)的上海舞厅研究(2008年)、榎本泰子(Enomoto,Yasuko)的上海工部局乐队研究(2009年)、叶凯蒂的晚清娱乐产业研究(2009年)、安德瑞·戈德曼(Andrea S. Goldman)的晚清北京舞台产业研究(2011年)、叶文心的上海时尚文化产业研究(2012年)、大桥毅彦(Ohashi Takehiko)的兰心大剧院研究(2015年)与饶韵华的唐人街戏剧产业研究(2017年)等等为代表,其成果之密集、丰硕,几乎彻底颠覆了20世纪以来形成的、以中国古典文化研究为重的海外中国文化研究格局(3)耶鲁大学东亚系孙康宜教授(2015年)曾对笔者表示:“在我撰写这篇文章(即《‘古典’与‘现代’——美国中国研究学者如何看中国文学》一文)十九年之后的今天,美国汉学界的倾向却完全反了过来: 那就是,现代文学已变得高高在上,而古典文学已不太受人重视了。”而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研究在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则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繁华的表象之下,仍有着一种深深的隐忧。那就是:时至今日,国内外学界既未提出“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这一概念,也无一部系统的“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问世,甚至连关于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的总体研究都未出现。两相对比,形成了“有实无名”的逻辑背离。
值得一提的是,进入21世纪以来的海外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研究成果不但在海外学界产生了影响力,而且在中国学术界影响力更大。随着中国学术界开始与海外学术界产生联系并频繁互动,国内从事现代文化史、文学史与社会史研究的学者对海外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研究持积极的响应态度。当中,傅才武的近代汉口戏剧市场研究、陈庚的北京民国戏剧市场研究、陶小军的清季民初的艺术品交易与文化市场的生成机制研究、葛涛的民国唱片业研究、李相银的抗战沦陷区期刊产业研究、李永东的民国租界文化生产消费研究与李斌的鸳鸯蝴蝶派与早期中国文化创意产业关系研究等等。均形成了较大的学术反响,甚至当中不乏国际水平的研究成果,将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近五年来,从唱片电影、印刷技术、摄影海报、期刊广告与时装舞厅等现代文化产业不同领域切入角度来研究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的硕博论文更是汗牛充栋。而一些青年学者所撰写的相关论文多达3000余篇。据不完全统计,这类选题的国内硕博论文大约有400余篇,遍及国内近百所高校与科研院所,当中不少研究已经意识到,自己所研究的对象属于中国现代文化市场、文化创意产业的重要组成,但还未能将相关问题置于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的宏大框架之下进行讨论或对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进行系统研究。
二、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研究的得失
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研究最早萌芽于海外学界,又在特殊的语境下被国内学界所重视,受到国内不少研究者的响应。我们应当警惕的是少数研究者逐渐放弃了自己应该坚守的研究立场,几乎完全按照海外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研究的范式重复工作。这导致了得失两方面的结果:一方面,因为海外相关研究多元多样,因此使得国内相关研究也异彩纷呈,共同促使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研究走向繁荣;另一方面,这也使得国内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学界同样忽略了海外学界也不关注的总体研究,致使至今仍无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的总体研究。
作为一门专门史的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研究,其根本意义是为了探索近代以来中国文化产业史的发展大势,分析当中决定或影响历史进程的因素,探索不同时期中国文化的生产、传播的特征,归纳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发展沿革的一般规律。如果将海外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研究照搬照抄到国内,则会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完全忽视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的总体性意义。对西方研究范式与理论的这种追随,从心态上实与当年海外中国研究界向“西方中心主义”理论的妥协有着惊人的相似。早在十年前,王德威对此就曾有着一针见血地评述:“海外学者多半追随西方当红论述,并迅速转嫁到中国领域。上焉者一秉‘拿来主义’策略,希望产生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颠覆效应,下焉者则是人云亦云,而且游走海内海外,一鱼两吃。究其极,理论干预成了理论买办,文化批判无非也就是文化拼盘。”[6]
谈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的得失,则无法回避一个问题:为何海外缺乏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的总体研究?就此而言,甚至连一些海外学者也找不到准确的答案。譬如张英进曾表示:“大家都知道中国现代文学史(4)张英进所言“中国现代文学史”,是按照海外中国现代文学(文化)史研究路径完成的文学史系统专著,因为在此之前的2001年,梅维恒(Victor H. Mair)主编的《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The Columbi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已经问世并在美国高校广泛流行,当中有不少篇幅与中国现代文学有关,张英进不会看不到这部文学史,但因为这仍是一部导读式的文学史而非张英进所谓之“现代文学史”,即关于文学生产、消费等文化产业问题研究的现代文学史著。是一个空白, 但为什么没有出现呢?这是我至今不能理解的。”然后张英进将此归咎于海外特殊的学术环境,因为写作者撰写这样的书是不符合海外学术环境与要求的[7]。这当然是一个原因,但笔者认为,除了这个原因之外仍有其他的主客观原因存在。当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与海外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研究的师承关系、沿革赓续等问题有关。
前文已经提到,目前海外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的研究,是为海外中国现代文化研究的第三个时期,也是美国中国研究与欧洲汉学研究共同发展到一定程度的结果。海外关于中国问题的研究最早是关于古代中国历史的研究,即伯希和(Paul Pelliot)、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与李希霍芬(Richthofen,Ferdinand von)等人的敦煌经卷、中国古代历史地理学与中西交通史研究,他们都是欧洲人,这也是海外中国问题研究首先出现于欧洲的缘故,故而中国研究被当时的欧洲人称之为汉学。美国的古代中国历史研究几乎与欧洲同步,美国东方学会(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与其会刊东方学报均于1840年代问世;1870年代,哈佛大学与耶鲁大学设立了中国研究的教职。受制于当时欧洲汉学的影响,当时美国学界研究中国问题,也多半只关注中国古代历史。及至20世纪之初,哈佛大学虽然成立了燕京学社,但却只资助文学和人道传统的研究,亚洲近代政治、制度、经济史和社会生活的研究并不受到重视[8]。
“冷战”前夜的1946年,哈佛大学开展了区域研究的项目,耶鲁大学、康奈尔大学等高校随之跟进。两年之后,费正清的《美国与中国》出版,提出“冲击—反应”学说,认为现代中国的出现是西方国家冲击之后形成反应的结果。此外,费正清还提出应当以跨学科的视角与历史研究的方法来进行中国研究。这是海外学界正式研究中国现代史的起始[9],也被学界公认为是海外“中国研究”诞生的标志。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刚刚在美国快速发展的中国研究受到了麦卡锡主义的迫害与异化。但费氏提出来的跨学科与历史研究相结合的范式以及“冲击—反应”学说,却被他的学生芮玛丽(Mary Clabaugh Wright)、史华慈(Benjamin I. Schwartz)所继承发扬,并且从美国影响到整个海外中国研究界,深刻地决定了海外中国现代史研究方向。因此,当时海外中国现代史研究,主要集中在探讨中国如何在全球化时代下回应西方国家“冲击”。这当然是一种西方中心主义的研究范式,它一旦与跨学科、历史研究相结合,很容易生成目前海外中国现代文化史研究:即重视文化的生产、传播与消费机制及其与政治、经济的复杂关系(5)张英进认为,这类研究是基于“解构”的立场,“解构”是西方学界非常时兴一个研究趋势,海外中国现代文化史研究难免受其干扰(见注9)。但实际上,海外仍有一些学者重视从理论与文本入手来阐释中国现代文学问题,当中两位代表人物是张隆溪与王德威。笔者认为,解构主义的盛行确实使得一批研究者忽略宏大叙事并热衷于将历史碎片化解读,但这并非是导致海外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研究的唯一原因。。这直接促进了海外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研究的生成。可见这并非学人自发的结果,而几乎完全由历史客观原因所造成。
欲谈海外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研究,则不得不提其母学科——中国现代文化史研究在海外的生存状态。我们知道,“中国现代文化史”在国内可以从“中国现当代文学”“科学技术史”“中国近现代史”等一、二级学科中生发出来,成为研究本国历史的学科分支或重要学科。但它在海外特别是美国却属于中国研究子分支“中国文化、文学与历史”(Chinese culture, literature and history)研究(6)这一划分标准笔者基于美国200所综合类大学的学科分类而总结,但在欧洲、日本等地的大学,“中国现代文化”归属则不尽相同,但总体而言,“中国现代文化”研究在海外的学科体系内长期只是一个三、四级学科分类,与“近代阿拉伯文化”、“新加坡制度研究”等边缘学科的地位基本等同。21世纪以来,中国经济迅速增长,受到世界瞩目,海外一部分大学开始借助孔子学院等机构设立中国研究中心,一些研究中国文化的学者开始陆续担任美国的东亚系或亚洲学系主任,譬如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亚洲学系自创系至今五任主任中曾有两任为海外中国研究学者(乐钢与Robin Visser),王德威曾担任哥伦比亚大学东亚语言文化系主任,而孙康宜则曾两度出任耶鲁大学东亚系主任,但大多数海外中国研究学者都只是担任“中国研究中心(或类似机构)”的负责人(如叶文心与柯雷[Maghiel van Crevel])、“孔子学院外方院长”(如梁镛)或语言学院下属汉语教研室的负责人兼“孔子学院外方院长”(如普西奇[Pusic, Radosav])。的孙分支。而中国研究又是作为区域学研究亚洲学(Asian Studies)的众多下属分支。因此,关于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的研究,多半散布于不同科系(如法学、经济学、历史学等)当中(7)美国除了哈佛大学、耶鲁大学等顶级高校之外的绝大多数大学,都没有“东亚系”这个科系,相对规模较大的大学,多半只设置一个“亚洲学系”,大多数系主任由日本、印度或阿拉伯研究学者担任, 系下设“中国研究”方向(或博士课程之下的课程项目)只有一两位教师,往往只有一位教师从事“中国文化”研究。至于一些规模中等的学校,从事中国研究的老师则多半分散在经济学、法学、文学等其他科系之中。,形成碎片化的研究状况,亦不为奇。
因此,认为广义上的“中国研究”不但包括海外学界对中国问题的研究思路、话语体系与理论架构,也包括了海外中国研究的发展脉络、学术环境。各种因素共同决定了海外中国研究范式。如果只是在海外相关研究的影响下进行研究,势必会降低国内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研究在理论上的原创能力。这也是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总体研究迟迟未能出现的重要原因,甚至使得国内相关研究不自觉地形成了“仿汉学”研究[10]。这是尤其值得反思的事情。
三、另一种得失:海外相关研究的影响及利弊
辩证地看,海外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研究对于国内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研究的影响,有弊有利。利在于,海外相关研究确实对国内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研究有着推动性的启发作用;弊在于,这使得国内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研究趋于碎片化与缺乏总体化。
首先,如果没有海外相关研究的影响,国内不可能如此迅速地形成日益繁荣的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研究。尽管目前尚无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的总体研究,但这种繁荣显然对推动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总体研究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基础性意义。如对《良友》画报、民营书局、孤岛电影、粤剧演出等各种对象的研究,以及与之相关的现代出版史、现代音乐产业史、广告史、近现代文化经济政策史、现代文化科技融合史、艺术交易史与舞台产业史等不同领域的探索,构成了今后开展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总体研究的基础。无论国内外,其基础研究业已成形,相关研究的起步性成果也颇为丰厚,它们已经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总体研究下属不同的重要领域。但是由于目前海外中国研究界并没有为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进行总体研究的意图,同时国内学界也忽视了对于这种意图的追求。这证明了: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的总体研究是一项本土化的著史工作,不可能诉求、期待海外学者来完成,而是国内学者责无旁贷的历史责任(8)部分中国门类史研究在海外的总体研究,确实在时间上早于国内。当中代表是日本学者青木正儿(Aoki,Masaji)的《中国戏剧史》于1938年由上海世界书局出版,这是第一部中国戏剧通史,但是这是由当时中国积贫积弱的国际地位与社会环境所决定的。嗣后海外学界一直有关于中国通史、门类史(特别是文学史)的总体研究,譬如《剑桥中国史》《哈佛中国史》《剑桥中国文学史》《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与《哈佛中国文学史》,等等。但必须正视:这些史论的撰写,其立场、目的是向西方介绍中国,我们显然不能等待等、靠、要这种机会来完成对于自己民族文化历史的研究。。
从国际学术研究的总体格局来说,国内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研究事实上已经成为了中国现代文化史研究的重要组成,甚至在数量上已经大大超越了海外研究成果。之于国内研究而言,海外中国研究的影响促进了批量新成果的问世,培育了新的研究热点,激发了青年学者们的研究热情。而且从文化产业角度来研究中国现代文化史,确实打破了之前中国现代文化、文学研究的局限性,在视角、研究观念上为国内相关研究打开了思路。长期的成见被修正、以往的误解被澄清,未被很好研究的领域重新获得了关注。以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为例,海外学界多半倾向于对现代文学市场、作品传播、版本流变进行研究、对国内现当代文学研究视野的拓展确实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并对于之前国内的文学研究确有一定借鉴之功[10]。
其次,趋于碎片化与缺乏总体化这两个弊端,乃是针对国内而非海外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研究而言,因为海外中国研究界包括不同国家、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当他们在面对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这个研究对象时,会依据自己的个人经验与具体情况进行研究。但这种研究范式一旦被移植进入国内,将直接造成了研究的碎片化,关注对象自然会集中在微观之处,难以形成对总体历史的观照,从而形成了微观史学与宏观史学的分裂,这是不正常的。特别是中国历史研究应当秉持唯物史观,以“小处着手,大处着眼”的态度,既注重微观的个案问题,更应重宏观的总体研究,两者不可偏废。就中国历史的研究者而言,纵使专搞微观史学,对宏观史学也得略知一二[11]。
“趋于碎片化”与“缺乏总体化”相辅相成,“缺乏”并非是基于对总体研究的反感,而是因为在对海外中国研究的误读之下,对总体研究重要性的认识不足。这在本质上实际上是“西方中心主义”与“后殖民主义”在当下学术研究领域中的表现,它所反映的是国内学界对海外中国研究的推崇与屈从。但凡海外中国研究界没有研究的,一些国内学者则认为“不够主流”或“不够国际化”而被弃之如敝屣,但凡海外中国研究界重点研究的对象,则多半被追捧为学术热点。
这里有一个值得追问的问题:为什么有的选题海外中国研究界没有关注或是关注不够?这是否意味着需要更多的本土经验才能完成?就目前的状况而言,国内文化产业理论研究几乎完全借鉴西方理论框架,而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研究有“东施效颦”之嫌。因此,文化产业研究的“中国学派”必须崛起,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的总体研究需要本土理论指导与本土学者的参与,本土经验必将在今后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研究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
四、回归本土化与唯物史观: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研究的前景
基于前文所述,本节拟对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研究的前景做一个展望,要解决目前国内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研究所出现的问题,建构一套适合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研究的主体范式是当务之急。目前既要求国内学者们既要有从“碎片化”走向“总体化”研究的自觉,又要选择一种适应于今后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研究的主体范式,从而开拓出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研究的新局面。
首先,今后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研究,势必以国内学界为主体,以国内研究为主潮,形成本土化的研究,从而产生从国内至海外的学术影响。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研究,归根结底是历史研究,历史研究水准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文物、史料(包括文献、档案)的获取与解读情况。而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由发生在中国的历史事件所组成。尽管1949年之后因为政权更迭导致一批文献流落在世界各地,但与之有着直接关系的文物、文献大部分都在中国境内,即使在华外侨(包括早期中国海关)所遗留的部分档案、日记,相当部分仍在国内。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研究不但需要借鉴方法、视角与学术思路,更依赖于本土史料、文献的挖掘与使用。
纵观国际学界,从来没有由其他国家主导一国历史研究之先例,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史的研究重镇公认为牛津、剑桥而非北大、耶鲁。日本幕府制度史的研究显然以九州大学、筑波大学为圭臬正宗而不可能是哈佛、清华。毫无疑问,作为国内的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学者,我们理应致力于如何提升国内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研究的国际学术地位,进而形成领先性的研究水平。20世纪的中国研究,是以西方的、欧洲的、美国的观念为中心而21世纪的中国研究,应该返回东方、返回亚洲、返回中国[12]。
近代以来的中国史学研究,研究的主体范式经历了多次变化。总体来说,首先是由封建史学向资产阶级史学的转变,紧接而来的是第二次转变,即从资产阶级史学向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飞跃[13]。20世纪以来,以唯物史观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不但推动了中国史学研究的现代化转化与本土化发展,而且还孕育了以《中国经济史》(何炼成)、《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田仲济、孙昌熙)、《中国史学史》(白寿彝)、《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游修龄)与《中国新闻事业通史》(方汉奇)为代表的专门史研究成果。但是发端于海外中国研究的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研究,一开始就缺乏唯物史观作为研究主体范式的指导,从而致使研究主体范式的缺乏,因此至今仍无上述具有宏观视野的总体研究成果问世。毕竟任何研究范式都是借助不同理论的学理性阐释。因此,对主体范式的选择依赖于其理论的阐释效能。之所以某种研究范式得以上升为主体范式,它在阐释度这个层面上一定是具有理性与公度性的,并且是对之前各种研究范式的建构、超越、反思、批判与继承[14]。就此问题而言,唯物史观具备对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研究的公共阐释。
其次,在建构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研究的主体范式时,必须要深刻理解唯物史观的内涵,将唯物史观与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的特性相结合,吸收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发展经验,真正地推进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研究发展,而不是将其照搬照抄,甚至庸俗化、教条化。
唯物史观亦称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有机组成,与唯物辩证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等马克思主义其他理论有着密切的相关性与一体性,是对人类历史的发生、发展、动力、道路演变的认识、研究与总结以及历史研究本身的宗旨、目的和方法。早在19世纪,马克思、恩格斯就立足世界,从不同国家的历史出发,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变革作为入手点,认识到历史起源于人类的活动与分工,证明了历史发展的内在动力是人的需要,这是唯物史观的源头。
在马克思、恩格斯之后,经历了数百年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建设者们还包括拉法格(Paul Lafargue)、考茨基(Karl Kautsky)、普列汉诺夫(Plekhanov, Georgii Valentlnovich)、E.P.汤普森(E.P.Thompson)、葛兰西、福柯(Michel Foucault)、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与格雷戈里·基利(Gregory S.Kealey)等各个时期欧美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们,他们都对唯物史观的丰富与发展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而且,李大钊、郭沫若、侯外庐、陈旭麓、章开沅等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也为唯物史观的中国化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因此,唯物史观并非恒定、不变,而是与时俱进、不断发展并始终处于中国化进程当中的。
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在内涵上是一部由文化史、经济史、世界史、交通史、移民史与城市史等不同门类史互相交杂的、并具备鲜明外史特征的门类史,必须要在研究上有一个主体范式。唯物史观在相当程度上可以作为研究主体范式的指导思想,并能有效地提升目前国内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研究的水平与质量。近年来对于“学术研究国际化”的过度推崇,使得不少国内学者忽视了唯物史观的重要价值,反而对海外学界尚处于实验期的前沿、新奇的理论热情有加,这是制约包括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研究在内所有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桎梏。关注前沿、新奇理论当然自有其必要性,但没有经历过时间淬炼的新理论究竟是否具有阐释性?这还需要历史与实践来予以检验。
当然,矫枉不可过正,笔者在此呼吁及时树立起以唯物史观为理论工具的研究主体范式,是基于对国内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研究现状而言,利用这一范式的主体仍是国内学者。但与此同时,我们当然不能忽视海外中国研究者们必须面对的生存境遇、薪火相传的师承关系与经年累月的研究习惯,因而不能苛求他们也必须要以唯物史观为纲,更不能将是否坚持唯物史观作为衡量海外中国研究学者们(甚至故去多年的学者)研究成果水平高下的标准,否则便是强人所难、不讲道理了。
从目前国内历史研究发展状况来看,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虽是诸多门类史中的新分支,但它与传统学科如中国现代文化史、经济史等有着密切的联系性,共同构成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们始终关注于中国现代化进程,在对中国现代文化的传承发展、近现代社会意识形态的新陈代谢、“西学东渐”与洋务运动史、半殖民半封建时期的社会观念史、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等问题的研究中均取得了重要的成果,可以说已经到达了一个相当成熟的水平,这为今后开展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总体研究奠定了优质基础。
综上所述,本文通过研究与论证证明了:目前中国文化产业史研究虽然成果丰硕,但受制于海外中国研究的影响,使得研究呈现出碎片化的特征,总体研究仍未出现,归根结底是研究主体范式的缺失。以唯物史观为理论工具,可以形成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研究的主体范式,从而促进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总体研究的形成。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研究的国际学术格局必然会获得彻底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