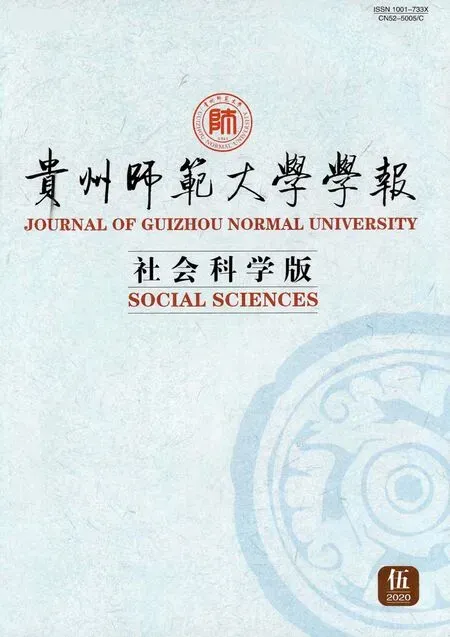不孕妇女的生活困境与秩序重建
——辅助生殖治疗对女性影响的社会学分析
2020-03-16邱幼云
邱幼云
(杭州师范大学 钱江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8)
一、问题的提出
众所周知,在世界范围内越来越多的人遭遇到生育困难,不孕症的发病率呈逐年增长趋势[1]。据统计,全球有15%的女性一生中有过不孕经历[2]。一旦被诊断为不孕,多数人会借助医学介入以期实现受孕生子,辅助生殖正是这样一项给不孕不育患者带来希望的医学技术。自从1988年我国内地首例试管婴儿诞生以来,辅助生殖技术迅速发展,其应用也越来越广泛,帮助很多不孕家庭圆了拥有孩子的梦。
在辅助生殖治疗中,无论导致不孕不育的原因在于男方还是女方,通常只有女性被认为是“病人”,她们更容易暴露在治疗可能带来的伤害和风险里。虽然生育是两个人的事,但男性往往是缺席的。侵入性的治疗、高昂的费用、漫长的治疗过程以及技术的不确定性等,都会给女性患者带来巨大压力[3],产生沮丧焦虑、失望、睡眠障碍等一系列消极反应[4],生活质量严重受损[5-6],甚至出现自暴自弃的想法[7]。在这样的身体痛楚与心理焦灼中,不孕妇女反复不断地被拉扯着。可以预见的是,随着不孕人群数量的不断增多,辅助生殖治疗不仅已成为威胁到个体正常生活的私人事件,更是亟需关注的公共问题。
现有的文献中,关于辅助生殖治疗的绝大多数研究集中在医学领域内,偏重于病理和治疗技术分析,也有一些医学工作者注意到了技术背后的心理和社会因素,转而关注女性患者的心理状态、社会支持、生活质量、社会伦理等问题。不过,辅助生殖治疗中的女性关怀和社会性因素,总体上还是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女性在治疗中的感受很大程度上被忽略。近几年来,一些社会学和人类学学者关注到了这一群体,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学者有赖立里、余成普等。他们都采用人类学田野观察的方法,主要聚焦于女性的具象体验,从身体、心理、情感等方面予以了较为细致的考察研究[8-9],所有这些都为本文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但总体而言,在社会学视角下分析不孕妇女辅助生殖治疗经历的研究仍很少见,尚待进一步拓展。
基于此,本文拟从社会学的视角出发,重点探讨以下几个问题:作为污名应对方式的辅助生殖治疗对不孕妇女产生何种影响,哪些力量在其中发挥作用?面对身体、心理和人生秩序失序的困境,她们采取何种应对策略?为了回答上述问题,本文将采用行动者导向的视角,注重不孕妇女自身的能动性,在调查中特别留意她们的感受,通过深入不孕妇女的日常生活世界,探讨不孕症患者日常生活世界如何被辅助治疗所扰乱以及她们给这段经历赋予什么意义、又如何重建秩序,分析的中心是不孕妇女的感知、动机和经历。
二、研究方法
借助辅助生殖技术求子是一条曲折、漫长而痛苦的治疗之路。行走在这条路上的都是“有故事的女人”,但这些故事里有很多悲伤,隐含着难以向他人言说的痛。故事里的女人感到羞耻和自卑,多数人不愿向他人公开谈论不孕。质性研究能有效打破沉默,给人以表达观点、诉说经历的机会,通过倾听被访者的声音能更好地理解其日常生活世界和意义世界,也由此体现得更加“人性化”。因此,笔者采用田野调查、深度访谈等质性研究方法来搜集和分析资料。
田野调查地点是上海J院辅助生殖科。J院的辅助生殖科成立于2003年,因其治疗成功率高、费用相对低等特征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患者。笔者利用自己曾是该院病人的“局内人”身份,顺利地找到了3名熟悉的“病友”,并通过滚雪球的方式,总共访谈了26名在此进行辅助生殖治疗的女性患者。对多数受访者来说,这次访谈是她们第一次面对“外人”分享不孕的治疗经历。访谈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帮助宣泄情绪和减轻秘密负担的作用。或许正因为如此,信任关系建立后,多数受访者敞开心扉尽情倾诉,她们的真诚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本文访谈资料涉及的4个个案都是因自身原因而导致的不孕,她们的信息如下。
个案1,娟子,30岁,来自浙江衢州。曾经是一名护士,因为不孕治疗辞去工作,目前是在家兼职做副业,无固定收入。三次促排取卵,两次移植。
个案2,阿华,34岁,来自浙江杭州,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中医调理三年,试管三年,四次促排取卵,五次移植。
个案3,小英,33岁,来自云南昭通,家庭旅馆老板。因多种原因,做过宫腔镜、腹腔镜等,三次促排取卵,三次移植,两次胎停流产。
个案4,妮诺,34岁,来自浙江杭州,自由职业者。三次促排取卵,七次移植。
三、辅助生殖治疗中的困境分析
(一)身体上的疼痛与失序
人们对自己和世界的了解始于身体[10],而身体在人患病的时候更易凸显出“在场性”。一旦进入治疗场域,无论在医院还是在日常生活中,施行辅助生殖治疗的女性便开始体验多种身体感受。在受访者对身体感受的描述中,疼痛是出现次数最多的一个词。
身体疼痛和不适的感受在辅助生殖治疗过程中非常普遍。频繁的注射、药物带来的副作用以及侵入性的检查和治疗,可能会导致卵巢压痛、腹部肿胀、淤青红肿等各种不舒服。妮诺回忆起自己第一次做试管的经历,“从降调到促排取卵,大概连续一个月每天都打针,屁股和肚皮都淤青了,每天肚子都是胀痛的感觉。移植前后还要打很多针,最难受的是打黄体酮,因为它是油性的,不好吸收,现在我屁股上应该有100多个针孔了,又硬又肿,要好几个月才能消下去”(个案4,妮诺)。因为J院的取卵不打麻药,医生从女性那里收集成熟的卵子(即取卵)被多数人认为是最痛的经历。“我躺在床上,感觉自己就是一只待宰的羔羊。因为卵泡位置不好,差点疼昏过去,只能用生不如死来形容,医生习以为常了,还喊我不要出声。下手术台腿都是打颤的,没有供休息的病床,就在椅子上斜躺了半小时”(个案4,妮诺)。
还有被访者谈到了因治疗产生的副作用。不孕症治疗的生理副作用是最具挑战性的身体压力之一[11]。治疗通常需要使用影响内分泌的药物,由此引发抑郁、恶心、疲劳、头痛、体重增加、易怒以及潮热烦躁反应。“打贝依降调的时候,浑身不舒服,疲倦、燥热、心慌、胸闷,晚上失眠,两小时就要醒一次……总之就是各种难受”(个案3,小英)。在医院遭遇的各种侵入性检查也让人很尴尬。回忆起做宫腔镜的场景,阿华的眼圈红了,“宫腔镜手术是男医生,这是上海有名的专家,有点尴尬,但可以接受。最难忘的是痛,虽然半麻,但痛不欲生,手术好后浑身瑟瑟发抖,找旁边一个护工阿姨借了一条床单包起来。闭上眼睛,眼泪就哗啦啦流下来了。这时顾不上旁边有没有人,是不是难为情了,脑海里只有一个字——‘痛’”(个案2,阿华)。小英谈及自己接受B超检查的感受是尴尬,“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脱换衣服,旁边是其他等候的女病人,最关键的是医生是男的,一开始我非常不适应。久而久之似乎习惯了,做生殖科的病人,就不能再考虑个人隐私了”(个案3,小英)。在这里,女性私密的肉体被袒露,侵入性的检查让她们产生了屈辱的感觉。
与女性需要接受吃药、打针、取卵、植入等复杂治疗及其导致的痛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多数男性只需手淫取精即可,两者的痛苦程度差异非常大。此外,受访者还提到了辅助生殖治疗对夫妻性行为的负面影响。不孕夫妇通常需要根据女性的生理周期严格安排性生活时间。当性成为一种工具而不是一种享受过程时,受访者认为它沦为了一种麻烦和负担,索然无味,令人感到沮丧。“成功怀孕的病友都说移植前几天性生活能提高成功率,不管我是否想要,也不管我的丈夫是否累了,今晚我们必须这么做,这让我感觉是一个负担”(个案3,小英)。在这里,性关系的重点是怀孕,而不是爱意的表达,性生活被剥夺了享受和性价值,成了用来实现生育目标的工具。
对不孕妇女来说,身体的“痛楚”令她们饱受煎熬,但这在医生那里似乎因司空见惯而不值一提。J院生殖科患者众多,甚至一度不得不采取限号,因人多导致就诊环境更加恶劣,在患者眼里“永远都是人山人海,连垃圾桶旁都没地方站,生殖科就是流水线工程,患者极少有机会与主治医生直接对话。只有在做B超时才能见到主治医师,如果人很多则会被分给别的医生,你想再找主治医师咨询点什么就不可能了,去了基本就像盲婚哑嫁一样”(个案2,阿华)。“取卵前要注意什么”“什么东西能吃、什么不能吃”“移植后要不要卧床”等此类疑问,很难得到详细的回复,尤其是治疗中生活上的注意事项,更多地只能从网络上搜索或依靠其他试管姐妹口口相传。
由此可见,在医疗领域内,一方面,医生代表权威,主导着整个医疗过程[12],由于专业知识差距导致的权力结构分化,患者在医生面前几乎没有话语权;另一方面,病人规模庞大而无组织,面对医生少、病人多的事实,医生每天需要面对大量的病人,一直处在紧张忙碌中,根本没有时间说什么。病人的感受和疑问经常被忽略,即使内心充满疑惑甚至不满,也只能顺从。
(二)心理上的煎熬与失衡
与身体之痛相对应的是心理上的煎熬与失衡。被访者一致认为身体上的痛尚可以承受,最难熬的是心理上的煎熬和精神痛苦——无奈、慌乱、悲伤、失望、失败感、失控、绝望等。对孩子的渴望使不孕家庭寻求各种各样的办法,一般先从运动和饮食调理、求神拜佛等做起,尝试不成再找中医,艾灸、中药、针灸等,这些尝试都无效才转求西医,输卵管造影、宫腹腔镜等检查或介入都没怀孕,抱着最后的希望才选择了“试管婴儿”辅助生殖治疗。可见,辅助生殖治疗技术是患者最后一线希望所在[13]。
但治疗的结果是不确定的,成功或失败都有可能。成败与否所引发的焦虑水平高达40%[14]。治疗中任何一个步骤的失败都可能会导致治疗停止,影响下一步进展,甚至需要从头开始一个新的治疗周期。阿华将辅助生殖治疗过程描述为爬山,一步一步往上爬,每一步都是痛苦的,一不小心就会从山上跌落,前进的过程伴随着恐惧,感觉自己面临着一个即将到来的死刑判决。“之前觉得走到试管这一步,应该会很快成功的,无非就是多花点钱,没想到两次取卵都没有得到冻胚,难过得想死,感觉人生没有了希望,整个都是昏暗的”(个案1,娟子)。娟子才30岁,因为卵巢功能几近衰竭,在生育上却几乎被判了“死刑”。她陷入一种深深的哀伤中,郁郁寡欢,“吃不下饭,睡不好觉,心情极其低落”。关于辅助生殖治疗后情绪调整的研究发现,治疗失败会明显导致抑郁水平升高[15],产生悲伤、焦虑和沮丧,许多女性表现出临床抑郁症的症状,包括失眠、疲劳、饮食模式的改变导致体重减轻或增加,以及感到无助和绝望。这也意味着实现人生目标再次落空,导致失去控制的感觉,同时伴随着沉重的失落感和丧失感[16]。
相比于初次周期的治疗者,多次治疗失败的女性患者表现出更高的焦虑和抑郁水平,失败的经历和不断增长的年龄让她们感觉生育希望越来越小。也有被访者产生委屈不公的感觉:“憎恨命运的不公,从小到大洁身自好,很喜欢小孩却求而不得。为什么这样的事儿,会发生在我身上呢?!”(个案1,娟子)。此外,受访女性还谈到了她们巨大的年龄焦虑。年龄是影响女性怀孕的重要因素,年龄越大生育越困难是医学上公认的事实。无论自然怀孕还是通过辅助生殖技术,女性35岁之后受孕几率会急剧下降。“七次移植了,每次都充满希望,但老天还是没有眷顾我。一年又一年的过得好快,一想到马上就35岁了,就像热锅上的蚂蚁,焦灼不安。也许我这辈子不会有孩子了……”(个案4,妮诺)。
对于多数不孕妇女而言,曲折的治疗经历带给她们巨大的精神痛苦,不稳定的心理状况随着每一次的治疗结果如过山车般起起伏伏,等待结果的过程以及希望的破灭都如同把她们的灵魂放在火上烤。
(三)人生进程的破坏与断裂
人们生活在一个由家庭、社会关系网、精神信仰等组成的生活世界中。个人是多重身份的主体,接受辅助生殖治疗的女性,除了患者这一身份,还同时扮演着妻子、媳妇、女儿以及职员等多重角色,这些都有助于她们建立起对世界的归属感。然而,不孕妇女明显感受到治疗对其人生进程的巨大破坏。人生进程的破坏是迈克尔·伯里在研究慢性病时提出的一个核心概念,其主要含义为,慢性病是一个破坏性的事件,它破坏了日常生活的结构以及作为其基础的知识形式[17]。由于辅助生殖治疗具有与慢性病类似的破坏性,故笔者在本文引入这个概念来探讨辅助生殖治疗对不孕妇女人生进程的破坏。
不孕是一个“破坏性事件”,进行辅助生殖治疗会进一步影响女人的生命轨迹,使其原先既定的人生进程发生改变——活动空间和时间受到限制、家庭计划和职业发展规划受到冲击。首先,施行辅助生殖治疗的女性,面临着巨大的时间挑战。治疗所需要的多种治疗程序,前期检查、促排、监测卵泡、取卵、移植等一系列操作,都需要女性多次到医院就诊。这必然会与工作时间发生冲突,不仅影响正常的晋升路径,甚至可能夺走她们的工作机会。毫无疑问,辅助生殖治疗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这使接受治疗的女性无法全心投入工作,对其正常工作产生较大的干扰,对职业发展和工作稳定性有诸多负面效果。
大部分不孕患者的年龄在25-40岁之间,这是个人职业生涯中极其重要的阶段,亦是事业上升的关键时期。而受访者阿华因为做试管放弃了外出进修的机会,“在走上试管之路时,就意味着事业上的牺牲和放弃”(个案2,阿华)。娟子这样描述她在工作上的牺牲:“这几年来,医院几乎成了我的家。以前我在医院做血透护士,收入很不错,但经不住经常请假来做试管,最后还是放弃了(工作),就为了一心一意做试管。没了工作,当然没钱,跟以前不能比,现在就做做副业,能挣一点是一点”(个案1,娟子)。还有被访者则是在决定做试管的时候就辞职了。妮诺认为做试管需要经常请假,很容易耽误工作,这样对公司不负责,所以选择辞职专心做试管。
对于接受不孕治疗的女性来说,如果没有工作,多数人面临着经济窘境。因为辅助生殖治疗花费巨大,且未被纳入医疗保险,不孕患者需要自行承担几乎全部的医疗费用,这对普通家庭来说是一项巨大的经济支出。一个试管婴儿助孕疗程一般也要花上3~5万,只有少数“孕气”非常好的人能一次成功,多数人需要尝试几个周期才能成功怀孕,还有的反反复复治疗却一直没有成功,投入的费用就更多了。此外,对多数人而言,辅助生殖治疗是她们尝试怀孕的最后希望。在此之前,她们进行过多种花费不小的治疗或尝试,比如阿华之前在杭州治疗花了七万多元。到上海后“取卵、宫腔镜、带环,加上移植,花了四万多元;这次移植五千九百元,打蛋白五千多元,中药一千多元,还有妇婴医院做免疫治疗等等这次花了两万多元。这三年花了十几万元,我都有记账。一般家庭真的花不起。而且不知道哪一天是个头,就像个无底洞,一直往里面扔钱不知道要扔到什么时候”(个案2,阿华)。被访者最担心的也往往是经济压力,“做试管这几年,花钱真的就是如流水,不仅把以前的积蓄都搭进去了,还借了几万块钱,真怕到最后还是没有成功,竹篮打水一场空。因为治疗花费很高,这几年我没有给自己买过一件新衣服,尽量省钱来看病”(个案3,小英)。对娟子家而言,不孕治疗使他们陷入严重的经济困境,“我们家庭本来积蓄就不多,现在做试管的钱都是借来的,三促三移失败,卵子也没有了。重新开始,只能继续借钱,快要崩溃了,压力好大”(个案1,娟子)。因为花费巨大,一些人给自己定下一个次数期限,比如33岁的小英打算再给自己两年时间,继续治疗到35岁,如果还不成功就放弃了。可见,生育治疗上的巨大经济负担,使一些经济不宽裕的女性不得不被迫停止治疗,放弃做母亲的梦想。
作为从生理层面拥有孕育新生命特权的女性,不孕是一种典型的破坏人生进程的形式。认知难题、解释系统和资源动用是伯里用来研究慢性病对人生进程破坏方面的三个互相作用的部分。这些部分同样适用于不孕症患者。在接受辅助治疗之前,受访者已经经历过受孕路上或大或小的失败,而辅助治疗的开始,意味着她们将真正进入到一个漫长而复杂的治疗周期,重新审视认识个体的身体、心理与意识状况。治疗直接打破她们现有生活的规划与进展,这一点尤其体现在工作与晋升方面。认知的革新赋予她们新的生活课题与挑战,不孕症促使这些女性开始深思许多问题,对自我价值与身体机能的不自信,对下一阶段人生历程该如何前进的方向感到困惑,在此种过程中,往往会引发较大的情绪波动。受访者原有的解释系统变得紊乱,反思与怀疑成了主要的声音。伯里曾指出,慢性病通常会破坏病人的社会网络状况与资源动员的能力[17]。辅助治疗对于治疗主体以及整个接受家庭而言,都如同一场大型考验:接受治疗的患者可能会为了怀孕被迫脱离社会关系,放弃工作;家庭在面临昂贵的费用时,也需要动用人脉资源进行筹备,在以家庭为单位的环境下,夫妻关系可能会面临挑战与危机。
四、生活秩序的调适与重建
辅助生殖治疗使不孕妇女的“人生进程”遭到前所未有的破坏,生活世界的原貌不再。因此,许多文献在结构式批判旨趣下,专注于患者的结构劣势和被动处境,研究不孕带来的消极影响,比如焦虑、抑郁以及其他负性情绪等对患者造成更大的负性体验,而忽略了患者身上的正性品质与能量。事实上,创伤性事件除了给不孕患者带来消极影响外,正向的积极改变也在发生[18]。笔者发现,在病痛挫折面前,面对生活世界的乱序与失序,受访者并非一味消极面对,而是想方设法积极赋以其新的意义,并采取行动重塑新的生活秩序。
首先,苦难让她们获得了更多的人生智慧。疾病让不孕妇女调整期望,并采用新的视角进行解读。她们用朴实而自然的 人生哲学“随遇而安”让自己的心平静下来去接受现实。辅助生殖治疗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可能持续数月甚至数年。而且治疗成功与否还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因素。就此,长期坚持治疗的女性相应地调整了过去急于求成的心态,将治疗失败归因于“子女缘薄”“缘分未到”“天意”等不可控的外因。“怀孕是个巨大的神秘工程,我能做的就是把身体交给医生,把结果交给上帝,把心情交给自己……试管就感觉是要历经九九八十一难才能成功的……每当觉得自己撑不下去的时候,想想多年的努力,告诉自己不要放弃。自从去算命说子女薄缘,我释然了,尽人事、听天命”(个案1,娟子)。这种看似认命的心态带有宿命论的表征,但这非但不会让患者变得消极,反而让这些不孕症女性开始自我接纳,真正接受现实,以更加坚强的意志来面对繁杂曲折的漫长治疗,帮助她们在不确定和不可控的境遇中获得了一种难能可贵的超然和主观能动性。
其次,不孕妇女在治疗中试图重新建立起一种个人权力感,其中包括尽管有诸多痛苦体验但对未来一直抱有积极的希望。辅助生殖治疗是周期性的,在未宣判失败之前,都有可能成功受孕。即使一个周期失败了,下一个周期仍有成功的可能性。每一个新的周期代表一个新的希望,“失败”只是暂时的,怀孕的希望从未在患者心中破灭。她们坚信,只要坚持下去,终有一天会怀孕生子,成为母亲。怀着这种信念,她们虽有痛苦,但仍满怀希望。“我相信苦尽甘来,昂起头就能看到曙光,我相信终有一天宝宝会到我身边来的”(个案2,阿华)、“想想美好的未来,想想一家三口的幸福生活,值得……”(个案4,妮诺)、“无数次自己一个人躲在被窝里嚎啕大哭,但哭好了,擦干眼泪仍然继续,感觉自己就像一个战士一样在勇敢战斗!只要还有一线希望,我就不会轻言放弃”(个案1,娟子)。在她们的话语里,不孕是暂时的,“希望”是一种不可或缺的感觉。她们乐观地等待着每一个治疗周期,哪怕时而悲观,她们依然对怀孕的可能性心存向往。想到自己正朝着成为一个“准妈妈”的目标前行,便不可名状地拥有了一股应对生活苦痛的力量。
还有一个积极变化体现在夫妻关系的重建上。施行辅助生殖技术治疗是夫妻的共同决定,这个经历也是夫妻一起分担责任的经历。在此意义上,不孕不育可能成为夫妻凝聚力的一个因素[19]。辅助生殖治疗是很艰难的旅程,人在其中变得更加脆弱,更需要互相分享情感、给予支持,夫妻间可能产生一种共渡难关又牢靠的“伙伴关系”。“当医生告诉我几乎不可能自然怀孕时,我跟老公说离婚吧!没想到不善于表达的老公紧紧抱住我说‘不能怀孕我们就一辈子这样过两人世界吧’。感谢善良的老公,即使可能无法有孩子,他仍对我不离不弃。当我们决定做试管的时候,中间经历了种种痛苦,他没有怪罪于我。比起治疗的结果,他更关心我的身体疼痛和感受。这让我松了一口气,也让我更体贴他,更用心经营婚姻”(个案2,阿华)。在一起经历了各种艰难困苦之后,风雨同舟的感觉更加浓厚,夫妻关系经过调整和重塑后变得更加稳固和坚韧。当然,也可能是因为辅助生殖治疗对夫妻关系的考验较大,如果夫妻关系脆弱,可能在女性被诊断为不孕或辅助生殖治疗几次失败后感情就破裂了。因此,夫妻感情随着辅助生殖治疗的进展而更加稳定,也可能是一种选择效应,只有那些关系特别牢固的夫妻才能让他们能够忍受长期治疗带来的痛苦。
可预见、可持续的秩序感是人类生活意义建构的根基所在[20],然而,不孕以及辅助生殖治疗打破了既有的生活秩序。面对失序和乱序,受访者也纷纷表示她们会积极应对治疗对个人生活世界的破坏,处理各种不确定感,以恢复秩序感,重建生活秩序。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从辅助生殖治疗亲历者的角度考察女性的诊疗体验及其对生活秩序的影响。透过受访者的述说可以看到辅助生殖治疗对她们生理、心理和社会三个方面都产生了负面影响。在此历程中,不孕妇女深刻体会到了刻骨铭心的痛,她们在身体的痛楚、侵入性的检查、不平等的医患关系与心理煎熬中反复不断被拉扯着。治疗的艰难和结果的不确定让大多数人体会了无奈、慌乱、悲伤、失望、失败感、失去控制、绝望等心理上的煎熬与失衡。同时,治疗也干扰了她们的人生进程,让她们在时间、金钱、职业等方面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然而,女性并不总是臣服于社会的型构,她们也是积极能动的行动主体,想方设法对辅助生殖治疗经历赋予积极意义,并采取行动重塑人生轨迹来让生活回到“正轨”,重新建立起生活秩序。她们视不孕为暂时性的状态,并将进行辅助生殖治疗的这段时间视为生命中暂时性的时空历程。由此积极进行调整和适应,也因此满怀信心与希望,充满勇气和力量去度过这段艰难的治疗历程,期待通过治疗成功怀孕,再度建立起对生活秩序的主宰权。
生育是女性生命历程中独有的阶段,也是构成女性生命完整性和存在意义的重要时段。“十月怀胎,一朝分娩”昭示了母子间一段为期不短的具身关系时段。从现象学视角看,这种关系是一种反个人主义的、彼此交融的“我们关系”。这种关系带来的不仅仅是一个新的生命这么简单,而是为母亲创生了一个崭新的“周围世界”。然而在现代社会,女性的生育过程正遭到各种现代性因素的破坏。本文研究的辅助生殖技术对女性造成的整体后果便是其一。个人的苦痛与社会之间存在复杂关系,现代生活方式、被延长的教育时间、工作制度、医疗技术都不同程度地破坏着女性生育的生命历程——夜生活、工作压力时长及劳动强度、流产手术、错过最佳育龄等等,无不对女性身体和生育能力造成或隐或显的伤害。事实上,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生育,生育可以是一种选择,只有消解母职重要性的社会规范,才能真正缓解女性需要为生育承担的职责与焦虑。
此外,在治疗过程中,我们看到,女性是试管婴儿等辅助生殖技术的主要实施对象,男性在整个生殖系统和话语中基本缺席,而女性的身体则需要持续在场,时刻接受来自社会、家庭以及不同医疗系统的审视、监测与改造。我们也看到,辅助生殖技术建立在生物医学知识之上,这种知识将人体视为不完美的机器,可以由不断完善的科学技术加以更替。因此女性生育过程也被划分为若干环节,并依试管技术替代其中的授精和胚胎发育环节;在此过程中,女性身体被视为被技术按程序宰制的机械,身体成为医疗专家那里按机械规程进行检查治疗的生物机体,而留给女性的唯有痛苦、羞耻、恐慌、煎熬、绝望等等。这是一种替代自然生殖能力的辅助生殖技术,“不孕”的标签也是经由生物医学诊断而贴上的。事实上,在一个“医疗化”的社会中,这到底是自然事实还是社会建构的“污名”还有待辨析。在此意义上,本文的研究只是一个开端。针对社会上蕴积规模愈来愈大的不孕女性群体,有必要围绕生活世界与现代性诸要素间的紧张关系进一步关注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