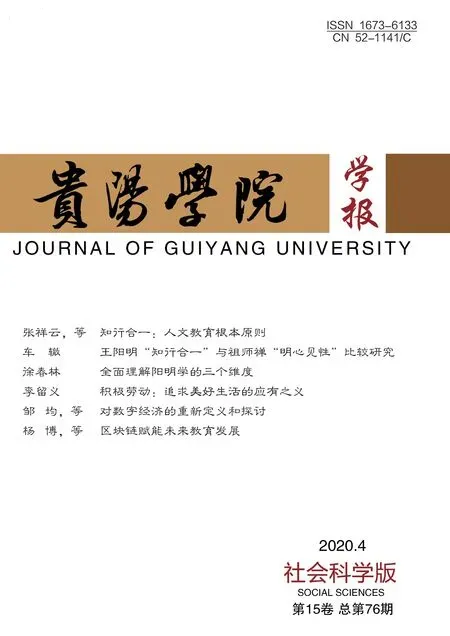牟宗三对熊十力内圣思想之超越
2020-03-15蔡家和
蔡家和
(东海大学 哲学系,台湾 台中 40704)
一、前言
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师从于熊十力,若以熊为第一代,则三位属第二代。此三位是熊十力学生中较为出色的学者,然三位相比,牟先生继承熊十力的思想最多。牟先生虽然在四十岁以前与熊常在一起,但主要自修的方向是西哲、逻辑方面(1)“有一次熊先生为我向梁先生要一个月三十块钱,熊先生和梁先生极相熟,三十块是小数目,熊先生是可向梁先生要的,他说:‘你一个月拿三十块出来,叫宗三到我这里住,让他读书。’梁先生说钱是可以拿,但有条件,第一是要读人生哲学,不能光看逻辑。这真是笑话,你怎可以干涉我读书呢?你看我表面是在念逻辑,便没有念人生哲学么?你以为我一天二十四小时都是念逻辑的么?”这表示在梁先生印象中,当时牟先生常以读逻辑为主。,与熊之专长于中哲是不同的[1]。但这些也成为他往后建构量论的材料,而补上熊十力的量论之不足。牟先生后来的发展,灵感来自于熊先生处亦多。
一九四九年之前,熊、牟二人尚有机会互相切磋,之后牟先生便来到港、台,熊先生则一直留在大陆,两人也就无缘再见上一面。牟先生后来虽然也读了熊先生晚年作品,如《原儒》(2)一九五四年作品,当时熊先生七十岁。,但牟先生自己的体系已越加成熟[2],而与熊渐有不同。
如牟先生依天台学圆教之建构运用在儒家身上。牟先生言:“圆教有待龙溪扬,一本同体是真圆,五峰明道不寻常。”[3]一方面,认为儒学②(3)②王财贵的论文观点近于牟先生,是以五峰、龙溪为儒家圆教。亦可如天台一样开出圆教[4],另一方面,也用圆教来解决“德福一致”的问题。“德福一致”是从康德学而来的问题意识,而这两点(圆教、德福一致)都是熊先生较少注意者。
牟先生又依康德美学来沟通两界,而有真善美之合一说与分别说,举康德来与儒家比配。此外,诸如自律、他律的问题意识,分析、综合之说法等,这些都非熊先生所关注。熊先生甚少谈到康德学,若有只字词组,也可能是一九四九年以前牟先生跟他提的。以下略列熊、牟之不同,计有十点。
二、熊、牟之不同
(一)归宗不同
1.熊:归宗经学
熊十力言:“遂欲专研中国哲学思想。汉学、宋学两途,余皆不契。求之六经,则当时弗能辨窜乱,屏传注,竟妄诋六经为拥护帝制之书,余乃趋向佛法一路。直从大乘有宗唯识论入手,未几舍有宗,深研大乘空宗,投契甚深。久之,又不敢以观空之学为归宿。”[5]7熊先生自述求学过程,早年契于二王——王船山与王阳明,之后又进入佛学有宗、空宗的领域。
晚年虽不全反阳明,但认为阳明等③(4)③“后儒宋明诸师,名宗孔,而实非其嫡嗣也。”这里提到熊先生宗孔,而不是宗宋明儒。宋明儒者[5]167,杂有佛老④(5)④熊先生对阳明的批评,大致有三:第一,阳明重体悟而轻知识,故该以朱子格物穷理之学,补阳明学的不足;第二,阳明学受有佛老影响,故有轻智、去欲之说;第三,阳明的良知不是本体,阳明良知只是本体发用的一端,只是心的一部分,而不包物。,故阳明有反知、少欲之说,于是改宗孔子。这也是熊先生《原儒》的转向,重新回到孔子⑤(6)⑤熊先生虽宗孔子,亦非全废阳明,其心目中的孔子仍是“心即理”式的孔子,故不废阳明,只是补阳明之不足。,甚至以六经为宗,并认为六经中的内圣学当以《易》为首,而外王学则以《春秋》为首,甚且,《易》的内圣学又比外王的《春秋》更为根本,亦可为外王铺路。孔子做《易传》⑥(7)⑥熊先生晚年《乾坤衍》一书有一特殊说法,认为《易经》乃是孔子所作,如此,便可与自己的体系配合。,自是易学的重要传人,《春秋》的地位,若依孟子,则是“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熊先生以孔子大易为本,以干、坤比配心、物而摄受百家。这里的百家,包括了西洋的唯心论、唯物论、心理学,甚至佛学的色法、心法,以及诸子百家等等。
2.牟:归宗阳明、五峰、蕺山而为子学⑦(8)⑦如孔子,既属经学,也属子学。
熊先生以易学的乾坤而来摄受心、物,而牟先生则较以自由无限智心为主,这说明熊、牟二人都是心学,但牟先生是以自由无限心来解决德福不一的问题。依牟先生,虽三教都可述及自由无限心,然佛、老是“纵贯横讲”,其以纵贯而言“道”,却于创生处有所不足,不及直贯的创生义,侧重于“不执”,所以又是横讲。故自由无限心之开出,当以儒家为首,尤以宋明儒三系中的心学一系与五峰(1105—1161年)、蕺山(1578—1645年)系为佳;特别是五峰蕺山一系,主张天道、性命相通为一,即心而即理,主、客观都饱满。
大致上,牟较依于子学,而熊则宗于经学。牟先生虽也尊崇孔、孟,却是“道德形上学”之下的孔、孟,其中,天道、性命相通为一,期勉人能践仁以知天!孔子的性与天道是不可得而言者,唯有透过实践,亦即践仁的同时,不可得言的天道方才得以默契心通。
(二)对于张载的评论不同
1.牟:张载属道德形上学
牟先生分判宋明理学有三系之说,分别是:五峰蕺山系、陆王心学,以及伊川(1033—1107年)与朱子“存有而不活动”的但理一系。至于周子(1017—1073年)、张子(1020—1077年)、明道(1032—1085年)等人,该属于何系呢?牟先生认为,应是不分系,若不得已归纳,则应属于五峰、蕺山的主、客满饱一系。如张子言“太虚即气”,牟先生谓,太虚是理,而即存有即活动,故下贯于心、下贯于气,气能全神是气、全气是神,这与“心即理”相通。因为太虚形上神体的贯注,气亦提升为神,而为超越的。
牟先生认为,张子言“虚”有二:一是超越的“虚”,另一是形下、虚实相对的“虚”;“神”亦有二:一是形上的太虚“神”体,另一是鬼神相对、形下的“神”。神者,伸也,是气的外伸。“清”字亦同于“神”与“虚”,亦有两种:一是形上的“清”,是一是形下、清浊相对的“清”。
2.熊:张载受有道家影响
熊先生大致认为,宋学受有佛、老影响,而张子则受有道家影响,“至云‘翕色辟心,袭《正蒙》余唾’,尤为狂谬,破者既未明征《正蒙》何义,横诬袭唾,此不成语,横渠精思固足多,然其虑封于有取、论堕于支离,与吾翕辟义元无合处”[6]。此出于《破破新唯识论》,熊先生反驳刘定权之语。刘氏写《破新唯识论》,认为熊先生的乾坤、辟翕之义,乃从张子《正蒙》抄袭而来。不过,熊先生认为自己的体系乃是体用不二,不至于支离,而张子《正蒙》则有支离。
熊先生言:“横渠曰:‘由太虚,有天之名。’又曰:‘太虚惟清,清故无碍,无碍故神。’又曰:‘成吾身者,天之神也。’云云。(以上均见《正蒙·太和篇》)按横渠之学,本于老子,而所窥于老子殊少。老子言神、言气(即阴阳二气)皆以太虚为本。横渠粗识于老子者只此耳。”[5]521-522熊先生认为,张子受有老子影响。如张子言太虚之“一故神,两故化”,这与老子的“谷(鬼)神不死”相似,谷神之不死,乃因其虚,故而日新而不死;而张子言气,老子亦言“冲气以为和”。然张子之学是否从老子而来,这涉及诠释,亦见仁见智。
熊、牟二人对张子的判断完全不同,牟先生推崇张子,视张子的“虚”为理,而“气”为形下,但形上可贯于形下,因为即心即理;而熊先生则对张子批评较多。(9)熊先生认为张子受有道家影响,亦是其来有自。如庄子之言:“予恶乎知恶死之非弱丧而不知归者邪!”《齐物论》,死是回老家,生是作客。而张子则言,由生到死乃是由客感客形回到无感无形,无感无形就是回老家。
(三)体用不二说与两层存有论之异大于同
1.熊:近似泛神论之体用不二说
熊十力言:“万物各有的生命,即是宇宙大生命。宇宙大生命,即是万物各有的生命。先儒有天地万物一体意思,正透此理。学者切勿作两层会去。”[5]193这也是熊先生的体用不二义,所以熊先生不断地以大海水与众海沤而来比喻体、用之说,离于海沤则无大海水。此喻应是出于佛经,如《唯识三十颂》言:“或俱或不俱,如波涛依水。”指的是人们五识与根本识的关系,正犹如波涛与海水。
熊先生强调:万物生命就是宇宙生命,不是离了万物而有宇宙!也许可用天台宗的“藏通别圆”与基督教义而来说明。在基督教,离了万物生命,还有上帝之生命,此属一神论,近似佛家之别教,其中有所区别,上帝为神而万物不神;至于熊先生此说较近于圆教,或是泛神论,也就是所谓的“即器(万物)言道”。这一点受有船山影响,在《周易内传》诠释“用九,群龙无首”时,船山言:
然期三百六旬之中,擅一日以为之始,则万物听命于此一日,德以有系而不富矣!且一日主之,余日畔之,一日勤之,余日逸之,其为旷德,可胜言哉!……然则一元之化,一代之治,一人之生,一善之集,一日之修,一念之起,相续相积,何有非自强之时,可曰“得其要而不劳,择其胜而咸利”乎?故论必定于盖椁,德必驯于至极,治必逮于絫仁。用九之吉,吉以此尔。[7]
这样的“群龙无首”,不以一神为本,而是万物皆神,不可刻以一日、一时、一念之悟为重而令万物听命。同样地,熊先生也不以一外在的大生命为首,而令万物听命,其“体用不二”说较为圆融,近于泛神论,重气化,理不可离气而独存。
2.牟:强调承体起用之两层存有论
牟先生的“两层存有论”虽与熊先生“体用不二,但可分”的说法有所相通,但牟先生的二元区分毕竟强烈一些。虽然牟先生推举天台宗圆教义理,但他重在“轨谲相即”义,如五峰的“天理人欲同体异用,同行异行”,或是龙溪的“佛即魔”“四无”圆融之说。
牟先生以五峰、龙溪为圆教,而真正主流如阳明、孔子则不是圆教,强调承体起用之两层存有论(执与无执的存有,中哲以无执存有为主,康德有执的存有),此中的证体之学,乃是由上而下贯(理贯于气)。这里的二元性较强。而所谓的承体起用②(10)②牟先生依于熊先生的《新唯识论》,因而主张哲学要能证体;以为世界当代哲学是无体之学,无体则无力,是一种虚无主义。,乃指以理御气——依牟先生的话③(11)③“这便是古人所说的‘以理生气’。坚定是诚守并明澈我们的理想与信念,开拓是扩充我们的理想与信念,以求生命之广大与感通。”则是“以理生气”[8],而非“即气言理”。这也近于明道的“以理胜之”④(12)④明道认为,治怒最难,须透过观理之是非而遽忘其怒,此亦是“以理胜之”。。明道言:“目畏尖物,此事不得放过,便与克下。室中率置尖物,须以理胜佗,尖必不刺人也,何畏之有!”[9]此中的“以理胜之”,正如牟先生的“以理御气”。
熊先生虽有“以心宰物”的意思,但熊、牟之间有着更多的差异。如牟先生的“道德形上学”,即是“天道、性命相通为一”的意思,此中,关于天道之超越,牟先生常形容以“超绝”,其言:
“天命”的观念表示在超越方面,冥冥之中有一标准在,这标准万古不灭、万古不变,使我们感到在它的制裁之下,在行为方面一点不应差忒或越轨。如果有“天命”的感觉,首先要有超越感(sense of transcendence),承认一超越之“存在”,然后可说。[10]
天道在万物之外,是为“超绝”,若如此,便与熊先生“万物生命即是宇宙大生命”说法不类。熊先生的说法更近于“天是万物之总名”的气化论,此为蕺山语,而郭象业已有言。总之,熊的“不二”义强,而牟的“二元”义强,然牟先生亦能说“不二”——却是“理气不离”、理气吸紧,还不到熊先生的“即气(器)言道”,理由在于,牟先生也想把基督教的特点、优点(超越而不流俗)收归至儒家。
(四)对于宋明儒学的判论不同
1.牟:受有佛老刺激而无掺杂
牟先生认为,宋明理学主要是固有的《易传》《四书》等思想的重新自觉,而非杂有佛老思想,牟先生言:
此种生命之相呼应,智慧之相承续,亦可谓“有本者若是”矣!此与佛老有何关哉?只因秦、汉后无人理解此等经典,遂淡忘之矣。至宋儒起,开始能相应而契悟之,人久昏重蔽,遂以为来自佛老矣。若谓因受佛教之刺激而豁醒可,若谓其所讲之内容乃阳儒阴释,或儒、释混杂,非先秦儒家经典所固有,则大诬枉。无人能因受佛教之刺激而豁醒即谓其是阳儒阴释或儒、释混杂。[11]40
牟先生认为,宋明儒乃因外在佛教之刺激,因而寻返老祖宗之经典,如藉《中庸》《易传》等而开辟形上学,既非杂佛,亦非阳儒阴释或儒、佛混。当然,这是牟先生的见解,熊先生则不然,至少与熊先生晚年见解不同。
2.熊:掺杂佛老思想
早年熊先生喜爱二王(阳明、船山),面对汉宋之争时,依循宋学而批评汉学,认为汉学只是工具之研究,还不到性命之学,只是研究经典的工具,并非目的。到了晚年,渐归宗于孔子、六经,汉学、宋学一概不取,其中的一个原因,便是认为宋明理学受有佛老影响,也因杂有佛老,所以有反知倾向,开不出科学。熊先生言:
宋明诸儒染于道与禅,其过同二氏也。(二氏,谓道、禅)……后儒(宋明诸师)名宗孔而实非其嫡嗣也。……世士疑理学之儒杂禅,不必本于道,实则濂溪、明道皆从柱下转手,而上托孔孟以开宗耳。(古史称老子为周柱下史。)[5]167
熊先生在此明确地肯定宋明理学杂有禅与老,并强调包括濂溪、明道皆由老子转手。如明道《定性书》尝言:“所谓定者,动亦定,静亦定,无将迎,无内外。……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万物而无心;圣人之常,以其情顺万物而无情。故君子之学,莫若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此说近于老子“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此外,“物来顺应”“无将迎”等说,则应是出自庄子,庄子在《应帝王》中言:“至人之用心若镜,不将不迎,应而不藏,故能胜物而不伤。”
至于周子《太极图说》,则采用了道家、道教的说法,如“无极”一词,出于庄子与老子。熊先生这样的说法近于象山、梭山。但牟先生关于《太极图说》论辩一事(13)“此为朱子解‘无极而太极’一语之正意,此解大体不误。象山之借题发挥,虽可谓为明道之文,然就辩《太极图说》之为真伪言,则失败。”,认为朱子是胜方[11]429。朱子的主张是“无极而太极”,无极用以形容太极,不是太极之上复有无极,无极是无形,太极是有理。
因此,熊、牟对于宋明理学的判别是有所不同的。
(五)看待欲求(形下)的态度不同
1.牟:依康德而贬视欲求
康德说:“一善的意志之为善,并不是因为它所作成的或所致生的而为善,亦不是由于它的适宜于达成某种拟议的目的而为善,而乃单是因着决意之故而为善,那就是说,它是其自身即是善的,而且以其自身而论,它是被估价为比它在偏爱任何性好中,不,甚至在偏爱一切性好之总集中所能做到的高过甚多。”[12]康德认为,善的意志高于世间所有性好之总合。
而牟先生则言:“私欲气质是感性的,其所牵连所决定的是现象。气之灵之心是现象,气变的物是现象。闻见之知是知此现象。德性之知则知物自身。”这也是因着康德的两层存有而发展出。然牟先生认为康德开展得不好,不能承体起用,且在现象处不能化掉,是一种“执的存有”,而东方哲学之儒、道、释则为一种“无执的存有”。暂且不对此说多作探讨,但看出因着康德对于性好、幸福的贬低,牟先生对形下之性好欲求亦不高看,例如牟先生贬低“生之谓性”之说。
2.熊:依船山而高看欲求
至于熊先生则受船山影响,对于欲望采取正面直视的态度,其言:
道家言去欲,而于欲无所简别,便一切去尽。佛氏抗拒造化,归诸无生,谓一切欲皆是惑,固无足怪也。……孔门论欲者今难详考。然孟子有言“可欲之谓善”(见《孟子·尽心篇》)。此必七十于后学相传之辞。孔子教学者以其可欲,则唯恐其欲之不强。如《易》干卦曰:“君子进德修业,欲及时也”云云。此欲如不强,其能成就德业德乎?《论语》,子曰:“人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云云。[5]199
如此言“欲”,则与康德或牟先生的贬低性好不同,与佛、老也不同。老子言:“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而佛家视欲为贪,乃是“三毒”之一;康德亦贬低性好,如《柏拉图全集》的《斐多》篇对于肉体欲求的贬抑。
熊先生则认为,若无欲求,也成就不了进德修业。熊先生的看法与船山相近,船山《读四书大全说》正是要剔除程朱学说中受有佛老影响的部分,所以不认同程朱“存天理去人欲”的说法,对于欲求持正面态度。
所以,牟先生与熊先生对于性好的看法不同,不过不是截然对反,而只是程度高低的不同而已;熊先生较正面看待,牟先生则不甚重视食色诸欲。
(六)对于西学摄受的程度不同
在熊先生的作品中其实早已谈到康德、黑格尔,不过都不是很深入,经常只是一两句带过。熊先生也尝以《易》的精神而来摄受西方唯心论、唯物论、心理学等,对于基督教的上帝信仰亦颇有同情,并且,亦曾论及西方的民主、科学,不过,大多未有深入挖掘。
而牟先生则亲自翻译“康德三批判”,以及《道德形上学之基础》《理性范围内的宗教》等,还有维根斯坦的《名理论》,也替教育部书写《理则学》一书。相较上,牟先生的西学功力深入许多。
(七)对于程子之判论不同
熊先生言:
宋儒程颢、程颐兄弟之“法言”曰:(理学家皆自信其言可为后世效法,故从彼而称以法言),“佛氏本心,(言佛氏以心为万物万事万理之本也。)吾儒本天。”(天者,天帝,程氏以为吾儒之学,则以天为万物万事万理之本也。程颐《易传》干卦篇,首发斯旨。朱熹载入《近思录》首篇,垂训后世。)余按本天之教,兴于上古,盛行于汉以来之小儒。孔子之《周易》,根本不容天帝存在。程氏泛称“吾儒本天”,似将孔子亦隐含于其言之中。自理学兴起,诸低能之徒诵法程、朱,诬圣侮圣而不自知,顾乃傲然不许非程朱。[5]514-515
熊先生这样的看法与牟先生不同。牟先生认为,宋儒正是道德形上学,而汉儒则是形上学的道德学,如董仲舒的阴阳气化论,而宋明儒则是透过心性体证而通于天。
又牟先生认为明道不同于伊川、朱子,朱子的天理、天道讲得不好,是存有而不活动,但与汉儒不尽相同。熊先生则谓“本天”说(14)熊先生的《乾坤衍》与一般对《周易》的认识不同,熊先生认为孔子撰写了《周易》,只是遗失了!其言:“昔者孔子托于伏羲氏而作周易。”这里不是谈孔子对《周易》作传,而是著作《周易》,与传统说法大异其趣。出于汉儒,非出于先秦儒,并谓孔子之《周易》不容天帝之说[5]333。《易传》中出现不少“天”字,“干”以“天”言,而熊先生反对天帝说,可能与其心物、乾坤说法有关,或是与其“即万物而言宇宙生命”的泛神论有关。
(八)对于王弼、郭象之判论不同
王弼、郭象有儒、道合流之倾向。牟先生认为,老子的精神是“作用的保存”,以“无”的精神保存了儒家的仁义礼智,这是采王弼说法而解释老子。老子本人是否为儒道合,则尚待讨论。
而熊先生便不如此认定,熊先生言:“老庄同深观群变,绝圣弃智之旨,辅嗣、子玄都无实悟,况其余乎!”[5]199意思是说,王弼与郭象对于群变、绝圣弃智之说并无实悟,不合于老庄要旨。不过牟先生却认为王弼合于老子。
(九)对于气论之判论不同
牟、熊皆反对唯物论,然熊先生之反对唯物,是认为既要唯心也要唯物,而不能独说唯物,要能心物并行、以心统物始可。而牟先生则因着反对唯物论,对于气论亦不喜欢,在“宋明三系”的判论中,也没有气论的位置。此外,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亦少有青睐。而熊先生虽不同意只有唯物,在论及船山时,则谓船山并非机械式的唯物,而是一种生机体的唯物,亦是对于气论的肯定。
熊先生对于西学较少关注,所以不从西学来作比配,而牟先生则谓气论近于西方的唯物论,将两者进行比配。再者,熊先生喜好船山学(虽不认为毫无缺点),无论内圣外王、天德王道等皆有研究;而牟先生对于船山学则只研究其外王学部分,在《历史哲学》一书用了不少船山《宋论》《读通鉴论》的说法,所以牟先生评价船山(15)“黑格尔与王船山相提并论,好像有点奇怪。实则他们两人很有相似处。这两位不同国度不同时代的大思想家,依照传统的标准说,都不算是好的哲学家,而却都是好的历史哲学家。”是个好的历史哲学家,却非好的哲学家[13]。而熊先生对船山则是颇有佳评。
(十)对《大学》的看法不同
牟先生认为《大学》是空壳子,看其填充内容为何,若以朱子的理学填充,则为格物以穷理,是存有不活动之学;若以阳明的良知说以诠释致知,则为心学。但都不见得是大学本意,大学的知,是知止、知本末先后,而朱子阳明的见解亦不见得准确。
至于熊十力则认为《大学》的格物义以朱子为准,致知义以阳明为准,一方面接受朱子的穷理的意思,以与西学的科学相接,而致知以致良知诠释,乃是以德性统摄科学,正是熊先生以中国之传统摄受当代欠缺的科学之做法,体用兼备,正德利用厚生兼备,熊先生不认为是空壳子,而是有其定准的诠释意思,合朱子与阳明两家之说。
综上所言,熊先生的体系是大易,以乾坤、心物而来摄受各家体系。牟先生则属道德形上学,“天道、性命相贯通”,且此天道乃“即存有即活动”而能下贯于心者。故熊、牟二人的不同,多在宋明儒的判别上有不同,其中,牟先生给予正面评价居多,而熊先生对宋明儒的评判则不高。然二人皆贬朱子,因皆宗心学之故。
三、结语与反思
牟宗三的哲学,有些常从熊而来,有继承处,亦有发展处。笔者认为大约各半,有一半是继承的,有一半是发展的。如熊以老子的“为学日益与为道日损”谈知识技术与德行,而牟宗三把它套用在伊川为前者,乃是以知识的方式讲道德,是别子为宗,是顺取的进路;明道为后者,是逆觉体证之学,是为儒者正宗。此判法的方式是同于熊先生的,但把它运用在二程身上,这是熊所未说的,因为熊先生认为二程是受道家影响,也未分别二程之不同。
牟先生与熊十力之为师徒,二人的体系,主要是依建构而成,是一种接着讲的形式。面对西学的冲击,必须响应与反省,熊先生大致是本土的,另一方面量论(知识论)最终亦未写出,但方向是以中国传统的德性为主,摄受西方的民主科学,而为一种体用不二之哲学,以乾坤辟翕比配心物,用以摄受西方的唯心唯物之说与佛学的心法色法之说。
至于牟先生之与熊先生亦有不同,他也是建构的,然他不从经学处建构,倒像是以子学来建构,以阳明心学为主,摄受天道,而为道德形上学,主客观饱满,近于他认定的五峰蕺山之说。在晚年,牟先生有圆教的看法,及真善美分别说,合一说的见解,常是以儒学与康德学的碰撞而来火花,如儒家不谈上帝,如何解决德福一致的问题。牟先生的学问不只是本土的,而是中西会通的。无论如何,二人都是为了中国哲学的未来所做的努力思考,为中国文化所少有的科学民主处作一思考,让文化的根里有科学的种子,而能生长茁壮,三统并建,有其道统的传统思想,及学统的开出,及政统的客观制度之说。牟对于熊有继承处,亦有不同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