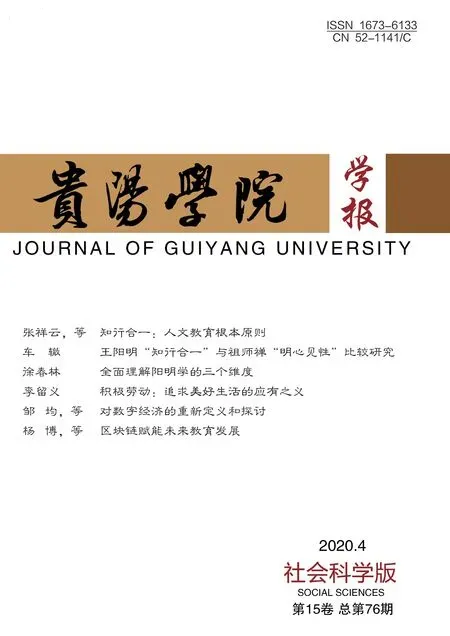李端棻与清季贵州的士风
2020-03-15余小龙
余小龙
(1.贵阳学院 教育科学学院, 贵州 贵阳 550005;2.四川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4)
作为著名维新大员与推进西学的先行者之一,李端棻与清季贵州的士人有着不少的互动,这种互动折射多个层面的意义:首先,李端棻与清季贵州士人各自对时代变化的因应;其次,李端棻与贵州士人的互动可以见出时代思想的潮头与相对僻远的贵州之间因地理距离而导致的思想距离,进而对清季趋新思想的传播方式有更进一层的了解;最后,亦可更好地认识清季僻远省份士人的士风变化和社会风尚。
一
甲午以前的贵州士林,大抵仍沿袭“传统”的应试之道,且因僻处西南一隅,文化不振。李少桓认为:道咸以来,一般士人,除当日所谓高头讲章外,“鲜读根底之书”,“至于应试之工具书,则有四书味根录,赋学正鹄,类典串珠,大小号文府,各省之乡会试闱墨,乃至私人中式分送之朱卷,皆当时一般士人朝夕所揣摩之工具书也”。直至道光中叶,贺长龄巡抚贵州,试图力挽学风,端正一般读书趣向,“遂开始刊印岳珂宋本相台五经,朱熹四书集注,沾溉士林。同时并刊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类叙,示一般士人以学术门径”。“就贵州言,实属创举也”[1]129-130。以常理论,四书集注一类“根底之书”至少不应“鲜读”,以此也大致可见其时一般士子的读书趣向。雷廷珍在《黔学会缘起》中也说:“吾黔自道真讲学于汉季,阳明提倡于前明,桐埜、子尹,辉映后先,汉学宋学,得谓无人”,然清季却“不惟经泽斩,来者无闻”[2]121。雷氏为经学名家,其感慨大抵还是从“传统”视角来说。
而咸同之际贵州全省饱罹兵燹,文教更是废弛。同治晚期,出任贵州巡抚的岑毓英在给朝廷的奏折中写道:“窃维地方之治乱,系于官师之贤否。有教化则有风俗,有风俗则有人才。贵州地本瘠贫,又当大乱之后,书籍散佚,物力凋残,期间嗜古笃行之儒,犹能报守遗经,讲明大义,著述所布,学者知归。良田僻在边隅,士习质朴,但使修明学校,先立基根,风气广开,成就更众:人人有诗书之味,人人生忠爱之心。今日治黔之事,莫要于此。”[3]不过在整体文风偏弱的情势下,亦有能察觉时代风向者,其间黎庶昌颇具代表。
同治元年(1862年),黎庶昌在《上穆宗皇帝》第一书中写道:“今尽困天下之聪明才力于场屋中而场屋之士又尽一生之精力,不为效命宣劳之用,徒用之于八比小楷试帖无足用之物,天下贸贸莫闻大道而其试之也又第取之于字句点画间。”且“术不遵孔孟程朱而墨守王安石之经义,士不讲修齐平治诗书礼乐,而专讲小楷时文,世不尚礼义廉耻而尚钻营奔竞。朝廷以此望士,士以此报效朝廷,以故人心日坏,人才日下,风俗日堕。皇路荆榛,圣道熄灭,悠悠长夜,良可痛也”[4]。他进而提出科举的变革思路:求才“不可以例限”,应“扫除一切文法,仿汉代求贤之意,参之以司马光十科之议,责诸臣以求贤”,“谘以时务,兼举实行,而又广科目以待之”[5]。
黎氏所言,虽大体仍囿于传统范围,但渐有逸出既有轨辙之势,提出“时务”和“广科目”等,已略有突破,特别是在其时的贵州,更属难得,因此上谕的回复中称虽“事多窒碍之处,间亦有可採择,业经另行降旨施行,并交该衙门分别核议”,且“以边省诸生,抒悃陈书,于时务尚见留心”[6]。正因为身处“边省”,即便学养深厚的郑珍对此尚不能完全理解,因此有论者认为黎庶昌卓然不群的识器,逾乎郑珍,超出时流[7]。此处所言“识器”,正基于对时代风向的敏锐感知。不过能有此等眼界者,对其时的贵州来说尚属凤毛麟角。
对于李端棻来说,他幼年在贵阳度过,家族文化的濡染给他一生的安身立命定下了基调,幼年失怙的他,幸赖舅父何亮清指点,不仅学业精进,心性修养亦渐展露,何亮清曾云:“苾园(端棻字)忠孝之忱根于性生,异日必能为国家尽瘁。”[8]而李端棻的叔父李朝仪,一生凛然正气,堪为循吏[9]10223。此二人实为其人生导师,故李端棻说“吾一生为人之道,得之吾叔;为学之道,得之吾舅”[10]。
李端棻于同治元年(1862年)中举,次年连捷成进士,入翰林,“为大学士倭仁、尚书罗敦衍所器”。而倭、罗二人旧学深湛,倭氏更属理学名家。此后李端棻先后出任山西、广东、四川、山东等省和顺天府乡试主考官,出督过云南学政,且担任过会试副总裁,《清史稿》记载他“前后迭司文柄,四为乡试考官,一为会试副总裁,喜奖拔士类”[9]10245。此时的李端棻大体仍是传统读书人的轨辙,据沃丘仲子所记,他1878年初见李端棻“于丁文诚(宝桢)座上,一恂谨书生耳”[11]136。
但因见闻较广,李端棻已逐渐显露出学问上的一些新取向。如在1889年典试广东时他所出题目为:一是“子所雅言诗书执礼”至“子不语怪力乱神”;二是“来百工则财用足”;三是“离娄之明,公输子之巧”。此外诗为“荔实周天两岁星”,得星字[12]。题中并无具体的西学知识,惟第二、第三条有较明显的现实针对性,颇具“时务”气息,正反映出出题者的命意所在。有论者认为李端棻是“把清流意识和洋务意识结合起来、并汇入维新意识的一个典型代表”[13],此评确有所见。
李端棻和黎庶昌两个贵州籍读书人拓展眼界的路径不同。前者追随叔父李朝仪于京城问学,博功名以入仕,其思想资源和信息获取显然便捷不少,易得风气。以此来看,黎庶昌在1862年能在上书中有此番见解殊属难得,亦可见贵州虽僻远,但道咸以下的风气变化仍有可能触及边省的读书人,也正因为如此,黎氏方能走上之后“开眼界”的“时务”之路。有意思的是这两个黔籍士人之间往还尚早。据黎庶昌《丁亥入都纪程》,黎于1887年7月初由李端棻在京城郊区迎接入京,此时的李端棻已是享有时名的“清流”,而黎氏的《西洋杂志》已成,二人于私谊之外,风味相投自属早有之意。不过此一阶段李端棻与贵州士人的联系目前看来尚且不多,可以推见,其时贵州除了少数如李端棻与黎庶昌这样的士人因不同渠道而有机会开拓自己的知识视野外,大多数士人仍是因袭既有路径。严修督学黔中,发现黔籍士子科考卷错讹百出:“黔中工诗者者绝少,应试者者率取他题之同韵,录其全联,不论其去题几许之远也,或取其不同韵者而强易其韵,不论其以句作何解也。其自出心裁者,往往劣不成说,无奇不有。”[2]172可见其时风气之一斑。
二
李端棻对西学有比较亲切的体认应在甲午之后。沃丘仲子(费行简)曾言其甲午谒李端棻于京师时李“颇论时事,娓娓道东西洋制度”[11]136。“娓娓道”大抵说明李端棻的西学已有一定程度,这也是其时风气使然,盖甲午之后,西学已蔚为风气,“迨经甲午、庚子两大潮流,国中学术思想,概不惜舍己从人,至以儒为诟病”[14]。胡思敬也称:“日难初平,德衅旋发于胶,士论嚣,庙谟不定,一二行险侥幸之徒,托名忠爱,鼓煽公卿,于是李端棻言学,荣禄、胡燆棻言兵,翁同龢议设昭信股票,新政始萌芽矣。”[15]此时的李端棻不仅能言西学梗概,更作为维新大员在制度化推进西学方面引领风潮,并进而鼎力支持康梁变法,在全国的学界和政治运动中瞩目一时。梁启超曾说:“乙未和议成后,士夫渐知泰西之强由于学术,颇有上出言之者,而刑部侍郎李端棻之奏,最为深切详明。”[16]
甲午的影响也波及贵州,加之学政严修的到来,一时风气蔚起。西学开始进入贵州士子的视野,时黔中宿儒雷廷珍所撰《誓学碑缘起》记载:“先生以士生今日,不通中学则体不立,不兼西学则用不周,中学之本在经,西学之本在算。……算于黔中绝学也,特每月朔,创设算课,捐廉重奖,以开风气,黔士通代数微积者,至今遂彬彬焉。……购置中西学书八十余种,创立科条,学兼中西,调四十人肄其中,无间风雨寒暑,日亲督课,十越月如一日焉。……黔士于中学西学,遂有日进之机。”[17]93雷廷珍本以经学名世,虽然认为“欲修齐治平之业,成智仁神圣之功者,舍五经更莫得其道”,不过其言说已明显融入了西学的内容,“是经也者,诚中西政艺之脑筋也”[18]。乙未丙申(1895—1896年),雷主讲经学于省门,后应兴义聘,主笔山书院,“士风丕变,学者辈出”,这也可略窥其时士风从省城向州府的流向。
作为学问的载体,士人所能获取的书籍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思想的格局,书籍、刊物的流通方式与渠道也往往是士风的风向标。严修督学黔中,所带书籍甚富,“比之当时文化较昌之三江,两湖、京津、岭南,当不足观。但书虽不多,而已纵贯古今,横及四部。窥其内容,于考证、义理,无间汉宋;于诗、赋、骈、散,不持偏倚。启迪士子,于文章之外,兼及经世之学。而于版本(士礼居丛书)、金石(金石粹编)之类,亦稍稍道及”[17]55。这些书对当时的贵州士子来说,并不易获得。严修在黔省各属岁科考时,发现“上游各郡,好学能文之士,所在多有,惟见闻太陋,志趣不广。每于复试日,叩其所学,则皆以不能得书为憾”。至镇远,也发现“此地读书讲求根底者亦颇有之,惟得书甚难,五经亦无善本也”[2]170。因此,严修设书局于省城之中,“全省之中,各地辽远,未能一律流通将现刻各局书目,每州县各寄一本,与其函商,其本地旧有书院,或别有款项关涉学校者,因地制宜,抽拨一款,愿意在所列书目中购买何书,即开列清单,派人到局取运,如果没有此书,则设法代购,约定日期,然后来取,脚价由各公款内开销”[2]84,用此法以便学子。此外,还为书院订购了《时务报》和《申报》,数量达四五十份,几乎住校生人手一册。正因为如此,《严学使范孙去思碑》中写道:“吾黔士多寒畯,书籍绝尠,……更复捐廉,购各种书籍于资善堂而以贱价售之,士虽贫如黔娄,亦得手置一编。于是士林蒸蒸向风,见闻一变,非复前之固陋矣。”[17]110
不过即便与邻省相比,贵州的书籍流通仍嫌不足。严修按试各府时,多次以数学题试士,“但报此课者,所至不多见,盖以习者少且亦无师可学”,本拟于贵阳三书院,择一先设此课,但“征之省内,终未获得师资,只得祈之于湖北”,算学一席,“本省中求一初通者而不得”,盖“海内通才,大半入两湖书院”[2]70。其时的湖北正引领一时风气,鄂督张之洞在饬行全省官销《时务报》札中说:“查上海新设《时务报》馆,该报识见正大,议论切要,……凡所采录,皆系有关宏纲,无取琐闻;……实为中国创始第一种有益之报。”而“湖北地据上游,交涉日繁,他日又为筑造铁路所自始,凡在官员士庶,于时务一门,固不乏留心探讨之人,第恐闻见稍隘,欲扩末由,则《时务报》裨益实多”[19]237。与贵州接邻的广西“向来风气未开,西学尤绝”,但甲午后,“以龙州筑路、梧州通商,彼中士大夫尤汲汲以讲求西学为务”[19]319。四川和重庆也因为商务渐兴,正拓展报业“以开固陋,俾吾川士商周知中外时务”[20]。贵州因交通阻遏、商务不兴,即便与周边邻省相比,也略逊一筹。
不过,在“公车上书”以及其后的戊戌变法中,贵州的表现却可圈可点,这与李端棻颇有关联。有论者认为李端棻的四位堂兄弟及不少亲故参加了这次公车上书,此“不可能与李端棻无关”,且“以中国的宗法制度而言,李端棻既为李氏家族在京的长者,又系贵州旅京人士拥戴的领袖,不可能不预闻并干预这次上书行为”[21]51,这是持平之论。另据茅海建先生的研究,即便康、梁的活动只是整个公车上书链条中的一环,他们对各省公车的影响并没有那么大的话,至少贵州、广西仍受到了他们相当的影响[22]。而其时的康梁能影响贵州其主要的凭借亦只能是李端棻。值得注意的是,被誉为“二百年无此文宗”的严修与夏曾佑、汤寿潜、熊希龄、徐勤、唐才常等在戊戌中被李端棻保举在“新保特科名单”中,从所保举人物来看,这位对贵州士子影响颇深的学政很得李端棻赏识[23]。
在康梁和李端棻等人的竭力推进下,维新风气一时风行,“时四方新学士子喜康梁之议论新颖,群相呼应,起而组织学会,讨论政治问题与社会问题”[24]。曾在1894年9月参与李盛铎等集会于谢公祠、松筠庵的编修吴嘉瑞出任贵州百层河厘金局总办时,在贞丰县办“仁学会”,研究谭嗣同的“仁学”,会中讲授代数、几何。贞丰本偏僻之地,因吴氏的到来而风气一变。且一些贵州举人戊戌年间纷纷上书,如余庆县举人余坤培上书,陈富强应讲求实务,建议“集资归公。讲求商务”[25]141;胡东昌上书,“缕陈弊端,严请查办,以辅新政”[25]364。
相较于甲午前,贵州士风与全国的关联更显密切,不惟贵阳,贞丰、兴义等多地也颇言维新。贵州的士子通过李端棻与康梁等人的关联而开始卷入全国的维新风潮之中。不过也要注意到,无论是李端棻、严修还是吴嘉瑞等,此一期间风气互动的关联仍嫌单薄,更多仍靠个别人物的提携和影响,并未有深厚的人文土壤,毋怪乎时人感叹严修离任后“学未成而功未竣,严公之憾也”[2]122,而参加公车上书的贵州举人回到贵州“害怕遭遇横祸,都讳莫如深”[26]。因此,贵州的士风仍未有扎实根基,我们不可“误以为浮在咖啡上浅浅的一层奶油,早已经渗透到整杯咖啡中”[27]4-5。
三
辛丑(1901年)后,清政府推行“新政”,戊戌年间所废止的兴学举措正式成为国家意志。1902年12月1日发布的上谕,明确表示选材必须中西学兼顾,即使已获三甲的新进士,乃至早已入仕为官者都不能例外:“著自明年会试为始,凡一甲之授职修撰、编修,二、三甲之改庶吉士用部属中书者,皆令入京师大学堂分门肄业。”[28]之后要求“各省教育官练习所,由督抚监督,提学使选聘本国或外国精通教育之员,讲演教育学教授管理诸法及教育行政视学制度等,以谋补充识力,每日限定钟点,自提学使以下所有学务职员至少每星期须上堂听讲三次”[29]。作为深谙教育之道的著名维新大员,李端棻赦返贵阳后,颇受地方当政者和绅耆敬重,积极从事地方文教活动以转移士风。
不过李端棻在贵阳的讲学活动也遇到抵斥。返筑不久李即主聘经世学堂,在第一次月课中所出题目为“卢梭论”。据殷亮轩回忆:“诸生不知卢梭是哪个朝代的人,遍翻人名词书,如《尚友录》《历代名臣言行录》,都查考不出来。”第二次月课,李又出题“培根论”,之后殷亮轩在街头发现“诽谤诗”三首,其一为“康梁遗党至今多,请尔常将颈子摩。死到临头终不悔,敢将孔孟比卢梭”[30]。既有研究多引用此文以说明清季贵州士风,自无问题,不过似仍有略作申论的余地。
李剑农先生注意到,辛丑(1901年)后,科举程式改变,废弃八股,改用策论后,一班应考的秀才、童生们骤然失了向来的揣摩工具,“《清议报》和《新民丛报》就变了他们的《小题文府》三山合稿了”;政府尽管禁止,国内却是畅销无滞;千千万万的“士君子”,“从前骂康梁为离经叛道的,至此却不知不觉都受梁的笔锋驱策,作他的学舌鹦鹉了”[31]。其时,卢梭这一名字不仅在一些报刊、小说中频繁出现,更是堂而皇之地出现在一些科考试题中,如湖北举人陈曾矩在1903年的试卷回答:“有谓天下者,以众人之盟约而成,此法人卢梭之说,而无君党之原理也。”[32]可见,辛丑后言卢梭可谓“风行一时”,作为开新维新大员的李端棻言,推行卢梭之说可谓正得其宜,当然其在贵阳所遭诋毁未必带有普遍性,但确实也显示出其时贵阳士风之一面,他无奈地说:“我国学风现以东南沿海及扬子江下流为最盛,然一旦变法,足供政府与本处之用否尚不可知,至贵州则相去尚远也”,“自严范孙编修督学以来人始知学,至于今日空疏如故”[21]338。贵州士风远逊东南,“所希望所构成者皆东南士大夫之力,我野人士无与者焉,是大可忧也。使就人之所希望所构成者,而我黔人士不惟无与,又不能因之以自致于学,则尤可忧也”[21]344。
他频频参与地方文教事业。1902年,李端棻与留日归来的乐嘉藻、于德楷、李裕增四人出于“谋黔省教育之发展,振兴贵州文化,培养新学师资以应教育发展之需求”的目的,创办了贵阳公立师范学堂。学校聘请在贵州武备学堂任教的日籍教习木滕武彦、金子新太郎等六人来校兼课,“教材全是日文课本,日本教习因为都通晓汉语,其教学效果尚可”[33]。黔抚林绍年究心教育,1905年,其在《高等学堂设立预备科并派员出洋考察折》中称:“黔绅前礼部尚书李端棻、云南布政使刘春霖等呈请变通高等学堂,整顿中学堂,……臣因与往返商榷,并督饬学堂总理、监督详加核议,佥以为黔省高等学生本非由中学堂卒业生升人,程度本低,不如设法变通,将高等学堂改为预备科,照中学堂章程教授,较为切实。”[34]除了支持兴办学堂,李端棻与于德楷等还“以奖掖后进,改革风尚为己任”,提倡学习外语,同时出资赞助修建资善堂书局,购置大量图书报刊及文化典籍供民众阅览,其间包括梁启超的《时务报》[35]。
那么,此际贵州的士风实情如何呢?由于有了政府“建制性”的推动,趋西式的兴文重教不用再含蓄遮掩,贵州的士风有了显著变化。有通省公立中学这样的名校:“校地之美,建筑之精,教授之良,管理之善,光线之合,卫生之宜,早为英博士、日教员所啧啧称羡不置者,固不待赘说也。”[36]一些地方绅耆也着力推行教育,如兴义的刘统之在笔山书院后山新建教室、图书室、仪器室、库房等,“派人赴上海、日本购生物标本、图表及物理和化学仪器、实验药物等,以适应学校改革之需”[37]。
一些会社等纷纷成立,1901年,黄干夫邀集凌秋鹗等十余人于贵阳城南忠烈宫创设“算学馆”,专门从事算学、物理之研究。1903年,在算学馆基础上,黄干夫发起成立达德书社,社员共计三十四人,“社员们分讲科学”。1907年,黄氏自东京归,为学堂购置图书、理化仪器数十箱,并亲自监运到学堂,“恰逢第一班学生毕业,即将这些图书、仪器在学校举办的第一次游艺展览会上展出,任人参观,前礼部尚书李端棻亦曾与会”[38]。此后的“科学会”“历史研究会”等也渐次成立,而且开始不再局限于专业知识范畴。
另一显著变化则是思想资源扩展明显,且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官方的支持。1907年6月,周素园创办了贵州第一张日报《黔报》,但“许多绅士看了一天,第二天就不要了,怕连累他们,没有法子,只有把这些人从送报名单上取消了”。巡抚庞鸿书“认为周素园是舆论的代表人,重大事件都向周殷切下问,他常把周的建议发交司道会议讨论”,而“报馆经费,官厅可以补助”[39]。更值得注意的是此时士子所能读到的书刊,已开始逸出政府所允许的范围。如1902年,遵义蹇季常与毛邦伟、黎迈东渡,求学日本,“曾草劝学书,告滇黔人士,应振奋求学,勿再恋于科举,弋取名位”[1]13-14。科举废除后,此风更甚,各地书店一时兴起,如萧季文之萧天顺书店,贞丰县人集资开设之黔南合资会社,青岩蔡衡武之崇学书局等,而黔南合资会社则以小学教科书为主,“暗中夹带当时一般之进步革命书籍,张石麒、王电轮两氏经常出入此店,购阅新兴书籍不少”[1]127-128。平刚自己也说,他就是在贵阳读到章太炎的《訄书》后才决心与清政府决裂的[40]。而在东京的于德坤在《民报》创刊后,“每出一期必购三册寄回贵阳,约两年间从未间断”[41]。军人出身的刘莘园回忆,1905年时在遵义城中,已有章士钊宣传孙中山的著作《黄帝魂》出售[42]。据统计,至辛亥革命前夕,在达德学校师生间传阅过的报刊有《国民报》《江苏》《汉声》《浙江》《民报》《醒师》《四川》《中国女报》等[43]。聆听过李端棻教诲的钟昌祚曾进入贵州武备学堂,更是认为“中国不出十年,必有大革命,而革命非用武力不可,学军事是我们这一代人难得的机会,为什么要轻易错过呢?”[44]
可见,李端棻晚年返筑后,其学识和名望颇受地方敬重,虽受到少数守旧分子的诋毁,仍积极参与地方的文教活动,对地方的士风产生了积极影响。不过我们也要看到,清季士风变化甚速,即便在贵州,士子的思想资源也愈发多元,正如林毓生先生所言:“政治体系(清王朝)的无能直接映衬着儒学意识形态自身的虚弱,相应的政治体系的权威危机也会逐渐过渡到儒学意识形态,而儒学意识形态的危机会再反过来消解政治体系的权威性,从而导致社会的整体性危机。”[45]此种情形下,对时局最为敏感的读书人逸出传统范畴甚至走上激进道路也是应有之意。
四
在晚清的风云变幻中,李端棻始终能感知时代风潮变化,从传统士子到清流名士,进而成为维新大员推进西学与新政,同时又能不忘桑梓,多方提携和参与贵州的文教活动。从甲午前的个别联系到戊戌年间的多种支持直至辛丑后的身与其间,李端棻与清季贵州士风的衍化反映出传统社会中的地方杰出士人与其籍贯地的丰富联系,尤有助于我们窥探僻远省份地方士风的变动方式。
李端棻对西学的认知在戊戌前后便卓然于当时,他的《请推广学校折》便是近代首先制度化推进西学的明证,在其《普通学说》一文中,更是直言“形上谓之道,形下谓之器,西学亦然”,“习理化者当以得其公例为主,习政治者当以得其公理为主”[21]344,这都是见道之论,即便在全国的舞台上,开明又能直探西学底蕴如李端棻者亦不多。不过转化一个地方的风气并非个人所能为,需要与地方士人的关怀相呼应。一直以来,贵州虽然教育资源匮乏,风气不开,但有清一代,教育政策和人口增长依旧使得贵州的教育有所长进,清代贵州每百万人口中的进士数有显著的增长,在全国行省的排名由明代的第17名上升到第15名[46],其中清季的增长尤为明显。
王汎森先生说:“历史不一定是数人头的游戏,……如果若干思想精英的思想与整个时代的关怀或渴望相契合,透过强烈的努力,也可能改变一整个时代的思想气候,逐渐由少数派变成多数,由‘思想的存在’变成‘历史的事实’。”[27]17特别是辛丑后,聚居贵阳的清朝遗老及地方官宦如郭重光、钱登熙、刘春霖等,“或以亲谊身份亲近于近代的知识分子中间”,“或以门生故旧的关系隐身于其间”,使“旧阶层于无形之中被侵蚀和消解”[47]。此言或有夸大之嫌,但仍可见风气变化。另一特别值得注意的便是留日学生的影响,“学生介于上等社会、下等社会之间,为过渡最不可少之人”[48]。其时贵州的留学生虽然在全国层面并不算多,但他们与贵州士人的联系却十分紧密,这一群体的思想也最活跃,正是他们让贵州士子“和更大的社会与政治空间做一个联结”[49],对清季贵州的士风和政局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1906年,王国维所撰《教育小言十二则》中,他观察到中国致力于新式教育者有四种:“有以为公益者焉,有以为势力者焉,有以为名高者焉,有以为实利者焉。为公益而为之者,圣贤也;为势力而为之者,豪杰也;为名与利而为之者,小人也。”[50]李端棻一生孜孜于学务,甲午、庚子后更是倡言西学、力行新政,着力提升贵州的士风,称其为“为公益而为之者”可谓宜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