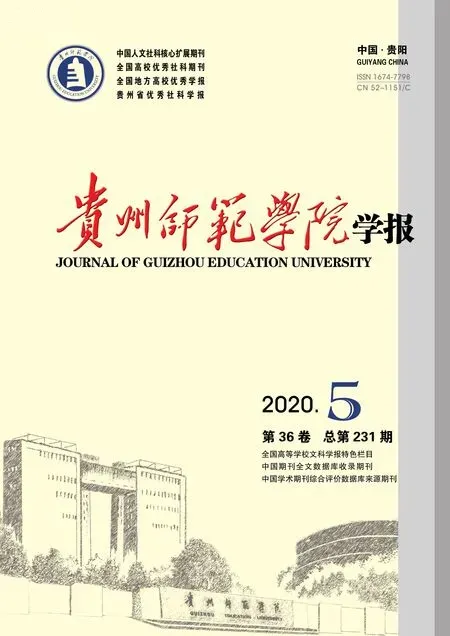“古今一般同”
——王小波“唐人故事”小说对唐传奇的化用
2020-03-14高心怡
高心怡
(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传奇”是中国传统叙事的重要模式之一,该文体发展至唐代渐趋成熟,在新文化运动以前,几乎作为中国古典小说的叙事范式而广泛流行于文人与市民读者之中。虽然唐传奇的叙事模式早已淡出文学主流,但实际并没有与现当代文学发生根本的断裂,正如张清华所言,“传统叙事在许多时候作为一种‘潜文本’或者‘集体无意识结构’,却也支持了新文学和革命文学的文学性。”[1]63王小波的“唐人故事”系列小说,是指王小波早期以唐传奇中的豪侠故事为蓝本创作的五部短篇小说,包括:《立新街甲一号与昆仑奴》《红线盗盒》《红拂夜奔》《夜行记》及《舅舅情人》。这一系列小说打破了长期以来传奇叙事在当代文学作品中潜文本的状态,通过对唐传奇故事与传奇叙事模式的化用,将这些故事印上了具有王小波独特风格的艺术标签。以王小波“唐人系列”小说与传统关系为切口,有利于反思当下学界关于当代文学与传统要么继承要么反叛的二元思维模式,对于如何实现传统在当代的价值转换,有着现实指导意义和启示。
一、传统与反传统
王小波在其杂文《我为什么要写作》中写道,尽管父亲并不支持他学习文学,但“我身上总有一股要写小说的危险情绪”[2]56,而“唐人故事”系列小说似乎就是这种无法抑制的情绪喷发的结果。至于为何要选择唐传奇作为故事蓝本,究其原因,可能与王小波的老师许倬云对国学的关注有关。许倬云的教导带给王小波潜移默化的影响,但是王小波对国学一直持有较为警惕的态度。本质上王小波有着反传统的倾向,唐传奇虽然是一种传统的叙事模式,但唐传奇本身却有着“反传统”的特质。正因为如此,与王小波的思想精神较为契合,于是其便在小说中融入了唐传奇的部分艺术特色和文化精神。
(一)反类型化的人物
唐传奇是经过文人的想象加工,虚构出来的带有娱乐性质的故事。其中的人物形象与史书中所记载的帝王将相、诸子巨匠等有所不同,如大义凛然的女侠、软弱贪色的文人、身怀绝技的家仆等,都是唐传奇中着力突出的人物形象,与类型化、神性化了的正史人物区别开来,表现出反类型的特点。尤其是其中的女性形象,不仅表现出女性意识觉醒的萌芽,还赋予了女性人物以超越男性的魅力。她们有的智谋过人、有的身怀绝技、有的武力高超、有的胸怀大志,不仅丰富了人物的性格,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平等自由,增添了故事的传奇色彩。
王小波在“唐人故事”中选取了“红线”“红拂女”“纫针女”三位女侠人物进行刻画,在原有形象的基础上进行艺术再加工,突出了整体故事的反类型、反传统意义。袁郊《甘泽谣》中的红线身怀绝技,为主人薛嵩排忧解难,能在一夜之间往返七百余里,无声无息地盗取田承嗣身边的金盒。原传奇故事中,仅在开头部分简略地提到了红线的身份为薛嵩的婢女,但并没有交代她的身世,也没有描写她与薛嵩平日的相处关系,以及她为薛嵩盗取金盒之后的情节。只是通过护卫众多的田承嗣被盗金盒而不自知的情节,侧面突出了红线的武艺高强。而王小波却大大扩充了故事的篇幅来刻画红线的形象。首先,他将红线改为薛嵩的侍妾,因此红线盗盒的动机就不单是奴仆的报恩,而是更为复杂的情感纠葛。其次,将故事发生的地点设置为湘西,红线与薛嵩成长环境差异巨大,红线是在山林里出身的“蛮婆”,丝毫不懂礼数,而薛嵩是中原人,一心想用礼法来教化红线,这样就确立了人物“训与被训”的对立关系,增添了更丰富的思想意蕴。薛嵩虽是名义上的主子,却无法完全掌控红线的行为,如两人被困在山上,薛嵩吵醒了睡梦中的红线,红线一改平日的温顺,对着薛嵩就是一顿破口大骂,“混账!我刚睡着!老娘又跪你,又拜你,又喊你老爷,又挨你打,连觉也不能睡?我偏要睡!”[3]152薛嵩以为可行的教化,红线虽然表面接受,但内心却充满鄙夷,有着强烈的讽刺意味。最后,小说情节中最精彩的部分,也不再是红线盗取金盒时的紧张过程,而是文末红线不愿被规训,拒绝成为薛嵩的正妻,回到山上做了女寨主,从别人的奴变成了自己的主。可见王小波笔下的红线已不单是身怀绝技的女侠,还是一个有着女性欲望和独立精神的强势女性形象,是对“女侠”这一反传统形象的再反叛。
(二)小说的诗化
唐朝是诗歌的黄金时代,由于诗歌氛围浓厚,传奇小说也不免呈现出诗化的特征,或是塑造浪漫的故事情节,或是追求意境之美,甚至在文中直接引用诗句等创作手法,都将传奇文本带入了一个诗化的世界。王小波早期的小说如《绿毛水怪》《战福》《地久天长》等,并不像他后期作品那样,虽然也极富趣味性,但小说的整体氛围是偏向浪漫诗化的,如《绿毛水怪》中“我们好像在池塘的水底。从一个月亮走向另一个月亮。”[3]20这样的句子,使整篇小说都充满了诗意的美感。
豪侠故事中也有才子佳人的浪漫爱情,但王小波并不刻意追寻唐传奇中原本的爱情模式,而是更注重诗化的氛围和感觉上的共通。这一特点在小说《舅舅情人》中发挥到了极致。《舅舅情人》改编自《潘将军》,原本小说中并没有爱情线索,王小波改动了人物关系,在非亲的舅舅王安与外甥女小青之间勾勒了一条“绿色的爱”。所谓“绿色的爱”文中并没有详细说明,但王小波却细致地刻画了这种无形的感觉,“他感觉到她贴体的触觉、嗅觉和遥远的听觉、视觉逐渐分开。她在很近的地方,女孩在很远的地方。当冰凉蠕动的感觉深入内心的时候,王安知道自己在爱了。”[3]252这种爱是五感相通的,当小青生活在山谷中时,她在寂寞中体会恐惧,又在恐惧中生出了爱,这便是她的绿色之爱。故事中有两条关于“寻找”的线索,一条是小青寻找绿色之爱,一条是皇上寻找丢失的手串,但实际上二人都是在寻找心灵的归宿。小说中无论是对感觉画面的呈现,还是对情感细腻的捕捉,都表现出抒情诗一般的伤感浪漫情调,而“绿色之爱”更像是一个空灵的意境,整体突出了一种诗意的氛围。“环境、气氛描写的象征性、意象化以及意境的追求。”[4]这本身就是唐传奇诗意表现的内容之一,王小波有意或无意的在其传奇小说新编中化用了这种艺术表现手法。除了《舅舅情人》外,在《夜行记》这篇并不包含爱情线索的小说中,也着力渲染了这种诗意气氛。小说是由带有武侠性质的《僧侠》这个传奇故事改编而来,虽然王小波沿用了其中的武侠元素,但却并没有因此削弱小说的诗意氛围,这主要归功于小说里对夜行中的“月亮”的描写。当书生对和尚充满了不耐烦时,小说写道:“太阳已经落山,一轮满月升起来,又大又圆,又黄又荒唐。月下的景物也显得荒唐。山坡上一株枯树,好像是黑纸剪成。西边天上的一抹微光中的云,好像是翻肚皮的死鱼。”[3]220这样的景象体现出书生心中的烦闷,而当书生在忍耐和出手间犹豫不决时,他又注意到了月色之美,“此时月亮已经升到中天,山里一片银色的世界。坡上吹着轻轻的风,又干净,又明亮,好像瓦面上的琉璃。”[3]222景物的美好暂时抚平了他的愤怒。月下景与人物的心情吻合,形成一种相互映衬的关系,尤其是对色彩的描写,令小说增添了诗的气质。因此,即使与阳刚的武侠元素搭配,诗意的刻画使小说依然有“柔情似水”的一面。
二、虚构与现实
在鲁迅看来,传奇已显出与六朝志怪不同的文学特质,“传奇者流,源盖出于志怪,然施之藻绘,扩其波澜,故所成就乃特异,其间虽亦或托讽喻以纾牢愁,谈祸福以寓惩劝,而大归则究在文采与意想,与昔之传鬼神明因果而外无他意者,甚异其趣矣。”[5]文采与意象可以说是传奇不可或缺的艺术特点,王小波对唐传奇的新编则又扩宽了想象的边界,突出了小说的虚构之美,强化了小说的叙事功能。同时,其小说通过机智的讽喻增添了小说的寓言性,在虚构的故事中对现实作出回应,呈现出杂文化的倾向。
(一)虚构之美
王小波热爱文学艺术,也很清楚自己的写作才华,他认为相比杂文、评论与简介,“写小说则需要深得虚构之美,也需要些无中生有的才能。”[2]65唐人故事中所用的豪侠传奇蓝本,本身就极具传奇性,内容往往出其不意,注重情节的起伏和故事的娱乐性。如《虬髯传》里面的风尘三侠,每个人都充满了人格魅力且深藏不漏,尤其是虬髯客,先是将他塑造成一个不拘小节的豪气之人,描写他行事随意,用仇人的心肝作下酒菜,文末又揭示他身家不菲,有“贵人”之相,还将自己的全部财产、奴仆都留给了红拂女和李靖,自己做了扶桑国的君王,整篇小说的故事性极强。对这个传奇故事进行新编,王小波选择另辟蹊径,不从故事性下手,而是更加着重行为动机和人物形象的虚构性,转移叙事焦点。短篇小说《红拂夜奔》里,原本文武兼备的大将军李靖,被王小波刻画成了一个街头流氓,少年无行,除了嗜酒之外还常常勾搭街巷妇人,卖酒的李二娘对他一往情深,但他却只图人家的好酒。李二娘是《红拂夜奔》里新增的人物角色,她身上兼有“淫妇”和“烈女”两种特质,平日喜好卖弄风骚,但又对李靖痴心绝对。而红拂女本是才智过人、见识不凡的侠女,但在此小说中却被塑造成了“一会人话,一会鬼话”,遇事就喜欢怪叫的“神经质”的小妇人,虬髯客更是从豪情万丈的义士跌落成贪图女色,奸诈狡猾之人。对这一系列人物形象的重塑,一方面是用戏谑的方式,贯彻王小波反对无趣的小说的观念,另一方面则通过调侃传奇人物,解构庄严与崇高,增添反讽的意味。值得玩味的是,文中王小波将他虚构的故事写成是对封藏已久的“野史”的记录,而这个记录人正是小说中的叙述者王二,并且还模仿古人传记,为该文作了序,但作序者却是王二的妻子小胡,就这样串联起了古与今,虚构与现实。
(二)小说杂文化
张清华将唐代“传奇”的特征总结为“怪诞奇幻”,将其宗旨归纳为“警世劝喻与闲暇消遣”[1]63。如舅舅情人里小青的原型“纫针女”,虽然盗取了玉珠环但并不是为了钱财而是为了玩乐,虽然能行盗天下但仍靠着缝制衣物来自谋生路,其中所包含的劝诫意味不言而喻。唐传奇素来被认为是一种“文备众体”的文体形式,也即是说传奇具有史说、议论、抒情等功能,而警示劝喻的宗旨正与杂文的功能一致。王小波的小说向来与其杂文有着思想性的相互关联,唐人故事小说一方面满足了王小波对叙事技巧的探索兴趣,另一方面也将他所强调的文学精神注入其中。在王小波的文学创作中,最常见的是施虐者和受虐者这一组人物关系。施虐者对受虐者发号命令,用暴力或是权力压制受虐者,但受虐者却能从中享受到被施虐的快感,这一模式看似不正常,但实际“小说所深入的不仅是以施虐/被虐面目出现的权力游戏,而且是此间极为微妙的身份政治。”[6]公差王安对小偷妻子的追捕,虽然是一种压制和规训,王安的妻子在被王安用铁链锁住脖子时却感受到了爱意,总是在夜晚变得温柔似水。但这又不单是一组固定的关系模式,白天王安的妻子就会恢复成夜叉式的形象对王安又打又骂,由受虐者变成了施虐者。在杂文《弗洛伊德和受虐狂》中,王小波分析了这种文化心理。当人必须面对承担不了的痛苦时,他便容易将这种痛苦看做是幸福,从中寻找快乐,甚至在一些情况下,他们会将记忆扭转,假装自己并没有身负这些沉重,将世界营造成假想中的乌托邦。王小波设立这样一组小说人物形象,实际也是在提醒人们不要试图忘记曾经的苦难,伪装成假想中的幸福姿态,一旦这种假想被戳破,痛苦会加倍而至。
除此之外,反同化的思想也几乎贯穿于王小波的每一部作品中。无论是红线拒绝教化规训,还是小青对绿色之爱的执着追寻,都体现出一种自由的人生态度。虽然“唐人故事”系列小说是历史故事的新编,笔调也是黑色幽默的,但并不能掩藏王小波在小说中关注的核心问题——人的生存状态,他以人文视角洞察古今国人共通的心理及精神,以古人的遭遇来映射现实的生存环境,以达到反思当下的目的。尽管王小波并没有明确说明过自己与古代传统文学之间的联系,但从其作品本身来看,确实有意无意的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唐传奇的艺术特征。
三、传奇与后现代文本的结合
从王小波本人所述的文学作品接受史来看,西方现代文本对他的影响远远大于中国传统文学,尤其是杜拉斯的《情人》,是他眼中现代小说最完美的范式[2]62。因此,即使小说的题材是唐传奇故事,但作为一个接受了后现代文学启蒙的当代作家,必然不可能仅仅去遵循唐传奇的“旧”,而是在思想及内容上都有所创新。“唐人故事”系列小说在叙事方法上对原传奇故事进行了改编,基本重塑了整个故事的面貌,但依然保留了原故事的传奇性,将故事的趣味性与叙述的实验性,巧妙地结合了起来。
前文谈到了《红拂夜奔》中,现代的王二与唐传奇中的王二,有着一种命运的勾连,这种叙事时间与叙事空间的转移变换,在另一部小说《立新街甲一号与昆仑奴》中表现得更加突出。在这部小说里,叙述人是“我”,“我”是现实世界里的王二,但在唐传奇《昆仑奴》中还有一个唐朝的王二,小说一会描写“我”与小胡两人在立新街甲一号楼中的生活,一会叙述唐朝卖狗肉的王二与昆仑奴和绝代佳人的交往。两条线索交错叙事,穿插在其中的是两个王二对一些事物相同的感觉,“这种依靠联想思维建立起来的类比叙述可以打断作品原有的叙述节奏,使作家的叙述显得摇曳多姿,增强作品的趣味性”[7]。同时,也正因为感觉的共通,从而缩短了历史与现实的距离,虽然是不同的时空、不同的故事情节,但并不会令读者感到“串戏”。传奇本身就较为贴合市民的审美心理,小说的故事性大于说理教训,而王小波的小说始终标榜着“有趣”。他常在小说中打造一个类似于《第二十二条军规》中的逻辑怪圈,给人以两种选择,但哪一种选择都不会带来好的结果。如《红拂夜奔》中,杨素判李靖不敬之罪,给了他公了和私了两个选择,公了就是将李靖押入死牢,择日处刑,私了则是把干女儿嫁给他,表面上看起来似乎因祸得福,但实际却只是做个死囚和风流鬼的差别,无论哪个选择都会要了他的命。这样的写法,暴露出事件的荒诞性,带着黑色幽默的意味。王小波认为黑色幽默是他与生俱来的气质,将简单的市民趣味上升为黑色幽默,在机趣中表现对不合理的社会现象的讽刺。在《舅舅情人》中,王小波将《潘将军》中丢失玉珠环的潘将军这一形象改写成了皇帝,而这个皇帝因为什么都不缺,所以得了抑郁症。抑郁症是个现代词汇,也是现代人容易患上的一种心理疾病,皇帝有抑郁症这个事情本身就带有浓厚的讽刺性,锦衣玉食的皇帝也和现代的普通人一样,会感受到人生的无常和生存的困境。将这种现代情绪带到唐传奇的故事中,一方面产生了一种陌生化的效果,令读者产生新奇的阅读感受,一方面也以怀疑的姿态,展现了人生无常的命题。
通常在研究者眼里,王小波是一个受西方文化影响明显多于传统影响的人,但事实上,哪一方面的影响更大无法定论也不必纠结。他对西方思想资源的汲取并不影响他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受哺于传统资源,恰恰是中西交融的知识背景赋予了王小波豁达包容的眼界。试图在小说中去厘清王小波所受到的中西方文学影响是无意义的,因为二者早已融合在了小说的文本里,呈现出复杂交错的关系。王小波对唐传奇故事的化用,在一定程度上给予了传统文学艺术的新生,但这也并非王小波的最终意图。通过这一系列的短篇小说,他把历史与现在串联到了一起,描写了人性、身份与人的心理,表现“古今一般同”的主题意蕴。与此同时,王小波也没有停止对叙事技巧与文本思想性的探索,因此对《红拂夜奔》与《红线盗盒》都进行了再改写,分别扩充成了长篇小说《红拂夜奔》和《万寿寺》,叙事实验性与智性思辨在这两部小说中呈现出了更饱满的状态。正如学者李遇春所说,当代小说家对“当代小说艺术探索与中国传奇文体传统的深层血缘是不容抹煞的。”[8]王小波所创造的“唐人故事”,并不是去挖掘历史的“秘传”,也绝不仅仅只是作为其后作的练笔。在他特立独行的小说世界里,唐人传奇是一片艺术的土壤,在其中可以开掘出诗意、智慧、妙趣、爱情与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