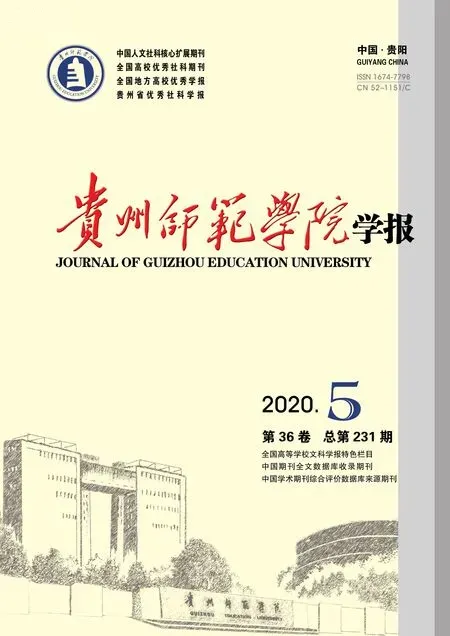夏同龢状元策研究二题
2020-03-14马庆洲
马庆洲
(清华大学出版社,北京 100084)
夏同龢(1874—1925年),字用卿,贵州都匀府麻哈州(今麻江县)人。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状元及第,成为贵州科举史上仅有的两名状元之一。近年来,随着各地对乡邦文化研究的重视,夏同龢也越来越多地受到贵州文史学界的关注。截至2019年底,相关研究文章仅在中国知网就能检索到近七十篇,涉及其生平、交游、书法造诣,以及政治、法律、教育等各方面思想。这些文章既有学术性的,也有普及性的,绝大部分发表于2009年之后,仅从数量上看,就足见其所受重视程度。殿试对策(习称状元策)是夏同龢不多的传世文章中的一篇,自然备受关注,相关研究之作时有所见。遗憾的是,相关研究所据文本错漏颇多,故有必要重新整理,以期为研究者提供相对可靠的文本。
一、夏同龢状元策的保存及流传
清代的科举考试与明代几无二致,采用的也是乡试、会试、殿试三级取士的做法,殿试是最高一级。《清史稿》云:“天子亲策于廷,曰殿试,名第分一、二、三甲。一甲三人,曰状元、榜眼、探花,赐进士及第。二甲若干人,赐进士出身。三甲若干人,赐同进士出身。”[1]
殿试(亦称廷试)名义上由皇帝主持,考试内容是针对皇帝的策问作一篇策对。考生的殿试答卷就是殿试卷,其文则称殿试策(或廷试策),状元答卷习惯上以“状元策”名之。殿试原卷是朝廷秘档,归内阁保管,外人无缘得见。由于保管不善及改朝换代等原因,清代存世状元卷大约只有15份(含残卷),分散在世界各地的图书馆及民间。[2]每科殿试结束后,礼部照例刻印《登科录》,这是殿试的原始档案资料。《登科录》的出现,一般认为始于唐代。至明代,登科录制度已十分完善。明朝自洪武以后,《登科录》只刻一甲三篇策文,偶有例外。从文献角度看,《登科录》所载策文,可以视为原始文本。
《登科录》是官方文献,刊印数量极其有限,发行范围亦有严格限制,非普通人所能得见。但是,根据相关史料可知,官方认可的书坊可以从礼部购买《登科录》,汇辑若干科后,以《状元策》或《殿试策》为名刊印发行。明清状元策的保存和传播,这是至关重要的一个途径。有清一代的《殿试策》或《状元策》版本众多,多数状元的殿试策文都可在此中找到。但国家图书馆、首都图书馆中所藏的《状元策》或《殿试策》中,均未见夏同龢的状元策。所幸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藏有《光绪戊戌科登科录》,夏同龢等三鼎甲策文,得以完整保存。
从现有资料看,国内最早着手整理夏同龢状元策的是陆辉南、杨真。据陆辉南所述,1988年6月,为编纂《麻江县志》,“赴首都北京查阅史料,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内阁大库、序号‘殿’30号《光绪戊戌科登科录》查到夏同龢参加殿试策文。”[3]陆辉南没有交代是不是抄录此文,但从查档时间及有关的档案规定推测,当时复制条件十分有限,抄录的可能性极大。整理工作也很可能就是以抄录的文字为底本,然后进行识读、分段、标点等工作。整理文本以《夏同龢的状元卷》为题,发表在《贵州文史天地》1994年第1期上(以下简称“整理文本”)。此文的发表,使夏同龢状元策得以走进公众视野,为相关研究提供了便利。近几十年来,这个整理文本不断被引用,几乎成为夏同龢殿试策文的唯一出处。虽然有的引用并没有注明来源,但稍加比对,也能知其源出此文,只是没有说明而已。
陆辉南、杨真的整理工作确有发轫之功,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在交通、通讯、食宿等各方面条件十分有限的情况下,他们不远千里,赴京实地调查,并获得这篇文献,体现了一种可贵的求真精神,应当充分肯定。但是,由于主客观条件限制,这篇策文的整理文本,还存在很多问题。文字识读以及断句等方面,错字、漏字多达近三十处;分段、标点等,也多有可商。而后来的引用者因无从辨别,只能原样引用,造成了错误的重复。下面是几种有代表性的文本,它们为传播夏同龢状元策做出了贡献,但遗憾的是未能将错漏处改正。
邓洪波、龚抗云编著的《中国状元殿试卷大全》出版于2006年,收录夏同龢状元策[4],但没有交代资料来源。笔者将其与“整理文本”比对发现,该书所收策文,除改正原文中几处明显错字(如“整理文本”将“俊乂”误作“俊又”,且将“俊乂”二字割裂,分属上下两句断句)和断句错误外,其他错误均无二致。可以肯定,《中国状元殿试卷大全》所用底本就是“整理文本”。
赵青、钟夏所著《戊戌状元夏同龢》出版于2011年,其中第四章《光绪皇帝策问及夏同龢对策》专门论述策对、策问。[5]27-40作者在《后记》中说曾到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查到《光绪戊戌科登科录》等史料[5]206,但可能没有核对策文文本。《戊戌状元夏同龢》所录策文,除了改正“整理文本”中两处明显错字(如“管肃”改为“管萧”,“万万年”改为“亿万年”),其他错误仍完全一致,而一些标点的改动也值得商榷。很显然,该书所依据的底本也与“整理文本”同源。
梁光华、饶文谊、张红辑校《夏同龢文辑》出版于2013年,该书收录了夏同龢状元策[6],改正了“整理文本”中四五个错字,标点及分段有所优化。但是,“整理文本”其他错误几乎未改动。对于书中所录策对来源,整理者在《辑校说明》中明确说:“点校者据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陈光辉、席凤宁主编《中国状元大典》所收录之文点校,统一采用规范新式标点符号行文格式进行点校。”[6]在策文文末,亦有与《辑校说明》相同的标注。然而,《中国状元大典》只收录了策问,并没有收录策对[7],不知为何会出现这样的失误。《夏同龢文辑》名之以“文辑”,且采用繁体字排印,是以古籍整理形式发表的著作,而这篇策文所据的底本并不存在,使得整理出的文本可信度降低。
二、状元策整理文本指谬
“整理文本”的错误,集中在文字和标点两方面。笔者据《光绪戊戌科登科录》所载原文校勘,发现其中错、讹、衍、夺约有27处。而分段、断句、标点方面的问题也有很多,无法一一统计。文字方面的错误之处如下(清代殿试答卷有严格的程式,层次清晰,而“整理文本”分段较为混乱,为方便起见,这里按答卷规范格式叙述):
策帽(开首段):“法则治”,“法”上脱“知”字。
颂圣段(第二段):“荷艰大业”,“大”后脱“之”字。“捣昧”当为“梼昧”。“是言为治不必遵成法也”,“不”字衍。
第一对:“俊又所以贵旁求也”,“又”是“乂”字之讹。“然历代取士之法”,“然”下脱“观”字。“不能知其弊于万事之后而豫防之”,“事”当为“世”。“恃有因时补救之而已”,“之”下脱“道”字。“今人议变科举者”,“人”当为“之”。“时议即变”,“议”当为“艺”。“即可举中”,“可”当为“科”。
第二对:“思有以悉机宜”,“悉”下脱“协”字。“因时以酌焉可矣”,“酌”下脱“制”字。
第三对:“尤以德以戢其心”,上“以”字当为“必”。“商岸四辟”,“四”当为“肆”。“我皇上整兵修戈”,“兵”当为“军”,“戈”当为“戎”。
第四对:“亚于管、肃”,“肃”当为“萧”。“苏轼策劄”,“劄”当为“别”。“不免漏厄”,“厄”当为“卮”。“复以开源之事责实于臣”,“于”下脱“诸”字。
收束段(末段):“张弛宜”,“弛”下脱“异”字,致断句错误。“且变法者不过日”,“日”当为“曰”(此字错,致断句错)。“致使列圣主法之精意荡然无存”,“主”当为“立”。“转念其变法之说”,“念”当为“恣”。“宣布中外臣工”,“布”当为“示”;“臣工”当属下句读,断句错。“万万年有道之长”,上“万”字当为“亿”。
这些错误,分析起来主要是抄写时漏字和识读错误,而这些错漏会导致文意不明,甚至恰恰相反。所以,不能简单的视同于印刷错误。断句、标点方面,问题也颇多。有些是对原文理解不准确,导致断句错误。原文的错字、漏字等,也必然导致文意不顺,不免有强行标点处,造成硬伤。从古籍整理的角度讲,对原文的理解不同,个别地方的标点会有出入,这是正常现象。但是,如对仗句、引文起止等,则不能破读。此外,书名也应加书名号。此类错误,难以一一列出,仅举一例:
收尾一节中,将以下此句标点为:“将英俊之士,可以兴军旅之威,可以振四夷之守,可以固九府之财,可以充斯所为,扬大烈、觐耿光,我国家亿万年有道之长基此矣。”稍微体会一下文意不难发现,这样标点是由于对原文理解有误而致错。从逻辑上讲,“兴”的当是“英俊之士”,“振”的当是“军旅之威”,“固”的当是“四夷之守”,“充”的当是“九府之财”。所以,正确的标点应该是:“将英俊之士可以兴,军旅之威可以振,四夷之守可以固,九府之财可以充,斯所为扬大烈、觐耿光,我国家亿万年有道之长基此矣。”由于将“可以”二字属下断句,“将英俊之士”便无法处置,大概是感觉到如此标点文意不通,因此《夏同龢文辑》在“将”字前增补了“可以”二字。增补的“可以”二字,既无校记,也无文献依据,实属臆改。
上述文字、标点方面的错误,《中国状元殿试卷大全》《戊戌状元夏同龢》《夏同龢文辑》基本上都原样未动,这也能证明他们同出一源,没有核对原文。
另外,分析一下有关策问的问题。该科策问《光绪戊戌科登科录》中有存,但“整理文本”没有涉及。《中国状元大典》及《中国状元殿试卷大全》收录策问,但均未注明出处。稍作分析可知,这两本书中所收皆出自《光绪实录》。《光绪实录》中“以布帛为租”一句,“以”字前脱“章帝”二字,《登科录》不脱,策对中亦有此二字。《中国状元大典》的文本文字方面无误,但标点多有不规范处。《中国状元殿试卷大全》文字有一处错,即将“综核之计甚详”中“甚”误为“真”,标点则中规中矩,颇具专业水准。
《戊戌状元夏同龢》和《夏同龢文辑》亦收录策问,均注明依据《中国状元大典》。《中国状元大典》所录策问,本身不是原始文献,用它作底本,有失规范。此外,两书在引用时又增添了一些新的错误,前者有四处,后者有十余处。具体如下:
《戊戌状元夏同龢》:“酌古济今”,“济”应为“剂”;“俊又所以旁求”,“又”当为“乂”,“旁”上漏“贵”字;“而戢其心欤”,“心”上漏“敢”字。
《夏同龢文辑》:“剂”“乂”“贵”三处错误同前书;“岩防”、“悬岩”,两处“岩”均应为“巖”;“乾羽”当为“干羽”;“岁终而会货贿之出入”,“而”应为“则”;“唐之财富”,“富”当为“赋”;“付讬”,“讬”当为“託”;“辟门吁俊”,“辟”当为“闢”;“而多士”,“而”应为“尔”。这其中,不少错误是因繁简字转换造成的。此外,断句方面,有一处十分明显的错误:“二者果何道之,从俾实有济于国用欤”,“从”字应在上句末。
三、结语
古籍整理是一项十分严肃的学术工作,除了应对古人有足够的敬畏之心,还应当有基本的专业训练,操作中更应严格遵守有关规范。无论是对一本书,还是一篇文章,都应当慎重对待,从文字到标点,都要尽最大可能做到准确无误,以便为相关研究提供可靠的文献基础。
清代同治、光绪两朝的状元策,《登科录》所载与坊刻本多有不同,异本颇多。夏同龢的这篇策文见于《光绪戊戌科登科录》,无疑可视作原始文本,值得信任。作为夏同龢为数不多的存世文章之一,这是后人了解其思想的重要依据,应当认真整理,准确解读。
夏同龢殿试策对
臣对:臣闻为治莫先于法祖,故方策以外无政书;效忠莫大于责难,故謇谔之臣多谠论。天下之事,百变不能言也;天下之患,百变不能知也。然则天下将奚治?知法则治。《荀子》曰:“法后王。”《孟子》曰:“遵先王之法而过者,未之有也。”恭读圣祖仁皇帝圣训:“致治之道,无过法祖。鉴于成宪,乃罔有愆。”大哉圣言!垂法万世已。窃见近日谋富强者,莫不竞言新法。夫穷变通久,往训维昭,苟利当时,何容泥古。然塞源求委,舍本治标,补苴之图,圣贤弗尚,故虽近于效忠责难而非其说。
钦惟皇帝陛下,躬圣哲之资,荷艰大之业,揆文奋武,日新又新,置特科,吁贤俊,以德礼化干戈,固已四海归心,群黎遍德矣。乃圣怀冲挹,犹孜孜焉举求才、经武、绥远、理财诸大政,进臣等于廷而策之。如臣梼昧,何足以承大对而赞高深,然臣尝诵法孔子之言矣,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人存则政举。”是言为治必遵成法也,其敢不本此义以为责难之先资乎?
伏读制策有曰:“天工人代,俊乂所以贵旁求也。”爰考历代试士设科之典,思有以综核名实。臣谨案:汉代以策科试士,得人最盛,如贾谊、董仲舒者,诚不乏人。汉唐经师,授受相承,以科第进者亦多。至宋之儒修,上感星精,下立人纪,或以保举,或由科目,流光史策,最为人才渊薮。明代取士以制艺,贤才之出,未闻今不古若也。今之议者动曰:“不变科举,不足以得真才。”夫科举至今,诚不为无弊,然观历代取士之法,三代以上,出于学校尚已。自汉以来,迄于有明,其流别异同,虽非一致,然其始皆足以得人,其后皆不能无弊。圣人立法,不能知其弊于万世之后而豫防之,恃有因时补救之道而已。今之议变科举者,谓时艺空言无用耳。夫凡宣之于口,笔之于书,皆空言也。时艺即变,果遂不至空言乎?苏轼有言:“得人之道在于知人,知人之道在于责实。”能责实,虽试以时艺而人才自兴;不能责实,虽制度日更,于造士终无所益。昔臣如舒赫德等,亦曾以废时艺为言矣,而列圣终未之变者,诚以变之而未有良法美意以善其后,且就是以责实,亦未尝不可得人,则莫如循名核实之为愈也。我皇上登明选公,量能授职,即科举中,何尝不可收奇杰之士哉?
制策又以:“古之帝王,有征无战。”因求命将行师之法,思有以悉协机宜,此诚德绥威服之至意也。臣谨案:《司马兵法》所云生聚教训之术,权谋运用之宜,后世言兵事咸祖之。军礼为五礼之一,至今犹可考见,《阴符》《六韬》《穰苴》《尉缭》《孙》《吴》之书,皆足以发明用兵之道。唐太宗、李靖论兵之语,亦足裨于实用。《左氏兵法》《通鉴兵法》,后人裒集,具有成书。其他书善论兵者,如《武备志》《金汤十二筹》《纪效新书》《练兵实纪》是也。其他书之论形势而有裨于用兵者,如《寰宇志》《郡国利病书》《筹海图编》,又其深明险要者也。推之岩防、江防、屯田、转运、攻守、战伐、侦探、间诱,虽处风雨冥晦之际,悬岩绝壑之境,无必胜之兵,亦无必胜之制,要在因时制宜耳。昔我太祖高皇帝,以八都统辖八旗,遂举辽阳一隅无敌于天下。及我世祖章皇帝,定鼎燕京,仍八旗之旧,更于各行省置绿营兵。至于高祖纯皇帝时,用绿营兵戡定川楚之乱,而八旗兵稍稍休息矣。文宗显皇帝时,绿营兵竟废弛不可用,于是专用召募,削平大乱。由是观之,制岂有定哉?大抵从古无必胜之兵,而有必胜之将,自来名将亦断无不自为制,而遂能操必胜之权者。皇上诘戎振武,安不忘危,亦专阃以任才,因时以酌制焉可矣。
制策又以:“惟德动天,无远弗届。”因思所以怀柔远人。臣惟诞敷文德,两阶干羽,所以格有苗也;风不鸣条,雨不破块,知中国有圣人也。伊古以来,四夷宾服,白雉贡于越裳,砮矢贡于肃慎,白环贡于西国,威以慑其志,尤必德以戢其心,然后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也。夫怀远之道,要在宽猛相济耳。冒顿之子复请和亲,《纲目》书之。至遣兵出塞,不过尽境而止,史称盛德焉。若夫陈汤击郅支,不讥其矫制;登燕然而刻石,等诮于金微;诸葛亮屯汉中,而自请贬官;李郭宣力效忠,而纪入援之回纥。综观往籍,亦古今得失之林也。臣以为论绥远于今日,较历代为尤难。商岸肆辟,门户洞开,教务蔓滋,潜生奸宄。不先用威,虽德不足畏其志;不先用猛,虽宽适以养其奸。此怀柔远人,万世不易之理也。高祖纯皇帝,平定准夷回部,奏累世未竟之功。通商以来,他族逼处,要挟百端,羊很狼贪,不知向化,薄海臣民,共深义愤。我皇上整军修戎,寓武功于文德,行见梯山航海,奔走而来宾已。
制策又以:“丰财所以储用。”因思财用之足,在有以开其源而节其流。臣惟《周礼》一书,半论理财,岁终则会货贿之出入,诚善政也。两汉时,武帝创均输之法,章帝以布帛为租。唐之财赋,归于左藏,厥后帑藏主以中官,而制遂坏;刘晏理财,亚于管、萧,其立法有上下交得者。苏轼策别,有或去或存之议;曾巩议经费,有或杜或从之谋,指陈国计,纤悉靡遗。夫今日理财,开源较节流为尤重,盖海禁既开,流虽节仍不免漏卮,不如开源乃足收利权也,而节流亦不可忽。昔高宗纯皇帝时,岁入不过五千余万,虽豁逋赋益军需而犹有余。今岁入约增二千万犹苦不足者,固由八旗生齿日繁,及直省防勇、绿营增饷所致,意者其犹有他事不急之需乎?比屡裁汰冗员冗兵,而所节亦无几,恐尚未尽核实也。总之,能核实则开源自见有功,否则,虽节流亦甚无补。伏冀皇上躬行节俭,复以开源之事责实于诸臣,则生财之道得矣。
且夫古今异势,张弛异宜。然天不变,道亦不变,安在法之必变也?且变法者不过曰“法久则敝耳”,果法之自敝乎?抑亦奉法者之敝之乎?行之既久,视为具文,苟且因仍,致使列圣立法之精意荡然无存,转恣其变法之说,其妄甚矣。臣伏愿特颁谕旨,宣示中外臣工,不必侈言变法,惟事事综核名实,奉法而力行之。将英俊之士可以兴,军旅之威可以振,四夷之守可以固,九府之财可以充。斯所为扬大烈、觐耿光,我国家亿万年有道之长基此矣。
臣末学新进,罔识忌讳,干冒宸严,不胜战栗陨越之至。臣谨对。
(底本:《光绪戊戌科登科录》,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号:会040;缩微号:B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