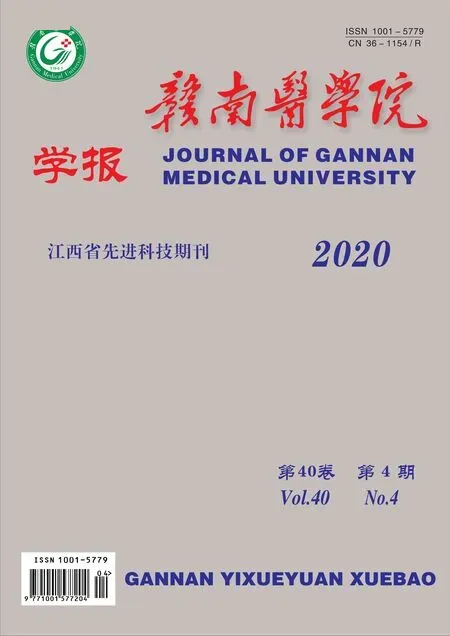婴幼儿型血管瘤患儿和家长心理影响的研究进展
2020-03-03谢明峰刘海金徐仙赟
方 涛,谢明峰,曾 勇,彭 威,刘海金,3,徐仙赟,刘 潜
(赣南医学院 1.2017级硕士研究生;2.第一附属医院;3.江西省脉管异常性疾病研究中心;4.基础医学院;5.心脑血管疾病防治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江西 赣州 341000)
婴幼儿血管瘤(Infantile Hemangioma,IH)是婴幼儿最常见的良性软组织肿瘤,在婴幼儿中发病率可达3%~10%,在早产儿中可达20%以上[1-2]。但由于人群和研究设计的差异,发病率介于0.2%至10%之间[3]。IH可出现在全身任何部位,尤其好发于头颈面部,约占总病例数的60%,其次是躯干(25%)和四肢(15%)[4]。近年来,对IH的临床表现[5],最新的分型、分类[6-7]、各种治疗方法[8-13]及并发症[8,14-16]等方面的研究逐渐成熟,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关注IH对患儿及其家庭的心理方面的影响[17]。由于IH好发于颜面部、增殖迅速、治疗周期长、并发症较多等原因,在临床普遍发现患儿家长存在程度不一的负性心理改变。这种心理情感体验对IH的诊治带来众多的不便,更直接影响患儿的治疗选择,进而影响IH患儿的身心健康。本文将对目前IH对患儿及其家长心理影响情况进行综述,为临床IH的治疗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
1 IH对患儿家长的心理影响
IH对患儿家长心理的影响很早就有学者关注。LANSDOWN等[18]研究发现血管瘤婴儿出生后,家长们会出现类似焦虑、抑郁、失落、悲伤、失望和罪恶感等负性精神状态。DYTRYCH[19]和TYL[20]对100名IH患儿家长进行问卷式调查的结果同时也证实了这一点。并且由于认识不足等原因,有高达75%的家长表示IH患儿的出生对他们而言是一个“精神打击”,随之而来的就是以焦虑、沮丧、失落等为主的负性精神症状。令人吃惊的是有报道[21]中指出尼日利亚约80%的IH家庭把IH的出现归因于超自然现象或者是邪恶力量,其中有70%的家庭会因此而责备患儿的母亲,从而严重影响家庭和谐。KUNKEL EJ等[22]利用心理健康量表(MHI)调查IH患儿家长的心理状况,也发现家长存在焦虑、痛苦等心理。同时POPE[23]指出,在日常生活中患儿家长常常会因为被迫解释患儿畸形的原因加重自身的负性精神状态。ZWEEGERS[24]在研究中指出,尽管在多数IH家庭心理的研究中使用的调查工具缺少针对性、可能存在结果偏差,但与IH有关的社会心理问题确实存在,特别是IH患儿的父母。
国内对IH家庭心理的研究较国外晚,最早主要集中于临床护理工作者对患儿家长临床表现的描述,认为临床上IH患儿家长多存在焦虑、抑郁、愤怒、期望值过高等心理,并针对各种心理提出了相应的护理对策[25-27]。赵艳君[28-29]则是利用症状自评量表(SCL-9O)和自行设计的一般资料问卷对80名颜面部IH患儿家长的疾病认知和态度以及心理状况进行了调查,认为患儿家长对疾病认知较差,颜面部血管瘤患儿父母普遍存在焦虑和偏执的心理。颜光堂[21,30]则是用生活事件量表(LES)和焦虑自评量表(SAS)探索了IH患儿家长的心理状态,结果显示患儿家长对疾病认知较差,普遍存在一种负性精神状态,如偏执、焦虑等,并多数伴有轻重不一的躯体症状。彭威[31]结合临床病例和心理学知识自行研制了一种IH患儿家长心理状况评估问卷,并调查了323名IH患儿家长,结果显示IH患儿家长主要存在焦虑、抑郁、心理失衡、病耻感、疾病恐惧五方面的心理情感体验,其中以焦虑表现尤为突出。
总之,对于IH患儿家长心理的调查结果显示:部分IH患儿家长会出现焦虑、悲伤及抑郁等精神心理症状,有的甚至会出现负罪感[22,24,32-35]。随着血管瘤的病程变化和儿童的生长,患儿家长常常会因为被迫解释患儿畸形的原因而加重自身的负性精神状态[23]。致使有的父母会尽量避免带小孩出现在公众场所,尤其对学龄期儿童,家长会更加担心自己小孩受到歧视和异样的目光[22,24,32-34]。这不仅加重了家长们自身负性精神心理症状,甚至有部分家长会出现抱怨医生的情绪。因此在学龄前对IH进行彻底有效的治疗显得尤为重要[36]。
2 IH对患儿的心理影响
早在1992年,DIETERICH-MILLER等[32]利用自我意识测试(JPPST)及儿童行为量表(CBCL)比较正常儿童与IH患儿的心理行为,研究显示5岁以前的IH患儿与正常儿童心理行为并无明显差异,他认为可能与自我意识的形成有关。TANNER JL等[33]研究也发现四岁之前的IH患儿并不认为自己与常人有不同。IH患儿父母则表示,小孩在12~24月时会开始意识到IH,而到4~5岁才会感觉到与常人不同。近年也有研究[37]以《Achenbach儿童行为量表》测试2~3岁的IH患儿,发现与正常小孩没有明显区别也证实了这一点。研究者普遍认为IH患儿在5岁之前其心理状况与其他正常小孩没有明显差异,并且这个观点也得到大部分父母的认同,但同时家长们也迫切希望能够在早期将IH治愈。有研究者对27例口服普萘洛尔治疗的IH患儿进行问卷调查发现,7岁时患儿心理问题的风险并没有增加,但随着治疗时间延长,患儿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和执行功能缺陷均有影响[38]。但由于病例数较少,研究者也提出需进一步验证研究结果。
3 影响因素
关于IH患儿及其家长心理的影响因素,研究者普遍比较关注IH的部位、大小、并发症对IH患儿及其家长心理的影响[22-24]。但因各个研究所选择的调查方法并不一致,所得结果并不能完全相同。一项自制问卷的调查显示病灶的大小对IH患儿家长的心理影响具有显著差异,不同部位IH对患儿家长的影响没有显著性差异[22]。但在另一生活质量相关问卷调查[34]的研究中,发现病灶的大小与IH患儿家长的生活质量也有着紧密的联系。赵艳君[28-29]则是利用症状自评量表(SCL-9O)和自行设计的一般资料问卷对颜面部IH患儿家长的疾病认知和态度以及心理状况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颜面部血管瘤患儿父母存在焦虑和偏执的心理,且认为患儿家长认知和心理与其学历层次密切相关。彭威的研究中明确指出IH患儿家长心理状况的影响因素包括家长因素及患儿疾病因素两方面。其中,家长因素中包括家庭月收入差异及文化水平差异;患儿疾病因素分别为患病时间、瘤体大小、有无并发症、单发或多发、是否治疗[31]等。该研究综合了患儿家庭一般情况,以及患儿疾病的相关情况,较为准确、细致的分析了IH患儿家长的心理状况影响因素。另外有研究表明,IH不仅能对儿童及其家人造成身体上的痛苦和情感上的担忧,而且这些最终都会影响到IH家庭的生活质量(quality of life,QOL)。并且有研究者利用多种生活质量量表,对217名2岁以下的IH患儿家庭进行问卷调查,结果显示IH对年轻患者及其父母的生活质量均有一定的影响。而且研究者发现儿童的年龄、血管瘤的位置和大小,以及父母的教育水平是影响患者及其父母生活质量的重要危险因素[39]。同时一项有趣的研究[35]发现68%的父母在试图画出小孩IH大小时,会高估IH的大小,病灶尺寸越大,家长心理压力表现得越明显。在众多关于IH并发症的研究中都揭示了出现并发症之后,IH家庭的心理状况会更糟糕,甚至产生绝望的念头[22,34-35]。
4 问题与展望
随着社会-心理医疗的模式的推行,IH的治疗不仅仅是单纯的药物或手术切除等治疗,还应该是涉及多学科、美容、精神心理的综合治疗。因此了解IH对患儿及其家长的心理影响显得尤为重要。目前虽不乏对IH家庭心理状况的研究,但仍然存在一些缺陷:①因为缺乏针对IH家庭心理的调查工具,各个研究使用的调查工具五花八门,国内运用的有症状自评量表(SCL-9O)[28-29]、生活事件量表(LES)、焦虑自评量表(SAS)[21,30]等,国外的有心理健康量表(MHI)[22]、自我意识测试(JPPST)、儿童行为量表(CBCL)[32]、健康相关生活质量量表(TAPQoL)[34]等,不同的调查工具导致调查结果也不尽相同、差强人意。所幸近年也有学者注意到这点,陆续有关于适合IH家庭调查工具的报道,如血管瘤家庭生活压力量表(Hamangioma family burden,HFB)[36]以及IH生活质量量表(Infantile Hemangioma Quality-of-Life,IH-QoL)[15]。②目前关于IH家庭心理状况的研究普遍存在被试数量较少的情况,缺乏大数据、多被试的调查研究,使得调查结果存在较大的系统误差,甚至因为自愿参与原则,可能出现选择偏移的情况。③因为家长们更便于沟通,研究多集中在IH对于家长心理影响的研究,对于IH患儿的心理影响则相对较少,长期、动态的IH患儿心理研究尤其缺乏。④研究多仅仅针对IH患儿及其家长精神心理的状况,较少涉及影响因素的研究,也鲜有研究提出了专业、可行的、适用于临床的干预意见。
在IH的研究中,对IH患儿及其家长心理的研究逐渐受到广泛关注。在IH的发生、发展和治疗过程中患儿和家长可能会出现复杂的精神心理改变。这种复杂的精神体验不仅仅阻碍医患之间的沟通及家长们对IH的理解,更直接影响着患儿家长对IH的治疗选择。因此,笔者也呼吁同行们重视IH家庭的心理状况,努力改善IH医患之间的沟通,不断优化IH的治疗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