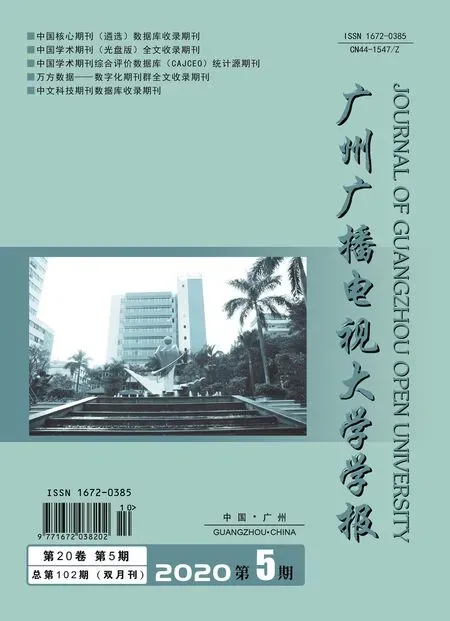穷困抗辩权实务问题研究
——论《合同法》第195条性质及构成要件分析
2020-03-02张菲菲
张菲菲
(华东政法大学 法律学院,上海 200042)
一、问题的提出
(一)引言
《合同法》第一百九十五条规定:赠与人的经济状况显著恶化,严重影响其生产经营或者家庭生活的,可以不再履行赠与义务。该条款关于赠与人可不履行赠与义务的规定,亦是我国立法上关于穷困抗辩权适用之规定。①关于穷困抗辩权在司法实务中的适用问题,各地法院的裁判标准不一,理论界也颇有分歧,主要体现在对穷困抗辩权的定性与构成要件两个方面。具体而言,其一,穷困抗辩权的性质问题仍莫衷一是,其素有解除权与抗辩权之争,亦有学者提出其应定性为赠与义务的免除;其二,穷困抗辩权的诸多适用问题尚不明确。如经济状况显著恶化事实本身应如何具体认定;经济状况显著恶化事实发生于合同订立前应如何处理;赠与人主张穷困抗辩权后,受赠人对已履行部分是否负返还义务;当赠与人经济状况好转时,受赠人可否主张继续等。针对以上两个问题,笔者将以“李如赠与合同纠纷案”为案例引入,以赠与合同基础理论为核心,通过现有学说综述与司法实务操作对上述问题予以解决。
(二)案情概要
1996年5月8日,赠与人李如将其名下房产赠与其祖孙曾远洲及曾志强。1996年5月10日,当事人双方办理了公证手续,但尚未办理过户登记。2012年10月24日,因赠与人李如称其年迈无劳动能力,生活困难无社会保障,故诉至法院请求解除该赠与合同。2013年1月5日,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原告李如的诉讼请求。法院认为,赠与人李如在赠与合同订立之前其经济状况既已恶化,不得依据《合同法》第195条主张解除赠与合同。赠与人李如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中级人民法院。二审法院依法驳回李如的诉讼请求,其认为:其一,《合同法》第195条并非关于法定解除权之规定,而系合同权利义务终止的一种情形,具体而言即免除;其二,依据《合同法》第186条之规定,在受赠财产的所有权移转之前,赠与人不得撤销已经公证的赠与合同。在二审法院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后,赠与人李如遂申请再审。2017年2月1日,再审法院认为赠与人的再审请求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之规定,故作出驳回李如再审申请的民事裁定。②
(三)论证思路
综上所述,该案争议焦点之一系赠与人可否依据《合同法》第195条对抗受赠人的请求权、免除赠与义务抑或解除赠与合同,也即《合同法》第195条应定性为抗辩权、解除权抑或赠与义务的法定免除。该案所涉法律问题之二系穷困抗辩权的适用问题,也即穷困抗辩权的构成要件问题。笔者认为,其一,穷困抗辩权应定性为抗辩权,进一步而言,应定性为一时之抗辩权;其二,穷困抗辩权的构成要件应包含如下内容:一是存在财产状况严重恶化事实,二是财产状况严重恶化事实应发生于赠与合同成立后且尚未履行前,三是须严重影响生产经营或者家庭生活。
就穷困抗辩权的定性问题,笔者将通过梳理分析解除权说、免除说、抗辩权说,其中抗辩权说又细分为一时抗辩权说与永久抗辩权说,通过历史沿革考察得出解除权说系因深受比较法三大立法例的影响而提出,其本身并无系统论述内容做支撑;并结合赠与合同基础根基在于情谊,驳斥过度保护赠与人的永久抗辩权说与免除说。就穷困抗辩权的要件建构问题,笔者将结合理论与实务,对经济恶化事由是否应当限于合同成立后履行前,穷困抗辩权的适用范畴是否应限于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以及经过公证的三项赠与合同、对经济状况显著恶化的事实如何认定等问题一一作出回答。
二、穷困抗辩权定性之争
(一)学说观点综述
就穷困抗辩权的本质问题,学术界存在三种学说:第一,将其定性为解除权。[1]持此观点的学者认为,《合同法》第195条应定性为法定解除权,其所称“不再履行”意指赠与义务的消灭。同时,因为赠与合同原则上系一时性合同,故合同解除的法律效力不及于已经移转所有权的财产,即赠与人对已交付财产不得享有返还请求权。但是,一是该学说属于早期的学者观点,并且仍欠缺比较详实具体的论证过程;二是在司法实务中,一般也认为《合同法》第195条所意指的合同义务“不再履行”并非合同解除。③
第二,将其定性为履行抗辩权。[2]第二种学说下存在两种对于穷困抗辩权定性的细分:其一,定性为永久之抗辩权;其二,定性为一时之抗辩权。[3]换言之,法条所谓的“不再履行”是指一时的不履行抑或永久的不履行。有学者认为,因学者普遍将《合同法》第195条之情形归类为“赠与合同的终止”,所以应将穷困抗辩权定性为永久之抗辩权。[4]但是,笔者持相反观点,认为《合同法》第195条应当定性为一时抗辩权,论证过程见小结部分。
第三,将其定性为赠与义务的法定免除。[5]第三种学说认为,《合同法》第195条规定的“不再履行”实质上意味着赠与义务本身的消灭,故应将其定性为免除。第三种学说的支撑理由如下:其一,若将穷困抗辩权定性为抗辩权,则当赠与人的财产状况发生良性转变时,赠与人此后是否继续履行合同义务或成难题。因为抗辩权制度在本质上是针对请求权的一时应对之举,而非终局彻底的解决措施。其二,若将穷困抗辩权定性为解除权,因为赠与合同系一时性合同,故当赠与合同被解除时,其具有溯及已履行赠与部分的效力。而对《合同法》第195条进行文义解释,无法得出赠与人得以诉请已履行部分的返还,故两者自相矛盾。其三,若将穷困抗辩权定性为解除权,但解除行为系积极行为,而《合同法》第195条对此未予规定,也无从推知。其四,该条规定与免除存在诸多共通之处:一是穷困抗辩权与免除均针对未履行的义务,且无溯及力;二是免除系终局的解决措施,符合《合同法》第195条的立法意旨;三是法定免除无需赠与人为积极行为,亦符合《合同法》第195条之规定。[6]
(二)历史沿革考察
国内学者的解除权、辩论权以及赠与义务的免除之争,实际上深受域外三大立法例的影响。[7]通过比较法规则的考察,在赠与人经济状况显著恶化情形下,存在三个方面涉赠与人合同义务的立法例:首先,在赠与人经济显著恶化之后,赠与人得以行使抗辩权对抗受赠人的合同履行请求权的抗辩权模式。德国民法、俄罗斯民法以及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等均采取此种模式的立法例,立法可见于《德国民法典》第519条第1项规定、《俄罗斯民法》第577条第1项规定以及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418条规定。④其次,将赠与人因困于经济显著恶化而无力履行赠与义务的情形规定为法定撤销权的行使事由,使得合同效力归于消灭的撤销权模式。瑞士债务法和西班牙民法采取赋予撤销权模式的立法例,立法可见于《瑞士债务法》第250条第1项规定以及《西班牙民法》第644条之规定。⑤最后,将赠与人于经济状况显著恶化并无力履行赠与义务的情形规定为行使解除权的法定事由,解除赠与合同效力的解除权模式。韩国民法典采取此种模式的立法例,立法可见于《韩国民法典》第557条之规定。⑥
显而易见,关于穷困抗辩权性质的争辩,国内学者的观点不同程度地受到了比较法规则的影响。但也正是因为这一影响,导致了在穷困抗辩权的性质之争中忽视了对赠与合同基础理论的关注。加之,对《合同法》第195条进行解释,无法得出该条系撤销权的结论。所以,在前述两者的结合之下,在穷困抗辩权定性的早期之争主要集中于抗辩权与解除权之间。近年来,随着研究的深入,诸多学者普遍倾向于将穷困抗辩权定性为抗辩权。但仍未明确其为一时之抗辩权抑或永久之抗辩权,这也是深受比较法规则影响而忽视对赠与合同基础理论的结果。另外,亦有学者力排众议否定了抗辩权与解除权之争,提出穷困抗辩权系赠与义务的免除的新观点。综上所述,通过梳理此问题的研究脉络,目前,争论之焦点仍限于抗辩说内部对抗,以及抗辩说与新学说免除说之间。
(三)小结
就抗辩说与免除说而言,笔者认为,免除说系于永久抗辩权说基础上过度强化了对赠与人的保护,《合同法》第195条应当定性为一时之抗辩权。具体而言,其一,从法律适用来说,免除本质上系形成权,亦是构成主张永久抗辩权之情形。两者在法律适用的最终结果上并无差异,其本质差别在于实现结果之手段。具体而言,免除说系通过直接否决请求权本身之存在而实现阻却受赠人债权请求权的目标,而永久抗辩权说系通过不否定请求权本身存在,以永久的对抗权以实现同一目标。其二,从立法意旨来说,《合同法》第195条本意在于一定条件下对抗受赠人之请求权实现,救赠与人于水火之中。[8]而相比永久抗辩权的被动性、防御性,形成权具有主动性、攻击性,对于法律关系的影响是终局性,乃至毁灭性的。因此,定性为免除,则存在对赠与人保护过度、顾此失彼、破坏法益均衡之虞。其三,从赠与之根基来说,如前文所述,免除说实际上建立在法律对赠与合同关系“横加干涉”的假设下,而赠与合同以赠与双方之间的情谊为产生根基,《合同法》第195条之适用情形并未使得赠与关系的根基丧失,法律自不必多加干预。
就抗辩说的内部对抗而言,笔者认为,穷困抗辩权应当定性为一时之抗辩权。究其原因:其一,从立法意旨来说,结合前述《合同法》第195条之规范目的,因赠与合同法律关系依旧存续,在赠与人不良经济状态消灭后,若赠与人拒绝履行合同义务则违背上述立法目的。[9]其二,从法益平衡的角度来看,此时受赠财产所有权尚未完全变动,赠与人仍有行使任意撤销权之余地。由此可见,法律对赠与人的保护足矣,则不必使得全部的法律关系土崩瓦解。其三,如前文所述,赠与合同基于情谊而产生,《合同法》第195条之适用情形并未使得赠与关系之根基丧失。定性为一时抗辩权,则因一时困难生活难以为继且无意撤销赠与的赠与人,在其经济状况恢复时再行履行的情形留下空间。[10]其四,从文义解释来说,“可不履行”的表述方式,既推断不出消灭赠与合同法律关系的结论,也为赠与人恢复经济能力后,受赠人再次请求履行赠与义务留下余地。
三、穷困抗辩权要件构建
(一)合同成立后且未曾履行前
一方面,构建穷困抗辩权以赠与合同依法成立生效为基础;另一方面,穷困抗辩权的构成要求财产状况严重恶化的事由须介于合同成立后且未曾履行前。然而,就经济恶化事由是否限于合同成立后履行前的问题,在学界颇有争议。有学者主张,穷困抗辩权制度的设立要旨在于先己后人,若赠与人财产状况已然恶化,则不应使赠与人陷于更为困窘的境地。[11]另外,就此种情形下是否存在赠与合同履行基础而言,持相反观点的学者则认为,正因赠与合同建立在赠与人的财产状况早已恶化的基础上,根据意思自治原则,即使赠与合同订立前财产状况已然恶化,赠与人也仍应履行赠与义务。[12]
笔者认为,赠与人财产状况严重恶化事由所发生的时间点须介于合同成立后且未曾履行前。首先,从赠与合同的基础理论来说,若赠与人本身财产状况早已恶化、无暇顾及自己,却仍赠与他人财产。本质上其并非基于情谊而为赠与之意思,赠与合同法律关系成立之根基亦不成立,故财产状况恶化的事由应限于发生在赠与合同成立之后。其次,从前文所述的穷困抗辩权系一时之抗辩权的结论着手,仅当受赠人向赠与人提出请求履行赠与义务的主张时,赠与人方得提出穷困抗辩权。因此,当合同履行完毕后,请求权已随之不存在,即使此时赠与人符合《合同法》第195条的其它要求,亦不能主张穷困抗辩权,故财产状况恶化的事由亦应限于尚未履行之前。[13]此外,在司法实务中对穷困抗辩权这一构成要件的释法说理鲜少有之,却也普遍认可这一构成要件。⑦最后,从司法实务来说,倘若赠与人于赠与义务履行后再行主张穷困抗辩权,则存在受赠财产已然消耗、受赠人因返还赠与财产而致穷困的操作难题。[14]进一步而言,亦有悖于公平原则与物权秩序的稳定。
(二)经济状况显著恶化的认定
穷困抗辩权的构成要件要求客观上须有赠与人经济状况显著恶化的事实。有学者主张,除赠与人恶意致其陷入经济状况显著恶化的情形外,原则上无需过问经济状况显著恶化发生的原因。[15]那么,因履行赠与合同本身所导致的经济状况显著恶化是否可以援引《合同法》第195条主张穷困抗辩呢?笔者对此持有异议,原因在于:其一,从赠与合同的基础理论来说,赠与建立在情谊之上,提倡济危扶困,而因履行赠与义务而致自身陷于危困有违赠与之精神;其二,从实务角度来说,在司法裁判中存在相当部分的判决也采纳了此种观点,认为经济状况显著恶化的事由不应包含因履行赠与合同所致。⑧有学者主张,如住所改变、年龄增加并非经济状况的恶化,自然也不构成经济状况显著恶化的事实。[16]
笔者认为,该观点具有一定合理性,但是仍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虽然住所改变、年龄增加本身并非直接关乎经济事实,却能够对经济状况产生一定影响,在司法裁量时也应当作为认定经济状况显著恶化事实的影响因素纳入考量。亦有学者主张,经济状况显著恶化的认定事实应包括消极支付的增加,例如,因结婚生育、收养子女使得子女增加而致负担增加的情形。[17]与此相呼应的,在司法实务中,有裁判认为:再婚并育有一女的事实并不足以证明赠与人存在经济状况显著恶化的事实。⑨
总的来说,主张穷困抗辩权所需的经济状况显著恶化的事实认定标准尚未统一。但是,通过检索现有司法裁判,笔者总结得出认可属于《合同法》第195条经济状况显著恶化的事实,至少存在以下三种情形:一是自然人赠与人患重大疾病而入不敷出;⑩二是自然人赠与人无生活来源,继续履行将严重影响其家庭生活;⑪三是法人赠与人无财产可供强制执行,严重影响其生产经营。⑫
(三)严重影响生产经营或家庭生活
严重影响家庭生活以及严重影响生产经营系并排平列的两个条件,仅具备两者之一即构成穷困抗辩权的成立要件。此外,经济状况显著恶化的状况须达一定程度,也即是若仅为财产状态呈现轻微不良,则不构成主张穷困抗辩权所需具备的要件。而对于“严重影响”的判断,应以客观标准判定,并以赠与人原有生产经营状况或者原有家庭生活情形为参照标准。[18]
理论上认为,对于严重影响生产经营的认定应限于:仅当法人赠与人须将受赠财产投入日常运营才足以保证正常经营时,才得以认定严重影响生产经营。而对于严重影响家庭生活的认定,则应限于:仅当自然人赠与人因财产状况显著恶化,生活开支无以为继或者不能履行法律上的抚养义务时,才得以认定严重影响家庭生活。[19]对于严重影响家庭生活认定的学者观点,实际上借鉴了《德国民法典》第528条第1款规定。⑬但是,因为立法上并不存在具体适用规则抑或适用情形类型化,以上参照标准仍无法在司法实务中得到有效适用。
实际上,无论是理论学说还是在司法实务中,就经济状况显著恶化的程度也未达成明确具体的规则标准。如在“杨军赠与合同纠纷案”中,⑭赠与人杨军失业且身负几十万的银行贷款,仅剩讼争房产暂时容身,但法院对赠与人的经济状况显著恶化,严重影响家庭生活的情形未予认定;而在“张某、李某离婚后财产纠纷案”中,⑮赠与人李某仅有讼争房屋可供居住,其本身无固定工作,缺乏稳定收入,法院却对其经济状况显著恶化,严重影响家庭生活的情形予以认定。因此,该问题仍有待进一步研究。
(四)其它构成要件
有学者认为,仅在社会公益性质的赠与合同、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以及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等三项中,才可行使穷困抗辩权。[20]首先,在赠与合同成立之后且赠与财产尚未移转之前,即使不符合穷困抗辩权的其它适用要件,赠与人也可依法行使任意撤销权。其次,赠与人之撤销权的行使会使得赠与法律关系归于消灭,对于该法律问题的处理是终局性的,有效地避免了赠与合同履行后经济状况好转时是否需要继续履行问题的观点分歧。最后,持此观点的学者认为,仅当赠与人无法行使任意撤销权时,方得行使穷困抗辩权。故符合前述要求下,其适用范围则被限缩为前述三项赠与合同。因为在此三项赠与合同中,除非符合行使法定撤销权的事由,赠与人原则上必须依法履行赠与义务。[21]因此,持相反观点的学者则认为,若仅适用于上述三项赠与合同,对穷困抗辩权的行使将受到极大限缩,故穷困抗辩权之适用范围不应限于上述三项赠与合同。
笔者倾向于支持否定说的观点,认为穷困抗辩权的适用不应限于前述三项赠与合同。原因在于:其一,从文义解释来说,立法未明确限缩穷困抗辩权的适用范围,从字面解释也无法得出此种含义。其二,从立法功能来说,穷困抗辩权系一时之抗辩权,而撤销权系形成权,究其两者不同既已论述,此处不做赘述。就一时无法履行而意欲嗣后履行抑或直接消灭赠与法律关系,赠与人有其选择之空间。若限于前述三项赠与合同,实际上剥夺了其它赠与情形下的选择自由,有过度干涉赠与关系成立之“情谊”。其三,是否将穷困抗辩权限在前述三项赠与合同的范围之内,至少在司法适用层面上尚无争议之必要。因为在涉及穷困抗辩权的司法裁判中,赠与人通常既主张任意撤销权,又主张穷困抗辩权,而在实际操作中因赠与人经济状况显著恶化事实缺乏类型化认定,严重影响其家庭生活或生产经营的具体标准尚待明确,故多数法院倾向于依照任意撤销之规定使得赠与人免于给付义务的履行。
四、穷困抗辩权行使及法律效果
(一)行使方式
首先,对于穷困抗辩权的行使,赠与人可以口头形式为之,亦可以书面形式为之,还可以于诉讼中作为抗辩事由提出,但是在审判中至少不应迟于诉讼辩论终结前主张此权利。其次,因穷困抗辩权系一时抗辩权,而抗辩权具有被动性、防御性的特征,因此,当受赠财产尚未移转且受赠人未请求赠与人履行赠与义务时,赠与人自然亦无必要行使穷困抗辩权。[22]最后,因其抗辩权的性质,法院不得依职权主动援用,仅赠与人主张时才可发生法律效力。同时,赠与人亦不得预先抛弃。
(二)可不履行赠与义务
依据《合同法》第195条之内容,赠与人权利主张的法律效果系赠与义务可不履行。然而,有学者认为,赠与义务可不履行实际上意味着赠与义务已然消灭。[23]但是,笔者认为,穷困抗辩系一时之抗辩权,而一时抗辩权能够产生的法律效果仅是针对请求权的行使而产生一时阻碍的效力。同时,在法律适用上,穷困抗辩权如前述仅针对尚未履行的部分,不溯及既往。[24]另外,对于已经履行的部分,则须借助赠与合同的法定撤销权予以救济。
关于赠与人经济状况恢复时,是否需要继续履行赠与义务的处理。如前文所述,穷困抗辩权性质上系一时抗辩权,仅具有延期给付的效力。因此,赠与人于此后经济状况恢复时,受赠人仍可享有债权请求权,赠与合同仍然合法有效,赠与人也应依法履行合同义务。究其原因,前文已阐释,此处不作赘述。需要注意的是,因此时赠与财产所有权尚未移转,赠与人亦享有任意撤销权。
五、结论
结合“李如赠与合同纠纷案”而言,笔者认为:首先,因为穷困抗辩权系一时抗辩权,并非解除权抑或永久抗辩权,故赠与人李如不得依据《合同法》第195条主张解除赠与合同或赠与义务的免除。其次,穷困抗辩权的适用范围不受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所限。因此,虽然经过公证的赠予合同在受赠财产所有权移转之前不得撤销,且该案赠与人在诉至法院时仍未履行,仍可依据《合同法》第195条行使穷困抗辩权主张不履行赠与义务。最后,即使对本案赠与人李如的经济状况恶化事实暂搁置争议,但该事实也因发生于合同成立生效之前,此时法律关系尚未成立,亦无请求权之存在,更不必言及抗辩权。实际上,本案赠与合同具有遗赠抚养性质,最终驳回赠与人李如的诉请,实质上是立足于受赠人依法履行了赡养义务,且赠与人并非陷于经济恶化严重影响其家庭生活。
综上所述,首先,在穷困抗辩权的定性问题上,其应定性为抗辩权,具体而言系一时抗辩权。其次,在穷困抗辩权适用问题上,适用条件系经济状况显著恶化的事实应当发生于赠与合同成立后且尚未履行前,且须严重影响法人赠与人之生产经营抑或自然人赠与人的家庭生活。再次,关于经济状况严重恶化事实的认定问题,在司法实务中至少可细化为三类情形:一是自然人赠与人患重大疾病而入不敷出;二是自然人赠与人无生活来源,继续履行将严重影响其家庭生活;三是法人赠与人无财产可供强制执行,严重影响其生产经营。然后,关于严重影响赠与人的生产经营或家庭生活的认定问题,目前,仍系审判者自由裁量范围内,有待进一步研究。最后,当赠与人经济好转时,受赠人仍可享有债权请求权,赠与合同仍然合法有效。赠与人也负有赠与义务,只是在财产所有权尚未移转前,其亦享有任意撤销权。
注释:
① 所谓穷困抗辩权,或称紧急需要抗辩权、拒绝赠与抗辩权或赠与履行拒绝权,是指赠与人与受赠人在签订赠与合同后,因赠与人一方的经济状况显著恶化,若继续履行会造成赠与人一方的生产经营或家庭生活受到严重影响,则赠与人有权拒绝履行其赠与义务。参见王利明.合同法研究(第三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227。
② 参见“李如赠与合同纠纷案”,(2012)深龙法地民初字第111号民事判决书、(2016)粤03民终13119号民事裁定书、(2013)深中法民终字第698号民事判决书等。
③ 参见“李如赠与合同纠纷案”,(2016)粤民申7989号民事裁定书;“申诉人单某与被申诉人单某4、单某5赠与合同纠纷案”,(2015)辽审一民抗字第69号民事裁定书;“李建新与李海鸣等赠与合同纠纷案”,(2019)鲁01民终3058号民事判决书;“黄×与郝×赠与合同纠纷案”,(2015)一中民终字第04509号民事判决书等。
④《德国民法典》第519条第1项规定:只要赠与人在考虑到自己的其他义务时,不危及其适当生计或依法律规定担负的抚养义务就不能履行赠与约定,赠与人即有权拒绝履行以赠与方式做出的约定。《俄罗斯民法》第577条第1项规定:如果在合同签订后赠与人的财产状况、家庭状况或者健康状况发生变化,致使新的条件下履行合同会导致其生活水平实质性的降低时,赠与人有权拒绝履行含有允诺于将来项受赠人移转财产、权利或者解除受赠人财产性义务的合同。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418条规定:赠与人于赠与约定后,其经济状况显有变更,如因赠与致其生计有重大影响,或防碍其扶养义务之履行者,得拒绝赠与之履行。参见《德国民法典》(第三版),陈卫佐,译注.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182。
⑤《瑞士债务法》第250条第1项规定:在赠与约定,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赠与人得撤销其并拒绝履行:一、……;二、赠与人在作出赠与约定后财产状况发生显著变化,以至于赠与成为其重大负担者;三、赠与人在作出赠与约定后需承担此前并不存在的亲属法上的义务,或者亲属法上之义务在作出赠与约定后明显加重者。再如,《西班牙民法》第644条规定:无子女、直系卑亲属或合法之夫妻关系而生存之赠与人及受赠人间所为之一切赠与,有下列情形时得撤销之:(一)赠与后,因赠与人有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或遗腹子女时;(二)当为赠与时,推定赠与人之子女已死亡,但赠与后,其子女尚生存时。参见《瑞士债务法》,戴永盛,译注.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6:79-80;易军.撤销权、抗辩权抑或解除权?——探析《合同法》第195条所定权利的性质[J].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3(5):16。
⑥ 《韩国民法典》第557条规定:订立赠与契约后,赠与人的财产状况发生明显变化,且履行赠与将对赠与人的生计产生重大影响的,赠与人可以解除赠与。参见《韩国最新民法典》,崔吉子,译注.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185。
⑦ 参见“陈莲燕、杨满兴赠与合同纠纷案”,(2017)粤01民终14289号民事判决书;“申诉人单某与被申诉人单某4、单某5赠与合同纠纷案”,(2015)辽审一民抗字第69号民事裁定书;“汪大中与金晖赠与合同纠纷案”,(2015)苏审二民申字第01036号民事判决书;“李如赠与合同纠纷案”,(2016)粤民申7989号民事裁定书等。
⑧ 裁判理由认为经济状况显著恶化不应理解为系因履行赠与合同所导致的案件,如“申诉人单某与被申诉人单某4、单某5赠与合同纠纷案”,(2015)辽审一民抗字第69号民事裁定书;“汪大中与金晖赠与合同纠纷案”,(2015)苏审二民申字第01036号民事判决书。
⑨ 参见“莫济帆与莫红、李世红不当得利纠纷案”,(2018)豫1103民初2094号民事判决书。
⑩ 参见“孙新平与周蓉赠与合同纠纷案”,(2013)海中法民提字第2号民事裁定书;“莫济帆与莫红、李世红不当得利纠纷案”,(2018)豫1103民初2094号民事判决书;“王立颖、高树娟赠与合同纠纷案”,(2019)津民申168号民事裁定书;“苏阳鑫与黎奇海赠与合同纠纷案”,(2015)桂民申字第1615号民事裁定书;“孙新平与周蓉赠与合同纠纷案”,(2013)海中法民提字第2号民事裁定书等。
⑪ 参见“李强、李秀岭赠与合同纠纷案”,(2019)鲁03民申4号民事裁定书;“张某、李某离婚后财产纠纷案”,(2017)鄂民申2216号民事裁定书。
⑫ 参见“中华儿童文化艺术促进会与曹洪涛等公益事业捐赠合同纠纷案”,(2018)京03民终12821号判决书。
⑬ 《德国民法典》第528条第1款规定:只要赠与人在执行赠与后不能维持其适当生计,且不能履行其对血亲、配偶、同性生活伴侣或原配偶、原同性生活伴侣在法律上所负担的抚养义务,赠与人就可以依关于返还不当得利的规定向受赠人请求返还所赠与的财产。
⑭ 参见“杨军赠与合同纠纷案”,(2017)闽民申610号民事裁定书。一审期间赠与人杨军也向法院提交了失业、租房的证据,但都没有被采纳。而再审法院审理认为,杨军虽主张赠与合同已经造成了生活困难,没有能力继续履行赠与义务,但未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
⑮ 参见“张某、李某离婚后财产纠纷案”,(2017)鄂民申2216号民事裁定书。再审法院认为,李某目前患病,无固定工作,无稳定经济收入来源,生活困难,且本案所涉房屋外,其名下无房可住,因此,原判决支持李某要求确认其对涉诉房屋的所有权的主张并无不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