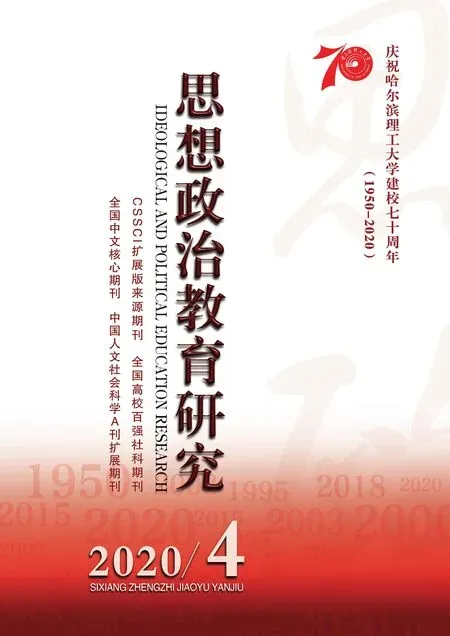先秦儒家德育主体性思想的逻辑理路
2020-02-25于欣
于 欣
(聊城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 聊城 252000)
先秦儒家德育传统中虽没有明确的“主体性”概念,却潜藏着丰富而深厚的主体性思想意蕴。在先秦儒家看来,人是自我思想建构和道德成就的主体,进而也是德育活动的主体。那么,先秦儒家的德育主体性思想究竟如何得以确立?本文力求梳理和探究其中的逻辑理路,以期对深入理解先秦儒家德育主体性思想内涵及发掘其现代价值有所裨益。
一、由“礼”而“仁”——开启内求“礼乐之原”的致思取向
先秦儒家用以表示主体的名词是“己”“我”。“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作为儒家学说的创始人,孔子基于对动荡社会现实的深刻反思,力求重振西周礼乐传统的权威与活力,为此而内求“礼乐之原”,开启了先秦儒家德育主体性思想形成的逻辑理路。孔子之前,对“礼乐之原”的传统解释是外求于天,强调“礼以顺天”(《左传·文公十五年》),“礼”是“天之经”“地之义”。孔子则在继承周人重德之人文精神的基础上开启了向内发掘的致思取向,着眼于人自身以探求礼乐道德之基,最终找到了“仁”。“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论语·阳货》)“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礼”的根本与实质不在于表现于外的各种礼仪规范,而在于人自身之“仁”。如果一个人没有“仁”,那么再周全的礼仪也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孔子以“仁”释“礼”,将“仁”视为“礼”的精神实质和内在根据,这正是孔子最伟大的贡献所在。
那么,作为“礼”之实质和根本的“仁”究竟是什么呢?在《论语》中,孔子大都将“仁”作为做人的标准或理想人格的基本特征来使用,以说明人“应该是怎样的”“应该做什么”。就“仁”的具体内涵来说,可以区分为狭义之“仁”和广义之“仁”。狭义之“仁”即“爱人”。“仁”是一种在处理人际关系时与人为善的“爱人”之心,这是“仁”最本质的内涵。“爱人”的基本原则是“忠恕”。《论语·里仁》记载曾参将孔子一以贯之之道概括为“忠恕”。通常认为,“忠”是从积极方面讲“爱人”,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 雍也》),要求每个人在追求己之“欲立”“欲达”的同时,也应充分尊重他人之的“欲立”“欲达”,并尽己之力帮助他人之“立”“达”;“恕”是从消极方面讲“爱人”,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强调不要把己之“不欲”强加于人。“忠恕”之道涉及“欲”“己”“人”,其实质在于协调人与人之间在实现自身欲求过程中的相互关系。“爱人”之心落实为“忠恕之道”,体现了“仁”尊重协调己欲和他欲及其相互关系的社会伦理本质。
广义之“仁”是各种美德的集合体。仁爱之心经由“忠恕之道”落实到人伦日用的方方面面,就呈现为各种美德。“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孝悌之德是“仁”在血缘人伦中的体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论语·子路》)“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论语·里仁》)“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论语·阳货》)恭、敬、忠、知、宽、信、敏、惠等德行是“仁”在社会人伦中的体现。“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 学而》)是“仁”在治国安民社会实践中的体现。“刚、毅、木、讷,近仁。”(《论语·子路》)刚、毅、木、讷之德是“仁”在人之言谈举止上的体现。此外,“仁者必有勇”“仁者不忧”“仁者乐山”“仁者静”“仁者寿”等诸多论述则是说明“仁”在人的心理、情感上的体现。在此,孔子围绕着“仁”构建起了一个道德范畴体系,“既包括有人的认知心理、语言仪表、道德感情、行为动机等主观因素,也包含有人的道德行为的客观因素,从不同的侧面反映着‘仁’的丰富的社会内容”[1]。
孔子由“礼”而“仁”,在对传统礼文进行反思的基础上发现并提倡“仁”, 这并不是对于“礼”的否定,而是为“礼”寻找存在的理由和根据,以便提高“礼”的有效性,使人们自觉遵守社会规范,达到“仁”(价值)与“礼”(规范)的统一[2]。正是通过“仁”的发现,才开启了人作为道德主体、成德主体的自觉挺立之路。从个体道德发展的角度看,这个过程即是从被动地遵守规则向自觉按照价值规范行事的迈进。在此之前,“礼”是天之经、地之义,人们对“礼”的遵从是被动的他律行为,要么迫于“天”的权威,要么迫于自身的功利性诉求。而“仁”一经发现,“礼”的根据便不仅外在于“天”,而且更内在于人之“仁”,人对“礼”的遵从成为了基于自身仁德的自觉主动的自律行为。在由“礼”而“仁”、由他律走向自律的过程中,人的道德主体意识得以凸显,道德责任感得以增强,对“礼”的遵循也因此而更加有效。
二、由仁而性——内求仁义道德的人性根基
孔子由“礼”而“仁”,开启了向人自身探求“礼乐之原”的努力方向。那么,“仁”又如何可能呢?其根源又何在呢?先秦儒家进一步由“仁”而“性”,将内求成德之基的努力引向了对人性的探究。
孔子罕言性与天道,在《论语》中只有《阳货》篇谈及“性相近,习相远”。在此,“性”“习”相对,“习”是后天的见习修为,那么“性”显然指先天、自然。可见,孔子论“性”延续了“生之谓性”的传统,主要是从范围上肯定了“性”即自然本性,但这种自然本性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其善恶评价如何,孔子在此并无明确解说。即便如此,孔子在发现“仁”的基础上,也已经开始了进一步探求仁德与人的自然本性之间联系的努力,并肯定了人的自然质朴本性在德性人格成就中的基础性地位。这主要体现在其尚质、重情的思想主张上。“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质即人的自然素质,文即包括礼乐在内的人文。质是文的基础,文是质的升华。质文统一的德性人格相对于质朴自然本性来说,不是完全的背离和否定,而是辩证的扬弃与升华。所谓“绘事后素”,人先天的自然素质构成了后天“文之以礼乐”以“成仁”的前提和基础。孔子所谓的“质”、自然素质具体主要是指基于血缘关系的亲亲之情。正是这种自然流露的真情实感构成了道德礼文的根基。《论语·阳货》记载了宰我对“三年之丧”的传统礼仪提出质疑,想改丧期为一年。这种修改合不合适呢?孔子将此问题归之于内心的亲亲之情。“食夫稻,衣夫锦,于女安乎?”“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显然,这里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丧期的长短,而在于亲亲之情的厚薄。“三年”不是一个抽象的数字,它代表着父母子女之间浓厚的亲情爱意,减一分则不足以表达这份自然亲情,从而心怀内疚而不安。“礼之本”即在于内心的真情实感,所以孔子讲“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论语·八佾》)
孔子的弟子和后学们在孔子文质合一的思想基础上,进一步探索了礼义仁德的人性论基础。郭店儒简《五行》篇对“仁义礼智”等德目进行了“形于内”和“不形于内”的区分,强调“形于内谓之德之行,不形于内谓之行”[3],认为只有内得于己、扎根于内心的仁义礼智,才能称之为“德之行”,才是真正的“德”;否则就只能称之为“行”。《性自命出》篇明确将“仁”与“性”联系起来。“仁,性之方也,性或生之。”“仁”来自于“性”,“性”以“仁”为用。“爱类七,唯性爱为近仁。”[4]出自于人之自然本性的“爱”最接近“仁”。“道始于情,情生于性。”[5]仁义道德是基于人的自然情性而形成的。《六德》篇也强调“仁,内也;义,外也。”[6]“仁”的依据是内在于人的。这表明郭店儒简的作者继续了孔子向内发掘的努力,虽然其“仁内义外”说因太过于强调仁义之别而把“义”归之于外,但毕竟有了仁“形于内”的自觉,逐渐明确了“仁”与人内在之性的密切关联。
先秦儒家由“仁”而“性”的内求努力在孟子处有了标志性的成果。孟子以“性善”论为仁义道德昭示了可能性的人性论根基。孟子的“性善”论具体包括三层内涵:首先,人之“性”不仅是生而具有的,而且是人所特有的本质属性。孟子并不完全反对“生之谓性”,只是认为如果对人之“性”的理解仅限于此,那么就不能把人和其他生物区分开来了,并非所有生来即有者都可以称之为“性”。为此,孟子区别了“性”与“命”。“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谓性也。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礼之于宾主也,智之于贤者也,圣人之于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孟子·尽心下》)与其他动物相类似的自然本性不能称为人之“性”,而只能称之为“命”。能够称之为“性”的,是人生来即有且异于禽兽者,是本质意义上“性”。其次,人所特有之“性”具体指“四心”,即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四种自然道德情感。同样是生而具有,“四心”不同于“四体”,它是人异于禽兽、人之为人的本质所在。“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孟子·公孙丑上》)“四心”以“恻隐之心”为主导和核心。“恻隐之心”又称“不忍人之心”,指对他人他物的同情、不忍加害之情。这就像“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恶其声而然也。”(《孟子·公孙丑上》)这是一种近似于本能的“临事不假思索、不藉人为的、当下自然的情感显现”。再次,“四心”之性乃仁义礼智“四德”之“端”,是“四德产生的可能性因素”[7]。“侧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孟子·公孙丑上》)“四心”虽然并不就是仁义礼智“四德”本身,却真实地包含着“四德”之因子,孟子称之为“端”。“端”即萌芽、根基。“四德”因此“端”而成为可能,对此“四心”、“四端”的扩充与顺成就是“四德”的最终成就。在《孟子·告子上》中,孟子借与告子的“杞柳与杯棬之辩”比较辩证地说明了仁义道德与人自然本性之间的关系。杯棬既是对杞柳的转逆和否定,又是顺乎杞柳自身的属性纹理而成。“杯棬之于杞柳是‘顺成’与‘转逆’的统一”,同样,“仁义之于人性也是‘顺成’与‘转逆’的统一”[8]。“四心”之性作为“四德”之“端”决定了这种“顺成”。
孟子专以“四心”为“性”,固然是将丰富的人性狭隘化了,而且具有“先天道德意识”的先验论嫌疑,但是他对人所特有的自然本性与仁义道德之关系的揭示却远高于同时代人。通常,古人都以吃喝等物质性自然欲求为“性”,从而往往只看到了仁义道德对“性”的否定和改变。但这样一来,仁义道德便没有了内在于人的可能性根基,人对仁义道德的遵从与成就完全成为了被迫为之的外在服从,人在求“仁”成“仁”的活动中很容易因此而丧失自觉追求的信心和内在动力。孟子有见于此,以“性善”论延续了先秦儒家内求成德之基的努力,明确将“四心”之“性”作为仁义道德的根基。这意味着“仁义礼智诸德虽为社会性的伦理规定,但它却不纯粹是人依其理性从外部为自然(‘情’)所立的‘法’。这‘法’本身即在人的情感生活中表现为人与自然的本原一体性。”[9]这种一体性昭示了人求“仁”成“仁”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是可以依靠自力而自为、自成的,人是道德活动的主体。
三、由“性”而“心”——成德主体的最终挺立
先秦儒家由“礼”而“仁”、由“仁”而“性”不断内求,揭示了仁义道德基于人的内在之性,其最终成就有赖于人自身的自觉自为。那么,人自身又该怎样自觉自为呢?先秦儒家进一步由“性”而“心”,将人的自觉自为最终落实呈现于“心”,并揭示了其具体内涵。
先秦儒家由“性”而“心”的探求始于孔孟之间的儒者。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出土的郭店儒简中,儒简作者对“心”给予了特别关注和深入思考,“心”被最早明确为能思的“主宰之心”。这集中体现在《五行》篇和《性自命出》篇中。《五行》篇的主要内容是强调仁、义、礼、智、圣五行与心的联系,凸显了“心”在德性成就中的重要地位,明确了“心”的生命主体地位。该篇从区分“形于内”的“德之行”与“不形于内”的“行”入手,强调真正的德行不只是服从规范准则,是发自内心的自觉自愿的活动。那么如何才能具备“形于内”的“德之行”?“善弗为无近,德弗志不成,智弗思不得。思不精不察,思不长不得,思不轻不形。”[10]“形于内”的关键在于主动“为”之、“志”之、“思”之。“思” 的工夫尤其重要,“思”如果不能达到某种状态,就不可能有“德”。而“思”则是“心”的一种活动。“心”是生命活动的主宰。“耳目鼻口手足六者,心之役也。心曰唯,莫敢不唯;诺,莫敢不诺;进,莫敢不进;后,莫敢不后;深,莫敢不深;浅,莫敢不浅。”[11]耳目鼻口手足等形体器官的活动都听从心的安排,在心的指导下进行。《性自命出》篇也肯定了“心”的能动性、主宰性。“凡性为主,物取之也。金石之有声,弗扣不鸣。人之虽有性,心弗取不出”。“性”只是人体的一种潜在可能性,“心”则是激活“性”的动力,“心”不取则“性”不出。《性自命出》同时指出,“心”固然是积极能动的、主宰性的,但起初并没有既定的方向,并不必然向善。“凡人虽有性,心无定志,待物而后作,待悦而后行,待习而后定。”心志的最终确定有待于与物打交道的实践活动和教习活动,其中教化尤为重要。“四海之内,其性一也。其用心各异,教使然也。”[12]“教,所以生德于中者也。”[13]必须用道德教化来引导心志,使“心”志于仁义。
孟子通过归“性”为“心”,视“四心”为“四德”之“端”,进一步发掘了“心”本身所内含的道德因子。孟子所论之“心”主要包括两个层面。首先,孟子继承了儒简思想,明确肯定了“心”是能思之官,处于支配、决定的主体地位。“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此天之所与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弗能夺也。”(《孟子·告子上》)“心”和耳目之官虽然都是人生而具有的,却有大小主次之分。耳目之官不能“思”,与外物相接触时很容易盲目被动地随外物迁移,最终迷失自我,受制于物,故为“小体”。心之官则独具“思”之职能,故为“大体”。如朱熹言:“凡事物之来,心得其职,则得其理,而物不能蔽;失其职,则不得其理,而物来蔽之。”[14]只要“心”充分发挥“思”的职能,不仅可以区分物我,而且可以自反于身,实现对自身所固有善端的觉解,从而自觉自为地走上成善之路。其次,孟子所论之“心”还特指心官本身所固有的“四心”,或称“本心”“良心”。“四心”是人所特有的“近乎本能而又超越本能”的自然道德情感,构成了仁义礼智“四德”之根基和萌芽,故可以称之为“德性之心”。在今天看来,“四心”虽然不像孟子所言是生而具有的,却是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实践中不自觉地形成并不断积淀渗透到人伦日用之中的。它如同人的第二自然本性,为人自觉追求仁义道德提供了内在的根据和源泉,使得仁义道德的成就不再是对外在道德规范的被动遵从,而是发自主体自身之道德情感的自觉开显。
荀子把“心”作为由“性恶”走向礼义道德的关键环节,从“意志之心”和“认知之心”的维度彰显了人在道德活动中的主体能动性。荀子所言之“心”,由体而言即“心官”,由用而言即“心官”各个层面的功能和活动,具体主要包括“好利之心”“意志之心”和“认知之心”。“好利之心”是由人的物质生命存在所决定的类似于本能的心理活动,荀子将其归之于“性”,肯定其天然合理性。但是,“利心无足”(《荀子·非十二子》),任由其发展往往会导致纷争、混乱等诸多罪恶,故应以礼节之、以礼养之,此即“化性起伪”。而“化性起伪”之所以可能,其关键则在于“意志之心”和“认知之心”。“涂之人也,皆有可以知仁义法正之质,可以能仁义法正之具,然则其可以为禹明矣。”(《荀子·性恶》)所谓“可以知仁义法正之质,可以能仁义法正之具”亦即有征知之能的“认知之心”和能够自主抉择的“意志之心”。一方面,荀子肯定“心”是主宰性的、能够自主决断的“意志之心”,以此彰显人之主体性。“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出令而无所受令。自禁也,自使也,自夺也,自取也,自行也,自止也。故口可劫而使墨云,形可劫而使诎申,心不可劫而使易意,是之则受,非之则辞。”(《荀子·解蔽》)“心”主宰着包括五官在内的人的整个形体及其各种活动,而且心的各种运作都是完全自主而不由他的,或禁或使、或取或夺、或行或止,都可以不受限制地自主抉择。如劳思光所说:“此‘心’即视为文化之根源,同时亦表道德意志 (因能作选择)。只观此种说法,荀子之‘心’似有‘主体性’之义。”[15]另一方面,荀子主张“心有征知。征知,则缘耳而知声可也,缘目而知形可也。”(《荀子·正名》)心官生而具有征知之能,能够根据感官应物所提供的信息察而知之,这也是人所特有的本质所在。“人之所以为人者,非特以二足而无毛也,以其有辨也。”(《荀子·非相》)“辨”是指“一种理性认知能力以至于足以分辨、区分之能力,故‘辨’也是一种‘心知’”[16]。“心辨知”的对象主要是仁义法正之道。“人何以知道?曰:心。”(《荀子·解蔽》)人只要自觉发挥“心”的认知之能,就能够长虑而顾后,就能够创造“道”、理解“道”,成为“道”的主宰。这里的“道”即人的礼义之道。礼义之道不是天生地成的先验之物,而是圣人为了解决人们所面临的现实问题而创制的。圣人实为先知先觉者,是能够自觉而充分地发挥“认知之心”的人。他们理性地自觉到人们正是基于生存的需要而结成了群体,而群体的和谐有序又要求必须对人的自然本性加以调节和约束,这就需要礼义之道的创制与产生。礼义之道是人的理性认知能力自觉发挥的结果。
相比较而言,“认知之心”比“意志之心”更根本更关键。“意志之心”的正确抉择是以对礼义之道的辨知为前提的。“心不可以不知道,心不知道,则不可道而可非道。……故治之要在于知道。”(《荀子·解蔽》)礼义道德的成就是一个“知道”“可道”“守道”的过程,其中第一步是以“认知之心”“知道”明义,进而以“意志之心”“可道”“守道”,最终成善。如果“心不知道”,“意志之心”就会“可非道”“守非道”,最终致恶。正如康德所说,“意志被视为根据一定的法则的观念而决定自己的能力。这种能力只能在理性存在者身上被发现”[17]。可见,在荀子这里,“心”本身虽然并没有道德的种子,却仍是道德生命之所以能够成立的内在根据。荀子以“认知之心”“意志之心”挺立了人在道德活动中的知性主体和意志主体地位。
至此,先秦儒家由“礼”而“仁”、由“仁”而“性”、由“性”而“心”的主体性探寻基本完成,构建起了一个涵盖“德性之心”“认知之心”“意志之心”等诸多方面内容的德育主体性思想体系,有力地揭示和论证了人“为仁由己”“求仁得仁”的主体性。人之道德生命之所以能够达成,其根据就在于人自身,在于人的自然道德情感,在于人自觉的理性认知和不懈追求。人自身是包括德育活动在内的一切道德活动的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