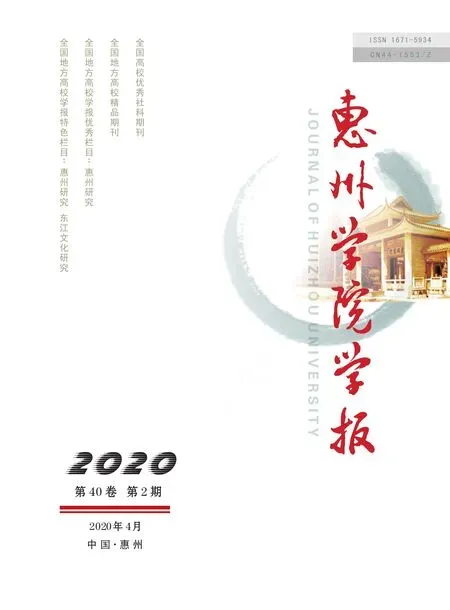生态翻译视角下《红楼梦》杨宪益译本之诠释新解
2020-02-25张蜜琳
张蜜琳
(武汉纺织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北 武汉 437000)
一、生态翻译学理论
从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起,全球兴起了一股“回归自然”的浪潮。Peter Newmark(1916-2011)和George Steiner(1929-)等学者都试图从生态学的视角审视翻译,例如生态学,环境学,生存适应等。
生态翻译学是中国学者胡庚申在二十世纪末提出的一种新型翻译研究理论,是一个涉及生态学和翻译学的跨学科研究。他认为生态翻译学结合了生态学和翻译学,依据整个翻译环境系统,解释并丰富了翻译的实质、特征、原则、方法以及完整的翻译过程和现象[1]。翻译中译者的主体性地位尚不明确,这源自原作者、译者与读者对文本均能产生影响,因而将译者确定为翻译文本的主体地位是有待商榷的。但是,译者在文本中的主导作用却不能忽视,在生态翻译理论中,译者由于翻译的生态环境从而表现为适应与选择的双向活动,一方面译者基于生存与发展需要对所处的环境进行适应,另一方面译者需要在适应的基础上对所生存的环境进行选择,从而影响实现个人的生存价值。于是,生态翻译理论中的适应与选择是相互影响和支撑的二元结构,即通过选择与适应译者才能在文本中确定其中心与主导地位。根据该理论,翻译的基本原理是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2]。在生态翻译理论视域下,翻译是以译者为主体、以文本为载体的为了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文本转换移植活动。其翻译方法主要集中于为“三维转换”,即通过对语言形式的适应性进行转换而形成的“语言维”、通过两种不同语言之间文化背景与内涵的转换而形成的“文化维”以及基于最终交际与应用成果进行适应性转换的“交际维”。
语言学界必须在回顾与前瞻的基础上思考与语言有关的问题[3]。一般来说,如果翻译后的文本具有高度的多维适应性和自适应选择性,则相应地具有高度的整体性适应性和选择性,因此被视为最佳翻译。优胜劣汰的原则适用于翻译者及其翻译。对于翻译者而言,适者生存并发展,而对于翻译而言,适者生存并生效。该理论是一项突破,因为它将翻译人员置于中心位置,强调了翻译人员在翻译过程中的中心性和主导地位。自文化转向以来,这是翻译者重要的清晰表达。
二、小说《红楼梦》生态视角翻译研究现状
作为中国古典小说的巅峰作品,《红楼梦》不仅从细微处描写了贾宝玉、林黛玉和薛宝钗之间的三角婚姻悲剧,也以宏大的历史性视角刻画了贾王史薛四大家族的人生百态与兴亡衰败,通过对封建社会以及贵族家庭的种种矛盾进行全面的剖析,从而以一种批判性视角表现了封建社会贵族阶级的骄奢、道德的沦落以及家庭的腐朽。当今社会,国际上的交流愈发频繁,将中华文化更好更快的传播出去符合当今时代的要求。《红楼梦》作为一部我国封建社会后期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在文学性上能够担起这样的重任。
根据对万方数据库2010年至2019年十年间,中国博士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以及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三个数据库中的论文(以核心期刊和学报为主),以“生态翻译《红楼梦》”为主题进行电子检索,得出相关研究的最终统计成果100篇。其中期刊论文78篇,学位论文22篇。将相关成果进行学科分类后发现,其主要应用于语言文字和文学方面。如刘艳明与张华的《译者的适应与选择——霍克斯英译<红楼梦>的生态翻译学解读》,文章的主要观点是,霍克斯英译的成功主要是因为他适应了翻译的生态环境[4]。如傅翠霞的《生态翻译学视阈下动物习语的翻译研究——以<红楼梦>两译本为例》,该论文的主要观点是,由于两位译者自身所处的生态环境有所不同,所以在动物习语的翻译方法选择上也存在着很大差异,首选的“三维”转换方法也有很大不同[5]。如陈云的《从生态翻译学视角看霍译<红楼梦>》,尝试用生态翻译学中的“适应与选择”和“三维”原则解读霍克斯英译的《红楼梦》[6]。又如杨芙蓉的《生态翻译视域下经典名著<红楼梦>中服饰颜色词英译探析》,从语言、文化和交际三重维度探析了《红楼梦》中人物服饰颜色词的英译[7]。根据计量可视化分析的检索结果显示,从2011 年起,相关研究数量一直呈现上升趋势,2014 年达到峰值(24 篇)。在此之后,一直呈下降趋势,2019 年仅有4 篇。从研究内容上来看,这10 年的文章多为应用研究,但对于生态翻译理论与其他思想结合的思考略有不足,文章从《红楼梦》的英译本出发,将生态翻译理论与“天人合一”的思想结合起来,希望能对翻译工作提供微小的借鉴意义。
三、《红楼梦》译文中的“三维转换”
文学小说翻译样式体裁繁杂多变,辞藻丰富,风格迥异。因此文学小说的翻译是最富有争议性的。作为翻译主体,译者在翻译《红楼梦》时要从语言维度、文化维度和交际维度来综合考虑译文的处理手段,做到恰到好处的“三维转换”,不能想当然的按照源语直接翻译。在注重语言转换的同时,也不能忽视文化和交际方面的转换。下面笔者将从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三个方面来分析讨论,杨宪益是如何在《红楼梦》的英译中实现“三维转换”的。
(一)语言维度的转换
语言维度的转换是指,译者翻译时在语言方向做出适应性的转换。汉语造句少用甚至不用形式连接手段,注重隐形连贯(implicit coherence),注重时间和事理顺序,注重功能、意义,注重以意役形[8]。所以汉语多用流水句,注重意合,比较简洁。而英语则注重形合,注重连接手段,比如一个英语句子里,一定要有一个主语,又比如在一个英语句子里,相关的两个句子大多又要用连接词将它们连接起来,否则就显得不够严谨。所以,译者在进行翻译之前,要先分析源语的意义和功能,然后才能确定译入语的结构和形式,做好语言维度的适应性转换。
例1:一双丹凤三角眼,两弯柳叶吊梢眉;身量苗条,体格风骚;粉面含春威不露,丹唇未启笑先闻。[9]19
She had the almond-shaped eyes of a phoenix,slant⁃ing eyebrows as long and drooping as willow leaves. Her figure was slender and her manner vivacious. The spring⁃time charm of her powdered face gave no hint of her latent formidability. And before her crimson lips parted,her laughter rang out.[10]50
这是《红楼梦》中一段非常著名的描写——王熙凤出场。丹凤眼、吊梢眉是中国式美人的审美标志,杨将其译为“eyes of a phoenix”“eyebrows as long and droop⁃ing as willow leaves”是不够精确的。其一是原文是一段有韵律、诗歌性的描写,一双眼,两弯眉,身量体格,粉面丹唇,配上乐曲几乎能够唱出来,但是译文在整体上显然完全失去了这样的感情,在语言上失去了源文本的美感,只是一段平平无奇的相貌描述。其二是杏仁般或是凤凰状的眼睛,并不会让读者感受到王熙凤的美。西方国家多喜爱挑眉,所以杨用“drooping”一词来描述王熙凤的吊梢眉是不妥的,因为在读者看来,这并不是描述美人的词汇。
例2:不一时,只听得箫管悠扬,笙笛并发。正值风清气爽之时,那乐声穿林度水而来,自然使人神怡心旷。[9]284
Soon after the serving-woman left on this errand they heard the lilting strains of flutes and pipes. The breeze was light,the air clear,and this music coming through the trees and across the water refreshed and gladdened their hearts.[10]795
“汉人平常说话不喜欢用太多没有基本意义的虚词,只是把事情或意思排列起来,让人去了解这两个事情或两个意思之间所生的关系如何[7]”。在这个例子中,原文是一段空镜描写,结构松散自然,逻辑意义隐含在字里行间,这是汉语习惯的特点之一。其次,汉语句式讲究前后对称、音韵优美,但英语则是主次突出、简单明确。杨宪益在翻译过程中,用了一个“of”和三个“and”将几个分句连接起来,符合英语的行文结构和语法规则,结构完整,以形显义。英语在句子连接中最常用的手段就是连接词,逻辑性很强,所以,在汉译英时如果不做处理,只是一味地直译,译文就会显得生涩僵硬没有感情。杨宪益做出上文的调整,在语言维度上就能够适应西方的生态语言环境,使读者更能理解原文的含义。
例3:青衣乐奏,三献爵,拜兴毕,焚帛奠酒,礼毕,乐止,退出。[9]363
Black-robed musicians played music while the liba⁃tion-cup was presented three times and obeisance made.Then the silk was burnt and wine poured. At the end of this ceremony the music stopped and all withdrew.[10]1085
该句中的“三献爵,拜兴毕”“礼毕,乐止,退出”,读起来一气呵成,朗朗上口。这就是汉语的表达习惯,不用任何无意义的连接词,但凑在一起仍然天衣无缝,没有痕迹。但是这样的行文结构,显然给译者加大了难度,因为在英语的语言环境中,没有主谓宾是很难完成一个完整的句子的。所以杨宪益使用了增译的翻译策略,用“while”“and”等连接词将几个分句连接起来,并且加上了“libation-cup”作为主语。另外,他也将“焚帛奠酒”译成了被动句,使得整个句子在忠实于原文的基础上,也与英语的表达习惯相契合,较好地完成了语言维度的转换。
(二)文化维度的转换
文化维度的转换是指,翻译时在文化内涵上,译者要注意源文本和译入语之间的文化差异与冲突,避免在翻译过程中丢失信息,导致曲解原文的文化内涵。每一种语言都植根于一种特定的文化,《红楼梦》中有许多存在中华文化深刻含义的词语,是中国特有的词语。所以在做翻译时,译者应当留心中西方的文化差别,要从文化转换维度出发,更好地将源文本的意思传达出去,尽可能少的发生偏差。
例4:临窗大炕上铺着猩红洋罽,正面设着大红金钱蟒靠背,石青金钱蟒引枕,秋香色金钱蟒大条褥。[9]21
In the middle were red back-rests and turquoise bol⁃sters,both with dragon-design medallions,and a long greenish yellow mattress also with dragon medallions.[10]55
这一段描写的是贾府富贵的日常用品装饰。在中国古代,猩红代表着地位的尊贵,比如在后宫中,只有皇后才能穿正红色的衣服。红色在西方文化中的意象与东方文化大相径庭,西方认为红色代表血色,“red”即“blood”是不吉利的,不令人产生好感的颜色。杨译在这个地方采取了直译的办法,也没有做任何注解,也许会使得读者产生一定程度上的误解,认为是带有血色的毛毡。金钱蟒在古时候是大户人家才会拥有的装饰物,象征着财权,在西方没有对应的意象,甚至连对应的单词也没有,杨译在这里将金钱蟒的意象换成了龙,站在读者的角度,某种程度上在文化上还原了源文本的要表达的含义。
例5:登仙非慕庄生蝶,忆旧还寻陶令盟。[9]267
No need to envy Zhuang Zi his butterfly dream;
Recalling old friends,let me seek out Tao Yuan⁃ming.[10]767
这里是在《红楼梦》第三十八回,林黛玉作的一句诗。诗句的意思是,飘飘欲仙的舒畅睡眠,/不是因为要去追随庄周梦蝶的典故,而是为了去寻找陶渊明从前过得那种悠闲隐逸的生活。第一,其中用了“庄周梦蝶”的典故。第二,陶渊明曾经做过彭泽令,所以诗中称为“陶令”。这两个典故如果直译,读者会很难理解其中的含义。因为这两个词属于中华文化中的特色词汇,作为外国读者,没有一定的基础,一定理解不了其所指的含义。如果忠实于原文来翻译,读者将会十分困惑,几乎完全理解不了其中的含义。杨宪益虽然将庄子和陶渊明的完整的翻译了出来,但仍然没有为受众扫清阅读障碍,读者在阅读之时仍然会摸不着头脑。
例6:虽是千金小姐,原不知这事,但你们都念过书识字的,竟没看见朱子有一篇《不自弃文》不成?[9]381
Though sheltered young ladies know nothing about such things,in the course of your studies you have surely read Zhu Xi's essay On Not Debasing Oneself?[10]1148
原文“朱子”指的是宋朝朱熹,由于他是儒学大家,学问颇深,后世尊称他为“朱子”。考虑到这个尊称的文化背景较为丰富,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将其简化,翻译为“Zhu Xi”。如果直接翻译为“朱子”,将会影响读者语义理解,甚至使得译文接受者混淆原文的含义。但是,即使使用了这样的翻译策略,对中华文化不了解的读者,只能明白“Zhu Xi”是一个人的名字,仍然不能理解其背后所蕴含的文化内容。所以在此处,最好能做上脚注,适当的解释一下能更好的适应文化维度的生态环境。
(三)交际维度的转换
交际维度的转换是指,翻译时要注意原文的交际目的。交际维度的转换是非常重要的,在遇到有丰富中式文化内涵的词句时,译者要注重沟通功能,要在忠实原文的基础上,做好交际维度的转换。
例7:庙傍住着一家乡宦,姓甄,名费,字士隐。[9]3
Beside this temple lived a gentleman named Zhen Fei,whose courtesy name was Shiyin.[10]7
在《红楼梦》中,许多人物的名字都是谐音,代表了许多含义,甄士隐就是其中之一,即“真事隐”,将真实的事件隐藏起来,甄费就是“真费”,暗含这个角色要消耗许多精神,他还没有正式出场,读者就知道这大约是一个反面人物。但杨译在这里明显丢失了很多信息,他采取直译的手段,简单粗暴地将甄士隐的名字译出,会让读者完全不明白其中的含义,完全失去了交际平衡,使得翻译中交际维度的生态环境失衡。
例8:我们娘儿们不敢含怨,到底在阴司里得个依靠。[9]233
Mother and son,we won't dare hold it against you,and at least I shall have some support in the nether world.[10]659
这是第三十三回,王夫人在贾政在打宝玉的时候所说的台词。“阴司”是传统的民间说法,指的是阴曹地府。这是中华文化特有的词语,在西方国家找不到完全对应的表达。所以杨宪益在翻译时,没有直译,而是处理为“nether world”,总体上达到了中英文在交际维度层面的平衡。
例9:正说着,只见二门上的小厮来说:“老太太房里的姑娘们站在二门口找二爷呢!”[9]274
Just then a page from the inner gate announced,“some girls from the old lady's apartments are waiting for you,Master Bao,at the inner gate.”[10]788
这是《红楼梦》第三十九回的最后一句话。如例子所示,“二门”“二爷”在英文中也无法找到一一对应的单词。所以译者只能尽量求其相似之处,将它们处理为“the inner gate”“Master Bao”,充分考虑了交际层面,最大限度地将原文的意思表达出来。
四、生态翻译理论与“天人合一”思想
东方人在“天人合一”的思想影响下,强调以人为本,重直觉,注重整体与形象逻辑。而西方人则在“天人相分”的思想影响下,强调客观事物对人的作用,重分析与抽象思维。将在西方思想影响下产生的生态翻译理论与在东方思想影响下的“天人合一”结合起来,能够从新的视角重思生态翻译理论。
讲求“天人合一”“以和为贵”是中华劳动人民在几千年的发展中总结出来符合中国人主体思想的智慧,这种思想主要来源于儒释道的中国文化。在汉朝,董仲舒的观点中,“天人合一”论只是一种神学,而后发展到庄子那里,才有了宏观上的天人关系推理演绎和朴素的世界观。在翻译活动中,“天”即自然生态环境,“人”即译者、读者、作者等翻译活动者。翻译活动者不仅存活于自然生态环境中,受到生态环境的影响;也反过来作用于生态环境,获得自身的发展。文本原本的意义,第一是在作者创作时发生的,第二是在译者进行二次创作时发生的,第三则是读者在理解时发生。一部作品要得以源远流长,就要三者顺应“天道”,将人的思维方式与翻译之道进行有机的结合。所以在“天人合一”视角下的生态翻译理论,更重要的是思维方式应该如何转换,如果思维方式不进行转换,读者的阅读活动就很难进行下去。比如《红楼梦》中描写大观园的一座玉石牌坊,“龙蟠螭护,玲珑凿就”[9]116。杨译为“rampant dragons and coiling serpent”[10]352,但在这里译文与原文很明显的貌合神离了,“螭”即蛇,中国文化中,蛇的意象是智慧吉祥与神圣的,而在西方则代表了非常强烈的消极意义,如色情和凶恶。杨译如此直白的将其表现出来,难免会造成读者对该玉石牌坊描绘的错误理解,如果将蛇这个文化意象省略不译,只留下龙的刻画,通过龙在中西方都传达尊荣与高贵的意象,将能更好地体现翻译思维方式的转换,去适应整体的翻译生态环境。
而“天人相分”是一种主观意识状态。那么在这种状态下,“人”应当能动的用“天人合一”的思维引导自己,将自己视为生态翻译环境中的一部分,实现自身价值、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如果将自身脱离生态环境,则会在翻译过程中丢失很多原文的意义。如红楼梦第七回中,宝钗说当初看病的时候,一个和尚告诉自己,她身上多年的病是“热毒”[9]48,这里面包含了许多的含义。首先一般情况下,这个词是中华文化特色词汇,只有中医看病时,才会说一个病人体内有热毒。其次,宝钗在文中是一直是一个规劝宝玉多读书,将来考取功名的人物形象。这在原作者看来,是凡心过于炽热导致了她周身不适。所以原文的意思是,宝钗虽然事事周全,看似是一个八面玲珑的人,但实际上还是活得不够通透。那么这样看来,杨译为“choleric humour”[10]135还是不够妥当,读者大概能够粗略的知道原文含义,但是其间蕴含的深刻意义,实在是丢失了许多。
翻译绝不是孤立的活动,翻译过程与文化和社会息息相关。就像每个生物都必须适应环境才能生存一样,每种翻译也要适应与之相符的生态环境,才能得到读者的认可。翻译不仅仅是文本的对照,更多的翻译者认为翻译是一种文化的继承[11],生态翻译学就是从这个角度出发,讲究译者应该总览整体,在源文本和译文两者的翻译环境中,找到翻译能达到的最佳适应选择度。“天人合一”的思想是东方哲学理论中最具特色的理论之一,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生态翻译理论也强调翻译生态环境与翻译文本的和谐发展。从“天人合一”的角度来诠释生态翻译理论,是一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翻译理论的合作尝试,根本目的就是将中西方文化相互融通,取长补短,双方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从而共同发展。
五、结语
“人类社会应该互相照顾关心而不是彼此冷漠。最简单的做法就是通过文艺沟通交流[12]”。在当今日益频繁的全球化交流中,文化沟通与日俱增。“理论的创新不一定是越复杂越好,要有从简原则的意识。近年来人们对翻译基本问题的问题意识已经完全竖立,可惜的是‘对等'等问题至今还未有定论[13]”。生态理论的本质还是一个生态语言环境对等问题,语言生态环境在西方是一种模式,在东方又是一种模式,所以译者在翻译时,不能不考虑产生语言文化意义的生态环境。要从社会语言环境来构建语言意义,使得译文所产生的效果与原文产生的效果一致。生态翻译学并不是万能的理论,只是从某一个角度切入,从生态的视角提醒我们查漏补缺,谨慎行事。生态的诞生是千头万绪的,不完全为我们掌控,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所以我们要以敬重的心态对待翻译的意识活动,心存敬畏。翻译的意义不在于要译成完全一致的文本,而是在译本在不同文化语境中的再生,这也就暗示着在不同的生态环境中产生新的语义,这也是翻译的本质和翻译的目的所在。
从达尔文的“适者生存”出发,但冲破了固有角度,以“和”为基石,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个中西结合的视角。所以《红楼梦》杨宪益之译本,虽不能完整的、全方位的处理中西方文字在语言转换中遇到的表达及交流问题,但从“和为贵”的角度出发,坚持发展的目光,时时调整译者可能存在的错觉,基于译者本身在生态中生存和发展中面临的问题和困惑,对文本及其作者视域进行不断地贴近和交融,并经过对“和为贵”无穷尽的思维进行辩证统一的整合,才能求溯原文本的精神花园,将自我与文本融为一体、神貌具合,抵达“天人合一”的理解与意识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