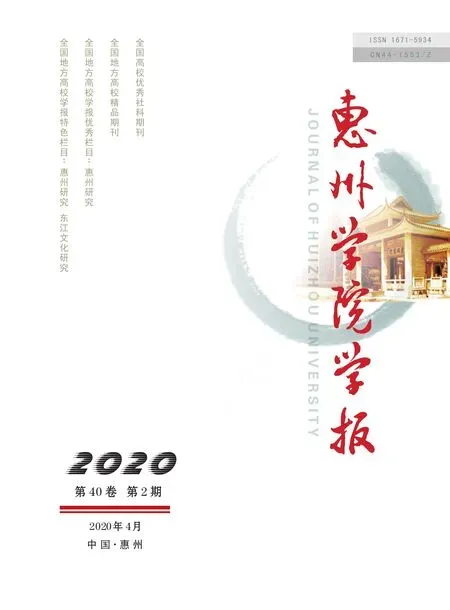男权视角下女性的逃逸叙事
——以《玩偶之家》与《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为例
2020-02-25刘莉红
刘莉红
(闽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福建 漳州 363000)
在女性的逃逸主题上,19世纪挪威著名的戏剧家亨利克·易卜生创作的《玩偶之家》与20世纪英国D.H.劳伦斯创作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有一种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意义。两部作品都聚集复杂的矛盾关系,是典型的社会问题文本,从小的方面看是夫妻之间沟通的矛盾,家庭内部的矛盾;从大的方面看却是女性个体生存与男权主义的矛盾,是伦理道德与不合理的社会法律制度的矛盾。文本都围绕女主人公自我牺牲、自我意识觉醒展开情节,最后都以自我追求的离家出走方式结束。通过娜拉与丈夫海尔茂、康妮与克利福德由表面上的相爱和谐转为彻底决裂的过程,层层剥开了资产阶级社会婚姻、宗教、法律、伦理道德等一系列的问题。在这些问题中,尤其是女性身心受到严重地压迫,命运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促使女性为挣脱传统观念的束缚,争取个体生存的自由平等而逃逸的处境,给人们带来深刻地思考。文章从空间叙事、身体叙事与男权视角,探索文本中女性逃逸的成因与出路问题,以及这种出逃给当代女性的启示与反思。
一、空间叙事:精神逃逸
随着人类思想的不断发展,人的主观体验与感知成为观察与表现世界新的视点,特别是个体的内心世界与潜意识。客观的时间叙事已不能满足文本的需要,作家开始利用空间元素来开展文本的意义建构,特别是空间并置的利用,不仅使空间叙事场景化,还可以利用空间转换推动整个叙事进程。法国著名哲学家亨利·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中提出“空间中弥漫着社会生活,空间为社会生活所改变”[1]190,在《玩偶之家》与《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中,这种弥漫着社会生活的空间凸显在家庭空间里。
在《玩偶之家》中,娜拉的生存空间是“一间屋子,布置得很舒服雅致,可是并不奢华。后面右边,一扇门通到门厅。左边一扇门通到海尔茂的书房”[2]100。文本中多次提到海尔茂书房的门,开了又关,关了又开,娜拉每次都是在门口偷听或张望,却从来没有提到她穿过那扇门。全知视角下利用这种特殊的空间布置,把女性排除在男性的权力范围之外,海尔茂的书房是男权主义的中心,他自己可以自由进出,自由的接待他的医生、柯洛克斯泰律师等,唯独妻子只能在门口徘徊。根据列斐伏尔的“空间实践、空间表征与表征空间”来区分的话,家庭空间的整个房屋是一种物化的空间实践。海尔茂的书房,是男人构想出来的具有主导地位、权力意义的空间表征,也符合福柯关于空间的权力关系论,他认为空间并非了无一物,嵌入了复杂的社会关系,是一个权力场所。与之相对应的,娜拉的活动场所是客厅,是具体展现女性地位边缘化的表征空间,是一种符号,是限制女性行动、代表女性身份地位的象征物。书房和客厅显示了空间的符号功能,男权与女性的地位差异,客厅可以任意入侵,但书房作为权力场所,却需要邀请。易卜生利用这种特殊的空间布置,不但可以观察文本中的人物如何在这特殊的空间布置中移动,更重要的是通过他们移动的过程,凸显他们之间的障碍,利用这些障碍来揭示人物的心理空间。
相对于娜拉的处境,在《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中,康妮的生存空间有很大的改善,她可以自由进出拉格比庄园任何一个地方。但生活在拉格比的康妮现实状态并不美好,不仅整个拉格比的地志空间压抑颓废,“拉格比是䡴狭长低矮,褐色石头筑就的老屋,始建于18世纪中期,时加增修,直到成就了一座无甚特色,拥挤狭窄的大房屋”[3]12,而且她与丈夫克利福德的心理空间也存在遥远的距离,她一个人孤独地住在三楼,几乎没有人来打扰她,而克利福德及佣人起居都在一楼。“在拉格比阴惨的房里,她听得见矿坑里各种嘈杂的机械声,能闻到硫磺气味,甚至连圣诞蔷薇上,也不可思议的铺着一层煤灰:好像是灾厄天空中坠落的黑甘露”[3]13,正是康妮对家庭地志空间的这种特殊触觉,使得她的心理空间时时充满了躁动、抑郁与不安。同时,这种心理空间折射也表现为心理空间的组合,“它是空间连接的又一特殊形式,同样不遵循时间顺序和惯常的因果关系,甚至超越现实空间,而以意识活动为支点,自由组接序列。在这种想象世界的组合中,情节表层的完整性和连贯性被破坏,故事由一些片断构成,序列围绕人物的意识中心不断往复和扩展”[4]128。康妮是整个拉格比空间移动的载体,她思想意识的自由流动,承载着现实家庭空间与理想社会空间的联结。劳伦斯用批判的眼光审视现实家庭空间,透过对现实家庭空间的极度不满,借助康妮的视角感知这种现实家庭空间中的苦闷压抑,从而上升到对理想社会空间的建构。
虽然娜拉和康妮生活的家庭空间场景布置有差异,但她们的精神都处于压迫中。娜拉的精神压迫源于她丈夫的男权思想与不合理的残酷的社会制度,即“家庭空间中不仅充满了女性印记,而且家庭空间已然成了困顿女性的樊篱。从这个角度来看,家成为一个残害女性的牢笼,在家庭内部男性对女性的霸权是引起女性悲剧的始作俑者”[5]125。同时,康妮居住的拉格比庄园,是一个权力关系的象征,暗示女性困守并奉献于家庭是一种理所当然的事,这一座经历了几个世纪的庄园,见证了女性的困境不是从康妮开始,也不是以康妮结束。康妮的精神压迫源于现代文明中的异化现象在个体身上的再现,精神异化是西方社会进程中,特别是工业化时代中的一种普遍现象,人们时常感到自我疏离与社会疏离,处于一种无助的孤独感与绝望感。因对现实空间的不满,娜拉与康妮都有不尽相同的精神逃逸,娜拉的精神出逃从偷吃杏仁饼干开始,康妮的精神出逃则是从不断地步入神秘的树林开始。她们在精神逃逸、追求自我的过程中,表面上的态度是消极地僵化服从,心理空间却在积极地反男权、反抗这种不合理的社会制度。
由此可见,空间叙事在文本中形成了一种社会文化载体,是人物塑造与主题意蕴表达的重要策略。文本中的空间元素蕴含着复杂多维的社会关系,它的指涉有社会物质文化的表现,也有精神文明的意蕴,不同的社会关系呈现在空间中的姿态及相对应的关系凸显时代语境。文本中女性人物内心的迷茫、失落与惶恐,从不同层面揭示了女性的生存危机,“生存危机又带来文化危机,信任缺失、金钱至上、人性扭曲,失去了终极关怀的人们心理错乱,发生精神生态危机”[6]15。家庭空间表现出来的精神压迫与道德的缺失,使得此空间不再单单是个体生存的住所,从这个细小的单元中衬托出整个时代的精神与道德的缺失,从而提升作品的主题意蕴。同时,女性的精神逃逸在此种虚伪与压抑的空间状态中,显得合情合理。
二、身体叙事:肉体逃逸
在现实家庭空间中,娜拉原本为自己的无私奉献感到自我沉醉,偶尔的精神出逃并没有引起她身体的反抗。在她丈夫面前像个宠坏的小孩,问她丈夫要零花钱、偷吃杏仁饼干、狂野的跳舞、跟孩子们一起玩游戏,像个没心没肺的快乐的家庭妇女,很满足。娜拉的这种自我满足感来源于自我牺牲:她为家庭的付出而自豪。为了维护她丈夫的尊严及家庭的欢乐,隐藏她自己的聪明,假装幼稚与白痴;在处理一些突如其来的尖锐问题上,如阮克大夫表达愿意为他付出生命时,她展示出成熟女人的能力,能抵住诱惑,守护家庭;在夫妻之间,她先一步承担家庭的责任,借债、还债。可她最后发现,孩子们有她没她一样,丈夫关键时刻也不挺身而出,反而责怪自己,她先是父亲的玩偶泥娃娃,现在是丈夫的玩偶妻子,她期待在家庭中做一个正常的女人,能与丈夫谈一些严肃的问题。当这种自我牺牲的好母亲、好妻子角色被现实生活打碎,她突然意识到自我追求比在公众面前的形象更有价值、更具有闪光点。从自我牺牲、自我迷失到真正的自我意识,娜拉面对现实,伪装出表演型的快乐,心理却承受着真实型的痛苦,她的精神与肉体早已分离,从心里抵制上升到身体行为的抗拒,大胆的与朋友分享她的杏仁饼干,试图撕毁舞裙,转移自己的焦虑情绪,开始肉体出逃。
法国著名女权主义者西蒙·波娃在《第二性》中写道:“身体是我们把握世界的工具,认识方式不同,世界也必然大为不同。物种对女性的奴役以及对她各种能力的限制,都是极其重要的事实,女人的身体是她在世界上的处境的主要因素之一”[7]36-40。在《玩偶之家》中,娜拉的身体受到压迫与限制,她的肉体逃逸是通过舞蹈展现出来的,舞蹈贯穿整个文本。第一幕中,娜拉的谎言被海尔茂拆穿后,内心极度不安。为了讨好丈夫海尔茂,故意撒娇让他为她在化装舞会上的角色出谋划策。海尔茂心生欢喜,让娜拉打扮成意大利南方的打鱼姑娘,跳塔兰台拉舞。第二幕中,林丹太太让娜拉拖住海尔茂,自己帮忙去找柯洛克斯泰,收回那封揭发娜拉为给海尔茂治病,伪造她父亲签名,无意之中犯下伪造字据罪名的威胁信。此时的娜拉惊慌失措,害怕海尔茂查看信箱,急忙在钢琴上弹起舞曲的开头几节,撒娇并带有强迫性质的让海尔茂参与,直到海尔茂说:“你这种跳法好像是到了生死关头似的”[2]168。娜拉肯定的回答,并要求海尔茂陪她一起练舞。第三幕中,娜拉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在舞会上像个疯子一样尽情地释放自己。
海尔茂让娜拉跳的塔兰台拉舞,不是一种单纯的舞蹈。塔兰台拉舞是意大利那不勒斯的一种快速旋转的土风舞,起源于塔兰托地区,表现为被一种毒蛛螫伤后身体中毒的疯癫症状,“发病的人或睡或醒,会突然跳起来,感觉到剧烈的疼痛,就像被蜜蜂蜇伤一样。他们窜出房子,奔向大街,跑进市场,极度兴奋地跳起舞来”[8]274。隐含作者通过全知叙述者的声音人物娜拉的感知来展示的这种舞蹈,是暗示娜拉肉体中毒了吗?娜拉是真的在跳舞吗?是在舞蹈中享受她的身体带来的快感吗?从整个文本可以看出,隐含作者意在凸显娜拉只是借舞蹈欢乐的假象,来讨好海尔茂的同时,发泄自己压抑的身体。舞蹈中允许女性暂时逃脱婚姻与母性的桎梏,歇斯底里的自由一会儿,无法律的音乐和不固定的移动使肉体能够不受约束的发泄。在舞蹈中,娜拉的肉体变成音乐符号,表达难以言说的痛苦,她反抗宗法社会控制她的身体,用舞蹈燃烧她的肉体,并试图毁坏舞裙,彻底释放这种身体压制。她的身体癫狂行为来自痛苦压抑,即使进入兴奋状态也只是一种消耗与疲惫。特别是第三幕中,她感到大难临头,做好了自我牺牲的准备。她竭尽全力地跳舞,用舞蹈散发她挫折的痛苦,伪装在获得快乐,并挣扎着请求海尔茂再跳一会儿。这种身体的伪装快乐在柯洛克斯泰的视角中都充满惊奇,他们竟然还在跳舞,家里还充满快乐的氛围,丝毫不受他威胁的影响。隐含作者用这种委婉的方式,传达娜拉在精神逃逸后,肉体一直在寻找发泄的窗口。
由上可知,娜拉善于伪装自己的身体,她的身体只能通过他者的声音传递,在丈夫口中是“小鸟儿”“小松鼠儿”,不能真实发出自己的声音,一直属于从属地位。相对于易卜生借用舞蹈隐喻娜拉肉体出逃的叙事,劳伦斯笔下康妮的身体叙事却是赤裸裸的。
正是身体的直接感知让康妮陷入沉思,她与米克的肉体接触没有唤起她对生活的渴望,那是因为米克的身体像个孱弱的孩子,而他的语言却十足的男权中心主义,他带着厌恶的口吻批判康妮在性生活中的主动权,致使康妮陷入迷惘、抑郁的状态。然而,梅勒斯在两性关系中的柔情让康妮对生活充满了希望,尤其在战后那种死气沉沉的语境下,创伤传染到每个人身上,活着的人需要一些实实在在的可以感知的东西。梅勒斯精瘦的身体引导着康妮的精神进入一个展新境界,实现了从个性的分裂到追求自我完整的转变。考虑到劳伦斯毕竟是男性作家,他的男权思想潜移默化地通过隐含作者渗入到文本中,因此在文本的身体叙事中,他给康妮的肉体逃逸设置了许多的障碍。
总而言之,由于历来根深蒂固的男权中心主义与时代语境的影响,“女性的劳动根本上还是维持居家生活,并且由于早期的劳动分工,女人常常是和家庭及家务画等号的”[9]118,娜拉是一个好母亲、好妻子,她无私、隐忍、忠诚、勇敢;康妮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女孩,出身良好,受到了自由教育,充沛的精力无处安放。她们从精神逃逸到实实在在的肉体逃逸,有偶然性也充满必然性,透过各自的内心世界与外部环境的反差,深刻地揭示出男权社会对女性身心的压迫与摧残。
三、男权作家视角下女性逃逸的出路探索
《玩偶之家》与《查泰莱夫人的情人》都为女主人公构建了一条出逃的主线与一条回归的辅线,林丹太太与博尔顿太太现在的处境作为回归的辅线,为出逃的娜拉与康妮提供了隐性参考。
从一开始康妮心甘情愿地帮她丈夫料理贴身事物,帮她丈夫打字出书,出席晚上她家客厅朋友圈的精神会谈,做一个称职的女主人,很知足。甚至如果她父亲还说她丈夫书的内容表现得空无一物的话,她要告诉她父亲去年靠出书挣了1500英镑,她的知足来自自我麻痹,她把这种空洞的生活当成了理所当然。慢慢地康妮感觉到:“所有伟大的辞藻都会被同代人视为毫无意义:爱情、快乐、幸福、父母、丈夫。所有这些能动的高尚词汇现在都要死不活的,慢慢走向衰亡”[3]50。她在拉格比庄园里有种窒息的感觉,她的身体憔悴了,无尽的空虚包围着她,于是她一次又一次地逃进树林里,寻找精神的安宁与肉体的释放。
从文本的角度分析,劳伦斯给康妮的出路或许表现为:一是保持查泰莱名分,带着孩子回拉比格庄园,像博尔顿太太一样,一边厌恶克利福德的身体,却一边又享受着克利福德的权力地位;二是靠她娘家的支助带着孩子与她姐姐一起生活,或是孩子流产,跟随与她地位相当的男性生活在一起。唯一无希望的是和梅勒斯一起幸福的生活,即使他们有微薄的收入。其理由是如果孩子生下来,孩子的名分问题、教育问题,梅勒斯前妻问题,康妮不会减少她的消费习惯,梅勒斯能真正接受康妮的消费习惯与生活习惯吗?从文本一开始叙述者就以全知视角透视梅勒斯的内心,他并不是那么热爱孩子,看看他对待他的女儿的方式。另外,可以从文本中找到他隐居山林的原因,因为他内心深处渴望着这样一种被遗弃的生活,不愿意与现代社会有太多交集。退一步,如果康妮愿意与他生活在森林里,深入思考一下他的性格以及劳伦斯笔下《白孔雀》中守林人的惨死结局,守林人的孩子们和妻子最后的悲惨生活,可以映射到康妮身上。康妮与梅勒斯在一起的主要原因是身体狂热的吸引,但性生活不可能是女性现实生活中一系列矛盾的灵丹妙药。劳伦斯的男权中心主义,使他对女性有一种既同情又厌恶的态度,他借隐含作者的口吻认为康妮想要过上自己的理想生活,就是无奈地无止境地等待,正如文本中所叙述的:“她耐心等待着……她总是等待,好像这都成了她的一项长处了”[3]161。她必须等待春天的来临,梅勒斯也许能够和他的妻子顺利离婚,等待孩子的出生,等待克利福德也许会良心发现,跟她离婚,等待初夏的到来。
同样,关于娜拉的出路,易卜生用全知叙述者之口吻在文本中也给了暗示,娜拉的未来或许就是林丹太太及安娜的现在。娜拉问安娜怎么舍得把自己孩子交给不相干的人出来当奶妈,安娜回答说:“我有那么好的机会为什么不下决心?一个上了男人的当的苦命的女孩子什么都得将就点儿”[2]145。与此同时,文本中林丹太太的尴尬处境,正是娜拉出逃后需要面对的,林丹太太靠自己努力生存,拥有经济独立后,发现自己找到了自我,却没有存在的价值,“现在总算过完了,我心里只觉得说不出的空虚。活在世上谁也不用我操心[2]120”。文本借用林丹太太的叙述声音传达拥有一个家比追求自我更重要,她说:“我学会了做事要谨慎。这是阅历和艰苦给我的教训……多大的变化!多大的变化!现在我的工作有了目标,我的生活有了意义!我要为一个家庭谋幸福!万一做不成,决不是我的错”[2]172-175。考虑当时的语境,女性的地位与处境差别不大,权衡利弊,或许娜拉还是回到了自己家,或许丈夫在经历她出走之后,有点改变。另一种可能,娜拉独自一个人生活,但概率不是很大。她的性格爱好是喜欢群居,喜欢一家人热热闹闹,喜欢疯狂的舞台表演等等,当然还有可能与当时兴起的女权主义者一起,有同性恋倾向。总而言之,娜拉想要真正过上自己的理想生活,按隐含作者的语调是希望渺茫:“那就要等奇迹中的奇迹发生了。那就是说,咱们俩都得改变到—喔,托伐,我现在不相信世界上有奇迹了。改变到咱们在一块儿过日子真正像夫妻”[2]195。
易卜生和劳伦斯都把现实生活中女性不可能完成的事摆到台面上,用艺术的方式表现出来,对女性充满同情,可他们为什么在给女性谋划出路的关键问题上,却没有设身处地地为女性着想,给女性一个明确的答案,而是一个靠期待奇迹发生,另一个却是靠等待。第一,由他们自身的矛盾性决定。作为男权作家,既希望女性独立又希望女性柔性,易卜生发现了女性的处境困难,但这种困难不是一时兴起,是根深蒂固的,所以也难有答案。劳伦斯对女性的态度,无论是现实生活的体验,还是作品里的艺术创造,都是又爱又恨,处在这种矛盾的心境下,他笔下的女性无法有完美的出路。第二,男权作家根本没有进入女性思维,设身处地地为女性着想,他们所传达的只是他们作为男性思维想传达的东西,女性到底怎么想,该如何做,对他们来说,根本就是一种闹剧。在《阁楼上的疯女人》中,女权作者多次反问道:“笔是男人的阴茎吗?”言外之意男权作家笔下的女性是对女性的第二次侵犯。
四、男权视角下女性逃逸叙事的意义
两位男权作家笔下的女性命运都具有现实主义特征,是现实社会中女性处境的再现,都希望女性具有叛逆精神的同时,对她们出走后的命运的不确定性充满疑虑,这与他们的创作理念和自身信仰是密切相关的。他们都受女权主义的影响,对贤妻良母型的女性人格,特别是具有牺牲精神的传统女性充满了同情,试图通过艺术世界为她们寻找出路,让女性试图自我追求,找到自我存在的价值,他们笔下的女性形象超出了以往作家对女性形象不是天使就是妖妇的命运特性,具有超前性。劳伦斯希望今后世界上男女双方“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独立、分离的个体……男人享有自己的绝对自由,女人也一样。互相承认各自的性范围,互相承认各自不同的特性”[10]228。易卜生最后那“砰”的一声关门声音,就像狠狠地打在男权社会脸上的一个响亮的耳光,在他的眼中,女性追求自我价值远比一个虚伪的家庭婚姻生活更重要。
从娜拉与康妮的精神逃逸到肉体逃逸,这种灵与肉失衡的异化精神状态表明:“家庭不再是一个温馨的精神港湾,反而成为一个令人孤独、压抑的场所。家庭成员之间往往呈现一种莫名其妙的疏离,人物总是有一种无名的挫败感,以致总想逃离家庭[5]192”。虽然易卜生和劳伦斯都试图把她们构建成为新兴的冲破传统束缚的现代女性,并敢于挑战男权社会的资产阶级自由女性形象,但从整个文本来看,隐含作者没有让她们走出家庭空间,进入社会空间,她们的主要生活场所还是在家庭中。考虑到空间是社会的产物,必然会留有各种社会分工,社会现象或社会身份印记,其中家庭空间就是一个明显的女性印记,“男人的空间总是和政治、哲学、国家以及工作联系在一起,女性在这些场合被边缘化,女人一般总是与生育子女、婚姻及家务联系在一起”[5]128,即现实社会是由男性主导的空间,女性的出逃是家庭空间异化的现实投射。
美国著名文学空间研究者罗伯特·塔利教授说:“文学绘图是通过小说人物以及他们对空间和地方的感知来表征的。我们不需要一张真正的地图,我们需要的是一张比喻意义上的地图,帮助我们审视一切,引导我们给自己和其他地方确切定位”[11]9-23。换言之,家庭空间就是一张隐喻地图,女性的从属与边缘化地位,导致家庭空间就等同于女性空间,而社会空间则属于男权空间。文学属于社会空间的一部分,由男权主导,女性是男权作家笔下的“他者”,娜拉和康妮也不例外,她们同样是男性的附属,她们的生活依然被限制在家庭空间里,她们的出逃之路只是男权笔下的实验品。就算现实生活中有少数女性能够冲破男权,走上社会空间并有自己的地位和事业,她们依然受到男性的歧视,很难真正实现男女平等的理想生活,无论是女性的精神出逃还是肉体出逃,都从侧面展现女性出逃的道路艰辛、困难重重。
总而言之,男权作家笔下的女性出逃是男性思维的再现,他们的局限性一方面在于把女性想象成是理性的,认为女性都能认清自身的地位,会朝对女性自己和他人都有利的方向选择;另一方面,早在17世纪,普兰·德·拉·巴雷指出:“男人写的所有有关女人的书都值得怀疑,因为他们既是法官,又是诉讼当事人[7]17”。男权作家笔下女性逃逸后不确定的命运告诫女性:女性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还是屈从于别人,一是取决女性自己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并为之而奋斗;二是受社会时代语境的影响,正如西蒙·波娃说:“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变成的”[7]2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