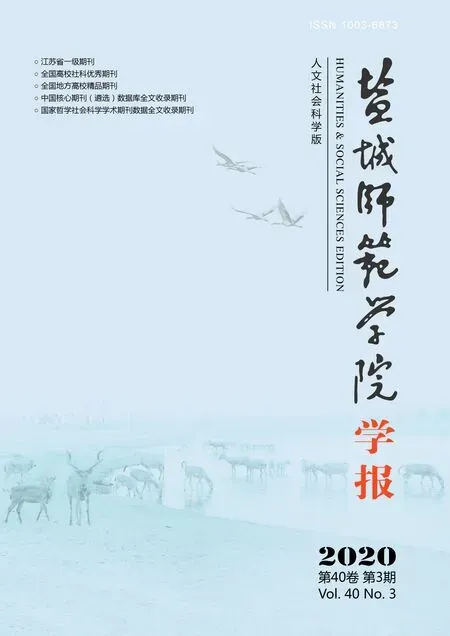洛阳时期:欧阳修文学创作与思想发展的逻辑起点
2020-02-22李光卫
李光卫
(上海教育出版社,上海 200031)
天圣八年(1030),欧阳修进士及第,释褐为西京(洛阳)留守推官,次年三月到任,景祐元年(1034)三月离任。洛阳三年,是欧阳修文坛和仕途的起步阶段,迄今为止,似乎尚无专题研究(1)王水照先生写过一系列研究西京文人集团的文章,包括《北宋洛阳文人集团的构成》《北宋洛阳文人集团与地域环境的关系》《北宋洛阳文人集团与宋诗新貌的孕育》,但都不是针对欧阳修个人的。参看王水照:《王水照自选集》,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第131-152页、第153-173页、第174-197页。。本文试结合作品和史实,分析这段时期欧阳修创作、思想两方面的进展,希望可以拾遗补阙,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古文风格的萌生与以文为诗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七著录《六一居士集》时说:“欧公本以辞赋擅名场屋。”[1]欧阳修中举前,致力于讲究声律对偶、隶事用典的科场文字。欧集所存古文,最早作于天圣八年。如《卫尉卿祁公神道碑铭》,传主父以子贵,本人无甚可纪。欧文只在他教子光大门庭一件事上作文章,正写、侧笔和反衬曲尽其致。虚处斡旋,注重剪裁,突出重心的作法,初步显示出欧阳修墓志、碑文之类作品的典型特征。又因为是实用文章,通篇散句单行。而文学性较强的作品,如《送方希则序》,说理抒情多用对句,则深受骈文影响。到洛阳后,欧阳修专攻古文,进步迅速。天圣九年(1031)的《游大字院记》,避暑、游院、咏诗三层文意,之间隔以两个“非……不……故……”缀连的相同结构的句子,布局整饬。对句虽然不多,但写景几乎全是四字一句,骈文痕迹犹未消退。而同年所作《伐树记》,用寓言手法引导论题,用主客问答推动文章,纡徐精细的说理之中隐隐透着意气风发的神态,艺术上已经足以自立。
明道元年(1032),古文数量明显增多。一些事务性、应酬性的文字,如《河南府重修使院记》和《丛翠亭记》,前者立言得体,后者以自然景观映带人工建筑,写法也都有可取之处。更值得注意的,是从这时起,欧阳修开始放笔进行各种试验,有些作法,与艺术成熟期的名篇一脉相通。如《红鹦鹉赋》,序里交代,梅尧臣、谢绛先有是作,观点截然相反,欧阳修读后意犹未尽,“因拾二赋之余弃,以代鹦毕其说。”(2)欧阳修:《欧阳修全集》,中华书局,2001,第834页。本文引用欧阳修文字,均据此书,以下不逐一出注。这显然是宋人同题竞作、热衷翻案习气的表现。欧赋弃铺陈而事议论这一点,略具文赋雏形。《非非堂记》由堂名引发大段议论,厅堂本身只在文末稍作介绍,情绪上虽没有《画舫斋记》那么感慨淋漓,写法上已是遥为先声。《送陈经秀才序》名为赠序,实为一篇“龙门游记”,和他后来把《送杨真序》写成了一篇“琴说”,同样体现出拓展赠序文体制的努力。
明道二年(1033)的作品,艺术手法更为自如。即使借鉴前人,亦能自出手眼。如《述梦赋》写梦中亡妻身影渺忽难凭:“或十寐而一见兮,又若有而若无:乍若去而若来,忽若亲而若疏。”上承宋玉《神女赋》写巫山神女“时容与以微动兮,志未可乎得原。意似近而既远兮,若将来而复旋”一段。宋赋用字错综变化,欧赋连用六个“若”,一气排比,变繁丽为疏朗。一些应酬文字,写来也自饶情趣。如《送廖倚归衡山序》,从衡山的地灵写到人杰。地灵则“其蒸为云霓,其生为杞梓”;人杰如廖倚者,“其文则云霓,其材则杞梓”。比喻就地取材,现成而妥帖。
通读这一时期欧文,不难察觉,他正在形成自己的一套常规写法,就是先从具有一定普遍性的现象或道理娓娓说起,之后再进入所写具体对象,使文章显得从容有逶迤之致。明道元年的《河南府重修使院记》《河南府重修净垢院记》《非非堂记》《送梅圣俞归河阳序》,明道二年的《东斋记》《送杨子聪户曹厅员》《上范司读书》《李秀才东园亭记》(3)《居士外集》卷十三系此文于景祐元年,今人多从之。但文末明说:“[李]公佐好学有行,乡里推之,与予友。盖明道二年十月十二日也。”这个日期可以有两种理解:(一)李公佐“与予友”之时;(二)作此文之时。而欧阳修幼时即“与李氏诸儿戏其家”(参看《记旧本韩文后》),和李公佐是旧识。这个日期,只能是写作此文的时间。“与予友”当属上句。所以这里系此文于明道二年。参看欧阳修:《欧阳修全集》,中华书局,2001,第933页。,景祐元年的《代人上王枢密求先集新书》《代杨推官洎上吕相公求见书》,皆是这种结构,形成相对固定的写法,进而确立个人风格,风格的确立往往是艺术走向成熟的一个标志,不过,写法过于固定,缺乏变化,也是创造力衰落的表现。欧文虽形成定式,具体用笔仍多变化,以明道二年四篇文章为例,各有特色。《东斋记》由自己官署东斋引出对“斋”之作用的看法,再写到张应之的东斋,既是从一般到特殊,也是以客衬主;而前略后详,笔墨主要放在张应之那边。《送杨子聪户曹序》恰恰相反,前详后略,从正反两面做足了铺垫,才请出主角杨愈,结合他的外形和声名,三言两语就达成结论。《上范司谏书》主要文意有两层:一是阐述谏官职责所系,理当直言极谏;二是反驳谏宫暂时无所作为,是心有所待的说法。第一层是一般道理,而范仲淹的道德声望,容易让人为他的沉默辩解,说是在等待适当时机。欧阳修选择在第二层上引入范仲淹,分寸拿捏得很准。这三篇文章从一般到特殊,都是直承,《李秀才东园亭记》则改直承为反衬,说随州素无美景才士,而今竟有李氏其人、东园其地,更见得其难能可贵。欧阳修洛阳时期的古文,有学习前人之处,如《伐树记》的论题来自《庄子·逍遥游》;《杂说三首》的题材和手法均模仿韩愈《杂说四首》,第一首的论点也是承袭《送孟东野序》。但总的来说,已初步形成委曲蕴藉的个人风格。释文莹《湘山野录》卷中、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八都记载欧阳修在洛阳时曾学习尹洙古文的“语简事备”“简古”,想必有所依据(4)详情参看王水照:《欧阳修学古文于尹洙辨》,载《王水照自选集》,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第452-467页。。不同的是,欧文除了“简重严正”,还有“肆放以自纾”(《与渑池徐宰》之六,欧集《书简》卷七)的一面。景祐元年的《代人上王枢密求先集序书》中有明确表述:“事信言文,乃能表见于后世”“事信矣,须文;文至矣,又系其所恃之大小,以见其行远行不远也。”事必征信是基本的文德,在此前提下要求所恃者大,就必然重视剪裁,批繁至简。而所写之事,又要求艺术的表达。结论自然是追求删汰枝节与叙写尽致的统一。可见这段时期欧阳修的古文,从理论到实践都为今后奠定了坚固的基础。
诗歌方面,明道元年所作《书梅圣俞稿后》,是最早的理论形态。王水照先生指出此文尚未确切把握住梅尧臣的诗风,原因在于“两人交往为时未久”,并且“梅诗本身尚处在初期阶段”[2]。而从行文思路来看,是这样一种逻辑:好音乐能感染人,“诗者,乐之苗裔”,与音乐功用一致:梅诗能感染人,所以是好诗。甚至对音乐和梅诗感染力的描述,字句都很类似。说到底是一种理论先行的批评。而且所谓诗应感人,就理论而言也嫌过于空泛,当然很难以此为基点准确概括出梅诗风格。不过这也不尽是坏事,因为理论的空泛,反而带来了兴趣的广泛。欧阳修梳理历代诗歌沿革,不但“汉之苏李、魏之曹刘”及唐代诗人各有位置,也承认南朝的“浮淫流佚”之声是诗之一体。他对宫体、西昆体都有拟作(5)明道元年有《拟玉台题七首》。至于西昆体,学者已注意到天圣、明道间的欧诗多有仿作。参看陈新、杜维沫:《欧阳修选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第27页;严杰:《欧阳修诗歌创作阶段论》,《文学遗产》1998年第4期。这类作品集中在《居士外集》卷五,其中与《西昆酬唱集》中诗同题的有《公子》《夜意》《即目》三首,而西昆诗人又是从李商隐那里转手来的。,即是明证。除此以外,这时的诗词,还涉及不少诗人诗作。如《河南王尉西斋》《暇日雨后绿竹堂独居兼简府中诸僚》《寄圣俞》均提到陶渊明。而《浣溪沙 堤上游人逐画船》一词,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八又发现其炼词是学王维的《寒食城东即事》。《和谢学士泛伊川浩然无归意因咏刘长卿佳句作欲留篇之什》,诗题中的“佳句”,指刘长卿《龙门八咏》。《送谢学士归阙》“马度雪中关”一句(6)此据《居士集》卷十。《居士外集》卷五《与谢三学士唱和八首 送学士三丈》是同一首诗,只不过换了个名字。参看欧阳修:《欧阳修全集》,中华书局,2001,第155页、第792页。,源出韩愈《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的“雪拥蓝关马不前”。《被牒行县因书所见呈僚友》之“晚烟茅店月,初日枣林霜”和《过张至秘校庄》之“鸟声梅店雨,野色柳桥春”,两学温庭筠《商山早行》的名句“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7)后一首的评析,参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第153页。。关注的要么是山水田园诗人,要么是非山水田园诗人的游览行旅之作,因此这一时期欧诗,成就主要在写景方面。略举几例:
《游龙门分题十五首 上方阁》:“闻钟渡寒水,共步寻云嶂。还随孤鸟下,却望层林上。清梵远犹闻,日暮空山响。”只写来回路上所闻寺钟梵呗,阁中所见一概略去,绘声而不绘色,留下充分的想象空间。《河南王尉西斋》:“云去入重城。”《张主簿东斋》:“山鸟入城啼。”云、鸟入城,既暗示斋室离城不远,又暗示幽居默处只不过是住宦生涯的调剂而已。《送谢学士归阙》:“人醒风外酒,马度雪中关。”前一句风、酒的意象组合,为这时欧诗所常用,如“酒色风前绿”(《钱相中伏日池亭宴会分韵》),“东风吹酒罇”(《送王汲宰蓝田》)等,后一句来自韩愈,而搭配起来,自成佳境。雪中马上的旅途况味,与挚友饯行的热闹场面对比,已觉清冷万状;而这个对比又是在宿醒初解时蓦然所悟,更添凄凉,《独至香山忆谢学士》前四句:“伊水弄春沙,山临水上斜。曾为谢公客,偏入梵王家。”交代山水、建筑,偏是句句扣住了伊水的流动来写,便觉姿态横生(8)这五首诗是按时间先后排列的,前三首作于明道元年,第四首作于明道二年,最后一首作于景祐元年。。这类作品总的特色是观察细,构思巧,设色多半明丽,时有佳句。
与此同时,欧阳修也写过一些“以文为诗”的作品。天圣九年的《答杨辟喜雨长句》针砭时弊,俨若一篇诗体政论。可惜议论尖锐大胆而写法呆板单调,艺术上并不出色。明道元年的《和梅圣俞杏花》,咏物绝句纯以议论出之,迥异常格。而长篇古体中的成功实践,则要等到明道二年。《绿竹堂独饮》是首悼亡诗。夫人胥氏病故时正值落花时节,诗的前半处花、人对写,花落犹可再开,人死不能复生,自然引起怅叹。后半处写自己平日意气,至此消磨殆尽:又纵谈道家齐同生死、佛教浮生如寄之说,结论是俱不能遣此悲怀。随心而言,絮语中见深情。下半年的《巩县初见黄河》,先正面描写黄河的湍急险怪;然后借大禹及历朝君主均束手无策,侧写沛然水势;最后称颂仁宗治水的功绩,诗中刻意详写大禹治百水的过程,而“惟兹浊流不可律”,两相对比,突出黄河之难治;大禹束手,与仁宗使之“改凶作民福”,又形成一重对比。整首诗融景物描写、史事追述和议论为一体,纵横古今,连环对比,章法布置极见匠心。笔力也像所写的黄河一般汪洋雄放,又多用“以”“于”“之”“且”“乃”等虚词,是欧阳修援古文入古体的典范之作。严杰《欧阳修诗歌创作阶段论》一文分析道:“首赋所见,次叙历代治河及水患情况,最后颂扬当代治河的成功,……章法嫌平直”[3],恐怕忽略了此诗连环对比的深层意脉。不过指出欧诗表层结构比较平直,也有助于深入了解其特点。不妨再看看景祐元年的《书怀感事寄梅圣俞》,开头写道:“相别始一岁,幽忧有百端。”接着追忆往日洛阳生活,写自己怎样初识梅尧臣,写几个朋友各自的特点,写当时的游宴,也写到钱惟演落职,梅尧臣、谢绛调离洛阳,看似倾泻而下,略无羁勒。但诗在挥泪作别、依依不舍时戛然而止,别后一年的“幽忧百端”再也不提。结尾与开头之间,其实有一个时间上的跳接。最后两句:“当时作此语,闻者已依然。”下一“已”字,意味深长。别时已如此难过,则别后情状,不问可知,直抒胸臆中暗含着敛蓄顿挫之势。欧阳修以文为诗的长篇,表面上往往结构严直,所以《宋诗钞 欧阳文忠诗钞》小传说他学韩愈而“一归之于敷愉”[4]。若是写得随意,难免散漫,如《答杨辟离雨长句》;若是在表面的平直下用点结构心思,则能直中寓曲,如《巩县初见黄河》和《书怀感事寄梅圣俞》。后者保持了流畅而又避免了率易,无疑是比较成功的作法。
洛阳时期的欧诗,既有学习宫体、西昆体的作品,也有尝试以文为诗的作品。从发展角度看,后者当然更能代表宋诗的走向。然而在欧阳修身上,两种现象兼容并蓄,都是不拘一格的诗歌兴趣的产物。笔者认为,这里不存在拿后一种风格去反对前一种风格的问题。以文为诗的作品,这时还不占欧诗主流,数量少而且发展晚,应理解为古文艺术进步带动的连锁反应。
二、“道”的实践层次、虚静人格与文化权力
(一)“道”的实践品格
明道二年,欧阳修作《与张秀才第二书》,批评张棐“述三皇太古之道,舍近取远,务高言而鲜事实”。类似的思想倾向在天圣七年的《国学试策三道》之一里就有所流露,不同的是这封书简正面提出了自己“务事实”的具体主张:“君子之于学也,务为道。为道必求知古,知古明道,而后履之以身,施之于事,而又见于文章而发之,以信后世。”列出“知古明道”的三个行动层次:首先是道德,其次是事功,行有余力,最后才发为文章。这三个层次,不仅是先后关系,而且是主次关系。人格修养是第一位的。《送徐无党南归序》说得很明白:“其所以为圣贤者,修之于身,施之于事,见之于言。是三者,所以能不朽而存也。修于身者无所不获,施于事者有得有不得焉,其见于言者,则又有能有不能也。……修于身矣,而不施于事,不见于言,亦可也。”今人肯定欧阳修“道”的实践品格,赞许他反对“弃百事不关于心”(《答吴充秀才书》)及看重辞章修养的态度,固然不错。但这只能是相对于空谈心性义理,轻观吏事,鄙夷文学艺术的道学家而言,不能绝对化。在欧阳修看来,“道”的实践原不限于此,而仍是首先体现在自我人格完善上。相比之下,事功、文章都是末节。只要道德可敬,事功、文章有无,都不必措意。因此也就不难理解,倡言“道”的实践品格的欧阳修,为什么会多次赞扬颜回,认为他一生居处陋巷,高尚其志,尽管事功、文章两皆无闻,却完美地履践了“道”(9)参看《居士集》卷六《感兴五首》之三、《集古录跋尾》卷三《后汉郎中王君碑》。欧阳修:《欧阳修全集》,中华书局,2001,第97页、第2135页。。
(二)“虚静”的人格要求
实践“道”的关键在于人格完善,欧阳修对士君子的人格也作了具体要求。明道元年的《非非堂记》,主题是“处身者不为外物眩晃而动,则其心静,心静则智识明,是是非非,无所施而不中”。明道二年的《东斋记》解释“斋”的含义:“谓夫闲居平心以养思虑,若于此而斋戒也。”同作于洛阳的《张应之字序》也说:“余知夫虚以待之,则物之来者益广,响之应者益远,可涯也哉!”后来门人苏轼多次发挥这个道理,如《送参寥师》:“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朝辞赴定州论事状》:“处静而观动,则万物之情毕陈于前。”与苏轼带有浓厚审美意味的阐发不同,欧阳修还停留在道德伦理领域。在此领域中,“虚静”又有两用:对外可辨是非,对内可养思虑。前者对后者起到定向作用。需要说明,主“静”是宋初士林风气,并非欧阳修所独创。嘉祐四年(1059),他在《论包拯除三司使上书》中追记:“国家自数十年来,士君子务以恭谨静慎为贤;及其弊也,循默苟且,颓惰宽弛,习成风俗,不以为非,至于百职不修,纪纲废坏。”认为一味求“静”,易于流为谨小慎微甚至因循苟且,无骨气可言。欧阳修主张心境虚静澄明,但要明辨是非,这便有所执持,变消极为积极。由此出发,才能成就真正伟大的人格。由有所执持的人格出发,才能成就真正不朽的事功和文章。系统论述见《答祖择之书》:“师经必先求其意,意得则心定,心定则道纯,道纯则充于中者实,中充实则发为文者辉光,施于世者果致。”
另一方面,“虚静”的人格要求,也必然造成简要平实的思想风格。“虚静”之心,对应的是简要的“道”。世间百事丛杂多变,其间一定要有一个一以贯之的“道”来统摄。能够执一驭万,以不变应万变,才谈得到“虚静”之心。《易或问》区分卦辞和爻辞:“卦彖象辞,大义也。大义简而要,故其辞易而明。爻辞,占辞也。占有刚柔进退之理、逆顺失得吉凶之象而变动之,不可常者也;必究人物之状以为言,所以告人之详也。”很明显,“详”总是用,“简”才是体。所以《易童子问》卷一强调:“天下之广,蛮夷戎狄四海九州之类,不胜其异也,而能一以感之,此王者所以为大,圣人所以为能。”既然“道”是简要的,自应以简要之法去求,所谓“圣言简且直,慎勿迂其求”(《送黎生下第归蜀》)。简要则易平实。《海陵许氏南园记》就说:“夫理繁而得其要则简,简则易行而不违。惟简与易,然后其力不劳而有余。”欧阳修论“道”应简要和平实,文字甚多,最早则见于明道二年的《与张秀才第二书》。此书简教人“务事实”,论述重点在“道”应平实上,即“其道易知而可法,其言易明而可行”。简要平实的思想风格和“虚静”的人格要求大体形成于同时,二者之间也是紧密联系的。
(三)士君子主体性的弘扬
欧阳修天圣七年应试所作《国学试人主之尊如堂赋》,在比君主为堂,维护其权威的同时,又比大臣为陛,认为堂高还须陛峻,臣贵方能君尊。到了洛阳时期,弘扬主体性的对象,由“迩臣”变而确定为士君子阶层。嘉祐年间的《内制集序》回忆:“昔钱思公尝以谓朝廷之官,虽宰相之重,皆可杂以他才处之,惟翰林学士非文章不可。思公自言为此语,颇取怒于达官,然亦自负以为至论。”欧阳修五十多岁还记得这一番议论,足证记忆深刻。这段话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肯定辞华文章,二是辞章之士与朝廷百官的对比。也许是受钱惟演影响,他这时弘扬士君子的主体性,根据主要是其文化素质,而且有意无意地跟达官贵人相对立。《送陈经秀才序》标榜自己这群“卑且贤者”真能得山水之趣,达官贵人是不懂的。《上范司谏书》说“君子之讥,著之简册而昭明,垂之百世而不泯”,比“有司之法”更为可惧。《杂说三首》之三说君子是“万世之所治,万物之所利”,“然则君子之学也,其可一日而息乎!”士君子的重要性,源于学养,源于所掌握的文化权力,这往往又是达官贵人所不具备的。从中可以窥见“穷者而后工”(《梅圣俞诗集序》)理论的萌芽。
欧阳修高度重视士君子阶层,终其生而不改,《易童子问》卷二、《论徐峤称弟子帖》(《书简》卷九)均有表述。但他的判断标准后来亦有变化,主要根据是其人格修养,而不是洛阳时期所说的文化。《论包拯除三司使上书》:“夫所谓名节之士者,知廉耻,修礼让,不利于苟得,不牵于苟随,而惟义之所处;白刃之威,有所不避,折枝之易,有所不为,而惟义之所守。其立于朝廷,进退举止,皆可以为天下法也。其人至难得也,至可重也。”欧阳修对士君子主体性的弘扬,重心有一个从文化素质向人格修养转移的过程。洛阳时期则还处在前一阶段。
洛阳时期欧阳修的思想,为其后提供了不少重要命题,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他论“道”的实践,首重“虚静”的人格修养。而他这几年的生活状态,是“尚好文华,嗜酒歌呼”(《答孙正之第二书》),才子气十足。更有甚者,生活上不自检束,他自己的词作如《少年游?偊b玉壶冰莹兽炉灰》,宋人笔记如《钱氏私志》皆有记载,殆无可疑。这一切均和他标举的“虚静”人格,不相一致。这种矛盾集中体现在明道元年拒绝“逸老”称号一事上。据程杰分析,当时的背景,“大约同时或稍早一些,石延年等人的放逸之风曾受到了士林的非议,欧阳修对此不会无闻。其拒绝称‘逸’,表明‘复古明道’大势之下不得不有所避忌,士人必须自觉地以儒家道德伦理规范自我。”[5]说明他提倡人格完善,仍是追随潮流,尚未完全付诸行动。
在事功层面,欧阳修这时也无可称述。他在洛阳,虽然关心民生疾苦,但自己做官是很舒服的。钱惟演“未尝责以吏职”(《河南府司录张君墓表》),使得他“但觉从军之乐,岂知为吏之劳!”(《上随州钱相公启》)洪迈《容斋随笔》卷四引张舜民《与石司理书》,记载欧阳修亲口说自己发愿习谙吏事,是在贬官夷陵之后[6]。覆按欧集,此说可信。欧阳修景祐三年甫抵夷陵,写信给尹洙就说:“到县后勤官,以惩洛中时懒慢矣。”[7]999五年写信给梅尧臣,又说:“某自作令,每日区区,不敢似西都时放纵。”[7]2447在洛阳不勤吏事可知。“道”的第二个实践层面,也几乎全然落空。洛阳时期的成就,主要还是诗文创作。
由于“尚好文华”,欧阳修把士君子的主体性,建立在文化素质之上。按说履践圣人之道,首要是人格修养,可以简捷地推论出,士君子为人所重、为世所法,人格修养是关键因素。而欧阳修在这个问题上,却向“道”的实践中最后也最不重要的一个层次倾斜,就理论本身来看,也有很大的漏洞。
综上所述,欧阳修在洛阳三年,主要成就是诗文创作。古文初步形成了委曲蕴藉的个人风格。诗歌上则兴趣广泛,兼收并蓄,不主一家。古文艺术的进步,带动了以文为诗一类风格的进展,但未能占据主流。
理论上,形成了简要平实的思想风格;明确提出“道”的三个实践层次,主次顺序是:道德、事功、文章。在前两个层次上,知、行还没有合一。而着重从文化素质角度弘扬士君子的主体性,与“道”的实践层次的主次顺序不合。及至洛阳阶段过后,论证重点从文化素质转到人格修养上,才弥补了这一理论不足。
思想和创作,当然不会各行其道,互不相干。譬如简要平实的思想风格,就和求简的文风、求易的诗风同一走向。尽管两方面都只是初具规模,尚未有自觉融合的迹象,但已经分别为以后的发展定下了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