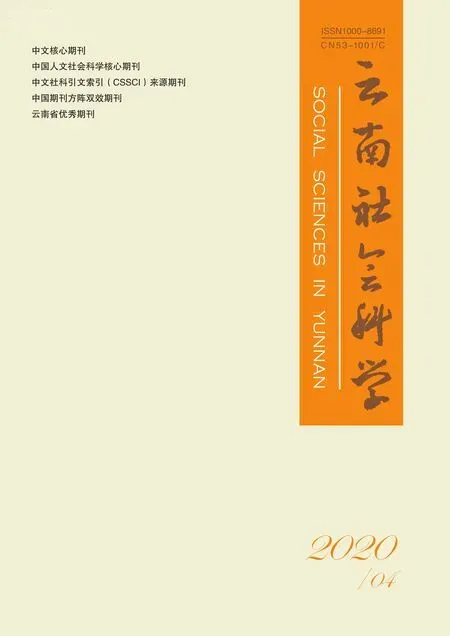明代市场演变与货币流通格局的变化
2020-02-21赵小平
赵小平
明初,政府以流通铜钱①以洪武元年(1368)发行的“洪武通宝”钱为法定货币,并允许朱元璋为吴王时铸行的“大中通宝”和唐宋钱为主的历代旧钱混用。为主,洪武八年(1375)开始发行“大明宝钞”,并允许铜钱与宝钞同时流通,这样,继宋金以后“钱楮并用”的货币流通局面再次出现。然而,这一格局持续时间并不长,可以说是昙花一现。明中后期,又出现了“银钱兼行”流通新格局。而要解释这两种货币流通格局的出现及“钱楮并用”流通格局迅速瓦解的原因,还得从市场和政府这两大因素入手进行分析。笔者曾对这两种货币流通格局演进情况进行过专门研究②参见赵小平:《明初“钱楮并用”的再现及其原因》,《思想战线》2012年第3期;赵小平:《明代中后期“银钱兼行”流通格局的形成及其原因》,《思想战线》2014年第5期。,但是,将这两种典型的货币流通格局及其演变进程放在整个明代进行考察,并从市场这个核心要素来进行深入分析,才能对有明一代货币演变的阶段性特征及其原因有更为全面的了解。因此,本文主要从市场这一因素入手,重点分析明代货币流通格局演变与市场因素变化之间的关系,以期从商品经济史的视角重新审视明代的货币流通及其演变动因。
一、明初市场的恢复与“钱楮并用”的再现
(一)明初市场仍然处于恢复期
蒙古平南宋后,把中国经济和市场最发达的江南地区重新纳入全国市场范围,这样一来,因为市场的空间无疑得到了空前扩大,其体系也进一步网络化、体系化。③对于元代市场拓展与货币流通格局演变之间的关系问题,王文成先生在《从“钱楮并用”到“银钞相权”——宋金元时期传统中国的市场结构与货币流通》(《思想战线》2014年第6期)中进行了系统研究。然而,元代市场的发展进程在元末农民战争的破坏下遭受了重大冲击,(至正)“十四年(1354),汝颖盗起,蔓延南北,州县几无完城……十七年春,乞致仕,以中原道梗,欲由蜀还乡,帝复不允。”①(明)宋濂等:《元史》卷182《列传第六十九·欧阳玄》,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4198页。战争波及区域广,破坏力强,“今燕赵齐鲁之境,大河内外,长淮南北,悉为丘墟,关陕之区,所存无几”②(明)宋濂等:《元史》卷186《列传第七十三·张桢》,第4268页。。可以说,战乱后出现的交通阻隔、人口减少或逃离、经济萧条,使元代原本拓展后富有活力的各级市场在元末再一次萎缩。
除受到元末战乱影响之外,元代曾经推行的禁商政策③元代曾于世祖至元二十九年(1292)、成宗大德七年(1303)、武宗至大四年(1311)、仁宗延佑七年(1320)先后4 次禁止海外贸易。、专卖政策④对盐、铁、酒、茶等大宗商品实行官营专卖政策。,不可避免地使全国性的批量贸易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衰退。而元末小农经济的破坏和纸币的滥行,又严重制约了小农市场的发展,经济萧条、市场萎缩已是不争的事实。
明初,国家在元末的废墟上重建,社会经济处于百废待兴的阶段。经过元末二十余年的长期战争,到明朝建立之初,全国范围呈现出一派荒凉凋敝的景象,如《明太祖实录》记载,“丁酉迁苏州府崇明县无田民五百余户于崐山开种荒田,时崐山县民上言,其邑田多荒芜,而赋额不蠲”⑤《明太祖实录》(卷231),洪武二十七年二月辛未朔条,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第3383页。。人口减少、土地荒芜已经是普遍现象。明初太祖皇帝以恢复社会经济为主要任务,“于时,东至辽左,北抵宣、大,西至甘肃,南尽滇、蜀,极于交趾,中原则大河南北,在在兴屯矣”⑥(清)张廷玉等:《明史》卷77《志第五十三·食货一·田制》,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884页。。可见,鼓励垦殖、屯田成为明初恢复经济的首要措施。总体而言,明前期的中国大地仍然处于小农经济的恢复时期。因此,明代初期的市场,仍然延续了元末萎缩的现状:即批量贸易、转运贸易发展受限,甚至对与周边民族或国家间的贸易进行控制,“敢有私下诸番互市者,必置之重法”⑦《明太祖实录》(卷231),洪武二十七年春正月辛丑条,第3374页。;而以零星交易、小额交易为代表的小农交易也在元末基础上尚处于恢复阶段。
(二)明初市场的需求与“钱楮并用”的出现及其瓦解
从市场对货币的需求来看,批量贸易、转运贸易等大额贸易需要价值大的金银或面额高的宝钞来进行,而以小农为基础的市场以小额交易为主,需要有与其相适应的小价值铜钱或其他金属货币作为交换媒介。
在明初,小农市场正好处于恢复期,对铜钱有一定需求,因此,明初前七年政府是打算以铜钱为主要流通货币的,故洪武元年发行货币时“命户部及行省鼓铸洪武通宝钱”⑧《明太祖实录》(卷31),洪武元年三月辛未,第535页。,“而严私铸之禁”⑨《明史》卷81《志第五十七·食货五·钱钞》,第1961页。。也就是说,明初政府为了保证市场对铜钱的需求量,命令在全国范围内同时鼓铸铜钱,甚至在鼓铸新钱不足的情况下,仍然允许历代旧钱(以唐宋钱为主)继续流通。⑩朱元璋早在应天府时就置宝源局,“铸‘大中通宝’钱,与历代钱兼行”;而“洪武四年改铸大中、洪武通宝大钱为小钱”(《明史》卷81《志第五十七·食货五·钱钞》,第1961页)。可见,除新铸“洪武通宝”钱外,原来的“大中通宝”钱也进行了新铸。这样,明初形成了以“洪武通宝”钱为主,“大中通宝”钱和历代旧钱仍然流通的局面。事实上,明初以发行和流通铜钱为主的货币政策,无疑是基于小农经济开始恢复、大额贸易相对萎缩的社会状况而实施的。
然而,虽然明初大额贸易处于萎缩状态是社会实际情况,但不可否认部分大额贸易仍然存在,且有恢复和发展批量贸易、转运贸易等大额贸易的社会需求。而以铜钱作为大额贸易的交换媒介并不太合适,加之国家赋税只使用小价值的铜钱也不现实,因此,明初完全用以小农为基础的市场上流通的铜钱来作为全国通用的货币显然是无法满足市场的全部需求的,换言之,以铜钱为主的流通格局肯定无法长久。而明初只发行铜钱无法满足市场需求的另一个重要原因,还有上文所提到的鼓铸新钱不足问题。彭信威先生认为,万历以前的明代这段时期里,铜钱的流通量“不但比不上宋代,就连汉唐也远不如”①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468页。。事实上,就有明一代来看,其流通的铜钱量比不上唐宋时期,不仅仅因为铜材缺乏②《明史》记载,明政府为了鼓铸铜钱,到处搜集铜材,“是时有司责民出铜,民毁器皿输官,颇以为苦” (《明史》卷81《志第五十七·食货五·钱钞》,第1962页)。导致铜钱鼓铸不足,也有明代铜钱鼓铸没有持续进行的原因③仅洪武朝至弘治朝这段时间来看,中间的建文、洪熙、正统、景泰、天顺、成化六朝都没有新铸铜钱。,即时铸时停,总量增加有限,这也是明政府允许此前所铸“大中通宝”钱和历代旧钱可以流通的原因。
那么,小农经济的恢复需要大量铜钱,但是铜钱鼓铸不足;大额贸易积极向好的趋势是明确的,因此明初元钞仍然有流通④明初除允许流通历代铜钱以外,元钞也是可以流通的,且因便于携带被商人所推崇,“而商贾沿元之旧习用钞,多不便用钱”(《明史》卷81《志第五十七·食货五·钱钞》,第1962页)。。而适应大额贸易的货币,只能优先在金银、纸币上进行选择:当时的实际情况是,明初政府对开采银矿并不鼓励,“太祖谓银场之弊,利于官者少,损于民者多,不可开”⑤《明史》卷81《志第五十七·食货五·钱钞》,第1970页。。据全汉昇先生研究,洪武年间银课收入为75070两⑥全汉昇:《中国经济史研究》下册,台北:稻乡出版社,1991年,第602页。,故而金银储备严重不足⑦黄阿明认为“金银储备缺乏,财政开支窘绌”也是发行“大明宝钞”的原因(黄阿明《明代货币与货币流通》,博士学位论文,华东师范大学,2008年,第12页)。;而发行纸币前有成功经验可借鉴,又可以避免铸钱伤民所带来的社会问题,“上以宋有交会法,而元时亦尝造交钞及中统、至元宝钞,其法省便,易于流转,可以去鼓铸之害”⑧《明太祖实录》卷98,洪武八年三月辛酉,第1669页。。加之明初商人仍然对元钞特别青睐,“而商贾沿元之旧习用钞,多不便用钱”⑨《明史》卷81《志第五十七·食货五·钱钞》,第1962页。,有现实需求。因此,发行“大明宝钞”⑩洪武七年(1374)设宝钞提举司,洪武八年三月命中书省印行“大明宝钞”(《明史》(卷81)《志第五十七·食货五·钱钞》,第1962页)。成为首选。
出于解决大额贸易、国家税收需要而发行“大明宝钞”,但是明初大额贸易未能快速发展起来,因而全部行用宝钞同样是不现实的;而出于适应小农经济的恢复而流通的铜钱,同样解决不了大额贸易与国家财政的需求。于是,自洪武八年(1375)开始,“大明宝钞”与铜钱同时流通,并得到国家认可:不但“大明宝钞”下端明确写有“中书省奏准印造大明宝钞与铜钱通行使用”11《明太祖实录》卷98,洪武八年三月辛酉,第1669页。,而且下令“凡商税课程钱钞兼收”12《明太祖实录》卷98,洪武八年三月辛酉,第1670页。。因此,基于长途贸易、转运贸易、批量贸易、其他大额交易(如土地交易、房屋买卖)与以小农经济为主的小额交易同时并存的事实,在政府禁止金银流通的情况下13洪武八年(《明太祖实录》卷98,洪武八年三月辛酉,第1670页)和洪武三十年(《明太祖实录》(卷251),洪武三十年三月甲子,第3632页)曾先后颁布禁银令。,大数用钞14如傅衣凌《明代前期徽州土地买卖契约中的通货》研究显示,洪武、永乐年间徽州土地交易中以钞为主。载《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42页。、小数用钱应当是当时最好的选择。也就是说,明初“钱楮并用”流通格局是在小农经济日益恢复和大额贸易萎缩(但仍然存在)的历史大背景下出现的。
而明初“钱楮并用”存在时间并不长,其原因还得从市场和政府这两个重要推手来分析:在明初宝钞与铜钱同时流通的进程中,民众更喜欢使用购买力较稳定的铜钱,而明政府为了维护宝钞的顺利流通,于洪武二十七年(1394)竟然宣布“令军民商贾所有铜钱,有司收归官,依数换钞,不许行使”15《明会典》卷31《户部十八·库藏二·钞法》,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224页。,即通过颁布“禁钱”令来想达到“保钞”的目的。正像前面提到的屡次颁布“禁银”令说明政府禁银并未能奏效一样,“禁钱”令同样没有让民间市场上的铜钱消失,铜钱在市场上仍然有流通。但是,从法定层面来讲,铜钱是不允许流通了,这样“钱楮并用”流通格局事实上已经瓦解了。而引起钱、钞二元流通格局真正解体的原因,无疑是“大明宝钞”自发行以后持续贬值、民众逐渐不愿意接受宝钞所致。“禁钱”令的根本目的也是为了“保钞”。这样看来,明政府先后通过“禁银”令、“禁钱”令都没有阻止“大明宝钞”持续贬值,既有宝钞自身的缺陷,也与当时小农经济正处于恢复期及市场实际需求(市场上一方面需要铜钱,另一方面宝钞的滥行与实际需求不相符)不一致原因有关。因此,“钱楮并用”格局的瓦解,表面上看是由于“禁钱”令这一政府行为引发的,实际上却是市场选择的结果所致。
二、明中后期市场的发展与“银钱兼行”的确立
(一)市场空间结构与层级结构的发展
明中期以后,社会经济有了较大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为市场提供了更多的商品。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长途贸易、转运贸易等大额贸易再次获得发展,市场结构在空间上、层级上都有了较大拓展,这无疑又会影响到流通领域中货币的变动。市场结构最主要的是两部分:一是市场的空间结构,二是市场的层级结构,而这两个市场结构对市场上货币形成的组合无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市场空间结构的发展
在宋、元、明初市场发展的基础上,明中后期市场空间结构发生了变化,主要体现为区域市场①如南方的江南市场、江西市场、湖广市场等,北方的齐鲁市场、京津市场、中原市场等。间和区域内部不同地方间的市场关系进一步紧密,决定了不同商品跨地区流通时与其相对应的流通中货币形态和货币流通需求量。从市场与货币的关系角度讲,不同的区域可以使用不同的货币,同一区域内一般流通同一种货币,这反映着这一区域内市场间联系已相当紧密,甚至可以叫作相对独立的区域市场。基于这类市场的出现,可以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货币区域,而跨出此区域就可能流通另外一种货币,甚至在两个区域之间同时流通的货币也可以不是这两个区域内部流通的主要货币。②如以流通贝币为主的云南市场与流通元钞为主的中原市场之间进行贸易时,往往选择的是白银或铜钱。当区域市场联结为全国性的统一市场时,全国市场内就会流通统一的货币。
宋代四川地区流通铁钱即是典型例子,区域内部以铁钱流通为主,出区域后以铜钱作为与不同区域间市场联系的货币;元代全国流通纸币时,岭南地区、巴蜀地区、陕西部分地区、云南地区仍然流通白银同样是区域内部流通区域货币的例子,而在与其他区域市场或全国市场发生联系时则用元钞。这种情况在明代也存在。铜钱在明代是流通时间最长的货币③期间虽然有政府禁钱法令的推行,但民间基本上没有终止铜钱的流通。只是在禁钱期间铜钱流通量减少、流通较为隐蔽而已。,但是,仍然存在一些地方不用钱的情况,如天启大数用银、小数用贝是明代云南的货币行用状况。天启七年(1627)云南巡抚闵洪学颁布《行钱便益》推行钱法,制钱始成为云南内部市场的法定货币。事实上,明末云南发行和流通的制钱数量很少,因而在云南流通货币中所占比例也小,实际上仅仅是在辅佐海贝之用。因此,大数用银主要体现在与外部市场(包括中原地区市场和周边国家与地区间的国际区域市场)的联系方面。也就是说,各区域市场自身的发展无疑增强了内部的活力,同时也为区域间的进一步联系打下了坚实基础。当全国统一的市场形成时,各区域间共同流通的货币自然而然就上升为全国性的货币。明代中期以后白银在各区域民间市场及区域市场间的普遍流通,为其成为全国性法定的流通主币同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市场层级结构间联系的加强
市场的层级结构与空间结构相关联,即具体到每个区域市场,其内部都可以体现出不同的市场层级关系:市场的最低层主要分布在区域内的广大农村,如草市镇、集市(包括西南的街子)这一类就是小市场,即市场的最低层;再高一层级的市场如城市中的小额零售贸易;而更高一级的市场则是区域性的批量贸易(这些批量贸易一般在市场的中心地进行),它联系着无数个草市镇、集市和零售点,逐级联系后形成了一个区域性的都会,又通过都会把不同的区域间联系起来。
从明代市场发展来看,最低层的集市在明中期以后有了较大规模的增加,如位于珠江三角洲区域的番禹、顺德等十余州县,永乐年间(1403—1424)只有墟市33个,嘉靖(1522—1566)时已增至95个,万历(1572—1620)时更发展到176个;①叶显恩、谭棣华:《明清珠江三角洲农业商业化与墟市的发展》,《广东社会科学》1984年第2期。韩大成先生也认为,“如果单从某一地区看,在经济不甚发达的明中叶以前的镇市集墟则较少,而在经济比较发展的明中叶以后则较多”②韩大成:《明代城市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135页。,并统计出镇市集墟有不同程度增加的就有90多县③韩大成:《明代城市研究》,第135—136页。。不可否认,低层市场的发展可以进一步增强更高层级市场的活力,甚至对于当时全国市场的发展也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许檀先生认为,农村集市网是明清商品流通网中的基础要素,“正是由于这一农村集市网的形成,才能沟通城乡市场,使商品流通几乎覆盖全国每一个角落,从而将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各个经济区域联结为一个整体,形成分工互补”④许檀:《明清时期农村集市的发展》,《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2期。。
在集市发展的同时,明中期一些根植于农村市场土壤之中的市镇也得到发展,尤其以江南地区的市镇发展最引人瞩目⑤关于明代江南市镇的研究成果颇丰,主要代表人物和著述有:傅衣凌《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经济的分析》,《历史教学》1964年第5期;王家范《明清江南市镇结构及历史价值初探》,《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4年第1期;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龙登高《中国传统市场发展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等。。市镇数量在明中叶后不但有了较快增加,而且出现了如江西饶州府浮梁县的景德镇、广东广州府南海县的佛山镇、湖广汉阳府的汉口镇等繁荣的大市镇。天津、上海、临清、杭州、苏州、扬州等工商业型的城市和广州这一类对外贸易型城市⑥韩大城先生将明代城市分为政治型的城市、工商业型的城市、对外贸易城市与北部边塞城市4 种。参见韩大成《明代城市研究》第二章,第47—125页。在当时已经相当繁荣。
在不同的层级市场中,由于贸易层次的不同,所要求与之相适应的交换货币也不同。最低级的市场主要以小额交易为主体,因此,这类市场需要与小额交易相匹配的小价值货币(如铜钱)。在再高一个层级的零售点贸易中,仍以小额交易为主,但是同时还存在少部分大额交易,因此,在流通货币方面需要适应大额贸易与小额交易两种形式的货币同时存在,在明前期是大数用钞、小数用钱,由于钞的贬值和市场的拒绝,在明中后期则是大数用银、小数用钱。而由更高一级市场形成的大都会,以其为中心将逐级下去的零售点和集市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因此,在以都会为中心的市场网络中,批量贸易、转运贸易及其他大额贸易与小额交易同时并存,因此,需要在该区域市场内流通不同的货币形态,从而促成了明前期的“钱楮并用”和明中后期的“银钱兼行”货币流通结构。不同之处在于,明前期批量贸易、转运贸易等大额贸易尚处于萎缩期,而明中后期这类大额贸易则取得了较大发展,故而市场对适应于大额贸易的白银需求增加,进而引发了大量外国白银的流入。⑦流入中国最多者主要是日本白银和美洲白银,其中,日本白银最早在明嘉靖以前就有少量流入,嘉靖以后才开始大规模涌入;美洲白银在隆庆、万历以后开始进入,且大多经由欧洲再流入中国。
而市场的空间结构和层级结构的有机结合,即个别的交换、零星的交换与批量贸易在区域内部的发展,再加上转运贸易在区域市场间的发展,这样一来,各类贸易共同发展,进而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市场体系。而在这个市场体系中的任何变动,都有可能引起流通中货币的变动。
(二)市场的发展推进了“银钱兼行”流通格局的形成
明中叶以后,各地区社会经济发展虽然仍然呈现出不平衡性,但在城乡市场共同发展的推动下,主要的区域市场已大体形成。而边境贸易、大规模的远距离贩运贸易、南北贸易的发展,使得全国范围内商品经济间的交流进一步加强,全国性的市场网络逐渐建立,市场在层级结构和空间结构方面都得到了开拓性的发展。与上述边境贸易、远距离贩运贸易及其他大额贸易⑧如土地买卖。参见傅衣凌:《明代前期徽州土地买卖契约中的通货》,见《明代社会经济史论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41—251页。发展相适应,要求有便利商人、适合大额贸易的货币在市场上大量存在。这时宝钞贬值严重,已开始不被民众接受,白银自然而然成为了市场和民间共同的首选。
可以说,作为“银钱兼行”流通格局中的主币白银,其主导货币地位的形成完全是市场推动的结果。首先,货币白银化(万明等学者亦称为白银货币化)是从民间开始的。正如前面提到的,明政府虽然屡次颁布“禁银”令,但白银仍然在民间市场上私下流通,且白银越来越受到民众的欢迎。不可否认,白银屡禁不止的根本原因,就是市场对白银的需求,亦即货币白银化“自民间崛起”①万明:《白银货币化视角下的明代赋役改革(下)》,《学术月刊》2007年第6期。。而正是白银在民间市场上的持续流通及需求量的日益增加,为明政府承认白银合法地位②正统元年(1436)明英宗下令“弛用银之禁”,白银开始可以公开流通。《明史》(卷81)《志第五十七·食货五·钱钞》,第1964页。并进而成为主导货币奠定了基础。万明先生认为明代白银由禁止流通到流通合法化直至成为主导货币,“经历了民间自下而上到官方自上而下全面铺开的历程”③万明:《白银货币化视角下的明代赋役改革(下)》,第135页。。因此,明中期以后白银在民间的广泛流通,无疑是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后市场自然选择的结果。特别是长途贸易、批量贸易、转运贸易、海外贸易等大额贸易的发展,助推了白银主币地位的确立。而当白银的流通合法化后,无论统治阶级还是普通民众,不同阶层的人们都对白银有了不同程度的需求,这种巨大需求伴随海外贸易的发展,为外国白银流入④关于外国白银的流入问题可参考梁方仲《明代国际贸易与银的输出入》,见《梁方仲经济史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32—179页)和全汉昇《明清间美洲白银输入中国的估计》(《“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66本),1995年,第679—691页)。中国提供了契机。这样,国内的需求市场和海外的供给市场的有机结合,进一步巩固了白银的主币地位。
而作为辅币的铜钱,之所以仍然可以流通,与小农经济的发展及小额交易的发展有重要关系。随着小农经济与乡村集市小额交易的发展,同样迫切需要有与之相适应的铜钱流通。因此,当从正统元年(1436)起“朝野率皆用银,其小者乃用钱”⑤《明史》卷81《志第五十七·食货五·钱钞》,第1964页。后,大数用银、小数用钱的“银钱兼行”货币流通格局已经出现。
综上可知,明初为了保障“大明宝钞”的顺利流通,曾多次颁布“禁银”令⑥除前面提到的洪武八年(1375)、三十年(1397)两次颁布“禁银”令外,永乐元年(1403)(《明太宗实录》卷19,永乐元年四月丙寅条,第346页)、二年(1404)(《明太宗实录》卷27,永乐二年正月戊午条,第497页)、十七年(1419)(《明太宗实录》(卷211),永乐十七年四月壬寅条,第2134页),仁宗监国时(《明史》(卷81)《志第五十七·食货五·钱钞》,第1964页),宣宗宣德元年(1426)(《明史》(卷81)《志第五十七·食货五·钱钞》,第1964页)都先后下令禁止白银流通,只是仁宗监国时下的禁银令和宣宗时所下的禁银令都明显比洪武、永乐两朝宽松。。然而,多次下“禁银”令,恰恰说明禁银效果并不理想,民间市场上白银的私下流通一直没有停止,且白银的私下流通有越演越烈之势,这无疑反映了市场对白银的实际需求,换言之,白银进入流通领域已是大势所趋。随着白银的解禁,在市场这一重要推手的推动下,白银逐渐成为流通中的主导货币,并与市场上同样有需求的铜钱一起形成了“银钱兼行”的货币流通格局。
此外,需要说明的是,本文重点探讨的是市场演变与货币流通格局变化之间的关系,但并不是说市场因素是引起货币流通格局变化的唯一因素。从历史上看,在“钱楮并用”和“银钱兼行”相继出现的历史演进过程中,政府行为也是重要的推手,其中,宝钞的流通更是完全依赖于政府的强制力量。而货币白银化进程也在民间推动与政府赋税征银的共同努力下才最终完成。应该说,明代货币流通格局的变化,是市场行为与政府行为两大推手共同推动、相互接纳的结果。不可否认的是,在这两大推手中,市场行为一直是自发的、主动的核心要素,而且影响着政府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