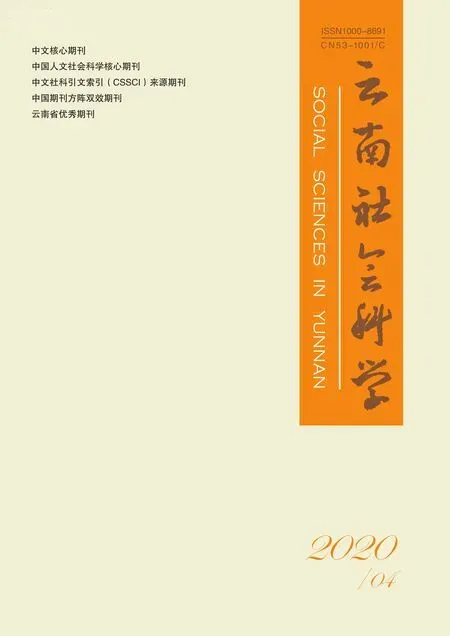论宋代桥梁记科技与文学的双重书写
2020-02-21李佳
李 佳
桥梁记,是因修建桥梁而作的记文,文章题目多为“桥梁名称+记”形式,属于中国古代记体文类。目前所见的最早桥梁记是后魏武定七年(549)于子健的《武德郡建沁水石桥记》,自此至唐存有4篇,而有宋一代则骤增到80余篇,可见宋代桥梁记创作的繁荣景象。目前,学界已经认识到了宋代记体文的独特价值,谭家健、曾枣庄、杨庆存、洪本健等人已有论述,尤其是以绘景抒怀为主的亭楼记、游记,因其文学性较强,为文学研究者所偏爱,研究成果较多,但对内容写实、风格质朴的桥梁记则关注不足。实际上,桥梁记内容丰富,包含建桥方案、施工过程、山川地貌、地域风俗、哲理阐释、人事评价等内容,具有文学、建筑学、地理学、史学等多维价值。桥梁记的繁荣与宋代的儒学复兴、科技发展息息相关,因此,从文学与科学并置统一的视角考察宋代桥梁记书写,分析实现双重书写的文体、文士、文化因素,对探究宋代乃至古代中国文学与科技的密切关联、中华文明的整体观念,具有重要意义。
一、抡材选址、缆舟架梁:宋代桥梁记中的科学记载
宋代桥梁记中包含的最为丰富的科学信息主要集中在桥梁建筑科学领域。自春秋战国时期的《考工记》倡导“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①闻人军译注:《考工记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4页。开始,历代百工匠人在追求优良品质的过程中,无不综合考量天时、地理、材美、工巧四大因素,宋代桥梁建造概莫能外。宋代桥梁记中,记载了桥梁的选料用工、修造原理、造型规模、尺寸功用等科学信息。以下按照桥梁外形并参照建材主料,分别考察宋代桥梁记所载的浮桥、梁桥的建筑科技书写。
(一)浮桥建造技术书写
浮桥,古时称为舟梁。它是用船只来代替桥墩,故又有“浮航”“浮桁”“舟桥”之称。①王俊:《中国古代桥梁》,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2015年,第13页。浮桥,是中国最早出现的桥梁,《诗经·大雅·大明》所载“造舟为梁,不显其光”②程俊英:《诗经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411页。,便指浮桥,因其联舟而成,营造难度小,见效快,故经汉魏至唐宋,一直是中国古代桥梁家族的重要成员。尤其是河面宽阔、水流湍急的大江大河,修建桥墩、架设桥梁非常困难,而联舟而成的浮桥则能快速有效地解决渡水难题。宋代桥梁记中有很多修建浮桥的记载,从中可见修造技术不断完善的过程。
凤林桥位于今江西吉安安福县,南宋王庭珪、周必大相继为此桥作记。南宋绍兴十年(1140)王庭珪因县令韩帮光重修凤林桥而作《凤林桥记》,文中详载桥之规模状貌:
桥长三百尺,广十有二尺,下为二十舟,鱼贯而浮。桥心为亭,其方如桥之广而益其三分之一,突出江半,名曰跨江亭,江之南为屋于堤上,以观浮梁之倒影,丹雘飞动,若欲凌鹜大空者,曰彩虹亭。
换算成现代长度单位后,桥长约100米,宽约4米,桥板用浮于水上鱼贯而列的船只承托。凤林桥不仅考虑到交通需求,而且考虑到审美需求,桥中间修建“跨江亭”,桥南岸修建“彩虹亭”,用以观览长桥卧波、水光天色的美景。浮桥相对易建,但木舟木梁随水涨落而伸缩飘荡,再加上风侵雨蚀很容易损坏。南宋庆元二年(1196)周必大受县尉陈章请托,因再修凤林桥而作《安福县重修凤林桥记》,而这已经是自王庭珪撰写《凤林桥记》50年来的第三次修缮了。周必大在文中梳理了凤林桥修建变迁后,指出了浮桥易坏的重要原因——材料不足、工匠不巧、维修不及时,陈章再次修造则吸取了教训:“抡材选工,举大舫二十而新之,冶铁为绠,纫竹为筰,图惟悠久之计”③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231册),上海、合肥: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235页。,与王氏《凤林桥记》记载相比,这次建桥挑选了能工巧匠,将小船换为大舫,绳索换为铁链,并辟专门资金用作日后修缮,以图桥梁使用久远。在此之后,凤林桥经历了多次毁修,并在明代万历、崇祯年间经乡绅邹善、知县陈宝泰等人相继维修加固,成为长约170米的石梁桥,更加坚固宜行。④注:凤林桥历代修缮使用情况,可参看刘崇坦主编,安福县人民政府地名办公室编印:《江西省安福县地名志》,1986年,第319页。
浮桥易建,也易毁。其常因水流大小涨落而被不断拉伸,特别在夏秋季节强降雨后,水量暴涨,往往拉断绳缆,解体船舫,瞬息之间,冲散浮桥。鉴于此,宋人不断改进浮桥技术,唐仲友《新建中津桥碑记》中,便详细记载了如何解决这一难题:
以寸拟丈,创木样置水池中。节水以筒,郊潮进退……桥不及岸十五寻,为六筏,维以柱二十,固以挞。筏随潮与桥岸低昂,续以版四。锻铁为四锁,以固桥。纽竹为缆,凡四十有二,其四以维舟,其八以挟桥,其四以为水备,其二十有六以系筏。⑤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260册),2006年,第353页。
中津桥由南宋唐仲友于淳熙八年(1181)任职临海(今浙江台州境内)时,亲自设计建造。他仔细考量河流变化,先按1:100的比例在水池中制作了桥梁木样,使建桥工匠明确桥梁原理构造,做到胸有成竹后,方予施工。唐仲友用6个木筏连接桥与岸,使浮桥长度可随水面宽度变化,这是中津桥最可贵的设计。“涨潮时,筏浮于水,但又靠柱和篾缆控制住位置。潮落时筏成坡道,各支点搁在两柱之间不同高度的楗上,成为名副其实的栈桥,由于潮水涨落坡道与舟节之间距离的改变,以及浮桥平面上曲率的变化,靠续以筏间的跳板来调节,一切自动进行。这一‘活动引桥’原理,现代浮桥还在应用。”⑥唐寰澄、唐浩:《中国桥梁技术史》(第1卷),北京: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389页。
上述以外,宋代还有很多记文写有浮桥技术信息,如叶适《利涉桥记》中的浮桥建于今浙江黄岩:“桥长千尺,籍舟四十,栏笝繂索,隄其两旁,梱图狻猊,讫三十旬,斤铁九千,木石两万五千,夫公六万余。”①叶适著:《叶适集》,刘公纯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170页。宋祁《寿州重修浮桥记》所建浮桥位于今安徽寿州,施工如是:“下令於冬,材集以春。百桴盘盘,泛溜而臻。是锯是斤,疏为千章。密贯致联,压柞扶持。舟牢索坚,垣为夷涂”②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24 册),2006年,第373页。。范成大在乾道五年(1169)任处州(今浙江丽水)郡守时修葺浮桥,并作《平政桥记》:“凡为船七十有二,联续架梁,为梁三十有六,筑亭溪南以涖之。”③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224 册),2006年,第389页。朱熹《信州贵溪县上清桥记》:“桥之修九百尺,比舟七十艘,且视水之上下而时损益焉。”④朱熹撰:《朱子全书》(第24 册),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上海、合肥: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第3802页。这些记文留下了江左、岭南大小型浮桥的诸多信息,为探究宋代浮桥应用地域和建造技术留下了宝贵资料。
(二)梁桥建造技术书写
梁桥古称平桥,可直接架梁于河谷两岸,也可架于木柱或桥墩上,外形平直,相对于拱桥容易建造。宋代桥梁记中出现最多的桥梁类型便是梁桥,主要有木柱木梁、木柱石梁、石墩石梁三种,建造者根据地形、财力等情况因地制宜,修建完毕作文以记。
石介《宣化军新桥记》所记“新桥”是木柱木梁桥,建于宣化军(今山东高青县),施工过程严谨科学:“工之巧拙、材之良恶,斧斤之高下、绳墨之曲直,必亲焉。如此九十有七日,桥乃成。凡五杠,三十七柱,七十八梁,皆大木也,所以取大壮而图不朽。”⑤石介:《石徂徕集》(2),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68页。建造者兼顾工匠能力、材料优劣、工具效用、测量方法等因素,特别考虑到木材易腐、质地柔韧的特性,专门精选多年生长、壮大坚硬的木料,设置37座木柱来支撑78根木梁,力图使用长久。中原和江右一带木柱木梁桥相对较多,盖因木材获取方便,台风暴雨较少,并非一定要石桥来抵抗恶劣天气侵袭。如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中汴梁城中的虹桥便是木拱桥,杨亿《南津桥记》所记南昌的南津桥:“以时斩木,必取楩楠之良”⑥曾枣庄、刘琳编:《全宋文》(第12 册),第2页。,楩木、楠木皆为大木。《战国策》载:“荆有长松、文梓、楩、楠、豫”⑦刘向编订:《战国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547页。,说明楚地盛产这几种木材,在南昌建木桥只需依照时令,去附近山中采伐即可,比较方便。
石桥比木桥更坚固耐用,然而大型石材的切割、运输、架设需要巨大的财力、人力和高超的技术,并不容易实现,故而长城才被誉为世界奇迹。运石上山困难,砌石江底、架石江面亦殊为不易,然而,凭借天时地利、众志巧思,宋代仍然修造了大型石梁桥,成为桥梁史上的奇迹。蔡襄于泉州任上,历时7年主持修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座入海口处大型石梁桥——万安桥,也称洛阳桥。竣工后,蔡襄作《万安桥记》载:“泉州万安渡石桥,始造于皇祐五年四月庚寅,以嘉祐四年十二月辛未讫工。垒址于渊,郦水为四十七道,梁空以行。其长三千六百尺,广丈有五尺,翼以扶栏,如其长之数而两之。”⑧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47 册),第198页。蔡襄记文朴素,只是记录了桥梁地址、规模尺寸、大略外貌,并未夸耀建造之苦与功绩之大,反而映衬其谦逊务实的品格。实际上,万安桥的先进技术在同期和后期其他桥梁记中,得到重要补充。北宋方勺《万安桥》记载:“多取蛎房散置石基上,岁久延蔓相粘,基益胶固矣”⑨程国政编注:《中国古代建筑文献集要·宋辽金元》(上),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15页。,利用牡蛎分泌物加固桥基,这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次采用“种蛎固基”的生物学原理加固维护桥梁,为蔡襄独创。明代仇俊卿《重修洛阳桥记》详细总结了蔡襄造桥时创造的“筏型基础”“浮运架梁”等先进科学方法,为后世留下宝贵的资料。万安桥建成后,闽地造桥多用其法,如晋江安平桥、连江县潘渡石桥等,“仅《泉州府志》中就记载了一百十座”①潘洪萱:《古代桥梁史话》,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7页。,很多石梁桥沿用至今,令人惊叹。20世纪英国科学家李约瑟曾在他《中国科技史》中道:“在宋代有一个惊人的发展,造了一系列巨大板梁桥,特别在福建省,在中国其他地方或国外任何地方都找不到和它们相比的。”②[英]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年,183页。
闽地出产花岗岩,修造石桥取材便利;海港大桥与内陆桥梁相比更要抗住海水侵蚀、风暴摧残,故此地建造石桥既有条件又有必要。其他地区虽然知晓石墩石梁桥坚固持久,但处理较难、费用昂贵,而木柱木梁桥,材料处理虽然方便,却不坚固,于是结合二者利弊,出现了石墩木梁桥。蔡襄修万安桥,起到了榜样作用,推广到浙江沿海一带,温州乐清名士万规便仿照万安桥在濒临东海的赤水港修建了万桥,《永乐乐清县志》卷7曰:“(万规)居海滨,有赤水港,旧以舟渡覆溺者多。规乃竭家资,率邑里,买石筑堤,仿泉之万安建桥”③《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永乐乐清县志》卷7。,但因为资金石材不足,万规便造了石柱木梁桥,并作《万桥记》记录靠一己之力建桥的过程,他先用石材建两岸滩地并向水中延伸以横截江水:“筑成东西两滩,上下一百寻,截江三十丈”④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75 册),第134页。本段引文,皆选于此。;继而江中垒起4个石桥墩,桥墩硕大坚固,迎水面尖锐,以减少水流阻力。“乃累横石为四柱,其形锐而大,一柱之广纵二寻,横一寻有半,其三寻有畸埋滩淤之下,出滩之上者裁二寻有半”;每个桥墩长约5米,宽约3.8米,高约14米,其中约7.6米隐埋在淤泥下。⑤注:八尺为一寻,宋代尺大约是今31.68 厘米,以此为标准计算石墩的长、宽、高。最后,在桥墩上横木为梁“上跨木为梁,其柱疏以立,其间迂而阔,以石不能跨故也。吾尝谋以石为梁,则曰:非刚厚极大者则不能长久,抑非绵力薄材所能致也”。可见万规最初是想在桥墩上架设石梁,以求桥梁使用久远,但桥墩之间距离较远,非厚且长的巨石不能实现桥墩间跨联,但单凭万规个人的财力、技术无法实现,只能暂时架木为梁。万规对此有遗憾亦有希望,他在文中讲:“吾于是桥,旷岁以观其变动,而后能尽其利疚。其梁木他日虽有坏,其址柱不坏,以其时损增之……吾之于利,不独在于落成之日,而又存于救坏之时。”万规在个人力量无法实现建造石柱石梁桥的情况下,桥柱全部使用石材,省却后人截水建基之难,梁板更换相对容易,暂用木材,待他日有条件可随时将木梁换为石梁。可见万规建桥并非贪图一时之功,而是倾尽全力,图其久远,便于后人。如万规所望,万桥经明清到现代的几次修缮,已换木梁为石梁,在九百多年的时间里一直普惠乐清百姓,至今仍是白龙江两岸的联通要道。
宋代桥梁记中记载的桥梁类型不唯以上几种,按造型划分,还有虹桥、单跨桥、多跨桥、屋桥等。如张玠《会湘桥记》所记为屋桥:“架屋其上,以庇风雨”⑥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270 册),第368页。,唐仲友《重修桐山桥记》所修的山间桥梁是单跨“飞桥”:“相水势不可与争,架木为飞桥,如兵书所谓天潢者,三节两重,长七寻有六尺,覆以板,甓甃其上,翼以石栏。岸高寻有七尺,叠石各广九寻”⑦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260 册),第360页。,并于桥梁两侧设置石栏,美观安全。
要之,宋代桥梁记中的桥梁书写与诗、词、赋文体中的桥梁书写的最大不同,便是书写方式与目的的不同。诗、词、赋中的桥梁书写多采用描写的方式,通过形象描摹,传达桥梁的美感,或以“桥”为一个意象,同其他意象共同构成意境,如王安石《渔家傲》:“平岸小桥千嶂抱,柔蓝一水萦花草”⑧高克勤选评:《王安石诗文选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93页。,范成大《州桥》“州桥南北是天街,父老年年等驾回”⑨高海夫选注:《范成大诗选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41页。。而桥梁记中的桥梁书写,多采用数字、叙述、白描等综合方法,全面书写桥梁的地域、选材、造型、原理、尺寸、工具等信息,精准、客观地展现桥梁本身与建桥始末,这种客观科学的书写方式,不仅使桥梁记本身具有一种严谨、质实、精简的美感,而且留存了大量古代建筑科技文献史料。宋代距今约千年,彼时桥梁多已毁废,但从桥梁记留存的诸多信息中,仍可见宋代领先世界的桥梁建筑技术,对于宋代建筑科学及文化发展研究,殊为可贵。
二、扬善贬恶、议理抒怀:宋代桥梁记中的情志表达
宋代桥梁记中除了大量桥梁信息的客观记录之外,另一突出内容便是抒情言志的主观表达,而主观表达是作品文学性的重要体现。宋代桥梁记主要通过议论叙述的方式来直接表达作者的情感态度,这与同时代的游记或者亭台记主要以写景叙事而升发出作者情感态度的方式有所不同。如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中淫雨霏霏、春和景明的描绘,苏轼《石钟山记》月夜绝壁、骇然声响的描摹,这类描写在桥梁记中极为少见。桥梁记作者不需要太多景象描绘作为自我情志表现的寄托或铺垫,而是多本于儒家经世观念,在文中直接阐明政治观点、品评人物风格、抒发哲思感慨、揭露时局弊端。
(一)美刺社会现状
桥梁记在汉魏时期初现,其功用一是记录建桥始末,二是赞扬建者功绩。记文完成,多勒石刻碑,立于桥旁。宋代记文沿袭了桥梁记文体的“称颂”基因,很多作者借“称颂”建桥者大发议论,歌颂笃诚勤奋、任责务实等高尚品格。
文同《众会镇南桥记》,记载了北宋鲜于端夫的建桥事件。文章开篇便称赞:“中山鲜于端夫淹茂而好善,正重而有谋”;继而简述其抵御羌虏、平定边陲的焯焯大功:“虏尝薄城,欲肆其丑者甚力,端夫先身麾士众乘陴,分制御具,随迮之。虏度不可角,遁去。已而正总守,事势益专,诸羌畏摄,不敢动创心,群疑释然而安”;边境安定后,鲜于端夫又乘其空闲,通沟修桥、惠利民众:“坐累家居,杅杅然不自废,犹视其所以当为者为之”;石桥建成后,过者歌德,文同亦赞:“余爱端夫好学而信道,以资其长才”。①文同:《文同全集编年校注》,胡问涛、罗琴校注,成都:巴蜀书社,1999年,第971页。本段引文,皆出于此。文章从建桥事件引申开来,插叙鲜于端夫抵御敌寇的事迹,意在彰显其疆场建功的大才和为民谋利的大义,以彰显爱国爱民、奋发有为的社会风尚。
其他桥梁记中也多有称美建桥者的言辞。罗适《洞山石桥记》,记载洞山邑良民应宗贵组织族人修建石桥一事。文末嘉叹其“能择子弟、率亲戚,教之以儒术,已而成粹美之器,中廉能之选,俾德泽仁术有所沾润”②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75 册),第324页。。郭知章《王公桥记》记载承议郎王成季建桥以解济涉之难,盛赞其能吏品格:“(王成季)静厚衍裕,政本于诚,介然与世吏殊好。并心一意,恻怛于吾民,培善使植,化悍使柔,狱讼不威而辨,赋役不猛而集”等。
宋代桥梁记中不仅沿袭了文体“称美”的传统,而且加入“讽刺”“批评”的意味,这是桥梁记在宋代的新变,文中常常批判政令、庸吏、恶俗。苏辙于熙宁七年(1074)任齐州(今山东省济南市)掌书记时,著有《齐州泺源石桥记》,记载了齐州知州李常、历城知县施辨等人建造石桥的事件,文末议论耐人寻味:
桥之役虽小也,然异时郡县之役,其利与民共者,其费得量取于民,法令宽简,故其功易成。今法严于恤民,一切仰给于官,官不能尽办。郡县欲有所建,其功比旧实难,非李公之老于为政,与二君之敏于临事,桥将不就。夫桥之役虽小,然其劳且难成于旧则倍,不可不记也。③苏辙:《栾城集》(上册),曾枣庄、马德富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500页。
苏辙认为州县建桥本是正常政务,但现在管理制度严苛,官吏做事没有自主权,一切以上级为是,导致政务处理阻力连连,民不获益。与昔日制度对比,弊端明显,那么昔日如何呢?从前政令灵活有度,建桥等惠民之事,可与民众商量共同出资,共同受益,如此一来,民生工程建设效率高、效果好。如今,民众急需桥梁解决交通困难,而政府修桥需要征得上级同意,并获得官方拨款,此类政事因资金不足常常作罢。齐州泺源石桥若不是利用附近废弃堤坝的石料铁器,亦恐难成。而今昔之变化,源于熙宁变法。王安石于熙宁二年(1069)开始主持变法,到此时是第五年,苏辙反对新法,他离任中央、任职齐州也与此有关。早在嘉祐末年(1063)王安石征求苏辙对“青苗书”(此书已具青苗法之雏形)的意见,苏辙云:“使吏倚法督责,非民之便”①脱脱:《宋史·苏辙传》(第31 册),卷339,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0823页。,便明确反对官吏严苛教条的执行政令,既不利于处理政务,又不方便百姓。《齐州泺源石桥记》中的观念与之一脉相承,苏辙先后任职河南、陈州、齐州,更能体会到新法具体施行中的弊端,便在文中借建桥之难,加以批评。
其他诸如此类在桥梁记中表达批评观点的还有曾巩的《归老桥记》,记写柳侯年老主动辞官归乡而建归老桥的事件。文中借释名“归老桥”,赞赏知老而退的柳侯,暗讽那些年迈无力却不舍爵禄的官员。正如张伯行《唐宋八大家文钞》所载:“老而致仕,进退之节宜尔。柳侯归老之乐,知止之意,所以风有位也。”②高海夫主编:《唐宋八大家文钞校注集评》,西安:三秦出版社,1998年,第4052页。石介《宣化军新桥梁记》记载宣化军使张景云建造清河桥,文中痛斥了地方恶俗。清河上屡次建桥都被15家摆渡人破坏,久而久之,形成奸孽之风,文章描摹其奸恶之状:“爪距森森、牙齿颜颜,相与横歧盘错于其间,崇奸深,树孽大”③石介:《石徂徕集》(2),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68页。。从夸张的言辞中,可见作者嫉恶之心。
(二)抒发感悟哲思
宋代理学大盛,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朱熹、真德秀等理学家辈出,即使以文称盛的苏轼、王安石等人,理学造诣亦颇精深。在士林浓郁的理学风气影响下,作者时常在桥梁记阐述经义哲思,使得宋代桥梁记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理学色彩。
真德秀是程朱理学传人,于宝庆丁亥年(1227)作《上饶县善济桥记》,当时其为史弥远所不容而退归故里。文章记载了里间富人叶泽出资建桥的事件,真氏赞赏叶泽仁善的同时,兼论“富”与“仁”的关系:“昔阳虎谓为富不仁,为仁不富。盖仁之与富,不相为谋,有富者之力,而无仁者之心,不暇以济物;有仁者之心,而无富者之力,不能以济物。”④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25,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437页。先引《孟子·滕文公上》“阳虎曰:‘为富,不仁矣,为仁,不富矣’”⑤王立民译评:《孟子》,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7年,第60页。,引出富裕与仁善关系的话题,并作进一步阐释,一般来讲,“富”与“仁”是矛盾的,拥有财富的人,多缺乏仁心,一心追求利益,没有心思去帮助别人。而心地仁善的人,多没有财富,想要助人,却没有能力。真德秀的理学根植于儒学,他对“富”与“仁”矛盾关系的认识,与儒家“重义轻财”观念,乃至由此进一步引出的中国封建时代“重士轻商”“重农轻商”的价值观,一脉相承。
再如周必大《邹公桥记》中总结封建社会中兴利济人的三种方式与各自局限:“力可兴利济人者有三:郡邑以势,道释以心,富家以资。然势者或病于扰而其成也苟,心者必借于众而其成也缓,资高者又丰入而吝出,瘠彼而肥己,能推惠者几何人哉?”⑥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231 册),第221页。他认为官府借助行政权威兴利济人,但常常为各种制度掣肘,成事勉强;佛道两家借助影响人心而促其做事,但需借助众人之力,成事缓慢;富人可凭其钱财兴利济人,但多不舍其私家财产,成事者少。周必大是南宋著名政治家、文学家,官至丞相,能高屋建瓴、顾览全局地总结社会问题,对待纷繁事物能击中肯綮、抓住要理,清晰而准确地阐释出来。桥梁记中的哲理阐发还有江公望《睦州政平桥记》感慨:“政之在事者有条,事之在物者有理,简而不疏、文而不害”⑦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121 册),第340页。,黄裳《坦履桥记》:“县令知其所以为政,邑人知其所以为善,二者相遇于邂逅,则是邦也常有惠民之最,利物之功。”⑧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103 册),第326页。凡此种种,皆为常见。
除哲理阐发之外,宋代桥梁记中也偶有兴怀抒情。如叶适《利涉桥记》中回忆往昔同乡邻娱嬉山川的悠游场景:“叔和与邑人日曳杖娱嬉于北山,潮生汐落,随江降升,悠然如泳汉浴沂,以咏歌令君之遗憾。”①叶适:《叶适集》,第171页。这一段与《论语》曾点言志“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②金良年译注:《论语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128页。所描述的场景极为相似,抒发了出叶适投身自然的怡然洒脱之情。但总体看来,宋代桥梁记的主观表达中,仍以议论时政义理为主,此类抒发超然之情的极少。
桥梁记中既包含造桥原理数据的科技信息呈现,又包含作者情志的文学色彩表达,这种科技与文学的双重书写,其他文体鲜见。传统文章如诗、赋重于情感渲染,策、论重于观点阐发,即便是桥梁记之近亲亭楼记也多是景象描绘和哲思抒发,文学韵味浓厚。而一些宋代科技文献,如《营造法式》《木经》《宋史·河渠记》等多是客观说明,几乎没有主观色彩。宋代桥梁记是鲜有兼备文学与科技双重表达的文体,它将文学的善感绮丽与科技直简冷静相杂糅,形成一种独特的美学风范。那么,为何这种双重书写是桥梁记而不是其他文体能够实现?为何是宋代而不是宋前能够实现?以下试作探讨。
三、文体、文士、文化的作用:双重书写的实现条件
关于宋代桥梁记何以能实现科技与文学的双重书写,应从文体、文士、文化三个层面分析。
(一)文体功用:宋代桥梁记具有“记录”“教化”功能
桥梁记是记体文的一种,记体文诞生之初的功用为——“所以备不忘”,文中一一记录建造桥梁的缘由、地点、经费、修建者等信息,便是以备将来查阅建桥始末的,并常将文章勒石刻碑,置于桥旁,用来彰显主事者的品格功业。因此桥梁记除了“记事件”外,还有“颂功绩”的意味,宋前的4篇桥梁记,于子健《武德郡建沁水桥记》(后魏),崔祐甫《汾河义桥记》(唐)、乔潭《中渭桥记》(唐),刘丹《西郭桥记》(唐)皆是如此,从文体功用角度看,“记”实与“碑”“铭”文体互有交叉。至宋代,士人“破体为记”,使得桥梁记也打破了原有“记事件”“颂功绩”的边界,大大增加了主观情志表达的成分,且多以议论的形式呈现,具有教化意义。宋人张玠《会湘桥记》说明作记目的:“既以此相勉,又将以观于异日”③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270 册),第368页。,“勉”便是勉励众人之意。明代吴讷《文章辨体序说》论宋代记文“专尚议论,然其言足以垂世而立教”④吴讷:《文章辨体序说》,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第41页。,宋人在桥梁记中不仅颂扬建造者,还鲜明表达了对时政、历史、风俗的褒贬态度,希望使文章发挥引领社会风尚的教化作用;甚而明经辨理,使教义传之久远。
宋代桥梁记继承了桥梁记文体自身的“记录”基因,使得文章可以客观记录建桥信息,这些客观信息中,便包括桥梁材料、规模、尺寸、技艺等科学信息,如本文第一部分所列举的桥梁记文本中大量科技信息,皆得益于桥梁记文体的记录功能,桥梁记的科学书写便有赖于此。宋代桥梁记变革后文体又新增“教化”功能,如叶适《赠薛子长》讲:“为文不能关教事,虽工无益也”⑤叶适:《叶适集》,第607页。,当然这并非是宋人特意强化桥梁记文体的教化作用,而是在崇尚议论的时代风气的熏陶下,文风的整体变化。关于宋文爱发议论的特点,诸多学者已有论述,郭预衡道:“文人学者中间,好发议论,也就蔚为风气”⑥郭预衡:《中国散文史》(中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373页。,张寿康言:“宋代杂记则多议论、抒情乃至有考据、说明的成分”⑦张寿康:《文章学概论》,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3年,第27页。,这也是文体自身发展变革规律的体现。桥梁记若要具有“教化”功能,仅仅客观记录建桥事件是无法实现的,必须要有主观议论和说理,如本文第二部分所列文献,桥梁记中常有态度鲜明的赞颂批判,或是平缓严谨的道理分析,相比宋前桥梁记,主观色彩尤其鲜明,而鲜明的主观色彩则凸显了宋代桥梁记的文学性。总之,正是桥梁记文体到了宋代兼有“记录”“教化”的两种功能需求,成为科技书写与文学书写融合一体的前提。
(二)文士特征:宋代士人具有博学、务实品格
宋代桥梁记的创作主体是宋代士大夫,桥梁记创作者与建桥者的关系主要分为两种:一是作记者与建桥者是同一人,如万规建造万桥后作了《万桥记》,有能力造桥者多是官员或乡贤,而无论是学而优则仕的官员,还是修养品格为人敬重的乡贤,都是有着良好文化素质的知识阶层;二是作记者与造桥者并非一人,如曾巩《归老桥》,乃柳侯修桥后向文豪曾巩请求而作,宋代桥梁记大部分都是应请之作,考虑到传播效应,所请皆是雄文硕学之士。
作为桥梁记创作主体的宋代士人,多兼官员、文人、学者于一身,与唐代及之前的士人相比,知识结构更加全面合理,且能知行并重,求真务实。曾巩读书涉猎广泛,“六艺百家史氏之籍,笺疏之书,与夫论美刺非、感微托远、山镵冢刻、浮夸诡异之文章,下至兵权、历法、星官、乐工、山农、野圃、方言、地记、佛老所传,吾悉得于此”①曾巩:《曾巩集》,陈杏珍、晁继周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285页。,其中的历法、星官、乐工、山农、地记便属于科学技术领域。周必大所学 “源深流洪、九流七略,靡不究通”②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282 册),第319页。,朱熹则“对自然科学问题非常关心,因为他建立哲学体系需要科学”③李申:《中国古代哲学和自然科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3页。。
州学、军学、县学、书院等教育机构所教科目也很全面,包括经、史、理、工诸类。如北宋初年胡瑗执教湖州州学时创立了“分斋教学法”,“设经义、治事两斋,以敦实学。经义斋学习儒家经典理论,治事斋学习农田水利、军事、天算等实学”④童一秋主编:《语文大辞海·语文教育卷》,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77页。。治事斋教授的是具有实用性的水利、算数等专业技能,中国教育史上从此诞生了集传统经义与科学技术于一体的教育机构。此后,分斋教学作为“苏湖教法”,推广于太学及各地学校。如此一来,科学技术教育的地位上升,并极大普及,宋代士人比以往任何时代的士人都更具理学素养和技术能力,且务求实践。他们担任地方官员时大多重视修桥、建堤等水利工程,如苏轼不但精通文学书画,还在徐州任职时修筑了抗洪堤坝,在杭州任职时疏浚西湖;曾巩在齐州(今济南)任职时修建了北水门,明州(今浙江宁波)任职时疏浚广德湖;唐仲友任职临海(今浙江台州)时亲自改良了浮桥的结构,兴建中津桥。正如学者所言:“在中国古代,那些在科学上做出贡献的科学家首先是一般的人文学者或是朝廷官员。”⑤乐爱国:《国学与科学》,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7页。
在桥梁建造等工程完成后,他们或是记载自己的造桥经历,或应请记录他人建造过程,而无论主动还是被动作记,在桥梁记书写中,宋代士人所具有的博学务实之精神,使得他们既能以文士的笔法去书写情志,又能以工程师的思维书写桥梁建设的数据和原理,这是实现宋代桥梁记文学与科学双重书写的重要条件。
(三)文化背景:宋代广泛开展桥梁营建活动
书写桥梁记的必要前提,是要有修建桥梁的活动。宋前桥梁记仅4篇,宋代则骤增到80余篇,不得不说宋代桥梁营缮的兴盛局面,是促使宋代桥梁记繁荣的直接动因。宋代造桥何以兴盛?除了建筑工艺提高之外,还跟国家倡导密不可分。
宋代官制变化频繁,而无论怎样变化,都设置了主管桥梁营缮的部门,用以筹划、主持、督查桥梁建设。宋初实行“二府三司”制期间,度支司发运案掌管都城汴京河道的桥梁修建,户部司修造案督查诸州桥梁营缮;元丰改制中,将作监、少府监、都水监都职掌桥梁建设,因桥梁与交通、农业、水利等领域均息息相关,故涉及的中央管理部门也比较驳杂。地方官员对桥梁的管理更加复杂,转运使、知府、知州多兼堤堰桥道劝农使主持桥梁修造,如欧阳修、沈括等均曾任职。知县、耆长等更是直接参与地方桥梁修建。桥梁建设还直接关系到官员的奖惩考课,《宋史·河渠志》记载:“留守向拱重修天津桥成……四月具图来,上降诏褒美。”⑥脱脱:《宋史·河渠志》(第7 册)卷94,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336页。向拱因修桥有功,便得到了皇帝褒奖。
在层层倡导督查之下,修建桥梁不仅是民之所需,而且是政之所显,很多官员士人将修桥济人作为重要政务。如魏了翁曰:“盖道之不除,已非善政;而梁不夙戒,则厉深济盈,涉者滋病焉。昔人之觇陈议郑,固不越是。虽近世亦有以驿传桥道观人者,殆不可以末务忽之也。”①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310 册),第441页。自古以来桥路修造便是考察官员吏能政绩的重要参照,不能忽视。韩元吉云:“古者,矼石彴木而为之桥,病其涉之利也,后世比舟而梁焉,盖所以济不通也。盟津之险,长淮之阻,国朝为制,庀在有司,凡州县之滨於巨川者,得用为法,然或为或否。君子常以是为观政,非甚力之不足,则亦志之有怠云尔。”②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216 册),第202页。意在说明桥梁于交通之重要,能不能克服困难营造桥梁,可反映出官员品性与吏能。
国家倡导、士人重视,外加宋代建筑技术发达,如科技史研究者言:“中国古代科技的发展在宋元时期达到最高峰”③[英]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1卷)《总论》,北京:科学出版社,1975年,第289、290页。,“宋代在桥梁建造技术中利用力学的成就是非常卓著的。宋代在材料的选择上表现出惊人的成就”④邵庆国主编:《宋代科技成就》,郑州: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4年,第221页。。座座桥梁在江河、山谷、海湾凌波而起,正如刘辰翁《习溪桥记》所描绘:“吴之垂虹,闽之水西,泉之洛阳,不论扬州金陵,钱塘姑苏,又略杓小者,亦不可为数”⑤刘辰翁:《刘辰翁集》,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54页。。如此一来,桥梁记书写便有了最直接的需求,那些桥梁科学技术、士人志向追求才有了进入桥梁记被书写的可能。
结语
综上,桥梁记到了宋代不仅出现创作数量上的繁荣,而且在书写上与以抒情言志为主的赋、策、论、表、书等文体明显不同,具有科技说明和文学表达的双重特点,这就使得桥梁记文体既具有科技文章的客观精准性,又具有文学作品的情思感染力,二者融合后,形成了桥梁记的独特文风。且如今宋代桥梁遗迹所剩无几,宋代桥梁记中保留的建筑科学信息,对古代建筑与文化研究,尤为宝贵。宋代桥梁记科技与文学双重书写的现象是多种因素促成的:文体自身的发展变化,使得宋代桥梁记要求其具有“记录事实”与“教化世道”的功用,这是桥梁记进行双重书写的基本前提;文士博学的知识体系、务实的做事理念,使作者进行双重书写成为可能;文化大背景上,国家重视修造桥梁、科技发展达到顶峰,使得桥梁营缮活动广泛开展,这是桥梁记创作的直接动因。宋代桥梁记是一座文化富矿,除了建筑学、文学价值外,其地理学、史学价值也很大,有待学人继续挖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