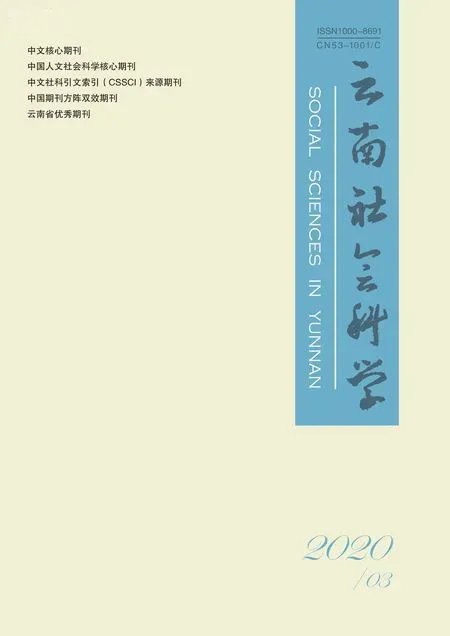梅兰芳早年成名与清末民初的社会变迁
2020-02-20刘静垚
刘静垚
“梨园,侵入乎文史者久矣。”①张艳藜:《梨园佚话·张艳藜先生序》,学苑出版社编:《民国京昆史料丛书》(第12 辑),北京:学苑出版社,2012年,第9页。在中国文史叙事传统中,不乏将优伶事迹与王朝盛衰结合起来的讨论者。这不仅由于伶人常与上层统治者的好恶关系密切,更因戏曲乃传统社会中最主要的消遣娱乐方式,映射着一个时代的审美品味与文化风气,透过重要伶人往往能够把握时世变迁中的某些关键。
梅兰芳无疑是中国近代以来最重要的伶人。他于1894年出生在北京,民初声名鹊起,至今仍是中国戏曲最广为人知的代表。目前关于他的学术研究虽已颇为不少,但大多皆从艺术层面着眼,少有以史学视角加以讨论者。②以往关于梅兰芳早年成名的叙事多侧重其师友授受传承及学艺经历,不注重对社会背景的探析,刘彦君《梅兰芳传》(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与李伶伶《梅兰芳全传》(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年)这两部长篇传记作品可谓是其代表。值得关注的是1952年唐德刚发表的《梅兰芳传稿》(氏著《五十年代底尘埃》,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97—126页),此文以流畅笔调对梅兰芳早年的许多史事及其社会背景进行了勾勒,不少分析在今天看来仍有价值。在近来研究中,吴新苗《宣统二年〈正宗爱国报〉中的梅兰芳演出广告——兼论及梅氏早期艺术经历》(《戏曲艺术》2016年第1期)对梅兰芳早年所处的梨园生态有所讨论。实际上,梅兰芳的成名不仅关乎个人际遇与艺术修为,更与清末民初中国社会的一系列重大变化息息相关,可谓是时代风气的缩影。而在关于近代社会娱乐变迁的研究中,以往更为侧重的是“新潮”一面,在地域上则多围绕上海这座新兴都市展开。但就声名而言,梅兰芳在近代娱乐史上占有绝对不容忽视的重要地位,其早年盛名的获得则主要依托北京这座古老城市,因而他这段人生轨迹能够更为清晰地展现中国从传统到近代的变迁,也更具时代的代表意义。本文即拟以梅兰芳的早年成名为线索,从阶层界限、性别构成、印刷传媒等方面深入当时的社会肌理,展现背后的社会变迁图景。
一、进入国民社会:旦角新生命时代的来临
在清末民初的社会转型中,阶层贵贱之分在观念和制度上均在逐渐淡化,一个更为平等的国民社会开始出现,这构成了梅兰芳早年成名的首要背景。
在阶层界限分明的清代北京,伶人属最下等之列,其中旦角又更等而下之。他们均由男性扮演,除登台演唱外,往往还需承担陪筵侑酒等应酬交际职能。这与政府的社会控制相关,清代在京师严禁女伶和女妓,然而正所谓“大欲难防,流风易扇。制之于此,则趋之于彼”①张际亮:《金台残泪记》,傅谨主编:《京剧历史文献汇编·清代卷》(一),南京:凤凰出版社,2010年,第440页。,士商云集的北京有大量娱乐需求,社交宴饮中也需陪衬装点,于是由晚明狎优风气沿袭而来的男旦侑酒之业便逐渐兴旺,并得到了官方默许,如郑振铎所述:“清禁官吏挟妓,彼辈乃转其柔情,以向于伶人。”②郑振铎:《郑振铎序》,张次溪编:《清代燕都梨园史料》,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8年,第7页。在此风气下,“私寓”这一独特的营业场所开始出现,其职能与妓馆相似,只是从业者均为男性伶人(男旦及部分小生)。客人可在私寓摆酒设宴,亦可“打茶围”消遣,其中的伶人也会响应客人的召唤而出局侑酒。③么书仪:《晚清戏曲的变革》,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第148—190页。王照屿:《清代中后期北京“品优”文化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台湾暨南国际大学,2008年。围绕这些伶人,汇聚京城的士子纷纷著花谱、评花榜,发展出了所谓的“品花”文化。④林秋云:《交游、品鉴与重塑——试论清代中后期北京的梨园花谱热》,《史林》2016年第4期。作为附庸的旦角不仅需要在戏台上色艺俱佳,在台下出色的应酬交际能力同样不可或缺,有时后者的意义甚至更为重要。⑤有记载称:“国丧例禁演戏,在词史辈各有其主,而倚此营生者不无仰屋之嗟,且有流为匪类。”艺兰生:《侧帽余谭》,傅谨主编:《京剧历史文献汇编·清代卷》(二),第21页。在严格的阶层与性别秩序下,男旦这一群体既需在戏台上跨越性别,更要在台下以虚鸾假凤形式满足公共社会空间中士商阶层的异性想象。梅兰芳最初便生长于这样的环境,在花榜上也曾占有一席之地。⑥在清末的最后一次花榜评选中,梅兰芳名列第七。见伦明:《伦明诗序》,张次溪编:《清代燕都梨园史料》,第1页。
时至清末,这一世风开始转移。中国知识界逐渐意识到,戏曲对下层民众而言具备强大的吸引力,因而可在启蒙国民意识方面发挥巨大作用,所谓“欲无老无幼,无上无下,人人能有国家思想而受其感化者,舍戏剧末由”⑦天僇生:《剧场之教育》,《月月小说》1908年第1期,第4页。。而欲达此目的,则必先明确伶人的独立人格与平等国民地位。1904年北京《顺天时报》便连载了两篇长文,指出:“欧美日本之名伶皆有教育思想,其人不敢妄自菲薄,国家视之亦甚重,从无以贱类目之者。”⑧剑雪生:《伶部改良策(续昨稿)》,《顺天时报》1904年7 月31 日,第2 版,傅谨主编:《京剧历史文献汇编·清代卷·续编》(四),南京:凤凰出版社,2013年,第212页。因此,私寓中周转流连于酒席之间交际酬应的旦角也遭到激烈抨击,有人称他们“同一五洲内奇特之怪物,人类中卑贱之奴隶”⑨晓痴:《菊部四主人》,《顺天时报》1907年6 月13 日,第5 版。,“一样的五官四肢,却不愿雄飞,甘为雌伏”⑩睡佛:《小琐出师消息》,《顺天时报》1907年4 月9 日,第5 版。。
在此风气下,伶界的自我主体意识得以萌发。1907年便有“姜慧波、王桐君辈,为各报章所激刺,为文明客所劝告,猛然醒悟,毅然改计异日革除相工之恶习,恢复优人之资格”11燕公:《花界外稿·答瘦棠花界问题》(六),《顺天时报》1907年5 月3 日,第5 版。。姜慧波、王桐君后来更为人熟知的名字是姜妙香、王琴侬,他们是较早力图终止媚人之业,凭借演出重塑人格的先行者,后均取得了不凡的艺术成就。不久这种自觉便在北京梨园扩散了开来,1909年,路玉珊、赵仙舫、俞振庭、王瑶卿、杨朵仙等名伶联合倡议:“将梨园、应酬分为两途,应酬者不得登台演戏”。这经梨园公议后以精忠庙首田际云、谭鑫培、余润仙、余玉琴的名义通知各班,有来自12 个戏班的承班、领班共27 人签押认可。12《请看梨园公议知单办法》,《正宗爱国报》1909年12 月14 日,傅谨主编:《京剧历史文献汇编·清代卷·续编》(四),第539—540页。通过将“应酬”从“梨园”当中分割,伶界以实际行动表达了对独立而有尊严之人格的强烈要求。
梅兰芳幼年因家道中落,曾住进云和堂私寓。①清末一份花谱便记有:“前景和 兰芳 偶应局 附住云和”,见菊佣:《燕兰续谱》,傅谨主编:《京剧历史文献汇编·清代卷》(二),第499页。“景和”指梅兰芳祖父梅巧玲经营的景和堂私寓,当时已停业。他晚年回忆自己9 岁那年到姐夫朱小芬家里学戏②梅兰芳:《舞台生活四十年》,傅谨主编:《梅兰芳全集》(第4 卷),北京:北京出版社、中国戏剧出版社,2016年,第26页。,所指即为此事。后来薛观澜曾忆及“畹华隶云和堂七载”③薛观澜:《我亲见的梅兰芳》,台北:秀威资讯,2015年,第111页。,据此可推断其身处私寓中大约是在1902-1909年间,而这恰为私寓走向凋零的时期。据清末京官许宝蘅追忆:“初入都时,雏伶之著者,云和堂、安华堂、国兴堂、颍秀堂诸家,选酒征歌,颇极一时之胜,戊申国恤遏密之后,遂亦寂寥。”④许宝蘅:《许宝蘅日记》(第3 册),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881页。戊申国恤即1908年的光绪与慈禧两宫大丧,已在观念层面被否定的私寓经营至此进一步受到国丧禁戏的冲击,再也未能恢复元气。至1912年民国建立,这种“旧染污俗”终被彻底取缔,在巡警总厅发布的告示中,“操业优伶,于国民之资格无损”被着重加以强调,旦角的人格地位得到了新政权的明确认可。⑤张次溪:《燕归来簃随笔》,《清代燕都梨园史料》,第1243页。
这番转变大幅改变了旦角的职业面貌。在私寓时代,因需在台下陪筵侑酒,旦角的职业生命极短,“不过五年为一世耳”⑥杨懋建:《京尘杂录》,傅谨主编:《京剧历史文献汇编·清代卷》(一),第464页。,韶华逝去后很快便会被新人取代。随着私寓被禁,艺术成为其安身立命的根基,旦角与绝大多数观众之间的关系也被限定在了戏台上下,这使他们有了凭借艺术表现而长盛不衰的可能。对梅兰芳而言,这一转变的意义尤为重大,因他幼年相貌平平,性格内向,不善交际,以艺术表现取代应酬能力作为旦角的评判标准正是扬其所长、避其所短。据其姑母回忆:“他幼年的相貌,也很平常。面部的构造是一个小圆脸。两只眼睛,因为眼皮老是下垂,眼神当然不能外露。见了人又不会说话。”⑦梅兰芳:《舞台生活四十年》,傅谨主编:《梅兰芳全集》第4 卷,第12页。也有私寓中的客人记载他“应客之际,端坐无言,每有含羞之态”⑧睡佛:《兰芳戏曲佳妙》,《顺天时报》1907年6 月9 日,第5 版。。这些腼腆特质与需要八面玲珑才能应付周全的交际场并不相宜。但若以舞台艺术表现而论,出生于三代梨园世家、自幼开始学艺并很早便登台演出的梅兰芳在无形中便已占据了一定优势。⑨梅兰芳在自述中便提及自己因需补贴家用,相较于同伴来说登台较早,受舞台之益颇多。梅兰芳:《舞台生活四十年》,傅谨主编:《梅兰芳全集》(第4 卷),第28页。
与此同时,自重与自爱意识进一步普及到了一般旦角个体及其周边亲属当中,这在初出茅庐的梅兰芳身上也有体现。革命后不久,招伶侑觞的习气在社会上仍有残留,但梅的长辈已在极力反对他参与相关场合。有这样一则记载称:
易实甫至京师,必欲获交梅郎以为快。得粤人某之介,设筵以延畹华。次日复欲宴客于其家,畹华已诺之矣。及归,大琐妇闻此事,则盛怒,召畹华至,痛责之,谓幸时会,乃脱贱业,兹复欲尔耶!畹华屏息不敢声。⑩姚鹓雏:《姚鹓雏文集》杂文卷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662页。
“大琐妇”即梅兰芳的伯母。面对易实甫这位文人雅士,她能以决绝的姿态表示排斥,这清晰体现了清末民初士人权势的衰落与国民平等观念的深入人心。后来梅兰芳能够专心于艺术修炼并保持高尚的人格,与此家风当不无关联。后来便有人针对此事评论道:“伯母督之綦严,无放辟邪侈行,故同辈如朱幼芬、朱素云等皆以淫败其喉,而兰芳独完,实守伯母之教也。”11潘国存编:《梅冷生集》,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第197页。很快,梅兰芳也对在此社会风气转移的过程中伶人应具备起的形象具备起了清醒的认知,开始自觉与带有私寓嫌疑的行为划清界限。据齐如山记述,二人相识之初(1912-1914年间),梅兰芳“为自己名誉起见,决定不见生朋友,就是从前认识的人也一概不见。”12齐如山:《齐如山回忆录》,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113—114页。1913年也有记载:“梅郎自谢绝风尘,一意歌舞之后,平时不越雷池一步,自有清规。”①逋仙编:《梅兰芳》,谷曙光编:《梅兰芳珍稀史料汇刊》(四),北京:学苑出版社,2015年,第1701页。这种自爱意识是顺应新时代要求的,对其日后艺术家形象的确立至关重要。
国民社会的到来开启了旦角的新生命时代,使他们得以摆脱“贱民”的身份制约,具备起“明星化”的潜质。亲历者在观察梅兰芳之成名时多会提及于此,如穆儒丐所述:“向之伶人,虽供奉内廷者,仅足温饱,无能富且贵也。民国以来,如梅兰芳辈,殖产百万,勿论矣。且谥以美号,几一跃而为民国总统。”②穆儒丐:《北京梦华录》,北京:北京出版社,2016年,第89页。在具备独立平等的国民身份之后,梅兰芳等何以能一跃至此?这自然离不开背后广大观众的追捧与支持。下文将着重对此展开分析。
二、女性进入公共空间与旦角发展的新动向
梅兰芳身为旦角,以其塑造的女性形象俘获了广大观众,这点当无疑义。值得思考的是,为何在民初戏台上女性角色大受欢迎?梅兰芳在其中又发挥了何种作用?曾经《申报》上便有人提出:“梅兰芳氏受一般群众的欢迎到这样田地,是否全靠他一己色相的美丽与艺术的到家?恐怕不尽然嘛!于伶界的历史,我虽然一点没有分晓,但想自有演剧以来以至今日,其中谅亦不少如梅兰芳的色相与艺术,然终没有听见过如梅氏的倾倒群众、洋溢四海。”③佛:《现在中国艺术化的梅兰芳》,《申报》1926年11 月25 日,第5 版。对此,他将原因归结为“时势造英雄”与“英雄造时势”,然并未详加探讨。今日笔者亦可由此两点入手展开分析。就“时势”而言,清末民初女性观众进入戏园使得梨园中旦行的地位大幅抬升;就“英雄”而言,初出茅庐的梅兰芳在师友帮助下对以往表演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既迎合了时代需求,又推动了旦角地位抬升的进程,且为后来者做出表率。
晚清北京的公共戏园有两大特点:第一,观众皆为男性;第二,台上最重要的是老生行当。有记载称:“京师戏园向无女座,妇女欲听戏者,必探得堂会时,另搭女桌,始可一往,然在洁身自好者,尚裹足不前。”④徐珂编:《清稗类钞》(第11 册),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5065页。这主要是出于儒教伦理的要求及政府维护社会风俗的考虑。因此,晚清北京公共戏园中的欣赏品味可谓是由男性观众单一塑造的。自道光以来,京剧中便形成了以程长庚、谭鑫培等老生为代表的“前后三鼎甲”。老生的艺术精髓主要沉淀于声腔表现,因而北京戏园更侧重“听戏”而不重“看戏”。所谓“贩夫竖子,短衣束发,每入园聆剧,一腔一板,均能判别其是非,善则喝彩以报之,不善则扬声以辱之,满座千人,不约同意”⑤王梦生:《梨园佳话》,上海:商务印书馆,1915年,第9页。,可谓生动概括出了晚清北京的“听戏”景观。老生走红或与晚清男性世界与儒家正统秩序遭遇的危机有关。因“所谓老生者,扮为贤相、忠臣、儒将、学者等脚……究不外代表善人正人等男性脚色”⑥波多野乾一:《京剧二百年历史》,鹿原学人译,上海:启智印务公司,1926年,第3页。,他们扮演的多为正统男性形象,是道德伦理的象征。在士大夫心中,老生的声腔中隐约潜藏有一条符合礼乐秩序的古音脉络,可将人们带回过往的理想境界,如孙宝瑄称:“京腔中老生所唱者,虽词涉鄙俚,而音节悲感苍凉,能曲传忠臣孝子仁人志士之胸怀。”⑦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348页。郑孝胥也记述:“夫乐者生于人心,声成文谓之音,此皆自然常存。故古乐虽亡,而人心之寄于音,不得而亡。特世变愈异,则音不轨于正耳。咸同以来,京师极尚二簧。余幼时犹及见程长庚、余三胜、张二魁等,皆名盛一时。”⑧郑孝胥:《郑孝胥日记》,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308页。可以想见,随着时局的动荡,老生所展现的正统形象与其声腔中传递的家国情怀尤其能够打动人心。
清末的社会变化打破了这一格局。随着秩序松动与观念革新,大量女性开始出入北京的公共戏园。1900年庚子之乱时,便曾出现“所有大家宅眷,咸趁此时会,争赴剧场。粉黛盈盈,座为之满”⑨狄葆贤:《平等阁笔记》,台北:弥勒出版社,1984年,第2页。的情形。秩序稳定后此风虽暂中止,但实已不可遏制。自1907年起,戏园多正式辟出了女客专区,如日华戏园“男女各有分座位”①《顺天时报》1907年5 月1 日,第6 版。,文明茶园将楼上专设为女客区,“堂客另由一门出入,不是和官客一个门”②《文明茶园听戏记》,《顺天时报》1907年11 月30 日,第5 版。。丹桂、吉祥等戏园也纷纷效仿。当时“一般白胡子老头儿总说风俗坏了。然而梨园买卖,日见兴隆。这些老头儿的姨太太前去买座,老头儿有装做不知的,有同姨太太一齐来的”③潘镜芙、陈墨香:《梨园外史》,北京:宝文堂书店,1989年,第403页。。可见这股潮流之强劲。最早入场观剧的女性多来自上层,后来关于下层女性观剧的记载也开始出现,如在1910年的天桥庆祝国会大戏棚中,戏台两旁便“妇女不下千人,于是不免有下等社会的妇人彼此拥挤,破口相骂”④《戏棚记事》,《顺天时报》1910年11 月17 日,第7 版。。
这些女观众可谓一股新鲜血脉,她们带入了新的审美品味,引发公共戏园中欣赏方式的改变。由于当时女观众尚鲜有能将观感诉诸文字者,可经由男性戏迷的笔端对此加以体察。许多老戏迷都曾提及女性的不同品味,如张燕侨对各类观众进行区分:“老于看戏、确有研究者,喜看大段唱做之戏;初出后进之爱看戏者,喜看穿插热闹之戏;妇女喜看长本家庭戏;儿童喜看滑稽布景戏。种种不同,总之因其性之相近。”⑤张燕侨:《廿年来戏剧杂谈》,《戏剧月刊》1928年第3期,第1页。王梦生记载:“‘全本戏’专讲情节,‘唱工’不贵。……近岁新排者如《雁门关》,如《五彩舆》,皆累日而不能尽,此类最为女界所欢迎,在剧中亦必不可少。”⑥王梦生:《梨园佳话》,第53页。许姬传分析称:“男看客听戏的经验,已经有他的悠久的历史,对于老生武生的艺术,很普遍地能够加以批判和欣赏。女看客是刚刚开始看戏,自然比较外行,无非来看个热闹,那就一定先要捡漂亮的看。像谭鑫培这样一个干瘪老头儿,要不懂得欣赏他的艺术,看了是不会对他发生兴趣的。所以旦的一行,就成了她们爱看的对象。”⑦梅兰芳:《舞台生活四十年》,傅谨主编:《梅兰芳全集》(第4 卷),第126页。更有怀旧者直接感慨:“观众多为妇孺,喜粉面而憎老脸,取热闹而舍艺术矣!”⑧商隔馆主:《旧剧漫谈·旦盛生衰之原因》,《立言画刊》1938年第12期,第4-5页。归结起来,女性更为侧重的是剧中的情节、表现与直观美感,“看戏”是更能得到其认可的方式。这意味着在剧情推动与视觉呈现方面更具优势的旦角行当将愈发重要。民国剧评家陈墨香认为,旦角崛起的趋势在清末便已显现,评论1904年旦角王瑶卿新排的《梅玉配》完胜老生李鑫甫新排的《孤注功》一事时他即指出:“旦角压倒老生,这便是先例。本戏材料,男女香艳事迹,胜似军国大事,这也是榜样。”⑨潘镜芙、陈墨香:《梨园外史》,第399页。
梅兰芳的早年成名与上述趋势直接相关。他的许多观众正是新近入园观剧的女性,1916年便有人记述:“兰芳风华既盛,香车宝马络绎来者,尤以大家闺秀为盛”⑩潘国存编:《梅冷生集》,第197页。,甚至“名姬荡妇,尤人人欲得而甘心焉”11凤笙阁主辑录:《梅兰芳》(下编),上海:出版社不详,1918年,第5页。。剧评家冯小隐也指出,民国之后“阔人姬妾,常虞银钱无处可用,而听戏亦为赏心乐事之可以销耗金钱者。若辈于戏绝无所知,但求人物之漂亮,衣饰之新奇,即为若辈所注意……此梅兰芳之所以能投机,为不世出之人才也”12冯小隐:《顾曲随笔》(七),《戏剧月刊》1930年第11期,第2页。。此语虽略带讥讽,但亦点出了当时女性品味与梅兰芳崛起之间的关联。只是其所谓“投机”,却并非仅以简单的“人物之漂亮,衣饰之新奇”一语便足以概括,其背后尚应包含梅兰芳为旦角艺术改革付出的诸多努力。这主要可从以下两点观察:
其一,改变传统青衣只重唱工的路径,更注重舞台的视觉呈现。旦行向以青衣和花旦为主。花旦饰演活泼灵巧者,青衣则饰端庄稳重者。传统青衣艺术“专重唱工,对于表情、身段,是不甚讲究的。面部表情,大多是冷若冰霜。出场时必须采取抱肚子身段,一手下垂,一手置于腹部,稳步前进,不许倾斜。”梅兰芳自幼主攻青衣戏,但在民初即开始对传统路径大加改革,这主要得到了前辈王瑶卿的帮助。王瑶卿是青衣中率先突破传统藩篱者,“他注意到表情与动作、演技方面,才有了新的发展”。其主要贡献在于糅合青衣与花旦之长开创了“花衫”行当,兼具端庄与灵动,在清末曾大放异彩,只是他中年后嗓音败坏,鲜少登台,而梅兰芳正是“向他请教过而按着他的路子来完成他的未竟之功的”①梅兰芳:《舞台生活四十年》,傅谨主编:《梅兰芳全集》(第4 卷),第30—31页。。这正与女性观众带来的新品味正相吻合,后来有人称梅能够“就前人演戏的原则,参加己意,化出种种的新腔,发明种种的身段……藉此标新立异,迎合社会的心理”②豁公:《哀梨室戏谈》,《剧学月刊》第1 卷第4期,第3页。。所道即为此意。此后,“一般正旦唱起这路戏来,却都学他这样,并且头衔上面还要加上‘梅派花衫’几个字”③豁:《梅郎小史》,谷曙光编:《梅兰芳珍稀史料汇刊》(四),第1897页。,可见其影响之广泛。
其二,适应男女两性共同参与的观剧环境,剔除旦角陋习,打造新的美感。在全由男性构成的观剧空间中,旦角(主要为花旦)为博人眼球常加入色情成分,被称作“粉戏”。这些因素随着女性大量进入公共空间显得不妥,民国后政府即开始严加整顿,正如梁实秋所述:“一有女客之后,戏里面的涉有猥亵的地方便大大删除了。”④梁实秋:《听戏》,《雅舍杂文》,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12页。管控力度之大,以至于有了“今时无专演花旦者”的说法⑤吴焘:《梨园旧话》,张次溪编:《清代燕都梨园史料》,第826页。。梅兰芳的改革本借鉴了许多花旦的戏路,但他在分寸拿捏上把握得恰到好处,适时塑造出了新的视觉审美。剧评家冯叔鸾在观看其《二本虹霓关》时便称赞:“兰芳之妙,在艳而不淫。”,“梅兰芳之美,天下人所共见共爱者也”。⑥冯叔鸾:《啸虹轩剧谈》卷下,上海:中华图书馆,1914年,第8页。这正顺应了男女两性共同参与公共戏曲欣赏时代的社会新风气。后来,通过与文人齐如山、李释戡、樊樊山、张謇、陈彦衡等合作,梅兰芳更从传统书画及昆腔戏中借鉴了许多元素,进一步去除了传统戏中狎亵不堪和粗俗无聊的部分,形成一种古典雅致之美,“能令顾曲家荡气回肠而不能自已,歌舞合一,有复古之功,群以梅派尊之”⑦无盦居士:《梅兰芳小传》,庄铸九等编:《梅兰芳》,上海:出版社不详,1926年,第3页。。
综上可见,梅兰芳的成长恰逢梨园审美因女性观众的大量涌入而发生改变之际,他以青衣新秀身份适时地对传统表演加以改革,把握住了这一形势。这不仅俘获了大量观众,更使他发展出了自己的艺术流派,并进一步提高了旦角地位。民国后不久,梅兰芳的地位便几乎可与享名数十年的老生谭鑫培并驾齐驱,在催戏单上,“谭梅”二字常常并列而书。⑧梅兰芳:《舞台生活四十年》,傅谨主编:《梅兰芳全集》(第4 卷),第118页。可以说,梅兰芳的早年成名是女性社会力量开始形成的一个信号,它意味着一个由男女两性共同参与构建的、更为开放与多元的公共空间正在形成。
但同时也需注意,清末民初的女性尚多不具备公共言说的条件,她们虽可经由实际参与影响梨园风气,但却很少能够直接作用于梅兰芳盛名的塑造与宣传。因此,研究的视线尚需转移到更为广阔的城市娱乐世界,尤其需要注重当时依托报纸书刊形成的印刷传媒空间。
三、印刷传媒的时代:报刊捧旦风潮及京沪间的交流
晚清以后,北京、上海等地的印刷传媒均得到了长足发展。为招揽读者,许多报刊都时常刊载关于伶界的报道以及戏评文章,不少娱乐小报也开始出现。这为戏曲娱乐带来多方面影响,其中与梅兰芳成名息息相关者主要有两点:第一,为捧旦风潮提供了平台;第二,促进了京沪之间娱乐文化的交流。二者皆为梅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
报刊捧旦风潮与清末民初社会上下对国家与政治的幻灭感有关。随着清政权瓦解,老生传递的家国情怀已部分失去市场,曾有人在听罢谭鑫培的《碰碑》与《卖马》后不禁悲叹:“已无天可叫,凄绝老何戡。犹是当年曲,居然亡国音。碑存谁肯碰?锏当莫沉吟。我亦男儿汉,无钱抱恨深。”⑨张肖怆:《菊部丛谈·歌台摭旧录》,上海:大东书局,1926年,第28页。该论意指“亡国”之后,已绝少再有肯效法杨业之忠君报国、秦琼之自重身份的人物,这无形中会减弱老生的意义。而自清末国家推行新学以来,一些受传统熏陶者已开始感到疏离苦闷,索性自甘颓废,北京便有人如此标榜:“吾宁沉湎于声色,而甘居于人之所谓下流者”,“吾之谈剧学,一若醇酒妇人,良得我心。胜于声光化电家、工商医之学,奚啻十倍”。①樲社:《剧谈·讨论评剧之伟言》,《燕报》1911年8月3日,傅谨主编:《京剧历史文献汇编·清代卷》(六),第551—552页。沉湎声色与“醇酒妇人”促使了旦色地位的抬升,这构成了梅兰芳早年成名的另一背景。民国后,许多丧失了国家寄托的“遗老”更以梨园为避世抒怀的乐土,如易顺鼎“民国以来,以满腔幽愤,一寄之于金樽檀板之间”②王森然:《近代名家评传二集》,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第95页。。罗惇曧“偃蹇人海二十余年,日以征歌选舞为事”③李宣倜:《李宣倜序》,罗惇曧:《鞠部丛谈校补》,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6年,第5页。。此时正对旦角艺术大加改革的梅兰芳自然受其高度关注。所谓“遗老本人虽不必然到处受人欢迎,而遗老之一管秃笔却具有伟大力量”④四戒堂主人:《记樊易罗》,《立言画刊》第73期,1940年,第9页。。他们的颂扬对梅之成名贡献极大。在当时,仅易顺鼎为梅兰芳创作的《万古愁曲》便曾被十多家刊物反复转载,流传极广。随着民国政局乱象的显现,热衷于通过报刊捧旦的阵容也日益壮大,并出现了“党争”局面。这一“党”字即寄托了时人对政局的不满与嘲讽:“夫剧界之有党也,始自贾碧云。人之党贾也,实以厌恶政党之翻覆污浊,故托言与其势力结合,奉亡国大老暴乱渠魁为党首,毋宁以色相取人,倾心低首于清歌曼舞工颦善笑之贾郎。”⑤冯叔鸾:《啸虹轩剧谈》卷上,第60页。“贾党”在上海诞生后,很快便出现了捧冯春航的“冯党”与之对峙。不久北京也出现“朱党”(朱幼芬)与“梅党”(梅兰芳)。所谓“南有冯贾,北有梅朱。”⑥逋仙编:《梅兰芳》,谷曙光编:《梅兰芳珍稀史料汇刊》(四),第1741页。各党相互之间“笔鏖舌战,凌厉风云”⑦冷佛先生:《梨云影》续编,傅谨主编:《京剧历史文献汇编·清代卷》(二),第472页。。与此同时,一些随革命而流行起的新观念也被加以“创造性阐释”。如易顺鼎便将“天下为公”之意融入捧梅诗歌:“吾之咏梅诗,乃是代表古今天下人民心理而为之,若专属我则谨辞。譬如议院推举一总统,此议员者不过代表全国人民以示护与拥,岂能谓此总统乃我一人捧。菊魂我今且勿论,请论数千年来之梅魂。数千年来之梅魂,乃在梅郎兰芳之一身”⑧易顺鼎:《哭庵赏菊诗》,张次溪编:《清代燕都梨园史料》,第749页。。后来他更发挥此意,“品定梅郎作国花”⑨易顺鼎:《哭庵赏菊诗》,张次溪编:《清代燕都梨园史料》,第760页。。1913年国会选举总统之时,竟有议员果真在选票上写下了梅兰芳的名字。⑩顾颉刚:《顾颉刚日记》(第1 卷),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14页。这充分体现了当时报刊捧旦风潮的影响力。
参与捧旦的有社会各类成员。易顺鼎的另一首捧梅诗中曾道:“冯郭娄黄罗谢我,固应唤作国花颠。”11易顺鼎:《哭庵赏菊诗》,张次溪编:《清代燕都梨园史料》,第755页。其中提到的7 个人分别是冯幼伟、郭逋仙、娄休莫、黄秋岳、罗瘿公、谢苏生和他自己,这或可被视作当年“梅党”的核心。这些人中不仅包括前朝遗老(易、罗)与军政中坚(冯、黄),还有像郭逋仙这样几乎与梅同龄的年轻学子,可谓已涵盖了社会中较为广泛的群体。其中年轻人加入捧梅队伍尤为值得关注,因为他们资历较浅,常常格外卖力,如郭逋仙便常摆出类似“非梅郎之剧不观”12逋仙编:《梅兰芳》,谷曙光编:《梅兰芳珍稀史料汇刊》(四),第1734页。的姿态,并为梅编印了第一部宣传专集。作为拥有明确归属意识的支持者,这些人为梅兰芳声名的扩展不遗余力。
经由报刊捧旦的宣扬,梅兰芳在民国元、二年间已成为北京炙手可热的新秀。但在当时,仅在北京成名已不再意味着伶人事业的顶点。印刷传媒发展带来的另一后果是全国正在成为一个紧密联系的整体,在其他城市引发的反响同样会影响伶人声誉。北京之外,最重要的城市莫过于上海。梅兰芳全国性盛名的取得,还需得到沪上观众的认可。
当时京沪之间的娱乐消息经由报刊等媒介已有了密切交流。前述“党争”在上海出现后很快蔓延至北京即是一例。当时身在北京的戏迷也很注重通过报刊等途径获取沪上梨园消息,如北京大学的预科学生顾颉刚在日记中便记载1913年10 月7 日他通过《时事新报》了解到上海醉舞台的名角情形,21 日又通过友人寄来的《新闻报》得览沪上各戏园的剧目。①顾颉刚:《顾颉刚日记》(第1 卷),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10、23页。由此,印刷传媒对京沪之间戏曲娱乐信息交流的促进可窥一斑。
当时京沪戏曲文化之间的张力颇有趣味。上海受传统的束缚较少,在很多方面都领风气之先。以女性观剧一事为例,在同治初年沪上戏园便已是“鬓影衣香,丁歌甲舞,如入众香国里,令人目不暇赏”②黄世权:《淞南梦影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16页。。这较北京约早40年。由此,相较于北京重视声腔的传统,上海戏园从一开始便注重视觉表现。但是,积淀的缺失也限制了上海戏曲的发展,其新潮很难转化为真正持久的艺术呈现,反而容易被北京超越。顾颉刚初入都时便发现:“在南每闻人言,北剧重唱不重做,故言观戏曰听戏。自今视之,观者虽大部注意于听,而其做工尤非南所可及,故知耳食者之无真也。”③顾颉刚:《致叶圣陶 八》,《顾颉刚书信集》(第1 卷),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10页。这说明一旦风气开通,北京很容易便能后来居上。因此,某种张力凸显于当时的南北戏曲娱乐之间。一方面,北京代表艺术发展的最高水平,沪人每每对京角十分看重。1867年首次有京班至上海,便使沪人“趋之若狂”。④周剑云主编:《鞠部丛刊·歌台新史》,上海:交通图书馆,1918年,第3页。1911年上海文明新剧社也“因有京角客串,卖座极为拥挤,几无容足之地”⑤慕优生编:《海上梨园杂志》(卷7),上海:振聩社,1911年,第28页。。另一方面,上海观众也有自己较为稳固的审美品味,不会一味唯北京马首是瞻。1912年谭鑫培赴沪演出时,便因未能迎合当地口味而被喝倒彩。⑥吴性栽:《京剧见闻录》,北京:宝文堂书店,1987年,第8—9页。这种张力构成了对赴沪京角的一大考验,如何寻求平衡是其必须面对的问题。
在此背景下,梅兰芳于1913年11 月4 日开始了首次沪上演出,连续演出了45 天。此行中他充分发挥了主观能动性,将南北间的张力转化为对自己的助力,并在印刷传媒的推动下成功取得了全国性声名,走上更为宽广的道路。
到上海后,梅兰芳最先着手的一件事便是主动结交报界与文界的名人。据其回忆,登台前,他便“拜访过主持《时报》的狄平子、《申报》的史量才、《新闻报》的汪汉溪”,“还认识了许多文艺界的朋友,如吴昌硕、况夔笙、朱古徽、赵竹君等”⑦梅兰芳:《舞台生活四十年》,傅谨主编:《梅兰芳全集》(第4 卷),第139—140页。。这在当时可谓开启了一个新时代,引得后来者纷纷效仿:“从前梨园到上海只知唱戏,他不理人人也不理他。自从梅郎到申改了风气,竞把本地名流礼尚往来,大交朋友,因此梨园身份日见增高,梅郎的名望也日加广播。伶人到了上海除了登台之外,还得应酬外行,比起谭鑫培、汪桂芬画后台以自守,成败听天,反正我就是来唱戏的,差的不可以道里计了。”⑧潘镜芙、陈墨香:《梨园外史》,第428页。不久之后,梨园行内对报纸的重要意义便已可谓人尽皆知,“唱戏的小孩子,也要报看。报上若说他们两句好话,乐得要上天。若说他们两句坏话,哭得不吃饭”⑨穆儒丐:《北京,1912》,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5年,第69页。。可以说,最先意识到这一趋势并积极采取行动的便是梅兰芳的这次沪上拜访。
梅兰芳并非仅在宣传层面努力,更注重将自身的艺术底蕴与沪上观众品味加以融合。在演出之前,戏园在《申报》上连续15 天登的广告为梅兰芳备注的都是“第一青衣花旦”⑩《申报》1913年10 月16 日至31 日,第9 版或第12 版。。将“花旦”之名加于素以青衣见长的梅兰芳乃是为了吸引观众,如当时顾颉刚所推测:“报纸谓其兼演花旦者,盖沪人习尚,非此不欢,乃姑为此欺人之言耳。”11顾颉刚:《顾颉刚日记》(第1 卷),第24页。演出后不久,梅兰芳便对沪人更为喜爱灵巧戏路的习尚有了切身感知,知道观众对“专重唱工,又是老腔老调的戏,仿佛觉得不够劲了。他们爱看的是唱做并重,而且要新颖生动一路的玩意儿”12梅兰芳:《舞台生活四十年》,傅谨主编:《梅兰芳全集》(第4 卷),第148页。。在朋友建议下,他赶学了《穆柯寨》这部更为灵动的刀马旦戏,并以此贴演大轴。这引发了轰动,有观众在去看时,“台下已无隙地,只好上台观听矣”①逋仙编:《梅兰芳》,谷曙光编:《梅兰芳珍稀史料汇刊》(四),第1716页。。这部现学的戏也成了他此行出演最多的一部。②张斯琦编:《梅兰芳沪上演出记》(上),上海:中西书局,2015年,第2页。既不失京角水准,又充分迎合当地观众,是梅兰芳沪上演出成功的重要原因。
当时北京一班热心的“梅党”正时时通过报纸转述上海的情形,汇成“梅消息”与“海上传来之梅消息”公之于众。③这些内容今可见于逋仙编:《梅兰芳》,谷曙光编:《梅兰芳珍稀史料汇刊》(四),第1697—1729页。通过京沪间的对话,梅兰芳正式确立了其在全国范围内的声誉,也进一步提升了旦角地位。至1916年三度赴沪时,他已正式替代老生王凤卿主演大轴戏。1917年谭鑫培辞世后,梅兰芳成为新一代的梨园代表已可谓顺理成章。
四、结语
史学家杨联陞曾总结出“游艺说”(game theory):“艺术与文学的某种特定形式是要遵守某一套规则,就像任何竞争性的比赛需要技巧一样。在这些规则下,只有一些有限的可能会被与赛者察觉,而那些察觉到最佳可能的人就成了杰出的大师。当然,那些发现有许多可能的新玩法,或者将一种旧游戏加以修改,使它更加好玩的人,也都是出类拔萃的。”④杨联陞:《国史探微》,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年,第20页。在察觉“最佳可能”与发现“新玩法”方面,梅兰芳都走在了时代前列。通过前文的探讨可知,梅兰芳的早年成名是清末民初之际伶人的人格解放、女性进入公共空间、印刷传媒的发展以及捧旦风潮兴起、南北交流加强等因素合力造成的结果,可谓社会变迁的一个综合缩影。放长历史的视线,可发现其中许多趋势在今日的娱乐世界仍有所延续,或许可以说,梅兰芳是中国第一位具备现代特质的“娱乐圈明星”。
在梅兰芳成名背后,曾以士大夫为中坚并由皇权作保障的儒教秩序正在渐行渐远,过去被压抑的需要迅速得到了释放,一时之间社会呈现出生动而富有活力的面相,这为人们留下了许多值得纪念的可贵遗产。例如,此时大量由“贱民”成为独立国民的伶人对新身份备感珍惜,梅兰芳及与之同时代大批艺人均以极大热情投入到对艺术的打磨当中,最终成为值得后人感佩景仰的大师,这与他们亲身经历的转折便不无关联。又如女性品味的注入促使传统旦角艺术得以革新,后来“四大名旦”均以各自的方式继往开来,打造出了一批宝贵剧目,其中许多至今仍在传承,并通过舞台给观众带来持久的审美享受与心灵震撼。追根溯源,这些均与清末民初的社会新动向密不可分。
然而生机之外并非没有危机,这一时期的许多现象亦可用一“乱”字形容。前文述及的大批文人将生命寄托于捧旦以及在总统选举时有议员投梅一票之事,便为显例。当时还有大批青年男女竞相沉迷于戏曲娱乐,如某女子“每日观兰芳剧后,归辄凝思,久之成病”,后“必欲得梅郎而嫁之”。⑤凤笙阁主辑录:《梅兰芳》(下编),第8-9页。类似现象同样是从那个时代开始广为出现的。民国时的旗人作家穆儒丐也曾认为,“四大名旦”的表率作用“致使良家子弟,不务正业,多入梨园,藉欲享富贵,出入骄人”,并由此感叹“国之不竞,岂无因哉!”⑥穆儒丐:《北京梦华录》,第89页。他将原因归结为纪纲的堕落,并发表了大量带有怀旧色彩的言论,希望能够重拾旧日道德,但时代的演进意味着其梦想终将落空。最终起而重建新秩序的是“五四”一代,他们的策略则是将旧戏与整个封建文化结合起来彻底打倒。在这些人笔下,梅兰芳又呈现出另一番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