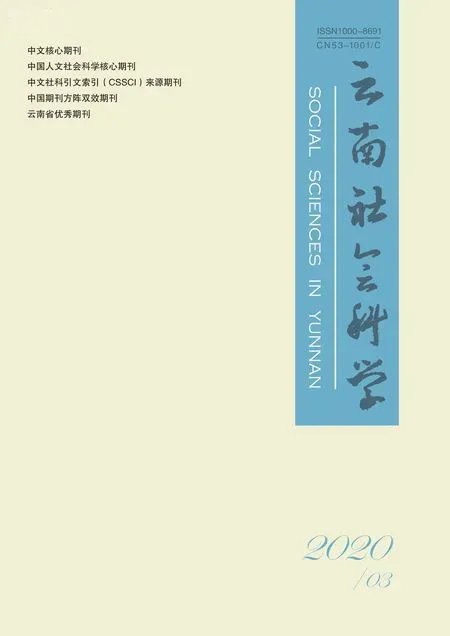作物结构、生计体系与产业扶贫的有效性机制
——基于华东一个县域的经验研究
2020-06-08熊春文
熊春文 桑 坤
无论是脱贫攻坚还是乡村振兴,乡村产业都是强有力的内在支撑。为此,乡村振兴强调产业兴旺,脱贫攻坚着重依托特色产业来带动贫困人口脱贫和致富。农业是乡村社会主要的生产方式,因而产业扶贫也多以农业为着力点,试图通过调整农作物结构、更新技术、注入资本、改换农民生计体系来实现脱贫致富乃至达到农业现代化。关于农业现代化,舒尔茨(Theodore W.Schultz)认为农业无法贡献经济增长、农民难以摆脱贫困的原因在于传统农业缺乏现代生产要素,国家要为改造传统农业注入技术、资本、人力等要素,并使农民易于获得它们。①[美]西奥多·舒尔茨:《改造传统农业》,梁小民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125—134页。显然当下产业扶贫中政府的做法无疑与舒尔茨的主张吻合。然而在产业扶贫项目实施过程中,并非如政策设计的初心那样得始终,许多产业扶贫出现目标靶向偏离②李博、左停:《精准扶贫视角下农村产业化扶贫政策执行逻辑的探讨——以Y 村大棚蔬菜产业扶贫为例》,《西南大学学报(社科版)》2016年第4期。、贫困户内生动力不足③侯昭华、宋合义:《“顽疾”还是“误诊”?产业扶贫“内生动力不足”问题探究》,《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2020年第2期。、产业同质化产品过剩④李冬慧、乔陆印:《从产业扶贫到产业兴旺:贫困地区产业发展困境与创新趋向》,《求实》2019年第6期。的情况,甚至沦为“亮点工程”以至脱嵌于乡土之外,无法达到预期的政策效果,也就难以改造传统农业。农民是理性的,并非无法理解或是不愿使用新技术、改种新作物、接纳新产业。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这些措施没有达到预期目标呢?
一、文献回顾与研究进路
自精准扶贫乃至国家实施发展政策以来,对于国家治理与农村发展的讨论就未曾停歇。农业产业扶贫形式多样,而关于扶贫产业为何达不到预期目标,学界主要有三种解释。
第一种解释关注产业扶贫模式。有学者将多样化的产业扶贫归纳为产业发展带动扶贫模式、救济式产业帮扶模式和瞄准型产业帮扶模式。①林万龙、华中昱、徐娜:《产业扶贫的主要模式、实践困境与解决对策——基于河南、湖南、湖北、广西四省区若干贫困县的调研总结》,《经济纵横》2018年第7期。也有学者将之归纳为企业带动型、合作社或大户带动型、电商带动型等模式,②孙久文、唐泽地:《中国产业扶贫模式演变及其对“一带一路”国家的借鉴意义》,《西北师大学报(社科版)》2017年第6期。并认为这些模式存在精准性不足、无法规避市场风险、背离“能力扶贫”的初衷,难以提高贫困人口可持续发展能力等问题。进一步,不同类型扶贫模式背后隐含差别的资源利益分配,③罗楚亮:《农村贫困的动态变化》,《经济研究》2010年第5期。若产业与贫困户利益联结不够紧密,极易造成分配不均。④周华:《益贫式增长的定义、度量与策略研究——文献回顾》,《管理世界》2008年第4期。虽可提升地方经济发展,但未必能带动贫困户脱贫。
第二种解释关注产业项目实施。这类解释认为扶贫政策执行机制得不得当造成项目资源或被精英俘获⑤黄承伟、邹英、刘杰:《产业精准扶贫:实践困境和深化路径——兼论产业精准扶贫的印江经验》,《贵州社会科学》2017年第9期。、或与市场存在冲突⑥渠敬东:《项目制:一种新的国家治理体制》,《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5期。。产业扶贫失败的原因在于基层政府主导、依托主体弱、扶贫资源的股份化运营成本高等不利于项目可持续性。⑦梁栋、吴惠芳:《农业产业扶贫的实践困境、内在机理与可行路径——基于江西林镇及所辖李村的调查》,《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科版)》2019年第1期。、⑧刘军强、鲁宇、李振:《积极的惰性——基层政府产业结构调整的运作机制分析》,《社会学研究》2017年第5期。甚至依托的企业自我逐利性过强、农村经济合作组织能力弱、贫困户主动参与不足,使得产业扶贫缺乏社会基础而失败。⑨胡振光、向德平:《参与式治理视角下产业扶贫的发展瓶颈及完善路径》,《学习与实践》2014年第4期。、⑩王春光、单丽卿:《农村产业发展中的“小农境地”与国家困局——基于西部某贫困村产业扶贫实践的社会学分析》,《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科版)》2018年第3期。此外,扶贫产业本身求政绩的行政逻辑、求效益的市场逻辑与济困的道德逻辑相互消解,因而产业扶贫不仅没提高贫困户的致富能力,反而陷入新的风险中。11陈恩:《产业扶贫为什么容易失败?——基于贫困户增能的结构性困境分析》,《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2019年第4期。、12梁晨:《产业扶贫项目的运作机制与地方政府的角色》,《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科版)》2015年第5期。、13蒋永甫、龚丽华、疏春晓:《产业扶贫:在政府行为与市场逻辑之间》,《贵州社会科学》2018年第2期。、14许汉泽、李小云:《精准扶贫背景下农村产业扶贫的实践困境——对华北李村产业扶贫项目的考察》,《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2017年第1期。
第三种解释关注产业类型选择,这类解释认为扶贫产业选择未能考虑地方的自然环境与资源禀赋,对当地发展基础和潜力研判不充分15周保吉、张慧等:《产业选择、利益机制与精准扶贫》,《江苏农业科学》2019年第23期。,产业选择不够科学,造成过于单一、零星分布16陈晓兰、沙万强、贺立龙:《当前扶贫开发工作面临的问题及政策建议——来自四川省广元市苍溪县的调查报告》,《农村经济》2016年第1期。,且难以形成规模与产业体系17许旭红:《我国从产业扶贫到精准产业扶贫的变迁与创新实践》,《福建论坛(人文社科版)》2019年第7期。,更难与周边的市场需求形成功能性的交换体系18黄承伟、覃志敏:《统筹城乡发展:农业产业扶贫机制创新的契机——基于重庆市涪陵区产业扶贫实践分析》,《农村经济》2013年第2期。。产业无法整合进城乡统筹发展的整体,导致产业发展达不到预期效果。
上述三类观点对于解释产业扶贫为何达不到预期效果各有其合理性。归纳起来,学界主要观点是产业扶贫在带动地区经济增长的同时并不必然使农民受益,因为国家提出的扶贫政策与基层政府具体执行之间以及产业发展与扶贫内涵之间存在内部张力,导致产业扶贫项目被差异化实施,因而未能达到预期效果。这些解释为从国家治理层面找寻产业扶贫何以未达到预期目标提供了参考。但这些解释更多关注政府主体,缺少扶贫主体农民的视角。这些研究背后隐含着这样一种假设,产业扶贫是政府的责任,未能达到预期目的也是因自上而下的行动机制存在问题,只要政策治理得当,农业农村的现代化指日可待。如若上述解释有力,那如何理解各地农民具有首创精神的特色实践呢?又如何解释让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的政策逻辑呢?
进言之,上述研究遮蔽了产业扶贫背后的社会文化整体性事实。诚然,在产业扶贫和农业现代化过程中,农民需要国家提供各类生产要素,但农民并非需要政府一直“带着”往前走。在产业扶贫过程中农民有其自主性。尽管有学者已呼吁农民的主体性①王春光:《中国社会发展中的社会文化主体性——以40年农村发展和减贫为例》,《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11期。、②朱启臻:《乡村振兴背景下的乡村产业——产业兴旺的一种社会学解释》,《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科版)》2018年第3期。,却极少整体性地呈现出来,且在政策实践中农民仍处于“被改造”的社会地位。③Byres.T.J,The agrarian question and differing forms of capitalist transition: An essay with reference to Asia ∥J.Breman and S.Mundle.Rural Transformations in Asia.Delhi,Indi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1.在政策实践中,调整甚至替代原有的作物结构成为常见的农村产业扶贫手段。但农民选择什么作物,往往是与其生计体系长期调适的结果。其背后还有当地自然环境乃至社会文化传统的整体关联。以作物结构调整为主要抓手的产业扶贫如不能处理好与农民生计体系的调适问题,极易出现政策失灵的后果。
鉴于此,本文将产业扶贫视为一个总体性事实,运用农业社会学视角与田野调查方法将其置于政府行为、作物结构与农民生计体系的多元因果关系中加以理解,但本文侧重处理因果链的一侧,即作物结构与农民生计体系及乡村社会文化传统的关联性。“农业作为人类一种基本的生产生活方式,始终深深嵌入在宏观政治经济结构与绵长的社会文化传统之中,这是农业社会学的基本洞见。农业不仅仅是一个技术或经济问题,其本质与特性需要在更广阔的社会结构与文化视角中才能得到充分理解。”④熊春文:《农业社会学论纲:理论、框架及前景》,《社会学研究》2017年第3期。农业产业扶贫表面上是对作物结构的调整,实际上必然涉及与农民生计体系乃至社会文化传统的交流与碰撞。新的作物能否嵌入农民的生计体系不单是由政策所决定,更重要在于它能否嵌入乡村既有的作物结构与社会文化生活中,并与农民的家户生计体系相互契合。扶贫政策要全盘考虑农民家户生计体系对于经济效率的不同理解。产业政策的最终目的应该是提高农民的生活支配能力或生活机会。⑤费立民,陆远:《改革时期中国的生活机会:生计、尊重、权利与风险》,《中国研究》2008年第1 辑。韦伯认为一个社会群体的“阶级状况”是由物品获取、人生地位和内在满足共同决定的。⑥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第一卷),阎克文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420页。产业发展的目标不应仅是物的现代化,更应是人的现代化。因而产业扶贫要充分照顾农民的生活机会,使农民在作物选择、产业发展上得到应有的尊重,并保有其支配生计体系、社会关系网络的能力。具体而言,本文要关注的现实问题是:在政府推动的产业扶贫项目中,为什么有些作物为农民所接纳而有些作物却被排斥?农民的家户生计体系是如何选择新作物与新产业的?
二、研究对象与田野点概况
2019年8月和10月,笔者调研团队先后在华东地区的罗县⑦本文依据学术惯例,对文中涉及的所有地名、人名和公司名均进行了匿名化处理。进行了两次实地调查,期间与此后又通过网络与电话多次补充调研。据县志记载,历史上罗县多以粮食作物为主,粮食作物又以水稻为首,大豆、薯芋次之。明万历年间烟叶自菲律宾经由福建传入罗县,清宣统年间又引进白莲,新增少量经济作物,但粮食作物依然占据90%以上的比例。1958年国家提出“以粮为纲”,此后较长时间,罗县经济作物种植比例迅速下降,其中烟叶和白莲种植面积几乎为零。直到1981年政府与民间不同程度地从福建重新引进新的烟叶品种后,罗县的经济作物比例才有所上升。1985年,罗县总播种面积约50万亩,其中水稻约27万亩,烟叶种植面积达8999亩,占经济作物种植面积的15%,与此同时白莲种植恢复迅速达3万亩,占经济作物种植面积的55%。①材料及数据来源于县志,由笔者整理而得。至此,罗县“烟·莲·稻”已基本形成三足鼎立格局,并主导农作物结构长达30余年。据县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12月,罗县总播种面积约有39万亩,其中水稻约25万亩、烟叶约3万亩、白莲约5万亩。
精准扶贫以来,罗县逐渐探索出“3+X”的产业扶贫模式,其中“3”指吸纳贫困户参与“烟·莲·菜”模式增收;“X”指选择发展脐橙、油茶、山地鸡、茶树菇等特色种养产业。这一模式的核心是将原有“烟·莲·稻”结构调整为“烟·莲·菜”的新结构,即主要通过引进蔬菜企业流转土地建设大棚,逐步扩大蔬菜种植面积,缩减水稻、烟叶、白莲的种植比例,以期通过蔬菜产业带动农民脱贫致富。截至2019年10月,罗县共建成蔬菜基地26个,总面积3.5万亩,主要种植茄子、辣椒、西红柿、豆角等果菜及少部分叶菜。在品种选取上按照当地市场常规菜品进行分类种植,以避免同质化带来市场供给过剩导致的价格低廉、销售困难等风险。同时,罗县通过“蔬菜企业+合作社+贫困户”的方式推广“433”产业扶贫模式,即钢架大棚40%由企业示范经营、30%返租给种植能手、30%无偿租给贫困户种植,并免费发放秧苗、提供技术与保底收购服务,以带动贫困户增产增收。②资料、数据来源于罗县农业农村局,截止到2019年10 月。此外,政府还提供多项不亚于烟叶的优惠政策,农民流转土地后若按照务工、反租倒包、股金分红、技术支持等综合测算收入要高于烟叶。然而,笔者调查发现,在政策实施过程中,农民从一开始的土地流转环节就予以抵制,大棚建成后带动农民就业的成效也不显著,农民承包大棚的案例更是少见。目前看来,与政策初衷相距较远,产业扶贫效果欠佳。
本文实际考察的田野点分别位于罗县东南的贝村和西南的胜村,两村均属该县蔬菜大棚重点建设村。贝村属“十三五”深度贫困村,距县城13公里,共9个村民小组,435户2030人。全村原有建档立卡贫困户91户366人。总面积5.6平方公里,其中有效耕地面积仅813亩。农作物主要为水稻、烟叶、白莲、油菜等。截至2019年11月,贝村通过引进富农有限公司流转全村220亩耕地建设高架大棚,主要种植茄子、辣椒、西红柿、韭菜等果蔬。
胜村也属“十三五”深度贫困村,距县城15公里,总面积12.2平方公里,其中耕地2257亩,辖18个村民小组,总人口694户2226人。全村原有建档立卡贫困户119户411人。主要作物为烟叶、白莲、水稻、翻秋花生等。截至2019年11月,胜村通过引进新福有限公司流转土地650亩搭建高架连体大棚,主要种植茄子、辣椒、豆角、黄瓜等果蔬。实际该公司连带流转邻近5个村约有2000亩的耕地,预计2020年底建成现代化、智能化的蔬菜基地。
上述两村的特点在于都有相当规模的山间平地,完整的“烟·莲·稻”主作物与其他辅助作物的种植结构,且都在产业扶贫过程中经历作物结构的快速转换。其中胜村在2018年仅用3个月时间就完成土地流转1500亩。截至2019年12月,蔬菜企业已初步完成1500亩的高架大棚建设,被称为“胜村速度”。此外,据访谈资料显示,20世纪80年代两个村落为摆脱贫困命运都有农民自主引进烟叶这一经济作物的经历。在烟叶种植过程中,村民也曾经历被村干部强制种植的过程,但烟叶很快被接纳并嵌入农民的生计体系中。而大棚蔬菜却没能得到同样的礼遇。这背后的原因看似在于技术的门槛差异。但实际调查显示,大棚与烟叶的技术和操作流程难度并无太大差别。而当地农民30余载的烟叶种植则证明他们并非排斥技术。在政府无偿提供大棚、种苗、技术指导等现代生产要素的前提下,是什么原因导致他们对经济效益可能更优的大棚蔬菜采取排斥态度呢?
三、作物结构:被接纳的烟和难被接纳的菜
从农业的社会起源来看,任何一种农业生产方式的创立与变革均以特定的社会条件为前提。一种新的农业形态出现,其主要动力并不一定来自农业内部,它往往是社会结构变动的潜在结果①Weber.Max,The Agrarian Sociology of Ancient Civilizations.London: New Left,1976,pp.391,403.、②黄宗智:《中国的隐性农业革命》,北京:法律出版社,第10—18页。,因而考察当地的社会结构是理解新作物能否顺利落地的重要路径。
(一)被接纳的烟叶
虽然罗县引入烟叶较早,但由于地理条件、社会变迁、政策方针等因素一度中断很长一段时间,待重新引入又是一个新作物连带新技术的习得过程。1982年,贝村张连成从部队转业回来旋即被选为村支书。当时的贝村主要种植水稻、大豆、红薯等粮食作物,每年的粮食收成既要应付国家的“公粮任务”,又要保证各家户的口粮需求。由于人均耕地少,技术投入与土地产量有限,再加上还没有全面放开外出务工。农民要想生存下去只能在土地上下功夫。鉴于此,张连成下定决心要带领村民致富。看到一衣带水的隔壁县通过种烟叶发了财,家家都成了万元户,张连成很是眼红,“离得那么近,人家能搞成,我们也能搞成。我就不信,我们日子过不好!”(ZLC012访谈)由于不懂种植技术尤其是收成以后的炙烤工艺,尽管知道烟叶能带来经济效益,但还是没人敢尝试。种烟叶就意味着要牺牲一季的稻谷,不仅家里没了口粮,还要冒交不起“公粮”的风险。为了突破技术障碍,张连成通过亲戚关系请来隔壁县两位种烟能手亲自指导村民种植烟叶。他们在村里一住就是一年,吃喝住由村集体供养,并给予每人每月400元技术指导费,这在当时属高工资。这样一年过后村里有一批人逐渐掌握了全套的烟叶种植技术,并在自家地里试种成功,不但没有亏损反而增加了总体的经济收入。农民把烟叶收入用于家庭开支,并采取“烟-莲-稻”轮作的方法保留口粮补齐“公粮”。烟叶的嵌入使农民的生计体系更具经济效益,于是,不懂技术的农民也开始跟在后面学。随后张连成让全村开始大面积种植烟叶。此外,他还担任烟叶站的站长,亲自学习新的烤烟技术,指导村民提升烟叶种植能力。为了解决销售问题,张连成专门成立合作社,村民收成的烟叶统一由合作社负责销售,这样村民便没有了后顾之忧。1983年贝村引入烟叶,1997年达到900亩的种植高峰(贝村总耕地面积1028亩)。
就自然条件来说,罗县气候温和,雨量适中,土壤磷、钾含量高,适宜种植烟叶,因而种植出的烟叶品质也高,1996年被指定为烟草企业优质烟叶供应基地,从此列入国家烟草计划。每年烟草公司给罗县下达指标,再由烟草局分配给各个乡镇完成指标任务。种苗、化肥、农药甚至技术都由烟草公司负责提供,如2019年罗县种植烟叶2.31万亩,按照村镇面积划分到11个乡镇种植。贫困户具有劳动能力者,亦可种植。烟叶成熟农民简单加工后运到卷烟厂,烟税返还作为补贴。此外,政府还为每亩烟叶补贴300元并购买48元的保险。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到,必要的技术支持、劳动力优势、能人带动、政府保障为烟叶嵌入到农民的生计体系提供了基础和条件。那蔬菜大棚具备这些要素吗?
(二)难被接纳的大棚蔬菜
罗县的自然地理条件也为各类瓜果蔬菜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先天基础,且又因毗邻粤港澳大湾区更具备了市场优势。此外,罗县发展蔬菜产业也是所属贡市整体区域规划所致。2010年贡市提出建设中心城区商品蔬菜基地的目标。2012年又进一步提出打造东南沿海和粤港澳优质商品蔬菜供应基地的目标。③http://www.ganzhou.gov.cn/ zfxxgk/c100449q/201206/ a659a856633a46ec81db7e22b8064520.shtml.这也成为罗县脱贫攻坚背景下调整作物结构的政策依据。
为吸引资本下乡,政府先是通过整顿高标准农田来流转贝村、胜村全部可耕地约有3000亩。在耕地实现“三通一平”后随即招商引资开展蔬菜基地建设。以胜村2000亩高标准蔬菜项目为例,项目总投资约有2亿元。每个钢架连体大棚实际造价约有6万元,县政府向企业承诺每亩地给予50%的成本补贴。截至2019年8月,企业方共建成5亩高标准温控育苗大棚、400亩钢结构高标准连体大棚、400亩标准单体大棚,配套建设3千平方米育苗中心和冷库。政府为企业方承担一半的成本支出约合3千万元,这还不包括其他税收、种苗补贴等。企业方在选地块时也总是挑选灌溉、交通等最为便捷之处。
为防备资本下乡的“不纯动机”①王晓露:《工商资本下乡的动因、问题及应对》,《农业经济》2019年第12期。、②周飞舟、王绍琛:《农民上楼与资本下乡:城镇化的社会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1期。,政府与企业方共同制定了利益联结实施方案。以胜村为例,在土地租金上,由政府做中间人,企业与农民签订自2017—2023年的土地流转合同。具体租金给付方案为:2017—2019年为500元/亩;2020年—2022年则按每亩430斤稻谷折价计算;2023年按每亩440斤稻谷折价计算。比起种植烟叶每亩地300元的补贴,在租金收入上农民有200元的增收。在反租倒包收入上,企业承诺免费给贫困户提供不少于1亩的蔬菜大棚,连接当地贫困户不少于100户;并免费提供种苗、技术指导,负责同类同价产品收销,实现户均年增收1万元以上。在务工就业上,企业日常劳动力需求100人左右,主要安排当地劳动力,日工资收入80—150元,可实现贫困劳动力月收入2000—3000元。最后政府与企业商定股金分红收入的形式,企业积极吸收贫困户资金入股,贫困户以产业扶贫信贷通每户贷款3—5万元作为股金入股,企业按12%保底分红,按季支付,期限为3年。贫困户股份由政府代持,每季分红由企业支付给政府转给入股贫困户。企业负责在约定的时间内偿还贷款本金。
政府如此费心为农民找寻利益空间的联结机制,最终效果究竟如何呢?据笔者调查的数据显示,在胜村原计划通过土地租金、反租倒包、务工就业、免费技术帮扶等措施带动当地农民脱贫致富。但实际到大棚就业的贫困户仅占20%,通过免费技术帮扶等措施带动的贫困户为零。更重要的是,土地流转就意味着农民可拓展的收入空间被剥夺,尤其是烟叶、白莲等经济作物无法种植,农民可掌控的传统作物结构与生产体系遭到了破坏,农民的整体收益未必有增加。因此,除土地租金收入外,反租倒包、务工就业、免费技术帮扶的效果一般,农民更不会通过信贷来入股,产业扶贫的总体效益并不显著。为何政府斥巨资支持且理论测算收益要高于烟叶的蔬菜大棚得不到农民的青睐呢?现有解释一般认为原因在于政府没有形成合理的上下互动机制,没有给农民主动参与创造机会,致使项目资源在实际执行的过程中被“精英俘获”③何毅、江立华:《产业扶贫场域内精英俘获的两重向度》,《农村经济》2019年第11期。而难以产生“涓滴”④H.Chenery,M.S.Ahluwalia,C.Bell,J.H.Duloy and R.Jolly,Redistribution with Growth: Policies to Improve Income Distribu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the Context of Economic Growth.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4.效应。这类观点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何主动去参与申领大棚的都是乡村能人而非一般贫困户。但无法解释为什么土地流转后的农民也不愿去蔬菜大棚劳动就业,以及大多数农民为何不愿申领免租金的大棚自主发展蔬菜种植。事实上如同烟叶一样,政府已提供技术支持、资金服务乃至市场保证,因而此时成本与风险等制约理性小农的因素业已降低,但为什么依然没能左右农民的行为选择呢?当政策与市场等外部因素无法解释时,就需回到当地社会文化关联性中加以分析了。
四、生计体系:作物结构与社会文化系统的关联
总体而言,中国的小农经济属以生计为目标的家户生计体系(Household Livelihood System)。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认为家户经济先要满足生计需要的目标而不是为利润,家户生计体系就本质而言是和剩余价值背道而驰的。即使在家户生计体系中发生交换也是为生计而交换,而不是为交换而交换。⑤[美]马歇尔·萨林斯:《石器时代经济学》,张经纬、郑少雄、张帆译,北京:三联书店,2019年,第100—101页。这种生计体系高度关联地方自然生态、社会文化系统,极具合理性与生命力。为此,斯图尔德(Julian Steward)认为文化内核就是文化与所处的生态环境之间经过磨合而形成的文化生态耦合体,其内容主要表现为当地居民的生计。格尔兹进一步认为文化核心是文化模式与生态环境相互依赖的最明显和最关键的部分,如他在《农业内卷化》所考察的爪哇岛稻作农业生计体系。①[美]朱利安·H.斯图尔特、潘艳、陈洪波:《文化生态学》,《南方文物》2007年第2期。该文译自D.L.ed.International Encyclopa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The Macnillan Company andthe Free Press,1968,Vol.4.可见,文化不是抽象的,可以落到具体的以作物生产为表现形式的生计方式上。当然,家户生计体系是家庭整体安排,不仅包括农业生产也包括非农生计。有些作物结构适合农民灵活的兼业化,而蔬菜大棚的公司化运作则排斥这种生计安排。显然罗县“烟·莲·稻”与“烟·莲·菜”两种作物结构与家户生计体系的内在逻辑存在暗合或冲突,才是造成农民对两种经济作物产生不同态度的深层原因。
(一)家户生计体系与“烟·莲·稻”作物结构
在前述分析烟叶进入的过程中,笔者已论及烟叶被接纳的外部性因素。但真正使烟叶嵌入农民生计体系的远非那么简单。如果说改革开放初期,非农就业的机会比较少,村里滞留大量劳动力恰好与烟叶种植加工需要大量人工相吻合,那么,为何当非农就业机会增加、农村劳动力大量外出以后,烟叶种植面积仍然占据相当的比例,且依旧是该县农业产业的三大支柱之一?一个更有意思的问题是,为什么经济效益如此好的烟叶没有替代水稻、白莲、油茶等其他作物,而是几种作物一直保持相对固定的比例?解释这一问题就要从作物结构与社会文化的关联中寻找答案了。
1.“烟·莲·稻”轮作的互补性与整体性
尽管烟叶收益不菲,但两村的农民并非每年都种植,总是要间隔两三年,而且尽量使烟叶与其他作物轮作,具体情况见下表。

表1 贝村与胜村“烟·莲·稻”轮作表
在多年的种植过程中,农民发现这样一个规律:“烟不能种长,种长了会害青枯病、黑胫病、根结线虫病,需要种点别的搭配”(LQS028访谈)。当烟叶种植茬口过于频繁时,极易因为重茬感染病虫害。后来农民发现水稻、白莲可与烤烟产生互补。水稻、白莲属喜水作物,生长过程浸水时间长,因而危害烟叶的病原不能很好繁殖,避免了病害发生。有研究指出水稻秸秆含大量C物质腐殖化系数较高,有利于土壤有机质积累、土壤结构和耕性的改良。②薛平:《罗县烟叶生产发展及其产业体系规划》,江西农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第32页。此外,水稻秸秆中钾素含量也很高,而这恰恰是烟叶生长的必备元素。而白莲的根、茎、叶对改善土壤条件也有相似功效,在烟叶的轮作周期中夹种这些作物,其根茬对土壤营养的互补作用,有利于烟叶栽培高产优质。③陈海飞、冯洋等:《秸秆还田下氮肥管理对中低产田水稻产量和氮素吸收利用影响的研究》,《植物营养与肥料学报》2014年第3期。“烟·莲·稻”轮作模式下烟叶秸秆还田增加腐秆剂,④黄功标、杨秉业、陈均:《连续2年稻草还田腐熟对连作烟田土壤性状及烤烟产质量的影响》,《江西农业学报》2014年第4期。为水稻及白莲的生长提供了肥料。烟秆中的烟碱是很好的杀虫剂,可减少水稻及白莲病虫害的发生。所以村民会说:“种过烟的田再去种水稻和白莲产量非常高。烟、稻、莲换着种,田才不会有问题”(ZCS056访谈)。事实上,土地在轮换过程中可改善土壤结构,对不同作物生长均有益处。但为什么是水稻和白莲,不能是其他的作物如西瓜、茄子、辣椒、番茄等果蔬呢?烟叶如果和上述果蔬轮作的话两种作物都难以达到预期效果,用村民的话就是“烟与水稻能配,烟跟瓜、菜不能配”(ZCS056访谈),因为烟叶与属葫芦科、茄科的果蔬作物存在同源性病虫害。①张忠武、鲁耀等:《前茬作物与施肥方式互作对烤后烟叶产质量的影响》,《贵州农业科学》2019年第2期。在作物轮作体系中,前茬作物的选择往往是影响烟叶及其他作物生长的关键。从这个方面考虑,果蔬没能入选当地农民“烟·莲·稻”轮作体系。因此,传统的作物结构是对生态环境的适应,在规避作物弱点的同时实现了对生态资源的高效整合利用,并确保了生产的可持续性。正是因为这一套生产体系的需要,“烟、莲、稻轮作”成为了当地农民根深蒂固的观念,并制约着他们对新作物的接纳。
2.作物结构与社会文化的关联性
首先,这种作物轮作体系也极为适应包括劳动力结构、生活节奏、饮食习惯与节庆习俗等在内的当地社会文化。罗县属南方稻作区,大米是当地人的主食,因而水稻的存在是为实现这一主粮功能。白莲除经济价值外也可食用,已成为当地人餐桌上必不可少的菜品。此外,白莲还与农民养鱼等产业形成种养结合一体化。烟叶主要承担致富创收的功能,“烟·莲·稻”及其他作物所构成的粮食作物与经济作物的合理比例满足当地人的经济需要与生活需求。这种生计体系满足于有限的经济目标,追求的是生活的途径而非量化的抽象财富。②[美]马歇尔·萨林斯:《石器时代经济学》,第105页。通过轮作,不同作物之间的季节性使得家中的剩余劳动力可以外出务工取得非农的兼业收入,农忙之际他们亦可回乡参与生产劳动。由于不同作物对技术、劳动能力的要求层次不同,因而一家之中能劳动者皆可参与不同作物的生产过程。如水稻属主粮作物,已实现小型机械化,但在晾晒环节仍需部分劳动力。烟叶种植技术要求较高,因而由家中年富力强者主要负责。而白莲的采收、剥壳、晾晒等环节,家中老人、小孩皆可参与。因而传统的作物结构既可以通过轮作充分利用家庭劳动力,又可以通过作物的季节性实现灵活就业,最大限度适应家户生计体系的生产生活。
其次,这种作物体系没有因经济作物的扩张而产生资本化,也没有因“公司+农户”的生产模式引起农民与土地的分离。虽然合同生产使农民卷入到市场分工中,但在一定意义上作物的互补性与轮作体系保存了农民耕作的相对完整性。如农民可以选择今年种烟还是明年种,与哪种作物搭配。因而轮作安排背后是农民自主权的一种体现,与农民的生活节奏形成一种调适不至于被市场所左右“沦为资本的奴隶”,甚至偏离农业的实质理性走向形式理性的深渊。③Patrick H.Mooney,My Own Boss? Class,Rationality and the Family Farm.Boulder,Colorado: Westview Press,1988.此外,烟叶在村落也没有采取规模化经营方式而引起贫富差距甚至阶级分化。反而在指标经济过程中,各家户均分烟叶指标再配合白莲种植实现相对的社会公平。
最后,这种作物结构与当地文化生活相互适应。文化的合理性在于它能够反作用于生计和环境,维系生计与生态的平衡。而文化的生命力在于对本地环境的认识和对人们社会文化生活的秩序维系。④Marvin.Harris,Good to Eat:Riddles of Food and Culture,Long Grove:Waveland Press,1985.罗县属客家人分布区,在长期的迁徙与客居他乡的过程中形成了宗族中心、家族互助的文化观念。这一共同体观念展演在村民“烟·莲·稻”等作物种植、红白喜事、房屋修缮或其他互助的生产生活过程中。当地客家人极为重视宗族团结,如若一宗族成员有生产劳作或其他需要,那么同宗家户无论如何也要亲自出工出力。至若清明,在外的客家人也要回乡祭祖。更不用说建造房屋、婚礼葬礼这些重大活动了。如果在家族的公共事务上不尽心,势必会失去共同体的支持甚至遭到排挤。而“烟·莲·稻”的轮作体系得以使邻里间的守望相助发挥功能。各家户能够在农事之余照顾到宗族邻里的帮工需求。
综上,烟叶能够嵌入当地农民传统的作物结构与生计体系的原因,就在于它能与农民传统的种植习惯以及社会文化传统相适应,甚至还有助于农民生计体系的优化升级。
(二)家户生计体系与“烟·莲·菜”产业结构
1.作物结构矛盾与蔬菜全面替代
罗县在脱贫攻坚中把“烟·莲·菜”作为主推模式,但深入分析就会发现这一作物结构存在内在矛盾。前文已述,从作物学的角度来看,由于存在同源性病虫害,烟叶与葫芦科、茄科蔬菜存在轮作障碍。而大棚蔬菜本身也并没有采取可轮作的形式推广,其特性就在于它的独占性。建设基地要求占据村落仅有的山间平地以方便设备、物资投入与产品输出。而大棚设施本身不具有作物兼容性,烟叶和白莲等作物难以适应其密闭的生长环境。随着大棚蔬菜产业的实施,其他作物的生存空间面临被替代的危险。
从表2可以看出,蔬菜产业的发展逐渐挤占烟叶、白莲、稻谷等作物的生存空间,打破原有“烟·莲·稻”的三足鼎立格局。大棚蔬菜是一种全面的替代,是要把农民原有的生计体系进行全新更换。正因如此,农民没有普遍接受和适应该产业,最终难以内化为一种生产能力,实现从“输血”到“造血”的过程转换。

表2 胜村2016-2019年农业产业发展基本情况
2.蔬菜的资本经营与家户生计体系之冲突
在本质意义上,大棚蔬菜是一种资本经营方式,而资本的核心在于逐利。如前所述,“烟·莲·稻”代表的是一种家户生计体系下的作物结构。家户生计体系的核心在于“为使用而生产”而不是为利润与剩余价值而生产,因而家户经济的“目标明确,工作灵活”①[美]马歇尔·萨林斯:《石器时代经济学》,张经纬、郑少雄、张帆译,北京:三联书店,2019年,第105页。。大棚蔬菜的资本经营特性在于控制生产资料、劳动力、生产过程以及资本的再投入,在土地与农民分离的基础上直接剥夺剩余价值。②Wright.Erik Olin,Class Crisis and the State.London:New Left,1978.大棚蔬菜采取流转土地的形式将农民与土地分离开来,以便为蔬菜准备充足的劳动力资源。当农民没有可耕种土地之时,除从事非农工作就是参与大棚劳动沦为企业雇佣工人。同时,大棚蔬菜的工作制度、劳动方式与农民既有的生产生活节奏极为不同。大棚蔬菜以市场为导向,采取8小时工作制,并以货币形式支付工资。工人的劳动强度、自身技能与最后的薪酬密切相关,农民为获取收入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劳动力。
虽然政府与企业达成协议制定了多重保障,但随着产业结构调整带来的是农民生计体系的改换。农民原有的多种作物种植、多重风险规避的复杂生计体系因土地流转、种植单一化而难以为继。现实中,年龄偏大的农业劳动力跟不上快速的产业结构调整带来的技术和市场门槛;同时,因土地流转,本地种植大户受到排挤、无田可种,有些只好重新外出务工,有些因家庭原因无法外出的种植能手则可能面临新的生计困境。自主经营大棚蔬菜的农户实际也难以从中受益,甚至可能遭受风险与损失。从胜村ZYC个案就可看出:
ZYC,男,40 岁。2016年因缺技术评入建档立卡户。2017年,为在家能获得足够的经济收入,ZYC 夫妇二人通过亲戚关系流转20 亩农田种植烟叶。在原有已成熟的社会网络支持下,ZYC 从烟草公司及同村种烟能手那里获取烟苗20 亩及相应技术支持,并在扶贫项目的帮助下获得水利灌溉、烤房、柴油机等生产设备。此外,ZYC 还搭配种植白莲与水稻。当年ZYC 仅烟叶收入就达8 万元。2018年初,胜村大棚蔬菜项目实施后,听闻对贫困户免费提供大棚、肥料、菜苗及技术支持。ZYC 主动领取1 亩大棚种植辣椒,并申请扶贫专项贷款5 万元。由于没经验,他虽整日待在大棚中观察蔬菜情况,但有很多障碍:一是市场瞬息万变,自己的信息相对封闭,无法随时根据市场需求来选择种植的蔬菜品种,2018年他也只是听取企业老板的意见选种了辣椒。二是销售价格不稳,6 月份是辣椒收获季,不仅有大量本地辣椒上市,外来海南辣椒价格也很便宜,给本地辣椒的销量造成冲击。2018年ZYC 种辣椒收入有5000 元,但因种辣椒需要无间断投入大量劳动力,因而他只能减少对烟叶的投入。同年,ZYC 的烟叶为此缩减至12 亩,减少收入5万元。(ZYC001 访谈)
可见,碍于技术、市场与经营能力不足,大棚蔬菜并不是农民的最佳选择,因过快调整种植结构而遭受经济损失的不乏其例。从个体层面而言,作物结构的调整并不总是积极正面的。尤其是对那些以农业为主要生计手段的种植大户,大资本的引入、土地规模流转极大地挤压了他们的生存空间。如案例所述的种植大户想把蔬菜纳入自身的作物结构与生计体系。但在此过程中,种植大户除要克服资本、技术及市场等不利因素外,还要面临种植结构单一化以及生计体系濒临崩溃的危险。加之罗县本身耕地面积较少,土地大规模流转后,这些种植大户进一步被压缩在较少的地块上种植传统作物。如果再缺乏政府的投入和帮扶,那么其收入已很难满足他们的生计需求。“以前我有自己的田的时候,每年种点烟叶、白莲,收入勉强还过得去,现在地也没了,给的流转费也不够日常使用,没办法不得不去干点别的了”(ZLK056 访谈)。一些农民因土地流转不得不离土甚至离乡,这一方面是对当地农业产业的打击,另一方面又加重了村庄空心化。因此,农民在适应新作物过程中,总会与其现有生计体系、社会文化结构做整体性权衡。大棚蔬菜引入过后不但没能与原有作物结构形成协调关系,反而使农民直接面对市场风险陷入资本的裹挟中。
不过,面对强大的资本,农民虽然无法与之正面抗拒,却也通过各种“弱者的武器”维持既有的家户生计体系。如企业主屡禁不止的“零碎地头种植”现象。在胜村和贝村,由于规模化的大棚搭建往往要求其规整性,因而许多“零碎地头”被闲置出来,农民会以这是自家承包地为名,种上传统的大豆、辣椒、黄瓜等作物作为自留的菜地使用。但农民不像企业那样讲究果蔬的品相而是任其生长,在种植期间更疏于喷药杀虫。但邻近的企业大棚内执行的规范杀虫作业效果,往往会因农民田间地头零碎作物带来的病虫害传染受到影响,为此企业主不得不再次喷药杀虫。而不浪费田间地头零碎地本身恰恰是农民出于生计对土地珍视的体现。此外,尽管胜村有20位贫困农民前去大棚劳作,但多数农民并不愿意从事严苛、繁重的大棚劳作,“经常有农民隔几天才来干活,干活过程中经常停下来聊天”(WSH023访谈)。农民的这种非理性行为恰是其“不为剩余价值而为生计生产”,想多获得闲暇时间,工作具有灵活性的体现。
3.农民、乡土社会与资本大棚蔬菜
资本化的大棚蔬菜经营模式也在落地乡土社会的过程中遭遇许多障碍,充分体现其与农村社会传统文化之间的潜在张力。①徐宗阳:《资本下乡的社会基础——基于华北地区一个公司型农场的经验研究》,《社会学研究》2016年第5期。由于蔬菜企业经政府引进而来又“拿”走农民土地,打破当地常规的“烟·莲·稻”轮作模式,农民对其多有排斥心态。农民认为他们在套取国家补贴的同时也从自己手中“夺走”了土地。因而村民始终与企业主之间存在一定的隔阂。事实上,企业也并非总是“专横强势”不懂“人情世故”,曾多方尝试融入乡土,会比当地人更加积极地参与村民的红白喜事,资助贫困大学生,还为有生理缺陷的贫困户提供轻松的工作岗位,甚至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主动为村民们提供各类果蔬来保证当地村民的蔬菜供应。但农民始终在心里觉得,他们不是本地人,因而也就不是自己人。在这种内外有别的思维方式影响下,当地农民常有一些不当行为发生,影响大棚蔬菜的管理(WCL036访谈)。
此外,在蔬菜大棚的高强度劳作对农民的身体也造成一定影响。“他们说让我去棚里面干活能赚到钱,但其实在棚里面干活太累了,尤其是在那个大棚里面干活,闷得很,能把人给热坏了,那个棚有心脏病、高血压的人根本不能去”(CHK067访谈)。封闭的大棚不仅空气不流通,也极易因农药操作不当发生中毒事件。有时植株密度过大无法直接进入时,农民只得弯腰曲背进入作业。由于从事大棚蔬菜劳作的多为45—70岁的中老年妇女。在大棚里连续劳作后,不少农民开始患有腰椎间盘突出、哮喘等疾病。
此外,大棚蔬菜的现代企业管理制度与村民的生活节奏产生内在的冲突。在年轻劳动力大量外流的状况下,留在家里的妇女与老人不仅要承担田间劳作,还要照看家庭、接送孙辈上下学。但企业的工作制度常与村里的生活节奏发生冲突。此外,当地客家人在生老病死、翻盖房屋、生产劳作方面常有互助帮工的习惯。企业的管理制度却常使村民陷入义利两难的选择境地,无法满足农民兼业化和社会文化生活需求。
综上,大棚蔬菜无法起到明显的扶贫带动效果,其原因在于大棚蔬菜的独占性使其无法与其他作物形成互补的轮作模式。此外,大棚蔬菜的资本经营与农民的家户式生产存在本质差异,使之难以与农民的生产生活与社会文化传统形成契合。因此,就整体性而言,大棚蔬菜无法有效嵌入到作物结构与农民生计体系当中,也就难以实现其产业扶贫的效果。
五、结论与讨论
农业产业扶贫不仅仅是一个政策过程和技术过程,更是一个作物结构与农民生计体系的调整与调适过程。从本质上说,农业产业扶贫是一个改造传统农业的过程。但这并不意味着只要政府提供现代农业生产要素就可以顺利完成新作物的结构转换,从而实现农业现代化带动农民脱贫致富。现有的经验表明许多抱有善意的产业扶贫项目常陷于失败的窘境。本文对罗县产业扶贫中两种经济作物引进的过程与后果进行了描述与比较分析。研究发现某些产业扶贫之所以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并不单是政策项目的实施机制、扶贫模式以及技术条件的问题。更为深刻的机理在于新作物无法嵌入到地方的作物结构、农民生计体系与社会文化传统之中。在过快地调整作物结构与产业结构,引进资本进行企业化生产过程中,贫困地区农民既有的生计体系可能受到冲击和破坏,从而陷入新的生计危机。
就总体而言,中国农民的生产方式属于一种以生计为目标的家户生计体系。农民的生产主要“为了使用与满足生活需求”而非“追求利润与剩余价值”。新作物的引入往往因其资本经营的逐利特征而与以生计为目的家户生计体系发生内在冲突,进一步也难以与农民的社会文化传统产生契合。家户生计体系下的农民以是否符合当地作物轮作结构、传统生计体系、社会文化契合度为标准,接受或抵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作物乃至产业被接纳而有些却被抵制无法达到扶贫效果的深层原因。农业社会学的视角有助于揭示其复杂机制与过程,从而为政策与实践提供启发。
就此而言,新作物之所以能被接纳的原因在于其可以在不破坏农民传统生计体系的前提下,以恰当的方式嵌入到原有作物结构与当地社会文化传统中,从而为解决农民的生计困境带来契机。相反,某些作物不被接纳表面上可能是技术门槛、市场风险与政策支持等原因,实则是因它与当地原有生计体系以及社会文化结构的张力和冲突。毋庸置疑,产业扶贫尤其是新作物引入一般都能带来作物产量与整体经济效益的提高,但对农民来说,新作物引入对传统农业的改造及作物结构的调整,带来的可能不是生计改善而是新的生计困境。因此,必须从农民生计体系和社会文化整体性视角去看待产业扶贫与作物结构调整的政策实践,尤其理解原有作物结构的合理性与社会基础。在产业扶贫过程中,新兴的作物与产业要为传统优势产业保留一定的土地资源与生存空间,要给农民提供蕴含生存能力、自主选择、社会文化网络支持的生活机会。同时,要找准衔接点,疏通体制机制,使新兴产业顺利嵌入到农民的生产生活、乡村多元产业体系和社会文化传统之中。制不同的作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