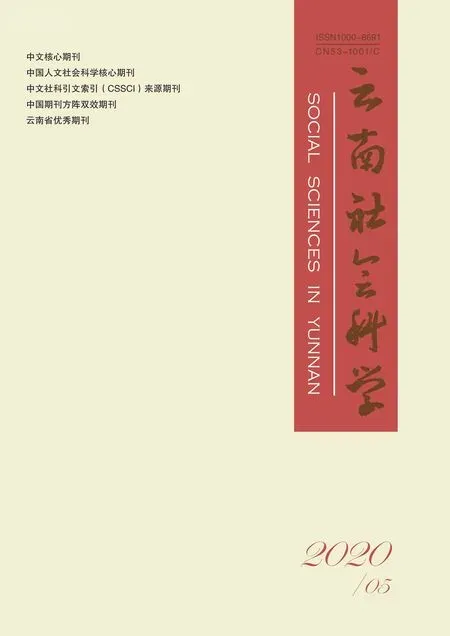社会嵌入与横向竞争:地方回应型创新的双重逻辑
2020-02-20王猛
王 猛
“基于局部条件的分级制试验”①Wen-Hsuan Tsai and Nicola Dean.“Experimentation under Hierarchy in Local Conditions:Cases of Political Reform in Guangdong and Sichuan,China”,The China Quarterly,Vol.218,(2014),pp.339-358.是中国国家治理的典型特征,是中国试验性与渐进性改革的重要基础。地方政府创新能有效实现“诱致性制度变迁”与“强制性制度变迁”结合,②何显明:《地方政府创新实践的生成机制与运行机理——基于浙江现象的考察》,《中国行政管理》2009 年第8 期。具有促进经济发展③陈国权、李院林:《地方政府创新与强县发展:基于“浙江现象”的研究》,《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重塑国家与社会关系④周庆智:《从地方政府创新看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化》,《政治学研究》2014年第2期。、推动政治改革⑤郭小聪:《中国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的理论:作用与地位》,《政治学研究》2000年第1期。等多重作用。因此,地方政府创新是观察与理解地方政府行为的重要视角。
行政改革、公共服务与社会治理领域的政府创新逐渐增加并维持在较高水平,是地方政府创新的重要趋势。随着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地方政府越来越多地通过推进行政改革、改善公共服务与提升社会治理水平,来满足地方社会需求与解决地方治理问题。那么,如何概括地方政府创新的这一趋势呢?又如何理解地方政府的这种创新行为呢?基于地方政府创新的理论研究和实践状况,笔者提出“地方回应型创新”概念来回答这些问题。基于中国地方政府创新的制度基础与地方情境,在区分地方政府创新三种类型的基础上,通过描摹影响地方政府创新行为的宏观社会背景与制度结构,从社会嵌入与横向竞争两个视角来解释地方回应型创新的双重逻辑。
一、理解地方政府创新的不同类型
识别地方政府创新的类型差异、作用机制是打开地方政府创新“黑箱”的重要途径。学界主要依据“内容—领域”和“动因—情境”两个视角对地方政府创新进行分类。如俞可平按创新领域将其分为政治改革、行政改革和公共服务创新①俞可平:《论政府创新的若干基本问题》,《文史哲》2005年第4期。,吴建南按创新内容将其分为管理创新、技术创新、合作创新、服务创新和治理创新②吴建南等:《政府创新的类型与特征——基于“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获奖项目的多案例研究》,《公共管理学报》2011年第1期。;杨雪冬则按创新动因将其分为危机—主动型、危机—被动型、发展—主动型、发展—被动型创新③杨雪冬:《简论中国地方政府创新研究的十个问题》,《公共管理学报》2008年第1期。,刘景江按创新情境将其分为体制内创新与体制外创新④刘景江:《地方政府创新:概念框架和两个向度》,《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这些类型划分有助于加深对中国地方政府创新的层次认知,但仍面临结构性与内在机制缺失的问题。一方面,这些划分缺乏在中国独特的制度结构中来把握地方政府创新的类型;另一方面,这些研究也缺乏在把握政府创新的核心作用机制基础上来进行类型区分。建构中国地方政府创新的类型框架,一方面需要关注地方政府行动选择所面临的制度结构与特殊情境;另一方面需要把握影响地方政府创新行为的核心机制。因此,我们从纵向的府际关系、横向的政社互动与内在的行政规范三个关键变量来构建地方政府创新的类型学。
对作为具有独立自主性的地方政府及其官员而言,其行动选择通常会考虑三层面的因素:第一,上级政府及其官员的政策、态度和行为。府际关系是影响和制约地方政府行为的核心因素,尤其是在中国“对上负责”和“压力型体制”的制度背景下。上级政府特别是中央在对地方进行适当分权的基础上,通过政治领导、晋升激励和绩效考核保持对地方政府的有力控制。因此,来自上级政府的政治控制会较大地影响地方政府创新行为的选择。第二,地方政府所面临的外部经济社会环境。地方政府作为区域性治理的责任主体,除需要落实上级政府的政治任务外,非常重要的任务在于回应辖区内的经济社会需求。因此,政社关系是影响地方政府行为的又一关键因素。而社会嵌入的强弱程度,会影响地方政府的创新选择。第三,地方政府内部的行政文化与规范。地方政府不仅要处理府际关系、政社关系,还要处理与自身的关系。地方政府的内在行政规范是一套处理与自身关系的文化知识系统。因此,行政文化是理解地方政府创新的再一重要因素。基于以上分析,可以说,地方政府创新是基于行政规范和治理文化,在特定的府际关系、政社关系下而进行的策略性选择。地方政府所需处理的三重关系实际上对应了影响地方政府创新的三个核心机制:政治控制、社会嵌入和文化规范。
基于三种机制作用程度的差异,可以将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区分为三种类型:上级主导型创新、地方回应型创新和地方自发型创新。上级主导型创新是指上级政府在保持对地方政府控制的基础上,赋予地方政府进行自主创新探索的权限,但在创新绩效与扩散推广等方面具有较大的裁决权,以为更大范围的改革寻找方向和突破口,如上级政府主导的政策试点。地方回应型创新是指地方政府为适应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在把握社会需求的基础上,改善公共服务与满足社会需求,以解决地方社会问题和通过创新获得竞争性资源的行为,如地方政府为适应经济发展而进行的行政改革,为满足基层社会治理需要而进行的社会治理创新等。地方自发型创新是指地方政府基于内在使命通过自我学习和创新,自觉回应地方治理问题和社会公众诉求,推动地方事业发展。如近两年由浙江省发起的“最多跑一次”改革,被视为“刀刃向内”、面向政府自身的自我革命。
如前所述,对地方政府创新实践的观察发现,地方回应型创新逐渐成为地方政府的主要创新形式。其原因在于:在改革开放初期,地方政府创新的动力主要来自于上级政府特别是中央权威。对急需改革创新与对外开放的中国而言,中央政府在改革初期的强力推动,打开了地方政府改革创新的局面。同时,中央在积极推动地方创新与全国改革的过程中,始终保持着对资源的控制和对地方的支配。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壮大、社会组织的成长和地方自主性的增强,其核心表现为社会嵌入能力的增强和地方自主性的增加,因而,地方政府创新受外部社会经济力量的影响也越来越多,开始更多地回应社会市场的需求。同时,地方政府创新也体现出更多的竞争性特征。接下来,将从地方政府创新的嵌入关系和竞争关系,呈现地方政府回应型创新的基本逻辑。
二、地方回应型创新的社会逻辑
本文将影响地方政府创新行为的外部社会经济因素统称为社会逻辑。地方政府创新内嵌于特定的社会环境中。理解地方回应型创新的社会逻辑,需要分析地方政府所处的社会经济环境的特征以及社会经济条件变化对政府行为的影响。中国变革的进程,也是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关系的调整和重构过程,突出表现为政府与经济的分离①[美]安·弗洛里妮、赖海榕、[新]陈业灵:《中国试验》,冯瑾、张志超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 年,第15 页。、单位制的解体②李路路:《“单位制”的变迁与研究》,《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3 年第1 期。。改革开放以来,地方社会经济环境的显著变化表现为市场秩序的扩展与社会力量的壮大。
(一)市场秩序的扩展与地方政府行为的转变
中国改革创新之路的一条重要线索就是市场秩序的不断扩展与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市场化改革是中国社会变迁的基本主题和动力,并诱致了社会结构的调整和变迁。改革开放后,为促进地方经济发展,中央与地方权力的分配呈现出“经济放权、政治集中”的非对称特征。以经济发展为导向的“策略性放权”,一方面使得地方政府行为呈现出更强的自主性;另一方面也使得市场力量不断向其他领域扩展渗透,导致了社会文化秩序与政府行政秩序的变化。
市场秩序的扩展显著影响了地方政府行为,表现为地方政府的“地区经营者”角色,具有不断增强的独立自主性和发展地方经济的强烈动机。这体现在:首先,随着财政体制改革,原有“一灶吃饭”体制下各级政府间高度一致的利益结构被瓦解了。特别是分税制改革,进一步强化了地方政府的相对独立性。中央与地方政府在事权与财权上进行了分配,各自相对独立的利益、地位和角色也更加明显。因此,地方政府围绕发展经济与增强财政收入的动机也越来越强。其次,财政分权的伴随性后果是中央将很多决策权下放给地方,特别是将大量微观经济领域的管理权限赋予地方政府,增强了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的自主权,使得地方政府成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经营者。最后,地方政府作为地方利益代言人的角色愈加凸显。地方利益成为理解地方政府行为逻辑的关键变量。③何显明:《顺势而为:浙江地方政府创新实践的演进逻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 年,第41 页。一方面,发展地方经济和为辖区公众提供公共服务,是地方政府获得政绩合法性的重要基础和手段;另一方面,地方经济发展、地方经济利益和地方政府的效用目标存在内在联系和利益共容。地方政府通过促进经济发展,以最大程度获取自主支配的财政资金、强化对地方资源的控制能力。
市场秩序不断扩展的同时,还促进了社会文化变迁与政府行政改革。第一,市场经济的发展推动了社会力量的兴起。社会资源的分散和社会利益的分化,导致政府无法再通过传统的强控制手段来维护社会秩序和依靠传统治理单位来整合社会利益。扩展的市场秩序塑造了一个更加开放、多元和动态的社会,这为社会力量的壮大和社会组织的成长提供了空间。第二,市场改革的深入推动了文化变迁。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促进了社会意识形态和文化观念的变化。市场经济所奉行的权利意识以及平等、竞争、自由、法治等基本价值,影响和促进了社会意识形态和文化观念的变化。这些现代市场经济原则成为社会吁求自身权益与评价政府有效性、合法性的价值标尺。社会权利意识和文化观念的变化,也提出了建立更具高效性、开放性政府和推动政府治理变革的要求。第三,市场经济的扩大推动了行政改革。一方面,市场经济的确立和发展逐步瓦解了计划经济时期所形成的封闭的政治结构和社会秩序,需要政府进行治理模式变革以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另一方面,推动市场经济发展内在地要求政府通过行政审批改革、政府机构调整、公务员队伍建设以及“简政放权”等手段,提高政府服务水平与激发市场活力。
(二)社会力量的壮大与社会嵌入能力的增强
社会成长是理解中国改革创新的又一重要线索。计划体制的解体与市场体制的确立过程,是政府对社会的控制范围缩小、控制力度减弱和控制规范增强的过程。④杨宏山:《当代中国政治关系》,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2 年,第276—277 页。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转轨、单位制向社区制的回归,意味着社会形态由“以抽象整体利益为主的单位组织,转向以具体个人利益为导向的契约组织”①李友梅:《从弥散到秩序》,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1 年,第214 页。,实现身份到契约的转变,尊重个人的发展。“单位人”向“社会人”转变是公民个体意识和权利意识增强的过程。这种转变意味着政府在面向社会和治理社会时必须考虑个体化的公民的权利诉求。②安·弗洛里妮等从公民对政府的行政诉讼逐年增加的视角对公民权利制约国家权力这一问题进行了论述。参见[美]安·弗洛里妮、赖海榕、[新]陈业灵:《中国试验》,第21—22 页。
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成长突出表现为社会组织的迅猛发展。中央向地方放权以及政府对社会控制的有限放松,为公民组建和参与社会组织的组织化需求创造了机会和空间。而社会自身也在经济市场化中、国家从微观社会生活组织者和承办者角色退出后,产生了愈益强烈的自我组织和自我服务的需求,催生了越来越多的民间组织。③陈光金:《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现代化转型》,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法学部:《改革开放 繁荣发展:中国社会发展和依法治国的时间与探索》,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年,第48 页。截至2018 年底,中国社会组织单位个数已达81.7 万个;其中,社会团体36.6 万个,民办非企业单位44.4 万个,各种基金会0.7 万个。社会组织涵盖了工商服务、教育文化、科技研究、医疗卫生、社会服务、生态环境、法律、宗教、农业农村发展和职业及从业组织类等各个领域。
社会组织数量的增长和组织化水平的提高意味其嵌入能力越来越强,因而,政府不得不回应社会组织的需求,同时也越来越依靠社会组织进行治理,如发挥中介组织和行业协会在承接政府职能转移和服务外包中的作用。当然,中国权力集中的体制和政党国家体制对社会组织的发展始终保持着天然的敏感,特别是对一些涉及政治活动、宗教活动、环境保护和权益维护的社会组织进行较为严格的限制。因而政府努力在对社会组织进行有效监管和与社会组织开展合作之间达成契合,寻求控制与嵌入之间的平衡。中国社会组织和民间社会固有的弹性与韧性,一定程度抵消了政府一直在努力保持着的对社会组织的有效控制。近些年来,随着大批草根社会团体的兴起、网络力量的壮大以及公民和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方式多元化、范围扩大化与作用深度化,社会组织在中国社会治理与改革进程中蕴含的特有价值和作用正被越来越多地认识。总之,社会组织已成为嵌入正式治理结构、影响和塑造国家治理和政府行为的重要力量。
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特别是市场化力量与社会嵌入能力的增强,地方政府越来越重视以社会经济需求为起点与回应社会需求,进而“通过体制创新推动区域经济发展,以形成制度创新与经济发展的互动”④金太军、汪波:《经济转型与中国中央—地方关系制度变迁》,《管理世界》2003 年第6 期。。因而,地方政府创新具有更多的“回应型创新”的特征。为呼应社会不断增加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需求,以及解决日益复杂的社会治理问题,在创新内容上则涌现出越来越多的公共服务与社会治理创新。可以说,地方回应型创新是为了适应和促进市场经济发展,回应不断壮大的社会力量对政府的治理需求,而采取的制度创新与政府改革行为。
三、地方回应型创新的政治逻辑
地方回应型创新的社会逻辑解释了政府系统外部社会经济条件变化对地方政府行为的影响,以及地方政府在内容上以公共服务与社会治理创新为主。那么,地方回应型创新的政治逻辑则从政府系统内部的制度结构解释为何地方政府需要回应社会需求。
(一)晋升锦标赛与地方政府竞争的形成
晋升锦标赛理论较好地解释了官僚体制内的竞争行为与政治激励机制。周黎安较早提出晋升锦标赛来解释中国地区间经济竞争或合作以及中国经济增长之谜。⑤周黎安:《晋升博弈中政府官员的激励与合作——兼论中国地方保护主义和重复建设问题长期存在的原因》,《经济研究》2004 年第6 期;周黎安:《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经济研究》2007 年第7 期。作为一种政府治理模式,晋升锦标赛主要指“上级政府对多个下级政府的官员而设计的一种晋升竞争,竞争优胜者将获得晋升,而竞赛标准由上级政府决定”。⑥李佳佳:《从地方政府创新理解现代国家:基于“非协调约束的权力结构”的分析框架》,上海:学林出版社,2015 年,第17 页。晋升锦标赛的治理机制在于经济增长、人事控制与政治激励的结合。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政府通过经济分权与行政分权实现了“治理权”下放,但上级政府仍然通过人事任免和政治激励来增强对下级政府的控制。这种纵向政府的权力分配被描述为“非协调”的特征,即治理权的预授与裁决权的保留。①李佳佳:《从地方政府创新理解现代国家:基于“非协调约束的权力结构”的分析框架》,第46—49 页。
“非协调”的分权结构与晋升锦标赛体制,促成了“同级竞争—上级裁决—政治晋升”的行为链条。理性的地方官员要实现在官僚体制内的政治晋升,就必须在横向政府间获得竞争优势。地方政府依托于较大的地方治理权限进行自主行为选择,通过提高显性的地方治理绩效来获得上级政府的认可和支持。上级政府掌握对下级政府治理绩效进行判断和评价的权力,并将裁决结果作为下级政府是否获得政治晋升的依据。因此,纵向层级政府间的分权与晋升锦标赛体制导致了地方政府表现出越来越多的竞争行为。这种竞争不仅表现在为谋求政治晋升的政治领域,更表现在为晋升提供绩效合法性支持的经济领域,也表现在辖区内地方政府间的“制度竞争”。②冯兴元:《论辖区政府间的制度竞争》,《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1 年第6 期。
(二)从“为增长而竞争”到“为竞争而创新”
改革开放后,中国很长一段时间都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级政府也将经济增长作为考核地方政绩与官员晋升的重要标准和依据。③Li Hongbin and Zhou Li-An.,“Political Turnover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The Incentive Role of Personnel Control in China”,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vol.89,no.9,(2005),pp.1743-1762.在此背景下,地方政府往往会迎合上级政府的目标偏好,展开了围绕GDP 增长为核心的竞争,以求在经济竞争中实现政治晋升。因此,锦标赛体制也由政治领域的晋升扩展到经济领域中的竞争,进而形成了“为增长而竞争”的模式。④陈钊、徐彤:《走向“为和谐而竞争”:晋升锦标赛下的中央和地方治理模式变迁》,《世界经济》2011 年第9 期。客观地讲,地方政府围绕GDP 而展开的晋升锦标赛促进了中国经济增长,但也带来了“重经济发展轻民生和谐”的后果。⑤蔡芸、杨冠琼:《晋升锦标赛与中国的基础教育发展失衡》,《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11 年第6 期。
但随着中央政府政策的调整和政社关系的变化,地方政府围绕经济增长的竞争格局也在发生变化。⑥何艳玲、李妮:《为创新而竞争:一种新的地方政府竞争机制》,《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 年第1 期。一方面,中央对地方政府的考核依据不限于经济发展,也更加重视社会治理、公共服务和生态环保等;另一方面,地方社会对优质公共服务与良好社会治理的需求逐步增加。因此,“为增长而竞争”为地方政府获取政治收益的空间正逐渐缩小,为获取相对竞争优势,地方政府开始围绕“制度创新”而竞争。制度创新能够在一定时期内带来制度的垄断利润,⑦刘强、覃成林:《地方政府竞争与地区制度创新:一个制度分析的视角》,《中州学刊》2009 年第6 期。通过制度创新的地方政府能够获得竞争优势,增加政治晋升的机会。在竞争性制度创新中,地方政府产生了对产权制度、行政审批制度与公共物品供给制度进行改革等创新行为。“增长竞争”与“创新竞争”的差异在于:前者是争夺经济发展资源,后者则是形成扩散性的制度经验;前者是存量竞争,后者是增量竞争。可见,在上级政府考核与地方社会压力的双重影响下,地方政府主要展开资源、政策与制度竞争。因此,地方政府竞争既强化了地方政府推动地方性事务发展的动机,也客观上刺激与加速了地方政府进行改革和创新。
四、地方回应型创新的效应、内容与后果
(一)地方回应型创新的双重效应
地方回应型创新的基本逻辑在于开放型体制的嵌入效应与竞争型体制的挤压效应的共同作用。换言之,地方政府不仅要回应来自社会的治理压力,还要回应来自同级的竞争压力。在中国对上负责的压力型体制下,上级政府主要通过行政发包、任务分解和政绩考核来实现对下级政府的激励和控制。地方政府既需要完成上级分派的行政任务,同时任务的完成情况也将作为其政绩考核与政治晋升的重要依据。而地方政府为了获取地方发展中的相对优势和政治晋升中的有利地位,围绕公共服务供给、资本吸引、法律制度、政府效率和社会治理等展开竞争。地方政府间不仅要争夺中央掌握的资源,还要与同级地方政府争夺区域内资源,也要和社会公众竞争社会性资源。因此,竞争型体制下的政府竞争既表现为横向政府间的资源争夺,也表现为纵向政府间的讨价还价。这种竞争既体现在政府体制内部,也延伸到行政体制之外。
地方竞争向行政体制外延伸,也意味着社会力量向行政体制渗透和嵌入能力的增强。转型中国的社会正由封闭社会走向开放社会,突出表现为社会组织的兴起、国家与社会的逐步分离。这成为推动政治发展与政府治理转型的重要力量。因此,地方政府越来越主动地回应社会和市场主体的利益诉求及制度创新需求,通过地方政府管理模式优化创新,应对市场和社会力量对地方治理产生的压力;通过政策和制度支持手段营造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的良好环境。对地方政府而言,回应地方社会需求有两个层面的考量:一是从政社关系来看,对社会需求的满足和回应,通过提升地方治理有效性以增强地方社会对政府的合法性认同;二是从府际关系来看,地方政府围绕满足地方社会需求而展开的竞争,可以通过提高地方治理绩效以为其政治竞争提供政绩支撑。而地方治理问题通常具有相似性,地方政府如果不能有效回应这些问题,在地方政府间的横向比较中将失去竞争优势。
(二)地方回应型创新的主要内容
地方政府受社会嵌入与横向竞争的双重影响,地方回应型创新表现出“弱控制—强嵌入”的特征。一方面,地方政府创新受中央控制的影响逐渐减弱,但通过政策试点与地方创新来为全国性改革累积经验仍是政府创新改革的重要形式;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创新越来越重视回应市场经济发展与社会结构变化所带来的需求变化。
一是为适应经济发展的行政改革。为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地方政府进行了大量的简政放权和政府创新。其核心形式表现为行政机构精简、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与政府管理模式创新。臃肿的政府机构和繁琐的官僚主义,严重制约了经济发展和政府管理效率,形成了倒逼行政改革的压力。因此,中央与地方政府进行了数次精简行政机构的改革,旨在通过机构调整、精简编制和理顺职能来提升政府办事效率。如广东顺德探索建立的政府大部制,就是力图精简政府机构、提高政府效能。但机构的物理变化并不一定使政府效率产生质的改变,提高政府效率的核心在于内部管理制度的创新。因此,为应对繁冗的行政审批手续与低效的政府办事流程,地方政府开始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和“一站式”服务的政务管理创新。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创新起步于深圳。深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承担着对外开放与制度创新的重要使命。为应对繁琐的行政审批手续,清除经济发展的制度壁垒,深圳市在国内最早开始了简化和删减行政审批手续和规章的改革。深圳推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与行政审批监察方式的政府创新成为全国的典范,其成功经验也在全国范围推广。近几年,各地围绕“放管服”和营商环境又进行了一批地方制度创新,也是行政审批改革的深化。
行政改革的另一项主要内容是政府管理模式的创新。为提高行政效率与转变政府职能,地方政府开始通过建立“一站式”服务中心(或“政务超市”)来方便企业和居民办事与获取政府服务。一站式服务最初是地方政府实现招商引资而采取为投资者提供便利服务的做法,后演变成为“一站式”行政服务机构。如深圳在1995年建立“外商投资服务中心”,浙江上虞县(今绍兴上虞区)于1999 年建立了全国首家行政服务中心。行政服务中心通过集中化、开放式和规范化的服务实现了服务流程的集成与服务内容的整合,因而成为地方政府转变职能与实现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载体,也是地方政府管理模式的重要创新。如近年来地方发起的“最多跑一次”“不见面审批”则是地方政府服务的进一步创新。
二是为适应社会成长的社会创新。第一,地方社会创新的重要内容是通过社会组织制度改革促进地方社会组织发展。随着政府对许多领域干预的减弱以及单位制的解体,政府逐渐难以满足日益增加的社会需求,这为公民追求自身利益而建立组织化的团体提供了空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组织一直处于快速发展之中。社会组织在部分实现了利益整合、集体行动和公共服务的同时,如何管理和规范社会组织也成为地方政府面临的问题。为适应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一些地方政府积极改革创新和先行先试,推动社会组织治理创新,将社会组织培育和发展成为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这些治理创新主要围绕政策法规、政府职能转移、政社分开、政社合作等方面展开,北京、广东、云南、海南、深圳、上海、浙江等省市是社会组织治理创新的活跃区域。①刘振国:《中国社会组织的治理创新——基于地方政府实践的分析》,《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0 年第3 期。如海口市1997 年成立的“外来工之家”,上海市普陀区长寿路街道办2002 年实施的社区民间组织管理体制改革、福建泉州市的维权工会、浙江义乌“工会社会化维权模式”等都成为“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的获奖案例。社会组织的治理创新表现出鲜明的特征:社会组织治理创新与经济发展、公民需求紧密相关,较多工会维权案例的出现也说明了经济发展中凸显出的劳工特别是弱势群体的权益保护问题。
第二,地方社会创新的重要趋势是公共服务与社会治理领域的创新增多。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类创新回应了社会成长对公共服务均等化与增强社会治理能力的要求。在公共服务创新领域,出现了诸如杭州市上城区“政府管理与公共服务标准化”、宁波市海曙区“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陕西省岚皋县“镇办卫生院新农合报销制度改革”、山东莱西市“为民服务代理制”、成都市“村级公共服务与社会管理改革”等创新案例。在社会治理创新领域,则出现了网格化管理、北京东城区“街道吹哨、部门报到”、浙江宁海“小微权力清单”、广东中山“流动人口积分制管理”、上海浦东新区“公益服务园”等代表性创新经验。
总体说来,地方回应型创新呈现出行政改革、社会改革与社会经济发展互动的特征。地方政府受上级政府控制和影响的程度逐渐减弱,而受市场和社会力量的影响逐步增强,社会嵌入政府的能力、地方企业和社会组织影响地方政府的强度越来越高,地方政府关注和回应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对地方治理带来的挑战。因此,地方回应型创新在内容上以服务于地方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的行政改革、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创新为主。
(三)地方回应型创新的异化后果
地方回应型创新是地方政府基于社会嵌入与横向竞争的双重压力而进行的适应性选择。地方政府通过创新竞争,无疑推动了地方社会经济发展与满足了地方社会需求,一些典型创新经验也成为推动全国性改革的重要力量。但是这种基于嵌入和竞争压力而进行的回应型创新,除具有巨大的创新动力和活力之外,还可能存在异化的情况。地方政府通过制度、政策创新来获得竞争优势是其行为选择的重要效用目标。因此,为获得竞争优势地位,地方回应型创新行为存在以下几种异化的可能:一是对社会需求的即时回应,或仅仅关注政府创新本身,而缺乏考虑创新的可持续问题。创新犹如昙花一现,陷入“创新容易、持续困难”的怪圈。二是为快速获得政治回报,偏重于显性的政绩工程而忽视隐性长期的创新,如集中围绕经济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而忽视民生服务和制度改进。三是可能陷入竞争的恶性循环。地方政府蜂拥进行创新以获取政治和社会关注度,在这之中可能存在两种情况:为了吸引眼球而进行“伪创新”或“盆景式创新”,和忽视地方实际而进行的盲目跟风模仿。四是地方回应型创新要权衡创新风险、政治稳定与政治正确,因而,一方面难以在发展改革的“硬骨头”上进行突破;另一方面,当创新进入“深水区”,可能难以继续推进,而陷入“内卷化”困境。①创新的内卷化则指地方政府创新发展到某一确定形式或阶段后,便停滞不前或无法继续推进的现象,即地方政府创新面临瓶颈。关于地方政府创新内卷化的讨论,参见李佳佳:《从地方政府创新理解现代国家——基于“非协调约束的权力结构”的分析框架》,第158—161 页。
综上所述,本文从政治控制、社会嵌入和文化规范三个维度将地方政府创新区分为上级主导型、地方回应型和地方自发型。随着地方社会经济环境、社会结构的变化以及地方政府间竞争的加剧,地方政府创新越来越多地呈现“回应型”特征。地方回应型创新是社会嵌入与横向竞争双向作用的结果。地方回应型创新的凸显也反映了地方治理更加注重来自社会市场的需求和压力,因而在内容上表现为服务于经济发展的行政改革和适应于社会成长的社会创新逐渐成为地方政府创新的重点。地方政府通过创新行为回应了社会需求与来自横向政府间的竞争压力,这种面对社会经济环境和制度环境压力而采取的适应性和回应性行为,客观上起到了解决地方社会治理问题的作用,但所面临的创新异化和内卷化等问题也需要高度重视。一方面需要实现政府与社会的有效对接,提高政府对社会需求的回应力和响应力,进一步规范地方政府及其官员的创新行为;另一方面需要加强地方政府创新过程管理,将地方政府创新转化为持续性的制度资源供给,提高地方政府创新的制度化能力。总之,要充分发挥地方回应型创新在推进制度持续改进中的正面效应,从而为完善地方治理体系与现代国家建设提供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