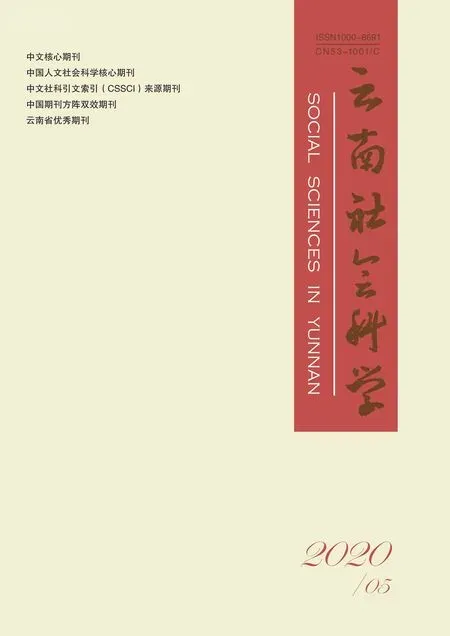健康中国的媒介治理路径考量
2020-10-29王雅婷
沈 悦 王雅婷
随着经济社会与生活水平发展的向好趋势,对于健康的获得以及如何维持健康这两个议题,因其与个人生活质量以及社会影响力紧密相连而日益受到关注。近期在中国及世界范围肆虐,造成全球民众巨大生命财产损失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再次使公共健康成为全球社会的共同诉求。在健康中国背景下,传媒作为联系医学与大众的重要桥梁,在阐述疾病机理、消除群众恐慌、促进健康行动、传播健康理念的媒介“善治”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不容忽视。
一、理论观照:健康传播研究的价值取向
健康传播研究从原先传播学中的“新生儿”逐渐成为传播学与临床医学、公共卫生学等跨学科研究的新领域。健康传播涉及人类社会多个领域,具有多个层级和组成要素。在全球治理背景下,媒介如何发挥其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作用,将普及健康意识、巩固健康认知、完善医患关系、促进健康行动,最终建构“民族—国家—世界”多维度的“健康共同体”理念是实现健康中国顶层设计下的新理论导向与价值张力。
(一)媒介与健康研究的多重面向
在西方传播学理论体系建立之初,美国的传播学及人类学学者即尝试将传播理论运用于疾病预防、解读致病机理、促进健康等社会实践。传播学界一般将1971年由麦考比(N.Macoby)和法考尔(J.Farqushar)创建的“斯坦福心脏病预防计划”(SHDPP)视为健康传播研究的开端。罗杰斯(E.M.Rogers)对于健康传播的两次定义分别是:健康传播将医学研究的相关成果转化为大众所能接受的知识,并通过传播过程中大众的态度以及行动的转变,降低人类的患病率及死亡率,并以提高大众的健康水平和生活质量为归宿的传播行为①E.M.Rogers,The Field of Health Communication Today,The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Vol.38,No.2,1994,pp.208-214.;两年之后他又将其定义为:凡是涉及人类健康相关内容的传播行为即是健康传播①E.M.Rogers,Up-to-date Report,Journal of Health Communication,Vol.1,No.1,1996,pp.15-24.。随着越来越多学者的加入,健康传播研究的发展形成了临床医学、公共卫生、心理学、公共关系、社会学、教育学、人类学、传播学等的跨学科合作。萨莫瓦(L.A.Samovar)等学者将健康传播界定为文化间传播的重要组成,并强调媒介在医疗领域对人际环境的影响较为显著。②L.A.Samovar,R.E.Porter,E.R.McDaniel,Communication Between Cultures,Cambridge:Wadsworth,2007,pp.266-291.时至今日,西方的健康传播研究大致分为5个领域:医患关系、健康社交与社区健康、健康组织传播、公共卫生运动、健康叙事③M.C.Green,Narratives and Cancer Communication,Journal of Communication,Vol.56,Issue.1,2006,pp.163-183.。随着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发展的持续深入,健康传播的研究视角不单单只局限于人的个体生理健康,研究主题呈现多元化、深度化、细分化的趋势,研究方式日趋向跨文化、跨学科演变。
中国的健康传播研究并非脱胎于传播学,其与公共卫生宣传工作关系紧密。首先,在“传播学者缺席”的早期阶段,该领域主要聚焦公众健康的教育宣传普及,以公卫健康学者为学术共同体的早期研究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应被称为健康教育而非健康传播。直到2003年突发的SARS疫情,“健康传播”的概念才开始逐渐被国内学者所论及,出现了一波学术探讨高峰④孙少晶、陈怡蓓:《学科轨迹和议题谱系:中国健康传播研究三十年》,《新闻大学》2018 年第3 期。。但是,此时的健康传播具有明显的媒介中心主义倾向,对于具有学科交叉的前沿研究甚少涉猎,跨学科研究依旧滞后,通常将大众传播与某个健康现象或议题简单结合(如突发传染病、医患关系、医疗信息公开),并以媒介效果研究作为主要方向,主要聚焦于高发性癌症的早期筛查、艾滋病的防控与反歧视、媒体健康报道框架、医患关系维护等。张自力从健康传播的9个方向特别是以人际传播及大众传播为切入点揭示健康传播的不同领域及实践价值⑤张自力:《健康传播学:身与心的交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年,第24—37 页。。近几年中国的健康传播呈现聚焦于社会化媒体及数据挖掘研究。计算传播、智能传播、数据新闻、建设性新闻等概念在新的媒介情境下成为健康传播研究的新鲜血液。需要指出的是,在信息总量飙升、言说机会更加平等以及网络媒体“去中心化”的特质之下,一方面,医院、公共卫生服务机构组织、通讯社等其他传统主流媒体等作为健康传播的“中心组织”能够与目标受众进行更为直接的双向对话,健康信息可通过社交网络迅速扩散,形成信息、知识、情感凝聚的新话语张力。另一方面,社交媒体的使用降低了公众对医生、医疗信息的信任,特别是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中尤其突出。例如,孙少晶等人以新冠疫情为背景,基于隐性主题分析、社会网络分析和多元对应分析等方法,考量微博话语表达随疫情发展而产生的阶段性差异研究,为厘清传统媒体与社交媒体在重大疫情背景下的复杂关系提供了新的思路⑥孙少晶、王帆、刘志远、陶禹舟:《新冠肺炎疫情语境中的多元媒介的微博话语表达》,《新闻大学》2020 年第3 期。。
进而言之,中国的媒介与健康研究还未形成自身的学术阵地,聚焦业务实践以及个案分析的研究占据了半壁江山。建构中国特色的健康传播理念,在全球治理背景下依托“一带一路”倡议,将健康中国战略作为话语桥梁,将健康作为实现民心相通、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情感纽带,将中国传统医药及文化精神实现世界范围的跨文化认同作为目标,这是中国传媒的使命担当。
(二)健康中国的话语诠释新维度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经济要发展,健康要上去,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都离不开健康。要大力发展健康事业,要做身体健康的民族”⑦来源于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18-04/11/c_1122668628.htm.。在十九大报告以及《“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中均强调了在未来发展时期健康中国战略的重要地位。作为一项复杂而长期的系统工程,健康中国战略涉及多元主体的协同参与;牵涉到多个发展面向、重点领域和关系治理要素⑧杨立华、黄河:《健康治理:健康社会与健康中国建设的新范式》,《公共行政评论》2018 年第6 期。;涉及健康权概念、大健康理念、预防为主理念的落实。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蔓延,仅靠单个国家或政府解决所有健康问题并采取行动显然是不可能的。新冠肺炎的暴发以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世界发展形势,让原本处于现代性迷思的世界格局更是雪上加霜。中美两国间政治关系的紧张,外加“去中心化”“去地域化”为目标的产业结构深度融合,两者间的二元张力使得国际社会更加关注中国在国际舞台的表态与行动。健康中国的提出和实施不仅标志着中国健康治理领域的重大范式转移,而且预示着中国主动参与全球健康治理、推行积极健康政策、讲好中国健康故事的信心和决心。
后全球化时代的健康安全与国家形象的关系日益紧密,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成为中国大国形象塑造的重要信号子集。①肖晞、宋国新:《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与中国大国形象塑造——基于信号表达的理论与实践》,《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0 年第3 期。在新冠肺炎的危机事件中,谣言、谎言、半真实信息的迅速传播扩散,加之官方媒体渠道的信息沟通不畅、信息滞后等,导致大范围社会恐慌、民众非理性行为、中国形象污名化等负面效应在媒介空间“去中心化”的情境下愈发超出其媒介治理的把控能力范围。健康中国战略作为中国迈向全球治理语境的国家立场话语,摆脱了过去国家形象跨文化传播中在地性与世界性相对区隔化的桎梏。在“一带一路”倡议持续深入地推动下,构建区域乃至全球的“健康共同体”有助于加强媒介系统对塑造拟态健康环境的能动性与感染力,突破中间阶层所普遍默认的健康意识形态,将健康理念与行动融入沿线民众生活。其次,健康中国战略作为国家话语表征所具有的实用价值、精神价值、符号价值是世界管窥中国人权及健康权发展,实现健康跨文化有效传播、延长健康对话链条的契机。基于对健康追求的价值认同是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多元价值跨文化认同的观念基础。尤其是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过程中,国家秉持“应收尽收,应治尽治”的负责任大国原则,保障了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也是面对他国污名化中国形象、诋毁中国人权问题的有力反击。
二、视域突围:健康“善治”传播的可能与挑战
新冠肺炎疫情的背后凸显了人类与自然、健康与疾病、个体与群体、封闭与开放、断裂与认同、真相与后真相、民族国家与后全球化等诸多二元范畴中各类表征的紧张对立。当下的传统管理(regulation)模式并不能完全应对区域性甚至世界性情境的普遍性问题。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暴发以来,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的概念逐步被学界所提及与接受。作为全球治理分支的媒介治理(Media Governance)试图协调信息传播中的各类机制,包括国家与超国家、区域与全球、集中与分散、正式与非正式等传播机制/体系界内与外部系统②D.Freedman,The Politics of Media Policy,Cambridge:Politic Press,2008,pp.14-17.,旨在实现各国相互依存、合作共赢的传播共同体。
(一)媒介健康治理的动因与可能
媒介治理研究始于横跨北美的传播理论以及欧洲的传播政策改良的号召,媒介治理因西方社会传播权利运动而兴起,以国家间认同为基础,有望实现传播媒介、公民社会、民族国家、国际社会的相互依存与合作共治。克莱·舍基(C.Shirky)将如今的媒介及媒介系统称为社会的连接组织(Connective Tissue)③[美]克莱·舍基:《认知盈余:自由时间的力量》,胡泳、哈丽丝译,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8 年,第9 页。。通过媒介治理,媒介管理方以及公共政策制定者能够在信息生产主客体、传播渠道与反馈、传播结构、权力关系、身份认同、公众舆情与危机管理、跨文化治理等不同“界面”以泛传播(pancommunication)形态实现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等模式的信息杂糅与传播平权化。信息传播的格局呈现多元化且多重主体将协同参与信息传播治理过程。媒介治理的参与元素包括:国家政府、私营部门/传媒集团、民间团体、国际组织、跨国机构、非政府组织(NGO)等。媒介治理通过精英群体和边缘集群之间的合作和权利共享,推动不同群体、社区、集团、国家、区域展开对话的进程,并且这些要素之间的相互连结④J.M.Dutta,Communicating Social Change:Structure,Culture,and Agency,New York:Routledge,2011,pp.50-52.,围绕一定的媒介议题(如健康议题)形成持久、稳定、动态、可建构的共同体,它们各自的边界以及内部结构都相对协调与稳定,为社会良性信息和多赢信息的建构提供了新的传播学框架①A.Hintz,Civil Society Media at the WSIS:A New Actor in Global Communication Governance?,in N.Cammarerts,N.Carpentier,Reclaiming the Media:Communication Rights and Democratic Media Roles(eds.),Chicago:Intellect,2006,pp.243-264.,此种多模态共赢的状态就是媒介“善治”所追求的多元共治帕累托最优(Pareto Optimum)。
如今的公共健康问题越来越体现出鲜明的跨国性特征。从新冠肺炎的全球蔓延管窥全球公共健康问题时,就会发现近年全球治理领域的一个重要变化,即全球治理正在从过去民众所认为的全球公共卫生治理向强调以公民权利为本位的全球健康治理转变。全球民众的健康问题直接或间接与跨国经济、贸易、社会稳定、技术完善等方面相联系,这使得公共健康领域的问题同时牵涉国际、国内的政策交织②D.Yach,D.Bettcher,The Globalization of Public Health:Threats and Opportunities,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Vol.88,No.5,1998,pp.735-738.。健康治理作为跨越国界的议题,其不仅代表着人的理想生理状态,亦是考验国家重要治理能力的体现之一。对于媒介健康治理而言,一般有这样3个层次:传播媒介对于公众个体健康的自我完善与健康促进;传播媒介对于国家权力(政府)支持健康政策与健康行动、健康权维护的协同共治;传播媒介对于超国家机构或跨地域组织的跨文化健康治理。
(二)媒介健康治理的困境
媒介健康治理在全球化语境下的建构并非一帆风顺。国际社会对健康问题在媒介治理框架中的定位问题至今在学界都未达成普遍共识。首先,在不同的治理框架中,健康治理在媒介范畴所处的地位不同。对于中国而言,治理的归宿是在于建构一系列社会符号、规则制度、关系结构,实现以健康中国为利益共同体的跨文化治理愿景。但由于健康治理本身所需的组织机构之间合作壁垒依旧存在,加之国内对于健康传播概念的“宣传”导向造成相关传播与媒介的论述趋于扁平化、碎片化、离散化,使得整个媒介框架网络松散而复杂,造成各相关组织面临“集体行动的困境”,由此产生了较大的媒介健康规制与执行效果偏差。针对媒介健康治理的误解则在中国公共卫生学者中较为普遍。该群体基本将其简单定义为医疗卫生领域的媒体宣传。2016年10月出台的《“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着重强调了“加强健康教育”“普及健康生活”等目标,对于新形势下国内医疗资源分布不均、老龄化严重、健康素养偏低、医患关系紧张的现实状况具有重要意义,但全文并未提到“健康传播”或“健康治理”,存有些许遗憾。笔者认为,面对诸如新冠肺炎这样关乎生命与身体、精神与文明,讲求传播、认同与对话的复杂问题,如何协调传播学、公共卫生、医学等领域的共同努力是当下学界亟需解决的课题。
其次,大众媒介及传播效果研究依然处于主流研究地位。由于当下的媒介资本和传播话语权仍集中在少数西方国家手中,媒介健康治理的研究视角依旧是“西方—东方”二元割裂的西方中心主义范式。不少学者仍然坚持强大的公共媒体总是与积极的社会参与和教育目的相联系③N.Couldry,Media,Society,World:Social Theory and Digital Media Practice,Cambridge:Polity Press Ltd.,2012,pp.93-94.。中国学者通常是将医媒关系作为切入点探讨当下的医患关系或“医闹”事件。但是,医患关系研究通常而言属于人际传播范畴,其研究方法一般都是通过数据建模对某个媒体样本进行分析,讨论该媒体平台如何呈现与健康相关的议题,区别在于媒体选择与理论来源不同,总体缺乏学术想象力。上述问题在海外健康传播中亦普遍存在,他们主要将西方理论或模型直接运用于中国语境开展样本研究,形成了涉及中国问题时的固定媒体框架,特别是突出中国紧张的医患关系和医生的职业认同,分析其“中国特色”的缘由,进而将中国医患形象和健康形象表征通过“问题疫苗事件”“郴州大头娃娃事件”等引起社会强烈反响的议题定义为自私自利、机会主义、缺乏信任等特征的媒介刻板印象。
再次,健康信息“新穷人”的出现。“新穷人”(New Poor)作为鲍曼笔下“流动现代性”理论的概念之一,特指社会上有缺陷的或者失败的消费者①[英]齐格蒙特·鲍曼:《全球化:人类的后果》,革和、郭国良、徐建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年,第93 页。。当下的健康信息“新穷人”并不是无法连接互联网获取健康信息或健康咨询服务,而是在数字媒介海量信息资源中陷入劣质健康信息的包围造成信息采纳、信息吸收、信息利用②A.V.Dijk,The deepening Divide:Inequality in the Information Society,London:Sage Publications,2005,pp.147-168.的差距与社群分化等健康信息获取不平等的现象,而且这样的健康风险极难规避且并不能完全依靠个人解决。由于当下媒介产业结构逐步转向平台媒体(platisher),在“流量经济”的商业模式下,资本逻辑与需求逻辑的冲突在用户的消费逻辑这个缓冲地带得以调和,并旨在追求利益最大化和资本增值。作为受众/用户则被迫置于冗余、碎片化、无效的信息,甚至真假难辨的谣言与虚假宣传之中。这恰好印证了阿玛蒂亚·森所认为的:“贫困的根源问题并不是收入,而是一类群体无法获取某些最低限度需求的能力”③[印]阿玛蒂亚·森:《贫困与饥荒》,王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 年,第202 页。。基于新媒体权利的媒介治理力图通过互动结构的耦合机制从全球健康治理的公共话语空间中挖掘健康行动与健康促进的共同体叙事。但上述的健康信息“新穷人”加之“治理”一词的多元性限制了自身的应用,而拘泥于空洞的宏观探讨④E.Krahmann,National,Regional and Global Governance:One Phenomenon or Many,Global Governance,Vol.22,No.9,2003,pp.323-346.,无法突破民族国家政治结构下的信息消费“失序”与国际竞合,阻碍了“相对无权者”的重新赋权,是健康治理理论存在争议的原因。
三、权利依托:媒介健康权与积极健康关系的塑造
上述媒介健康治理困境是治理要素难以协调、传播方式单一、危机信息隐匿与积聚的症结之所在。在诸如新冠肺炎疫情等全球流行疾病的应对问题上,少数西方发达国家的狭隘利益观、短视功利性、工具理性逻辑三者构成的“治理陷阱”成为世界卫生组织(WHO)等国际组织在构建全球健康治理公私伙伴关系过程中亟需依靠自主行动的长期掣肘因素。基于媒介治理所关注的传播系统平衡、多元治理转型、多模态共赢媒介图景,媒介健康治理的过程中也应关注某些聚合元素的生成以推动积极的健康政策的推行与传播。媒介健康权作为一种权责机制保障多元行为体共同参与全球健康治理的进程,对于降低全球公共卫生领域本身的脆弱性和复杂性具有积极作用。
考古学家认为,女娲和伏羲的诞生地,或许就在汉水畔安康。佐证是安康市下辖的一区二县——汉滨区有伏羲山、平利县有女娲山、旬阳县城地貌酷似天然八卦图,这地名、地貌自古有之,非今人臆造。
媒介健康权作为一项人权的健康权的延伸并不是国家政策立法或协议制定那么简单。它并不是人们获得健康信息并保证每一个体都拥有“完美健康”(Perfect Health)的权利,而是获得健康、维持正向度健康状态的一个先决条件⑤A.Hendirks,The Right to Health in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Jurisprudence,European Journal of Health Law,Vol.5,No.4,1998,pp.390-391.,也是对享有基本卫生和保健服务的提供与指引,主要包含:对获悉主要流行病的免疫和防控的媒介接近权;健康说服、日常饮食供应及营养等健康知识和健康话语的建构;对诸如HIV/AIDS等严重疾病患病者的人权与隐私保障⑥R.Jǜrgens,J.Cohen,Human Rights and HIV/AIDS:How More than Ever,New York:Open Society Institute’s Law and Health Initiative,2007,pp.2-4.;药物滥用的信息干预指导、临终关怀的叙事治疗(Narrative Therapy)等特殊群体的精神慰藉⑦J.Yamasaki,Though Much is Taken,Much Abides:The Storied World of Aging in a Fictionalized Retirement Home,Health Communication,Vol.24,No.7,2009,pp.588-596.;对处于边缘化群体、贫困群体获取健康资源的途径拓宽等⑧R.Jamil,J.M.Dutta,A Culture-centered Exploration of Health:Construction from Rural Bangladesh,Health Communication,Vol.27,Issue.4,2012,pp.369-379.。
从全球健康治理的维度探讨健康权以及由此拓展而来的媒介健康权来看,一方面,媒介健康权所针对的是每个个体所拥有的普遍权利。《世界卫生组织宪章》(1946)、《阿拉木图宣言》(1978)、《渥太华宣言》(1986)、《赫尔辛基宣言》(2013)相继阐明应以权利为本位“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health in all policies)的主张①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健康事业的发展与人权进步》白皮书,2017 年。,使各环节决策者与执行者承担对民众健康造成影响的责任,将其纳为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重要战略构成,使健康权问题纳入各国各层级的健康治理议程之中。值得一提的是,2020年6月1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该法案将近年国内民众所关注的“医闹”、戴口罩与公筷入法、垃圾分类、用水安全、婴幼儿食品配方安全等健康民生问题纳入法制的保障范畴,为较被动与脆弱的公民健康权提供了较为全面的立法保障。随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6月7日又发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白皮书,其中明确指出:在抗击疫情的过程中,始终坚持将人的生命高于一切、平衡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民生,提出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号召。白皮书的内容将维护与保障人民群众的健康权提升到了新的高度,并指出“以非常之举应对非常之事,全力保障人民生命权、健康权”②来源于中国经济网:http://www.ce.cn/xwzx/gnsz/gdxw/202006/07/t20200607_35062162.shtml.。白皮书兼顾国内外疫情形势的发展,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纽带,呼吁全球各国坚持科学理性而非政治分歧,在新冠疫情肆虐的阴霾下,彰显维护全球公共卫生健康治理、同心打造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信心与决心。
另一方面,全球健康治理中的媒介健康权强调促进不同背景与价值观的整合,并以媒介“善治”为核心将有效健康信息作为主体间共同利益的价值载体,将实现信息自律和良性重构的话语场域作为最终目标。媒介健康权从媒介框架上旨在建立一种自律的信息观,对于公民而言则是媒介素养与健康诉求的培养与形成,避免管理部门与人群的资源争夺与博弈行为,以期促使国家战略将健康纳入政策领域的积极举措。
媒介健康权作为健康权的延伸不同于以往的法定权利形式,其中蕴含了传播规则治理与传播关系治理的双重媒介话语框架,加之全球治理范式大大拓宽了其概念外延,涉及到了诸如知情权、参与权、受教育权等多个法定实质性权利。这就需要重新界定个体与国家在媒介健康治理中的权利与义务,保证人人享有获取积极的健康与健康信息的条件和能力,其实现方式应从消极权利与积极权利两个维度来审视。从消极权利而言,政府不应限制公民获取健康信息与健康服务的公平机会,不歧视或忽视脆弱人群的信息诉求并给予及时反馈,消解“数字鸿沟”,不妨碍并适当引导民众参与健康促进运动的各类信息资源获取,对媒介健康信息的污染、退化、自我净化保持理性和自觉性;从积极权利来看则体现在以国家为主体的机构在健康信息与舆论引导的过程中应发挥多元传播方式,在构筑的健康话语体系中提供质优价廉的健康服务与体系保障,鼓励在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对媒介健康权的优先考量。
四、治理展望:基于健康中国的媒介跨文化治理路径
健康中国战略所秉持的“健康共同体”理念作为国内民众和他国民众所共通的价值理念具有了实现跨文化传播的内在基础,更是其话语背后中国形象认同的观念前提。由于媒介健康权作为一种跨国的健康权利载体,其规制机理中带有天然的跨文化因子。因此,对于围绕健康治理的跨文化路径可从全球传播视角出发,以期挖掘文化认同在提升跨文化健康治理过程中的“行动元”。
(一)把关路径
“把关”一词在舆论研究中早已有之,旨在将大众传播中的各类信息按各类部门的职能或需求进行过滤与筛选,最终形成对新闻话语的把控。笔者在此提出的把关路径并不是将维护或争夺健康传播话语权作为最终目标,而是在健康危机等特殊情境下如何推进规则治理与关系治理的健康实践。新冠肺炎疫情的突然暴发导致象征“平权化”的社交媒体成为了疫情话题讨论的重要平台,但高密度、多篇幅、离散化的信息传播特质使得这样的健康传播话语网络显得极为脆弱。不实信息的大量生产转发,特别是在新冠疫情暴发的2020年1月下旬呈现指数型迅猛增长,从而造成非理性行为等焦虑情绪的上涨与社会动荡危机加剧。可见,媒介在疫情中起到解读疫情信息以及辟谣虚假消息的同时,也塑造了新的拟态风险社会。
由于跨文化传播研究范式本身就是极具弹性的理论框架或一种理论视域,笔者将健康中国背景下的把关路径界定为主要针对中国内群体的健康信息跨文化传播情境,而非基于现代民族国家关系或东西方文化差异的范畴。在社会多元构造之下的媒介情境中,传媒与社会大众之间的传受关系与互动关系发生了较大变化,不同的官方话语与民间话语逐渐从冲突走向协商,并在此基础之上再造“想象的共同体”。但单从受众/用户层面来看,社会互动关系的建构不再或极少依赖于“共同经验”。也就是说,既有的各类社会群体被置换成个性化、垂直化的“个体经验”,起初所具有的媒介耦合性特征在内群体的跨文化传播中变为媒介自主性。因此,在“把关”过程中,公共健康话语网络中建构类似于“意见领袖”的“关键影响者”(Key Influencer)是其核心内容。在重大疫情或突发医疗卫生事件发生后,关键影响者是维护积极健康关系、提升健康话语传播效度、构筑媒介健康情境、缓解民众焦虑恐慌的重要平台。
媒介健康“把关”在这个动态过程中持续以关键影响者作为话语节点对健康信息流进行 “把关”与话语链“整合”。社会空间中人类交往的本质取决于信息的流动而非物理环境,健康信息的发布机构(如WHO)与政府相关部门(如CDC)等作为健康信息的集中发布者与话语中心置身在海量信息的社交媒体网络中,关键影响者所建构的健康媒介情境如何作用于社会交往与意见竞争对于不同语境下大众行为的变化具有关键作用。在媒介健康权以话语权再分配、媒介多元协商、媒介技术民主的多维机制下,关键影响者通常能在治理过程中化解舆论僵局并减少话语间的对抗和疏离。例如,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中,以政府新闻发布会为载体的直播节目常常遭遇公众的质疑与误解,但钟南山、李兰娟院士等公共卫生领域专家在央视新闻频道播出的《新闻直播间》栏目,尤其是在微博、微信以及抖音平台中充当起了内群体中关键影响者的角色。究其原因,电视直播所固有的仪式性传播和事件性直播特质成为维系传统媒介时代形塑主流价值观“以点到面”的大众传播形态的功能属性。在此影响下,公众在基于重新消费和反权威的“微观政治”语境中竭力解构或重构官方话语的同时,也加剧了网络媒介中谎言、谣言、半真实信息的传播。以互动为媒介前提的社交媒体使得健康信息传播浮游于公众日常生活之上,并通过信息的快速更迭创造多重信息空间。关键影响者在健康媒介“把关”中充当了健康日常经验的构建者,以及健康传播在人际间的新内容生成模式与平台。从新冠肺炎疫情所引发的人际生理与情感流动重构了内群体的关系场景,关键影响者的重要网络节点效应以及网络传播/直播“以点到点”的传播方式,预示了未来微观化的健康信息网络互动场域正在逐步生成。
(二)叙事路径
健康叙事在生物医学范式之外诠释对疾病、医患关系以及媒介健康权的理解,注重疾病与健康带给人的切身感受,其最重要的作用是在患者面临疾病、恐惧或创伤时起到缓和作用,并建立事件及行动的意义。特别是在公共卫生领域的劝服功能对于病患具有一定的媒介赋权效果。跨文化健康治理首先应发挥健康叙事在媒介健康权建构中的劝服功能。通过跨文化劝服的柔性传播,将说服者的目标与用户的期望相匹配。在这样的情境下,媒介健康权的治理意涵是在说服者与受众的“互文”叙事中形构,侧重在媒介公共领域超越叙事本身所囊括的媒介话语、社会权力、政治经济结构框架。基于健康中国的跨文化治理建构不仅是包含中国健康形象“走出去”的姿态,还应注重在中国与全球化流动、与全球治理体系相互耦合的过程中对外传播理念的策略性调整及其深层包裹着的多元主体的网络化叙事修辞,实现“文化巧实力”的话语特质。
跨文化健康叙事建构中还应注重个体与国家身份的形塑。从个体而言,作为病患及其家属,严重的疾病或相关手术(如乳腺癌)使患者中断了正常生活,造成身体上的长久不适以及对于自身认知的骤变,会导致个体身份包括家庭定位、社会角色、人际关系以及社交圈的负面效应。因此,叙事建构应避免病患被污名化的情形,通过叙事获得自身身份的连续性、持久性、身份转变的表达与认知建构,以及对于该角色和身份的协商与适应。从国家层面而言,国家叙事的“健康叙事—媒介健康权—话语权—软实力”传播逻辑对于健康建构以及理解构建健康意义重要性在健康传播理论的视域拓展以及应用评估上意义深远①D.Bergman,Theoretical Approaches to Entertainment Education:A Subaltern Critique,Health Communication,Vol.20,No.3,2006,pp.221-231.。
近年来围绕讲好中国故事为主旨的国家传播战略成果丰沛,这一类文化书写依据中国传统文化为源流的话语体系,加之观照具体的现实国际议题,探究如何弥合二次传播效果的问题。健康中国作为国家健康叙事的集体话语表征与文化符码,成为反映国家健康整体动态变化的经验流,也是中国跨国叙事生成机制的独特路径。例如,在国内遏制新冠肺炎疫情蔓延期间,武汉不得不关闭离汉通道。在此期间,网络作为大众唯一与外界沟通的媒介塑造了民间话语、国家话语等多种感人故事②在2020 年1 月中下旬,新冠肺炎疫情突然暴发蔓延之下,武汉市曾发生多件感动中国与世界的真实故事,这些故事成为凝聚国内民间话语的聚合元素,也成为彰显中国形象跨文化样本。可参见:https://www.sohu.com/a/373003467_100273365.,这些跨文化健康叙事不但实现了内群体跨文化传播的国家叙事,而且对国际社会在针对中国抗击疫情的官方及社交媒体报道中对中国形象污名化表征加以柔性话语反击,并能使国家所秉持的尊重生命、尊重公民健康权的中国形象得以诠释。
(三)对话路径
健康叙事路径作为以健康权为内涵的跨文化治理与文化软实力整合传播的动态过程使得话语实践以叙事过程中“秩序的概念”③[法]米歇尔·福柯:《词与物:人文科学的考古学》,莫伟民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6 年,第52—68 页。权力关系得以形成。在全球公共话语空间中,健康叙事在对外传播的意义结构的塑造需要以传受双方互动为基础,因此,在健康叙事的基础之上应有“对话”理念的加入。可令人遗憾的是,中国的对外传播总是面临“传而不通,通而不受”的窘境,这与缺乏“对话”叙事思维密切相关。
“对话”概念起源于强调文化路径的“对话理论”(Dialogic Theory)。对话路径以身份、话语、差异和权力等文化要素的连结与沟通中呈现出对话的多元以及动态性特征,尝试将健康传播以“技术中心”为圭臬的传统研究向“文化中心”跨文化治理范式转型。在媒介健康治理实践中,媒介健康权的实现与对话理论强调的要素相呼应,针对健康对话的深度研究有助于掌握国际健康话语框架主轴及各方健康信息要素带来的多元意义,在西方话语霸权统摄的舆论环境中挖掘主体间跨文化对话的可能。
以对话方式为理论依据的学术思维重新将媒介健康治理回归“人与人”“人与媒介”“人与社会”三组积极健康关系的话语场域之中。第一,对话理论在一连串故事、人物、结果、反馈中更注重传播的仪式性而不是通过理论性数据的健康信息传递等方式,在降低用户/受众的抵抗性、提升文化编码的接受力、提供替代性的社会连接、凸显情感与说服力的效果更佳。将中国健康故事传播至认知对象国,首先应遵循以受众/用户的文化差异出发,以患者本位或公众本位为逻辑基础奠定健康对话的主体能动性。第二,认识到了传统健康传播研究方法论的局限性以及媒介健康权建构的复杂性,健康媒介治理实践的归宿并不是在生理或物理层面上对病患或公众施加影响或给予信息服务那样简单,而是在心理或精神层次上认识如何塑造健康的自我,使得健康在现代族群认同中得以跨文化传播与建构。第三,传统的健康治理将治理目标停留在了公众这一环,特别是潜在病患或高危人群,因而忽视了诸如物理环境、社会制度、媒介文化与价值观念对改变公众健康认知与行为的影响与作用。基于对话的媒介健康治理旨在关注文化要素在健康信息中的再现与赋能,使得在全球健康治理体系中不同的健康文化与健康规制彼此展开对话。在这个过程中,不同主体的媒介健康话语在“对话”语境中保持自主性但又相互接近,产生相似性的文化共识并促成媒介健康权的“文化间性”落地。
(四)平台路径
所谓健康“平台”指的是在跨文化传播语境下中国健康形象与健康叙事的构建,以及健康话语传播与生成的媒介治理场域。在“灰犀牛”“黑天鹅”事件频发、西方诸多发达国家陷入现代性反思的十字路口,外加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不断恶化的叠加影响,全球健康治理的理念更应突破陈规的藩篱、跨越理念的隔阂、超越想象的贫瘠,在尊重个体媒介健康权的前提下,以新世界主义理念建构全球主体间积极健康关系为实现目标。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曾坦言:当前人类面对的最大敌人并不是新冠病毒本身,而是恐惧、谣言传播、污名化。①来源于WHO Director-General’s Opening Remarks at the Media Briefing on COVID-19,http://www.who.int/dg/speeches/detail/who-director-general-s-opening-remarks-at-the-media-briefing-on-covid-19-28-february-2020.shtml.以话语平台作为传播场域,将各类形式与特质的健康信息统一于健康中国以及人类公共卫生健康共同体的健康话语治理体系中,有利于缓解西方某些国家通过其国际话语权造成的中国形象污名化、歪曲或干扰中国在疫情防控和维护健康权等方面所传播的正向度的国家形象,并放大中国疫情防控中的负面话语,导致国际公众难以获悉真实全面的防控态势,从而质疑中国新冠疫情防控的意图与真实性。因此,风险社会中的危机传播、媒介垄断、媒介恐慌等非理性传播形态所引发的非传统安全也是媒介健康权难以形成全球共识与行动的一个重要原因。
健康“平台”是针对在跨国空间中以健康中国为话语核心的、通过信息自律和多方对话的方式对全球健康治理产生良性、协调、互补、循环的媒介健康制度性话语权生成模式,其构成的主要方式则包括了上述的把关、叙事、对话机制,并以情境融合作为实现积极健康关系的途径,在既有的国内、国际社会互动关系所再现的语境中构建起一组新的健康情境关系,即真实的健康情境与基于媒介健康权的拟态社会情境的互动。与此同时,这一组健康治理传播情境的边界正在不断扩展,并构成跨文化语境下定义媒介健康权的全新注脚——这种定义或许正在解构原有传播语境中民族国家间的固定关系和既定规则。在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等人类整体性危机,原有的国际机制处于部分失灵的状态,各类国际组织在行动上表现迟缓,大国间因泛政治化倾向造成合作难度加大,最终导致消极意涵、成效甚微、公众误读、片面认知等限制性发展的消极后果。健康“平台”正是以健康中国为价值理念,整合各方话语在具有主体间性的媒介健康治理话语圈层之中以实现主体间在健康公共领域的跨文化协商、对话、合作与“善治”。同时,通过平台的话语圈层聚合效应收集健康话语的多方样本为健康中国的媒介健康权及健康话语生产提供新符号表征、价值观共享与新话语调适空间(见图1)。

图1 基于健康中国的媒介跨文化治理模型(作者自绘)
综上所述,媒介健康治理的出发点和归宿点都是完善国家、国际组织、媒体、公众的行为优化并以维护积极的健康关系为理想状态。与健康传播的诞生所秉持的态度一致,健康中国战略更应突出其全球视野与世界胸怀。全球健康治理所“治”的就是公众长期默认的将疾病或健康视为传统认知中简单的生物学概念,医疗技术也不应被误解为调整病患身体的工具手段,而是完善身体、心理、社会、精神健康四者的有效调节要素。以健康中国为价值核心建构人类公共卫生健康共同体,是未来一段时间内中国传媒所肩负的使命,也是在重大疫情之下讲好中国健康故事的重要一环。